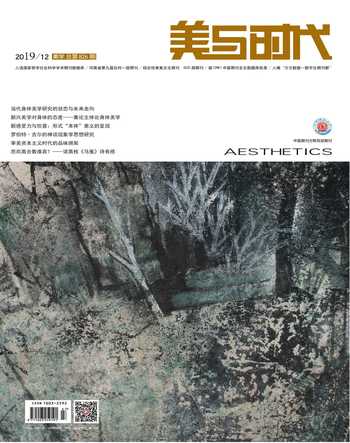浅谈反乌托邦思想
2019-09-10邵路鸣
摘 要:随着工业技术、民主政治等一系列现代化概念的出现,反乌托邦也悄然出现。乌托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理性和科学,柏拉图的《理想国》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就是因为诗人过于热情,而理想国是一个理性的世界。但反乌托邦就是从这入手,将乌托邦的理性和科学极端化,从根源上对于乌托邦提出质疑。在时代的大潮流下,反乌托邦也许已经失去了其活力,消散在那段特殊的历史中,但其警示意义却永远具有价值。
关键词:乌托邦;反乌托邦;理性;科学
提到反乌托邦,也许人们感觉不如乌托邦熟悉。要想弄清楚反乌托邦是什么,首先要明白乌托邦是什么。乌托邦自古希腊时期就已有雏形,阿里斯托芬的《鸟》、柏拉图的《理想国》都为人们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柏拉图《理想国》中提出了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而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真实的,现实世界是虚幻的,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以及人们对自己欲望的表达等。所以,柏拉图塑造的乌托邦世界是无法实现的,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构想。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推崇共产主义,反对私有制,打下了近代乌托邦文学创作的主基调。反乌托邦与之相对,描写的大多是看似稳定又平等的社会表面下,有无数暗潮涌动。人民的思想观念、本能欲望被压制,规则禁令囊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极度压抑的思想、政治禁锢之下,统一化的管理标准和生活准则使得个体发展趋向扭曲,个性化发展被压制,社会变成了标准化生产车间,个人成了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工具,按照严密的组织形式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行。
一、反乌托邦产生的背景
20世纪初,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人所诟病,金融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的缺点开始暴露出来,人们对其感到失望并逐渐开始探索新的出路。乌托邦所营造出的理想社会给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人们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共产主义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野,社会平等、物资充足,人们各司其职、按需分配,没有压迫,人们憧憬着共产主义的曙光。但“二战”爆发了,法西斯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进行种族屠杀,强权暴力,对内进行冷酷剥削、恐怖统治,对外残酷镇压侵略掠夺,欧亚非陷入人间地狱。
二、反乌托邦的特征
乌托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理性和科学。柏拉图的《理想国》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就是因为诗人过于热情,而理想国是一个理性的世界。但反乌托邦就是从这入手,将乌托邦的理性和科学极端化,从根源上对于乌托邦提出质疑。
(一)反对以理性主义为教条
乌托邦主义者的理性主义是和真理观上的绝对主义、权威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真理观容易导致压迫和强制,是一种不宽容的真理观。乌托邦主义者看不到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局限[1]76,就如《我们》中,人民没有名字,而是以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号码来识别彼此。他们认为舞蹈之所以优美是因为它的不自由,娱乐活动就是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踩着拍子一起伴着音乐在大街上踏步。人们生活在不能拉上帘子的玻璃房中。人的原始欲望被极端压制,想要发泄欲望需要领取玫瑰券,然后填上对象的号码。人们自由繁衍后代是违法的,延续几万年的自然规律就这样被加上了禁锢。而且不幸的是,身处扭曲社会环境中的人们认同这种强加的禁锢,并且在这种畸形的环境中适应了模式化的“幸福”生活。“如果他们不能理解我们带给他们的是算数般准确无误的幸福,那么我们将有责任强制他们幸福。”[2]1打着为了人类幸福的旗号,但是本就感性的东西在外部强制施加理性是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的。幸福不能强制,是当人在体会到了身心愉悦自然产生的情绪表达。绝对理性且不说能否做得到,即使能做到也是在极大程度上消磨人性的代价之上实现的。
社会之所以进步,理性是不可缺少的推动剂。理性使人们看到了君主统治的局限性,开启了认识自我的大门。人们不再盲目服从统治者、权威者的说法,不再低头苦干,而是开始肯定自己的能力、看到个人的价值。对社会进行理性批判,可以使得个人产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保持社会进步的同时维护其民主性。而将理性主义推向极致并以之为教条,就达到了另一种状态的神性真理主义,将理性放置在神的高台上,认为理性、人的能力无所不能本身就带有片面性。人具有思想是人与动物的一个区别,人可以独立思考,这就使得人在做决定或者日常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感性色彩。人的生活经历、社会状况等一系列因素都决定了每个人针对同一突发状况也许会做出带有个人色彩的反应。所以,反乌托邦主义者对于绝对理性主义是持怀疑不认可态度的。既然个人不是机器,就不应该用各种条条框框事无巨细地对人的生活、精神、思想等进行禁锢和束缚。就如《1984》和《我们》中的主人公,无论社会多么黑暗专制,即使是先进残忍如电幕、气钟罩等依然无法阻止人思想的解放和追求自由的渴望,压制越强,反抗就越早到来。理性和感性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是同等重要的,对于处理不同类型的事务,它们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仅依靠理性去解决感性才能解决的问题是不合时宜的,这种违背人类本能冲动的做法很容易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而勉强维持社会运转的上层建筑的崩溃则迟早会发生。
三、唯科学技术主义的祛魅
自文艺复兴之后,科学的地位不断提高。科学对社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航海术的改进促成了新大陆的发现,伽利略、哥白尼等发展了天文学,打破了地球中心论,用科学否定了上帝创造万物的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为颠覆教皇统治奠定了基础。自自然科学独立之日起,科学便渗透进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19世纪初期至今的200多年里,很多人预测科技乌托邦即将到来,相信科学技术将会把人类从劳动、疾病、痛苦甚至死亡中解脱出来[3]3。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思潮的源头,它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初的法国,后流行于英国[4]。这就催生了“科学万能论”的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将自然科学知识当做人类知识的典范,将科学方法看做是万能的,认为科学在人类活动中具有绝对有效性。唯科学主义对科学文化秉持至高无上的优越感,把科学视为可以解决一切問题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和方法[3]117。“书本与噪音,鲜花与触电——已经在这些婴儿的头脑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过两百次相同或类似的重复教育,将会变得根深蒂固。人类缔造的联系是大自然无力解开的。”[5]这就将科学技术上升到自然也无法干涉的高度,想要借科学技术干涉人类的自然发展,这本身的科学性就难以使人信服。
科学对于近代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双面性,“物极必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人类的现代生活便捷高效,科学家穷尽毕生的能力想要赋予机器人思维,使其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甚至创造。当机器人可以拥有思维,它是否愿意一直作为人类的朋友为人类服务?它是否不会想着为自己争取利益最大化?就能力本身而言机器比人类拥有太多先天优势,如果再加上人类独有的头脑思维,人类是否还可以控制得了机器?这一切都是未知数。科学技术拥有两种极端社会形象:一种是宙斯式形象,一如至高无上、威力无比的巨人;一种是撒旦式的形象,一如《圣经》中的魔鬼,带给人类灾难,使人性堕落[6]。这句话的准确性先暂且不论,但它十分形象地比喻了科学技术的两面性。有许多科幻作品都表达了对这个角度的思考,《生化危机》被不少人看做恐怖片的代表,但它的实质却是为了让人们看到随着科技进步,人类的欲望不断膨胀,当人性被撒旦引诱,手中所持有的科学技术就如同潘多拉的宝盒被打开一样,人间就会变成地狱。就如同“二战”时期,人们以为的乌托邦社会并没有到来,却迎来了核武器投入战争、日本在战场使用生化武器、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回顾历史,科技带来的不只是幸福和快乐,当它被不加节制地滥用之后,之前带给人们的短暂幸福瞬间烟消云散,而其产生的巨大灾难却是人类所无法承受的。
四、对集体主义的反思
“集体”一直被当做团结、合作的象征。当国家遇到灾难,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向心力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但凡好的事物都是有其可适用的范围,超过了这个范围便会产生相悖的作用力。乌托邦者的思想带有一元论的色彩,柏林认为,一元论是一种压迫性的哲学观念,因为,它相信“一”是本质的、真实的,而“多”则是非本质的、虚假的。“一”是高级价值,“多”是低级价值。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容易借高级价值之名对低级价值进行强迫和压制,借集体、民族、国家之名对个人的强制就是它的表现[1]10。“二战”时期纳粹对德国民众进行思想麻痹,宣称日耳曼民族至高无上,犹太群体则应该清除。在德国很有渊源的民族主义此时成为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作为实现民族理想而存在的工具,狂热的社会氛围带走了人们的理智。个体无论情愿与否都无法从集体中脱离开来,失去了自由和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消失在集体中,个体无法掌控事态的发展,局面也随之开始变得失去控制。
“乌托邦”的初衷是要带领人们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力,使人获得独立自主,人格被保障并得以健康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往往难以控制其走向。有统治阶层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这样才可以保证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而其中对于压迫和民主的使用体现的便是统治者的智慧。压迫着所有个体为了所谓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集体的管制,就如同《动物农场》中所写的那样“杀戮和恐怖并不是老少校第一次鼓动大家造反的那一天晚上,大家所期待的。如果她能想象出未来的图景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动物们不再挨饿、挨打的社会,大家平等,各尽所能的劳动,强者保护弱者……谁也不敢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凶恶怒吠的大狗四处游荡,而你不得不看着自己的同志在供述了可怕的罪行后被撕成碎片”[7]。人们对于所处时代感到厌恶,想要寻求一个美好自由又幸福的世界的愿望会激励人们不断奋斗,为了实现如此宏伟的目标,个人的能力就显示出了其局限性,只有个人凝聚在一起形成集体才能不断向这个美好愿望靠近。而这个过程中一旦出现偏差,就需要个人暂时放弃某些权力以实现集体利益,这种暂时放弃可能会不断延续下去,直到人们忘记了当初属于自己的基本权利。毕竟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并不美好,人们不愿意因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失去现在所谓的美好。个人融入集体之中,就不再需要个性了,只要保障集体平稳运行,个人利益就成了可以随时被放弃的东西。在奋斗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往往没有被纠正,而是愈走愈远。“你看,甚至思想。这是因为没有人是‘唯一’,而只是‘我们中的一个’。我们是如此相像……”[2]6失去了个性的人已经不能称作是完整的人了,他们不过是统治者用来维持国家运行的傀儡,如此说来科技也将停步不前,人们失去了创造性的思维,不再追求进步与发展,如此这般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绝对不是进步,而是返古。尊重个体差异,在鼓励其个性发展的同时使之以建设社会为抱负,以国家民族为向心力,才能推动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五、结语
在时代的大潮流下,反乌托邦也许已经失去了其活力,消散在那段特殊的历史中,但其警示意义却永远具有价值。乔治·奥威尔的《1984》准确地预测了苏联现实的发生,反乌托邦主义者并非是崇尚暴力、血腥及战争的狂热之徒,也不是满腹黑暗恐怖色彩的悲观主义者,他们其实与乌托邦主义者一样相信理性和科学,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理性和科学的局限性。在完善所处时代的同时,又该怎么科学合理地控制制度的发展以及如何避免极端理想化的乌托邦统治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反乌托邦思想带有些许极端,其中蕴含的深刻思考值得我们关注。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小裂缝会变成大沟壑,在及时反思历史、规避风险的同时也应步伐坚定地创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谢江平.反乌托邦思想的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扎米亚金.我们[M].王莒,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3]邬晓燕.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建构与解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4]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2.
[5]赫胥黎.美丽新世界[M].陈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25.
[6]李伯聰.略论科学技术的社会形象和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态度[J].自然辩证法研究,1988:4.
[7]奥威尔.动物农场[M].余谨,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54.
作者简介:邵路鸣,郑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思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