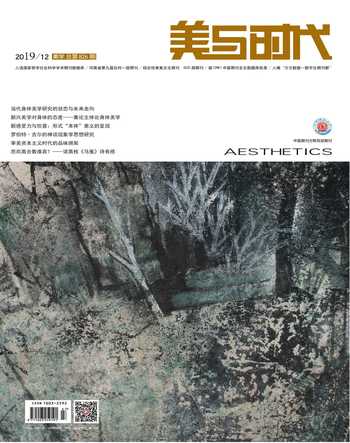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品味绑架
2019-09-10池小芳
摘 要: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品味”是其核心,并成为资本主义得以克服种种困境而达到无限发展的内驱力。当资本主义走向审美资本主义时,品味问题相应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引人深思的现象——审美品味绑架。审美品味绑架实质上是在大众媒介绝对权威的引领下审美主体去中心化现象。自由化的审美是人作为自由主体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主体品味主权的丧失表征着审美与资本共谋产生的对人性的压抑,因此冲破审美资本对人性的束缚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审美资本主义;审美品味绑架;审美主体缺失;大众传媒霸权
审美品味是西方美学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之一。西方美学家对“品味”的阐释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共通感”。近代休谟与黑格尔关于趣味标准与审美判断的探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直至当代,舒斯特曼与布爾迪厄对审美品味背后隐藏的权利的揭示,将审美品味问题推向高潮。品味是审美的基础。审美活动无关于以经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活动。人们一直将审美视为抵抗经济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异化现象的基础,认为审美具有救赎与批判作用。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壮大,21世纪以来的审美活动发生变化。美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无限动力。审美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阶段。正如法国哲学家奥利维耶·阿苏利在《审美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当资本主义迈入高级阶段时,审美活动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并非只是对立关系,而同时可以成为激发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审美是当今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精神支柱,是其克服种种困境而达到无限发展的内驱力。当资本主义走向审美资本主义时,品味问题相应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引人深思的现象——审美品味绑架。审美品味绑架实质上是在大众媒介引领下的审美主体去中心化现象。自由化的审美是人作为自由主体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主体品味主权的丧失表征着审美与资本的共谋产生的对人性的压抑,因此冲破审美资本对人性的约束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审美品味绑架
品味原属于贵族阶级展示自身的手段。贵族社会要求其成员养成优雅的品味,以凸显本阶层的优越性。审美品位在此时还只是一种“欣赏能力”,吸引他人目光的审美与判断能力还只是贵族的特权。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贵族阶级的品味转变成通过自我展示来获得他者认同的方式。在历史不断发展过程中,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大众品味则成为审美批判的新标准,不再是贵族阶级的专属,趣味成为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替代品。
21世纪,资本主义带来丰富的文化产品。当审美品位的边界趋于混沌,“不同历史时期、体裁、对象、属性、感受间的组合表现出了品味兼收并蓄,导致了传统等级制度的混杂与坍塌”[1]133。“在审美资本主义的核心里,每个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享乐的主体、自己的奴隶,并由同样的原因鼓动自我解放。”[1]155从一定意义上说,审美资本主义带来了社会生活中世俗化、自由化与普及化的审美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审美资本主义时代个人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我社会状态、能完全自由地占据商品。因为从审美品味被归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之中开始,具有审美属性的商品就可能成为维持经济秩序的手段,即审美资本主义使审美活动演变成社会的专制统治力量,强迫人们被动接受某种审美品味。资本将主体的审美活动异化,主体唯有通过资本的力量弥补异化的审美实践。审美资本主义将原来自由的审美活动变成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力量与强制权威。因此,即使审美已经演变成具有日常生活化的特点,但人们在审美活动中依然受到强制权威的约束,即我们所说的审美品味绑架。换句话说,审美品味绑架也就是审美主体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审美客体时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依从权威、主流看法,被迫接受并认同他者观点的一种现象。例如,在诸多广告中出现的关于女性形象的扭曲审美。这类广告经过无数的拍摄,而后利用修图软件进行修饰,最后进入大众视野,并产生了一个标准外貌模板:鼻如胆,瓜子脸,樱桃小嘴,大圆眼,导致整形美容医院充斥大街小巷;而电视、广告中展现的骨瘦如柴的明星大受追捧,都在编织一项社会公理:瘦即美,造成减肥产品遍地横行。不可否认,广告成功地将某种消费品与美学联系起来,使经济焕发生机与活力。但事实上,广告所宣扬的通过艳羡他者来否认自身的价值观,形成了严重的审美品味绑架问题。消费者在消费时所获得的并非是商品,而是利用商品寻求他者认同。
审美品味绑架是审美资本主义发展对人性压迫回归的社会现象。审美资本主义初期的典型特征是对大众的重视,期望通过审美消费改造大众,使人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在审美资本主义时代,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且通过消费来实现自我。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已经由以压迫为动力的社会演化成一个以享乐为根本的社会。但随着审美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其压迫、束缚人性的本质特征再一次显露。这印证了特里·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在价值领域内,资本主义不断使主体中心化,目的是为了在物的领域内使之非中心化”[2]78。在物质极度丰富的全民审美时代,社会对人的压迫性结构仍然存在,只是现在的压迫不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外在的阶级与国家的压迫,而是公众实施的自我压迫,即人们希望自身的审美品味得到他者的认同与赞赏。因而在当代生活中,大众对自己身体外观形态相当重视,不断追求外在形态符合当代审美品味与时尚标准,力图使身体“美学化”。实际上,品味是一个主体间性的概念,其“核心不仅在于通过审美感性来对主体性进行确证,而且更在于对作为个体之间纽带联系的主体间性的建构”[3]。审美品味先天地需要他者的认可。美的社会性使美感满足变成集体主观性和感受性。因此,审美品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模仿他者品味获得的。所以,资本主义利用审美品味这一特性发展经济,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资产阶级利用大众媒介确立品味规范,向大众强力灌输审美观念。其塑造的身体美学标准,高举“高品位”的旗帜,悄悄潜入所有追逐现代性审美品味的个体观念之中,成为操控其消费观念和品味取向的手段。审美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审美品味,但工业化生产模式决定了商品无法一一满足不同需求者的审美追求,于是催生了被绑架的审美观。消费者购买商品并非出自自我需求,而是将物品作为一种有品位的象征符号。大众在日益丰富的商品面前,越来越崇尚其审美价值和符号的象征意义。社会经济发展中品牌的产生正是通过这样的生成机制形成的。品牌的经营策略就是以审美品位理念打造而成的。对品牌商品的消费成为品味的代名词。在不断消费的过程中,消费最终成为围绕品牌与广告的消费,品味也终将演变成强制权威的品味。
审美品位绑架造成审美主体盲目接受或被迫接受主流时尚与品味。在这一过程中,审美主体并没有发挥自身审美的主观性,大众的自由被消费欲望驱使,以人性的奢侈与强制权威的品味取代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并非人性解放,而是主体进入一种新的异化形式。
二、审美主体缺失
事实表明,审美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享乐,人作为个体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娱乐的主体,这增进了主体的个性解放。特里·伊格尔顿指出,“我们之所以在社会里生存得自在,既不是由于责任也不是由于功利,而是我们实现了天性的一种愉悦”[2]21。主体处于审美状态中,其本质力量恢复为人性,成为实现主体解放的一种最佳途径。但当资本与审美的共谋进一步深化,当工业化不断推进,其对主体审美品味的束缚与規约显露无遗。
在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品味绑架造成审美主体的缺失。品味从根本上说是追求超功利性,这与审美资本主义相对立。当大众根据审美品味进行判断时,审美品味就进入生产环节。这种商品化审美品味的出现将大众从固有的狭隘观念中解放出来,逐渐形成了自由、平等的个体间交流的基础。但在工业化高度发达的时代,审美品味同时也必然面临着规范化与单一化的缺陷。原因在于,市场参与者在获取经济利益时,对产品进行的市场调研与预测所根据的审美品味存在单一性问题,因而结果单一,在某种意义上忽视了大众审美品味的多样性。当代社会资本获得者则采取更为便捷的手段——大众媒介。通过大众媒介传扬销售商品的理念,赋予商品一定的价值意义与审美特征以吸引消费者。这种有预谋的引导审美品味以达到销售商品目的的手段,往往将审美品味置于边缘地带。审美资本主义追求自由、追求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征在这一时期中显然朝相悖的一面发展。品味作为一种个体间精神交流的方式,是不能强加于他者的。审美品味应是自由、多样的,应是在主体的认知基础上达到个体的共鸣。然而,这种具有强制意味的标准化、单一化的品味是商业化的必然结果。自由的个体化审美品味与受限的标准化审美品位是相悖的。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品味无需情感的投入,品味主体通过消费获得的物质身份认同和确认成为消费的主要目的。资本权利具有的符号象征意义成为具有审美品味的表征形态。在这一状态下审美主体成为追求高品味的奴隶。审美品味的超功利性决定了审美主体做出审美判断或选择时应是恣意、无拘的。而标准化的审美品味的本质缺陷恰恰在于审美主体的品味自主权的丧失,这是在主体无意识状态中产生的,主体始终处于被动。人作为同时拥有自由的主体与被动的客体两种存在形态,其主体性如若始终处于压抑状态,在社会中或将成为屈从于在物质与精神上对自身没有影响的观念的奴隶。一如审美资本主义时代中对既有审美观念的被动接受。审美品味绑架是审美品味标准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的共同基础是审美主体面临去中心化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审美主体纯粹性的丧失。“人们追求的品味体验已不再是席勒式的超越性经验,而变成了以感性愉悦和符号性交往为特征的世俗经验。”[4]面对异化的审美品味,主体成为享乐的奴隶。审美主体的缺失威胁个体的存在价值及意义。
审美主体的缺失一定程度上源于大众媒介引领下的消费膨胀。消费行为在这一时期既是建构力量,也是解构力量。消费在利用自身属性不断建构自由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渐渐解构主体品味的个性化追求。随着消费的进一步推进,主体品味在消费过程中呈现出去中心化问题。大众对物品的感受过程不断缩短,审美经验的反思性与超越性在这一阶段中转变为感官的愉悦。审美品味不再是由反思判断力作用,自由选择的存在。审美资本主义时期主体对事物的审美活动必须遵守权威或资本提供的法则,在一套由话语指意的表象体系中获得既定的审美对象,从而取得愉悦。美的事物由权威话语建构出来,大众的审美品味必然受其制约。因而美感已经被外在的知识体系融合,成为被许可的事物。抽象概念代替情感成为审美活动的中介,审美品味也演变为对权威、资本等因素的迎合,缺少主体性特征。审美从本质上说是人存在的问题。审美活动对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建构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现阶段,公众为彰显自身具备权威话语体系提出的审美品味而抛弃自身审美判断能力,使主体丧失内在价值性,成为被迫从客体中产生价值、意义的主体,这种审美品味绑架是对人存在意义及价值的否定。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品味绑架是审美的变异形式,审美物质化与审美感官化是这一现象的表征,表面的审美泛化身后潜藏着人类审美价值与意义缺失的困境。审美资本主义应是更深刻地体现文明的进步、人性的解放,但是现在却成为禁锢人性的枷锁,这实属事与愿违。审美品味在推动经济活动朝着健康、繁荣的方向发展时,审美主体应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审美。审美自由是人本主义核心取向,即对人主体作用的重视。要想获得审美自由,即成为主体,意味着要充分发挥主体性,只服从于自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将自身的行为转变为最终目的,而不是成为达到他者认同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主体的自由性具有本体特征,是无法采用抽象的概念直接把握的。它需从个体的实践活动中进行体认。从审美活动上说,主体的自由化体现在每一个体都拥有审美权力,而非极端的中心化审美,即以权威话语体系表征个体。个别的主体应该成为时代的核心,并以个体自我为基础阐释客观世界。但审美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体对世界的专制统治范围不断扩大,将世界的一切与自身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形成完全自我的局面,从而体现自身的优越性。但如果全面特权化的资本主体将世界演变成“自我镜像”[2]56,事实上,主体自身的优越性也终将无法展现。因而,审美品味绑架现象显露了大众审美主权丧失的同时,也揭露了资产阶级主体自身的悲剧性。全面特权将权威人群的自我肯定不断进行自我否定,在不断地击败自我中,毁灭其所建构的世界。审美资本主义在当代所产生的品味绑架问题所揭示的正是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
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品味绑架带来了审美主体缺失,亦即主体品味主权的丧失。这一结果的形成除与时代经济发展相关外,在很大程度上与科技进步密切联系。科技促进大众传媒的发展,并形成一定的霸权力量,致使大众受制于此种话语体系。
三、大众传媒霸权
20世纪的社会发展史告诉人们,大众传媒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互影响。大众传媒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现代化的深入开展,大众传播媒介的崛起,客观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主体活动空间,它以图像、声音为传播介质,从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审美观念转变的信息渠道。大众审美观念、审美品味通过大众媒介的强化,建构出一个崭新的审美文化空间。但同时,其话语权力的日益膨胀,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催生了诸多弊端。这一弊端在审美资本主义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审美资本主义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大众传媒在其中扮演着无可取代的角色。这一阶段中,大众媒介对审美品味有绝对的话语权,而非审美主体。大众传媒的控制力量使大众处于传媒无意识的状态之中。大众传媒对大众审美意识形态的操控,使大众依赖技术手段,这一过程将技术理性带进审美活动,主体性原则遭到极大的冲击,人的审美自由与独特品味受到相当程度上的压抑。因而,审美主体在无意识之中被大众传媒引导,改变自身审美品位。
大众媒介是一种有组织的技术传播手段,快速向大众传达信息。这些大众媒介传达出的信息成为一种统一性审美的强制权威。正如波德里亚所说:“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5]。以广告宣传为例,它并未发挥教大众应如何诗意地栖息的作用,而是传播如何羡慕“他者”从而厌弃自身,通过塑造对现实的不满,促使消费者购买广告中所宣扬的生活方式,从而刺激某种商品或服务的销量。这种消费并非自由的审美消费,而是一种被霸权力量控制和操纵的变异,是审美品位绑架,是一种异化审美。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大众传媒无时无刻不向大众传播信息,但其传递的信息只是这一媒介想要传达的且带有一定强制意味的信息,并非大众真正需要的。大众媒介对审美活动的全方位渗透,导致主体审美非个性化,一定意义上造成了主体美感的钝化和惰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将直接影响大众對审美客体的分析,潜移默化地同化大众的审美品位。这一时期的审美品位受到大众媒介的规约。权威人士的肆意宣传使公众相信所贩卖的商品具有审美价值,于是,购买成为彰显自身具有审美品位的手段。这也就是大众媒介的掌控者通过制造审美舆论来改变、操纵公众的审美认同。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大众传媒实质上就是一种霸权式的操控群众,也是大众传媒让公众处于一种传媒无意识之中。消费者在消费时看不到商品的本真价值,只是在大众媒介的引导下,做出机械的选择。在大众媒介的技术效应下,商品带来的虚假享乐,将人的审美品味抹杀在浅薄的消费行为之中。当主体性为权威话语所诱导时,将处在一种非审美的异化状态中,即一种被奴役的强权控制状态,亦即席勒所强调的非人状态。这种品味绑架是对审美品位个体性的放弃,是一种审美自主权的丧失,属于“机械的审美品味”[1]145,损害审美品味的多样化。
公众在大众媒介的引领下,丧失了对自身审美品味的决定权。技术理性的极端化将作为主体的人异化为被动的客体,媒介的霸权控制使人失去超越现实的主观能动性,丧失主体性。而人一旦丧失主体性,最终将成为大众媒介操控下的傀儡。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所认为的,“机器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通过根本的奴役来征服自然、驯化自然,机器是一个可用来使他人成为奴隶的奴隶”[6]。大众传媒正是利用自身权威,以极端化的技术理性对公众实施审美品味的规训。在大众媒介霸权地位中,主体的审美品味面临着无形的精神压力,而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状态。这种审美品味绑架并不符合人的主体性特征。因此,如何应对大众媒介的霸权力量所带来的审美品味绑架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可否认,大众媒介的发展提升了公众的审美品味,但极端化的霸权话语造成了审美主体去中心化,压抑、束缚了主体对事物、现象的思考与反思能力。面对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大众媒介需掌握好“度”,实现传媒自律。这将更加合理、适当地引导大众的审美品味,给大众更多的空间,实现审美主体的自由判断与阐发。此外,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挣脱大众媒介枷锁的桎梏,打破权力结构和权威话语体系,也是反抗传媒霸权地位的有效手段。人性理念虽不是主张作为主体的人应该实现所具备的天生的能力,但它主张主体所要实现的最高价值应是源于自身天性的组成部分,它们并非是大众传媒随意选择与建构的。“每一个人的自由的自我实现是通过所有人的自由的自我实现而达成的。”[2]396因此,大众传媒的权威话语是无法取代每一个体的独立观点,大众传媒的部分审美自由无法代表公众的整体审美自由。
大众媒介的霸权地位操纵并改变大众的审美品味,形成统一性的审美品味。这是一种审美自主权的丧失,是对人性的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因此,解决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大众媒介霸权所造成的审美品味绑架问题,应力求实现审美主体对自我审美倾向的自由表达,实现审美主体自由的对审美对象作出审美评价与判断,可能会有效突破这一困境。只有在自由的审美关系中,大众才能回归本性,才能与自身优越地位保持适当的距离,以清晰的思维准确把握自身能力与现实的关系。
四、结语
在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审美趣味不断成为诱导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与此同时,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又陷入审美品味绑架的困境之中,违背了人类本身审美品味自由化的特征,导致审美过程中主体性缺失,致使大众不再依据自身的喜好进行判断与选择,而是在大众媒介的霸权统治下进行审美选择。个性化的审美在这一阶段中成为异类,似乎也表征着个体审美品味的低下。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审美品味问题是一种有悖于自由人性的品味异化问题。因此,在这一时期应给审美主体充分的尊重与自由,不抑制审美品位的多样性发展,不将主体置于大众媒介的物化力量之下。应给予作为主体的人充分的话语权,使其不为权威话语“绑架”。力求品味话语权的自由表达,冲破审美资本对人性的束缚,是审美资本主义时代不懈努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M].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修订版)[M].王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3]吴键.品味的工业化与当代审美共同体建构——以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为中心的思考[J].文艺评论,2015(9):4-8.
[4]刘玉梅,方国武.“品味”的变迁:从审美到物质[J].社会科学家,2014(4):155-158.
[5]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5.
[6]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7.
作者简介:池小芳,江苏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