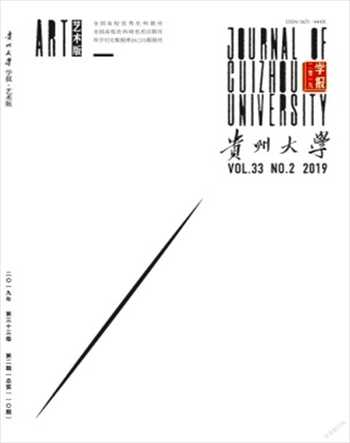《清史稿·艺术列传》的“技术”谱系研究
2019-09-10李倍雷
李倍雷
摘 要:《清史稿·艺术列传》是继《北史·艺术列传》“消失”以来延续的“香火”,其间并不意味着“艺术”概念及其内容的消失。“艺术”自《晋书·艺术列传》以降,以一条“暗线”的方式贯穿至《清史稿·艺术列传》,保持着“艺术列传”的原型“方术列传”的基本内涵即“技术”的内容,只是《清史稿·艺术列传》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理念并纳入“艺术”的范畴而立传,这种做法在逻辑上与前史“艺术列传”中的“方术”“方技”“术数”等是相通的,构成了一个“方技”谱系。因此,戴梓、丁守存、徐寿等中国近代启蒙科学家都被列入《清史稿·艺术列传》,他们的科技成果诸如“火炮”“船舶”等机械制作都被作为“艺术”看待,体现了《清史稿·艺术列传》包容科学的整体艺术观,同时“工业设计”的观念也早已在《清史稿·艺术列传》中体现。
关键词:《清史稿·艺术列传》;“技术”谱系;格致书院;蒙养斋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9)02-0011-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9.02.002
《二十六史·艺术列传》包含的内容丰富而宽广,诚如《晋书·艺术列传》小序所言:艺术之兴,由来尚矣。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详观众术,抑惟小道,弃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经。载籍既务在博闻,笔削则理宜详备,晋谓之《乘》,义在于斯。今录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纪者,以为《艺术传》,式备前史云。[1]
《晋书·艺术列传》的“小序”为中国传统“艺术”定下了基调,而后《周书·艺术列传》《隋书·艺术列传》和《北史·艺术列传》基本上沿袭的是这个路径结构和这些内容。宋代郑樵(1104-1162年)在《通志·艺文略第七·艺术类》收集了历代“艺术”内容:“射”“骑”“画录”“画图”“投壶”“奕碁”“博塞”“象经”“樗蒲”“弹碁”“打马”“双陆”“打球”“彩选”“叶子格”“杂戏格”。[2]我们看到传统“艺术”包含了技术性很强而且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技术”性的内容一直延续到清代并使“技术”与近代科学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清史稿·艺术列传》是继前史“艺术列传”的复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史“艺术列传”较为全面的传承,其中也有变动。《清史稿·艺术列传》所包含的“特殊”内容更加值得我们今天研究与探讨,譬如其中“戴梓”“丁守存”和“徐寿”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具有很大程度上的近代科学技术的内容,这是我们主要探讨的重要内容。
一、《清史稿·艺术列传》的边界与内涵
诚如前面所引《晋书·艺术列传》“小序”,《清史稿·艺术列传》大抵延续了前史的“艺术列传”,因此《清史稿·艺术列传》的范畴基本上与《晋书·艺术列傳》至《北史·艺术列传》的范畴相近。我们先看看《清史稿·艺术列传》“小序”: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大抵所收多医、卜、阴阳、术数之流,间及工巧。夫艺之所赅,博矣众矣,古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士所常肄,而百工所执,皆艺事也。近代方志,于书画、技击、工巧并入此类,实有合于古义。[3]3548
《清史稿·艺术列传》首先从《史记》开始追溯祖述,第一段阐释的是“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因为自司马迁《史记》开始立有“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而“史家因之”说的是《后汉书》立有“方术列传”,《魏书》立有“术艺列传”,《晋书》《周书》《隋书》和《北史》皆立有“艺术列传”。“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告诉了我们“艺术列传”是从“方技列传”变迁而来。也就是说“方术列传”是“艺术列传”的原型。《史记·日者列传》的所谓“日者”即指的是“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4]2435所谓“龟策”即“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4]2441二者都是“决悬疑”的。所以《后汉书·方术列传》“小序”云:“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5]实际上《后汉书·方术列传》是把“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合在一起谓之“方术列传”。那么“艺术”的内容到底是哪些呢?如《清史稿·艺术列传》“小序”所云:“大抵所收多医、卜、阴阳、术数之流,间及工巧。”这就是说“医”“卜”“阴阳”“术数”“工巧”皆为正《二十六史》列传中的“艺术”。这就可以从《清史稿·艺术列传》清楚地看到“艺术”的结构路径:“日者”“龟策”——“方术”(“方技”)——“艺术”。《清史稿·艺术列传》“小序”进一步阐释艺术所涉的内容:“夫艺之所赅,博矣众矣,古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士所常肄,而百工所执,皆艺事也。近代方志,於书画、技击、工巧并入此类,实有合于古义。”这也是《清史稿·艺术列传》对“艺术”所限定的边界。《清史稿·艺术列传》所提到的“六艺”来自于《周礼·保氏》。其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6]这一脉络路径实则也在《后汉书》里延续下来。《后汉书·伏湛传》云:“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如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予百家、艺术。”[7]李贤阐释“艺术”为:“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7]除了“礼”“乐”“书”,“射”“御”“数”乃在李贤所认为的“艺术”里。《清史稿·艺术列传》再次把“六艺”纳入了“艺术”的范畴,换句话说,《清史稿·艺术列传》把在前史里中断了的儒家教育体系“六艺”的要求或标准重新纳入“艺术列传”中,认为“六艺”是士族阶层所经常学习的。而“百工所执,皆艺事”,即《考工记》中所说的“百工”:“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8]这些都是属于《清史稿·艺术列传》的范畴。“近代方志,于书画、技击、工巧”即清代以降的“书画、技击、工巧”也是“艺术列传”的范畴。这样看来,《清史稿·艺术列传》的范畴相较于前代的“艺术列传”范畴都有所扩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技击”和“工巧”超越了前代“艺术列传”的内容。“技击”在《二十四史·艺术列传》以及其它相关的艺术文献中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通知》《文献通考》包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艺术类》均没有把“技击”纳入“艺术列传”或“艺术”的范畴。同时,《清史稿·艺术列传》这里说的“工巧”应该是具有科学性质的技术即科技。我们往下看《清史稿·艺术列传》小序“云”:
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其文学侍从之臣,每以书画供奉内廷。又设如意馆,制仿前代画院,兼及百工之事。故其时供御器物,雕、组、陶埴,靡不精美,传播环瀛,称为极盛。
沿及高宗之世,风不替焉。钦定医宗金鉴,荟萃古今学说,宗旨纯正。于阴阳术数家言,亦有协纪辨方一书,颁行沿用,从俗从宜,隐示崇实黜虚之意,斯徵微尚矣。[3]3548
这里提到了关于“西学”的事情,于是“艺术”概念的理解以及内涵做了适当的调整与变动。“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泰西艺学诸书,灌输中国,议者以工业为强国根本,于是研格致,营制造者,乘时而起。或由旧学以扩新知,或抒心得以济实用,世乃愈以艺事为重。”所以,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将“测绘地图,铸造枪炮”纳入艺术的范畴,这就是《清史稿·艺术列传》范畴扩展和超越前史“艺术列传”边界的地方。
二、《清史稿·艺术列传》有关“科技”
《清史稿·艺术列传》共分四个小部分。第一部分是“医术”“占卜”“风角”“形家”,该列传共有37人;第二部分是“书法”,该列传共有13人;第三部分基本上属于“绘画”,该列传共有47人;第四部分是“技击”“投射”“营造”“园林”“陶窑”“火器”“轮船”等,该列传共有17人。我们重点探讨“艺术列传”第四部分“火器”“轮船”等有关科技的内容。我们这里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以及他们从事的“艺术”活动的记载,作为探讨的主要内容。我们先看“戴梓”條目:
戴梓,字文开,浙江钱塘人。少有机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所造连珠铳,形如琵琶,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凡二十八发乃重贮。法与西洋机关枪合,当时未通用,器藏于家,乾隆中犹存。西洋人贡蟠肠鸟枪,梓奉命仿造,以十枪赉其使臣。又奉命造子母炮,母送子出坠而碎裂,如西洋炸炮,圣祖率诸臣亲临视之,锡名为“威远将军”,镌制者职名于炮后。亲征噶尔丹,用以破敌。
根据《清史稿·艺术列传·四》条目内容的记载来判断,戴梓(1649—1726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机械、兵器制造技术专家,他制造火炮的技术在当时也算是非常先进的。戴梓研制的“连珠铳”是可以连发铅弹的火炮,“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凡二十八发乃重贮。”这种功能上相当于今天“自动步枪”或“冲锋枪”的连射功能,可以连发28发子弹。而后戴梓又奉命仿制西洋“蟠肠鸟枪”,“蟠肠鸟枪”是一种枪管有来复线的枪,子弹射出去旋转稳定且穿透力强。戴梓还制造“子母炮”相当于西洋的“炸炮”。戴梓所制作“火炮”的技术已经具有近代科技的性质与特征,在清朝时代应该算的上高科技了。这位被康熙称为制造火炮天才的戴梓,而是被《清史稿》立入“艺术列传”中,这不但暗含着历代正史中的“艺术列传”对技术、技巧、才能重视,也昭示了《清史稿·艺术列传》对“技术”的传承,同时也证明了《清史稿·艺术列传》来自于“方术列传”或“方技列传”。
我们再来看《清史稿·艺术列传·四》“丁守存”条目:
丁守存,字心斋,山东日照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守存通天文、历算、风角、壬遁之术,善制器。时英吉利兵犯沿海数省,船炮之利,为中国所未有。守存慨然讲求制造,西学犹未通行,凡所谓力学、化学、光学、重学,皆无专书,覃思每与闇合。大学士卓秉恬荐之,命缮进图说,偕郎中文康、徐有壬赴天津,监造地雷、火机等器,试之皆验。……所著书曰丙丁秘钥,进御不传于外;所传者曰造化究原,曰新火器说。[3]3564
丁守存(1812—1883年)是清代科学技术专家,通晓传统史籍,同时兼通天文、历算、风角、火炮制造,并研习天文、地理、测量、数学等自然科学,并“监造地雷、火机等器,试之皆验”,完成《自来火铳迭法》,其内容是研究雷管等起爆装置。丁守存的科学天赋很高,“西学犹未通行,凡所谓力学、化学、光学、重学,皆无专书,覃思每与闇合”,似乎天生就通晓西方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所思考的自然科学暗合西方的力学、化学、光学、重学。就这样一位火炮制造专家,也是被纳入《清史稿·艺术列传》里。
最后我们看《清史稿·艺术列传·四》里的“徐寿”条目:
徐寿,字雪村,江苏无锡人。生于僻乡,幼孤,事母以孝闻。性质直无华。道、咸间,东南兵事起,遂弃举业,专研博物格致之学。时泰西学术流传中国者,尚未昌明,试验诸器绝尠。寿与金匮华蘅芳讨论搜求,始得十一,苦心研索,每以意求之,而得其真。尝购三稜玻璃不可得,磨水晶印章成三角形,验得光分七色。知枪弹之行抛物线,疑其仰攻俯击有异,设远近多靶以测之,其成学之艰类此。久之,于西学具窥见原委,尤精制器。咸丰十一年,从大学士曾国藩军,先后于安庆、江宁设机器局,皆预其事。
寿与蘅芳及吴嘉廉、龚芸棠试造木质轮船,推求动理,测算汽机,蘅芳之力为多;造器罝机,皆出寿手制,不假西人,数年而成。长五十馀尺,每一时能行四十余里,名之曰黄鹄。国藩激赏之,招入幕府,以奇才异能荐。既而设制造局於上海,百事草创,寿於船炮枪弹,多所发明。自制强水棉花药、汞爆药。[3]3564
徐寿(1818—1884年)专研博物格致之学,涉猎天文、历法、物理、算学、化学、机械、制造等,清末化学启蒙者和科学家,是清代造船工业的先驱。他亲手尝试科学实验,“磨水晶印章成三角形,验得光分七色”,涉足光学,又“知枪弹之行抛物线,疑其仰攻俯击有异,设远近多靶以测之,其成学之艰类此”并“试造木质轮船,推求动理,测算汽机”。徐寿还在“船炮枪弹,多所发明”,以及“自制强水棉花药、汞爆药。”徐寿不但是航舶机械制造专家,也称得上是一名火炮技术专家。《清史稿·艺术列传》同样把徐寿这样的科学技术专家列入其中。
上面三位近代科学技术领域的突出人物,皆以科技制造见长,其贡献也在“火炮”“船舶”“地雷”“火机”“光学”等科技领域,实际上是涉及到工业设计的内容。这印证了《清史稿·艺术列传》“小序”所说的“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同时,《清史稿·艺术列传》的内在逻辑与思路与前史“艺术列传”的逻辑与思路是一致的,都是把“技术”“技巧”“才能”纳入“艺术”的范畴进行立传。这也是我多次在不同的文章中提出,《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前身是《二十四史·方术列传》,“方术列传”的前身是《史记·日者列传》和《史记·龟策列传》。换句话说,《二十四史·方术列传》是《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原型,《史记·日者列传》和《史记·龟策列传》是《二十四史·方术列传》的原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史稿·艺术列传》依然坚持把科学性很强的“技术”置入“艺术列传”,实际将“科技”作为“艺术”的范畴立传。
三、“蒙养斋”与“格致书院”
《清史稿·艺术列传》“小序”和个人条目提到“蒙养斋”与“格致书院”,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清史稿·艺术列传》里,这两个机构与“艺术列传”有什么关联?我们这里简要地做一个探讨。
《清史稿·艺术列传》“小序”云:
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
中叶后,海禁大开,泰西艺学诸书,灌输中国,议者以工业为强国根本,于是研格致,营制造者,乘时而起。或由旧学以扩新知,或抒心得以济实用,世乃愈以艺事为重。
这个“小序”明确地提到“蒙养斋”,并阐述其意义和功能。很显然“蒙养斋”属于宫廷所设置的一个机构,类似《清史稿·艺术列传》还提到的仿前代画院的“如意馆”。“如意馆”是招纳画家的官方机构,显然不完全是画院的性质,也是“兼及百工之事”机构。“蒙养斋”的意义同样如此,是官方织造机构,它将所藏一技之能人招纳入馆内,聚集着有才华技术的人士,“于是研格致,营制造者,乘时而起”。“研格致”即究自然科学。“格致”来源于“格物致知”的略语。《礼记·大学》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9]朱熹对此有所阐释:“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知之,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穷极处无不到也。”[9]“格致”在清代末期有时也用来指物理、化学一类科学,但章太炎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比较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格致为日本所谓的物理学也实为荒谬。[10]从章太炎不赞同“研格致”亦物理等自然科学,相反也说明“格致”在当时确实受到日本的影响作为物理等学科来认知,也可以看作是清代学者受到外来影响后对“格致”的重新阐释。因此“研格致,营制造者”前面有一句话是,“中叶后,海禁大开,泰西艺学诸书,灌输中国,议者以工业为强国根本。”这就是海禁大开的清代“研格致”的背景,总之,“研格致”就是研究科学及原理。我们看到了《清史稿·艺术列传》将“格致”纳入“艺术”范畴探讨的理由。顺着“格致”的逻辑我们再来看与“格致”有关的“徐寿”条目。其云:
创议翻译西书,以求制造根本。于是聘西士伟力亚利、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寿与同志华蘅芳、李凤苞、王德均、赵元益孳孳研究,先后成书数百种。寿所译述者,曰《西艺知新》及《续编》,《化学鉴原》及《续编》,《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说》,《汽机发轫》,《营阵揭要》,《测地绘图》,《宝藏兴焉》。法律、医学,刊行者凡十三种,《西艺知新》,《化学鉴原》二书,尤称善本。
同治末,与傅兰雅设“格致书院”于上海,风气渐开,成就甚众,寿名益播。山东、四川仿设机器局,争延聘寿主其事,以译书事尤急,皆谢不往,而使其子建寅、华封代行。大冶煤铁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经始之际,寿皆为擘画规制。购器选匠,资其力焉。无锡产桑宜蚕,西商购茧夺民利,寿考求烘茧法,倡设烘灶,及机器缫丝法,育蚕者利骤增。[3]3564
这里提到了“格致书院”的建立。徐寿在清朝是一位研究科学的先驱,而且他还是通曉西文能够从事翻译工作的学者,常与西方传教士兼学者一起研究科学技术并翻译西学,亦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自然》杂志刊发《声学在中国》论文的人。从《清史稿·艺术列传》“徐寿”条目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翻译的“《西艺知新》及《续编》,《化学鉴原》及《续编》,《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说》,《汽机发轫》,《营阵揭要》,《测地绘图》,《宝藏兴焉》。法律、医学,刊行者凡十三种,《西艺知新》,《化学鉴原》二书,尤称善本。”不仅如此,“同治末,与傅兰雅设‘格致书院’于上海,风气渐开,成就甚众,寿名益播。”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徐寿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创建格致书院,并于清光绪二年(1876)在上海落成。“决定在书院内:一、陈列机械设备、科学仪器和工业产品等供人参观;二、举办科学知识讲座和开设有关培训班;三、建设图书馆和阅览室。”[11]同时,还创刊《格致汇编》科学杂志。所以“有意识地、比较系统地进行科学启蒙,自傅兰雅编辑《格致汇编》、中外合办格致书院开始。”[12]“格致书院”的创建直接影响到四川、山东等地,纷纷效仿设立机器局并争聘徐寿为主管。徐寿任江南机器制造局总管时,还聘请傅兰雅为期3年的翻译员。傅兰雅“口译的译著达116种,占江南制造总局译书总数的一半还多。学科门类覆盖数学、物理、化学与化工、矿冶、机械工程、医学、农学、测绘地图、军事兵工等方面。”[13]“格致书院”设有六类课程:矿务、电学、测绘、工程、汽机、制造。这些课程的基础皆是数学,也即是说在几何、代数等学科的基础上研习这些专门的课程。这种专业课程的设置是将清代启蒙教育思想“学——技——艺”付诸实践,“格致书院”开启了晚清中国较为系统地接受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14]
以上我们简要地探讨了“蒙养斋”和“格致书院”,二者所从事的事情大致相近,都与近代科技相关,甚至就是聚集有学科技术的人才从事科研、学习和科技实践的结构。蒙养斋就是“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因此“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而“格致书院”则是中西合办的机构,不仅研究科学技术与翻译西学科学书籍,还专门设置自然科学的课程培养科技人才,并将所学到的科学技术用于社会实践,各地所设的“机器局”即是专门的实践机构。
为什么要专门探讨这个问题,其意义在于《清史稿·艺术列传》是把“科技”纳入艺术的范畴来立传的。其实,也只有到了清代才有将“科学技术”作为“艺术”的范畴的机会,因为《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只有《晋书》《周书》《隋书》和《北史》为“艺术”立传,《魏书》是“术艺列传”,当然与“艺术列传”没有太大区别,此后《二十四史》中的“艺术列传”便中断了,直到《清史稿》重新为“艺术”立传,即《清史稿·艺术列传》复现在所说的《二十六史》里。而中国明清之际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清史稿·艺术列传》把“科技”纳入“艺术”范畴的逻辑方式,实则是延续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方伎列传”——“术艺列传”——“艺术列传”的逻辑路径。天文史学家席泽宗先生认为:“《后汉书·方术列传》说,占卜,也是君子之道:‘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占有神明,遂知来物者也。’各种占卜术,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它们‘时亦有以效于事也’。圣人之言,校验的事例,使人们把占卜和天文、数学、医学、机械制造等科学技术成就放在同等的地位上。”[15]而《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就是延续的《后汉书·方术列传》,这也说明《清史稿·艺术列传》为什么把技术包括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纳入“艺术”范畴中,其中的逻辑结构就是“日者列传”“龟策列传”“方术列传”“术艺列传”一脉谱系的逻辑结构。
结 语
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实则早在《清史稿·艺术列传》就把这个问题明确地融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在《清史稿·艺术列传》中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艺术与科学对于《清史稿·艺术列传》来说完全没有分离的意识,它是延续《史记·日者列传》《史记·龟策列传》——《后汉书·方术列传》——《魏书·术艺列传》——《晋书·艺术列传》——《周书·艺术列传》——《隋书·艺术列传》——《北史·艺术列传》的立传观念,将“技术”融入到“艺术”范畴并立传。《魏书·术艺列传》和《晋书·艺术列传》本就无区别,甚至《周书·艺术列传》在探讨或描述时,还使用“术艺”的概念,这就是说,《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就是把“技术”与“艺术”本身视为统一的一个整体,技术本身就属于艺术的范畴。很自然《清史稿·艺术列传》就把西学传来的“科技”也纳入“艺术”的范畴并为其立“艺术列传”,它本身就是把“科技”作为前史“艺术列传”中“技术”的内容来认知的。这个逻辑结构前面我们就讲过了,“艺术列传”是由“方术列传”或“方伎列传”演变而来。“方术列传”则又来源于“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由于“日者”“龟策”等占卜技术与观测天文、地理有关,所以形成了古代早期的天地观思想,“日者”“龟策”等这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的具有科学观察方法上的,亦即《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暗含了一条技术脉络的“谱系”,因此,《清史稿·艺术列传》不仅包含了科技而且把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业设计”也涵盖其中。
总之,中国传统的“艺术”概念及其内涵早已规范着它自身变迁的“谱系”路径,一开始就体现出了“科技”融入“艺术”范畴的完整观念和艺术思想,我们今天很多探讨的艺术与科技的问题,所谓现代工业产生的工业设计等问题,其实都在《清史稿·艺术列传》“方技”谱系里阐明清楚了。
参考文献:
[1] 房玄龄.晋书(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67.
[2] 鄭樵.通志·二十略(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5:1707-1737.
[3] 赵尔巽,等.清史稿(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 司马迁.史记(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 范晔.后汉书(下)[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1825.
[6] 周礼(上)[M].正弦,注.贾公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99.
[7] 范晔.后汉书(四册)[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4:898.
[8] 考工记[M].张道一,注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2-8.
[9] 朱熹.大学章句集注[M]//四书五经(上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5.
[10] 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学科出版社,2004:286.
[11] 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学科启蒙[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73.
[12] 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01).
[13] 武志勇.傅兰雅与《格致汇编》[N].联合时报:史苑版,2018-07-03(5).
[14] 熊月之.新群体、新网络与新话语体系的确立:以《格致书院课艺》为中心[J].学术月刊,2016(07).
[15] 席泽宗.中国科学思想史(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463.
(责任编辑:杨 飞 涂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