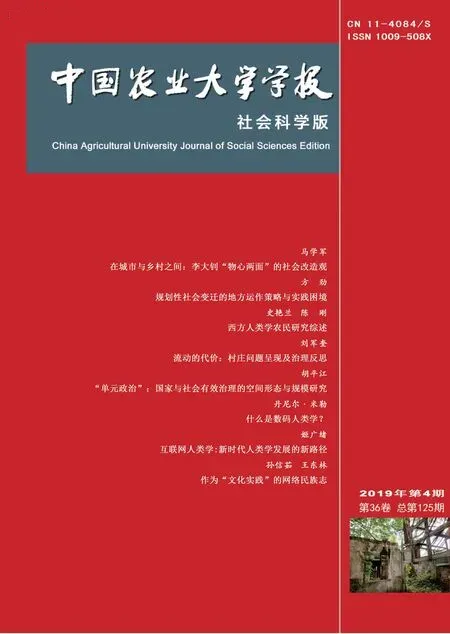“单元政治”:国家与社会有效治理的空间形态与规模研究
2019-08-21胡平江
胡平江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其中,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曾专门印发《关于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方案》。由此,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的探索成为广大地方政府推进改革的重要举措。而村民自治以“基本单元”的调整为突破口,也引发学界对“基本单元”的再思考,并成为学界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但是,目前学界对于什么是“基本单元”,如何衡量基本单元的治理成效等问题还缺乏深入研究。
一、文献梳理与已有研究
长期以来,“基本单元”问题是影响国家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目前,学界大量研究聚焦于国家这一单元本身,而对于国家治下的基层单元重视相对不够。但是,从有限的文献中能够窥探出基本单元的一般性规律与特点。
(一)“基本单元”的形态研究
早在古希腊时期,先贤们就对治理单元进行了探讨。柏拉图曾指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1]58在柏拉图看来,作为基本治理单元的城邦是不同个体基于共同需要而形成的共同生活区域,这种因共同需要、共同生活形成的城邦具有某种共同体性质。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对“单元”进行了分层分析。人们首先因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家庭,多个家庭为着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东西而联合起来形成村落,多个村落结合形成的共同体则是城邦。[2]3可见,家庭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村落则是具有社会联合属性的最基本社会单元。但是,村落这一基本单元在实践中如何形成、如何运行,亚里士多德并未进行详细分析。
人类学家摩尔根通过调查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基本单元。一种是以人身、纯人身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单元,这种组织的基本单元是“氏族”,这是古代社会所普遍流行的形式。[3]6-7另一种是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组织单元,其单元层次首先是乡区或市区。[3]7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摩尔根的研究认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4]187而血缘氏族等传统单元之所以被替代,重要原因在于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这一前提已经不复存在了。[4]187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摩尔根对治理单元的判断有其经验局限性。其所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古希腊以及西欧等深受商业以及战争影响的地区,由此带来的人口流动打乱了血缘关系的束缚,形成了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乡区”“市区”。因此,两种形态的基本单元能够进行有效区分。
(二)“基本单元”的规模研究
密尔从居民有效参与的角度考察治理单元的规模,指出“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5]55换而言之,适合居民直接参与的单元范围是有限度的,在超过“小市镇”这一范围之外,需要采取代议制等形式进行治理。而这种市镇在西方国家具有独特地位。托克维尔曾对美国的乡镇进行考察,并指出,“乡镇是自然界中只要有人集聚就能自行组织起来的唯一联合体”[6]66,“其人口一般为两三千人,其面积并未大得使全体居民无法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地步;其居民人数也足以使居民确实能从乡亲中选出良好的行政管理人员。”[6]68
美国学者达尔从治理规模与民主的关系进行考察,达尔发现,在一个国家之内,为了使参与和效能感的价值最大化,可能需要的单位大大小于通常假设的规模。而在瑞典,这一单位少于1万人。[7]60集体行动理论从组织规模与行为激励的角度指出,“集团越大,就越不可能去增进它的共同利益”[8]31,而“相对较小的集团具有更大的有效性。”[8]64在较大的集团中,一是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总收益份额有限,二是行动者所获报酬不足以抵消所付出的成本,三是组织成本与组织障碍较大。[8]40可见,从便于居民参与的视角而言,相对较小规模的单元更能够有助于实现有效治理。
国内学者也围绕“基本单元”的规模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如邓大才指出,“基本单元是最接近家庭、位于治理层级最底端且不可再分割,但是又能满足一定公共生活的组织平台、范围和空间。”[9]郝亚光、徐勇从组织单元的功能视角研究认为,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是基于“便于自治”的实际需要。[10]史亚峰、李松有等人从规模与利益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自然村组织规模较小、利益相关性较强,因此是村民自治合适的基本单元。[11]由此可见,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大量学者将自然形成的规模较小的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
总的来看,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可能呈现不同的形态。在国家产生之前,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主要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形态,如氏族、部落、村落。而在国家产生之后,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主要是国家区划的结果。然而已有研究在诠释中国事实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忽视了传统血缘单元的延续性。在中国社会,血缘关系并未被打破,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基本单元并未呈现出马克思、摩尔根等论述的清晰分界。二是忽视了国家建构的重要性,当前无论是集体行动的研究,抑或村民自治的研究,都侧重从居民参与的单一视角进行考察,从而认为较小的基本单元往往越有助于社会的自我治理。
二、“基本单元”的形成与变迁
在传统中国,不同区域社会条件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如在华南地区主要呈现“聚族而居”的存在状态,在长江流域地区呈现出“村落散居”的状态,而在华北地区则是“集村而居”。[12]而围绕“基本单元”这一问题也形成了不同的认同。如施坚雅先生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存在一个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地区城市的等级化、体系化的单元层次。[13]10而“基层市场地区的分散以及它们对各种地形的囊括倾向,促进了它们与地域性行政单位的自然结合,是农村重构努力的合适单位”。[13]151但是,这种市场单元往往具有某种重叠性,也难以寻找明确边界。
村庄也被视为基本单元。如萧公权指出,“村庄是中国乡村社区生活的基本单位”[14]12,且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地方官发现,利用自然的乡村组织所提供的功能是最方便的。”[14]42因此,“乡与村组织最终成为保甲体系的运作单位。”[14]42同时,部分学者对中国东南地区的研究发现,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宗族”本身可能就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如弗里德曼认为,“我们在中国东南地区所看到的这种宗族当然是政治与地方组织,在国家的支持下,地方宗族通常是解决宗族成员纠纷的最大单位。”[15]145科大卫也认为,“明王朝通过法律来创造里甲,而宗族则通过礼仪来继承里甲。”[16]10
由此可见,社会治理基本单元在不同地区可能呈现出不同类型。如在华南宗族地区,传统时期可能主要以宗族作为基本治理单元。而在华北地区,传统时期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则以自然聚居形成的“村庄”为核心。为了认识各区域的特殊性,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于近年对中国华南宗族型村庄、长江流域个体型村庄、华北集体型村庄、西北部落—庄园型村庄、东北移民型村庄、西南少数民族村庄、东南农工商结合村庄等七大区域进行了深度质性调查。本论文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所开展的深度中国农村调查,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对华南宗族型村庄选点之一的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山池村进行深入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析华南地区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的形成过程。
山池村是一个多姓氏宗族聚居村庄,村庄面积约2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约1 800亩。1949年村内人口约1 740人,其中谢氏宗族1 500人左右,另有王氏、杨氏、黄氏、温氏、吴氏、叶氏等7个姓氏宗族。在谢氏宗族中,分为上镇、下镇两大房支。山池村作为一个自然形成的居住聚落,与其地理环境不无关系。山池村四周山峦叠翠,村内地势平坦,呈盆状,因其形其状故名山池。由于周围山峦的阻隔,山池村与其他聚落相对隔离①参见胡平江.大族崛起:以分促合的治理——粤北山池村调查,徐勇,邓大才主编.中国农村调查(总第2卷·村庄类第1卷·华南区域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7:9。。

图1 山池村村庄位置与宗族聚落分布示意图
(一)国家不在场与“宗族单元”
在谢氏宗族迁居山池村之前,村内居住有罗氏、许氏、邝氏、张氏、李氏、王氏等姓氏宗族。谢氏落居山池村之后,王氏、黄氏、杨氏、叶氏等宗族也先后聚居于此。尽管居住于此的居民有“村”的概念,如清朝时期《谢氏族谱》记载,“彦良公葬本‘村’社山,林发葬本‘村’双坟树下”。但是,此时“村”并非一个治理单元,更不具有村长等治理主体。据族人介绍,山池村第一任“村长”产生于1949年。此时,宗族本身才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反过来看,法律又承认家长、族长为家族的主权,而予以法律上的种种权力。”[17]29
在宗族内部,存在着的治理体系。其一是族长。在山池村谢氏宗族内部,族长往往是族内文化最高、威望最高的族人担任。由于山池村分上、下两镇,一般山池村谢氏由两人担任族长,上镇下镇各一人,两位族长经常遇事商量,共同管理全族事务。族长职能包括代表宗族进行对外交往,调解族内房长、绅士调解不了的矛盾等。其二是绅士,由部分辈份较高者、富有者以及有功名者构成,是宗族内部日常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其三是房长,一般由房内辈份最高且年纪较大者担任。房长可以对族人进行教育,但在处理重大事情,特别是对族人实施惩罚时则需要请示族长。
村庄的公共事务以宗族而非村庄为单元进行组织。如在清朝后期,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山池村。为避免太平天国军烧杀掠夺,村内宗族新建大量炮台、山寨等防御设施。其中,谢氏共有太人寨、罗屋寨、高明寨、罗锅寨等四个山寨,山寨由居住在附近的族人按照“就近原则”共同使用,而其他姓氏宗族遇到太平天国军来袭时只能选择逃到外村。同时,在宗族发展过程中,谢氏宗族形成有“用祖公钱打架”的说法。即族人与外族人或官府发生冲突,需要宗族蒸尝来赔偿以对族人进行保护,避免族人陷入官司。而在村庄层面,并没有建立有共同的防卫措施或者安全保护机制。
(二)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保甲单元”
在晚清以及中华民国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被纳入国家治理的重要日程。其中,1930年,龙川县设立七个自治区署,其中山池由“约”变为“乡”,属于第六自治区。1947年,龙川县全县设3个区署、39个乡、420个保,其中,山池所在的平山乡隶属第三区署。山池村内设有3个保,其中谢氏宗族上镇为第四保、下镇为第五保、王、黄、杨、吴等其他姓氏宗族第三保。保以下的甲则与“房”相对一致。如林福公一支因人口相对较少,划为一甲。泰宇公一房因人口较多,划分为两个甲,其中长房一个甲,幼房一个甲。

表1 1949年之前山池村行政区划调整统计表① 参见胡平江.大族崛起:以分促合的治理——粤北山池村调查,徐勇,邓大才主编.中国农村调查(总第2卷·村庄类第1卷·华南区域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7:18。
在保甲制度下,治理主体主要由保长、甲长担任。其中,保长一般由族内有文化的族人以及甲长选举产生。选举保长时一个甲由两位代表参加选举,其中一个代表为甲长,一个代表为甲内相对有文化者。担任保长或副保长的最主要人群为“小学教师”。而“甲长有的有文化,有的没文化,且大部分没文化。”与宗族族长、房长等不同,保长、甲长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一部分,享受着国家给予的工资补贴。据介绍,保长与甲长工资一般为一年2石谷,主要为收取税收时的返回部分。同时,担任保长与甲长,其本人及家人可以享受免除兵役的待遇。
保长职能主要是两点,其一则为抓壮丁,其二则为收税。且这两大职能较少受到宗族影响。如在税赋收取过程中,往往宗族归宗族,家庭归家庭。宗族公田的税赋由公田蒸尝支出,而个人家庭税赋则由族人自己承担,宗族既不会协助政府收税,也不会替族人交税,更不会组织族人拒绝交税。同样,对于抓壮丁,族长也不能干涉。据族人介绍,谢氏宗族内一位房长谢观大的儿子被抓壮丁,该房长找到族长谢耿然请求帮忙,但谢耿然表示无能为力。同时,对于保长的任务来源,族人将之概括为“县长追乡长,乡长追保长,保长追甲长,甲长通知各户”,即保长听从乡长安排。
(三)国家形态下的“行政村单元”
1949年之后,山池村正式形成“村政府”这一建制。1954年山池村成立初级合作社,山池村有两大社,分别为烽火社和红光社,初级社打破传统宗族、房支的地域区分,完全按照地域条件进行划分。1958年,岩镇成立岩镇人民公社。山池村成为岩镇人民公社下辖的生产大队之一。而山池大队又划分为四个生产小队,即一队、二队、三队、四队,生产小队按照地域相近原则以“划条条”形式划分。由此可见,国家权力的强势进入,打破了传统的宗族单元,并借助“行政区划单元”替代宗族房支认同单位。
山池村下辖41个村民小组,尽管宗族单元已经为行政单位所取代,但是大多数村民小组依然以独立的房支为单位。其中重要原因在于族人认为房份之间有隔阂,不同房支划分在一个村民小组往往难以管理。以谢氏宗族泰宇公一房为例,人民公社时期划分为3个生产小队,其中幼房部分家户与九牧公部分后裔合为一个生产小队,幼房另外部分家户与皇焕公部分后裔合为一个生产小队,长房单独一个生产小队。但分田到户后,泰宇公长房、幼房各自独立组成两个村民小组,不再与九牧公、皇焕公后裔合在一个村民小组。可见,尽管村一级的单元是以国家权力为主导进行划分的,但宗族仍然对治理单元的划分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村庄治理主体则由族长、房长等过渡为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等主体。从山池村历任党支部书记以及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构成来看,谢氏族人始终占据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两大职位。同时,为照顾小姓宗族,在选举过程中村民委员会中的“文书”一职由谢氏之外的王氏族人担任。特别是,在村民委员会选举过程中,小姓宗族反而成为“关键少数”。“村内小姓则占据四分之一的选票。但谢氏上下镇两大房支互相竞争,互相不认可对方推选的候选人,因此双方都无法过半,需要靠小姓来支持才能当选。”也正因如此,王氏宗族族人王桥妹曾连续多届当选“文书”一职,且每次当选都是获得票数最高者。
在以“村”为基本单元的治理过程中,大量宗族之间的公共事务得到有效治理。据族内老人介绍,村内没有大江大河,1949年前洪水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村内溪流曲曲折折,下大雨时因树枝垃圾堵塞溪流而引发溪水漫出。但因为流经不同的宗族,难以统一改直。而1949年后,“共产党领导,直接组织村民拉线扯直,没有人敢阻挠。”同时,随着公共事务组织方式的变革,村民认同也从宗族权威转为村庄权威。如王氏宗族一位村民介绍,“新主任尽管是谢氏一族,但当选不到三十天给村内两条村道安装有路灯,不到两年修了两条村道。如果没有能力,我的儿子我都不选”。
三、“基本单元”的构成与有效性
从山池村的个案分析来看,“基本单元”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时期分别形成有宗族、保、行政村等基本单元。其中,在现代国家建构完成之前,宗族这一“基本单元”更多的是一种内生性的认同单元。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保、行政村等“基本单元”与国家权力的作用密不可分。可见,不同历史条件下,“基本单元”呈现不同的形态。但是,不同形态的治理单元是否有效,是否能够满足实现有效治理的需要,则必须有一定的衡量与评估标准。
所谓治理有效,可以理解为有效的治理,即治理能够达到设定的基本目标或者能够解决所面临的治理问题。治理有效是一个客观评价概念而非价值评价概念,并不涉及民主、自由等价值问题。俞可平教授曾指出,“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18]对此,本文从特定治理单元中治理主体是否独立、治理规则是否具有公共性以及是否能够有效提供社会秩序三个方面对宗族、保、行政村单元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一)治理主体的独立性
在国家权力并未完全渗透进入乡村社会的情况下,宗族有其独立的治理主体,族长、绅士、房长构成了纵向的权力网络,能够对宗族、房支成员有效施加影响。这些治理主体的重要特征在于其内生性,其权力来自于宗族成员的认可而非外界授予。如宗族中的为官者、富裕者并不一定为族长。据介绍,清朝时期村内族人下围修建者谢仁宗非常富有,且通过捐钱获得“地保”功名,但在族内并没有实质权力,在族内不管事,也需要听族长的话。与此同时,村庄地域内并不存在独立的公共治理主体,也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基本单元”。
在保甲制度下,国家设置有独立的保长、甲长,并通过提供工资等进行保障。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受制于宗族的社会关系影响,保长、甲长只能在国家任务中获得独立性。而对于宗族本身事务的治理,由于族人认同的是宗族权威而非国家建构的保长权威,因此保长所能发挥作用极为有限。如保长谢汉驹曾参与谢观先、谢观贱两兄弟与谢雄广房屋纠纷事件的调解过程,但事件的调解主要还是谢维汉、谢国强等族长和房长主导,保长谢汉驹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说过一句话,不过就是当了一个桶而已”。
“在二月初的一个晚上,有观先、观贱二兄弟与雄广争屋,引起吵闹打架。第二天观先兄弟办席投人,由国强等人调停。国强在雄广面前说,你不要去回席,就拿五斗谷作为回席费。在观先观贱面前说,由雄广出五斗谷,作为帮给汤药费。当时我(谢汉驹)没有说过一句话,不过就是当了一个桶而已”①参见胡平江.大族崛起:以分促合的治理——粤北山池村调查,徐勇,邓大才主编.中国农村调查(总第2卷·村庄类第1卷·华南区域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7:178。。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在基层设立的党支部以及村民委员会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组织。与传统宗族社会中族长、房长等权威不同,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等组织的权威更多的源于国家的建构与赋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就规定,村民委员会具有“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职能。而在宗族之中,族长已经不再存在。尽管各房房支拥有房长,但房长并不拥有实际权力,而更多的作为仪式象征,如在举办红白喜事时房长在主位就坐。
(二)治理规则的公共性
任何社会治理都需要依据一定的公共规则。但是,不同社会治理形态下,其所依据的规则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在以宗族作为基本单元的宗族治理过程中,所依据的规则尽管受到国家规范的引导、控制,但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宗族本身的观念、默契与共识。“宗族在村庄中操纵着政治机制,决定着村庄的村务管理、公共活动。”[19]66-67如民国时期王氏宗族因卖窑草给谢氏族人烧石灰而获得较大财富。但为了防止王氏宗族的壮大,谢氏宗族制定族规,禁止族人收购王氏宗族的窑草。可见,宗族治理依据规则的独立性、公共性受到极大约束。
在保甲制度下,尽管设置有相当独立的治理主体,但是对于保甲内公共事务的治理规则,国家则明显供给不足。因此,社会中农民行为关系的调节更多的依赖于宗族自身的规范或惯例。“现代化政权的新型政治学说并未成功地找到一种使乡村领袖和国家政权合法化的传统文化网络的可行替代物。”[19]209在现实生活中,族人认为寻求保长以及官府介入并不会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会借机来敲诈宗族。如谢氏宗族内曾发生一起命案,在县衙介入下打官司长达三年。但三年间政府并未捉拿凶手,而是借机到该房来索取钱财,自此族人对打官司敬而远之。
1949年之后,以“人民公社”“行政村”为基本单元的农村基层治理所依据的治理规则具有外生性的特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遵守并组织实施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这种外生性的规则更加符合一般性治理、社会公共治理的需要,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因此,近年来尽管山池村谢氏宗族与邻村王氏宗族因水库产权归属、山林产权归属而发生纠纷,但村民委员会在调解过程中主要作为法人代表通过法律诉讼形式调解,而非传统组织械斗形式处理。
(三)秩序供给的有效性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20]67宗族作为一个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边界往往是宗族活动的边界。因此,宗族治理主体只能对宗族本身进行有效治理,而不能超越本宗族对其他宗族进行治理。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避免鸡鸭偷食稻谷,山池村谢氏宗族一般由族长指定族人进行“巡视”。每逢稻结谷之时族人看到有鸡鸭偷吃稻谷可以请巡视者去打,同时,如果禾苗被人偷割也可以请巡视者负责追查。但是,即使其他宗族的田地临近本宗族的田地,巡视者也不能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在以宗族为基本单元进行治理过程中,宗族之间的公共秩序难以得到有效供给。“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4]110
在保甲制度下,保、甲边界与宗族本身的治理单元重叠,保长、甲长等治理权力同样并未突破宗族的边界。因此,对于村内宗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保长也无法有效调解。如1931年时,一次谢氏族人因打猎与王姓族人发生纠纷并引发械斗,致使王姓族人伤2人。在此过程中,乡长、保长并未出面协调。而在大型宗族冲突过程中,政府本身也可能涉及其中。如山池村谢氏宗族有一个祖坟在上坪乡。1942年,该乡乡长在该墓地旁建造房屋,引发两大宗族大规模冲突。当时洋田镇谢氏宗族后裔谢鸿恩得知此事后带领县保安总队驻上坪的中队前来协助谢氏进行械斗。
1949年之后,国家建构的生产大队、村民委员会成为村庄的核心治理者。与传统的宗族单元、保甲单元不同,村庄单元摆脱了宗族关系的束缚,成为独立于宗族之上的治理单元其权力作用范围不仅能够深入到宗族内部,而且能够在村庄范围内有效处理不同宗族之间的公共事务。在日常矛盾调解过程中,族人也并不找房长调解,而更多选择寻求村干部甚至派出所调解。“现在基本没有房长,后生都不尊敬长辈,更不承认有房长。现在有事都是找干部、找政府,甚至找法庭。”

表2 不同时期基本单元的治理效用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尽管宗族、保、行政村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但是在治理主体独立性、治理边界范围以及治理规则公共性上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对于传统宗族单元而言,其治理主体、治理规则具有强烈的内生性,容易为治理对象所认同。但是,以“宗族”为基本单元开展治理也有其不足之处,即治理范围局限于宗族本身,对宗族之间的公共事务缺乏有效治理。同时,治理规则为宗族本身所控制导致公共性不足。相反,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开展村民自治尽管存在范围过大,内生性不足等问题,但是其所依赖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更加符合现代治理的需要。
四、结论与讨论

图2 基本单元的形成机理示意图
“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是国家和私营部门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实施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21]6治理并非对国家的彻底的否定,而是国家与社会相互合作的结果。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前,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国家权力在人们实际生活中是松弛的、挂名的和无为的。[20]59此时,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往往依托于社会自发形成的共同体单元。但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社会的治理不可能抛弃国家而完全独立运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与社会存在着相互竞争、相互争夺权力的过程,并引起治理单元的变迁。“在存在冲突的环境中,国家和血缘群体、种族群体及其他群体相互争执,相互争夺,各自都力求在其领导人认定的势力范围内建立普遍的社会控制。”[22]42
在西方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单元存在一个自我解体的过程。由于贸易、战争等因素导致的人口流动性,“旧的制裁、旧的奖赏、旧的调解方式,开始变得没有意义。”[22]89因此,国家替代传统的氏族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并按照地区来组织社会,以此代替氏族的血缘组织原则。[4]187但是,在中国社会,传统氏族社会解体后血缘宗族却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成分和强大的社会力量的结合体而成为社会生活中农民的主要组织形式。[23]61也就是说,国家治理基本单元并不是在血缘单元解体基础上设立的,因此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既受到国家建构的影响,也受到血缘宗族的约束。
在当前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的探索过程中,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出现了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实践形式。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传统血缘宗族单元与自然村、村民小组单元基本一致,以此为基础开展村民自治,具有“地域相近、群众自愿、利益相关、文化相连、规模适度”等优势。[24]但是,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基本单元”,不仅应该考虑到其历史延续与群众参与问题,还应该考虑到现代国家治理的需要。在宗族共同体单元中过度挖掘传统治理要素,可能使村民自治面临治理主体难以有效独立、治理规则公共性不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