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税则谈判”看何桂清与中央政策的博弈
2019-08-01邢志宇
邢志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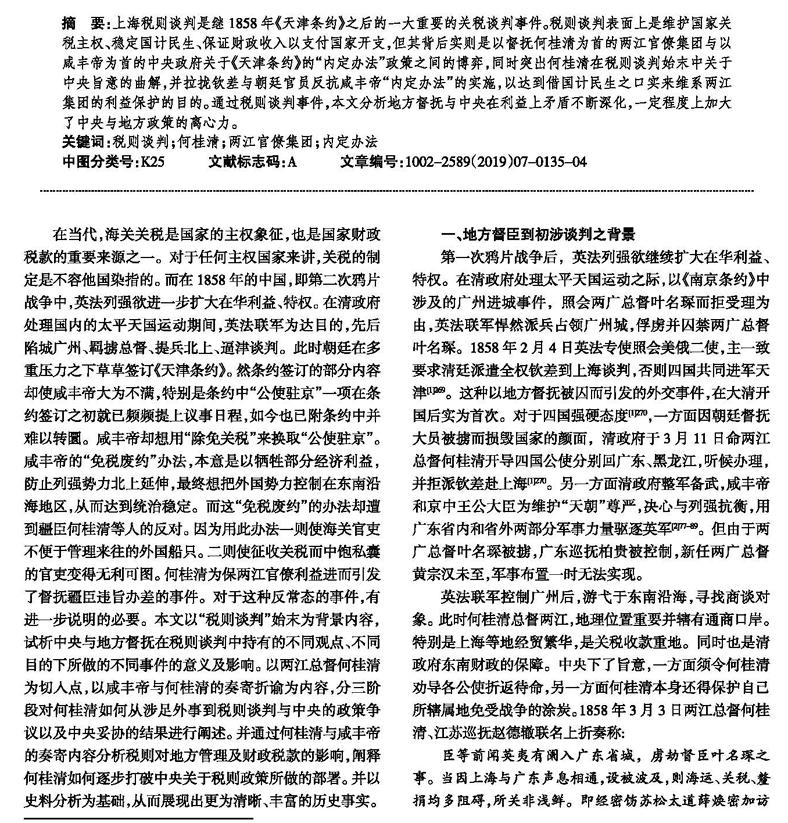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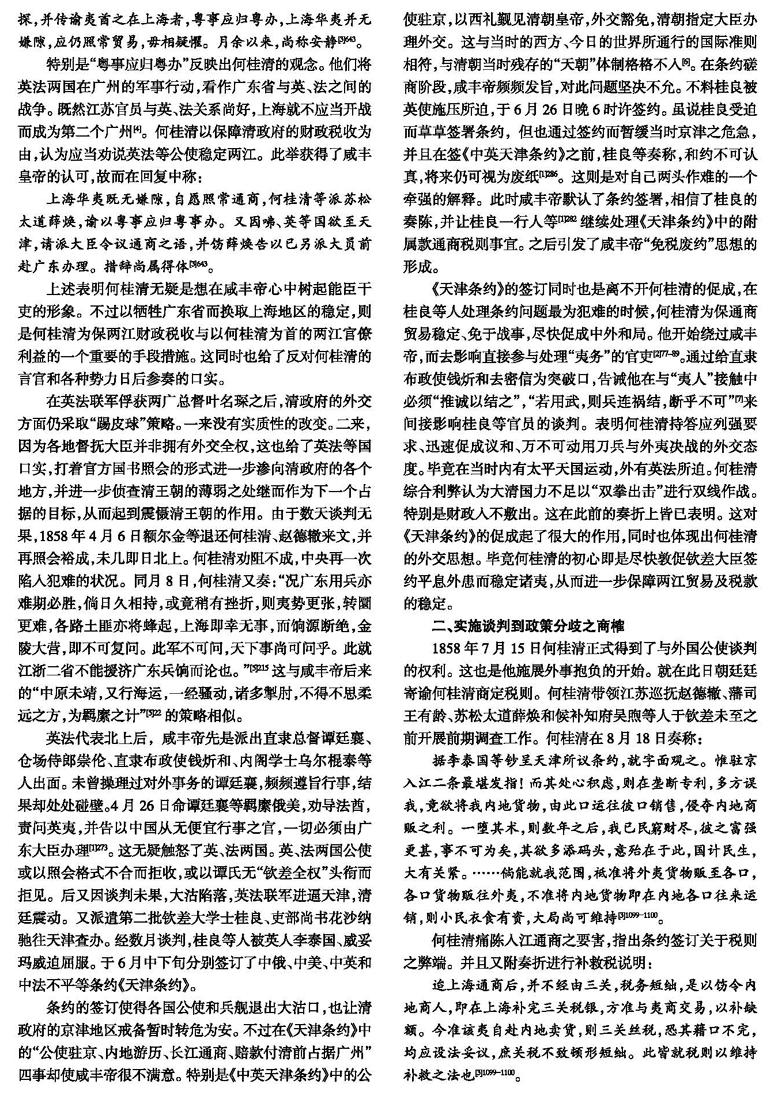

摘 要:上海税则谈判是继1858年《天津条约》之后的一大重要的关税谈判事件。税则谈判表面上是维护国家关税主权、稳定国计民生、保证财政收入以支付国家开支,但其背后实则是以督抚何桂清为首的两江官僚集团与以咸丰帝为首的中央政府关于《天津条约》的“内定办法”政策之间的博弈,同时突出何桂清在税则谈判始末中关于中央旨意的曲解,并拉拢钦差与朝廷官员反抗咸丰帝“内定办法”的实施,以达到借国计民生之口实来维系两江集团的利益保护的目的。通过税则谈判事件,本文分析地方督抚与中央在利益上矛盾不断深化,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央与地方政策的离心力。
关键词:税则谈判;何桂清;两江官僚集团;内定办法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7-0135-04
在当代,海关关税是国家的主权象征,也是国家财政税款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于任何主权国家来讲,关税的制定是不容他国染指的。而在1858年的中国,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列强欲进一步扩大在华利益、特权。在清政府处理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英法联军为达目的,先后陷城广州、羁掳总督、提兵北上、逼津谈判。此时朝廷在多重压力之下草草签订《天津条约》。然条约签订的部分内容却使咸丰帝大为不满,特别是条约中“公使驻京”一项在条约签订之初就已频频提上议事日程,如今也已附条约中并难以转圜。咸丰帝却想用“除免关税”来换取“公使驻京”。咸丰帝的“免税废约”办法,本意是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防止列强势力北上延伸,最终想把外国势力控制在东南沿海地区,从而达到统治稳定。而这“免税废约”的办法却遭到疆臣何桂清等人的反对。因为用此办法一则使海关官吏不便于管理来往的外国船只。二则使征收关税而中饱私囊的官吏变得无利可图。何桂清为保两江官僚利益进而引发了督抚疆臣违旨办差的事件。对于这种反常态的事件,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本文以“税则谈判”始末为背景内容,试析中央与地方督抚在税则谈判中持有的不同观点、不同目的下所做的不同事件的意义及影响。以两江总督何桂清为切入点,以咸丰帝与何桂清的奏寄折谕为内容,分三阶段对何桂清如何从涉足外事到税则谈判与中央的政策争议以及中央妥协的结果进行阐述。并通过何桂清与咸丰帝的奏寄内容分析税则对地方管理及财政税款的影响,阐释何桂清如何逐步打破中央关于税则政策所做的部署。并以史料分析为基础,从而展现出更为清晰、丰富的历史事实。
一、地方督臣到初涉谈判之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列强欲继续扩大在华利益、特权。在清政府处理太平天国运动之际,以《南京条约》中涉及的广州进城事件,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而拒受理为由,英法联军悍然派兵占领广州城,俘虏并囚禁两广总督叶名琛。1858年2月4日英法专使照会美俄二使,主一致要求清廷派遣全权钦差到上海谈判,否则四国共同进军天津[1]269。这种以地方督抚被囚而引发的外交事件,在大清开国后实为首次。对于四国强硬态度[1]270,一方面因朝廷督抚大员被掳而损毁国家的颜面,清政府于3月11日命两江总督何桂清开导四国公使分别回广东、黑龙江,听候办理,并拒派钦差赴上海[1]270。另一方面清政府整军备武,咸丰帝和京中王公大臣为维护“天朝”尊严,决心与列强抗衡,用广东省内和省外两部分军事力量驱逐英军[2]77-89。但由于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掳,广东巡抚柏贵被控制,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未至,军事布置一时无法实现。
英法联军控制广州后,游弋于东南沿海,寻找商谈对象。此时何桂清总督两江,地理位置重要并辖有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等地经贸繁华,是关税收款重地。同时也是清政府东南财政的保障。中央下了旨意,一方面须令何桂清劝导各公使折返待命,另一方面何桂清本身还得保护自己所辖属地免受战争的涂炭。1858年3月3日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巡抚赵德辙联名上折奏称:
臣等前闻英夷有阑入广东省城,虏劫督臣叶名琛之事。当因上海与广东声息相通,设被波及,则海运、关税、■捐均多阻碍,所关非浅鲜。即经密饬苏松太道薛焕密加访探,并传谕夷酋之在上海者,粤事应归粤办,上海华夷并无嫌隙,应仍照常贸易,毋相疑■。月余以来,尚称安静[3]643。
特别是“粤事应归粤办”反映出何桂清的观念。他们将英法两国在广州的军事行动,看作广东省与英、法之间的战争。既然江苏官员与英、法关系尚好,上海就不应当开战而成为第二个广州[4]。何桂清以保障清政府的财政税收为由,认为应当劝说英法等公使稳定两江。此举获得了咸丰皇帝的认可,故而在回复中称:
上海华夷既无嫌隙,自愿照常通商,何桂清等派苏松太道薛焕,谕以粤事应归粤事办。又因■、英等国欲至天津,请派大臣令议通商之语,并饬薛焕告以已另派大员前赴广东办理。措辞尚属得体[3]643。
上述表明何桂清无疑是想在咸丰帝心中树起能臣干吏的形象。不过以牺牲广东省而换取上海地区的稳定,则是何桂清为保两江财政税收与以何桂清为首的两江官僚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措施。这同时也给了反对何桂清的言官和各种势力日后参奏的口实。
在英法联军俘获两广总督叶名琛之后,清政府的外交方面仍采取“踢皮球”策略。一来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二来,因为各地督抚大臣并非擁有外交全权,这也给了英法等国口实,打着官方国书照会的形式进一步渗向清政府的各个地方,并进一步侦查清王朝的薄弱之处继而作为下一个占据的目标,从而起到震慑清王朝的作用。由于数天谈判无果,1858年4月6日额尔金等退还何桂清、赵德辙来文,并再照会裕成,未几即日北上。何桂清劝阻不成,中央再一次陷入犯难的状况。同月8日,何桂清又奏:“况广东用兵亦难期必胜,倘日久相持,或竟稍有挫折,则夷势更张,转圜更难,各路土匪亦将蜂起,上海即幸无事,而饷源断绝,金陵大营,即不可复问。此军不可问,天下事尚可问乎。此就江浙二省不能援济广东兵饷而论也。”[5]215这与咸丰帝后来的“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5]22的策略相似。
英法代表北上后,咸丰帝先是派出直隶总督谭廷襄、仓场侍郎崇伦、直隶布政使钱■和、内阁学士乌尔棍泰等人出面。未曾操理过对外事务的谭廷襄,频频遵旨行事,结果却处处碰壁。4月26日命谭廷襄等羁縻俄美,劝导法酋,责问英夷,并告以中国从无便宜行事之官,一切必须由广东大臣办理[1]273。这无疑触怒了英、法两国。英、法两国公使或以照会格式不合而拒收,或以谭氏无“钦差全权”头衔而拒见。后又因谈判未果,大沽陷落,英法联军进逼天津,清廷震动。又派遣第二批钦差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驰往天津查办。经数月谈判,桂良等人被英人李泰国、威妥玛威迫屈服。于6月中下旬分别签订了中俄、中美、中英和中法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
条约的签订使得各国公使和兵舰退出大沽口,也让清政府的京津地区戒备暂时转危为安。不过在《天津条约》中的“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通商、赔款付清前占据广州”四事却使咸丰帝很不满意。特别是《中英天津条约》中的公使驻京,以西礼觐见清朝皇帝,外交豁免,清朝指定大臣办理外交。这与当时的西方、今日的世界所通行的国际准则相符,与清朝当时残存的“天朝”体制格格不入[6]。在条约磋商阶段,咸丰帝频频发旨,对此问题坚决不允。不料桂良被英使施压所迫,于6月26日晚6时许签约。虽说桂良受迫而草草签署条约,但也通过签约而暂缓当时京津之危急,并且在签《中英天津条约》之前,桂良等奏称,和约不可认真,将来仍可视为废纸[1]286。这则是对自己两头作难的一个牵强的解释。此时咸丰帝默认了条约签署,相信了桂良的奏陈,并让桂良一行人等[1]282继续处理《天津条约》中的附属款通商税则事宜。之后引发了咸丰帝“免税废约”思想的形成。
《天津条约》的签订同时也是离不开何桂清的促成,在桂良等人处理条约问题最为犯难的时候,何桂清为保通商贸易稳定、免于战事,尽快促成中外和局。他开始绕过咸丰帝,而去影响直接参与处理“夷务”的官吏[2]77-89。通过给直隶布政使钱■和去密信为突破口,告诫他在与“夷人”接触中必须“推诚以结之”,“若用武,则兵连祸结,断乎不可”[7]来间接影响桂良等官员的谈判。表明何桂清持答应列强要求、迅速促成议和、万不可动用刀兵与外夷决战的外交态度。毕竟在当时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英法所迫。何桂清综合利弊认为大清国力不足以“双拳出击”进行双线作战。特别是财政入不敷出。这在此前的奏折上皆已表明。这对《天津条约》的促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体现出何桂清的外交思想。毕竟何桂清的初心即是尽快敦促钦差大臣签约平息外患而稳定诸夷,从而进一步保障两江贸易及税款的稳定。
二、实施谈判到政策分歧之商榷
1858年7月15日何桂清正式得到了与外国公使谈判的权利。这也是他施展外事抱负的开始。就在此日朝廷廷寄谕何桂清商定税则。何桂清带领江苏巡抚赵德辙、藩司王有龄、苏松太道薛焕和候补知府吴煦等人于钦差未至之前开展前期调查工作。何桂清在8月18日奏称:
据李泰国等钞呈天津所议条约,就字面观之。惟驻京入江二条最堪发指!而其处心积虑,则在垄断专利,多方误我,竟欲将我内地货物,由此口运往彼口销售,侵夺内地商贩之利。一堕其术,则数年之后,我已民■财尽,彼之富强更甚,事不可为矣,其欲多添码头,意殆在于此,国计民生,大有关紧。……倘能就我范围,祗准将外夷货物贩至各口,各口货物贩往外夷,不准将内地货物即在内地各口往来运销,则小民衣食有资,大局尚可维持[3]1099-1100。
何桂清痛陈入江通商之要害,指出条约签订关于税则之弊端。并且又附奏折进行补救税说明:
迨上海通商后,并不经由三关,税务短绌,是以饬令内地商人,即在上海补完三关税银,方准与夷商交易,以补缺额。今准该夷自赴内地卖货,则三关丝税,恐其藉口不完,均应设法妥议,庶关税不致顿形短绌。此皆就税则以维持补救之法也[3]1099-1100。
何桂清用国计民生为由来衬托出口岸关税的重要性。一是为了保证关税收款的数额,明辨分析,则体现能臣干吏生财有道之本事。二是为了表达其不辞辛劳、咸与钦差同舟共济的公忠体国的形象。本以为皇帝能够支持其办法实施。但是9月12日的廷寄内容却给何桂清泼了冷水。廷寄中回复称:
所有夷务,自应遵照内定办法,未可擅出己见,倘于地方有窒■之处,不妨与桂良等悉心筹议,稍加变通,大致不可更改。不得以现议办法,恐致军饷短绌为词,须知办成后,各口税课,足以相抵,毋庸过虑[3]1116。
9月14日何桂清又因钦差迟迟未至上海,各国公使各欲回国之时又向朝廷递折子。一面说明各国公使在沪欲走的情况,一面又向咸丰帝就税则问题而奏称:
臣维皇上驭天下之大柄,惟信兴财,而藏富于民,尤为理财之要诀。今在天津所议条款,任其周游天下,无论何货,互相贸易。则我内地货物,亦听其在内地兴贩矣,垄断罔利,莫此为甚[3]1117-1118。
对于何桂清此举,咸丰帝仍然坚持己见,无动于衷。时过不长,在9月20日,明善、段承实带密件到常州(因南京被太平天国攻占,两江总督驻地迁至常州),晤何桂清(此密件即“全免税课,开弛烟禁,换回北京驻使长江通商二款”)[1]286。看到旨意使得何桂清痛心不已。因当时清朝的海关年收入为数百万两白银,这在咸丰朝的艰难财政中已是不小的收入。何桂清属地上海海关更是朝廷税款收纳的大宗进项。咸丰帝打算以国家财政大宗来源的关税换取“公使进京”的“内定办法”,却与何桂清所条陈的税则补救法策略相“左”。故而引起君臣的政见之争。
面对税則上的政策之争,何桂清并不退却。因为他知道如若按照咸丰帝的免税政策来实施,必然造成地区内的经济、行政因素的不稳定化。造成其不稳定原因有三:第一,税则全免必然损及关税的收入急剧下减,无法保证和承担地方军需的粮饷供给,必然严重影响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经费来源。第二,税则全免必然导致直接冲击封建经济的发展,使洋人尽获其利,而侵夺内地商贩之利。且因税则全免则无法查验夷船货物,洋人肆意夹带违禁品,致使不便于管理,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第三,税则全免必然损及靠关税款中饱私囊的两江各级官吏的利益,不利于何桂清拉拢利益集团的关系。何桂清向明善、段承实两位上差说明原委,并晓之以税则全免来废弃前约作为条件的不可行因素。成功地拉拢二人走到了统一的战线上,并于9月29日与明善、段承实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联名上奏称:
至查办从前短收税课一层,奴才等现与督臣再三商酌,■虑该夷闻之,将各关冒收之款照数给还,是以未便轻举。其全免入口税课一节,亦不敢早为吐露,总看开导之后,该夷光景若何,再为宣布皇仁,俾知感激。若■能消弭一二要件,或可不需免税,岂不计出万全。设夷性犬羊,坚执不允,再从税务作为转圜,又多一层办法[3]1126-1127。
面对明善、段承实二人的奏陈,咸丰帝本欲通过二人将旨意传递给何桂清,并共议处置。然二人竟受何桂清游说而不遵旨意办差,并想出一个折中的法子以桂良等未到而迁延时日。但既已说明情况,也算是不敢明意违旨,索性在回复廷寄中写道:
此次桂良等赴上海,应照原定办法,俾各夷感服。■能消弭一二事,则该夷仍要赔偿兵费,广东省城即不即时退出。况待该夷坚执不允,然后再以免税为转圜,则该夷必以我为背约,愈多藉口[3]1128。
面对咸丰帝廷寄中的决绝态度,何桂清为了打破咸丰帝“内定办法”的实施,再一次动员参加税则谈判的大部分官员并拉拢钦差桂良[1]286等人来反对“内定办法”。两江同僚皆与何桂清有着非亲即署的密切关系,在这次捍卫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事件中,都纷纷站起来与何桂清态度保持一致。他们批判咸丰帝的计划:“内定办法,不但不能行,且开无穷边衅,书生误国,实非浅鲜!”“如不思变计划,诚哉数也。”[8]同时在10月27日以桂良、花沙纳领衔回奏:
今若免税而该夷仍执定见,不肯轻弃条约,我亦何必免其纳税乎?至于夷人交纳税课,锱铢洞悉,全不容我浮收,非十三行未撤之时可比……若遽宣露免税一节,设该夷视为大皇帝格外之恩,戚而受之,而于条约仍不能罢议,已非计之得也。或■能消弭一二事,即以每年数百万巨款轻于一掷,纵帑金不足甚惜,而其中可虑之处,实难枚举[3]1179。
随后又举出“十虑”[3]1180-1181列于奏折之后,充分说明理由。并且在此之后桂良、何桂清等又联合上奏:“纵能免税,亦难罢弃条约。即臣桂良等屡奉圣训谆严,亦曾密令随员将内定办法,从旁探询,实属难行,令人无计可施”[9]1189疆臣督抚联合钦差大臣共同公然反对皇帝旨意,这使咸丰帝勃然大怒,在廷寄中写道:
何桂清身任封圻,特命会办要事,而坚执己见,竟于国计无裨,桂良等随同附和,牢不可破,清夜扪心,亦当自愧……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尽一分心力,即为天下消一分祸害,桂良等受恩深重,身在局中,责有攸归,朕不能再为曲谅也[9]1191。
面对咸丰帝之怒,何桂清作为臣子还是有所顾虑的,毕竟初衷是说明情况、分析利弊,请求皇帝俯允税则谈判问题让其抛弃“内定办法”的实施,而不是以纠结地方官员集体向皇帝发难逼宫。何桂清一面安抚咸丰帝缓和君臣意见之争的矛盾。一面转借列强之语代己之言,目的则是敦请咸丰帝俯允税则签订。咸丰帝因闻列强之言,顽固不化,即便给了英法等国恩典,也不可能换回“四事”之约废除,故而也勉强同意何桂清所谈税则。
三、谈判后对何桂清之评价
1858年上海税则谈判最终于11月8日达成协议并签署。两江总督何桂清涉足外交事宜是偶然的。大清国最初的外交场地在广州,因两广总督被掳、公使兵船北上,才有了沿海督抚遵旨对外夷调解,这也才有了何桂清初涉外交的可能。
按大清律令,地方与中央必是政出一辙的,但为什么最后地方政策与中央决策相悖呢?以税则谈判为例,可以分析出原因有二:一是因中央与地方相距太远,中央对地方的消息来源只能靠奏折、廷寄,没有切身体会地方的处境。并且地方事务日经变则,无法及时向中央汇报,导致地方诸多事宜无法转给中央政府。所以在特殊的条件下,地方的政策与中央决策意见相“左”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地方沿海督抚有权过问港口通商事宜,并且有权管理。因当时没有统一办理对外事宜的机构,地方对外事宜皆由地方督抚代中央办理,并请旨施行。这使列强对当时的中国官僚政体看法有误,误以为督抚就是中央授权的外交官。并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上包括条约签订中都找当地督抚进行处理。因为这是中央所默许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督抚潜在的权力还是很大的。这就使何桂清可以巧借列强之言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迫使中央答应而保护辖地的利益。从而把自己树立成遵旨的忠臣形象。并且地方政府内部联系较为坚固,整体性突出。派系内部利益复杂,在特殊情况下,并非中央政府与一二钦差所能撼动。特别是地方对外事宜的处理,在一定情况下足以和朝廷政策正面对立。
综上两条原因,可以说明督抚疆臣在地方上的势力,作为中央是不可轻视的。因为有了权势,督抚培植私党更显常态,譬如何桂清在两江任上亲近的官员,浙江布政使王有龄昔日是何桂清的同窗好友,江苏巡抚赵德辙、候补知府吴煦等人也都是何桂清的属僚,并在税则谈判中以何桂清马首是瞻。另外还有钦差桂良、花沙纳、明善、段承实,以及直隶布政使钱■和也都与何桂清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一个人脉关系网放在地方上,何桂清可以说是手眼通天了,并且还奉皇命处理税则谈判,这就难免飞扬跋扈。就连咸丰帝也没有想过派出的一干钦差去两江办理《天津条约》善后事宜却被何桂清给游说利用,反帮何桂清办差。咸丰帝认为何桂清假借税则问题为由,实质来保护两江官吏的钱袋子利润不被夺走。并在廷寄中写道:“特恐属员虑及免税后,无可沾润,因而设词淆惑”[3]1134,来点明何桂清所坚持税则谈判的最终目的。
如果说何桂清违旨办差的第一个原因是为了保证两江属僚与自身利益的话,那么第二个原因则是何桂清敏锐地分析出了当时的时局。因财政问题严重,饷银军需难支,万不可轻言出兵对抗外夷,双线作战。此意极大地说服了在津谈判的桂良等人。同时也使咸丰帝深以为是。在当时这种言论无异于老成谋国之见。除此之外,综合何桂清筹办税则始末来看,何桂清还是很会做官的。首先在《天津条约》签订之时,他就在两江分析夷情和国内时局关系,做出严谨判断并上奏咸丰帝,咸丰帝感其言针砭时弊。并且何桂清又私下联系处理天津谈判的钱■和以渗入谈判大员的思想。这是他为自己树立处办夷务的权威做出的前期准备,自己铺垫自己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是赶上巧合。鉴于他在两江署任上于广州事件时全力保全上海口岸,与叶名琛政策有所不同,使得外国公使很满意。又因在天津谈判时,清政府不愿外使进京面商,更不想让外使来北方谈判。所以才选一个既是南部地区,又有通商口岸,并且也得到外国公使所认可的地方——上海。恰巧上海又是两江总督辖地,而总督何桂清又不与外使交恶,所以中外一致认可了何桂清。这就给了何桂清参与谈判的机会。自从接了谈判税则差事后,何桂清就开始进一步为自己树立权威形象,把保住税赋来源、安定国计民生的大方略与他的稳定两江集团利益联系起来。并吸纳了钦差同流,打破咸丰帝制定的“内定办法”。尽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拉拢官员上折子陈述利弊,说服咸丰帝,但他的做法还是高明的。一来他借洋人之口来恫吓朝廷,并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二来作为督抚大员,他掌握拿捏咸丰帝脾气的火候也是相当准确的。虽然咸丰帝也看出何桂清的意图,但又不得不承认何桂清的做法。同时又让桂良背这个办理失宜的黑锅[1]290。
四、结语
围绕着《天津条约》谈判与上海税则谈判始末,何桂清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上海税则谈判是以何桂清为首的督抚疆臣久经数月与外夷转圜才换来的清政府对关款的保障。一定意义上来讲何桂清是有功的。但实际上何桂清的做法是以出卖国家权利而换来的地方的关税保护,在海关税则的商定中包括鸦片合法化、聘用英国人来管理中国海关等一系列条款,使中国的半殖民地经济进一步加深。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起到保护内地经济利益的效果,相反加深外夷对内地的经济侵夺。
参考文献:
[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1829-1885)上[M].北京:中華书局,1987.
[2]郭卫民.何桂清与咸丰帝的对外政策之争及其影响[J].近代史研究,1993(6).
[3]中华书局.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2-3:11卷-3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79.
[5]齐思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6]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91.
[7]中华书局.筹办夷务始末: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4.
[8]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46.
[9]中华书局.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中华书局.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