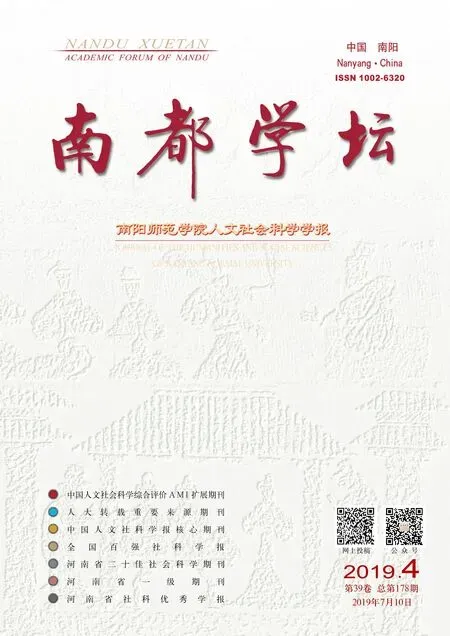“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报刊舆论的兴起、革新
2019-07-27陈占宏
陈 占 宏
(上海远东出版社 综合编辑中心,上海 200035)
一、思想的“物质力量”的认识和启发:新文化运动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启蒙作用
五四运动中,在上海专注于理论建设,而不再只注重实际革命的孙中山,亲眼看到了五四运动中舆论的力量,以及由此而激发的民众的力量。数月后的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写了那封著名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在这封信中,他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1]
这段文字是孙中山极少有的评价五四的文字,广为人知。孙中山看到并强调思想革命之于实际行动的作用。这个道理就是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一面强调实际斗争的有效性,但同时也强调理论、意识、精神所能激发和唤起的“物质力量”的作用。“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是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为人。”[2]五四运动,成为一个最终获得成功的民众运动,思想的启蒙和民众的觉醒,功不可没。
正是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这一启发,他对他的同志们提出加强舆论鼓吹的要求。他自己也坦承以前的宣传做得不够。在五四运动当中,曾前往拜访孙中山的张国焘回忆称,“他承认我们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3]。

不只是孙中山有些认识和转变,追随孙中山的一些革命同志也有这样的认识和转变。1919年6月7日,五四之际,朱执信在对蒋介石的信中,也表达了其“弃枪从文”的认识和决心。“弟现在观察中国情形,以为非从思想上谋改革不可。故决心以此后得全力从事于思想上之革新,不欲更涉足军事界,故漳(按,时蒋在陈炯明军中,居漳州)行只可暂罢矣。”[6]他也正受孙中山有指派,参与创办《星期评论》工作,作革命舆论之鼓吹。
对于孙中山在五四运动中的此一发现和强调,胡适在关于五四的纪念的一些演讲和文章中,经常加以援引。胡适称这种说法“很正确很平允”,“在那封信上中山先生便提到北京学生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启发,竟有化新观念为力量,便赤手空拳的使反动的北京政府对他们让步”[7]。1935年,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纪念“五四”》时也说,“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5]580。1960年五四纪念,胡适在台北广播电台谈话录音时又引用孙中山关于五四的那段话,进而说,“他的看法到现在我认为是很公允的”,“至少孙中山先生说,因为思想运动,文学运动在前,所以引起‘五四’运动”[5]855。
多年来,相信不只胡适,我们绝大多数都是这样认为的:即发轫于1915年《新青年》创办时的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文学革命)至少是“隐在地”催化着随之而来的五四学生运动。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两个运动毫无关系,即新文化运动在先,五四学生运动在后。
二、孙中山所言的“新文化运动”指的是“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
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力量,五四学生运动与思想启蒙之力相关,孙中山的确有这个意思,我们也认可这样的说法。但孙中山和我们所理解的这“观念”“思想启蒙”的具体所指不同,我们理解的思想启蒙是“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而孙中山所说的则是“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
他在信中就明确指出“新文化运动”是指五四“以来”(注意,不是“以前”)思想舆论的蓬勃发展,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并非一回事。至于“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这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下意识地认为新文化运动只是五四学生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而没有看到在五四学生运动取得成功的刺激和鼓舞下,又产生了又一波与此前新文化相比,更为广泛、更为高涨的似乎是又一次的新文化运动。而孙中山所受感染和启发的,正是这所谓的“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不能仅被视为只是指“五四前”的文化运动,而且还包括了“五四后”的文化运动。
胡适不断地说到孙中山所说的化观念为力量的看法很正确,似乎这样他所置身并参与的“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就功不可没。其实,他对孙中山所指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只是“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不清楚。比如,1947年,他在纪念五四时就说:“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长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运动。五四之后,有全国知识青年热烈参与的新文艺运动,和各种新的政治活动。”其中所说的“五四后”学生热烈参与的“新文艺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的继起和发展。
他甚至将孙中山评价五四的那段话,逐句地解释得清清楚楚。
他说的“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就是指《新青年》《新潮》几个刊物。他说的“学潮弥漫全国,人皆誓死为爱国之运动”,“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就是指五四运动的本身。他说的“一般爱国青年,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各种新出版物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就是指五四以后各种新文艺,新思潮的刊物(据当时的统计,民国八九年之间,全国各地的白话新期刊,至少有四百种之多)。中山先生把当时的各种潮流综合起来,叫作“新文化运动”,他承认“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5]796-797
孙中山所说的新文化运动正是“五四以后各种新文艺,新思潮”,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的、《新青年》《新潮》几个刊物所引导的、五四学生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山先生把当时的各种潮流(‘五四以后各种新文艺,新思潮的刊物’)综合起来,叫作‘新文化运动’。”可见,“此新文化运动”非“彼新文化运动”也。我们如果将五四前、后两段新文化运动总括起来,并一并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话,这就需要纠正我们的“刻板印象”,这个“刻板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文化运动”只是“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而很大程度上,正是这“后半段”的新文化运动,才焕发出磅礴之力,使得“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
那么,如果从孙中山那段著名的五四评语中得出“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至少隐在地)催化了此后的五四学生运动,就不符合孙文之原意了。而这样的结论,又是大多数人的认识。比如,罗家伦就认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发生与“此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有关,或者说是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发生的。1931年,罗家伦论五四运动时,就是从蔡元培掌校时期的北大所引领的“新文化运动”谈起的,他称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8]。
何况,不只孙中山,其时很多人都能意识到、也提到了五四学生运动后仍有一个更为蓬勃的新文化运动,他们也和孙中山一样,不只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五四前的那个新文化运动。比如,1925年,周作人就说,“五四是一种群众运动,当然不免是感情用事,但旋即转向理智方面发展,致力于所谓新文化的提倡”[9]。这就说得很清楚,群众运动后就是“新文化的提倡”。又如,1929年5月4日五四纪念时,有金志骞发表《五四运动之经过及其影响》一文,其中有云,“五四运动是以政治运动始而以文化运动终”[10]。明乎五四后仍有新文化运动存在,就不会感到这句话与我们所理解的“思想运动在前,民众运动在后”相矛盾。再如,梁实秋在《“五四”与文艺》一文所用的也是孙中山所说的“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他说,“五四运动原是一个单纯的爱国运动,后来转变为新文化运动”。按我们对新文化运动即“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一个五四运动参与者、过来人,说出如此违背常识的话来,真是不可思议。对于梁氏的这句话,李敖就曾纠正说,“这一说法,是大错特错的。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在前,五四运动在后”。但如果将梁之新文化运动理解为孙中山所说的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就不仅没有大错特错,而且一点不错。
三、“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对出版业及社会舆论的影响
孙中山说到“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时说,“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正如孙氏所云,五四之后,社团林立,期刊迭出,言论蜂起。
这种情形可从以下诸种材料中得到佐证。1921年1月14日,内务部在提案设立监督控制舆论的“著作及出版物研究委员会”时就说,“查近来新思潮之传播,几有日盛一日之势,而印刷物实为其媒介。本部为维持治安,预防隐患起见,拟就部中组织一研究委员会,对于著作物及出版物,认为有研究之必要者,随时搜集研究,以期洞见症结,因事补救,不致蹈凭空过当之弊”[11]。1930年,站在反共立场上的陶愚川就曾骂道,“反动的刊物,反动的言论,真是盛极一时”[12]。
可是,当时出版物到底有多少种呢?朱光潜称,“五四运动一年之中,新出版的刊物突然增加到四百余种之多,这在任何文明国家里可以算是一个奇迹”[13]。胡适也说到他个人曾经收到学生邮寄的“豆腐干报”就有四百余份(按,其他地方说是四百余种)之多。“各处学生皆有组织,各个组织皆有一种出版物,申述他们的意见。单说民国八年一年之内,我个人所收到的学生式的豆腐干报,约有四百余份之多,其他可无论了。”[5]727“现在差不多每星期都有新报出现”,这种层出不穷的新报,以至于叫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发起人陈独秀大为抱怨,他甚至呼吁大家不要一哄而上办那“内容大同小异”的报。“出版物是新文化运动底一端,不是全体”,“总希望大家拿这些人人力财力,去办新文化运动中比出版物更进一步更要紧的事业”[14]。从中可见,五四后报刊繁盛之程度。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五四前、后成立的社团和发行的刊物的情形,就可以了解“五四后”报刊舆论之蓬勃发展。
就五四时期所成立的一些重要社团来看,五四前成立的社团有1918年10月20日成立的国民杂志社,1918年11月19日成立的新潮社,1919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等。五四之际、之后成立的社团有1919年5月3日成立的工学会,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1918年6月30日),1919年9月1日成立的少年学会,1919年9月16日成立的觉悟社,1919年成立的平民教育社,1919年11月成立的曙光杂志社,1919年底成立的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1920年成立的觉社等[注]参见张允侯等著《五四时期的社团》,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显然,五四之际、之后成立的社团多于五四前成立的社团。
就五四时期所创刊发行的期刊而来看,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三集六册中所介绍的159种期刊(包括报纸副刊)中,据笔者统计,1919年5月4日之前,出版的刊物共有22种,这22种期刊中,有一些则是1919年前夕出版(如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的《每周评论》,创刊于1919年1月的《国民》和《新潮》等),也就是说在五四之前,并没多少种刊物的出版。而在1919年5月4日以后出版的刊物有137种。这137种期刊中有一些刊物正诞生于五四运动之中。可见“五四后”创刊的刊物要远远多于“五四前”创刊的刊物。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状况。
这“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的“后半段”,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 “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多是受五四学生运动的刺激和鼓舞而发生。与“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受五四运动的激发不同的是,“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受当时袁世凯政府复古倒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刺激而发生的。一方面,在这场由北京的学生运动波及并演变为全国的民众运动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客观上人们有了更为迫切的表达需要,需要更多的发声渠道;另一方面,这次运动最终迫使政府退让,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深受鼓舞、“尝到胜利甜头”的学生“更上一层楼”,期待以舆论来推动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
第二,新文化运动被五四运动一分为二,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其刊物更为丰富,范围更为广泛,声势更为浩大,效果更为明显。
罗家伦曾说到五四运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三者的关系。1950年,他在《五四的真精神》一文中就说,“五四运动一部分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却因五四运动而波涛汹涌,一漫全国”[15]。1968年,他又说了同样的意思,“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16]。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当年北京高师被捕“八勇士”之一的初大告也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在这之前,就有《新青年》。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更加蓬勃发展起来”[17]。这和罗家伦所说极为相似。当代学人杨天石先生亦云,“以五四爱国运动为分界,新文化运动可以分前后两个阶段。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教育和熏陶了一代青年,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提供了思想准备。仅就运动从北京大学学生中开始这一点,就不难看出,它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关系。五四爱国运动后,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蓬勃气势继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外来思潮的引入更加丰富,思想界更加活跃,各种社团、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样,新文化运动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18]。
与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由北京(其实就是“北大”)主导,并“一枝独秀”相比,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但需要注意的是,有的期刊,看起来好像是各地所办,但实则是当地学生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所举办。如《秦钟》是由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在北京创办,《新陇》是由北京读书的甘肃青年在北京所创办,《新湖北》是由旅沪湖北自治协会在上海创办,《新安徽》是由旅沪皖人在上海创办。
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除规模和范围有所扩大之外,其质量和影响也有所提高。周策纵在谈及五四带给中国出版和新闻舆论的进步时说,“中国的出版和新闻舆论界在五四事件后也有了较大进步。如果把‘五四’前后出版的报纸和杂志做一比较就会发现,‘五四’以后的报纸杂志在技术和内容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这类出版物数量的迅速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所拥有的读者大众比以前大为增加,政府和公众对之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视”[19]。当然,其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更为明显,1919年10月19日,时养病西山卧佛寺的杨昌济在日记中说,“今年国民始有自觉之端绪,新文化之运动起于各地,新出之报章杂志,新译新著之书籍,新组织之团体,逐日增加,于是有新思想之传播,新生活之实现。此诚大可欣幸之事也”[20]。这就是孙中山所称赞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致使“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
第三,这些期刊多由“青年学生”和政党主办。与《新青年》《新潮》《国故》等由北大师生主办的刊物相比,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主要是由学生团体和政党(主要是国民党(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复改为国民党)和共产党(1921年成立))主办。在这些期刊中,不同政党、团体所信奉的主义五花八门,如马克思主义、孙文学说、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等,所讨论的问题也包罗万象,如废督裁兵、地方自治、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等。
与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相比,这后半段的运动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出现了一批政党所举办的刊物。就国民党来说,在孙中山的推动下,国民党人创办了《星期评论》和《建设》。《星期评论》于1919年6月8日在上海创刊,1920年6月终刊,由戴季陶、沈玄庐等编辑。《建设》杂志于1919年8月在上海创刊,由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五人组成建设出版社出版,1920年终刊,共出版13期。罗家伦说,“所以新文化运动一发动,他(按,指孙中山)就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以积极的方案相号召,而命干部同志办《星期评论》,完全用语体文,俾与北大几个有力量的刊物相呼响。胡适之先生作文介绍他的《孙文学说》(以后改名《心理建设》),《新潮》的书评里推崇《建设》,其余互相讨论井田和其他问题的文章还很多。地虽隔开南北,声气却很相通”[15]。后来更加注重宣传的共产党亦不后人,创办了《共产党》《先驱》《劳动界》等刊物。《共产党》月刊是中共于1920年11月在上海创办的一个理论性的机关刊物。“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主义的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及其与其他一切党派的区别,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方向。《共产党》月刊发表了许多文章来论证共产主义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21]而《先驱》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1922年1月15日创刊,其在发刊词中称“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之以反抗的创造精神……本刊的第二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其后期主要偏重于讨论青年运动和团的建设问题[21]13。
第四,很多刊物都偏好于标“新”立异,宣传新思想、讨论新问题成为当时刊物的主流。这从刊物的名称中可以管中窥豹。如《新时代》《新中国》《新社会》《新生活》《新学生》《新生命》《新妇女》《新学报》《新空气》《新共和》《新教育》《新人》《新群》《新韩青年》等。“各省各地”的刊物也面目一“新”。如《新江西》《新湖南》《新湖北》《新安徽》《新四川》《新浙江》《新山东》《新海丰》《新陇》《浙江新潮》等。简直是“无新不成刊”,这和五四前的《新青年》《新潮》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种力求创新、唯新是从的思维,今天仍能看到。
第五,正是因为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受五四学生运动的影响,因此,待到学生运动余波渐息时,新文化运动也就盛况不再。于是,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现象,五四后的这些期刊多是不定期的、且是“短命”的,所谓“狂风不竟日,暴雨不终朝”也。
以上五点系“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特征。
综上,人们通常会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指“五四前”陈独秀等人所提倡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并认为这样的新文化运动促成了随后的五四学生运动。其实,新文化运动并没因五四运动而中止,反而“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这表现为“五四后”社团林立,期刊迭出,言论蜂起。这“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受五四学生运动的刺激和鼓舞,以知识青年和政治团体为主体,承继“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注重思想革新之精神,对政治、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相比,其刊物更为丰富,范围更为广泛,声势更为浩大,效果更为明显。然而却常为人所忽视和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