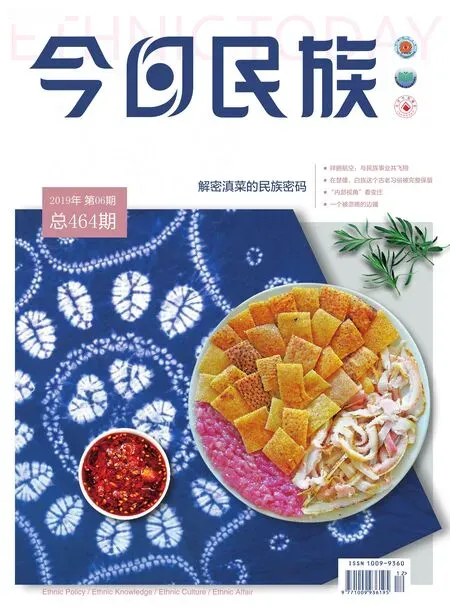一个被忽略的边疆
——李希霍芬笔记里的辽宁
2019-07-20

李希霍芬:“丝绸之路”的命名者
李希霍芬是19世纪德国著名地质学家,他的大名远不如他创造的“丝绸之路”“黄土高原”等概念有名。他是1868年来到中国大陆(此前就去过中国台湾),在4年多的时间里,对中国进行了七次旅行考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晚清的中国,国门初开,吸引了各种专业背景的欧美探险家,李希霍芬是其中的佼佼者。李希霍芬出生于1833年的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卡尔斯鲁赫(今属波兰),1856年在柏林获地质学博士学位,之后从事地质研究,游历欧洲、日本、中国台湾以及缅甸等地。在来中国之前,李希霍芬花了5年时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做地质勘探。此次地质勘探成功地发现了金矿,成就了中国第一代美国移民眼中的“旧金山”——当然,也间接地导致了华人在北美最初的扩散。
1868年,李希霍芬是延续与加利福尼亚州的合作,带着地质勘探的目的到中国来。在中国的4年间,李希霍芬完成了其作为地质学者的中国地理和地质巨著——《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正是在这部书中,他首次提出具有深远意义的“丝绸之路”的概念。
在结束中国旅行之后,39岁的李希霍芬回到德国。第二年他出任德国地质学会主席一职,这表明中国之行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它在德国地质学界的地位。此后,李希霍芬在大学任教(还担任过柏林大学校长),晚年还长期担任德国地理协会会长。其培养出的学生,在中国旅行考察方面,也不乏杰出人物。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以新疆探险而闻名的斯文·赫定。
李希霍芬关于中国的著作,除了地质学专著《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外,还有一本面对大众的通俗读物——《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也就是我们要介绍的书。不过,这本书并非出自李希霍芬之手,而是他的弟子E.蒂森帮他整理的。书中主要收录了李希霍芬在中国期间的日记、书信,统编成册,于李希霍芬去世两年后,即1907年出版。该书中译本20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讲述了李希霍芬七次旅行中的见闻和感受,勾勒了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该书翻译后,不少学者根据他的记录,进行了各种类型的梳理——这也说明这本书值得深读——而笔者为避免重复,则专门聚焦于他笔下的辽宁。
辽宁:一个被忽略的边疆
李希霍芬1869年5月抵达辽宁,从1869年5月18日到7月18日,2个月间,其足迹遍及大半个辽宁,既有靠近渤海的辽东半岛,也有辽宁中部、西部较为内地的乡村,甚至还有辽宁东南部境内的中朝边界一带。
今天,说起中国的边疆,一般人不会首先想到辽宁。今天的辽宁是一个人口稠密,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东部省份。大众所熟悉的东北“二人转”,就是辽宁给外界的文化形象,这一源自当地汉族民间的娱乐形式,一定程度上已被我们今天想象为北方文化的一部分。
在李希霍芬考察辽宁时,以及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辽宁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边疆,有着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的管理体制。
以行政地理而言,由于东三省是清朝建立者满族的“龙兴之地”,因此与十八行省的治理模式并不相同,实行旗民分治制度,即以盛京(奉天)将军系统辖治旗人,以府州县管理其他人。
这一管理制度在人口管控方面表现明显,清政府严格控制汉人进入东北(当然,包括辽宁),希望保持“龙兴之地”在民族和文化上的“原貌”。因此,从民族上看,清朝中前期,这里不仅有多个少数民族,而且少数民族人口比率较高。这种状况,符合我们对“边疆”的想象。
这种状况,在晚清时期,也就是李希霍芬考察辽宁时有所改变。随着晚清边患危机的加深和管理松懈,针对汉人的禁令逐步失效,于是大量内地人开始移民到山海关以东的东三省,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的现象。李希霍芬的考察日记,就是这个历史转变时刻的一个记录。
正在转变的辽宁,不止有汉人的涌入这一人口现象。事实上,随着中国与朝鲜、日本、西方列强的外交接触的加深,辽宁和东三省也从较边缘地位,逐步转变为中外各种政治事件的筹码或主角。
过去,辽宁因为与朝鲜接壤,承担了很多清朝政府对朝事务的工作。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日本占领朝鲜。这之后,辽宁成了中国边疆危机的前沿,辽宁南部的辽东半岛在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中被日本割去,随后还有俄、德、法三国的“干涉还辽”等外交风波。再后来,“九一八”事变让包括辽宁在内的东三省事实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人的边疆危机意识和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中国由此被深刻改变。
东北的近代历史对近现代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李希霍芬1869年东北考察时还看不到这样的端倪,那时的东北和辽宁,还是一个有限开放的宁静的边疆。
李希霍芬眼中的辽宁
李希霍芬笔下的辽宁,土地辽阔人口稀少。比如,靠近辽东湾的锦州市李王村,李希霍芬就认为是他“至今为止走过的人口最稀少的地方”。这里今天位于京哈高速路旁,是距离锦州市区不远的乡村,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李希霍芬也注意到辽宁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闯关东”的北方汉人,正日益增多。在大连旅顺龙王河附近的山里,李希霍芬就发现当地的居民有一些是新近从山东迁入。李希霍芬没有对这些移民进行专门介绍,不过,从零星材料看,这些移民已经深入到中朝边境。
近代历史上,东北的受难不仅因为战略位置,也因为资源。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可能是第一个对东北资源进行深入考察的西方人。在他的这本日记中,留下了对当时的辽宁不知是福是祸的描述。
关于东北土地之肥沃,李希霍芬特别提到大连的貔子窝,他说这里土地肥沃到不用给耕地施肥。所以在山东“一匹马排便的时候,总是有几十只眼睛盯着,他们手里提着小篮子等着捡粪”,但在辽宁的貔子窝就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土地已经很肥沃。
旅行到旅顺的龙王河时,李希霍芬更是把这里盛赞为一个物产丰富、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这里有“肥沃的土地、茂密的森林、鱼类众多的河流、品质很好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气,完全可以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神仙日子”。
探索矿产资源是李希霍芬此行的主要目的,所以他还探查了辽宁煤炭的情况。他日记中说,本溪湖(今天辽宁东部钢铁、化工为主的工业城市)煤矿的数量不少,但是质量一般。这里的煤一部分供周边地区使用,一部分用来炼铁。
除了土地资源以外,海洋资源也很丰富。貔子窝渔业发达,在李希霍芬看来,这里的蟹和贝壳便宜到好像人们都不识货一样,30分钱就可以买一箩筐牡蛎,简直是牡蛎爱好者的天堂。
即便如此,不太合理的开发也导致了环境的问题。李希霍芬说貔子窝的人把能用来烧火的树木都砍倒了,只有在内陆无法把树木运出去的地方,森林才侥幸保存。比如,在西土岭附近的山上,只有山顶还覆盖着树林,很多巨大的树干都顺着河流被运出了山贩卖。永平府(今辽宁西南)也是一样的情况,山上很少有植被了。这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在大凌河(辽宁西部)的时候,李希霍芬遇到暴雨,加之森林少,土质疏松,雨水就冲刷出大量泥沙,泥沙堵塞河道,导致河水暴涨。
相对于自然景观,辽宁地区的人文景观则呈现出文化的多样化,体现了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
比如,牛庄(海城市西部)的建筑可能是“源于满洲或是蒙古部落”,其风格是院墙和房子一样高,从院外只能看见屋顶。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牛庄镇2008年10月被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2015年7月,又被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授予“第三批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称号。李希霍芬对其建筑的历史描述可能不靠谱,但他或许是最早注意到牛庄建筑特色的西方人。
李希霍芬在辽宁发现很多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沿着这个方向,他还发现一个叫“付家子村”的地方,其房屋也有游牧民族的文化元素:有一个大院子,院子旁边围绕着屋子,形成了一个长廊。在大连的貔子窝,房屋也有很多游牧民族的风格。在新民屯(沈阳市辽中县),房子是圆形顶的,风格也非常独特。
在李希霍芬看来,沈阳的妇女也不太像汉族妇女。在服饰上她们不裹小脚,衣服是睡衣一样的长袍子,没有腰身,女人在田地和市场都能见到,这让游历过内地的李希霍芬感到很吃惊。因为他印象中,内地的女人不允许在外抛头露面,但沈阳的女人就会来围观李希霍芬,跟他们一行搭话。
辽宁的东面是朝鲜,李希霍芬对中朝边境也着墨颇多。当时中朝的贸易口岸叫做“高丽门”,这是理论上两国人民可以接触的唯一地方。这里没有宏伟的建筑,也没有防御工事,只有一间很小的屋子,道路也狭窄到只能容一辆车通过。朝鲜人的主要贸易品是牛皮以及各种动物皮毛、纸张、丝绸等等。
李希霍芬的旅行遭遇和对中国人的印象
在辽宁和中朝边境考察,李希霍芬得以比较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因此对旅行中的人和接触到的社会面貌做了一些描述。
据李希霍芬的观察,大部分辽宁的城市和乡村都脏,而且穷,即使是沈阳、锦州府、牛庄都十分破烂。中国的社会阶级差别不大,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并没有截然区别。而且,参照西方标准,他觉得他们文化或精神方面的生活内容很匮乏。
在大连的貔子窝附近,李希霍芬就问过一个富人家的18岁男孩,问他用什么东西消磨时间。男孩回答:“吃饭、睡觉和干坐着。不会打猎骑马或是进行社交活动。”因为貔子窝、牛庄和省城都没有学校,所以他们也不去上学校。不过,这位文盲小哥,却整了一副近视眼镜戴着,遮住了他差不多半张脸。问他原因,他说是为戴着好看。
这位已经相当时髦的富家少爷,在李希霍芬眼里,依旧是显得木讷、无知。至于穷人的孩子则更是麻木、迟钝。
李希霍芬认为中国人没有勇气对外界进行探索,对知识也没有渴望,只知道抽烟和吸鸦片。就连问问题也没有水平,从来没有人问过“怎么样”或者是“为什么”。显然,不仅缺乏知识,还缺乏探索知识的方式,以及勇气。
对看不见的东西,中国人都不会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比较具体。比如,一提到钱,就竖起耳朵听。在李希霍芬眼中,这里人的生活,都以赚钱为目的。连小孩子也想和他做生意。在沈阳的时候,车夫就地起价,李希霍芬不答应,准备解约,于是车夫就使用浑身解数不让他找新的车夫。客店掌柜也趁机多收了李希霍芬钱。在滦州过青龙河(凌源市西南部)的时候,船夫趁船拉到一半的时候多要价钱,价高到李希霍芬这个一向出手阔绰的人难以接受。不过好在当地的官员主动过来帮助他化解困境——李希霍芬眼中,官员经常主动热情地提供帮助。
尽管有种种不满,李希霍芬对中国这个科举制度下的教育大国,还是有比较积极正面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总体的文化水平高于欧洲,最底层的农民也比欧洲农民有文化,但他也指出,中间阶层的学识很低。另外,他认为中国人自大,只承认自己的孔教文化。李希霍芬毫无保留地称赞的,大概就只有中国的耕种技术了。
让很多人意外的是,李希霍芬对朝鲜人评价很好。说他们爱干净、懂礼貌、爱学习……堪称楷模。爱干净方面,他认为朝鲜人是世界上最整洁的民族,比日本人还干净。相形之下,中国人就逊色很多。朝鲜人的礼貌和矜持,主要表现为,对李希霍芬这一行人也表现出足够的敬畏,至于中国人则非常放肆地把他们当成怪物围观,连吃饭都远远地看着。朝鲜人会向李希霍芬一行人请教知识,而中国人对考察团所做的事,则漠不关心。
“差评”都是互相的
李希霍芬给中国人的“差评”,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展开讨论篇幅会比较长,但有一点特别要提到:这种“差评”,是互相的。这不仅有对李希霍芬本人的“差评”,也有对以往接触过的西方人的“差评”。
比如,在青堆子,李希霍芬本想把银两换成铜钱,结果就被断然拒绝。为什么当地人是这个态度?原来,李希霍芬到来的前一年,一个叫“宁”的欧洲人,在这里以买草药的名义行骗,引起了当地公愤。
这不是一个特例,在本溪湖,还出现过欧洲无赖鞭打村民的事情,这也引起了当地人对外国人的敌视。所以李希霍芬旅行到这里时,也颇感害怕,只好在天黑之前离开这里。
这种因为中西接触导致的中西文化冲突,是当时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新问题。要理解李希霍芬笔下的辽宁人,离不开这样的语境和双方的关系。因此,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的中国,并非完全客观的事实,而是旅行者与所接触的文化、族群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