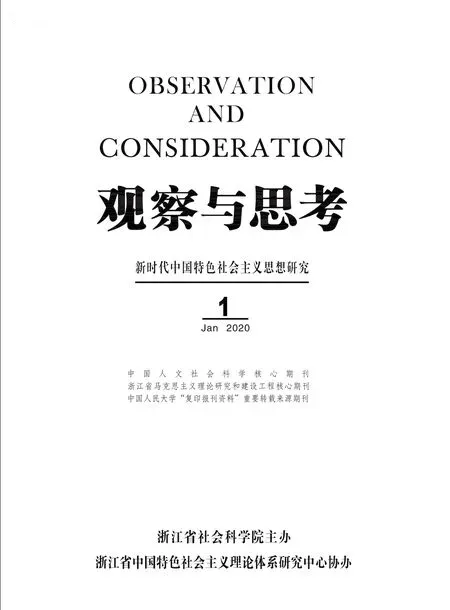从“温州模式”的兴衰回望改革开放40年*
2019-07-14傅守祥魏丽娜
傅 守 祥 魏 丽 娜
提 要:温州是民营经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缩影和前沿阵地,曾以其敢闯敢拼的草根创业精神和独特的“温州模式”名震全国。温州的先行先试与改革开放40年,创造的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样板,更重要的在于其“敢为人先”与“活力民间”的文化意义的确认。新世纪以来,温州经济出现疲态甚至滑坡;当前,必须正视已有发展模式中的短板与陷阱,关注“新常态”下的提质增效与品质发展,助力温州走出暂时的困境,以文化力量推动“温州模式”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温州,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民营经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缩影和前沿阵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温州人勤行天下、商行天下、智行天下,铺展了新时期温州商人成长成功的生动画卷。在外温州人的奋斗崛起,不仅为所在地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更重要的是向全国和世界各地输出了温州地域文化,输出了当代温州精神,输出了温州人率先进行市场化探索的成果,从而为全国各地提供了制度创新的榜样,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温州模式”。早在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曾在访俄时提出要求:“我希望温州要总结经验,抢抓机遇,发挥优势,加快走出去步伐,不但成为‘本土的温州’、‘全国的温州’,更要发展成为‘世界的温州’。”①《习近平访俄首站:温州要成为“世界的温州”》,华语广播网,2010年2月23日。新时代的温州人,主动走出温州、走出浙江、走出中国,已有68.8万人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经商创业,其中38万温商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②参见《电视剧〈温州一家人〉出口中亚背后》,澎湃新闻网,2017年6月14日。
过去40年取得的巨大发展成绩,是中国加大内部治理力度、营造良好政商环境并不断扩大开放、以开阔的胸怀迎接世界的结果。正是有了改革开放40年的坚实积累,党的十九大豪迈宣示继往开来的“新时代”的到来。中国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进入新的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我们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当前,中国更重视的是发展质量,而不是数量;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速;是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全面发展战略,而不是只盯着狭义的经济增长。
一、草根创业的脱贫创举与温州模式的民营典范
温州地处浙东南地区,人口密集,资源匮乏,受到“三山六水一分田”的局限,改革开放前的温州人常常面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境。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放松了对商业经营的管控,灵敏的温州人立刻闻风而动、冒“险”经商、临“危”创业。大多数温州人当时既没有创业资本也没有文化知识,更没有可信的政策保障与“顺气”的社会风习,但凭着不服输与“不要脸”、敢闯敢拼与“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不惧政治风险的劲头,草根创业的温州人率先摆脱了贫困,将温州商人的名号传遍天南海北。这里面的痛苦与辛酸、忐忑与磨难,也许只有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能体会得深入甚至痛彻骨髓。当时,温州选择生产与国有企业具有较强互补性、较低竞争性、较小体制和资本制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取得极大成功。这种产业结构演化创造了“温州模式”。①参见《是什么拖累了温州经济?》,《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3月18日。“温州模式”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形式,使温州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一飞冲天,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温州模式”不仅开创了民营经济的新局面,同时改变和引领社会风气,打破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诸多的陈规旧习,重新焕发了民间活力和创造力,解除了广大民众身上的精神枷锁。40年后回望温州“先行先试”的历史价值与浙江经验,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温州式改革开放,创造的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样板”,最重要的更在于其“敢为人先”与“活力民间”的文化意义的确认。
从整体高度审视,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获得松动进而一点点转向,中间夹杂着许多政治性停滞与经济性反复,任何市场经济的开拓与确立都充满了艰难险阻。而从局部细节来看,任何经济活动的原始积累和商贸细节中都充满了血泪辛苦、旧习突破与福祸难测,包括身体之“过劳”与价值之重构。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人冲破陈规与旧习,尝试做各种生意,有的以捡垃圾起家,有的通过沿街叫卖获得“第一桶金”。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但他们有着灵活的商业头脑。这一时期的温州商人无孔不入,将生产的小商品售往全国各地。他们通过草根创业,让自己摆脱了贫困生活。同时,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存在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为助力民众脱贫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独特的温州经验进而沉淀为具有代表性的“温州模式”并传遍四方。温州模式指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②参见新望:《苏南模式的终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9-161页。敢闯敢拼、敢为人先的温州人,以其独特的商业头脑关注到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小商品方面市场的空缺,在政府睁只眼闭只眼的“不作为”下,他们从一开始采取“戴帽”、合股方式创办企业,到自己开厂售卖,温州产品销往大江南北。温州人从制造、运输成本均低的轻工业出发,以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逐步做大,使全国市场上都充斥温州制造的日用品,甚至全球市场上也多见许多温州商人的身影。1978-2004年间,温州的GDP增速为14.1%,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位居全省首位,创造了省内最脍炙人口的增长奇迹,①参见吕淼:《为什么说“温州危机”正说明“温州模式”生命力?》,浙江新闻网,2017年9月4日。这都是“温州模式”曾经辉煌的坚实证明。可以说,温州模式在全国都打出了响当当的名号,为全国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可供借鉴参考的道路。
温州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源远流长的温州文化,是探求温州当代发展奥妙和未来发展规律的根和魂。之所以能够创造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正是基于温州文化的滋养和传承,基于温州人的识势和善为,是传统优秀文化基因在改革开放时代萌芽、生长、灿烂的结果。继续弘扬“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精神,奋力续写好温州这部创业创新史,让温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自信。
二、高端阙如的发展瓶颈与贫富悬殊的社会时疫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形势几经剧变,温州经济也开始出现疲态甚至滑坡。2004-2012年,温州的GDP增速为10.5%,落后全省同期水平1个百分点,居全省末位。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财政总收入、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多项增幅指标均全省“垫底”,温州经济遇到了诸多挑战。②参见吕淼:《为什么说“温州危机”正说明“温州模式”生命力?》,浙江新闻网,2017年9月4日。从辉煌的“温州模式”到新世纪的没落,是多年积垢所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国内经济形势的转变、早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产业转型滞后、规则意识薄弱、教育重视不足、贫富差距悬殊等现实局限,都在说明温州的老一套已经行不通了。所谓“时移世易,变法宜矣”③语出《吕氏春秋·慎大览》,今人选文名曰《察今》。,温州人更需要严肃审视当前困境与不足,尽早摆脱危机。
其一,是产业转型滞后问题。时代瞬息万变,没有一种模式是能够永远生效的,风靡80年代的“温州模式”面临着转型的困境。早期温州的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人力物力成本低,通过销售量来带动利润。随着经济发展与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下土地成本远高于从前、劳动力工资亦不断上涨。同时,粗放型经济带来的环境污染已经引起政府的注意,对高污染型工厂的整改要求使其艰难求生。温州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不再明显,利润空间逐渐压缩。而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优势产业逐渐从制造业、重工业转移到了高科技产业。光伏技术、电子芯片技术等顶尖技术领域才是各国着力发展的重点领域。但温州在此方面却有“天然的劣势”:温州地处偏僻,技术人才缺失,科研实力弱,对科研的投资力度不足——温州市的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偏低,在省内明显低于杭州等城市。更重要的是,以制造业为根本的温州商人显然对这些高科技也并不怎么“感冒”,他们固守自己的小工厂,不愿意在前期以较大的成本引进技术,只注重短期、眼前的利润。
温州的产业多为纽扣、制鞋、服装等低端制造业,这注定了温州只能在经济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中低端运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低端的利润规模只会越来越小,温州商人将会面临“吃力不讨好”的局面。在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较低的同时,其产业规模也缺乏“质”的内涵。温州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所生产的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产品缺乏核心技术和研发力,趋同现象非常严重。④参见《是什么拖累了温州经济?》,《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3月18日。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在产业结构转型之余,温州商人的集团管理方式也值得反思。温州的公司多是家族企业,公司高层都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自家人”。血缘关系的联结有灵活度高、决策快、信用度高等优势,但家族企业同时是“缺少规范”的代名词。这样的公司大多在细节之处比较含糊、管理上没有严密的逻辑,缺少法制的制衡。要想跟上现代经济发展的步伐,显然规范、法制是必不可少的,如何尽快将现代“职业经理人”制度落地生根是温州商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其二,是规则意识薄弱问题。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市场同样有市场的准入规范。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商人在“规则意识”方面的短板就已经露出了苗头。缺少必要的文化知识,他们在国内外打拼靠的全是厚着脸皮的“硬闯”,亦即“野蛮生长”。虽然靠着草根创业进入了市场,但市场对商人们必然有所规约与要求。规则意识不足带来的危害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愈发凸显。中国“入世”意味着在遵循国内自有市场体系的同时要适应国际市场的规则与形态,而中国商人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放眼当下,中国企业规则意识不足导致受阻的事件仍然存在,最近受到制裁的中兴就是例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加强规则意识,熟悉各国的相关法律条款,对于中国商人、温州商人更快融入世界经济、打开更广阔的市场都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诚信同样是市场顺畅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进入市场的基本规则。
其三,是教育重视不足问题。对教育的忽视在温州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体现。早期的温州商人为了摆脱贫困的桎梏,大多年纪轻轻便外出打拼,读完初中都能算是较高学历。在当时的温州人眼里,有无知识储备似乎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有头脑能赚大钱才算厉害。虽然温州商人取得了今天显赫的地位,但早期知识教育的不足仍然限制了他们的发展,让他们走了不少弯路,导致了温州商人商业经营中规则意识的缺失。
改革开放初期,教育缺失在温州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人们连温饱都是问题,自然谈不上让孩子去接受教育。80年代的温州商人一飞冲天后,开始关注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同时,早期原始积累暴利阶段的结束让他们意识到今后经济发展中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大量“不差钱”的温州商人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送到国外留学。知识教育跟上了,家庭教育却不容乐观。大多数的温州商人有钱将孩子送进名校,却没有时间和孩子交流相处。父母陪伴的缺失、金钱的过分滋养等使得温州的新一代在心智成长上仍不健康,金钱能带来富足的生活,却带不来幸福的家庭生活,更培养出不健全的儿女。
其四,是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用“先富带动后富”,但这一美好愿景实现起来却相当困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温州商人在经济上率先富起来,但理应“后富”的一批却没有跟上。在温州,富裕的只是开厂办企业的大老板们,普通市民和乡下农民却没能搭载上这一班快车。温州富人真的很富,而穷人也的确很穷,许多乡下的农民依然过着传统耕种的日子。仅在温州内部,瑞安乐清等城市和文成、泰顺等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天差地别。商人与普通人之间、温州各县市间的贫富悬殊制约了温州城市化的整体发展。
另外,靠着敢闯敢拼的劲儿,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温州模式”名声在外,令无数国人慕名而来,而实际上温州市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水平与其响当当的名头却不匹配。提起温州,大家的印象都是“有钱”,人们确实可以在大街上看到各种飞驰而过的豪车,在温州的消费高水平中感受到“有钱”,但是这样的富裕却没能转化为温州城市发展硬件和软件上的领先,譬如与三线小城市几无差别的主城区、横冲直撞的公交以及狭窄的道路规划导致大范围堵车与急刹车等。而且,大批温州企业、大量民间资本投机性地转入矿产资源、房地产、造船和金融投资等资金密集型行业,导致了本地的“产业空心化”。①参见《是什么拖累了温州经济?》,《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3月18日。
结语:温州模式的提质转型与品质城市的文明自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闭塞到开放、再到扩大开放的社会巨变。中国经济的发展腾飞离不开千千万万温州商人,是他们的敢闯敢拼、勤劳奋斗、屡挫屡战造就了被称为“民营经济典范”的温州模式。同时,我们也应该正视已有发展模式中的短板与陷阱,关注“新常态”下的提质增效与品质发展,助力温州走出暂时的困境,瞄准高端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注重短期收益而不愿做长期投入、关注来钱快的生意却忘记了社会责任,温州人需要反思的是自己的“短视”问题。不能仅仅看到眼下炒房带来的高额收益而不顾对房产市场造成的混乱,不能仅仅为了投入产出的最大比就将资金无限流向其他投资。促进自身企业转型升级,提高设计创新能力,提高产品竞争力,才能实现稳妥发展。同时,也要看到自身发展和城市反哺的紧密相连,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了,才能为企业带来更好的服务,促进企业的发展。温州商人甚至全国的商人都需要“负重前行”,将商业诚信、家庭道德与社会责任作为行事的准则,展现新的“契约精神”与“市场伦理”。
面对曾经的辉煌和当前的窘迫,小富即安抑或临渊羡鱼都不足取,直面危机与奋起直追才是正道。如何深入细致地反省“温州商人”“温州模式”与“温州文化”的优劣得失成为当前温州“再出发”和“再领先”的理论门槛。当前总结反思温州的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独具特色的“温州模式”,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参照维度:一是相比于倾全国之力和政策优势而成功的“深圳速度”与“浦东模式”,“温州模式”的特色在于民间的“自发”与乡镇企业的“活力”,而其相应的内在劣势就是工业与商贸的“小—散—低”,灵活有余而大气不足、投机取巧多而朴拙坚守少、善于铺摊子而难于做高端。二是走进“新时代”后的国内国际形势已经与此之前完全不同,“温州模式”要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必须设计出超越性、前瞻性的整体战略,让暂时的滑坡与垫底转化为“后发优势”,以适应甚至引领生态文明转向、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特色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等。当前,“两山理论”引领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温州有天然优势;经世致用传统里的品质城市创新,温州欲弯道超车。温州发展的目标与核心就是在新时代里再度领先。如果温州模式的辉煌在于胆识,那么命运共同体时代的关键是抢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
简言之,温州的提质转型还须深度的文化自觉,从温州文化、温州精神、温州品质切入全面思考温州经济发展和温州模式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发展阶段、文明自觉层面上探索与时俱进的“温州模式”的创新发展,是一个事关温州品质前途的重大课题。我们要立足新的时代背景、顺应新的发展潮流,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保持文化自醒,回归文化本源,进一步传承温州文化底蕴,弘扬温州精神与品质城市战略,在行政理念、改革精神、创新文化、开放气度和城市内涵等方面查补短板、厚植优势,以更加厚实的文化力量推动“温州模式”再出发,不断注入新的内涵、新的活力,特别是以文化理念的创新来构建动能强劲的经济生态,以文化内涵的植入来构建品质卓越的城市生态,做好传承、塑造、谋划“三篇文章”,彰显城市历史底蕴、现代气派、宏大格局,最终实现新时代温州的制度之变、模式之变、动能之变,以实际行动助推温州再造新优势、再创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