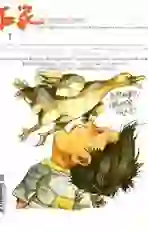魔鬼的恐惧亦是我们的恐惧
2019-07-08李振
李振
一个人硬生生地杵在那里,你很难对其视而不见,他在呼吸,在咳嗽,弄出种种响动,散发着烟气或者其他什么味道,他让周围的温度升高0.01度甚至更多。你不觉察,他还是杵在那里,也许这就是所谓存在,他是他的,与别人无关。而存在感就麻烦了,它多多少少逼着人跟外界发生关联,微妙,啰唆,让人心生厌恶又不算不上什么罪过。双雪涛的新作《预感》和《剧场》是两篇很不一样的小说,一个面对的是天外来客,一个要架起摄像机拍下晨练的大爷大妈,这分明是天上与地下的距离,但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若隐若现的勾联,仿佛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突然闯到你面前,结果周遭一切都需要重新证明。
《预感》来得毫无征兆,就像李晓兵突然跟妻子提出单睡。生活自然有它的琐碎和越解释越不清爽的尴尬,但妻子这次很识趣地给他铺好沙发,便从小说里隐去了。李晓兵是谁可能不重要,尽管他目前是个“用中文写作的顶级科幻作家”。而妻子方灼是谁却很重要,她是“市城建局的一个副处长,在外面相当能事儿,白酒能喝一斤多,说话还不走板,家里外面面面俱到,只有一点问题,就是凡事爱穷究竟,口头禅是你给我一个理由”。方灼的重要不在于她能喝或能干,而在于她成为了李晓兵的一个来路。因为方灼的存在,当然也包括他们多动敏感的儿子李大星,证明着李晓兵是个实实在在浸泡于日常生活里的人。但是,预感的来临让他决定一个人面对。于是,小说迅速变成李晓兵的个人史,五岁、十二岁、二十七岁三次类似预感的出现以及相应而来的事件不但预示着它的准确,而且因此成就了今天这个作为科幻作家的男人。因为预感的来临,李晓兵的日子似乎过得更为随性,尽管不知那将是什么,但反正躲也躲不掉,也就有了半夜独自前往郊外夜钓的兴致。
夜钓不仅钓上了鱼,还钓上了人。这个从水里走出来的男人自称安德鲁,来自几百光年之外的星球。他说我是来杀你们的,S市的七十多万人都活不了,因为这里有人偷走了他祖先的一句话。由此,小说似乎完成一个由情节推动到语言和逻辑推动的过渡,因为场景被固定下来,李晓兵和安德鲁就那么紧张、拘束又看似不着边际地进行着一场语言的较量。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紧迫的前提,那就是天亮之前李晓兵必须帮安德鲁找回那句话,否则全市的人都要遭殃。与其讲小说自此具有了科幻的色彩,不如说它更多地带上了先锋戏剧的影子——一个人如何承载着死亡的威胁去寻找一句丢失的话?令人庆幸的是,安德鲁还讲一些地球人的情理,或者说小说依然运行在现实的逻辑里。他给了李晓兵一些机会,承认地球上的名词和动词,甚至让李晓兵在想到方灼和李大星呼呼大睡不知自己将被外星人引来的大水沉没时,忽然理解了安德鲁这个某星球最后一名幸存者还惦念着祖先的遗憾,“在死之前,开着破旧的飞行器来到这里,谋求某种正义”。几经波折,包含着偶然、猜测和推论,小说几乎布起了一场同义词与反義词的迷魂阵,当李晓兵说出“魔鬼害怕他不存在”时,安德鲁如释重负般地跳进湖里,连同湖水和周围的小山不见了。
安德鲁是魔鬼吗?也许是,至少他具有将整个S市淹没的能力和决心。但双雪涛并没多写他的诡诈或残暴,反而不断提示着他的无助和窘迫。“他的鬓角有白发,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穿多久了,让雨水一淋,像过期的蛋糕一样更加显得不成样子”,身心俱疲也会不自觉地睡过去。这时的安德鲁不像魔鬼,他只是个可怜的愁苦人,千里迢迢来到地球,仅为寻找一句话。不管他算不算得上魔鬼,可以肯定的是他也害怕不存在。他是个高贵的邮差,像他的祖辈和父辈一样,丢了一句话就等于丢了一封信,也可说是丢了自己存在的证据。这显然不是一个仅存于外星球的命题,它同样潜伏于地球人李晓兵们身边。事实上,它更关乎存在感而不是存在,它像是一种卑微到需要别人来证明的心灵慰藉。小说借助安德鲁写出了它的重要、荒诞和不可靠。人们不计成本地去寻找和确认,就像安德鲁满身狼狈来到地球。但可笑的是它仅仅是语言,这不是因为安德鲁们“对文字特别敏感”,而是这种感受的呈现往往只是语言的结果。它是实在的,那种感受就像语言或文字一个一个地钉在那里,但它又是虚无的,它没法自证存在,如同魔鬼唯独害怕自己不存在。安德鲁手中的那封信,将这种矛盾呈现得尤为剧烈。那是一个士兵写给恋人的信,“不出意外的话,三天内我就会死”,而就在士兵写下这封信的一刻,恋人能否读到它也无从知晓。事实是当邮差安德鲁成为星球最后一个幸存者的时候,这封停留在他手中的信根本不能送达。那么,一方面是坚如磐石的确信:“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就算死了,也会一直存在”;但另一方面,是这种确信最终没能实现有效的传达,信无从投递,恋人也无法阅读。只有当安德鲁违背了他的职业操守,或者说某种外部的力量打破了信这一存在本身的逻辑,它所承载的意义才被呈现出来。这个过程既是一种来自外部的确认,又让事情本身带有了不可回避的虚无。而更加微妙的是,信中所描述的爱情“就像所有不可描述的秘密一样,没人知道其存在,也没人为其消失而悲伤,除了我们自己”——这几乎构成了对魔鬼执着地寻找一句丢失的话最终却发现这句话是“魔鬼害怕他不存在”的浪漫演绎。
双雪涛在《预感》里将一种普遍的存在与存在感的博弈以夹杂着幻想与狼狈现实感的方式呈现出来,他把某种形而上的追问十分强硬地安插进一个普通人、一种普遍的生活里。这种强硬让小说自身产生了内部的映照,它在安德鲁的故事里实现了自我循环与佐证,而天外来客的方式看似某个外部的力量触碰了小说人物安逸又略显无趣的生活,不如说是它带着既有的前提与处境介入到那个从天而降的寻找与追问之中。在此,李晓兵与安德鲁构成了力量悬殊却至关重要的映照,那琐碎的、并不一定有理由的日常生活与预感,有关存在的追问,乃至遥远的外星又形成了微妙且带着现实投射的奇异张力。
如果说《预感》是对存在充满想象又十分直白的表达,那么《剧场》则显得更为含蓄而富有现实感。《剧场》里,一切都是具体的。大学毕业,“我”回到L市电视台工作;电视台有五个频道,“面向市内的二百万人口和卫星城的三十万人口,统领共计二百三十万人的文娱生活”;早年家里的饭菜是“芸豆炖粉条,小白菜汆丸子,早上一碗鸡蛋糕”;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枚大金镏子,“泛着铜光,上面还有几个牙印”……这种具体背后是时间上不断重复,人和人之间不断重复的平静、乏味到令人恼火不起来的每一天的生活。这个时候,好像应该有点冲击,但双雪涛就那么抻着、靠着,让“我”在电视台旁边租下了一套绝大多数时间见不到阳光的房子,让“我”去劳动公园拍老人晨练的镜头,那些老人也就在镜头前拖沓又异常心安理得地或练或唱起来。可是,“我”的心思完全在镜头之外,他想到了那张毕业之后每天坐地铁游荡只为花光钱扔进垃圾桶的地铁卡,想到了大三那年筒子楼燃起的一场大火,还想到了自己在筒子楼的邻居曹西雪。小说在晨练的场景与“我”的回忆之间任意切换,更准确地说那根本不是回忆,而是穷极无聊之时任凭一些杂七杂八的片断在脑子里更加无聊地滑过。它对于“我”来说是无效的,连打发时间都算不上,但对小说来讲却很重要,因为这就是“我”以及不知多少“我们”所面对的或者不愿意面对的时间的内涵和存在的形式。双雪涛死死地拽住小说的进度,让它卡在那个无聊、空洞又杂乱不堪的时间里,这既是小说情节能够推进的精神背景,又是小说节奏与情绪积累上不动声色的压制和酝酿。它几乎让人听到双雪涛在小说对面挑衅又带着嘲讽的声音:无聊吗?继续吗?还绷得住吗?那么好,曹西雪的电话可以进来了。然而,曹西雪的出现又伴随着新一轮的叙事绑架。这时候,不见得有多少人在乎她“脖子长,腿短,屁股大”,是不是“像一只鸭梨”,但双雪涛还是要这么写,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想让人能在这篇小说里爽一下。二人相见,曹西雪话多,“我”的话少,曹西雪都是真话,而“我”就不一定了。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无论是对话,还是两个人的关系,就像大马路上错车,过去也就过去了,没人愿意细掰扯。
小说就这么一点一点消磨着人们的好奇心,直到“我”重新回到那座梯形房子。房子里,曹西雪正带领六个盲人在排戏,“每周二和周三,我用车把她们接来,十点之前把她们送回去,周日她们去教堂做礼拜”。这事很荒唐,“我”也觉得荒唐,但这并不妨碍曹西雪就这么做了下来,当然也不妨碍丢了工作的“我”真就给她们写了一出戏。剧本的一幕完整地嵌插在小说里,毫无征兆,也毫无过滤,比安德鲁的来访还要强硬。剧中,长袍男子奔赴被瘟疫吞没的故乡,路遇六个盲女,他将她们救上船,开始听她们讲L城的故事。据说L城的瘟疫源自一场大火,但大火的起因却有不同说法,重要的是她们都说自己就在现场。在一连串类似七宗罪式的陈述过后,其中一个盲女提示“别忘了,我们每人眼中都钉着一个游魂”。她们莫名唱起歌来:
大海黑黢黢,风儿送低语
魔鬼在人间,地狱空荡荡
天火烧不尽,吾等筋骨躯
大雨浇不灭,尔等贪嗔相
游子少离家,归时一张皮
相逢不相识,唯有泪两行
儿时天落雪,母姊给汤碗
而今鬓斑白,无处把身藏
去时怀心属,归来似尘土
谁能如草木,一歲一相忘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
歌词的末句应和着曹西雪带领盲女们排演的《暴风雨》,戏中的大火何尝不与当年筒子楼里的大火存在某种诡秘的关联?整首歌唱的就是剧中人的处境与心思,但这又如何不是“我”和曹西雪所面对的生活?剧中,长袍男子问盲女,此时去往L城会如何,盲女答“去则死,返则生”,而他毅然下令全速前进。所谓“所有过往,皆为序章”可能就是向死而生,可能就是到远方,到一种不确定中去寻找存在的证据。实际上,梯形房子、盲女和戏剧就是曹西雪的远方,而一度置身故乡的“我”也终于决定离开。但在小说结尾,那座梯形房子已经被拆掉了,这时的曹西雪又将到哪里去寻找“救自己的方式”呢?那个房东的话很有意思:“北京有什么好呢?走起来停不住的,回头又要去纽约,又要去月球了。”如果所有过往皆为序章,那么存在或存在感就成了一个不断告别、不断找寻、不断怀疑又不断确认的过程。
《预感》和《剧场》各有各的侧重与写法,但它们在深层里带着一种相通的、源自现实处境的疑惑和忧虑。无论是《预感》中的李晓兵、安德鲁,还是《剧场》中的“我”或曹西雪,他们都与自己所在的环境存在着某种疏离,这种个体的孤独既是一种选择,又是一种宿命。它让人产生了面对自我时的焦虑,让人不可避免地为之寻找一个可以确定的或者至少能够自我安慰的来路和所在。它无疑是源自个体内部的巨大力量,向内的思索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宏大的精神圣殿,成为抵御外部世界的坚固堡垒,它是所谓希望,据说可以左右生命、征服死亡。但是,它又先天带有无法克服的虚无,它的强大伴随着致命的恐惧,它害怕它不存在,害怕那个为之提供力量的前提本身就是一个黑洞。这种恐惧或忧虑潜伏在所谓希望或寻找体内,不经意间就会探出头来,就像艾略特在《荒原》中面对活生生的、川流不息的人群,“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许多人”。在这个层面上,魔鬼的恐惧亦是我们的恐惧,双雪涛把这种恐惧以及为之付出的寻找与代价安置在小说里,但其中充满了犹豫和迟疑,他将探索的过程和结果放在一个凭空降落的圈套中,而对于当事人或者我们放任自流,毕竟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责任编校 王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