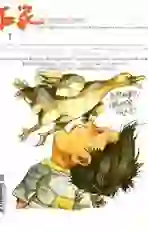吉狄马加《火焰与词语》美国版序
2019-07-08弗兰克·斯图尔特曹明伦
弗兰克·斯图尔特 曹明伦
我初识吉狄马加是在2016年夏天,当时我应邀去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去讲中国诗歌在西方国家的出版发行问题。文学院有一幢现代化的红石墙大楼,大楼周围环绕着一条林荫道,林荫道旁塑有中国和其他国家著名作家诗人的铜像,铜像和真人一般大小。大楼内的廊厅墙上装饰着刻有各国文豪头像和简介的纪念铭牌。一幅以鲁迅头像造型的巨型镂空挂帘从高高的廊厅天顶垂下——鲁迅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近现代作家之一。
吉狄马加和我在一个与廊厅相通的房间里共进午餐,同桌的还有几位中国翻译家、出版商和学者。吉狄马加五十余岁,膀阔腰圆,面部线条柔和,大方框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在接下来与他相处的两周里,他衣着随意,总是穿着长袖格子衬衫和长裤。吉狄马加是中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也是身居高位的中国少数民族的代表,但他从不装腔作势,而是诚挚热情,和蔼可亲。
吉狄马加是彝族人。彝族是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也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约有九百万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0.6%)。彝族分为上百个支系族群,如诺苏、黎波、聂苏、阿哲等。吉狄马加所属的诺苏族群是其中最大的族群。
在北京初识几天后,我们又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重逢。这座城市位于青藏高原东侧边缘地区,在四川省西南部,西距云南省的香格里拉500公里,离东北方向的北京有2500多公里。
凉山是彝族文化的中心地区,吉狄马加就在这里出生并长大。西昌的大多数彝人都说彝语,这里有彝文报纸、电台广播、卡拉OK酒吧,父母还可以送孩子上彝语学校。许多个世纪以来,彝族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习俗和社会结构。地处边远,交通不便,这也有助于他们保持其生活方式。直到近年,偏远山区的很多地方还只有土路,一到雨季就泥泞难行。不过,随着新建公路的延伸、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进行,彝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在悄然变化,逐渐受到凉山其他许多现代化地区的影响。
西昌城周边是中国西南风景最美的地方之一。附近的邛海就是这种美的极好体现,邛海位于芦山脚下,是一个水域面积约30平方公里的大湖。一天傍晚,我在湖边宽阔的木质便道上跑步,看见身旁有不少漫步休闲的市民,有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妻,有白发苍苍的男女老人,还有人悠闲地骑着自行车。木质便道架设在环绕湖岸的湿地上方,满目青翠的湿地引来了不少白鹤、苍鹭、燕子和其他许多野生鸟兽。邛海景区每年有八百多万来自外乡的游客,这使西昌的酒店和商店生意兴隆,各种节日活动热闹非凡。加上60公里外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生态旅游为政府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提供了助力。
高科技的航天中心与周围美丽的大自然相互衬映,这正是该地区现代化与彝文化传统习俗碰撞的象征。在《火焰与词语》这部诗集的许多诗篇中,吉狄马加都表达了对这种碰撞的忧虑。他是个思想者,常凝思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问题。在第一首诗《自画像》中,诗人拥抱他作为彝人的身份,拥抱他那由彝人祖先滋养的灵魂。他在诗中写道,正是在这片雄奇的土地上,他像“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与他的民族血脉相连。但在后来写的《分裂的自我》一诗中,他又表达了对内心处于分裂状态的焦虑——那些冲突的自我困于被他稱为的“殊死的肉搏”中,一边是“呈现太阳的颜色”的苦荞麦地,另一边是回荡着钢铁碰撞声的陌生城市的高楼。在《自画像》一诗末尾,诗人提出那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你是谁?随后他再次宣称:“我——是——彝——人”。但他是一个成人后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都市的彝人,正在目睹城市向他成长的山区扩展。
吉狄马加于1961年出生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乡下。他家乡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在海拔2400米以上的山区。从青藏高原源源不断流下的雪水汇成湍急的河流,如穿过高山峡谷流经他家乡的安宁河与金沙江。他在昭觉县一直生活到十七岁,然后去成都就读于西南民族大学,在那里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和现代世界诗歌。大学毕业后,他开始在四川一些文学杂志上发表诗作,随着中国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新时代,他迅速成长为20世纪80年代那批志向远大的青年诗人之一。当时中国的民族政策有所改变,政府开始鼓励少数民族认同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还鼓励中国公民走出国门,融入国际社会,向其他国家学习。当代诗歌在中国比以往更受欢迎,四川也成了中国的诗歌重镇之一。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诗人一样,吉狄马加既从中国古典和现代诗歌寻求灵感,又从世界诗歌吸收营养。此外,他常常书写彝族的文化遗产,宣示自己的彝族身份。
1985年,吉狄马加的诗集《初恋的歌》获得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这使他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在其后出版的几本诗集中,他继续书写彝族的民族性,涉及的主题有男女爱情、家庭亲情、祖先崇拜,以及对凉山那片土地和彝族历史的眷恋。作为诗人,吉狄马加摈弃了现代派的反讽和当代的先锋试验,努力让彝族诗歌在世界诗歌舞台上有其独特的位置。不久后他被调往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并开始参加国外的诗歌活动。尽管他已是中国的著名诗人,这样的活动还是让他大开眼界,使他对自己的诗歌和别国的诗歌写作都有了愈发开阔的国际视野。他开始在国内外组织大型国际诗歌节和诗歌会议。在这些活动中,他得以与外国诗人和翻译家面对面交流,这些诗人和翻译家都很欣赏他的诗作,并积极促成这些诗作在自己国家翻译出版。于是吉狄马加在近些年已广为世界所知,陆续获得了英国、波兰、秘鲁、南非、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颁发的诗歌奖项。他同时还担任过政府官员,曾一度出任青海省副省长。他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代表。
经过多种工作的历练,吉狄马加在诗中以多种身份说话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有时会用高亢而严肃的声音对全人类说话,劝诫大自然的剥夺者,祈求世界和平与相互理解;有时他又会为诗辩护,坚称诗是危机时刻灵魂的避难所。他经常讴歌那些有英雄情结的国际诗人,他敬重那些诗人的英雄主义。但《火焰与词语》的中心是他重点书写的彝族人民。他维护他们的基本尊严,呼吁保护其创世神话、传统习俗和民间信仰,宣称他们有权在“世界最古老民族之林”占有显著的地位。当他以这种方式发声,呼唤英雄祖先的回归时,他的语调往往是忧伤的、怀旧的,很少有祈使的意味。吉狄马加可以气贯长虹,但他诗歌的基调显示他是一个温和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温和常清晰地显现在他写音乐、孤独、血缘亲情和自然之美的诗篇中。
吉狄马加的诗歌根植于彝族文化,对《火焰与词语》中涉及的文化背景稍加介绍,也许会有助于英语世界的读者阅读这部诗集。比如在《自画像》一诗中,诗人就追溯了自己的血缘——也是所有彝人的血缘——源于彝族创世史诗中传说的英雄支呷阿鲁。支呷阿鲁生于天地相交。相传他诞生之前,他母亲濮嫫娌伊在室外织布,看见一群龙鹰在头顶盘旋,随之滴下三滴血,溅落在她裙子上,使她即刻怀孕,当晚就生下了半是龙鹰半是人类的支呷阿鲁。支呷阿鲁由龙鹰抚养,很快就长成了一名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强壮武士。他一生建立了许多功勋,比如射掉多余的太阳和月亮,以免大地被烤焦,人类无法生存。在另一个传说中,他制服了捣毁人间灶台的雷神,从此炊烟又可以飘向天空。
《自画像》还写到传说中一个名叫呷玛阿妞的美丽姑娘。呷玛阿妞是女性坚贞不屈的象征。据史诗讲述:美丽的呷玛阿妞早已与恋人安哈木嘎订婚,但汉族官府的一位老爷被她的美貌吸引,要将她占为己有,她外逃躲避,但终被官兵抓住。阿妞不从,被囚入牢房(也许就在西昌)。率人来救她的木嘎被官兵杀死。官府老爷百般折磨呷玛阿妞,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她向狱卒谎称要用五色丝线装饰头发,好面见官府老爷。然后乘狱卒不注意,将丝线织成的彩绳,套上自己的脖子,含愤自尽。
在其他诗篇中,吉狄马加呼唤河流、动物和祖先,赞美体现彝人及其文化之精神实质的日常物品,描写彝族的仪式、节日、农人、猎手、妻子和寡妇。他始终强调舞蹈、音乐和乐器的重要作用。
口弦是彝人的身份标志,口弦声几乎响彻了整部《火焰与词语》,口弦也是最后一首诗的主题。典型的彝人口弦由长约三寸,宽约五分的薄竹片或铜片制成。在《口弦的自白》一诗中,口弦的簧片形如蜻蜓的翅膀(译者注:把口弦簧片描写成“蜻蜓的翅膀”实际上见于《做口弦的老人》一诗)。传统上,口弦是彝族女性的乐器,用一根线串起来挂在胸前,就像诗中写的“睡在她的心房旁边”。口弦能够发出或粗犷或哀伤的声音,可以表达悲哀、思念、幸福等情感,甚至可以讲述故事、伴奏舞蹈、奏出悲歌和悦耳的颤音。曾有一天,我在一个彝村听彝族男女演奏口弦,小小的乐器竟能发出那么震撼人心的声音,令我感到十分惊奇。
就在那同一天,我听见一位彝族女性站在旷野用抒情的女高音对着树林、山峦和峡谷歌唱。随着轻微的山风,她那纯净而伤感的歌声似乎会传到数英里外,传到远方田野里牧人和农夫的耳中。
舞蹈对彝族的重要性尤见于庆典,比如仲夏夜的火把节。在西昌,人们从偏僻的村寨赶来,围着熊熊的篝火,手拉着手载歌载舞。老人讲故事,年轻人约会,女人穿着绣有红黄蓝黑色艳丽图案的盛装:长及脚踝的百褶裙、刺绣精美的大襟衣、羊毛织成的披衫、工艺繁复的帽子或头帕,以及嵌有血红玛瑙和其他宝石的银饰。农民从偏僻的山寨把公牛赶到城里,牵到备好的斗牛场上成对相斗。两头公牛用角互相顶撞,有时会斗得异常惨烈,直到一方落荒而逃。就像《死去的斗牛》一诗描写的那样,获胜的公牛会每年都来参战,直到被打败为止。如今,火把节上的斗牛表演已成了吸引游客的一项精彩活动。
吉狄马加的诗中充满了对动物和自然的敬畏之情。对彝族具有文化意义的另一种动物是麂子,一种体型较小、犄角较短、在民间传说中会变形的鹿科动物。麂子把野生动物表现的灵性拟人化了。在《秋天的肖像》一诗中,麂子作为土地的梦而出现,而在《夜》中,麂子又因为缺席而被提及。在后一首诗中,猎人也是缺席的。在吉狄马加的许多诗篇里,猎人都象征着家庭和族群的理想领导,如果诗中的猎人死去,则表明社会结构的瓦解。
《火焰与词语》中的其他诗篇写到了恋爱、求婚和对父母的愛——尤其是对母亲的爱。恰如全世界的民俗诗都会感怀一样,吉狄马加也会理直气壮地多愁善感。在《初恋》一诗中,年轻的主人公想要引起一个像蜻蜓一样难捉的漂亮姑娘的注意。一群少男少女“在树下捉迷藏”,“在月下‘抢新娘”,他们尚不能体味求爱的激情。游戏模仿成年人的婚俗:新郎要“抢”新娘,然后骑马一起逃走。但在《初恋》一诗中,男孩的母亲没法让孩子明白他心中那种神秘而朦胧的情愫。
在北京的一个晚上,我参加了吉狄马加的生日晚会。被朋友、同事、妻子和孩子们簇拥,他头戴一顶金色纸制皇冠——汉堡王快餐店赠送的那种。孩子们也都戴着晚会纸帽,兴高采烈地在桌子间追逐,跳跃,舞蹈。生日蛋糕切分了,礼物也都打开了。吉狄马加保持着他非凡的平静,始终微笑着面对他的客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我开始觉得,在今天这个不同价值观相互冲突的世界里,吉狄马加仍能保持其坚定的信念,是因为他心中充满真诚的希望,这种希望正是他诗歌的源泉。在英国剑桥的一次演讲中(讲演稿全文见本书附录),吉狄马加对听众讲到了全球化,讲到了艺术,讲到了灵魂,但他也讲到了自己矛盾的心境。他说:“令人欣慰的是,正当人类在许多方面出现对抗,或者说出现潜在对抗的时候,诗歌却奇迹般地成为人类精神和心灵间进行沟通的最隐秘的方式,诗歌不负无数美好善良心灵的众望。”
(弗兰克·斯图尔特,1946年生,当代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夏威夷大学教授,1986年度怀廷作家奖诗歌奖得主,曾出版诗集评论集多种。)
责任编校 王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