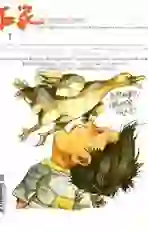预感
2019-07-08双雪涛
双雪涛
这天晚上李晓兵跟妻子提出要单睡,妻子感到很不理解,希望李晓兵给出一个理由。李晓兵想了想说,没什么理由,就是想睡沙发。妻子说,我打呼噜?李晓兵说,不打。妻子说,你觉得热?我发热?李晓兵说,没有,你一直很凉爽,而且家里有空调。妻子说,那你为什么要单睡?孩子此时已经睡了,李晓兵的儿子叫李大星,七岁,多动且敏感,一言不合就记在心里,等待日后随时拿出来证明大人的出尔反尔,但是晚上睡觉并不折腾,一旦睡着,一宿不动。李晓兵说,我讲不出理由,可不可以没有理由,让我现在去睡觉?妻子沉默了几秒钟说,好吧,我把沙发给你收拾一下。李晓兵的妻子名叫方灼,是市城建局的一个副处长,在外面相当能事儿,白酒能喝一斤多,说话还不走板,家里外面面面俱到,只有一点问题,就是凡事爱穷究竟,口头禅是你给我一个理由。李晓兵就怕这个,一旦方灼说出这句话,他就头脑发蒙,本来有理由的事儿也变得没了理由,况且生活里很多事情,本来很有理由,一旦把理由说出来,理由就像氧化的半拉苹果,马上不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天晚上,方灼并没有和他较劲,原因很简单,方灼了解李晓兵,李晓兵话不多说,也不是个爱提要求的人,一件衣服能穿三年,吃饭也不挑食,只要不是馊的,都能吃。他想单睡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时间也晚了,你让他给出一个理由,对两人的睡眠都不好,第二天她早起还要陪领导出行,需要养精蓄锐,于是方灼铺好了沙发,茶几上倒了一杯凉开水,自己去卧室睡了。
李晓兵躺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书,不困,客厅里十分安静,窗门紧闭,家具各安其位。他在厕所里蹲了一会儿,出来之后感觉有点意思了,马上关灯躺在沙发上,把眼睛像书本一样合上。不困。李晓兵说话不多,不是因为没有话,是因为把话都写在了书里。他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写得不错,这么说有点保守,应该说是用中文写作的顶级科幻作家,但是一是因为生活在小小的S市,和文坛疏远,所以名不配实,二是性格上比较封闭,所谓名满天下,对他来说没什么了不起,不就多几个不相干的人吗,也不是家狗还可以随时调遣。三是虽然他是个内敛的人,但是相当狂妄,他觉得击败现在市面上的科幻写作者是题中之义,這一点狂妄使他有点孤独,从另一个层面也保护了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第三点和第二点有点联系,狂妄的人总能自娱自乐,因为才华就是朋友。
2018年8月8日的晚上十一点左右,科幻作家李晓兵正在竭力钻进自己的睡眠里,他换了好几个姿势,又抽出了枕头,并没有多大的起色。S市是一座北方小城,人口只有七十多万,原先没有这么少,很多年轻人都走了,路上鲜见婴儿。这城市入了暑之后有几天极热,好像要向漫长的寒冬示威一样,证明四季的必要。这几天不但热,还下雨,每天一阵一阵地落雨,每一阵都不大,也不能减去一点酷热,反倒水汽浮起,贴人的皮肤,把热又物质化了一点。现在来说李晓兵为什么要单睡,且给他理由一个,因为这天早晨起来他便有一种预感,预感到会有事发生,虽然他和方灼在一起生活了八年,和李大星一起生活了七年,但是预感来临的时候,他还是想一个人面对,虽说预感不是十分确凿,也正是预感的特点。对于他来说,预感并不是第一次来,在他三十五年的人生里来过三次预感。第一次有了生事的预感是在他五岁的冬天,他作为独生子躺在家里的炕头上,正在发高烧。那时他家住在城郊,白天父母上班,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太负责看护他,给他喝水,喂他吃饭,其余时间就把插满糖葫芦的木束摆在他家门前的空地上,正常做生意。他在迷迷糊糊中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要来,不是走来,跑来,而是飞来,他想告诉老太这种感觉,可是嘴巴像给什么镶住了,老太以为他睡了,在偷吃他家炕柜里的饼干,那饼干又黄又圆,和几个果丹皮放在一个同样圆的铁盒里,老太吃得口干,去高低柜上拿凉开水瓶。他张嘴想说,水瓶的位置不太好,那玻璃水瓶就像是一块磁铁,像一只扭动在鱼钩上的蚯蚓,像一只吃饱喝足的羚羊,这时一颗子弹穿窗而过,打中了水瓶,水瓶如释重负一样喷散开,玻璃碴子像火星一样飞出,嵌入老太的脸中。这子弹从哪里来到最后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来要,要也找不见,因为子弹从另一扇窗户飞出去了,不知飞向哪里,又打中了谁,什么时候落地。除了他以外,没人看见这颗子弹,水瓶毫无疑问是自己爆炸了,也许是老太的手太热了,也许是早有了暗藏的裂纹,李晓兵多少有些愧疚,他因为自己的幼小而自责,要不然可以走过去把水瓶或者老太移开的。
第二次预感是在他十二岁,小学刚刚毕业,爷爷因病辞世了,他还不懂得悲伤,而且和爷爷见面也少,交流也少,爷爷从他八岁开始,就卧床不起不会说话了。出殡那天他一直瞄着他的表妹,表妹比他小一岁,却长得比他高,穿着扣带儿的凉鞋,脚指甲涂了红色的指甲油,俨然是一个少女了。他很想跟她玩耍,最好是追逐,一个跑前一个跑后,但是葬礼的气氛相当肃穆,爷爷的几个儿女都围着遗体号啕大哭,父亲是一个钢铁一样的男人,面无表情,等着别人哭完,好进行下一个程序。他忽然感到有什么东西要来到这个告别室找爷爷,他的眼睛离开了表妹的脚脖子,看着门外。爷爷是抗美援朝的老兵,是不是他的战友?还是他的仇敌?或者他在朝鲜时有个不为人知的儿子,说着朝鲜话一路找来?还是死在他手中的哪一个年轻的游魂?这时从门外飞来了一只蜻蜓,又大又黄,飘摇自在,左晃右晃,轻轻地落在了爷爷的脸颊,蜻蜓跟爷爷说了一句什么话,爷爷无动于衷,蜻蜓又说了一句什么,爷爷的耳朵和嘴角缩动了一下,他吓了一跳,他回头看妈妈,妈妈因为起得早,这时有些昏昏欲睡。哭声的高潮已经过去,扬起的手也已经落下,爷爷的遗体突然从停尸台上翻落下来,脸朝下摔在地上,所有人都大叫一声,赶紧把爷爷再搬上去。他看见蜻蜓这时飞走了,摔了一跤的爷爷和刚才的表情已经有所不同,他的下巴松动了,露出了里面早已放好的一个假元宝,他知道爷爷已经把他想说的话,想承认的事情说了出来,原来紧绷的脸也平整了。他忽然感到表妹的脚丫并没什么意思,人要活这么久,肚子里要装这么多事,费劲巴力,死就在一瞬间,了结所有漫长的活,所有爱和牵挂。一股困意袭来,他在妈妈的怀里睡去了。
第三次预感是在他二十七岁第一次写小说的时候,那时他还在城里的飞机厂上班,研究飞机翅膀的力学。上午开过了会,下午四点接孩子的接孩子,打乒乓球的打乒乓球,洗澡的洗澡,李晓兵坐在自己的电脑前面突然想写点东西。他这二十几年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和数学物理混在一起,大学是数学系,研究生是物理系,写文章这件事情他从未想过,偶尔写个便条,得琢磨半天,有时候主谓宾还落下一个。《时间简史》是看过的,《包法利夫人》也是听说过的,但是一直以为是莫泊桑写的。中国作家只熟悉鲁迅,因为小时候家里没有别的书,只有一套鲁迅全集,小开本,上面有个鲁迅的头像。他喜欢读鲁迅的杂文和书信,杂文是觉得鲁迅有逻辑,不愧学过医,骂人抽丝剥茧,直指要害,书信是因为看着鲁迅严肃得如同版画一般,说起情话来也有一手,这是他的逆反心理,读书不爱读主筋,爱读自我矛盾的角料。这天不知为啥,他突然觉得悠悠的时光河就在他面前流淌,他看见那粼粼的波光,映着自己日渐衰老的影像,他感觉心里也敞开了一个黑洞,把光线都逮捕进去,另一头是喧嚣的无意义的黑暗。他建立了一个文档,想写一封信,上写了一个“亲爱的”,后面就不会了,他没有去信的人,他努力想了想远方的人们,一个都不值得写信给他,况且,写信要用信纸,在电脑里写信算啥呢?一封官函?一封邮件?他把“亲爱的”删掉了,写了一个“我”字,我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从我开始?我要如何发展?干吗去?我,一个主体,有过什么样的历史?是要交代自己的问题?我,是要开疆拓土,或者要忏悔?他想了半天,也把“我”删去了,写了一个“他”。这时他感觉好像一个漂泊的人终于看到了妈妈炒菜的炊烟,闻到了家里被褥的香味,他,让一只手啊,轻轻拍醒了,对的,他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坐在深深的海底,正在用吸管喝奶,重力啊,压力啊,全没有作用。李晓兵忽然有了一种复杂的预感,他知道曾经来过两次的预感又来了,不过这一次是混合型的,两种相反的预感交织在一起,如同祈祷时的手掌,正有人从两旁拉开。他预感到他要变换一种生活,他一边这么预感,一边打字,叙述的河流奔腾而去,好像从来就存在的地下河因为地震而浮出水面,他的生活在隆隆的水声中破碎,虚假,置之度外,不值一哂;另一种预感是有什么要落下,这落下比过去两次预感的飞来之物要庄严,要更像歌剧的帷幕拉起前的高亢的尾声。几分钟之后,窗外传来了尖叫和人们狂跑的脚步声,一架试飞的飞机坠落了,摔成了一堆不可辨认的残渣。
李晓兵在黑暗里坐着,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这次的预感始于清晨,但是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带孩子去上英语课,在监控录像里看孩子和老师玩得挺好,虽然到现在为止,他除了听见孩子说“no”,其他一句也不会说。中午孩子午睡,他在书房写东西,他最近在写一部小长篇,已经反反复复写了大半年,写废的比留下的多,但是他已经习惯于现在这种状态,所谓作家就是写作困难的人,他接受自己的变化,每天不悲不喜地写一点,他知道自己心里还有挺多东西,不少路径,关键是这些东西越藏越深,钻头要穿过不少岩层,如果说过去写作是洗牙,现在就有点像拔牙了。晚饭吃得不错,两碗过水面。一个老同事约他去钓鱼,他拒绝了,因为天气预报说今夜有雨。除了写作,李晓兵喜欢钓鱼,平常的时候都是在河里钓,S市的腰身处有一条河,穿城而过,时清时浑,他们每次都去河的上游,钓一些小小的鲫鱼,钓了再放,纯属西西弗。同事晚上告诉他,从他所住的地方驱车一个小时,在S市的市郊,他们发现了一眼小湖,并非死水,今年夏天的雨水尤其多,小湖看上去是新形成的,也可能是上游泄洪所致,给他发了定位。李晓兵是有兴趣的,在河边钓鱼像吃食堂,在无人知晓的小湖边钓鱼就是小灶,但是因为他一天心神不宁,雨又要来,小湖也不至一天就干涸,所以他准备回头再说。预感和睡意一起不见踪迹,李晓兵看了一眼表,十一点五十,他给老同事发了一条微信:夜钓去否?等了二十分钟,没有回音,老同事还在原来的单位工作,想来已经睡了,人家第二天还要上班,不像他,时间像活期存款,都由自己支配。他又给另一个渔友发信:城郊有新现小湖,有兴趣今晚去踩踩乎?这人回信说,父亲昨天拉屎时摔断了腰椎,现在正在医院陪护,钓鱼不可能了,只能看着吊瓶。他放弃了,自己把自己掉了一个个儿,头在刚才脚的位置,假睡了半小时,然后起来,收拾渔具,带上雨衣和手提灯,推门出去,下电梯到地库,开车出发。
路上没几个车,小城的夜晚安静,好像掉光了头发的头颅,头上有乌云集结,摆在户外的摊子也收了。李晓兵沿路往南开,过了一片新建的楼区,房子就少了,他跟着导航拐到一条土路上,周围逐渐有了平房和庄稼,这一路向南,似乎时间的逆旅,渐渐退回到平矮的时代。又开了半小时,过了一片简陋的温泉旅馆,看见一座小山,城边还有这样的地方?他不知道,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几年,一次没来过。他放慢了车速,仔细看那山,高约二百米,孤零零的,黑暗中看不清上面是不是有植被,形状细长,如同高塔,还有这种山?他在脑中过了过力学,确实也是有可能的,也许早年炸山取石,留下了削过腮的细脸。路还有,只是渐渐坑洼,绕过小山,他看见了那个湖,真不小,大概有两千平方,汽车的大灯照上去,如同黑眼仁儿一样凝固,若不是友人发的位置精确,湖被山所遮,路人是无法留意的。只有他这一辆车,一个人,两盏车灯,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点作妖儿,好好的觉不睡,跑到荒郊野岭钓鱼,清晨的预感已经完全散去,好像起床气一样荒谬。既然来了,总得比画一下,至少带两条鱼回去,要不然第二天方灼问起,更显奇怪,最好鞋底再踩点泥,多准备一点证据。他把车停下,开着车灯,从后备箱取出渔具,往湖边走。其实李晓兵怕水,不会游泳,也不敢坐船,但是却喜欢钓鱼,怎么说呢?下水等于交托,钓鱼等于交谈,他喜欢后者。在卷着湿气的夜风中,他展开马扎儿,坐在了湖边。
事实上那天晚上谁也没有看到李晓兵,他钓鱼的地方是一个视觉上的死角,这条路本来车就很少,偶尔过去一辆,也没有人会发现他,他就像小时候玩藏猫猫的孩子,不小心藏到了一个谁也发现不了的地方。李晓兵过去也夜钓过,但是从来没有超过凌晨还在钓鱼,鱼也要睡觉不是?好好地睡着觉的鱼,梦里被鱼钩拉住嘴唇拽上来,是不是有点残忍呢?他坐在马扎上感到挺惬意,虽说有蚊子,还不少,围着他的脚脖子咬,空气也没有夜晚该有的凉爽,闷热,好像比白天还热,但是此地确实十分安静,水也不臭,甚至散发出一点清香味。他的儿子越长越像他,他有时候偷偷把自己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看,李大星比他同龄时要高一点,但是模样几乎一样,尤其不高兴时,吊着个脸,并不哭泣,只是暗藏冷笑的神情,好像重新搬演的话剧一样。他时而高兴,毕竟证明了血统纯正,时而恐惧,我小时候就这样?他想,然后现在这样?这是一个复杂的方程式,解出来的东西竟是现在的他。婚礼他几乎不去,葬礼他极爱参加,戴着白花看人躺在那,无依无靠,只有自己,从而明白那么多欢快的相聚都是花瓣,终于一天会掉落,剩下孤零零的一根枯枝,他便显出暗藏冷笑的表情。但是他毕竟没有看破,每天写作就是明证,再消极的写作也是作为,不是无为。冬天去旧书店买书,看见两个书店服务生围在炉子周围烤火,两人都很年轻,书店又冷又破,屡经搬迁,搬一次就换两个店员,总是有人应聘,炉子一直是这个炉子,他忽然觉得将来有一天自己老了,不愿意去养老院,也可以来这里工作,他连飞机都修过,手脚是利索的,只要对方不嫌他年龄太大就好。
頭顶的云又低了一点,原来一丝风也没有,现在风突然刮起了,李晓兵钓起了一条鱼,一条健康的黑鲤,像假的一样结实。他把它放在桶里,很快它似乎就适应了桶的大小,游得蛮舒畅。李晓兵看着鱼,心情不错,出师告捷,平时在河里钓,看不到这么大的鱼,忽然他感觉到心慌,一股子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渗出来,两只脚掌像触电一样发抖,如同跟着什么音乐打着拍子。一道闪电在远处横亘了几秒,雷声翻滚,炸开,硕大的雨滴突然落下,紧接着就连成了瓢泼大雨,李晓兵赶紧把雨衣穿上,他第一反应是回到车上,但是雨幕里他看见渔线突然下沉,他咬了咬牙,走过去收线,刚一使劲,鱼竿就折进了湖里,李晓兵脚下一滑,险些也掉了下去。这时他看见一个人从水里走了出来,鱼钩挂在他的耳朵上,那人把鱼钩摘下,扔在水里,然后手里撑起一把大伞,慢慢走上岸来。
李晓兵吓得一动不敢动,想起后备箱有改锥,但是浑身动不了,只有思想飘过去,掀起后备箱,拿改锥在手,横刀立马。那人走到李晓兵近前,说,是你钓鱼?李晓兵说,啊。那人说,你别紧张,我也是刚来。钓了几条?李晓兵说,一条。这人年纪四十岁出头,穿着一整套黑色西装,皮鞋,里面是白色衬衫,冷丁一看,除了年纪大点,好似一位伴郎。男人说,你等我多久了?李晓兵说,我没有等你,我在钓鱼。男人说,深更半夜在这儿钓鱼,你不是等我是干吗?李晓兵本来害怕,看他这么自作多情,害怕减了百分之五十,这人虽然从水里走来,可是衣服一点没湿,仔细一看,嘴里还嚼着口香糖。李晓兵说,我睡不着觉,打发时间,这就要走。男人说,我大老远来的,你能不能别这么着急?你们不是有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还有一句话叫,赶日不如撞日,还有一句话叫,前世多少次回眸才造就了今生的一次相遇啊。李晓兵说,这几句话是有,但是跟我关系不大,我明天要有工作,现在得走。男人说,你不问我从哪来?好奇心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吗?李晓兵忽感烦躁,这人好像看久了电视节目,比方灼还要啰唆,一会儿估计也要让他给一个理由。李晓兵说,好吧,你从哪来?那人说,让您问着了,我从几百光年之外的星球而来,你瞧这湖,波光粼粼,其实是一个飞行器,你的鱼钩一直在我的飞行器里头当啷着。我呢,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安德鲁,你觉得这个名字如何?李晓兵说,我觉得这个名字相当平庸。男人说,对啊,平庸的名字好养活,你叫李晓兵,咱们俩五十步笑百步,不也都活得挺好?李晓兵一时语塞,此人确实善于运用成语。男人说,你脖子上那颗脑袋,对于我来说,等于一个显示屏,现在你因为紧张,脑细胞在收缩跳跃,心脏压出的血急速向你颅内增援,几条航道都已经满仓,但是我跟你说,没用,你还是想不出所以然。我呢,不想拥有这种智力优越感,但是你确实比我傻,我也不能罔顾事实。李晓兵这人大体是个温和的人,极少和人红脸,但是也有人说,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一旦有人当面否定他,他是绝不退让的,甚至要变本加厉报复的。李晓兵说,你怎么能证明我比你傻呢?男人说,我是来杀你的,你有感觉吗?李晓兵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感觉?男人说,你没有显示出你的感觉。李晓兵说,你算哪一个?我为什么要对你显示我的感觉?
雨势渐渐小了,乌云融化,黑暗的天空没有光,已变成透明。两人站在山的背面,湖的边缘,一动不动,桶里的黑鲤在翻腾,用尽全身力气嚎叫,没人能听懂它说什么。李晓兵知道今天遇到了麻烦,他也有点沾沾自喜,躺在沙发上的时候他怀疑自己已经丧失了预感的能力,他甚至怀疑从小到大的几次预感都是巧合,或者那预感是他追认的,他赋予了自己一种不曾拥有的能力。看来并不需要担心,今天的预感和事实之间距离的时间稍远,不过还是来了,只是他自己成了那只凉开水瓶,这是他没有料到的。
安德鲁收起了雨伞,系好,扔进了湖里,雨伞迅速地沉入了水中。他伸手到湖水里,掏出一只红色的电话,电话线一截在水里,他把电话放在脚边,把双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说,既然你知道我要来杀你,你现在还站在这里,我就认为你接受了这个事实。李晓兵说,那倒不见得。安德鲁说,这么跟你说吧,不但你得死,S市的七十多万人都活不了,你肯定要问为什么,我直接给你原因,因为你们这里头有人犯了罪。李晓兵说,哪里没人犯罪?安德鲁说,此罪非彼罪,你们有人犯了弥天大罪,偷了我们的东西。李晓兵说,我们离你们那么远,还能偷你们的东西?你们那么高级,一直能看到我们的头脑里,东西还能让我们偷了?李晓兵不知道为啥自己夜半三更还头脑清晰,口齿伶俐,平时他不爱说话,今天却好像一个辩手,他一边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不错,紧要关头还有潜力可挖,一方面,在话语的缝隙里,他觉得也许他真的会死,就像安德鲁说的那样,被他杀死。可是他没有太大的感觉,这令他有点惊异,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像凉开水瓶那样凉爽,光滑,他相信如果现在给他体检,他准保前所未有地健康。
安德鲁说,你们当然没能力偷走,是我们过去来旅游的时候掉的。就掉在你们S市,就掉在这个地界。李晓兵说,且慢,你这是丢,不是我们偷的。安德鲁说,是丢了,但是你们并没有归还,这就叫偷。李晓兵说,我们怎么知道是谁丢的?你今天这个模样,听说也是刚来,谁知道是你丢的?就算知道,到哪找你?你贴过失物招领的启事?在广播电台里登过广播?或者挨家挨户问过?话又说回来,是你本人丢的吗?从你裤兜里漏出去的?安德鲁犹豫了一下说,是我祖先丢的,反正是我们家的东西,谁丢不是一样?李晓兵说,我爷爷在世时,经常说起家里的宝贝,皇宫里的瓷碗,祖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因为打仗逃难搬家,都丢了,谁家没有几个虚拟的宝贝?你那东西你就确保真实存在?安德鲁叹了口气说,这你不用担心,那东西确实有的,不是我爷爷那时候有的,是我爷爷的爷爷那时候就有。李晓兵说,是个什么东西?安德鲁说,是一句话。李晓兵说,一句话?安德鲁说,是一句话,我爷爷的爷爷早年来过这,临时想起一句话,觉得特别好,憋得难受,就说给了他旁边从井里打水的一个S市的人,那时候S市还不是S市,只有十户人家,一个村庄,他说给了那人,那人把水桶挑在肩上走了,他就再也没想起来。这话就丢了。后来来找过,几代人都来过,没找回来,打听了不少人,有的人还在这儿生活了很久,都不是那句话。你们把这句话藏了起来。李晓兵说,你们想不起来这句话了?安德鲁说,想不起来了,从离开我祖先的嘴唇,这句话就想不起来了。李晓兵说,那我们即使还给你,你也不知道啊。安德鲁说,非也,只要是那句话,说出来我们就知道,就像如果你儿子让人抱走了,多年之后,他已经七十岁,你已经一百岁,两人一见,你还是能感觉到他是你的儿子。李晓兵说,就因为这个你要杀我们?安德鲁说,是了,你们有个鲁迅不是说过,他要肩着黑暗的闸门,把后来人放过去,我们就干了这个事儿,谁想到你们还不领情,过去之后就把我们忘了。这难道不该死?李晓兵说,你们现在过得不好?安德鲁说,岂止是不好,我们已经完了,跟你说实话,我们星球就剩我一个人了,你今天晚上单睡了吧?李晓兵说,单睡了。安德鲁说,让你天天单睡你受得了吗?我现在孤身一人,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区别,想来想去,死之前得先把你们灭了,要不然呢心有不甘哪。李晓兵说,那你这个电话是干吗的?你一个人怎么还需要电话?安德鲁说,电话不是打给人,是打给一个机器,你现在朝天空看,云散了吧,你瞧,那是不是有一颗孤星?就是它接电话,一个电话过去就继续下雨,是现在的十倍,淹死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李晓兵说,说实话,我不相信你。
安德鲁蹲下身子,拨通电话,哎,再下三分钟暴雨,要世界末日那种感觉,不用范围太大,就在我方圆五米。天空中的孤星一闪,一片乌云飘来,硕大的雨滴落下,就在安德鲁和李晓兵站着的地方,形成一片雨柱,车的位置一滴雨也没有。两人都给淋透了,好像刚从河里给打捞上来。安德鲁说,这是我们的旧机器,只会下雨,要不然我的选择还多点,地震啊,瘟疫啊,大火啊,或者干脆把你们所有人大头冲下扔到太空里。李晓兵走回车上,找出一条干手巾擦了擦脑袋,然后递给安德魯,你们丢的那句话有没有什么线索?比如,那句话几个字?安德鲁说,据说是八个字。李晓兵说,不含标点?安德鲁说,不含标点。李晓兵说,那可能是一句谚语,比如,三九四九,棒打不走,是这句吗?安德鲁说,不是。李晓兵说,还有别的线索吗?安德鲁说,有三个名词,一个动词。
夜深得像没有灯的黑屋子,李晓兵站累了,就坐在马扎儿上,安德鲁也累了,坐在一块石头上。李晓兵说,我还能钓鱼吗?我习惯一边钓鱼一边想事儿。安德鲁说,可以,你想钓鲨鱼吗?李晓兵说,不想,我就想钓点鲤子。安德鲁说,你钓,有。李晓兵装上鱼饵,把鱼钩甩进湖里,三个名词,一个动词,正常想来,句式应该是名词动词名词名词,比如李晓兵钓上金钱豹,但是这个句子里,金钱好像有点形容词的意思。这样想来,真是大海捞针,不可能找到。李晓兵想到方灼和李大星,都沉沉睡着,不知道自己就要被大水淹没,一个想着明天的出差,一个做着跟动画片有关的梦。安德鲁给的线索太少了,这不是他的错,他碰巧是那个星球最后一个人,还记着祖先的遗憾,在死之前,开着破旧的飞行器来到这里,谋求某种正义。八国联军时丢掉的文物,我们不也想要回来吗?李晓兵在心里头很理解安德鲁,一个将死之人很有可能想到亏欠。
安德鲁坐在石头上,如果仔细看,他的鬓角有白发,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穿多久了,让雨水一淋,像过期的蛋糕一样更加显得不成样子。李晓兵也想过是不是用改锥捅死他,但是他既然能从水里走出来,想来一把改锥是杀不死他的。原来哪个星球都有愁苦的人哪,也不是愁苦,安德鲁从水里出来到现在,可说了不少的话,估计是憋得够呛,夜晚闪烁的星星,密谋着灾难,可是谁知道他在上面呢?李晓兵想起自己写的第一篇小说就和水有关,今天遇见了一个从水里走出的人,S市也就要被水吞没,从小怕水,可说是冤家路窄,怕什么来什么。李晓兵说,安德鲁。安德鲁直了直脖子,原来刚才他睡着了,李晓兵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说,你除了要淹死我们,在那你从事什么职业?安德鲁说,我是一名邮差。李晓兵说,你们那还需要邮差吗?安德鲁说,需要,我们每天都写信,寄给别人,这是我们的习惯,一直没有更改,说了你也许不信,邮差在我们那是很高贵的职业,而且是世袭的,我爷爷的爷爷也是邮差,他来你们这游玩,是政府提供的福利。所以啊,我们对文字特别敏感,丢了一句话,等于丢了一封信,我爸爸就是因为丢信自杀的,不说这个,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你想不出来我就要打电话了。李晓兵说,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也许你是一个连环杀人犯,畏罪潜逃也不一定。安德鲁涨红了脸,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说,这是我拿到的最后一封信,发信人和送信人都死了。李晓兵说,我可以看看吗?安德鲁说,不行,我们送信人永远不能看信,这是职业操守,就算两头的人都没有了,也不能看。李晓兵说,你想一下,你现在是你们星球剩下的最后一个人,你如果不看,这封信就等于没有存在过,写信的人也不想这样,还有一点,这是你们的文字啊,等于一个人跟你说话啊,你不觉得孤独吗?有人跟你说话不好吗?
其实自安德鲁从怀里掏出这封信开始,李晓兵就意识到这封信他会打开,这不需要什么预感,只需要一点同理心,也有可能他早就把信看了十遍八遍了,熟得都可以背出,只是不承认而已。两人又谈了一会儿话,只是聊了聊各自的风土人情,再转回这封信上,安德鲁就打开了。李晓兵说,不认识你们的字,你如果不念,我就不会知道,你决定。安德鲁想了想说,好吧,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跟你太太也不要说。李晓兵说,我很多事儿都不说,你念吧。
“亲爱的I,我们的部队已经战败,虽然长官还在谋划反攻的事,但是所有人,包括我们身上的虱子,都意识到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逃窜了,可是令人欣慰的是,所谓胜利的对方,也已经从内部溃烂了,作为对手完全能感受到这些事情,他们已无心收拾尸体,就任由他们被灼热的战场熔化。瘟疫横行,这种瘟疫不是身上的疮斑,而是心里的绝望,因为已经清楚地看到,我们无法返回家乡了,几天之内我们就都将死在这里,以相当耻辱的方式。我们已被逼到山的背面,冥河的边缘,我们将毫无还手之力地被歼灭,就像用杀虫剂喷杀飞蚊一样。自杀的人数这几天内猛增,虽然自杀的人要高挂起来示众,长官也说,这些人死后无法成为星辰,但是还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杀,人数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我准备战斗到最后,不是因为勇敢,是我想见证一切,我走了这么远的路,还是想要清楚地看到如何终结。听说家乡已经毁坏了,因为战争损坏了地壳,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我已经好久没有收到你的信。离开时我们吵了一架,原因好像是吃饭时我没有坐在你的旁边,我过量地饮酒,把你忘在了脑后,第二天凌晨就被抬上了军车。亲爱的I,如果你死了,我相信你死前会想起我,尽管我还没来得及娶你。不出意外的话,三天内我就会死,我也会想着你死去,我们之间不只是爱情,我们是一切美好的联系的缩影,我们是世界的左手和右手,我们是河流和河床,我们是组成一个单词的两个字母。我们都是普通人,没人知道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威力,这也是美妙的地方,我们就像所有不可描述的秘密一样,没人知道其存在,也没人为其消失而悲伤,除了我们自己。这多么好啊!
“本来想写得更长一些,但是时间来不及了,炮声越来越近,希望今晚我们还能守住我们的山坳。如果你能读到我的信,希望你能把其当作求婚,当然仅限于心理层面的,你不用答应,你只需要记得我确实做过这件事,然后想办法活下去。如果你已经死了,那也没关系,我们曾经认识,就已经很好了,希望我们再见时能认出对方,那并不难,因为这次我就是因为遇见你才存在的,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就算死了,也会一直存在。就写到这里,邮差已经等了很久了。
“爱你的X。”
安德鲁把信折起来,放回信封,揣进怀里。他的声线不错,低沉冷静,很适合念信。远处已经有了一点天光,两人呆坐了一会儿,信的内容搅扰着李晓兵,他还是没有想出那句话,八个字的那句话。安德鲁忽然抬头说,这就是邮差为什么不能看信。李晓兵说,为什么?他说,信变得太沉了,已经背不动了。李晓兵说,明白。他说,你不明白,这些士兵最后都在写信,我送个不停,可是大多没有送到收信人手里,有的死了,有的根本不存在,有的活着,可是根本不认识来信的人,又给退了回去。李晓兵说,明白。安德鲁说,你不明白,无论如何请你想出那句话吧,拜托你,还剩最后半小时了。李晓兵说,我确实想不出来,这么久了,早已经消失了,这句话已经消失了。安德鲁说,我们把它找出来吧。从第一个名词开始,你给出几个名词。
李晓兵看了看周围,名词,他曾经写下过不少名词,他曾写下过成千上万个名词,他也命名过一些新奇的事物,可是这些好像都离他那么遥远。他忽然明白,他不是要找到那句话,而是要写下这句话。他说,鲤鱼?安德鲁说,不是。他说,山?安德鲁说,不是。李晓兵说,希望?安德鲁说,不是。李晓兵说,天使?安德鲁想了想说,有点意思,但是不是。李晓兵说,上帝?安德鲁说,不是。李晓兵说,魔鬼?安德鲁站了起来,说,是。李晓兵说,魔鬼?安德鲁说,是魔鬼。请继续。李晓兵也站起来,在湖边快走,魔鬼干什么呢?魔鬼有什么坐骑来着?手里拿着什么兵器?他回头说,魔鬼喜欢?安德鲁说,不是。他说,魔鬼手拿?安德鲁说,不是。他说,魔鬼讨厌?安德鲁向他走了两步说,有点意思,但是不是。他说,魔鬼逃出?安德鲁说,不是。他说,魔鬼害怕?安德鲁点点头说,是这个,是魔鬼害怕。魔鬼害怕,魔鬼害怕,是的,是魔鬼害怕。李晓兵说,魔鬼害怕什么呢?后面是两个名词,我们先找到其中一个如何?安德鲁说,这是你的自由。你还有十五分钟。李晓兵看了看那个红色的电话说,魔鬼害怕电话?安德鲁说,你们害怕电话,魔鬼不怕。李晓兵说,魔鬼害怕水?不会,魔鬼水火不侵。魔鬼害怕光?不对,那是吸血鬼。你怕什么,安德鲁?安德鲁说,你在浪费时间。李晓兵说,我们说的魔鬼是一个魔鬼吗?安德鲁说,这不重要,你找到了魔鬼这个主语,这很重要。李晓兵说,我已经有所进展,你的电话可以推迟吗?安德鲁说,不可以,别忘了我是一个邮差。李晓兵说,魔鬼害怕承诺?安德鲁说,好像近了一点。李晓兵说,魔鬼害怕信仰?安德鲁说,不像。李晓兵说,魔鬼害怕相信,相信算名词吗?安德鲁说,你说了不少同义词。李晓兵说,魔鬼害怕存在?安德鲁说,好像又近了,但是好像又完全错了。李晓兵突然有了前所未有的预感,这预感比早上还要强烈,他起床时那个预感和现在这个相比简直是一堆瓦砾,现在就像有强光打到他的脸上,照到他飞旋的思路,光的颗粒飞舞,与思维的颗粒搅在一起,不分彼此。代词,代词也是名词,近了,又反了,一颗子弹,射向凉开水瓶,一架飞机坠落了,暴雨就要淹没这座城市,一句丢失的话,一个远方来的固执的邮差,一封没有收件人的信,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就算死了,也会一直存在。
李晓兵说,魔鬼害怕他不存在。
安德鲁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看上去好像想和李晓兵握一握手,但是最后并没有这么做。太阳还没完全出来,但是能感觉到气温在上升。湖水像缩水的衣服一样,开始蒸发,从天上来的水,现在正在飞速地回到天上去。电话线一点点变短,电话滚落到水里,旁边的小山变成一根天线,折起,像两根拐杖,“哒哒”走入湖心,露出一片巨大的平原,露出远处S市高高的彩电塔的金属尖顶。安德鲁用双手理了理鬓角,从兜里掏出那封信,摸了摸,确信它还在,然后又放回里怀。他从桶里抓出黑鲤,扔到水中,然后头也不回地跳到湖里,几分钟之后就和这湖一起消失不见了。
2018年7月20日星期五初稿
2018年7月22日星期日二稿
2018年7月27日星期五暫定
2018年9月27日星期四最终
责任编校 王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