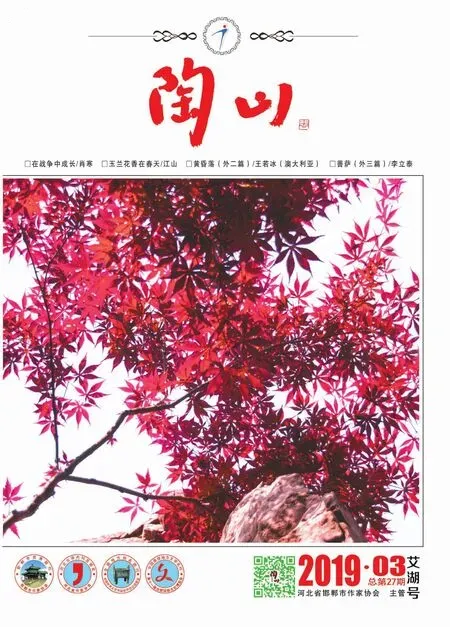文都河的柿子树
2019-06-26张雁
◎张雁
柿子树,于北方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而我,却独念念不忘文都河的那些柿子树。
文都河是平山县位于革命圣地西柏坡西北不远的一条小河流。从山巅顺谷而下,蜿蜒30多公里流入岗南水库,把几道沟谷,十几个山村串成一个小流域。因为路过我的老家文都村,便被叫做了文都河。不止这条河流,凡是这条河流经的沟沟岔岔,村村落落,一草一木都被叫作文都河。包括这里的人,被问及哪里人时,习惯回答,文都河的。
文都河的柿子树也是司空见惯的。
这里的柿子树都是野生的,河谷山地,沟沟坎坎,不经意间就有一两棵高大的柿子树映入眼帘。它们不同于城市里嫁接后的景观柿子树,柔柔弱弱,而是粗犷斑驳的。它们不同于桃梨树那般娇贵,需要浇水施肥格外呵护,也不挑土壤肥瘠,只是在野外自然生长;它们也不像白杨树那般高大伟岸,而是枝杈旁出,体型庞厚,蔽日遮天。在这里,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几棵标志性的柿子树,出县城,顺文都河一路向上,转几个湾,过几棵柿子树,就知道老家到了。
文都村,我的老家,一个坐落在文都河北岸山坡的小山村,因了文都河而比其他村庄更多些名气。这里周周边边的柿子树我都熟悉,大的小的,路边的,抑或偏僻的,几乎每一棵都留下过我的印迹。我家老宅在村庄山坡的最高处,每每转过山湾,还没进村就能高高地看到老家的院子。尤其是后门口那棵不知道长了多少年的巨大的柿子树。
我老家的院子足有半亩地,正房13间一字排开,院子里曾种有苹果、梨和石榴树。大门外是猪圈、茅厕,土崖下才是村子。院子后门外是几分自留地,再远处百十来米远就是那棵大柿子树了。算来我家的老宅子已经将近50年了,而与这棵柿子树比,老宅子还只能算是个孩童。
后门外的柿子树有多大树龄,谁也不知道。从我记事起树身几个人就合抱不住,主干中空,一个洞口,人可以钻进钻出。树高足有十几米,枝干纵横,夏日里浓荫蔽日,煞是壮观。冬天树叶凋落,一树火火的柿子刺破蓝天,我童年满脑子记忆。在我老家,柿子是不被当作正经水果的,顶多是零食。但对我们孩子,却是满满的幸福。夏日柿子青绿,乒乓球大小,上树摘下,埋进河渠水边,做好记号,7天后寻迹挖出,已经甘甜如饴。有时被同伴提前挖去,免不了要打上一架;秋日火红柿子挂满枝头,用一竹竿,顶端挂一布兜,在树下高高举起,看准一软柿子,网住,用力一兜,收杆掏出,娇嫩软糯,吹去表皮虱虫,掰开吸吮,那个甘甜,感觉飞上了天。除了鲜食,冬日柿子还可以做成柿饼,晾晒在屋顶、山坡,一下霜,表层薄薄一层白霜,甘甜翻了几倍。
做柿饼,奶奶是高手,年年晾晒一房顶。
奶奶是土生文都河人,胖胖嘟嘟,没有文化,却是手脚勤快,地里家里的活儿,闲不住。倒是爷爷忙完地里的活儿,回家一壶茶,躺椅上能歇半晌。面对爷爷的清闲,奶奶也不时嘟囔几句,做饭喂猪喂鸡,收拾家务却不停歇。文都河,我,爷爷就是她的全部。多少次带着我去省城我老姨家,她亲妹妹处走亲,住不了几天就要回。谁也劝不住,说,回吧,回吧,城里闲得慌。实际上牵挂爷爷的饭食,还有家里的鸡和猪。
我自小随奶奶长大,一岁多就跟奶奶睡,初中了还非得钻奶奶被窝才能睡。几次爸妈晚上把我从奶奶被窝抱到他们房间,一觉醒来,哭着跑回奶奶屋。初中到五里开外的外村上学,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步行去上学。山村冬日寒冷异常,奶奶每天五点多就在土炕下边的炉子上弄一锅大米白菜腌肉一锅烩的饭,加猪油,打开锅盖,异香扑鼻,奶奶叫它米苦楚。吃一碗米苦楚,挎上书包上路。五里多地山路,黑黢黢,阴森森,全靠米苦楚热乎乎撑底气。一路经过五棵大柿子树。累了冷了,小伙伴抱一堆路边玉米秸,在柿子树下点燃,烤一会儿火,笑笑闹闹,再走,走着数着过了几棵柿子树,就到了学校。
柿子好吃却不好摘,每年都有爬树摘柿子摔死人的。每逢此时,奶奶就说,命,该着的,却严禁我上树去。记得一次因为自己上树被奶奶知道了,不敢回家,躲在后门口大柿子树下,家里人急得到处找。天快黑了,家人和邻居真急了,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的找,不停地互相埋怨。就听见奶奶安慰别人说,他胆子小,跑不远,都别急。自己却嘴里不停喊着我的名字,绕着村里一圈圈地跑。
后来,我上高中,上大学了,只能假期回文都跟奶奶一起呆上个把月。每次飞奔上山,扑进家门,第一句就大叫,奶奶,我回来了。奶奶总是马上出现在屋门口,笑盈盈应着,却憨憨地手足无措。奶奶去世后,几次回家,下意识叫奶奶,却不见应,一时混沌,醒神来大哭。 每次离家回学校,奶奶总是在家门口那棵小柿子树下看着我下坡,拐弯,走远, 快看不到了,她还不停挥手,挥手。我知道,直到我走远,看不到了,她还得在那儿矗立良久。
想来,奶奶生前最后一眼也应该是家门口的那棵柿子树。她去世时我不在身边,亲戚把我从大学接回家,她已经躺在了正房的地上供人祭拜。听人说,她那天去猪圈喂猪,突然感到头晕,就急急往院里走,到大门口时已经支撑不住,在那棵常注视我离去的柿子树下仰面倒了下去,再没醒过来。出殡那天,突然意识到世上再也没有奶奶了,我一路嚎啕大哭,一直到山上坟地里。懵懂中,奶奶下葬,培土,磕头,天旋地转,就看到了坟地旁那两棵硕大的柿子树,枝干虬曲,刺破苍穹。如今那两棵柿子树依然苍翠浓绿,果硕叶茂, 而奶奶坟头的杂草已一人多高了。
世人多惧怕死亡,我却幻想那一刻躺回奶奶怀里应该是幸福的。
再后来,爷爷也过世了,我们都搬到了县城住,老家的老宅子就荒废了。我跟弟弟虽不时回家看看,却挡不住残垣颓墙的发展,院墙脱落,屋顶漏水,院子里杂草丛生,几乎进不了门。父母几次三番说,老宅不能老是荒着,整整吧。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我跟弟弟最终决定修葺一下老屋。30多年过去,回到村里,风貌依旧,儿时的柿子树依然伫立,村里人却大多已不相识。从村子里通往山坡老宅的路基本荒废,车不能行。顺路查看,主要是北沟拐弯处,一棵柿子树挡住了行车。弟弟说,现在柿子也不值钱,跟主家商量一下,给不了几个钱,把树砍了吧。顺着斑驳的树干抬头看看粗硕的树冠,我们小时候就在这里,现在依然繁茂的柿子树,顿了顿,我说,留着吧,让它在这里吧。
吱呀推开锈蚀的大门,走进残垣颓瓦的老宅,尘网中居然发现了几把儿时的布凳子,布面还是奶奶缝的针脚。墙上褪色的挂历画,也是我跟爷爷奶奶蹬炕上贴的旧历。堂屋的桌椅,瓦罐,茶壶,每处都依稀看到奶奶躺卧活动的身影。二十多年了,物犹存,心还在。
走出老宅大门,门口的小柿子树却没有了。厕所也坍塌了,猪圈废弃,土崖下的村庄依旧。顺山路下去,拐弯,回首,老宅门口萋萋。再走,快看不到老家时,依稀门口一棵小柿子树婆娑,树下一胖胖身影挥手,挥手。眼泪就下来了。
唉,老家,最后咱都得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