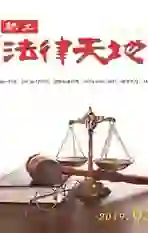审查逮捕实践问题初探
2019-06-12慕森
慕森
摘 要:审查逮捕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及捕诉一体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构罪即捕、高羁押率等顽疾仍不同程度的存在,需要予以关注和解决,本文在分析审查逮捕实践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扩展探索羁押替代性措施、强化刑罚条件的轻罪过滤功能、探索落实社会危险性证明机制的解决路径。
关键词:审查逮捕;侦查监督;实践问题
一、审查逮捕运行机制的实践问题
德国法学家耶林说:“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1]逮捕是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因此法律不仅对逮捕的条件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而且将批准逮捕的权力赋予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是检察院实行侦查监督的一项重要权力。司法实践中,审查逮捕运行过程仍不同程度存在着如下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一)逮捕异化为打击犯罪的手段
从理论上来看,逮捕本身作为一种强制措施,是一种临时性的程序措施,其价值在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排除诉讼障碍,如防止嫌疑人脱逃、串供及毁灭证据等,而非实体上的刑罚惩罚手段,正如有学者“强制措施对于刑事诉讼而言是一种必要之恶,从人权保障的需要出发,对强制措施的适用必须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2]但司法实践的运行过程中,逮捕承担起了打击、震慑犯罪,甚至惩罚犯罪的功能。
(二)审查逮捕程序的封闭性
审查逮捕权从本质属性上来看,应当近似于司法判断权,是一种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是否逮捕的批准裁判过程,但是实践中,刑诉法虽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及听取律师意见进行了规定,但由于刑事辩护的参与度不足、检察机关内部的审查过程仍然具有封闭性。
(三)构罪即捕
在审查逮捕中仍旧存在着构罪即捕的观念及惯性,具体而言就是办案人员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的过程中,常常只重视对逮捕条件中构罪条件的审查,将构罪条件的审查视为工作的重心,而忽视了逮捕条件中刑罚条件及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审查,导致只有犯罪嫌疑人符合构罪标准,皆可予以逮捕,最终使逮捕成为适用强制措施的常态。构罪即捕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主要有增加犯罪嫌疑人人权被侵犯的风险,犯罪嫌疑人在起诉审判前被普遍羁押给外界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落下口实,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曾指出:“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短暂。”普遍的未决羁押严重影响我国的司法形象,同时也会消耗人力、物力、财力,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
二、改造审查逮捕运行机制的实践路径
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构罪即捕、高羁押率等司法顽疾,刑诉法试图通过细化社会危险性条件、增设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听取律师意见、讯问犯罪嫌疑人等规定予以解决,但从纸面的规定落地为现实的司法实践仍然存着一定的距离,还需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扩展探索羁押替代性措施
在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办案实践中,虽然仍存在构罪即捕观念的影响,但是由于人员更替等因素,现阶段逮捕理应回归强制措施本来制度定位的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但很多办案人员仍然觉得对实践中较高的逮捕率,刑诉法的效果有限,并未彻底扭转逮捕率高的现实。究其根本除了受制于诉讼结构等大背景的影响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缺乏落实,例如在现阶段虽然刑诉法规定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但由于这些强制措施在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的无力,经常陷入,一放就跑的难题。特别是现阶段人口流动频繁的背景下,公安机关仍然依靠人力来保障取保嫌疑人到案,效果不尽理想。取保候审的方式也只有保证人和保证金两种,实践中,有地区为解决外地人没有取保条件这一难题,以开展帮教基地的形式进行探索,帮教基地大部分为企业,而由于企业是以商业盈利为目的,又牵涉到企业的监管责任的问题,效果可想而知。事实上,科技的进步已经促使,电子腕带等电子监控措施适用于国外的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应当加大在此方面的探索投入,有效的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保证犯罪嫌疑人参与诉讼的顺利进行。
(二)强化刑罚条件的轻罪过滤功能
由于审查逮捕过程中对刑罚条件即“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判断被虚职,导致实践中捕后被判轻刑的案件被还保持一定的比例,该刑罚要件对轻罪的过滤功能并没有有效的展开,有学者曾提出将逮捕的刑罚要件提高至“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笔者认为,在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完善后确实可以考虑,适当的提高刑罚要件,但是至于提高多少为宜,可以进一步探讨。在现有条件下,也应该强化刑罚要件的轻罪过滤功能,除了对构罪条件的审查外,进一步加强对量刑规则的学习和使用,尽可能准确的对刑罚进行预判,对于不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予以不批准逮捕。
(三)探索落实社会危险性证明机制
刑法努力将社会危险性条件细化,希望以此来制约逮捕的使用,降低审前羁押,但目前看来效果有限,除了受构罪即捕观念的影响及对社会危险性的审查不够重视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建立完备的社会危险性证明机制,具体而言就是没有规定侦查机关需要承担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实践中已经有很多地区出台规定对该机制予以明确,如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宁波市公安局《进一步规范逮捕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三条: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引用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条款并詳细说明理由。第十四条:检察机关应当对公安机关提供的“社会危险性”理由及有关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并视情开展必要的复核和调查。公安机关未对具有“社会危险性”列明具体条款并详细说明理由的,检察机关应当通知公安机关及时补充说明。然而实践来看,公安机关的社会危险性证明材料仍然存在材料单一,内容过于简要,开展社会危险性调查不充分等问题,需要在执行过程中加强沟通协调,进一步落实好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机制。
参考文献:
[1]耶林语,林山田.刑罚学[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7页.
[2]孙长永.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强制措施[J].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