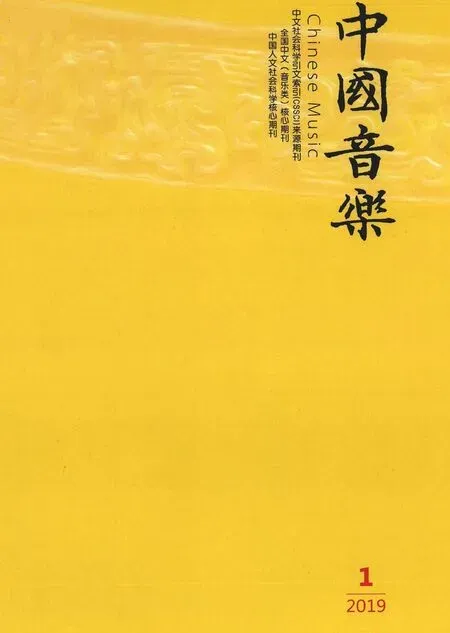关于中国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2019-05-22赵书峰
○ 赵书峰
历史民族音乐学是针对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中出现问题进行不断反思的产物,即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要关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音乐表演行为,而且要针对这种在场表演文本的“历史构成”轨迹结合历史文本文献与口述历史文献进行的梳理与考据。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已经开始提出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观念与思考。如“第二届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①1982年在中国音乐学院召开。论文内容中已经有学者率先提出音乐史学应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范畴。②参见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二次年会秘书处:《会议纪要》,《中国音乐》,1982年,第4期,第1页。近年来,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这一学术盲点,很多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个案与历史文献学方法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代表性学者主要有:项阳③项阳:《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第1-7页。、杨民康④杨民康:《历史民族音乐学:把音乐史还原到上下文语境中进行研究——兼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书写的难题与对策》,《黄钟》,2017年,第1期,第119-126页。、洛秦⑤洛秦:《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第34-46页。、赵志安⑥赵志安:《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述见》,《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3期,第137-144页。、齐琨⑦齐琨:《历史地阐释:民族音乐学之历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83-90页。、李延红⑧李延红:《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音乐艺术》,2006年,第3期,第113-122页。、赵书峰⑨赵书峰:《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问题的新思考》,《音乐研究》,2015年,第6期,第86-94页;赵书峰:《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历史与变迁》,《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2期,第12-20页。、李亚芳⑩李亚芳:《透过文本:对西方传教士记录的鄂尔多斯音乐的历史民族音乐学考察与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吴少静[11]吴少静:《“跨界”概念中的“历史民族音乐学”思考》,《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第157-161页。等等。他们(她们)针对历史民族音乐学的概念、定义、研究理念以及个案实践等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思考。其次,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在受到历史学(尤其历史人类学)的影响下,学科研究出现了比较重要的转型,即,它不但是针对研究对象的即时性表演文本进行重点关注,而且也对其表象背后的历史变迁过程给予深入思考。如理查德·魏狄斯(Richard Widdess)认为:“历史民族音乐学所重视的此类物象包括早期的声音记录、口传历史、文字和乐器资料、插图和考古学数据等。”[12]转引自杨民康:《音乐民族志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53页。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口述文本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是对音乐事项中的乐人、乐事过往的有关的历史记忆的一种重构过程。同时,它也是基于长期深入的田野考察工作基础上,对当下具体的音乐事项的发展、变迁的集体性记忆的一种描述与阐释(结构与解构)过程,因此,学科倡导在走向历史的田野过程中,我们不能只关注对书面文献文本的考察与关注,而是要对乐人有关乐事历史的个体记忆方面的口述资料有必要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挖掘与整理。[13]赵书峰:《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问题的新思考》,《音乐研究》,2015年,第6期,第88-89页。为此,本文主要针对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历史文本”与“在场文本”、作为他者兼具汉文化书写体系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以及权力与话语背景下的“口述音乐史”书写等问题展开初步的思考。
一、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是历史与当下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是音乐的整体(宏观)与局部(微观)性质的考察
我们知道,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一般多关注音乐在场文本与文化语境互动性质的思考,却很少结合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构成”问题展开历史与田野互通性质的挖掘,也就是无法捕捉到当下鲜活的音乐即时性文本背后承载的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尤其是我们更无法看到传统音乐发展背后所隐藏的丰富的历史画面,这也是常被学界诟病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只关注当下音乐表演文本而忽略其“历史构成”轨迹的纵向考察。所以,历史民族音乐学的产生也是对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理念缺失的一种矫正,因为,我们往往只过多关注音乐的田野在场文本,而对其背后的历史变迁轨迹缺乏梳理与考证。也就是说,只关注音乐的“结局”研究,而对其“流”态视而不见,或者说只关注个案(局部)而忽略对整体(宏观历史)的考察,这样的研究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当下的中国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理念多是受到欧美以理查德·韦迪斯(Richard Widdess)、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谢勒梅(Kay·K·Shelemay)等学者的影响,在基于中国历史人类学(尤其以华南学派)的研究理念的影响下展开的一种关于音乐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互动性质的研究。正如笔者认为,学者们在历史人类学研究理念的影响下,开始将历史学视野投射到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开始关注到走向历史的田野(注重口述历史文本与书面历史文本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田野与文献之间的互通。亦即民族音乐学在保持自身研究特点的同时,开始注重对研究对象“历史构成”文献的考证与梳理,即追寻传统音乐表演活动表象背后的、过往的现代历史结局的考察,即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研究。[14]赵书峰:《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问题的新思考》,《音乐研究》,2015年,第6期,第86页。比如,项阳《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15]项阳:《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杨民康《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16]杨民康:《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以及2016年10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历史与田野:中国礼俗仪式音乐学术研讨会”,等等学术专著与学术活动都带有鲜明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理念。“当下学界倡导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矫正了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中缺乏历史性研究的弊端,同时也丰富与开拓了世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理论与视野,因此可以说属于典型的民族音乐学‘本土化’理论研究。当然虽然这个概念不是中国学者率先提出的,但是这是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在传播到世界各国“本土化”过程中的一种学科反思,同时也是学科理念与视角、思维的一种调试与补充,当然尤其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功不可没。”[17]赵书峰:《再思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问题》,《民族艺术研究》,2018年,第5期,第97页。总之,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在不断关注当下音乐表演活动,同时要充分挖掘和梳理这种音乐表演背后的历史变迁轨迹,即民族音乐学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考察。正如华南学派温春来在《历史人类学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中认为:“强调走向田野,在历史现场解读文献。相对于只在书斋或图书馆的苦读,这种方式可达致对历史的更亲切认知,并有可能体验到历史在当代的延续与影响,从中激发出不一样的思考。此外,在阅读中遇到的困惑之处,如果联系田野场景并辅之以实地调查和访谈,或可收到解惑之效。”[18]温春来:《历史人类学实践中的一些问题》,“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578.html),2018年4月2日。
二、如何看待田野实践与案头工作中“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的差异性问题
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理念要求我们不但要关注当下的音乐表演活动,同时针对其过往的音乐表演文本的历史变迁轨迹结合传统的历史文献(包括官方历史文献与民间历史文献)、民间遗存的实物资料,考古资料以及口述音乐历史文献资料,对研究对象进行多维度的审视与观照。但是,在实际的田野考察现场与案头工作中,研究者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搜集与挖掘到的传统书面历史文献与历史长河中发生的历史真相之间出现差异或偏差。因为结合后现代主义思维认为,任何历史文本都是被选择的一种人为主观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基于主流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一种叙事模式。当下我们看到的传统书面历史文本都是每个时代审美观、价值观、社会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具体呈现。因为“历史是个被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当下我们看到的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音乐历史真相)之间是有很大的偏差的。尤其是作为“他者”身份呈现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信息更是具有这样的特点。古往今来,任何时代的音乐文化历史信息的书写与表述都带有权力与知识互动体系中的一种主观话语建构。正如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认为,“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19]〔意〕贝内德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页。这个“当代”笔者的理解就是音乐历史被建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历史过往的那个“当代”)。因此,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要重点观照历史与当下的“接通”问题,同时对于上述两者互通、互证过程中出现的偏差问题也需要我们结合历史学研究的“多重证据法”进行综合观照,即在考古与文字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和现场的“口述历史”信息进行“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差异性问题的综合辨别、对比与思考。总之。所谓的历史文本,其实就是一种主观的有选择的文本(Text)编织过程,它与历史长河中客观发生的音乐历史事实之间在书写内容与表述方式是有区别的。我们在面对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不但要对其进行上下贯通性的思考以及相互求证,同时也是让我们通过当下去反观历史,通过历史来映照当下,这种二维的互动关系,正是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价值与理念。正如笔者认为:“历史与田野的互动问题,不但要关注历史与当下的互证研究,同时要关注历史与当下研究出现的偏差问题的思考,就是说我们要考证到的书面与口述的‘历史文献’中挖掘到的历史信息与当下田野现场观察到的‘历史事实’的差异性问题是由哪些深层原因导致的。所以,我们不但倡导‘接通’背后深层的学术内涵,同时也不能忽略由于‘历史文献’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性问题的后现代主义思考,同时也要求证导致‘历史文献’‘历史事实’的‘差异性’原因的深层逻辑结构在哪里?所以,走向历史与田野互通性质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是为了挖掘研究对象过往的历史发展轨迹的相关史料,同时也是为了用历史文献史料(书面文献与口述历史文献)来反观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当下的发展变迁的结局。”[20]赵书峰:《跨界·区域·历史·认同——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四个关键词》,《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25页。
三、如何看待传统历史文献记载与在场音乐表演文本之间的差异性问题
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如何处理田野在场的表演文本与其背后的“历史构成”文本之间的偏差问题。也就是传统音乐文化在其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在“濡化”与“涵化”的二维互动中不断地经历着历史传承与发展变迁的一个立体过程,这其中也经历了“传统的发明”导致的本土音乐文化身份的持续性、动态性的重建过程。这种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语境中不断的重建过程,其实也就是传统音乐文化身份(认同)的变迁过程,因此,当下我们在田野中看到的在场表演文本是长期的社会历史积淀而成的音乐表述与书写。所以,也就产生了传统历史文献中有关音乐文化历史信息的记录与当下田野中看到的即时性的音乐表演文本之间是有很大的反差,最主要原因就是传统音乐在其发展的历史语境中不断的变迁使然。比如,笔者发现湘、粤、桂瑶族传统历史文献记载的婚俗仪式与音乐信息与当下的田野考察中有一些出入,尤其是婚俗中前期的盘王庙中“对歌结亲”仪式中,在当下田野现场几乎已不复存在。如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人语·傜人》(卷七)记载:“岁仲冬十六日,诸傜至庙为会阆。……徭目视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庙,男女分曹而坐,唱歌达旦。以淫辞相合。男当意不得就女坐,女当意则就男坐。既就男坐。媒氏乃将男女衣带度量长短,相若矣,则使之挟女还家。越三日,女之父母乃送酒牲以成亲。”[2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傜人》(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7页。上述历史文献记载与当下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在场文本之间存在一些偏差,这与瑶族民俗生活方式的历史变迁息息相关,如瑶族祭祀仪式中盘王庙由于“文革”期间多已经破坏,同时现代化、城镇化等多重文化因素导致的瑶族民俗仪式的生存语境发生了变迁,因此瑶族婚俗仪式中一些古老的民俗仪式场景我们在当下已很难看到。还比如笔者在考察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族群边界的阶段性、动态性建构与音乐认同问题时发现,传统音乐历史文献记载与当下音乐文本的族性表述之间有很大区别。因为,明、清、“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多重历史维度,政治认同、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变迁致使满族传统乐种的族性表述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即清代以前—“中华民国”—20世纪80年代成立满族自治县),如果我们忽略了上述政治、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维度,一度关注当下的音乐表演文本,我们也很难看到关注到传统的历史文献与当下的在场文本之间的偏差,当然情况是由于长期的不同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变迁、政治与文化认同,以及跨文化、跨族群间文化涵化原因造成的。
四、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由于权力与话语操演背景的不同导致的口述音乐历史资料的可靠性、稳定性、完整性问题遭到质疑
中国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有浩瀚的传统历史文献资料,而且也有很多重要的口述音乐历史文献信息供我们进行挖掘与采集,尤其对于有语言无文字的族群来说,口述音乐历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至关重要。其次,很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由于缺少主位文化的表述符号系统,这就造成其传统音乐文化的纵向传承中,基本是靠口传或口述方式进行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但是,这种文化传承的方式与载体的主要弊端是,由于某一文化母题在跨越时空的发展与变迁过程中,由于传承者审美观、价值观、文化认同理念的差异,会导致某一音乐“文化母题”在不同的传承人(或口传者)的叙事过程中,出现信息筛选或者改造的情况,因而会造成其传统的“文化母题”信息的本真性发生变异,也就是我们学界认为的口述音乐历史文献信息缺乏可靠性、稳定性、完整性。因此,为了尽可能还原音乐文化历史信息的事实与真相,在实际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过程中,我们的研究者要充分结合田野考察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尽量做到类似局内人文化身份的观察与体验方式,分析与观察被研究者在面对某一音乐的“文化母题”内容的叙事结构与逻辑思维,重点审思我们的叙事主体人在田野在场语境中是如何言说的?言说的方式(如语言逻辑组合)的差异,以及作为文化转译的翻译者的再阐释,等等因素对于“文化母题”本真性叙事的影响。因此,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口述音乐历史文献信息搜集的可靠性、稳定性与完整性内容,是与研究双方的文化身份(官员、民间艺人、学者、NGO,等等)、访谈双方在场的互动、访谈者的田野深度,以及叙事者的言说方式,等等因素直接关联。正如笔者认为:“无论是历史地田野还是案头工作的史料分析,民族音乐学研究者还要深入关注音乐文化史料的叙述方式(书写方式),分析其史料背后隐藏的不同寻常的文化逻辑与含意。注重田野工作现场(仪式)音乐在特定文化语境中被如何操演的,以及口述文本资料的搜集中,被访谈者对“乐人”“乐事”的历史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叙述的),要关注音乐文化的历史史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问题是如何形成的,等等问题。”[22]赵书峰:《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后现代思维——基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反本质主义思考》,《音乐研究》,2017年,第4期,第65页。所以,这里也说明一个深刻的问题,即,我们在田野实践中搜集到的口述音乐历史“文献”难道就一定是本真性的音乐史料吗?
五、作为汉文化表述系统的“他者文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书写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历史文献的书写方式,多是一种客位的表述系统,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历史文献(比如苗、瑶、壮、侗、毛南族、土家族等等),多是借助汉语表意系统的一种书写表述方式。这些族群的民歌、宗教仪式音乐、历史传说、历史故事等等带有历史文献信息的史料系统基本都是借助汉文化书写而存在的。比如南方少数民族的宗教经文文本。但是,这种以客位文化书写进行主位文化表述的方式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其一,作为一种客位文化表述系统的书写方式在传达某一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历史信息之时,由于受到不同族群语言之间表意功能差异性的影响(语义学),借用汉文化的语言表述方式来记录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历史信息,难免会因语言(语义)的表意系统的差异在传达某一段少数民族言语所表达的实际内容时,其语言的所指将会不完整甚至是缺乏准确性;其二,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历史信息,多是作为一种“他者文化”被汉文化表述。这种客位身份的书写方式,难免带有受“汉族文化中心论”影响下的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审美等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以及政治、权力与话语相互作用背景下的主观建构。因为,“所有的表述,因其是表述,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23]〔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49页。“正是用汉文创造了一套以王朝叙事为主的表述系统使得文献记载都是先由中心,而后产生与中心发生关联的边缘,没有关联的,就隐没在历史中。”[24]沈海梅:《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姓与认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页。因此,汉族传统历史文献(不但是官方历史文献还是民间历史文献)在记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历史文化信息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种文化系统综合价值判断后的武断思维。这样也会导致当下遗存下来的传统历史文献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客观性问题遭到质疑。因此,在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中,面对汉字书写的少数民族音乐历史文献记载,我们要用历史学研究者的眼光对文献进行分析与辨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相对客观与接近真实的历史文献信息。
六、少数民族音乐历史文献信息(尤以中国南方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两种表达系统:口述历史文献——母语系统(主位);传统书面历史文献——汉字文化书写系统(客位),呈现出少数民族与汉族传统文化二维(“濡化”“涵化”)的历史结局
承载着两种文化表达系统的族群代表主要是以苗瑶语族、壮侗语族为主,这些少数民族音乐(苗、瑶、壮、侗、土家等等)文献的记载方式主要分为:以族群母语符号为载体的口述传承,以及借助汉字文化(甚至受汉字影响的“土俗字”)为载体的文本书写。[25]据笔者2018年2月对老挝、泰国尤勉瑶传统音乐的调查研究看到:不但在中国西南的大部分族群传统文化的书写系统中多用汉字表述方式,而且在东南亚国家(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苗瑶传统音乐中也保留着大量的汉文化表达习惯,比如瑶族还盘王愿、度戒、丧葬仪式等民俗活动的经文中都以汉字书写为主。比如在瑶族“盘王大歌”仪式经书中,对于瑶族文化历史的记载中,仪式师公在唱诵经文歌书之时,仪式中的声音语言符号(瑶语)与作为历史文化信息记载的书面文本(汉字或拼音),两种所表达的语言中的“能指”内容各有差异,因为上述两者之间虽然诵唱内容与经书一致,但是由于声音代码和经文文字代码是属于两种不同的表意系统。前者是主位的声音表意系统,后者是客位的受汉文化影响与建构下的书面文本表意系统。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鲜明地表达出瑶族传统音乐文化在其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语境中,文化之间的“濡化”与“涵化”的当代结局。同时,西南其他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也存在着这种十分独特的音乐文化的表述系统,并鲜明地体现出“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过程,这种文化变迁样态,折射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其过往的发展历程中文化的“变体链”“时间链”的两维叠构。
结语
总之,正如笔者认为:“在日常的田野与案头工作中我们不但关注到对研究对象的当下鲜活的存在状态的在场文本的考察研究,同时针对其过往的历史发展与变迁轨迹进行纵向的挖掘与梳理。同时,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绝不是纯粹地偏重于文献文本考察整理性质的历史音乐学研究。我们要借鉴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念,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当然也是田野现场),重温历史记忆。因为,历史民族音乐学思维告诉我们: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要关注当下鲜活的音乐(仪式)活动的文化隐喻问题,同时也要针对其过往的历史构成轨迹给予历史文献与口述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将历史事实与田野资料之间进行相互贯通。”[26]赵书峰:《跨界·区域·历史·认同——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四个关键词》,《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25页。所以,当下的中国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我们的学者不但要进行研究对象的历史与当下的互通性研究,而且也要面对音乐历史文献不同的文化表述系统、研究者与对象之间的权力与话语操演系统的差异,以及“汉族文化中心论”思维影响下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历史的主观建构,等等系列因素导致的音乐“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与“口述文本”之间的偏差问题进行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