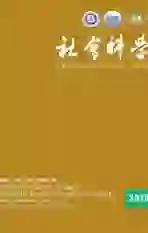作为身心治愈的“神圣”
2019-05-15金寿铁
摘要:海德格尔一边宣告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的终结,一边号召人类为迎接新的世纪做准备。西方形而上学之所以宣告终结,是因为它始终以存在者为中心、以理性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大幅压缩裁剪存在的视域与意义,以致彻底根除了“无”的历史地位。鉴于西方理性主义思维不可逾越的界限与种种弊端,海德格尔的从存在到神圣的思维转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导向意义。但是,海德格尔因噎废食、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把理性视为“万恶之源”,不除不快,以至于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理性主义的泥沼。
关键词:理性主义;理性;无;神圣;治愈;新的理性
中图分类号:B516.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5-0132-13
作者简介:金寿铁,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吉林长春130033)
当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地球村。在这个地球村时代,支撑西方文明的三根逻辑支柱是科学技术、自由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本溯源,这一切都根源于西方“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①的思维模式。多亏理性的繁荣昌盛,“现代人”过上了锦衣玉食、安枕无忧的日子。但为了维持这种富裕生活,现代人信奉“消费即是美德”的口号,不惜“比阔斗富”“奢靡挥霍”。然而,现代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更富裕、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正是以自然的破坏与人心的崩溃为前提的。事实上,就像古代世界文明一样,西方文明正在衰败没落,建立在西方所谓“理性”(Vernunft)传统基础上的现代科学技术文明酝酿着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紧张和对峙,正把整个人类和地球万物推向万劫不复的地狱深渊。②
面对20世纪“世界的崩溃”、“地球的荒芜”这一无家可归的人的命运,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rgger,1889-1976)一马当先、单刀直入,严厉斥责以主体为中心的西方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以及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无情揭露“非地球的宇宙支配逻辑”及其危害,进而强烈主张一种新的哲学思维基础上的新的开端的必要性。据此,他坚定地认为,人类当务之急的是,必须从自身的生活世界中,即当下“绝对的技术国家”中,重新找回被放逐掉的那个存在的“神圣”维度。他把这一迫在眉睫的“新的思维的任务”表述如下:“只还有一个神能拯救我们。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在思维与诗歌中为神的出现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神的不出现作准备。”Martin Heidegger, Spiegel-Gesprch mit M.Heidegger, Antwort. Martin Heidegger im Gesprc h , Neske, Pfullingen 1988,99/100.
一、理性主义思维的界限与弊端
西方形而上学的展开过程历经2500年,海德格尔的哲学思维将这一展开过程的开端和主轴规定为“一个叫做人的存在者进入存在者全体的事件”。Martin Heidegger,Was ist Metaphysik?(1929) In: GA 9,Wegmarken (1919–1961), ed. F.-W. von Herrmann, Frankfurt/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76,S. 105. 这正是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理解,而这一理解的起点是人对宇宙论存在发生事件的态度,即对存在者全体的态度。为了从不计其数的宇宙秘密中查明这一维度和深度,为了进一步接近并熟悉自身的生命空间,人们不惜引入莫名其妙的 “神话故事”。通常人们怀着一颗谦虚之心,试图通过全盘感受N维和无根据性,进一步如实接受N维的、无根据的宇宙的生成与展开。然而,即使在此神话阶段,也包含着某种狂妄傲慢的努力(筹划),即借助对宇宙事件的说明和理解,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化为己有,将其变成人的活生生的现实。换言之,在此,人偷换概念,暗度陈仓,将无底的宇宙秘密还原为肤浅的神话故事。
人是可思维的、可言说的理性动物,所以人渐渐为语言的威力所吸引。人不再满足于安静漠然地认知并接受可思维的东西,不再满足于依存于想象力的神话故事,而是开始关注凭借理性所能知晓的所谓“有根据的故事”。人开始了解到,他可以用理性语言装载各种宇宙事件、自然现象,并与其他人交流相关故事,对其事态交换彼此的经验和知识。于是,人开始尝试把经验和知识加以综合和体系化,开始认为,唯有“有根据的话语”(逻各斯)所揭示的东西才是共同的普遍东西。由此出发,产生了作为学问的哲学,人开始相信,他所形成的世界是可以用语言加以说明和把握的。于是,人主要靠理性语言来构筑人与存在者全体的关系。
人的思维的工具无非是普遍范畴。人对宇宙理性根据的探究意味着用“存在者”这一普遍范畴来束缚并说明自然中遇见的一切东西。人开始尝试并固定多种多样的说明框架,力图通过语言(概念)来说明和解释现实世界。凭借一种普遍概念框架,人不仅抽象地解释现存的一切东西,还赋予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东西一种一般的存在意义。然而,在抽象化、一般化这双重过程的作用下,世界万物被迫“洗硫酸澡”,直至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全都丧失其鲜活的具体性和个别性。尤其是,哲学理性借助存在、理念、实体等普遍范畴将单个个人所特有的具体性和个别性、时间性等加以抽象化、概念化,使其仅仅在理性王国中被保存为笼统的知识,即逻辑符号和象征。
不仅如此,按照主语谓语的语言结构,现实也都被解释为“实体(本质)与属性”,从而造成现实本身的实体化。于是,哲学的任务就是撇开一切现存事物的具体个别性、时空条件性,着力阐明所谓永恒不变、亘古如斯的实体及其本性。问题在于,存在者的实体论本质是一种超驗的东西,即肉眼不可视的、隐匿于感觉背后或底层的东西。对此,我们只有凭借精神(灵魂)之眼,才能一窥堂奥,洞察其蛛丝马迹。
然而,哲学却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开始致力于从“实体论”观点阐明现实,认为质料是万物的基质,是宇宙万物的组成材料。但是,它发现哪儿都找不到“原初质料”,即没有形式的纯粹质料。于是,这种观点无奈低头求助于“理念论”,认为造物主以“理念”(Idee)为摹本、原型塑造原初质料,创造存在者本身。因此,所谓实体论的考察方式与世界的理念化过程一脉相承、同流合污。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一过程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以至于造物主的创世观念被推翻以后,这种考察方式依这一过程依旧纵横捭阖,主宰世界命脉。在此所不同的只是其理论根据不再是上帝的观念,而是代之以具有同等能力的“世界理性”(Weltvernunft)罢了。Martin Heidegger ,Vom Wesen der Wahrheit , Frankfurt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97,S. 181.
作为理性主义思维的代言人,所谓“世界理性”为自身立法,从而也要求其合乎逻辑的程序的直接的明白可能性,其结果现实与理念头足倒置,导致笛卡尔意义上的“实体二元论”的无序与混乱。最初,理性主义思维把万物的根据统统归结为“神”这一最终根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越俎代庖,开始把现实也一并纳入加以说明的范畴之中。神的存在植根于启示和信仰,这种存在可以成为有所保留的“启示真理”,但不能成为作为哲学乃至学问(科学)基础的第一原则。由于意识到这种真理的局限性,哲学越发恣意妄为,开始进一步探索所谓颠扑不破、确定无疑的真理。既然唯有理性才有资格探求真理,那么也只有真理探求者的“主体”(Subjekt)才能成为最重要的哲学主题。
于是,第一哲学由神学转变为认识论,实体转变为人的主体。对此,海德格尔解释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其自我规定性在于,人成为存在者的中心和尺度。人成了决定一切存在者的主体,也就是说,人成了决定现代一切对象化和想象力的主体。”Martin Heidegger,Nietzsche Zweiter Band, Neske, Pfullingen1961,S.313.唯有作為主体的人才是确定不移的认识基础,而作为客体的其他一切都是与人这一主体相对应的、可认识的对象。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展开历程中,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主客二元分立模式恰恰酿成存在者乃至现实方面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物化现象:
第一,存在者的同一化、划一化。由于现实被二元化为思维与空间,所以,一方面,现存的一切东西都占有空间;另一方面,一切占有空间的存在者都可以计量化。根据数量的单一性与空间的计量化,一方面,现存的一切东西都可作为占有同等空间的事物划一化;另一方面,计量化、可量化的存在者既当作可重复的东西加以实验,也当作可生产的东西加以制造。人是认识主体也是存在主体,根据使用目的以及对人的存在的意义,一切与人相对的对象均可实用化、功能化。
第二,存在者的生产化、产品化。存在者被功能化,导致存在者自身独立地位丧失殆尽。换言之,存在者不再是与人相对的独立存在,而是按其总体脉络中的功能而被赋予存在意义。于是,就像一架机器上的螺丝钉,存在者的功能只是充当一种随时随地可搭配的零件。在一个全面产品化的世界中,根据存在者全体的功能,一切东西都按其功能待价而沽,都可被其他东西替代,或者都可被制造为其他零件。
第三,存在者的原材料化、商品化。存在的一切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纯然是因为它是某种可替换的零件。换言之,它必须作为全体所需零件的可能原材料而存在。现存的一切东西都是用以制造其他某物的可能的原材料。根据存在的原材料化,现存的一切东西都成为可使用、可利用、可活用的材料。于是,一切东西都具有双重功能,既是金钱可购买的商品,又是可再生产的产品。
第四,存在者的消耗品化、需求化。根据存在者的商品化,一切产品(商品)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切消费品都必须符合消费者的癖好,因为任何消费品之所以存在,纯然在于供人消耗。于是,广告业勃兴,各行各业都争先恐后使用广告战略,以刺激消费者无限膨胀的需求,创造新的需求。昔日人的需求是维持基本生存的必要手段,而如今人的需求早已冲破底线,开始走向无限制的所有和消耗,而广告媒体正中下怀,可以轻而易举地操控这种不知厌倦、欲壑难填的需求。
第五,现实的形象化、虚拟化。正如现存的一切东西都成为进行生产的原材料一样,现存的一切东西也都可以成为触发人的需求的形象。如今人们与其期待消耗具体的产品,毋宁期待抽象的消费形象(影像)。现实已成为形象消费的素材。现实作为形象被投递到家家户户。然而,被投递的形象现实已不再是实在的现实,而仅仅是想象中的虚拟现实。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被消除,虚拟一跃变成更现实的东西,进而以假乱真,占据了现实的位置。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只有完整地说明理由才会得到保证。任何前置的东西随时随地都能够指望对象和算计对象。”Martin Heidegger,Der Satz vom Grund, Pfullingen,Verlag Günther Neske, 1957,S.196.一句话,现实即虚拟,虚拟即现实。
在1936-1938年的一部草稿《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中,海德格尔围绕“本有”(Ereignis)概念,全景式地展开了西方理性主义思维所造成的满目疮痍的荒芜现象。其基本景象是:诸神在“本有”中显现,召唤了大地与世界的争执,启明了稀罕之人,将之置入“此在”中;然而存有的本质现身也是一种自行遮蔽的澄明,自身就注定了世界的黑暗化的命运;而人降低到用逻辑对象化技术谋划来把握存有(Seyn)时,存有隐匿,诸神遁去,只剩下硬化的存在者和荒芜。\[德\] 马丁·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现代人笃信,投递到家的形象就是实在的现实,所以各自躲在狭窄的的密室里,不分昼夜凝神关注电视、电脑、手机等机械,日益沉迷于恍惚的虚拟现实中。随同机械所提供的虚构现实,现代人时而欢笑,时而悲泣。换言之,现代人将自身的需求全盘托付给机械操作,按照机械发出的指令解决他们的欲求,从疯狂的游戏和消费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就像机械怀抱里的婴儿一样,现代孤独而机械化的隐者门将自身完全托付给机械,期望由机械来解决自身所无法处置的“自由时间”,即无处消磨的余暇。
如今整形手术一路走红、魅力不衰,一时间,似乎什么问题都可从肉体维度加以修复和解决。然而,人不仅仅是肉体,而是人格与灵魂。“人本质上就是一堆烂肉”这句赤裸裸的话恰恰使灵魂、理性、人格一落千丈,变得一文不值。于是,自私、贪婪、平庸、虚伪等大行其道,而精神文化、相知相遇、友情与朋友、爱与宽容等逃得无影无踪。对现代人而言,精神快乐只是错觉或歧途而已。他除了一片空荡荡的周遭,只剩下赤裸裸的肉体快乐。至于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基于爱的精神合一之类的东西恍如隔世,不啻痴人说梦。
总之,按照海德格尔的分析,西方理性主义正是现代人“茫然若失,无家可归状态”(Unheimlichkeit)的始作俑者。Vgl. 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 19. Auflage,Niemeyer, Tübingen 1979.S.277.究其本质,这种奉“理性”为圭臬的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只顾眼前存在的“在场的形而上学”,是一种以“理性”之名驱赶黑暗势力的“启蒙的辩证法”,是一种无条件贯彻人的支配意志的“意志的现象学”,其实质是排他性的“欧洲文化优越论”、自大和虚妄的“西方话语霸权”。
二、哲学的终结与思维的任务
鉴于西方理性主义思维的种种弊端和危害,在《泰然任之》(Gelassenheit,1955)一文中,海德格尔有意识地将思维划分为“计算性思维”(das rechnende Denken)与“沉思性思维”(das besinnliche Denken)。Martin Heidegger, Gelassenheit, Neske,Pfullingen 1977, SS.21-22.所谓“计算性思维”是指工具技术的、关涉目的的、因果律的、表面的思维。这种思维注视并分析業已显现的东西,并从因果律角度把它们连接起来,然后,进一步预测萌芽状态,眺望未来,判断关联事态。
与此相反,所谓“沉思性思维”是指揭示深藏于形而上学问题深度的那种隐匿的、有保留的东西的思维。如果从计算的思维角度,即从技术的、工具的、合理的、目的论视角看哲学,那么哲学确已终结了。不过,这种形而上学思维的限度也标志着哲学思维可能性的终结吗?由于这种偏狭的计算性思维,从事哲学研究的思维也终结了吗?海德格尔认为,追问就是寻找答案之路,而答案并非仅仅止于谈论某种关系事态。追问意味着必须敞开思维自身的变化可能性,追本溯源,寻找答案之路。而且,一旦这种答案妥当到位,它就势必变革思维。因此,我们不应从一种外部的、表面的、日常语言视角看待这种追问与答复的关联性。这样,海德格尔心目中的“追问答复”的关联性意味着因势利导,将计算性思维转变成沉思性思维。
哲学是自身时代精神的反映。在自身时代精神的反映中,哲学持有自身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换言之,在自身时代的危机中,哲学持有“对应”(Not-Wendigkeit)这一宿命任务。海德格尔把当今尖端“生物技术”(Biotechnologie)视为科学的极端可能性,并从这一现代尖端科学中,他看见了哲学的命运般的终结。那么,在这哲学的终结时期,思维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任务呢?Vgl.,Martin Heidegger, Das Ende der 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 des Denkens In:Zur Sache des Denkens, Tübingen, Niemeyer1976, SS.61-80.在他看来,所谓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对特定哲学的理解,即某一时代特定形态的形而上学达到其极端可能性而归于完结。作为完结,终结乃是极端可能性的聚集。简言之,如今哲学已到达其极端的可能性,即哲学已进入到自身的终结之中。
但是,这种终结并非是突然爆发的结果,而是西方哲学历经2500年长期酝酿发酵的结果。早在希腊哲学时代,哲学的决定性特征就已经出现在时代之中。就是说,哲学乃是在开放的视野中发生的科学的形成。科学的形成过程同时是科学从哲学独立出来的过程,是如此这般奠定自身独立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属于哲学的完结过程,是对这种完结的缓慢准备。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独立性、文化人类学和人类学的独立性、符号逻辑学和审美逻辑学作用等都是在哲学的完结中凸显的现象。Ebd., S.63.
今天哲学已沦为关于人的经验科学。通过无所不能的人的技术,所有能够成为可经验的对象的东西都已成为经验科学的对象。作为基础科学,这些经验科学为新的“控制论”(Kybernetik)所规定和调节。哲学从独立科学中如此展现出来,恰恰意味着哲学的一种合法的完结。哲学在现时代中终结了。这一哲学的位置在于关于社会行动这一人性科学之中。然而,这种科学性的基本特征就是自身的控制论,即技术特征。从前哲学的任务是记述自然、历史、法、艺术等存在者的诸领域,如今可谓风水轮流转,这一任务早已由科学取而代之。旨在表象的、计算的思维操作领域和力量如此辽阔强大,以致席卷天下,压倒一切,占据绝对支配地位。
哲学沦为科学,而科学行使哲学所特有的使命。于是,哲学水到渠成,到达其终结。那么,这种哲学的完结除了留下技术化的科学所致的“哲学的消解”这一最终可能性之外,是否还留下第一可能性?换言之,如今哲学的可能性不得不从“被消解”这一最终可能性出发,但哲学作为哲学是否还留下另一种可能性,即虽然无法如实经验、亲眼看见,但可接收来自“无”(das Nichts)的一丝微光的可能性?Ebd., S.65.
在《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的讲座中,海德格尔将“无”规定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实际上,在人的生存中,这个基本问题一直作为存在的本质而存在于形而上学中。只有在“无”中脱颖而出,人的此在才能表现为存在者的状态。只有从“无”中脱颖而出,人的此在才能表现为存在着的状态。只有“无”的问题作为此在的原因被特意追问时,人才能跃入此在中。然而,问题在于从前的西方形而上学完全排除了“无”的范畴,以至于“无”不是作为否定和否认的思维方式而存在,而是作为从中派生其一切否定和否认的思维方式而存在。
何谓“无”?就像“存在”(Sein)一样,“无”不是人,不是神,也不是存在者。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存在的另一面,“无”是对存在者之总体的完全否定,是从存在者方面被经验的存在。“无”既不作为存在者显现自身,也不成为认识的对象。“无本身虚无化。”Ebd., S.65.因此,唯有通过区别存在着的东西,并超越作为知性的存在认识,才能洞悉“无”的蛛丝马迹。“无”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重要的是,我们直面无,坦然接纳无。“无”恰恰通过“畏”(Angst)显现出来。唯有当作为“常人”(das Man)的我们回归于我们本真的自我,即“生存”(Existenz)时,我们才有机会遇见这个“无”。我们日常感受到的、无法知晓其对象的“畏”正是源于这个“无”。
在弗莱堡大学1955/56年冬季学期讲座《根据律》 (Der Satz vom Grund)中,海德格尔正式宣告了“理性主义的终结”(Das Ende des Rationalismus)。他指出:“无并非無根据” (Nihil est sine ratio),这正是根据律。在这种形式中,根据律比下述肯定的陈述更明确、更有约束力:“一切都有其根据”。根据对于每一种存在者都是必要的。在本次讲座中,海德格尔着手形而上学的展开或解构,这意味着把根据律提升为最高的根据律,但同时假定根据律这一概念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海德格尔揭示了形而上学基础上的一种循环论证,即“无”是根据逻辑规则所不可能证明的东西。这个问题,即“无”作为最高根据律是不可证实的,但同时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根据律中,通常假定关于“无”的根据律的言论是三缄其口、默不作答的。然而,海德格尔敏锐地指出,在核物理学中,人们与物体的联系方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核物理学决定性改变了人们对整体的看法。”Martin Heidegger, Der Satz vom Grund (1955-1956),Verlag Günther Neske, Pfullingen1958,S.10.由此得出的结论只具有暗示意味,但其重要性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的第7个年头,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的第26年,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他显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核能的毁灭性后果,而不是它的和平使用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毕竟哲学为这种来自“无”的微光的第一可能性留下了地盘,因为除了表象性、计算性思维之外,还有沉思性思维。在哲学的开端中,思维曾经一石二鸟,尝试这两种可能性,但随着理性的兴起,思维越来越偏离最初的双重旨趣,越来越沉伦为纯粹的表象性计算性思维,最终变成单纯寻求根据与说明的形而上学思维。因此,在当下世界文明进程中,我们所遭遇的哲学的终结仅仅是表象性计算性思维的完结,而不是沉思性思维的终结。但是,唯有当沉思性思维回归我们自身的本真的生存时,我们才有望感受并捕捉“无”的蛛丝马迹,从而为遇见“无”铺平道路。因此,现在思维应当回溯自身,学会与自身中仍然保留的东西,即沉思性思维发生关联。与此同时,在这种学习中,思维也应当做好变革自身的准备。
那么,在西方哲学关于哲学的事态及其方法论探讨中,究竟还留下哪些未经思维的东西?那就是哲学的事态借以显现的那种“亮光”(Helle)。这种亮光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此时此地,或适逢其时,存在可以制造这种亮光的一种敞开的场所、豁然开朗的场地。换言之,现存的东西得以在其现存状态中显现出来,其先决条件是场地的敞开状态。海德格尔用“林中空地”意义上的“澄明”(Lichtung)来标明这种使显现成为可能并确保其外显的敞开状态。Martin Heidegger, Das Ende der 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 des Denkens In:Zur Sache des Denkens, Tübingen, Niemeyer1976, S.71.澄明就是“无蔽”。光渗透这敞开的场地,这是光明与黑暗在游戏。值得注意的是,光不能缔造亮光,相反,光须以亮光为前提。然而,亮光,即敞开的场地不仅对于光明与黑暗是自由状态(敞开状态),而且对于响声与响声的停息、音响与音响的停息也是自由的。在此意义上,亮光是为着一切现存的(在其位置的)东西与不在的(不在其位的)东西而敞开的场地。
海德格尔强调,对于思维而言,重要的正是关注“亮光”之名下的某种敞开事态。而且,此时尤其重要的是,格外留意在亮光之名下,合乎事态地被命名的独一无二的事态。海德格尔把思维在其中所遭遇的理应被思维的东西,即这种为“应被思维的思维的事态”所击中的敞开的场地命名为“原初事态”(Ursache)。Ebd.,S.72.亮光不仅保障通向在场之路的可能性,也保障在场性自身的可能的出席。作为澄明的“无蔽”(Aletheia),亮光必须上下通达、左右逢源,确保存在与思维在彼此敞开中相互在场。Ebd.,S.75.人可以经验和思维作为澄明的无蔽,但并不能直接经验和思维作为自身的无蔽究竟是什么。这是一种蔽而不明、深不可测的的隐匿状态。这是因为在无蔽中,隐匿自身的特性,即“隐蔽性”(lethe)不断得到提速和加强。对于这种隐匿、这种“无”,我们应当虚怀若谷,孜孜以求,时刻敞开心扉,持之以恒,以捕捉其经验的可能性。人的一种独特能力在于,心有灵犀一点通。在飘忽不定、可望而不可即的地平线上,他能够为“无”所击中。但是,现代人为存在者所笼罩,执迷不悟,越陷越深,为了不断填充存在的空虚,他下意识地反复说:“无的东西就是无”。
众所周知,达尔文等人的进化论把人视为由猿猴进化的结果,由此大胆冲破了神创说的宗教神学思想,率先为人的肉体恢复了名誉。但是,作为现代哲学史的一大特征,现代人借题发挥,将“肉体的发现”推至极致,达到大错特错,甚至荒谬绝伦的地步,以至于在他们那里出现各种极端的兽性退行和返祖现象:“我只是我的肉体,我既不在肉体之上,也不在肉体之下”。我所赋予的最高的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享受这唯一的肉体。现代人仅仅满足于从猿猴到人的进化,一味强调和标榜自身的肉体。但再美丽的猴子与人相比也丑陋百倍。即使进化得再好,猴子终归还是猴子。如果蝇营狗苟、浑浑噩噩的日常生活世界就是全部生活世界,如果生命的最高目标仅仅是寻求最大的物质利益和生活安逸,那么就绝不会有拯救。进言之,如果完全剔除精神的东西而仅仅追求肉体的快乐,那么天下就绝不会有拯救。在沉思性思维中,绝对没有无魂魄的、无灵性维度的日常生活的拯救。
哲学的终结意味着科学技术世界及其社会秩序控制可能性的凯旋,意味着建立在西欧理性主义思维基础上的世界文明的开端,意味着工业社会全盘占领古老的历史传统的地盘,其结果导致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命运”。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存在者被存在自身所遗弃。存在的遗弃包罗万象,涉及到一切存在者,而不仅仅只有人这一种存在者,人把存在者想象为存在者自身,在想象过程中,存在自身失去了其真实性。”Martin Heidegger,Nietzsche.Zweiter Band , Neske, Pfullingen1961,S.195ff.现代人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孤零零地置身于工业社会的钢筋水泥之中。在极度的精神困境中,荒谬而无助地“等待戈多”——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未来面貌吗?参见 \[法\] 萨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余中先、郭昌京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面对不确定的将来的彷徨苦闷,海德格尔一再重申思维的任务:在神圣的视域下,把昔日当作虚假不实的东西而打入冷宫的“无、空、虚”统统召唤到存在的场所,为其开辟新的遇见可能性,以此缔造新的交往机制和对话场所。这是一个攸关人类命运、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想倒退到野蛮、颓废的“工业幼虫”中去,我们就必须立刻行动起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寻求解决危机的对案。
三、“神圣”的意义与维度
西方近代化趋势与宗教改革以后的启蒙运动一脉相承。启蒙运动和形而上学世界观携手并肩,普遍控制人的生活世界,统合了所有人的情感状态和精神領域。但是,随着近代化的日益推进,这种统一的世界观开始土崩瓦解,世界日趋分化。以神为中心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开始让位于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世界观。然而,神的隐退或逃逸恰恰造成了一个双重贫乏的时代:即逃遁的诸神的“不再存在”(Nichtmehr)与到来的神“尚未存在”(Nochnicht)的时代。
由于神的逃逸和缺席,神性光辉在世界历史中的黯然熄灭,世界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基础,径直悬于无底深渊(Abgrund)之中。世界一片漆黑,就像深不见底的黑洞。正是在这种无所傍依、一片黑暗,不可测度、持续扩张的混乱漩涡中,海德格尔率先把“神圣”引入哲学思维之中,其目的在于,将神圣经验当作追踪诸神之神性的痕迹,引导人们返朴归真,消除身心疾病,达到宁静致远的澄明之境。
语源学上,德语“神圣”(das Heilige)一词与“完好”(perfekt)和“治愈”(heilen)相关。神圣意味着“无损伤”(das Unversehrte)。例如,我们常说,有人大难不死、遭遇飞来横祸却躲过一劫(Heil)、安然无恙(Heil)等。即在危难之境中,某个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完好无损地脱险。此外,神圣还有动词“治疗、治愈、愈合”(heilen) 之意。例如,一个人受伤了,医生通过治疗使患者康复。即救死扶伤、治病救人。Vgl.,Johannes B. Lotz, Vom sein zum Heiligen Metaphysisches Denken nach Heidegger, Frakfurt /Main 1990, S.120ff.进一步讲,德语versehren意味着“致伤、致害”,而heilen则意味着使受伤、受害的东西重新完好如初。因此,一方面,完好(heil) 状态是本来的初始状态;另一方面,神圣意味着进一步可到达的某种最高状态。
由此可见,“治愈”(heilen)意味着某物恢复完好状态,或者意味着为它通向这种完好状态铺平道路的最高状态。日常用语中的“神圣”(das Heilige)概念是指在受生存威胁、命悬一线的状态下,人的此在在其中所具有的独特二重存在方式。人们处在威胁的漩涡中,但某些人化险为夷,得以完好无损(heil)地保留下来,或者在席卷天下的破坏的漩涡中,这个世界竟然固若金汤、完好如初(heil)。这种对“完好如初”的原初经验是迄今哲学家们几乎完全没有在意的独特的、新的存在经验。一旦我们试图勾勒日常用语中未经反省的这个单词,我们就遭遇其独特性。当我们指称某物完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它与不完整的东西,即支离破碎的东西或受到伤残的东西(废弃的)东西严格区别开来。
我们说某物完好,借此凸显某物完好地保留下来。我们特别凸显这一点,是因为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令人惊愕。因此,在自身茫然无知的存在中,全然不致毁坏的东西,例如,路上横亘的一块巨大的岩石,我们称作完好无损。此外,易于破碎的东西,例如,在破坏的漩涡中,一只小巧玲珑的花瓶居然毫发未伤,我们也称作完好无损。再者,当我们说某人完好无损的时候,特别指某人从战场上安然无恙荣归故里。这时,完好地保留下来的东西经常被视为一个奇迹,尤其把它视为承蒙从毁灭的深渊中受到庇护的某种东西。
综上所述,在日常用语中,神圣的基本特征可概括如下:
第一,神圣涉及易碎的东西、易受伤的东西、易受损的东西,但神圣并不谈论从一开始就不会破碎的东西。第二,神圣涉及在注定会破碎的状态中,某种易碎的东西居然未被打碎而保持完好。第三,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中,突破重围、转危为安,仿佛冥冥之中受到苍天眷顾,总让某物劫后余生。这一切都指明一个全新的维度,显然这是日常理解所无法想象的、用合理思维所无法解释的另一维度。第四,正是这个未经说明的维度制造和维持“完好”,从而暗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力量。如果更加仔细地考察日常语言用法,那么神圣还意味着伤口的治愈或身心的康复。
作为心身治愈的良方妙药,神圣指向下述两个维度:
第一,与某一生命的肉体状态相关,神圣不仅确保该生物体完好如初,也确保期治愈(Heilung)的过程。这一痊愈过程,我们归功于自然的复元力量,即痊愈力量。因此,所有有机体都显示出不顾一切创伤,重新追求并复归完好状态。这时,在某种程度上,医生的人为技术有所裨益,为其恢复助一臂之力。在此,我们也深深体会到借以痊愈和复元的那种隐匿的、深邃的存在的根据。其实,易碎的东西、易受伤的东西、易损伤的东西等字眼已经预设了伤情及其预后的判断。正因如此,曾经受伤的东西才有复原过程,或者才有“治疗、痊愈、完好”等话语。在此不难想象,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犹如春风化雨、枯木逢春,它使某一生物体完好无损地复归初始状态。自然有机体或生命体都呈现这种奇特的恢复能力,这正是神秘的自然的力量。相比之下,作为人为技术,人的治疗行为充其量是一种辅助,好比开闸排放自然固有的神秘力量,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而已。
第二,与宗教救赎意义相关,神圣确保“灵魂拯救” (Heil der Seele),即促使一个人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时,拯救意味着一个人在最严重的生命威胁中得到终极拯救。这里也预设了“灵魂易于受伤害”这一前提,即由于自由意志,灵魂着实容易受伤。但要洗心革面,复归纯洁完好的状态,这已经超出了灵魂自身的力量,因此,这种复归必须诉诸于神圣的力量。在更积极、更肯定的意义上,神圣拥有比治愈更深的维度。此时,如果某种东西受到伤害、毁损、减少或破坏,那么这东西就与不可受伤、不可侵害或毁损这一神圣本质背道而驰。此外,我们还必须郑重守望这一要求,认真接受与此相应的行为。藐视这种尊严并拒绝这一要求的人是亵渎神圣的人。这种亵渎从人的此在中夺走其最后的高贵完成,将其驱入极度混乱之中,使其陷于翻转一切价值的通俗性之中。在此,作为一种绝对价值,神圣保存和维持“完好”,使之安然无恙、完好无损。
简言之,在日常用语中,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神圣是指保存、维护乃至制造完好状态的过程。下面,我们试着结合这一日常用法,进一步考察海德格尔是如何说明神圣的维度和意义的。
“神圣”(das Heilige)是海德格尔其后期著作中的核心概念。自尼采以来“神死了”、“神逃逸了”、“神失踪了”等话语一直甚嚣尘上、不绝于耳。无论如何,“神的缺席”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今的问题已不再是神是否已死,而是如何使“死了的神”重新复活?如何把“逃逸的神”、“失踪的神”重新召唤回来?如何为新的神的到来做准备?关于“即将到来的神”(Der kommende Gott)的详细讨论,Vgl., Manfred Frank, Der kommende Gott Vorlesungen über die Neue Mythologie, Frankfurt /Main,Suhrkamp1982.海德格尔断言:“只还有一个神可以拯救我们”。在他说来,在这漆黑的漫漫长夜里,人类必须为拯救之神的到来做准备,而当务之急的是为神的来临搭建一个平台,即缔造“神圣”的领域。我们只有在神圣之维中才能有幸遇见神,然而,只要人的无尽欲望之火仍然一统天下,我们就到处都与神失之交臂。
我们可从如下四个方面界定海德格尔视域中的“神圣”(das Heilige)的维度:
第一,海德格尔把自然的本质视为神圣。当自然苏醒时,或者,当有诗人应答自然的搭话时,自然就把自身的固有本质眨眼(zwinkern)为神圣。诗人中的诗人荷尔德林所领悟的作为自然的神圣是自然所固有的本质自身,它包罗万象、亘古如斯,它比任何时间都古老,比任何诸神都高远,它是不可伤害、不可损伤的、不可打碎的完好本身。换言之,自然的本质自身是一切起源的原初起源,一切由来的原初由来,它从自身不断溢出分支和支流,而它自身却毫发无损、毫不减少。作为永恒的万物之源,自然的本质自身是永不枯竭、永无止境的源泉本身。
第二,海德格尔把神圣视为敞开的场地。存在的一切东西,例如,自然事物、人为工具、人的历史和文化、诸神或神等都在这一敞开的场地中发生并展开。在这一敞开的场地中,不仅死者与其他人相知相遇,从而经验到不朽的东西,而且现实的一切东西也都相知相遇,从而经验到神性。这个场地一如过去,将来也会继续敞开着,它是任何境界都不可阻挡、不可关闭的无边无际的敞开本身。这个场地的敞开状态是一切存在显现的可能条件,是一切经验的可能条件。但是,如此这般地使显现成为可能的东西、使经验成为可能的东西不是在那里显现的、被经验到的某种东西,不是映入眼帘的某种东西或它自身就是可视的某种东西,不是水能够冲洗的某种东西或它自身就可被冲洗的某种东西。简言之,它是可以点燃火的某种东西,但它自身却不是可点燃的东西。
第三,海德格尔把神圣视为一切事物的动因和视域。神圣使我们将一切现实的东西都经验为现实的东西,神圣使一切自然的東西都作为自然的东西生成、变化和消灭,并且在其一切经验和变化中深深地隐匿自身。神圣的本质中持有这种隐蔽自身同时拔出自身的特征。因此,我们无法直接体验神圣。这是凭借秘密本身所无法说明的神秘的东西。作为无底深渊和本质,神圣犹如海底深流,深沉内敛、波澜不惊,无论其表面如何泛滥,它都深藏不露、不为所动。
第四,鉴于上述神圣的意义和作用,海德格尔进一步把神圣视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而神奇的力量。作为不可破碎、不可损伤的完好自身,神圣完美地治愈受损伤的东西。作为敞开的场地,神圣在自身的敞开状态中,赐予存在的一切东西一种完好无损的栖息。不仅如此,神圣救死扶伤,竭诚治疗一切不幸和损害,使其恢复原状,永葆青春活力。
根据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诗作的解读,我们可以把神圣的诸特征归结为完好无损(全体性)、敞开状态(开放性)、隐蔽自身(隐匿性)、神秘性(作用性)等。此外,这些特征都指明,神圣超出人的经验维度。以存在者为根据的视角,缺乏洞察力,无法预感这个神圣。因为作为无所不包的全体性,神圣压根就不进入经验视野中,即作为经验的可能条件,敞开自身不仅是不可经验的东西,也是隐匿自身的、不显露于外的神秘力量。
从单纯存在者的观点上看,神圣很难说是存在着的东西。严格地说,它是纯粹“无”的东西。以存在为中心的视角同样无法预感神圣。因为神圣不仅包含了敞开场地的敞开状态也包含了作为存在方式的时间空间,所以作为无所不包的全体性,神圣不可能进入存在视域。相反,神圣乃是使存在视域成为可能的无限敞开的存在、无底的黑暗深渊、无边无际的虚无。如果说“有”的东西以时空内的滞留为前提,那么包罗万象的神圣则把无边无涯的空间与无始无终的时间全体集于一身、融会贯通。因此,它绝非所谓“有”的意义上的某种东西。
如果人们被存在者蒙蔽眼睛,为当前化的(gegenwtigen)存在理解所束缚,以致仅仅从当前化的东西的当前(Gegenwart)中观察存在,就没有神圣的领域,也就谈不上神圣如何存在、何时存在。与存在遗忘的历史一道,神圣的领域归于消失,诸神纷纷逃之夭夭,这是存在史事件发展的必然的逻辑归宿。根据海德格尔的时代诊断,在科学技术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圣遭到冷遇的“不神圣的”(heil-los)时代。但是,我们时代的真正不幸在于,我们生活在这种不神圣的时代里不仅全然感觉不到这种“不神圣”,反倒称心如意,感到十分温暖和安稳。最高的危机就在于置身于危机而对此浑然不知。如果我们今天把“伤害”(das Un-heil)预感为一种危害,我们就会觉察到神圣在隐匿自身中时所留下的蛛丝马迹。
这个时代我们所能经验到神圣的痕迹就是神圣的缺席所留下的痕迹,即关于神圣的痕迹的痕迹。“如果是这样,至少若干死者将会发现作为绝望的(das Heillose)绝望正在到来。”Mrtin Heidegger,Wozu Dichter?,In:Holzwege, Frankfurt/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72,S.272.根据荷尔德林的诗句:“神近在咫尺 / 却难领悟 / 但危险所在 /也是救恩萌生之处。”Friedrich Hlderlin, Patmos(1802) : Nah ist / Und schwer zu fassen der Gott / Wo aber Gefahr ist, wchst / Das Rettende auch.In:Friedrich Hlderlin: Smtliche Werke,6 Bnde, Band 2, Stuttgart 1953, SS. 191-195.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拯救。神圣的痕迹恰恰作为危害的危害使我们意识到完好或完好的痕迹。完好呼唤神圣,并向我们眨眼神圣。神圣束缚神性,而神性则使神临近。Mrtin Heidegger,Wozu Dichter?,In:Holzwege, Frankfurt/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72,S.294.神圣的痕迹作为危害的危害向我们敞开完好的痕迹,因而“完好”(heil)是关于神圣的痕迹和道路。就是说,神圣的痕迹作为危害的危害促使我们直面完好。“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也许,比起自明的当前化所能做的东西,完好使我们更加明晰地、敏锐地直面完好。在自身方面,完好即意义经验并不是继续指明任何别的东西的记号或作为指向某物的眨眼,而是在其自身的完好中,恰恰是对它的这种发生本身的眨眼。
在自身中,意义经验呼唤人们去看原本什么东西在发生,即指示人们从神圣的角度去看“神圣的完好”。但是,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这种呼唤聚焦于我们受到眨眼这一事实,或者我们受到召唤这一事实。在意义的眨眼中,出现神圣。换言之,正在记号之中发生眨眼,神圣通过记号而成为当前的东西。意义事件“呼唤”自身的神的名字。然而,在特定名字之前,意义经验呼唤神性一般。不过,在海德格尔那里,被呼唤的东西并非神性而是神圣。只有神圣才能“束缚”神性。因此,可以说,正是完好在呼唤关于神性的召唤。赞美神性的东西,在神圣的领域里,呐喊与被呐喊已经悄然发生。但是,领域(神殿)却做出限制并划定界限。此即“束缚”(binden)。意义敞开神性所显现的领域。神性使神临近。它使姗姗来迟的神终将到来并使其当前化。
总之,在海德格尔那里,神圣的显现成为持续不断的东西的显现和当前化。在某一特定视角下,神性自我显现的方式把神性“进一步带给人”,从而人对神性赋予与自身相称的名字,使其变成以这种方式可认识的东西。因此,海德格尔得出结论说:“思维是从追问存在的真理出发思考的。……只有从存在的真理出发才能思考到神圣的本质。在神圣的本质之光中才能思考和谈论‘神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Martin Heidegger,ber den Humanismus,Frankfurt/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49,SS.181-182.所谓“存在的真理”,即“无蔽”的敞开和蔽护就是把思维降到最近的东西,亦即降到作为神圣的“无”的近处,在人的生存中,离开形而上学的生物的人的范围,“思维人道的人的人道”,亦即思维作为身心治愈的神圣。
四、新的“理性”与跨文化开放对话
20世纪人类历史曾经见证了“人心的崩溃”、“自然的破坏”等诸多严重的人与自然问题。面对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各路哲学家饱蘸浓墨、奋笔疾书,试图指点迷津、化险为夷。屈指数来,在这众多哲学家当中,做“大文章”、讲“大故事”的当属海德格尔其人。海德格尔一边宣告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的终结,一边号召人类为迎接新的世纪做准备。为什么西方形而上学濒于终结?海德格尔的诊断是,这种形而上学始终以理性为中心,以存在者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其结果必然会寿终正寝,无可奈何花落去。
追本溯源,在西方思维的萌芽时期,人的思维能力中既有“计算性思维”这一表象思维,也有解读存在意义的“铭刻意义的思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铭刻意义的思维”渐行渐远,淡出历史舞台,变得遥远而陌生。于是,人的认识能力一味倒向存在者的全体,全面凸显“有根据的话语”(逻各斯、理性),诗和神话却越来越被遮蔽,以致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误入了存在歪曲、存在缩小、存在遗忘的歧途。在现代科学技术中,这种以逻各斯为中心的形而上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技术化的、科学化的、产业化的、信息化的现代,形而上学无可奈何却名正言顺地“完结”了。
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普遍哲学思维中,潜伏着人的冥顽不化的工具支配意志和贪得无厌的欲望结构:“占有、支配、消费”。在这种工具支配意志和欲望结构的驱使下,现代人将存在的一切都把握为当前的意义,即把它树立为眼前的存在,改变为可计算的东西,重组为可重复的东西,体系化为可生产的东西,随时随地都把它变成可用的东西。根据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和解释路径,以理性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仅仅关注眼前可树立的存在者,追问并寻找其根据和原因,仅仅致力于存在者的说明和解释、支配和操作。但是,这样一种“计算性思维”绝不能解读存在的“意义”。值此形而上学的终结之际,新的思维的迫切任务是摆脱理性中心、当前中心、人类中心的思维态度,扩大“存在的视域”、“思维的视域”。
海德格尔聚焦科学技术时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背景,批判了西方理性主义思维模式,宣告“理性主义的终结”Martin Heidegger,Der Satz vom Grund, Pfullingen,Verlag Günther Neske, 1957.,阐明了这种思维模式不可逾越的界限和种种弊端,由此提出了面向新世纪的思维任务。西方形而上学以存在者为中心、以理性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大幅压缩裁剪存在的视域与意义,以致彻底根除了“无”的历史地位。然而,“无”并非无根据,“无”只是被假定为默不作答而已。因此,唯有全面抛弃这种对“无”的错误态度时,人才能本质上拥有对“无”的经验可能性。人是“无”的捕捉者,正因如此,人类应当意识到他被赋予了与神性的交往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当下思维的迫切任务是努力探讨神圣维度与“无”及其经验的关联性、“无”与神的关联性,为其保留固有的地盘,进而开辟新的遇见可能性。
对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而言,海德格尔从存在到神圣的思维转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导向意义。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海德格尔认为,在哲学的终结中,新的思维的任务就是为“无、空、虚”沉冤昭雪,还其本义,进而敞开存在的新视域、新维度,返朴归真,走进澄明之境。但是,在批判西方理性主义思维模式时,海德格尔因噎废食,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把理性(Vernunft)视为“万恶之源”。从一开始,海德格尔就拒绝以某种理性的方式构筑自己的思维。事实上,他根本不信任理性。在他那里,这种对理性的怀疑与日俱增,导致其哲学解释笼罩在一股深深的怨恨情绪中。例如,在晚期詮释尼采的作品中,他这样写道:“唯当我们经验到几个世纪以来荣耀不已的理性正是思维的最顽固的敌人时,思维才开始。”Martin Heidegger,Nietzsche .Zweiter Band , Neske, Pfullingen1961,S.212.
海德格尔对理性的怨恨可谓无所不在、无所不及。他不仅怨恨普遍的理性,也怨恨尚未精确地指定的理性,甚至怨恨固定的、良好的、机敏的理性一般。早在1933年弗莱堡大学校长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中,他就声称:“‘精神(Geist)既不是空洞的敏锐,也不是无拘无束的诙谐的游戏,也不是根据知性(verstandesmiger)肢解的无尽驱动,更不是世界理性(Weltvernunft),相反,精神最初是有情绪的,知道关于存在的本质的决心。” Martin Heidegger,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Breisgau,1934,SS.5-22. 在这里,海德格尔把文化层次上的“精神”加以绝对化、情绪化,使其完全脱离理智层次上的“知性”,进而用以取代统一体层次上的“理性”乃至“世界理性”。其结果,他与纳粹主义一拍即合、相见恨晚,径直把纳粹赞美为“庄严而伟大的觉醒”。就像尼采的“黑夜激情”一样,在逐渐展开的“世界天命本质”进程中,他的这种情绪化的“精神”也以果敢的决心、陶醉的狂热,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努力追求所谓“存在的本质”。可谓盲人瞎马、铤而走险。1933年5月1日海德格尔公开宣誓效忠希特勒政权,毅然加人了民族社会主义党。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对理性的怨恨是原始性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显然,作为一件“向来我属性”(Jemeinigkeit),思想家在自身的生存中已经发现了这种怨恨。正因为这种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怨恨,海德格尔才决意一不做二不休,直捣理性主义的老巢“理性”,誓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后快,以致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理性主义的泥沼。与此相对照,海德格尔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则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地捍卫“理性”的尊严,要求正本清源,重树哲学思维中理性的权威。与海德格尔充满诅咒的“理性怨恨”相反,雅斯贝尔斯坚决反对我们时代的各种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他义正言辞地把理性宣布为哲学思维的基本要素和共同背景。
在《我们时代的理性与反理性》(1950)中,雅斯贝尔斯掷地有声地说道:“我只是想提请大家注意哲学思维的基本要素,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背景。我所指的就是自明的理性的能力,它像山峦一样古老而常新,人们有时会遗忘或轻视它,然而总会重新获得它,但又从来不能使它彻底完成。”Karl Jaspers,Vernunft und Widervernunfu in unserer Zeit,München, R.Piper1955,S.9.在他看来,哲学思维与理性密不可分,二者须臾不可分离:理性是哲学思维的本源,理性的实现成为哲学研究的目的。因此,早在20世纪50年代,雅斯贝尔斯就高举理性的大旗,把自己的哲学称作“理性哲学”(Philosophie der Vernunft):“今天我更喜欢把哲学称之为理性哲学,这对于强调哲学的本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旦丧失了理性,哲学就丧失了自身。哲学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现在也仍然是获得理性、恢复理性。”Karl Jaspers,Vernunft und Widervernunfu in unserer Zeit,München, R.Piper1955,S.50.
就像海德格尔将“计算性思维”与“沉思性思维”严格区别开来一样,雅斯贝尔斯也将“知性”(Verstand)与“理性”(Vernunft)严格区别开来。对他来说,虽然理性没有知性就寸步难行,但理性又无限超越了知性。在他那里,与可证实的概念和以推理为基础的知性截然不同,理性的作用是综合或统一,理性既是追求全体统一的意志,也是追求全体交往的意志。Karl Jaspers, Von der Wahrheit,München,Piper2001,S.967,S.115.值得注意的是,与雅斯贝尔斯的理性交往哲学一脉相承,另一位当代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也致力于扩展理性的维度与内涵。鉴于我们时代的全球现实,哈贝马斯将理性界定为生活世界中与生活一道形成的“生活世界理性”,由此出发,他积极倡导 “交往理性”(Kommunikative Vernunft),呼吁全球范围内不同言谈者之间的开放对话,以促使这个世界上的“孤独主体”向“交互主体”转变。Vgl.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r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2,Frankfurt/Main,Suhrkamp1985.
由此可见,21世纪哲学思维的任务并不是要像海德格尔一样全盘否定或废除“理性”,而是进一步丰富和扩展“理性”的具体内涵,进而使理性的实现成为哲学研究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于重新审视和扩展“理性”的具体内涵和要义。例如,人们除了谈论技术性、工具性理性之外,也谈论审美理性、艺术理性,甚至还谈论伦理理性等。无论如何,西方知识分子大都已经意识到了西方理性主义思维的界限和弊端,正在寻求一种适合于21世纪地球村时代人类借以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新的“理性”形态。那么,何谓“新的理性”?新的理性就是新的“交往共同体理性”、新的“道德理性”,这种理性在人类大共同体视域中,努力寻求“新的精神性、新的灵性、新的宗教性”。
毋庸讳言,在确立新的理性方面,海德格尔的西方理性主义思维批判不仅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也有助于认同多元文化,进行跨文化开放对话。根据“多元主义”而非“一元主义”的真理观,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往始终反对排他性真理主张,拒绝把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宗教、文化、逻辑学、伦理学加以绝对化、至尊化。如今西方哲学所声称的西方文化的唯一性、绝对性、普遍性说法早已站不住脚。“如果歐洲民族不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民族,那么他们的精神文化价值也就不再是被赋予特权的东西。如果欧洲民族连这种特权都没有,那么更谈不上无可置疑的文化权威。”Mircea Eliade,Die Sehnsucht nach dem Ursprung. Von den Quellen der Humanitt,Frankfurt / Main,Suhrkamp1989,S.16.
在《哲学世界史导论》中,雅斯贝尔斯这样写道:“一切民族只有以自身的历史形态才能拥有哲学,而且,只要这种历史形态是真正的历史形态,那它本身就是任何人都无法占有的拯救哲学的表现。”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Einleitung,Aus dem Nachla,hrsg. von Hans Saner,München ,Piper 1982,S.20f.就像海德格尔“神圣维度”的目标一样,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之思”的目标也超出了一切存在者而指向“存在”自身。但是,与海德格尔不同,在他那里,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存在,而是“存在如何显现给我们?”通过把存在理解为“大全”(Umgreifende)及其基本样式的显现,他创造性地阐明了东西两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一种开放而包容的“多元主义”(Pluralismus)真理观,由此率先开启了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多元文化认同与跨文化开放交往的序幕。
(責任编辑:轻舟 )
As A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ing “Sacred”
——On Martin Heidegger's Critiqu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Thinking
Jin Shoutie
Abstract: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one hand, proclaimed the end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of 2,500 years, on the one hand, called on mankind to prepare for the new century.Western metaphysics is the end of the reason, because it is always centered on the existence, rational as the center, people-centered, drastically compress the sight and meaning of being, so that the eradication of the “Nothing” historical status. In view of the insurmountable boundaries and various drawbacks of Western rationalist thinking, Heidegger's shift from the Being to sacred thinking ha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However, Heidegger is overkill, from one extremity to another and regards reason as “the source of all evils”, and if he does not remove it, he will be unhappy, so taht fall into an irrational and even anti-rationalist slogan.
Keywords: Rationalism; Reason; Nothing; Sacred; Healing; New Ration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