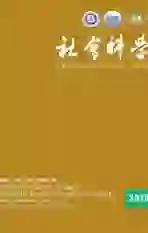董事会人数违限的规范适用研究
2019-05-15李建伟毛快
李建伟 毛快
摘要:公司法强制规制公司董事会人数的上下限,是我国公司法的一项特色规范安排。关于此规范的司法适用,一方面在法解释论上,宜将其解释为自治性强制规范,违法的后果仅限于引发进一步的公司自治行为,不当然带来包括司法强制、行政强制在内的国家强制,由此可以更具适应性的安排法律救济措施,消解国家强制介入,守护公司自治的宝贵空间;另一方面,强制规制董事会规模的规范模式是一项无效率的制度安排,不仅增加公司的守法成本,还可能增加执法成本,引发策略性滥诉与选择性执法等诸问题,理想的规范模式是:区分公司类型而确立宽严不一的规制模式,同时将法律规制的重点转移到确立董事会人数的程序规则,确保当选董事人数的合法性,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董事会规模;人数违限;强制性规范; 规制失范; 公司自治
中图分类号:DF411.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5-0095-10
作者简介:李建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毛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博士(北京100088)
引言
比较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法对董事会规模的规制,可以发现中国公司法的一处特色:强制设置各类公司的董事会人数的上下限。现行《公司法》第44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三人至十三人”,第108条第1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五人至十九人”。立法层面强行规制董事会人数区间,从比较法的角度可谓一项中国特立独行的一项规范安排。长期以来,这一规范深刻影响了我国董事会的治理实践,并产生诸多司法适用实践上的困扰:规制董事会人数规范的法律属性如何?如有公司的董事会人数违反上限抑或下限,如何处理之?救济路径的法律依据何在?这涉及到相应法律规范的适用,由于鲜有比较法上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诉诸普通公司法理以及我国长期的公司法实践经验,来进行深入的讨论。
一、 规制董事会人数的规范属性分析
与公、私法的分类相对应,私法上的法律规范的最重要分类是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这一对基本概念范畴的区分标准,乃是当事人是否可以排除其适用。任意性规范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做出约定,就其语言表述多用常见字眼如“可以”、“有权”等,以赋予当事人意思自治空间,当事人得通过约定排除其适用。通说认为,任意性规范的功能首先在于引导当事人正确实施法律行为。有学者认为任意性规范相当于法律行为的“专家建议版本”,其既可以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为,也有助于帮助当事人减少交易成本,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交易选择参见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载《民法总则论文选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二是鼓励当事人意思自治,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三是弥补当事人约定不足的作用。四是引导法官正确裁判,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法官适用任意性规范来进行裁判。相对应的,强制性规范乃是法律要求当事人必须遵循的,不能通过约定加以改变或者排除适用的规范。一般认为,强制性规范可以再分类,一为禁止性规范,即禁止私法主体为一定行为的规范,立法语言的常见字眼是“不得”、“禁止”,二为命令性规范,即强制私法主体为一定行为的规范,立法语言的常见字眼是“必须”、“应当”胡田野:《公司法任意性与强制性规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 上述分类及其依据,完全适用于公司法规范。由于不同类型的规范对当事人行为的规制模式和适用后果截然不同,正确定性公司法上的董事会人数规范,是指导当事人在实践中如何设置董事人数,判断当事人行为偏离这一规范时的法律效果,以及司法机关对选举董事之公司决议效力裁判的前置性问题。
上引《公司法》第44条第1款、第108条第1款并未使用“可以”、“全体股东约定……的除外”、“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等任意性字眼,也未冠以“必须”、“应当”、“不得”等强制性字眼,似乎难以从立法语言的文义直接判断其规范属性,公司法学界也就存有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公司法》“仅提供了一个参考人数”,在实际运作中没有对任何一个公司都适用的董事数目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原则研究课题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及其解说》,《南开管理评论》2001年第1期。。也有学者认为,公司股权结构各异,各公司据此安排董事人数实属内部治理事务。依照公司法理论,董事人数为非核心性的结构性规则,无论对封闭公司还是公众公司,都宜为任意性规则。公司法对董事人数的限制为任意性规则罗培新:《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边界之厘定:一个法理分析框架》,《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还有学者认为应区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关于第44条对有限公司董事会人数的限定,从实然法角度应理解为强制性规范,但从应然法角度,理解为任意性规范更好,至于第108条的解释,则应遵循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应有所不同的原则,股份公司的大多数结构性规范,无论从实然法角度还是应然角度,都宜为强制规范 参见胡田野《公司法任意性与强行性规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504-506页。。 实务界也有人持类似观点,认为如果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规定组成一个15人的董事会,不宜因为其不符合“3-13”人的公司法规定而认定其无效,也即将《公司法》第44条解释为任意性规范,不损害公众利益,亦不违背区分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立法宗旨,但“对股份公司而言,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以倾向于强制性规定为主。”王林清:《公司诉讼裁判标准与规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由于立法背景资料的缺失,我们还无法考证立法者規定董事会人数的立法详意,但虑及《公司法》作为商事基本法律,很难想象惜墨如金的立法者做出这种具体限定的目的仅仅是提供一个参考数据。我们认为,如对现行《公司法》进行体系化解释,有以下几点可以佐证董事会人数的规定乃属于强制性规范。
1.佐证一,《公司法》第45条第2款关于辞职董事“留任义务”的规定。该款规定:“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该规定为2005年《公司法》新增条款,明确指出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人数下限为“法定人数”。期满离职、主动辞职是董事的权利,但当离职或辞职导致董事人数低于“法定人数”时,董事的“离职权”、“辞职权”被暂时悬置——“应当”继续履职,直至新董事就任,此即为特定情形下董事的“留任义务”蒋大兴:《公司法的观念与解释I》,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查《公司法》文本中使用“法定人数”一词的条文还有三处,分别是:23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需符合“法定人数”(2-50人);第78条股份公司发起人需符合“法定人数”; 第52条,监事任期届满或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少于“法定人数”的,监事应继续履职。没有疑问的是,股份公司发起人人数、有限公司股东人数的规定均为强制性规范,这也从一个角度印证了《公司法》对董事会人数的限制亦属强制性规范,至于《公司法》对监事会人数的规定,其性质应该与董事会人数作同样解释。
2.佐证二,《公司法》第100条对董事缺位时补选事项的立法用语选择。《公司法》第100条第(一)项规定,董事人数不足本法规定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补选。“应当”补选,而不是“可以”补选或不补选,也未赋权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款亦印证了《公司法》对董事人数的限定为强制性规范。这一规定有立法历史传统可以依循。民国政府1929年《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董事会人数下限5人,配套法规《公司法施行法》随即规定“公司董事名额原定不足五人时,应于《公司法》施行后六个月内,补选足额并呈由主管官署报部备案。”此例还显示,强制规定董事会人数似乎是一种历史传统
3.佐证三,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辞职问题的规定。考察相关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辞职问题的规定可以发现,无一例外地都规定若董事辞职导致董事人数低于“法定人数”,辞职报告“暂不生效”。如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第100条规定,“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时,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履行董事职务。除前款所列情形外,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订)》第100条作出了相同规定。采此立场的还有保监会2008年发布的《保险公司董事会运作指引》,其第15条还规定,因董事被免职、死亡或者存在其他不能履行职责的情况,导致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时应及时补选,在补选完成前,“公司可以通过章程约定董事会职权由股东大会行使,直至董事会人数符合要求。”
综合以上,《公司法》关于董事法定人数的规范属于强制性规范无疑。尽管学术界对于我国公司法过多的强制性干预公司治理的规范安排多有批评且不无道理,但并不能因此而可以一厢情愿地将一些本来意义上强制性规范曲解为任意性规范,以此减轻公司法上的国家强制力度的初衷虽好,但违背公司法立法本意又是不妥的。至于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通过对相关强制性规范的进一步细分,在承认该规范的强制性属性的前提下,来有效消解国家强制性,引导司法、执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宝贵努力。
二、董事会人数规范的国家强制性之类型化分析
(一)公司法上强制性规范的类型化
现代私法部门或多或少都包含一些强制性规范,而在公司法等商事组织法部门的强制性规范的比重相对较高,这是由其组织法(团体法)的强制主义属性所决定的参见王保树主编《中国商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1页。。就公司法而言,立法者除了在涉及第三人、不特定公众的事项上设置了大量强制性规范外,在公司内部治理事项也设置了不少含有“应当”、“必须”等字样的规范,公司法学理论与实践一般也将其视为强制性规范。公司法本质为私法,如何理解公司法中存在的这些强制性规范?苏永钦教授认为,“私法中的大多数条文为赋权性规范,虽具有效力上的强制性,但其功能在于建立自治的基础结构,为裁判者提供裁断效力的依据,而不在于影响人民的生活,指示人们为此种行为或不为彼种行为” 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载《民法总则论文选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据此,赋权性规范的意义并不在于“管制”人民的行为,以管制人民行为为目的的强制性规范在私法上是极少数的。与此相呼应,有公司法学者提出,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并不一定导致国家强制,强制性规范与国家强制之间不应该划等号 李建伟:《有效市场下的政府监管、司法干预与公司自治:关系架构与制度选择》,《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实际上,如果要区分公司法中不同性质的强制性规范,与公司自治、行政监管与司法干预等法的实现的三类方式相对应,也即依照法律规范实施主体的不同,强制性规范可以再分为公司“自治性强制规范”、“行政强制规范”与“司法干预规范”。
自治性强制规范,是指体现与维护公司自治、赋予公司参与人自主选择、自主决策的行为规则,多数表现为任意性规范,但有时候也体现为强制性规范,正如前引《公司法》第100条规定,“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此处使用“应当”一词,在性质上归属为强制性规范,却无“国家强制”的含义,故应理解为公司自治规范。依此,如股东大会没有照此规定召开,不会引起行政权的干预,也没有司法权的介入,只是引发下一步的公司自治行为——如有股东依据《公司法》第101条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自行召集股东大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政强制规范与司法干预规范则包含了某种国家强制力,对这两类规范的违反会引发公权力对公司事务的介入。具言之,前者指法律规范中体现行政权力的意志、为维护公共利益等公法目标而强制公司参与人须遵守,若违反则可能导致行政机关采取强制干预行政法中的“行政强制”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即时强制和行政调查中对相对人施加的各种强制措施。此处的“行政强制”与行政法中的“行政强制不同”,应做广义解释,包括行政法上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监管等含有国家强制性在内的具体行政行为。。后者指公司内部利益以及部分特定的外部利益冲突无法由参与人自行解决的,许可各方采取诉讼,引入司法权介入公司纠纷的解决。
考诸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及其实施实践,应该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分类。根据“自治性强制规范”、“行政强制规范”、“司法强制规范”这个框架分析,有助于人们根据国家强制性的不同來进一步区分公司法等组织法上的诸多强制性规范,防范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错误适用法律,尊重与守护公司自治领域,消解不必要的国家强制措施介入。按照上述分类,《公司法》规定的强制性规范的多数属于自治性强制规范、司法强制规范,对前者的违反将引发进一步的公司自治行为,对后者的违反则使一方当事人获得诉权,或者通过诉讼外的其他方式触发相应司法救济程序,例如董事、高管违反第148条的强制规定与公司进行自我交易的,公司对董事、高管所得收入享有归入权,据此获得一个请求权基础,故而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返还。需要指出,对自治性强制规范、司法强制规范的违反一般不会直接导致行政强制。最典型的行政强制性手段为行政处罚,《公司法》涉及行政处罚的强制规范集中于第十二章“法律责任”中所对应的强制性规范,多集中在资本制度、财务审计制度、清算事项、违法营业等事项中。如第201条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在法定的会计账簿以外另立会计账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万元以上以下的罚款。”该条款规定了一个典型的行政处罚行为,对应的强制性规范乃是《公司法》第171条“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该条文是典型的“行政强制规范”。总之,将公司法上的强制性规范进一步区分为自治性强制规范、行政强制规范、司法干预规范,是一个有法律意义的分类,对于公司治理而言尤其如此。下文结合违反董事人数上下限这一强制性规范的后果,来展开分析由此导致的不同类型的国家强制性之内涵。
(二) 董事会人数违限的国家强制性介入
依据上述强制性规范的“三分法”,尽管有关董事人数区间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但对之的违反并不必然产生出自司法、行政的国家强制措施。对董事会人数违限的国家强制性后果之分析,似有必要区分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后者有时候适用更严厉的行政监管措施。关于此点,详见后文的分析。关于董事会人数违限的司法干预介入,需要分别而论。根据下文关于公司章程条款的违限与非由于公司章程条款的违限的分类体系,对于由于公司章程条款规定的董事会人数违限的,自然无法透过公司进一步的自治行为而补正,股东可以也只能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章程(合同)条款无效或者相应的修订公司章程条款的决议无效。在此意义上,公司章程条款违限的,私法上的后果是将导致章程条款效力的否定,故而可以得出董事会人数区间规制条款属于司法干预规范的结论,需要引入司法干预的国家强制力。
至于非由于公司章程條款的违限是否引发行政强制措施与司法干预,需要分别违反下限与上限而论。一般而论,董事人数下限规范虽为强制性规范,但多数非出于公司的“主动”违法意思的后果,比如由于个别董事的辞职、死亡而致使公司“被动”处于违法状态的,对其的处理不应该直接引入行政强制措施或者司法否定措施,仅仅触发进一步的公司自治行为即可望补正。
与低于下限不同的是,超过上限的违法行为乃是公司主动而非被动的意思所为。在董事会人数规范为强制性规范的背景下,超出上限的公司主动违法行为的效力需要得到否定,因为不能如因董事辞职导致违反人数下限那般的触发进一步的公司自治行为而得以弥补,但是至少对非上市公司而言,并不必然导致行政强制如果公司章程规定选举出的董事人数高于法定人数时,得票最低者被自动排除,则对人数上限规范的违反自动触发公司进一步的自治程序,纠正了违法状态,进而排除了股东的诉权。。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董事人数违反法定上限的是否同时具备行政强制规范的效力?也即对其违反会不会导致行政强制的发生?目前尚未见相关法规规定,但考诸证监会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背景,证监会通常将通过行政监管措施对上市公司治理中所有不合规情形进行行政强制监管,在证监会的相关规则未明确上市公司董事人数突破法定上限时可以采取自治措施自行纠正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如有突破董事会法定上限的,几乎可以肯定将引发证监会以公司董事会治理不合规为由要求上市公司责令改正的后果,也即将引发国家的行政强制性措施。
至于董事会人数违限的私法效力尤其规制董事会人数的规范作为自治性强制规范的适用,是问题的核心,下文展开分析。
三、董事会人数违限的私法效力瑕疵及公司自愈行为
对董事会人数违限行为的私法效力评价及救济安排,需要区分违反下、上限而分别讨论,又基于董事会人数入公司章程的这一背景,首先将违限分为公司章程条款的违限与非属于公司章程条款的违限。
(一)类型化分析的基本框架
1.公司章程条款的违限
也即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人数违反公司法定区间,基于章程条款规定的抽象性,也可称为抽象违限。《公司法》第81条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的组成”乃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此处的“董事会的组成”应否解释为包含人数事项?对此的定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也有规范性文件的佐证,比如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106条特别注释说明“公司应当在章程中确定董事会人数”。当然,第25条未明确“董事会的组成”属于有限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仅仅规定“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应该如何理解此处的“公司的机构”条款设计?仅就董事会而言,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基于有限公司群落差异较大,包括设立董事会抑或仅设执行董事都有所不同,所以赋予有限公司更多的自治空间,故属平常,但一旦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设立董事会的,则应该如前述股份公司一样明确包括董事会人数等要素在内的“董事会的组成”。据此的结论是,但凡章程规定设立董事会的所有公司,都应该同时明确董事会人数,也即董事会人数此时属于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又据《公司法》第103条,任免董事属于股东大会的一般决议事项、修改章程属于股东大会的特殊决议事项,那么董事会人数既为章程必备条款,其变更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涉及股东的重大权益,因此董事的人数调整应比选举、任免更为重大。既然董事会人数属于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如果章程规定的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下限或者超出法定上限,显然属于违法行为,究其后果将如何处理?如从私法效力的视角,承认关于董事会人数的强制性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展开讨论如下:其一,如初始章程规定了超限的董事会人数,对于有限公司与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而言,由于初始章程由全体股东签字后生效,属于合同行为,所以该条款归于无效;对于募集设立的股份公司而言,由于初始章程由经创立大会的多数决议通过,所以该项决议的本身也是无效的。其二,如公司初始章程无此规定,则后来的章程修订条款规定超限的董事会人数的,则该特别决议自身是无效的。
2.非由于公司章程条款的违限
如章程规定的董事会人数合乎法定区间,由于选举决议等某一行为导致董事会人数超限事实的发生,即为“非由于公司章程条款的违限”,也称具体违限。此将如何处理?需要区分违反上、下限分别而论。只是需要指出,如果说章程条款的违限是公司“主动”违法意思所致的话,那么非由于章程条款的违限可能出于公司“主动”违法意思所致,但更多可能非出于公司的“主动”。这一区分的意义是,基于违法行为模式(原因)的不同,处理后果有很大差异。
(1)对董事会人数下限的具体违反的处理。前已指出,多数非出于公司的“主动”违法意思,乃是某些事实行为的发生而致公司“被动”的违法状态,对其治愈主要依赖进一步的公司自治行为。如前引公司法规定因董事辞职导致董事会人数违反下限的,引发董事的“留任义务”,辞职“暂不生效”;由于其他原因比如董事死亡、丧失任职资格而被解聘等而造成违反下限的,通过公司及时补选这一进一步的公司自治即可消弭。当然,逻辑上也不排除公司章程规定了合乎法定区间的董事会人数,但公司选举、聘任的董事会人数低于章定或者法定下限的情形,对于这一主动的违法行为,其处理参照下述关于公司主动违反董事会人数上限的处理模式。
(2)对董事会人数上限的具体违反的处理。首先需要指出,与董事去职造成的“被动”违反下限的“违法”状态不同,违反上限的必然都是由于公司“主动”增补超过上限的董事人选所致。对此如何处理?未见公司法的明确规定,这是董事会人数违限较为棘手的规范适用问题之一。从公司法理上析之,假定公司章程规定了合乎法定区间的董事会人数的前提,超限的增补董事首先违反了公司章程,否则,就属于上文已经讨论的公司章程条款的违限情形。由于该批次董事的增补本身违反公司章程,在此意义上,超过上限的具体违法行为乃是公司主动的意思所为,在肯认强制性规范的背景下,超出上限的公司主动的违法行为不能像因董事辞职导致违反人数下限那般的触发进一步的公司自治行为而得以治愈,故其私法效力必须得到否定。
总之,由于具体的行为导致董事会人数违限的,都将导致私法上的效力否定后果,也即修改公司章程條款的股东会决议或者选举董事的股东会决议决定所产生的董事人数超过法定上限的,被视为违反私法上的强制性规定,这将导致公司意思的无效。如是公司股东会决议选举的董事人数超限的,则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不仅违法而且违反公司章程,按照违法行为的重者吸收前者的基本法理,该股东会决议得被股东等利害关系人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决议无效,如果不适用吸收原理,则也可以引起决议的可撤销之诉。
(二)非由于公司章程条款的违限下的若干具体问题
1.董事会人数低于下限的
根据前文的分析,造成董事会人数低于下限的缘由是由于部分董事任期内的去职,董事去职的情形包括在任期内的的死亡、解职原因包括丧失法定的任职资格,具体规定见《公司法》第146条。 董事被解职的方式包括被撤销指派、委派以及撤职的选举决议,原因包括丧失任职资格(详见《公司法》第146条的规定),以及其他不胜任职务、对公司有不当行为等。 比如《公司法》第146条第3款即规定,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第一款所列情形的,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与辞职。一旦由此出现董事会人数低于下限的“违法”、“违章”状态,私法上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尽快消除这一违法违章的状态?二是在违法违章状态消除之前,作为一种违规存在状态的董事会是否可以履职?对于前一个问题,需要区分董事去职的具体情形分别而论。前已指出,对于董事辞职的,适用《公司法》第45条第2款关于辞职董事“留任义务”的规定,即可保持董事会人数在合法、合章的状态;但是对于董事死亡的,自然无法适用留任的规定,自不待言,对于董事被解职的,实际上也无法适用留任的规定,此时只能尽快增补新的董事,以尽快消除董事会的违法违规存在状态。在后两种情形下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在董事会违法违章状态未消除之前,董事会是否可以做出决议?对此,《公司法》仅仅要求股份公司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补选 参见《公司法》第101条。,对于有限公司无此要求,但均未明确补选前的董事会可否作出决议。我们认为,处于违法违章存在状态下的董事会不得行权,由此作出的决议因董事会自身组成的违法或者违章,而分别适用《公司法》第22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分别属于无效的决议、可撤销的决议。当然,如果长期的董事会违法违规存在状态严重影响公司治理的运行,尚有其他的替代性救济措施安排,比如《保险公司董事会运作指引》规定,保险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下限时股东会还可以代行董事会职权。这一替代性救济措施的安排不仅合法合理而且非常必要,类似的立法规定还见于《公司法》第124条的规定:如上市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有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而导致“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由于现行公司法并未直接规定这一或者类似的替代性救济措施,所以宜由公司章程条款做出这一事先安排,以备不时之需。
2.董事会人数超出上限的
如前所述, 超出董事会人数上限的原因很单纯,就是董事增补超限。超出上限的状态一旦形成,类于上文的低于下限情形,私法上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尽快消除这一违法违章的状态?二是在违法违章状态消除之前,作为一种违规存在状态的董事会是否可以履职?依照前文关于否定其私法效力的结论,对于后一个问题,应该适用与上文讨论的低于下限情形的同样规则,但棘手的问题是,超出上限的违法违章状态如何获得消除?按照现行法有关规定,董事会成员按其产生方式有三种情形,一是股东代表董事(包括独立董事),普通公司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国有独资公司则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派、指派,还有一些国有公司的外部董事也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派、指派;二是职工代表董事,由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三是不少公司章程规定,非执行董事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一旦超出人数上限的局面形成,是全体还是部分成员的选举、委派(指派)无效?如果是后者,则究竟哪一部分的选举、委派(指派)无效?由于不同成分的董事获任方式不同,这一问题的解决稍显复杂。此处要区分是增选、增派形成的超限还是一次性选举、委派形成的超限,如为前者,既有董事会成员不受影响,唯有后来的增补成员的全体抑或部分面临无效的问题;如为后者,将面临全体成员的选举、委派无效抑或部分成员的选举、委派无效的问题。总之,人数超限的某次董事选举、委派,是全体抑或部分成员的选举无效?对此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见解,一种意见认为,应是该次选举、委派的全体成员无效,公司需要重新进行选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是该次选举、委派的部分成员无效,以避免重新选举的进行,提升公司议决的效率,此处所谓“部分成员”是指相应的选举得票最低者、委派名单排名靠后者,比如某公司董事会已有15名董事,后股东大会决议一次增补股东代表董事6名,则得票最低的后2名当选无效,以组成不超限的董事会。对于后一种意见的诘难有二,一则,可能面临的一种极端情形是,如有后3名及其以上的当选者得票数相同,又该如何处理?二则,一次性选举的公司决议是一个完成的意思表示,法律对其效力的处理又如何切分出整体与部分的意思表示呢?诉诸公司决议的意思表示法理,尽管后一种意见似乎有效率上的优势,但终究于公司组织法的法理不合,前一种意见似更为可取。
四、失范之惑:一个节外生枝的规范适用困境
作为一个集体行权的常设委员会组织参见李建伟《公司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298页。,董事会在任期内的人员构成及其数量有所变化乃是非常正常之事,公司法如强设禁区与红线,不仅生出一系列始料未及的法律规范适用困局,也给司法介入、行政执法带来不确定性。
(一)人为增加的守法成本与自治障碍
一是人数下限经常被不经意的触犯。罢免董事乃股东会的法定职权,董事也有权基于各种理由随时辞职,至于董事死亡、失去任职资格等意外情形也不鲜见,由此导致的董事会自然减员触犯了董事会人数的下限要求,常使公司由此陷入被动违法之境地。“被动违法”无疑给公司运行带来额外的制度风险,为规避这种风险,公司将付出额外的成本。另一方面,为确保董事会人数下限规定的实施,立法者不得不配套设置更多的强制性规范,以消除一连串的违法效应。如《公司法》第101条第(一)项规定“董事人数不足本法规定人数,应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会补选”,即其适例。这一规定还附带一个负效应是,补选完成之前可能意味着存在长达两个月的董事人数低于下限的“违法期”,有关董事会人数的一整套强制性规范遭到破坏。为填补这一漏洞,2005年修订《公司法》又特意增加第46条第2款关于届期、辞职董事的“留任义务”,规定因届期、辞职造成董事人数低于下限的,原董事继续履职直至新董事就职之时。这一规定给治理实践带来的尴尬是,一些董事的辞职离任,原本就是缘于内讧导致合作基础破裂,有的还因为董事涉嫌犯罪或因其他变故而不适合继续履职,但该规定迫使那些不再适合担任董事者留在董事的位子上,于公司治理并无益处。尽管有了届期、辞职股东的留任义务,但立法仍百密一疏——第46条第2款仅解决了因届期、辞职跌破人数下限的问题,但除此之外,董事人数跌破下限的原因还有董事死亡、被免职、失去任职资格等,在诸如此类情形下如何在补选完成之前保证董事会人数的“合法性”?《公司法》未作规定,形成一个不完全规范,这一“违法状态”目前无解。
二是人数上限抑制了大公司董事会的正常扩容需求。大型公司因为业务扩张而引入更多专业董事以提高经营、监管能力的,实属常见。在大型国有公司集团走向股权多元化的改制实践中,股改带来股权的多元化、分散化与相对均衡化,自然产生董事会扩容的需求。此外,《公司法》与《独立董事意见》也存在潜在的冲突,后者规定独董的任期与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且不低于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形是:某公司已有顶格的19名董事,其中7名为独立董事,达标不低于三分之一的要求,但随后一名独董失去独立性而转为普通董事的,如其不被免职或者离职,公司应再聘一名独董才能符合比例要求,这样一来将出现20名董事,逾越上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立法的一些细节疏漏将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但更大的问题似乎还在于立法管制的思想。 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要之,有关董事会人数的强制性规范群不仅压缩了公司的自治空间,带给公司治理额外的制度成本乃至负面效应,而且为了一个强制性规范的实施,立法者不得不加大成本制造出更多的强制性规范,法律体系的内在简洁与和谐也遭破坏。
(二)不确定的违法后果与执法成本
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多集中在7-13人之间 郑江淮:《中国上市公司最佳董事会治理与绩效评价:2005—2008》,《董事会》2009年第5期。,为法定的5-19人区间所包含,但并不说明没有公司有更大、更小董事会的需求。法律预设的意象未必能够完全实现,相反却常常为现实所打破。近年来董事人数上限遭到突破的案例不断涌现。在曲丽清对上海126家A股上市公司的调查中,已有1家公司的董事会人数达到20人 曲丽清:《董事会规模与运作效率关系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2期。。在张安平以2010年全部创业板公司和上证180公司的研究中,董事会规模最大的达到了21人 张安平:《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及其结构研究》,《时代金融》2013年第2期下旬刊。。2013年5月,内地大型房地产企业碧桂园公司一举选出6名新董事,使该公司董事会规模一度达到21人,一时引发广泛关注。应该说,碧桂园公司原来的董事主要为家族成员,封闭性强,导致公司业绩不稳定,董事会扩容引入更多专业人才,是该家族企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必需,但这样的合理市场需求却可能面临着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又例,早在2006年交通银行董事人数已达19人,截至2014年9月达到22名人,突破上限不少,超大型董事会的成因是股权结构改革后股权较为分散、均衡所致,尤其引入汇丰银行作为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打开了交通银行股权结构多元化的背景。联系此次改革针对国有上市公司一股独大、董事会一言堂的弊病,扩容后的董事会反而堪称国有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改革的典范 宋克刚:《详解交通银行董事会》,《董事会》2006年第1期。。尴尬者,超大型董事会将因突破人数上限而违反公司法;更尴尬者,违法的交通银行董事会组成不仅未受否定性评价,还被视为改革成功的典范。抑或一种良性违法?实际上,当公司运作实践出现大量“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现象时,通常说明现行法已滞后于实践 李建伟:《公司制度、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51页。。削足适履式的立法究竟行不甚远,仅就私法上的司法救济与公法上的行政执法而言,可能带给公司以下多重困扰。
一是未卜的法律效力。一方面,关于董事会上下限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无疑,另一方面公司法未明确超限董事选举的决议效力究竟如何,是有效、全体无效还是相应的最后名次无效?加大了人们关于董事选举的焦虑,增加了公司运行的法律风险。
二是策略性滥诉。如果肯认关于董事会上下限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那么根据《公司法》第22条第1款,如某次修订章程、选举董事的决议决定的董事人数超限的,该等决议可被提起决议无效之诉,引来司法干预。这一诉讼安排留下了“策略性滥诉”的隐患,给公司运行带来不确定性风险:股东明知董事会人数不合法的,可以暂时选择沉默,一旦董事会做出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決议,便起诉请求确认董事选举的决议无效,进而否定该届董事会作出的决议。
三是选择性执法。公司法尚未规定对董事人数不符合规定的公司施以行政处罚,但针对上市公司,证监会施加责令上市公司改正等“行政监管措施”,应无障碍,从而使董事会人数规范具备了行政强制性。“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在2002年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体制的通知》第一次被提出,后来通过十几部部门规章文件获得了空前的“扩容”。有学者将其细分为29类,包括出具关注函、出具警示函、约谈提醒,重点关注、记入诚信档案、责令更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包括责令股东转让股权等柯湘:《中国证监会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研究》,《政法学刊》2008年第2期。。“行政监管措施”在某些时候的严厉性较行政处罚有过之而无不及,却不受《行政处罚法》的约束,行政相对人也缺少事前听证、事后申诉等救济机制。一旦出现董事会人数超限,上市公司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与否全由证监会裁量,可能带来“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的结果。在Becker和Stingler指出执法成本要素后,人们认识到执法存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严格执法的成本甚至远超违法损害,这就解释了选择性执法的局限性戴治勇:《选择性执法》,《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选择性执法不仅影响监管的效果,有损法律权威,并容易导致权力寻租行为叶小兰:《选择性执法的内在悖论与消解机制》,《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目前尚无公开资料显示证监会对董事会人数超限的上市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但这种备而不用的状态如同达摩之剑,一旦由于运动式执法的需要,或者执法人员出于寻租的动机而执行该规范时,市场主体将面临不可测的风险。
结论
公司治理领域的国家干预必不可少,但作用又是有局限的,应有其明确的边界,否则,不当的国家干预会带来负面效应。从规范法学的立场虽然可以解释《公司法》关于董事会人数规范的私法效力及其违反后的救济,但必须指出现行的强制规制模式可能是一项无效率的制度安排,除了徒增公司的守法成本、不当干预公司自治,还可能导致策略性滥诉与选择性执法的问题,增加公司运行成本。法律的稳定性、抽象性、概括性、定型性与公司治理实践的具体性、活泼性、实践性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张力,如前者的架构被嵌入强大的国家强制性,很容易趋于僵化,不可避免地对公司参与者的创造性活动造成阻碍李建伟:《公司制度、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51页。。具体到董事会规模的强制规制,关于人数下限的規制,主要妨碍小型封闭公司的自治,上限的规制则伤害大型公众公司的自治,理想的规范模式安排似乎是:对于前者,彻底取消董事会人数的上下限限制;对后者,废除上限,仅仅保留至少三人或者五人的下限要求,以确保董事会的集体决策机制;对某些公众性极强的特殊行业如金融业,以及施加更强度规制的国有企业,可通过特殊立法确定董事会人数的上限。还要指出,普通公司法出面规制董事会人数的重点应转移到确立董事会人数调整的程序规则,明确董事会人数调整属于股东大会的法定职权,适用特别决议事项程序,以防范多数股东、管理层通过增减董事会人数来强化对董事会的垄断。在保留董事会上、下限规范的前提下,《公司法》需要明确人数超限的董事选举的效力,适用全体董事选举的决议无效规则抑或自动排除得票最低者规则,以确保当选人数的合法性,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李林华)
The Study on the Rules of the Viol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Li JianweiMao Kuai
Abstract: Compulsory regulation of the upper and lower limits of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is a characteristic normative arrangement of the Company Law in China. O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is norm,on one hand, in legal hermeneutics,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compulsory norm of autonomy. The consequences of violating this regulation are limited to triggering certain acts of corporate autonomy,rather than causing state compulsory acts such as judicial compulsory acts or administrative compulsory acts. Thus, we can arrange legal remedies more adaptably, eliminate the compulsory intervention of the state and protect the precious space of corporate autonomy.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rmative model of mandatory regulation of the board size is an inefficie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 which not only increases the cost of company's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but also may increase the cost of law enforcement, triggering strategic indiscriminate lawsuits and selective law enforcement. The ideal normative mode system is to distinguish the types of companies and establish different regulatory modes. At the same time, the focus of legal regulation should be shif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cedural rules for the number of board members, so as to ensure the legitimacy of the number of elected directors and eliminate the uncertainty of the law.
Keywords: Board Size; Viol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Mandatory Norms; Regulation Anomie ; Company aut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