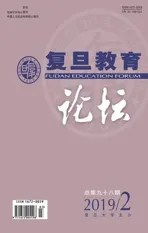领导创新支持对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的作用机理
——团队积极情绪和团队创新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2019-05-15张建卫李海红任永灿
张建卫,李海红,赵 辉,任永灿
(1.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1;2.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3.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北京100011)
一、问题提出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持续引领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在全国高校蓬勃展开,各类探索性、前沿性和交叉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作为团队科学创造力的载体,正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Team Scientific Creativity),已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一项核心内容,也开始演进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主题。团队科学创造力是指在科学任务情境中,团队成员在团队领导者带领下,通过团队协作产生具有新颖性、独特性社会价值的科学成果的智能品质或能力[1]。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研究者对企业组织中的团队创造力及其影响机制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而高校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的形成机理,则是一个亟待探索的崭新领域。因此,有必要结合大学组织情境与团队情绪-认知特点探讨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发展的内在机理。
领导创新支持(Supervisory Support for Innovation),是影响创造力的一个关键性组织情境因素。研究显示,与控制型领导相比,支持型领导更能关注成员情感需求、鼓励其表达自我观点、提供积极性反馈,通过知识共享和内在激励增强成员的主动性和好奇心,进而促进其创造力发展[2]。虽然学者们已经注意到领导创新支持促进个体创造力的作用路径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3-4],但其影响团队创造力的过程机制尚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和实证验证。当前,快速发展的积极情绪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抑或为此带来某些启示价值:根据Fredrickson“拓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具有拓展“思维—行动”范畴和建构长久的身体、认知、社会等资源两大功能[5],为个体成长提供持续性资源;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外在环境激发人的行为反应,人的内在因素(如自我效能感)是重要的中介路径[6]。研究者将上述理论应用于企业团队创造力领域,发现团队积极情绪(Team Positive Emotion)对团队创造力及团队创新效能感(Team Creative Efficacy)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显著预测作用[7-8],但目前鲜见探索二者共同作用的整合性研究,更未揭示二者在领导创新支持影响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中的作用路径。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究领导创新支持对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同时考察团队积极情绪和团队创新效能感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以期为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促进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一)领导创新支持对团队科学创造力的影响
Deci和Ryan认为领导可分为支持型和控制型两类:前者主要体现为关心下属的情感和需求,鼓励成员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积极而重要的信息反馈,促进成员的能力发展;而后者则会密切监督成员的行为,拒绝成员参与决策,对成员的思维及行为施加压力[9]。Amabile等人则认为,领导创新支持主要表现在设立明晰目标、与下属开放性互动、支持团队工作及创意等方面[2]。West和Farr在其研究中将领导创新支持定义为,在工作环境中领导者对引入新技术或改进工作方式的期望、肯定和实际支持[10]。本研究借鉴此概念,认为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中的领导创新支持是指在高校科技创新情境中,领导者对新理念、新方法或工艺等给予积极期待、有效回馈和充分支持的程度;并采用Scott和Bruce开发的量表[11]进行测量。其中,领导者是指指导教师或队长,前者由具备较强科研实力和丰富项目经验的专业教师担任,后者由团队创始人或具备优秀科研能力及丰富项目经验的优秀成员担任。在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中,基于共同的团队目标和互动过程,团队成员往往会对领导情境形成一致性认知。因此,本研究将领导创新支持作为团队层面的变量加以考察。
创造力成分理论认为,组织情境力量通过提供直接帮助、开发专长及提高内在动机等途径对个体创造力产生影响[12]。在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中,领导创新支持是团队创新实践的重要情境力量和影响因素。当领导者表现出设定合理目标、提供建设性反馈、包容新观点等领导创新支持行为时,不仅会使团队成员更加专注于任务本身、增强对创造力的关注度和努力度[11],从而有机会获得与创造力相关的技能与策略,进一步提升创造力,而且会增强其参与创造性活动、应用创造性技能的内部动机,弱化其对外在激励的依赖[13]。实证研究已表明,领导创新支持对个体创新绩效及创造力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并通过员工情绪状态、内部动机和心理投入等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3-4]。然而,尚未有研究直接验证领导创新支持对团队科学创造力的预测作用,以及上述变量关系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适用性。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领导创新支持对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
(二)团队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
情绪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14]。Fredrickson和Losada从积极情绪视角提出了“拓展—建构”理论,认为快乐、愉悦等积极情绪既能开拓注意、认知和行动范畴,又能建构新资源,为个体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撑[5]。而作为团队成员共享的正向情绪体验,团队积极情绪同样具有“拓展—建构”功能[15],在团队建设过程中发挥催化剂作用,影响团队决策和行为。
领导创新支持对团队积极情绪具有显著影响。创新支持型团队领导者由于经常实施设定创新目标、鼓励与赞赏创新行为、提供创新资源等创新支持行为,因而会较大程度上增强团队成员参与创新任务的热情与团队士气,降低其抑郁及焦虑水平,使其拥有较为积极的情绪体验。West和Farr认为,当领导对下属提供时间、资源、信息及鼓励等支持时,会激发下属的积极情绪进而产生更多的创意[10]。Madjar等对企业员工创造力的实证研究发现,来自工作情境与非工作情境的创新支持均能提升员工的积极情绪水平,并最终影响创造力绩效[3]。
团队积极情绪有助于提升团队创造力水平。在个体层面,积极情绪一般通过促进创意形成所必需的认知和动机过程提升个体创造力[16];而在团队层面,团队积极情绪则通过拓展建构性互动提升团队创造力。根据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水平较高的团队,不仅能够拓展团队成员的注意范畴和知—行序列,促进新思想的迸发、传递和融合,形成更广泛的问题解决视角,而且能够帮助成员建构持久的身体、智力、心理及社会资源,为团队创造活动提供持续动力。与此观点相一致,Rhee的研究发现,与消极情绪相比,团队成员间更多地分享积极情绪会使其内部产生更强的“拓展与建构性”互动,此类互动会提高团队创造力和成员满意度[15]。Shin的研究指出,即使在控制了团队消极情绪的条件下,团队积极情绪仍然能够对团队集体认知、行为动机产生积极影响,并最终提升团队创造力[17]。但是,上述关系和作用机制在高校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情境中的表现如何尚待检验。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团队积极情绪在领导创新支持与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团队创新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团队创新效能感是指团队成员关于集体创新能力所共享的、一致性认知[18]。这一团队创新共享信念并非个人创新效能感的简单加总,而是在团队水平上涌现生成的特征,对团队创新与团队创造力均具有积极影响。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是将环境影响传导至行为的重要中介机制。若将该理论应用于团队层面,我们推断,领导创新支持可能通过提升团队创新效能感进而作用于团队科学创造力。
领导创新支持与团队创新效能感紧密相关。领导创新支持通过影响团队成员对创新“行为—结果”关联的预期进而影响团队创新效能感。具体而言,如果创新团队领导者以开放性态度对待变化,鼓励与赞赏团队追求新创意、包容成员的多样性观点并辅之以人员、资金、设备等条件支持,团队成员则会降低对创新风险及创新资源匮乏的担忧,更易建构起创新的间接经验,更倾向于实施创新性行为,进而增强其对创新成功的积极期望与信心。与此相一致,Tierney和Farmer的研究发现,领导创新支持水平越高,员工所报告的创造性自我效能水平也越高[19]。
由于创造性自我效能明确指向创新性能力,研究发现创造性自我效能比工作自我效能更能有效预测个体的创造力绩效[19]。而团队创新效能感对团队科学创造力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团队成员动机和团队创新过程有效性来发挥作用。对创造力持有高水平预期信念的团队,一方面,在团队创新活动中倾向于打破传统的行事方式,勇于挑战现状和承担风险,并在面临困难和阻碍时表现出较高的坚毅水平[20];另一方面,在团队互动中更可能主动交换、共享及重塑创意和观点,并倾向于通过表达信心和信念鼓励成员参与和保持创新活动。Shin和Zhou及隋杨等关于企业研发团队样本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团队创新效能感在团队输入端因素与团队创造力、团队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18][8]。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团队创新效能感在领导创新支持与团队科学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四)团队积极情绪和团队创新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作为影响团队创造力的两个关键变量,团队积极情绪与团队创新效能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认知理论与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均阐明了积极情绪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密切关系。根据Bandura和Whyte的理论[6][21],团队效能感与自我效能感有着相似的发展来源,即过去的成败经验、替代榜样、评价与劝说及情绪唤醒。作为一种正向情绪刺激,团队积极情绪是团队成员创新效能感的重要来源。而根据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团队积极情绪既能开拓团队成员的注意和认知范畴,又能建构新的社会和心理资源,进而促进团队科学创造活动中的沟通、合作行为与团队士气建设,提升团队成员胜任科学创造任务的信念水平即团队创新效能感。与此相一致,实证研究发现,团队积极情绪氛围对团队效能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2]。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团队积极情绪和团队创新效能感在领导创新支持与团队科学创造力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拟从团队情绪与认知的整合性视角,考察领导创新支持对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的作用机制,提出领导创新支持、团队积极情绪、团队创新效能感与团队科学创造力关系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与调查过程
本研究以参加全国各类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的来自54所高校的80个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为研究对象,每个团队保证至少有3名成员填写问卷。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分两次收集数据(时间间隔为1~2周),并通过独特编码(要求研究对象提供身份证号码后六位)匹配前后两次问卷。时间点1,测查变量为人口学变量、领导创新支持、团队积极情绪与团队创新效能感,共回收有效问卷781份;时间点2,测查变量为团队科学创造力,共回收有效问卷756份。最终经匹配获得743组有效问卷,问卷匹配率为95.13%。
本次问卷调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分个体和团队两个方面。就个体样本特征来看:男生629人(84.7%),女生114人(15.3%);本科生700人(94.2%),研究生43人(5.8%);年龄25岁以下725人(98.5%);参队时间6个月以下127人(17.1%),6个月~1年308人(41.5%),1年~2年222人(29.9%),2年以上86人(11.6%)。就团队样本特征来看:来自“985”高校的团队40个(50%),来自“211”非“985”高校的团队11个(13.8%),来自其他高校的团队29个(36.3%);成员来自1~2个学院的团队31个(38.8%),来自3~6个学院的团队49个(61.3%);3人团队17个(21.3%),4~8人团队18个(22.5%),9~13人团队25个(31.3%),14~19人团队20个(25%),团队平均规模为9.29人。
(二)研究工具
1.领导创新支持量表
采用Scott和Bruce编制的量表,并根据薛会娟的研究[23]和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情境进行改编,共6个项目[11]。问卷要求被试报告所在团队领导创新支持表现的情况,如“导师或队长鼓励、强调并促进团队提升创造力”。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1-5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01。
2.团队积极情绪量表
采用邱林、郑雪和王雁飞修订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24]。由于本研究探索团队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因此只采用问卷的积极因子(PAS),共10个项目。问卷要求被试报告所在团队成员最近2~3个星期内的情绪感受,如“大家是全神贯注的”。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几乎没有”到“非常多”分别计1-5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95。
3.团队创新效能感量表
采用Tierney和Farmer编制的量表[19],共4个项目。被试根据相关描述与所在团队平时表现的符合程度进行自评,如“团队成员对团队运用创意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信心”。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1-5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10。
4.团队科学创造力量表
采用刘玉新等编制的团队科学创造力量表[1],共12个项目,包括团队知识学习、团队创意产生、团队创意促进和团队创意实施4个维度,如“我们团队能及时分享、交流新知识和技术”。被试自评相关描述与所在团队平时表现的符合程度。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1-5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03,各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在0.737~0.812之间。
(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单一来源的自陈问卷法收集数据,很可能出现共同方法偏差。根据周浩、龙立荣的建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和“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25]。Harman单因子检验的结果表明,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X2/df=9.234,RMR=0.067,RMSEA=0.105,CFI=0.672,NFI=0.647,TLI=0.650,GFI=0.630,IFI=0.673,RFI=0.623)是最差的,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单因子模型,这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然后,采用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方法,在四因子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方法因子之后,模型的拟合指数(X2/df=2.464,RMR=0.022,RMSEA=0.044,CFI=0.946,NFI=0.914,TLI=0.938,GFI=0.916,IFI=0.947,RFI=0.899)优于四因子模型,但X2/df仅提高了约0.40,其他指标的改善程度均在0.01~0.03之间,拟合指数并未出现较大改善。由此再次表明,本研究所测量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四)统计分析
采用SPSS19.0和AMO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首先,采用AMOS17.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其次,采用SPSS19.0进行团队数据聚合检验、描述性统计及Pearson相关分析。然后,采用AMOS17.0进行结构方程建模,检验团队积极情绪和团队创新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效应,并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Bootstrap检验。
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团队数据聚合检验
由于将领导创新支持定义在团队层次,且所有问卷均是由团队成员填写的,所以需要把个体层次的数据聚合到团队层次,并验证聚合的合理性。根据James等的建议[26],采用组内一致性指标Rwg和组间异质性指标ICC(1)、ICC(2)这三个指标来检验各变量聚合的可靠性。结果表明:领导创新支持、团队积极情绪、团队创新效能感和团队科学创造力四个变量的Rwg均值(分别为0.754、0.823、0.687、0.844)均基本达到或高于0.70的临界标准;四个变量的ICC(1)值(分别为0.252、0.083、0.129、0.109)、ICC(2)值(分别为0.758、0.458、0.580、0.532)基本达到了0<ICC(1)<0.50和ICC(2)〉0.50的经验标准。因此,所有变量在团队层次上的聚合是适当且有效的。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整合后的团队层面数据进行基本的统计描述和相关分析,所有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的领导创新支持平均分为3.925,说明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的领导创新支持水平较高;团队积极情绪、团队创新效能感和团队科学创造力平均分在3.927~4.061之间,说明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的团队积极情绪、创新效能感水平较高,且拥有较好的科学创造力表现。此外,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在0.332~0.675之间,呈中高程度相关且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其中,领导创新支持与团队科学创造力(r=0.591,p<0.01)、团队积极情绪(r=0.332,p<0.01)以及团队创新效能感(r=0.500,p<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团队积极情绪(r=0.549,p<0.01)、团队创新效能感(r=0.675,p<0.01)与团队科学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团队积极情绪与团队创新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0.509,p<0.01)。结果表明,研究变量满足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假设的基本要求。

表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n=80)
(三)假设检验
为验证研究假设,使用AMOS17.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考察团队积极情绪和团队创新效能感在领导创新支持和团队科学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为了节约自由度和增强模型的简约性,根据卞冉、车宏生和阳辉的建议[27],采用平衡取向法对领导创新支持、团队积极情绪和团队创新效能感等单一维度潜变量分别进行打包处理,打包后的观测变量以每个项目组内项目的平均分代替。领导创新支持形成领导创新支持1和领导创新支持2两个项目组,团队积极情绪形成团队积极情绪1、团队积极情绪2和团队积极情绪3三个项目组,团队创新效能感形成团队创新效能感1和团队创新效能感2两个项目组。
本研究通过建构3个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团队积极情绪与团队创新效能感在领导创新支持和团队科学创造力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首先,以领导创新支持为自变量、团队科学创造力为因变量构建模型M1,探讨领导创新支持对团队科学创造力的直接作用;其次,加入团队积极情绪和团队创新效能感作为独立的中介变量,构建模型M2,探讨二者的并行中介效应;最后,在模型M2的基础上,建立团队积极情绪与团队创新效能感之间的联系,即设置“领导创新支持—团队积极情绪—团队创新效能感—团队科学创造力”链式中介路径,构建模型M3,探讨二者的链式中介效应。各模型拟合指数见表2。本研究发现:在模型M1中,领导创新支持对团队科学创造力的路径系数显著(β=0.393,p<0.001),且模型拟合较好,说明领导创新支持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团队科学创造力,验证了假设1;在模型M2中,模型拟合较差,排除了团队积极情绪与团队创新效能感的并行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模型M3建立了团队积极情绪与团队创新效能感的链式中介路径,模型拟合良好,同时模型中所有路径系数均显著(见图2)。因此,根据联合显著性检验可以判断,团队积极情绪与团队创新效能感各自的中介效应显著,二者在领导创新支持与团队科学创造力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也显著。以上结果表明,领导创新支持分别通过团队积极情绪、团队创新效能感和团队积极情绪—团队创新效能感三条路径间接影响团队科学创造力,即验证了假设2、假设3和假设4。

表2 各模型拟合指数

图2 中介效应模型(模型M3)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检验,重复取样1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结果表明,团队积极情绪和团队创新效能感在领导创新支持和团队科学创造力的关系中起多重中介作用。总中介效应由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领导创新支持经团队积极情绪、团队创新效能感、团队积极情绪—团队创新效能感中介链对团队科学创造力产生的中介效应均显著,置信区间分别为[0.009,0.140]、[0.046,0.167]、[0.006,0.087],均不包含0,再次表明各中介路径均成立。由表3可见,从领导创新支持到团队科学创造力的直接效应值是0.202;总间接效应值即总中介效应值为0.180;总效应值为直接效应值与总中介效应值之和,即0.382。效果量为各中介效应值除以总效应值,三条中介路径的效果量分别是13.6%、24.9%、8.6%,总中介效果量为47.1%。各路径的效应值及效果量详见表3。

表3 领导创新支持影响团队科学创造力的路径及效应分解
五、研究讨论
(一)理论贡献
基于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本研究考察了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领导创新支持对团队科学创造力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领导创新支持对团队科学创造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团队积极情绪和团队创新效能感在领导创新支持与团队科学创造力之间兼具单独中介和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拓展并丰富了团队创造力研究内容
本研究发现,领导创新支持正向预测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β=0.393,p<0.001),此结论与以往个体层面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8][4]。这既验证了创造力成分理论在团队层面的解释力,又将团队创造力的研究范畴拓展至高等教育领域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情境及科学创造力维度。在具有高挑战性和高不确定性的大学生团队科技创新活动中,领导创新支持的重要价值愈加凸显,领导者对创新价值的期望、对错误的容忍等心理支持和积极的信息反馈、充足的资源等工具支持,更可能通过开发团队创造力技能、激发团队内在动机进而发挥其对团队科学创造力的协同与集聚效应。如今尽管对于团队创造力的研究日益丰富,但仍缺乏从团队中的领导创新支持视角来思考如何提高团队创造力这一问题,对于领导创新支持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个体层面。本研究将领导创新支持作为团队层次的变量加以考察,为我们理解团队创造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丰富了现有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2.整合了团队积极情绪与团队创新效能感两种中介机理
研究还发现了团队积极情绪和团队创新效能感在领导创新支持与团队科学创造力之间的单独中介与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分别为13.6%、24.9%、8.6%,这为“双创”时代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创造力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1)揭示了团队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在支持创新的领导情境下,积极情绪体验不仅能够扩展团队成员的注意范畴和知—行序列[29],提高成员的认知效率和灵活性[30],还有助于提升合作、降低冲突[31],促进成员之间产生彼此共情、鼓舞他人、及时反馈等[13]积极性互动,进而提高科学创造力表现。(2)发现了团队创新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在较高的领导创新支持水平下,创新效能感较高的团队不会拘泥于传统行事方式,不惧挫折与失败并表现出较高的坚毅和冒险水平,而且更加注重成员间分享创意,从而产生更高水平的科学创造成果。此外,与团队积极情绪相比,团队创新效能感的中介效应量较高,其原因可能在于,团队创新效能感这一集体创新能力共享认知与团队科学创造力的内在关联度更高。(3)验证了团队积极情绪与团队创新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效应。该结果从实证研究视角和团队层面支持和深化了社会认知理论与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的核心观点,发现团队积极情绪体验是科学创造过程中团队创新效能感的源泉;而共享的积极情绪体验对团队认知、社会关系等具有显著的拓展建构功能,进一步增强了团队的创新信念和效能感。
(二)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团队科学创造力的形成机理,也对“双创”背景下的创新教育管理实践具有如下重要启示:
1.发挥“重要他人”的作用,强化领导创新支持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指出,在个体迈向最近发展区的进程中,重要他人(如导师、队长等)发挥着尤为重要的“脚手架”作用[32]。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指导实践应注重如下方面:(1)健全创新激励制度。针对团队成员的创新行为,指导教师或队长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为成员提供创新创业知识、信息、智力和情感等必要支持,并对创新行为及时给予精神或物质激励。(2)培育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针对创新文化,Csikszentmihalyi指出,创造力只有在具有文化准则的系统中才能获得承认,并且只有在获得支持时才能造就新的突破[33]。为此,团队领导者应关注团队成员的创新思维,适时给予正向反馈,为成员冒险、试错提供自由空间,为新思想、新创意、新做法的孵化厚植文化土壤。
2.营造积极情绪氛围,开展团队积极情绪训练
研究结果显示,团队积极情绪不仅在领导创新行为与团队科学创造力之间发挥直接中介作用,而且还通过与团队创新效能感的链式中介关系作用于团队科学创造力。该发现具有如下实践启示:(1)营造创新团队积极的情绪氛围。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情绪决定了个体在创造性活动中对智力的运用[34],团队积极情绪对团队创新实践发挥着十分重要的聚智和融智功能。团队领导者可通过传播“正能量”、提供积极反馈、展示成功案例等途径传递积极情绪,激发成员的创新主动性和创造激情,进而提高其调动和建构新资源(认知和社会资本等)的能力,形成乐于并善于创新的文化氛围。(2)开展团队积极情绪训练。在大学生“双创”教育实践与科技创新管理活动中,学院可通过乐观思维训练、笃行善举等团队心理辅导活动开展积极情绪训练,提升成员的情绪控制与调节能力,保持适度的团队情绪积极率(Positivity Ratio),为科技创新营造积极和谐的人际氛围。
3.培养科技创新的内驱力,提升团队创新效能感
本研究还发现,团队创新效能感是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的关键性认知路径,因此建议指导教师或队长积极采取如下行为策略:(1)提升团队创新自信。可通过列举过去的成功经验、树立替代性榜样、启发引导、促进创造性角色认同等途径增强团队成员的创新自信,创设“更多的创新资源保障、更低的创新风险承担、更强的创新期待”等创新支持性环境。(2)增强团队创新效能感。强化团队成员创造性自我效能的差异化互补和相互传递,为团队成员设立不同挑战性水平的创新目标,构筑创新成果分享与认可平台,不断增强整个团队的创新效能感,进而促进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的持续发展。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虽然本研究发现了上述有价值的结论,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使用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能完全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且领导创新支持对团队科学创造力的作用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未来可采用纵向追踪研究进一步探讨在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二者关系的动态演化机制。其次,采用单一来源的自陈式量表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后续研究可尽量扩展数据来源主体并尝试采用客观度量工具测量大学生团队科学创造力等变量,以增强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最后,本研究探讨了领导创新支持与团队科学创造力关系中情绪路径与认知路径的单独与链式中介机制,但影响过程中还有哪些中介机制,尚需更深入探讨;同时,本研究未涉及二者关系中的边界条件,一些契合高校科技创新团队特点的情境因素(如团队领导信任、团队竞争氛围等)是否会影响领导创新支持激发团队科学创造力的过程,尚待未来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