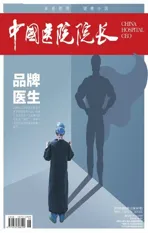儿童缓和医疗:美好待完成
2019-05-14吴佳男
文/本刊记者 吴佳男
多方倡议和实践过后,儿童舒缓医疗渐现新发展契机。

北京儿童舒缓治疗活动中心内,稳定期的孩子们在自在玩耍。
“张开双手,伸出五指,恭喜你,你给自己放了一次烟花。”2019年1月1日,一部纪录片中,对着镜头,一个名为杜可萌的少女交替向上舞动双手,动作像极了嘭嘭作响、绚烂而又转瞬即逝的烟花。
这部纪录片,名为《人间世》(第二季),第一集的名字叫《烟花》,反映的是多个重症患儿的真实状态。《人间世》的第一季,豆瓣评分为9.7,而第二季,至记者截稿,评分为9.6。公众热切关注本剧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对终末期“不治之症”孩童的集体“共情”。
“如果还有家伙没有闹够的话,来吧,让我们来奉陪吧。”孩子们面对镜头发出了呼喊。
而对于这些呼喊,医疗机构如何“奉陪”?
时势所需
《烟花》中的主要出镜对象为骨肿瘤患儿,主要摄制场所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公众对骨肿瘤了解太少,多数家长很难第一时间确定孩子症状,一些医生也不能及时准确诊断病情,导致一些孩子在确诊时已经发生癌细胞转移,难以治愈。”
推动公众对儿童重疾的认知,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蔡郑东教授及其团队大力配合此次拍摄的重要动力。
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每年大约有25万儿童罹患癌症,中国每年新增患儿为3至4万名,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小时就有4名儿童被诊断为恶性肿瘤患者。这些疾病中,除了较为罕见的骨肿瘤,大多为白血病、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淋巴瘤等,1至3岁儿童中,肝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和恶性生殖细胞肿瘤也较为多见。
以上疾病,治疗过程多数身伴重度疼痛,病程或“漫长”或短暂:“漫长”指代的是数年,短暂对应的则为几个月。而对其中20%的患儿来说,患上此类疾病,意味着更早离开人世。
“要让这些孩子更有尊严,痛苦更少地离开。”这成为近年来部分有识之士呼吁、关注并践行的目标。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原陆军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多年来一直在倡导并推动缓和医疗,在他看来,关照儿童舒缓医学发展,是当下和未来一代医者的共同责任。
“儿童舒缓治疗和成人的临终关怀具有同样的伦理意义,让患儿有尊严、舒适地离开,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人道主义在医学领域的升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社会工作部主任刘芳告诉记者,儿童缓和医疗研究与实践已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多年来,中国形成了“4+2+1”式家庭结构,儿童成为整个家庭的重要核心,一旦其身患重症不幸离世,对家庭冲击性更强;另一方面,与成人相比,儿童受年龄限制,心理发育不成熟,对死亡认识模糊,儿童舒缓治疗需要以患儿和家庭为中心,基于共同决策、家庭文化等因素开展。
“患病后,终末期儿童还遭受着和成人一样的疼痛,却难以准确表达”。在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樊碧发看来,相关疼痛学研究成果,也应在儿童缓和医疗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在全国建成较早,学科能力排名靠前,尤其是在神经痛和骨关节痛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位置。多年来,樊碧发和团队几乎每天都要密集“接待”初始入院和终末期儿童患者,为其出具有针对性的疼痛治疗方案。“不过现有处理办法并不多,多数仍处于剂量调整和常规镇痛药物使用层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周翾是国内最早的儿童舒缓医疗践行者之一。
艰难尝试
1月8日下午,位于北京西城区一家酒店5层,北京儿童舒缓治疗活动中心的大厅里,几个孩子和家长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这些是病情暂时处于稳定期的孩子”。大厅旁边的会客室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周翾介绍,自己在2011年创办了这个小小的“医患之家”。当时,一位特殊的淋巴瘤患儿遭受的疾病痛苦,以及患儿父母坚持救治的决心,激励她在未来从事儿童临终关怀事业。
在很多业界人士看来,周翾属于国内最早一批践行儿童舒缓医疗的医生之一。2011年至2013年,周翾曾先后前往美国圣吉德儿童研究医院、摩根斯坦利儿童医院、英国Great Ormand儿童医院等地,实地考察儿童缓和医疗经验。
2013年,周翾在第二次探访美国圣吉德儿童研究医院之后,邀请到一位同行的护士,就在医院开始落地这一新服务。接下来的一年中,在各类儿童血液病或其他重症医学会议上,她演讲的内容都集中于儿童舒缓治疗和镇痛,“目的在于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和参与”。
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已形成儿童舒缓治疗的固有模式和流程:从患者需求出发,以疼痛和症状管理为抓手,医生主导,团队精细分工,联动社工和志愿者。具体诊疗过程中,他们采取“门诊流动”形式,每周举行电话例会,以多学科协作形式讨论各项疑难问题,进而分解各项工作,整个链条完整而又高效。“在美国,21岁以下患者的临终关怀有医保,但也鼓励有支付能力者费用自负,节省下来的费用用来关怀贫困患者”。
中国患儿的治疗费用一直是个大问题,西方经验在中国的推广,首要问题也是经费。化缘大半年后,因为机缘巧合,周翾在一次患儿遗体捐赠仪式上结识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刘正琛。当时,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设立一个专项基金,以此助力国内儿童缓和医疗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
“从达成意向到签约,我们仅用了一个月”。2014年8月,以“尊重生命、守护生命”为宗旨,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儿童舒缓治疗专项基金正式成立。在周翾看来,正因有了这一资金募集渠道,部分想法在后来逐步变成现实。
在2017年5月举办的全国小儿血液与肿瘤学术会上,在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王天有教授和周翾等人的倡议下,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儿童舒缓治疗亚专业组正式成立,来自全国三十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式成为亚专业组成员。“专业组几乎涵盖了国内有能力展开儿童舒缓治疗的医疗机构”。
2017年10月31日,由新阳光儿童舒缓治疗专项基金和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共同打造,北京第一家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雏菊之家”正式启用,旨在为肿瘤末期的儿童和家庭提供临终关怀服务。
“临终关怀是针对生命预期小于6个月的病人,而舒缓治疗则在诊断时就可以开始”。周翾表示,尽管仍是病房,但相对于大型公立医院病房的嘈杂与纷乱,“雏菊之家”无痛而又温馨的家庭式环境,对患儿和家长均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患儿离世时会更平静,家长们的绝望与悲痛也被相应缓解。
在周翾看来,至今成立一年有余,雏菊之家正成为一块重要阵地,也是“样板间”。她希望可被复制到更多地方。
多种模式
“周翾主任在推广儿童舒缓医疗上作出了很多努力”。2011年2月至2012年年底,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郑州三院”)血液科小儿血液肿瘤病区副主任王娴静先后多次前往北京儿童医院血液中心进修,学习小儿血液病治疗及小儿造血干细胞移植,其间与周翾接触颇多。
2013年8月,郑州三院成立了儿童血液病区,王娴静正式开始在该院进行儿童舒缓治疗。
新阳光-儿童舒缓治疗专项基金合作中心2015年8月落地郑州三院,周翾团队和王娴静团队合作更为紧密。截至2018年年底,医院已接收并救治了数十名终末期患儿。
“我们的原则,首先是准确评估病情,使患儿避免在临终前一段时间内接受不必要的过度放化疗,享受健康儿童应享受的一切。医务人员也在尽量为孩子创造正常的环境,掌握更多、更好的无痛用药疗法。”
除北京和郑州,上海、深圳、长沙、长春、哈尔滨等地部分医疗机构或社会福利机构,也逐渐摸索出各自的诊疗路径。

1北京第一家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雏菊之家”。

2 2019年春节期间,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科小儿血液肿瘤病区副主任王娴静和志愿者看望终末期患儿。
2008年,在美国圣述德(St.Jude)儿童研究医院的儿童舒缓安宁疗护技术和资金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拥有了国内三甲医院中唯一一间“儿童临终关怀”病房,主治医师王坚敏成为该医院最早系统学习儿童安宁疗护的医生。
“做的人很少,更需要相互交流和抱团取暖。”2013年,周翾曾专程前往上海,和王坚敏等人进行过深入交流。
2017年,深圳市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病童医院(SickKids)进行了“三名工程”合作,在医院社工部配合下,在地区率先开展了儿童舒缓治疗项目,为患儿提供舒缓治疗及陪护志愿服务;“蝴蝶之家”位于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内,近年间,在英国退休护士Lynda(中文名金玲)创办的慈善基金帮扶下,呵护众多16岁以下、预期寿命6个月以内的孤残儿童走完了人生路。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肿瘤科近年来收治了相当多的儿童神经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淋巴瘤及各类神经系统肿瘤、骨肿瘤等重症患儿。在这些儿童中,约40%处于恶性肿瘤中晚期,治疗难度大,预后相对较差。联动医院社工部,帮扶患儿及家属向社会筹集治疗费用,引入儿童营养师、药师、心理师和志愿者,强化对患儿的支持治疗,成为该院治疗团队的目标。“给孩子们捐赠假发、建立图书角,组织患儿和家属看电影等,都只为让患儿和家属暂时脱离痛楚,让孩子‘生时灿似夏花,去时美如秋叶’。”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肿瘤科主治医师王立哲告诉记者。
近几年间,每年三到四次的频率,周翾坚持前往每家合作医院义务指导终末期患儿舒缓治疗。至今,雏菊之家已与郑州三院等医院建立了顺畅的上下转诊渠道。“以前,很多终末期孩子在一些大型医院,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回家,要么住进重症监护室,被过度治疗。现在,尽管我们的作用微弱,但至少部分患者多了一个选择。”王娴静表示。
“大家都在尽自己的力量去推动这项工作,尽管这个网络仍很稀疏而又单薄。”周翾举例说明,在香港癌症基金会统筹之下,特区的各个区域均配备了专职团队,团队成员间合作非常紧密。相反,内地各有志于此的团队仍显得过于松散,专职人员状态又超负荷,殊为不易。
医社结合
2014年至今,在新阳光儿童舒缓治疗专项基金的支持下,面向全国各级医疗机构,联动北京儿童医院等单位,周翾团队开展了大小十余次儿童舒缓治疗培训。“参与者从几十到一百余不等”。尽管每次参会人数并不多,但经费逐渐捉襟见肘,理念向更广、更深层面普及的想法只能暂时搁置。
不止理念和相关研究成果普及难,在樊碧发看来,在各医疗机构间,达成疼痛管理的共识,更是儿童缓和医疗进一步推进的重中之重。“西方国家重症儿童的疼痛管理共识,不能直接应用于国内,中国传统医学相关因素和东西方文化差异,都决定了中国应有更符合国情的疼痛管理共识。”
实践过程中,王娴静也发现,尽管止疼泵等可应用于儿童癌痛治疗,但无法解决患儿“仍然叫疼”这一老大难问题。“这需要更多人进行更深入、更精尖的研究,也需要更多人愿意去做”。
“团队人数少,能直接服务的患儿数量有限”。这是王坚敏和周翾目前最为担心和头疼的问题。在周翾看来,换句话说,目前,包括一些家长在内,有意愿参与此项事业的志愿者并不少,但让有能力、可践行责任的医院都拥有成熟的诊疗团队,颇有难度。这一点,从此前相关培训推进之难便可见一斑。
王娴静也认为,除了更多医院的病房“以治愈为目标”这一现实约束,将儿童舒缓治疗作为专业进行研究,当下也并不现实。“引入的社工和心理师,大多是免费帮忙,薪酬难进医保。”
中华安宁疗护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人、总干事张泽涛近年来致力于成人缓和医疗,曾联合北京海淀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了多个安宁疗护项目。
2018年11月,在北京市民政局组织的2018年度志愿服务活动培训会上,“海医安宁”项目被作为典型案例分享。“但儿童舒缓医疗,既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张泽涛“一针见血”:只有各级民政部门、医疗机构,甚至社会公众达成广泛共识,形成联动机制后,国内儿童舒缓医疗才能迎来大幅前进的契机。
刘芳也认为,未来,儿童舒缓医疗需要更多支持,各方应积极探索建立本土化的儿童舒缓医疗服务体系。“通过立法,明确主管部门及其监督管理责任,明确投入、保险、收费、绩效等筹资与补偿机制,明确对儿童舒缓治疗对象的界定和儿童临终关怀医院或病房的设置标准、技术标准及操作规程,以及从业人员的资质、职责和伦理要求,机构的设施、设备、药品以及资金的管理,收费标准等,甚至结合分级诊疗相关政策,才能将这一体系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院、居家临终关怀服务大的链条中。”
不过,事实证明,近年来,越来越多公立医院已关注到这一领域。
2018年5月,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儿童临终关怀与家庭卫生保健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儿童舒缓治疗与家庭健康照顾专业服务研讨会在北京儿童医院召开,来自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家庭发展司、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财政部社会保障司等多个单位参与了本次会议。
会上,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表示,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与会各方将在理念、儿童舒缓医疗服务方法、技术和医务社会工作等方面发力,将诸多崭新服务因素、专业力量引入儿童医学领域,提高儿童医学与家庭卫生保健服务质量,以改善儿童、家庭的健康福祉。
联合各级儿科同道和相关学会,推出儿童舒缓医学专家共识,也是樊碧发在2019年的重要工作内容 之一。
“医院之前对儿童舒缓治疗病房未做考核,未来也将鼎力支持。”王娴静感慨。
“构建医、药、护、技、社多端共助模式,将有更多患儿收获温暖。”王立哲介绍,借助财政支持,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医路有我”项目有力帮扶了医院儿童舒缓医疗。2019年,这一工作也将迈入崭新阶段。
“不少民营医疗机构关注到了儿童舒缓医疗。”周翾以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前来邀约合作为例,向记者展示了行业利好,坦承了未来期望:“希望2019年,雏菊之家再建成几间病房,这是锦上添花,也是责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