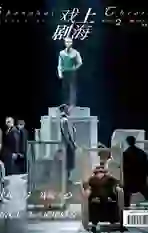丹麦王子的跨时空质询
2019-05-07末之
末之
今年年初,上海大剧院上演了李六乙导演的《哈姆雷特》。笔者近年来看了许多不同版本的《哈姆雷特》,各种感觉沉淀交杂在一起,恰如导演所言,每十五分钟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就在上演《哈姆雷特》。尽管此话的确切性有待考证,不可否认的是,经典之作的不同诠释必然会揭示主创的艺术、生命和价值观,甚至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信仰。由此看,这个丹麦王子早已跨越时空,成为某种衡量人们情感和思想的基准线,各种心理的、身体的、语言的复调意义都在他身上聚焦和折射。
在《哈姆雷特》的舞台表演上,剧场空间历来是创作者重要的考量。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剧场设计就是全剧的一个意义象征体系,即这个空间得承担揭示现实背后和秘密所在的象征功能。此后又有莎剧专家认为,《哈姆雷特》的表演剧场的设计旨在不断推动观众的自我意识,而非让观众与人物形成角色代入和共鸣感受。
此剧就舞台形式而言,其简约留白的特征从大戏开演之初就彰显无疑,一大块围绕中轴可以四周高低倾斜的活动平台,一个挂在上方可以升降的球体,让现实背后的秘密昭然若揭。于是观众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了演员的演绎和语言表达上。
令我疑虑的是背景中那个自始至终都在持续的读秒“嘀嗒”声,虽然声音微弱低沉,似乎不会干涉演员的台词表达,但在节拍的规律中会对剧场中的观众产生心理催眠效果,以至于笔者很确定地认为这次观戏是迄今最需要动用自我意志力与瞌睡抗争的一次体验,必须屡屡挣扎着保持清醒,理智上不断告诫自己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自有深意。不过,或许主创有意含蓄地放入时间这一恒久的生命母题,无奈对于心理催眠机制了解不够,否则不会冒如此巨大的催眠风险吧。
此外,《哈姆雷特》的东方诠释在表演中有着独特的艺术体现。从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处理,到女性歌者不断引领人物情绪和渲染氛围的无词吟唱,甚至是东方色彩浓郁的服装设计,无不显现出莎士比亚地方化的跨时空特质。空灵、叹息般的旁白式吟唱让简约空茫的舞台更显出中国水墨画的留白韵味,这种文化空间移植和陌生化处理,在审美上颇有新意。尤其是歌者的无词吟唱感叹,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剧场公共空间和演员及观众的个体情绪,让作品有了气韵的流动,同时潜在地传递了改编创作上的主题意图。
此剧的另一个独特设计点是让奥菲莉亚和王后葛楚由同一位演员扮演,无论是年龄跨度、声音的有意违和,例如故意让少女奥菲莉亚的表述语调显得沉静稳重等,这些都易引发争议和讨论。尤其是墓地的一场,葛楚和死去的奥菲莉亚在舞台上合二为一,不再是之前不同时出场的两人,观众无需特别告知就立即明白了两者合一的设计。王后白衣飘飘,宽袖大幅度甩动,刚为少女的消亡哀伤怜惜,为她撒上鲜花朵朵,随后就地躺下,王后即刻成为了逝去的少女本人。这瞬间的转化,显然寓意着这两位女性在哈姆雷特生活中的高度同一。她们是王子情感的依恋和投射客体,是王权和男权之下的犧牲品,也是脆弱和被动的女性形象象征。
美国当代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曾经创作过一部现代小说《格特鲁德和克劳狄斯》(2000年),从女性主体追求情爱和自由的角度颠覆性重塑了王后形象,让原本副线的弑兄娶嫂故事成为了主线的爱情传奇。
然而这个版本的设计恰恰是选择性省略了女性在爱情、伦理、价值选择上的主体能动,更多突出了她们相对类似甚至一致的辅助功能,即以渲染哈姆雷特的情感、思想发展为主,两者合体成为男性审美及情感的被动客体。不知女性观众是否感受到其中的微妙,又会有怎样的反思?
亡父幽灵和克劳狄斯在剧中也由濮存昕一人饰演,但是这两个人物却是截然对立和反差巨大的,这恰好与女性角色的一人分饰两角形成比照。不过笔者个人认为男性角色的一人分饰并非出自艺术设计需求,可能是更多考虑知名演员的戏份和票房号召力吧。
该剧最引人关注的重点在于,哈姆雷特的行动延宕和犹豫在这一版中被解构和稀释了,因而那段最脍炙人口的“To be or not to be”独白,前半段遵照原剧本,放在了戏剧中间部分,但形式上并非孤独的沉思,而是与奥菲莉亚的感喟形成了某种平行对话。
当笔者还在迟疑为何只有未完的半段时,出乎意料之处显现了:剧终时,当其他人物一一退场,倒地身亡的王子起身再次走到活动舞台的中央,照明的光影显然极具未来感,死去的王子复活般再次吟诵着这段话,似乎要在曲终时分将人们的思绪给予显在形式的升华。而且原来的独白段落增添了不少行数,尤其是萦绕不去的“To be or not to be”,在中文表述中,从最脍炙人口的朱生豪译文到此后各位译者的版本渐次被一一表述。
从这一版令人耳目一新的译文“在还是不在”,到“生存还是毁灭”“活着还是死去”……多重中文诗行将原本复调含混的简单一句不断排比铺陈、变奏演绎。观众似乎被这个需要作出选择的“A还是B”的结构给镇住了,于是大家领悟到,王子在复仇和爱恨上并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而是执意要抛掷给观众一道选择题,一个关于在场和缺席、生命和信仰、意义与虚妄、理智与情感的设问。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一,也许主创的核心创意就放在了这个独白位置的调整上,目的是要让强烈的戏剧间离效果拽着人们进入更高层次的思索。
这一质问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或许也是本质的选择,即人究竟是命运的受控者,还是掌控者?
根据一位戏剧学者所言:“剧作家创作戏剧作品;台词则是特殊制作中的内在图解;剧场艺术是演员在特定的演出中演绎的一套特定姿态;而表演就是观众和演员同时参与的完整事件。”(Chitanu)那么在剧终时刻,不知观众能从这同时参与的完整中反思到怎样的自我生存状态,又将如何从这看似历史的故事中,面对现在和未来。这大概也是主创想要最终达成的思想触动吧。
莎剧中哈姆雷特的独白首先具有强烈的非对话性质,对戏剧情节的推动形成某种反讽式的中断或障碍,因而成为舞台改编上的重要挑战。这一内心化的心理揭示在这一版中改换到剧终,从原先设定的自我反思悄悄地转为面对观众的、带有质问和启发性质的倾诉。有趣的是,这段独白即便在莎士比亚剧本中,也因为观众深知剧中众人在舞台隐蔽处或帷幕后的“旁听”而被称为“所有莎剧中处于最拥挤状态的独白之一”(Charney)。
此版中,這一独白最初与奥菲莉亚的祈祷交织对应,在意义上相互对应补充,在情感推进上动力充足。独白表达的同时,哈姆雷特自觉意识到这段话正被旁人偷听,甚至带着有意被听见的心理在倾诉。此剧最终,王子游离出剧情,演员超越了剧中角色进行吟诵,他要表达的就不再是丹麦王子是否要采取复仇行动或结束生命的迟疑,此举的目的也不再是原来的王子有意引导幕后窃听者步入他需要的理解情境,而更多是演员以自身真实的身份跳脱出剧中人物身份,对全剧的创作主题进行了总结性反思。当然,这样的改变也因此可能会承担寓教过重、略嫌用力的风险。
反倒是有不少回味隽永的诗意表达,因为在对话交流上展开,观众回顾起来会因其不着痕迹的自然流露,有了更生动的启迪作用。例如,哈姆雷特在和自己同学罗森格兰茨和吉尔登斯登对话时,因谈及梦想,感叹自己要不是有了恶梦,“那么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2.2.255-7)这一句话的意味常常超越了戏剧语境,让当下的人们在反思生存意义时发出“身陷樊笼,心鹜八极”的生命感叹。
《哈姆雷特》在莎剧中一直被公认为最具有丰富、灵活、有力的语言特色,诗意潜能巨大,表演和改编的挑战难度最大,在艺术上的影响焦虑毋庸置疑。不少片段,尤其是王子独白的真诚和假装程度历来是人们不断解读的对象。戏剧反讽抑或真挚坦言,人物心声或是剧作家、导演的意图介入,这些程度不一的不同异演绎和诠释,也由此汇成了观众心目中始终活跃生动的莎剧意义。
(作者本名张琼,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Chitanu, Cristina. "Theperformativity of literature." TheAnaChronisT, 2010, p. 73+. LiteratureResource Center, http://link.galegroup.com/apps/doc/A361553256/LitRC?u=fudanu&sid=LitRC&xid=3bec6c64. Accessed 17 Jan. 2019.
②Charney, Maurice. "Asides,Soliloquies, and Offstage Speeches in Hamlet: Implications forStaging." ShakespeareanCriticism, edited by Michelle Lee, vol. 91, Gale, 2005.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http://link.galegroup.com/apps/doc/H1420067062/LitRC?u=fudanu&sid=LitRC&xid=361f0e69. Accessed 17 Jan. 2019. Originallypublished in Shakespeare and theSense of Performance, edited by Marvin Thompson and Ruth Thompson,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1989, pp. 116-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