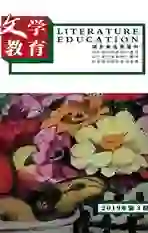浅析《梅雨之夕》中的无意识过程
2019-03-30宣菲
宣菲
内容摘要:《梅雨之夕》是出版于1933年的新感觉派小说,具有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作者在作品中运用了许多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理论,巧妙地塑造出情理矛盾而饱满真实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梅雨之夕》 心理分析小说 施蛰存
梅雨,初夏江淮流域一带经常出现一段持续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正值江南梅子黄熟时。梅雨之夕应是缠绵的、暧昧的、而又引人遐想的,能够无限引起文人心中涟漪的时刻,如此一个标题就已为小说朦上了独特的滤镜和气息。
《梅雨之夕》全篇没有过于曲折惊心的剧情,讲述一个已婚男子在一个雨夜归家途中邂逅妙龄少女进而引发一系列复杂心理活动,最终回归现实的故事。它甚至算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故事”,情节上只有简单的男子主动提出用伞送少女一段路程,却让心理刻画占据了篇幅的八成以上。主人公内心丰富的活动和脑袋里辗转回旋的思绪,毫不比好莱坞老片《雨中情》的歌舞来的逊色。
《梅雨之夕》作为新感觉派小说中具有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中国真正的现代主义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山之作,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一个非传统的角度探索人性。
从小说的描写不难看出,文中的男主人公对于雨并不厌嫌,甚至还有些享受与喜爱“对于雨,我倒并不觉得嫌厌……我喜欢在滴沥的雨声中,撑着伞回去……沿着人行路用一些暂时安逸的心境去看看都市的雨景,虽然拖泥带水,也不失为一种自己的娱乐。”①与周围选择坐车的同事形成对比,似乎是一种“独特”的自怜。且后面男子由风吹少女的图案联想到日本画伯铃木春信的一帧题名叫“夜雨宫诣美人图”的画,又从她的粉香在嗅觉上联想到古人有“担簦亲送绮罗人”这么一句诗,能看出男子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修养的“小资”都市青年,不怪他见到这瘦削可爱的妙龄少女会不自禁带上诗意的着迷眼光。对于这样一个注定心理活动丰富、感知敏感的男子来说,梦想是平凡生活中的药剂,与这女子的美好相遇甚至让他选择性遗忘自己已有妻子的事实而钻入遐想。
男主人公在无意闲暇之中邂逅了从电车上下来却没带伞的美丽小姐,有如戴望舒《雨巷》中那个彷徨在悠长寂寥雨巷的丁香姑娘,像是代表着男文青年理想的女性形象,一切都是偶然的,命数的安排让他更加痴迷这份浪漫、不断美化少女的形象。他先是不断观察少女焦急查看雨势的表现,内心随着这光景不断活跃,在向前迈一步伸出雨伞与情理世俗中不断纠结进退,在焦灼的纠结中竟也度过了一个多小时。虽然清楚这般行为怪异却最终选择鼓起勇气搭话,羞赧的姿態回应少女的注目,假作神色泰然地提出送少女“回府”。
这一路,“我”假象着路边的人可疑的神色,“我”猜想着少女的内心活动,“我”由这个陌生的少女形象远想到几年前十四岁的初恋,又挣脱樊笼轻快起来。在这丰富的描写下仅存在一个平淡的现实,只是短暂而又局促的一段同行罢了。最终还是呆呆坐上人力车回到家中,天晴了,妻子身上那少女的幻影也忽地消散,这一场自我意识的狂欢也就作散了。有人说文中的青年男子是猥琐的、善于意淫的,在我看来这般评价过于偏执而狭隘的,文中的“我”更多是富有艺术色彩的,不应用世俗道德框架评判的存在。
施蛰存先生的名字中的“蛰”字,能让人轻易联想到惹人清新的酥酥春雨,《梅雨之夕》的我也被赋予了与雨相关联的特质——敏感、向往诗意。也有人轻易评论男主人公满怀着冲破伦理禁锢的激情。其实从作者施蛰存先生的写作习惯出发可以发现,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学,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尤其在接触到弗洛伊德的学说之后,作品风格上借鉴了不少其理论。除了西方现代主义,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也受到日本新感觉派启发,楼适夷先生也将其评论为新感觉派,又很大程度上倾向心理分析小说。作品中的“我”是繁华上海都市中的小职员,多情、温柔细腻且知书达理,或许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人格的投射。在这雨夜中他暗涌的情感与欲望交织成一个梦想。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②文中的“我”连走路的规则都是十分在意,“……我在上海住得很久,我懂得走路的规则……”①且对这都市人群的描写“第一个,穿着红皮雨衣的俄罗斯人,第二个是中年的日本妇人……”①可看出上海这城市是非常国际化和工业化的,在这样高度文明的城市,“我”的行为受规则牵制影响着,“我”的“本我”被文明深深征服。作者通过生理和社会共识的碰撞来表现人物心态的变化,探寻并还原其被压抑极深的真实人性。再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有三重人格:本我、自我和超我,后两者经常交织在一起形成双重人格。本文是产生各种原始本能冲动的地方,它常常被压抑在无意识深处,处在人格最底层。因此一个人出现在别人面前的形象就常常不是一个本来的‘我‘的形象,而是一个压抑了本我有着理解的自我,有时这种自我还带有不少超我的成分。”②《梅雨之夕》中的“我”的“本我”通过他变化多端的心理活动与真实欲望呈现出来,从苏州少女的视角来看,这名男子的举措是小心翼翼而不失礼貌的,这就是“我”在社会道德下“自我”与“超我”交织所呈现的表现。
尽管作者对“我”的心理与爱欲用赤裸的笔触展现出来,尽管“我”从一开始遇见这美丽少女便忘记自己有妻的事实,可理性与道德秩序缠绕干扰着“我”——“我”见店里有犹豫的女子便幻想这是妻子,“我”害怕此番同行被认识的人撞见、假想路人可疑的神色,甚至在少女身上闻到了“我妻”所有的香味,想到“我妻”的信。这些都是“自我”与“超我”在其意识中的体现与化身。在小说结尾妻开口问“我”何故归家这样迟,是规训的话语,也是这场梦想终将结束的声音,且“我”编造了谎话,暗示着欲望深陷于道德命题中,“本我”最终如往日被压抑。
在这篇小说中“雨”和“伞”又是两个重要的隐喻。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工业化、国际化…….无愧于真正意义上的都市。雨在文中笼罩着这个都市,也笼罩了整个文本,它或是都市意识形态的表征,又或是人性欲望的隐喻。这雨召唤着“我”,吸引着“我”。“我”作为都市主体的个体协同“伞”构成同一性关系,“伞”一方面保护着“我”免受着梅雨的侵袭,一方面扮演着“我”与苏州少女交往活动的契机,这“伞”是表面的理性秩序,是掩盖真实欲望的保护罩(“我”通过伞躲避可疑眼光等)。但“伞”作为与“雨”这感性存在对抗的理性意识,使得“我”对少女的幻想不断遭到破坏且流变,“伞”将“我”从初恋对象、日本画的少女中拔出来,最终认清她只是个不相干的少女,欲望在这一过程中被压抑。
从作者的角度看,其作品中情与理冲突是具有文化渊源的。施蛰存先生本人的家庭环境对她的文学之路影响很大,他的父亲是清末的秀才,施蛰存对中国古典文化兴趣浓厚,其作品虽然是基于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笔下的人物却多少带有传统伦理色彩。如在小说《春阳》中,婵阿姨渴望着与陌生男子面对面吃饭,却无法冲破内心传统观念带来的阻力,只能在心中幻想,其中隐约可见施先生笔下人物的共性。现代都市意识与传统伦理的冲突在作品的张弛中有意无意地被透露、被释放。该作品写于1933年3月,彼时中国历经了各种变革,新文化运动刚过去十余年,这是一个观念动荡巨变的时代,施蛰存先生的作品正是这苍茫时代下的一个折射。
《梅雨之夕》全篇又离不开对美的追求,美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文中美是这初夏不尽的梅雨,是少女瘦削而不露骨的得体,是“我”翩翩浮想中的《夜雨宫诣美人图》……苏州少女相对于作为一个真正存在的实体,更像是美的化身,是主人公在碌碌生活中向往的未来和诗意,他的欣赏甚至超越了性欲,戏剧化的开端使这个向往美好的已婚青年为这场相遇不断加分。审美心理学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沉醉于他的审美对象时,很容易勾起他深层意识里的情感经验,尤其是少年时代的情感经验。反过来,这种情感经验的复活又加深了他对审美对象的情思。③所以我们看到少女在主人公的遐想中变成了那年少时的初恋对象,而偶然悲哀的时候她是一个妇人、甚至是一个年轻的母亲,这般的变化我们也不难看出主人公的审美偏好与习惯,初恋的少女是不折不扣的美丽。苏州少女是美的,是文人的维纳斯,也是作者审美偏好的表现。
《梅雨之夕》用细腻的笔触将一场平淡相遇写成翻涌的博弈,是都市秩序下人性的丝丝显露,是本我的呼喊,是不同理念的冲撞。这是一场梅雨带来的旖旎,梦被雨带来,又跟着雨离去。最终“我”还是为证实这谎话,夜饭吃的很少。现实在空气中无情发笑。
注 释
①施蛰存.施蛰存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②[美]赫伯特·马尔库塞.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8
③罗田.一幅清图淡雅的心画——施蛰存《梅雨之夕》心态扫描.《名作欣赏》.1986(3)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