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看唐德宗时期的佛教与政治
2019-03-29孙少飞
孙少飞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承接前代国政之弊,德宗继位伊始,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时局危难。在此背景下,德宗锐意革新,而对于重要社会力量之佛教则偏重于抑制打压的态度。在臣僚的建议下,德宗欣然倾向于沙汰佛教僧团规模的策略主张。然而,德宗所面对的政治时局错综复杂,尤其是东方藩镇叛乱以后,其对佛教的态度有所缓和,乃至进一步趋向于崇信支持。此方面在他支持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以及对《理趣经》《华严经》的信奉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由德宗态度转变而表现出来的佛教与政治之关系,引起了我们对此问题的探讨之兴趣。
一、政治的受挫:唐德宗对释教态度的转变
李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经受到削弱,政治上的弊端逐渐地显现。外部有吐蕃回鹘之患,内部则有藩镇割据之乱。开元、天宝年间,唐王朝在西北之兵力最为雄厚。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朔方、河西、陇右而外,安西、北庭,亦置节度;又有受降城、单于都护庭,为之藩卫。”[1]206“用能北扞回纥,西制吐蕃。及安、史难作,尽征河、陇、朔方之兵,入靖国难,而形势一变矣。”[1]206安史之乱以后的代宗与德宗时期,边境外患日渐凸显,尤其以吐蕃的不断入寇最为严重。吐蕃自为郭子仪与回纥所败,唐蕃之间曾有四次会盟,“然吐蕃视如无物,终代、德两朝,几于无岁不寇”[2]。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自禄山之乱,河右暨西平、武都、合川、怀道等郡,皆没于吐蕃。宝应元年,又陷秦、渭、洮、临。广德元年,复陷河、兰、岷、廓。贞元三年,陷安西、北廷,陇右州县尽矣。”[3]由此可见,吐蕃入寇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其势力对安史之乱以后代宗、德宗朝产生着严重威胁。
德宗时期的政治形势,除了吐蕃回纥外患之外,尚有日益严重的藩镇割据,尤其是河朔三镇以及淄青诸州割据。此诸处的割据始自代宗时期,当时唐王朝军事力量还不十分雄厚,无法根除安史之乱的残余势力,遂让安史降将“分帅河北,自为党援”[4]7141,将河北等地分为成德、魏博、幽州卢龙三镇,由田成嗣、张忠志、李怀仙等安史降将担任节度使。此外还有昭义、淄青、泽璐等藩镇他们不仅“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4]7175,而且相互之间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4]7175,以土地传其子孙。唐德宗继位伊始,试图起衰振敝,矫正肃宗、代宗以来的对于藩镇的姑息政策,“然以是时藩镇之力太强,朝廷兵力、财力皆不足,而德宗锐意讨伐,知进而不知退,遂致能发而不能收也”[1]242。德宗的冒进之举造成了山东、河北藩镇之变,田悦、李纳、朱滔、朱泚、李希烈等相继为乱。德宗派去的前往关东作战的泾原士兵,临时倒戈,攻破长安城。在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的策动下,群起拥立朱泚为主,这就是“泾师之变”。德宗仓惶逃离长安,北奔咸阳,直达奉天。此次兵变使李唐王朝濒于灭亡。此后,德宗再没有采取对藩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代宗、德宗时期,“几经丧乱,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藩镇也最为跋扈”[5]。由此可见,藩镇之祸对于李唐王朝的威胁,尤其是对德宗初期统治的威胁。
承前朝弊政,德宗继位伊始,即锐意于政治经济的革新。史书称其:“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6]400例如,唐德宗在边患方面着力于同回鹘结盟以对抗吐蕃,军事方面发起针对东方藩镇叛乱的平定,经济方面实施“两税法”的财政改革。而前朝崇佛佞佛的政策,尤其是唐代寺院经济的膨胀发展,自然也成为唐德宗政治革新举措的目标对象。
唐德宗之父、代宗李豫崇佛靡甚,其“初喜祠祀,未重释氏,而宰臣元载、杜鸿渐、王缙皆归向佛僧(王缙造宝应寺)。代宗尝问福业报应事,元载因而启奏,由是信之过甚”[7]247。代宗对不空三藏尤其崇信,于永泰元年(765年)“制授大师特进试鸿胪卿,号大广智三藏”[8]292,并敕命其以密教之法广行护国之术。于兴善寺立道场,“又赐二七日入道场,大众斋粮。近侍大臣、诸禁军使,勅令入灌顶道场。道俗之流,别有五千余众”[8]292。永泰元年(765年)三月二十八日,代宗敕命兴善寺建立方等戒坛,其所须一切财物等皆由官方供给。同年四月,敕京城僧尼临坛大德各置十人,永为常式[7]250。代宗曾作《戒坛敕》,曰:“戒分律仪,释门宏范。用申奖导,俾广胜因。允在严持,烦于申谢。”[9]535大历八年(773年),代宗敕令天下童行策试经律论三科,给牒放度[10]377。代宗不仅从诏令敕命等制度上保证佛教戒律度僧的正常运作,还从国家财政赋税等方面对戒坛度僧提供优渥的支持。例如,不空三藏为五台山金阁等五寺度人抽僧所提及的,“寺别度二七人,兼诸州抽道行僧一七人,每寺相共满三七人为国行道,有阙续填”[11]835,不空所言及的“五寺,例免差遣其所度人”[11]835。法华寺亦同五寺之例。五台山五寺不仅可以每寺别度十四人,还可以从诸州抽调七人,并且对所度之僧人免除其赋税差遣等责任。在为东都荐福寺请抽名行律师七人,并请置戒坛院额时,不空三藏说:“每年为僧置立戒坛。”[11]841在此基础上,“抽名大德七人,四季为僧敷唱戒律”[11]841,并且“前件院抽僧及置额等,请有阙续填。其府县差科及一切僧事,并请放免不同诸寺”[11]841,此则明确指出对戒坛传戒度僧活动应免除府县差科以及其他僧事。
代宗时期的内道场盂兰盆会,更是花费靡常,恒为代宗朝之定式。代宗敕命百余名沙门在禁中陈列佛像经教,进行密宗念诵活动,此即为“内道场”[10]456。他还令掌管国家财政的度支部具廪供给内道场僧人,以致“供养甚贵,出入乘厩马,度支具廪给”[7]247。此外,代宗还在大历三年(768年)七月,“诏建盂兰盆会,设高祖下七庙神座,自太庙迎入内道场。具幡华鼓吹,迎行衢道。百僚迎拜。岁以为常”[10]377。由此可知,无论是代宗时期佛教戒坛度僧,还是内道场的佛事活动,其所花费靡常,皆紧密关涉于国家财政。
因此,唐德宗在其父去世的当年,即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即敕命“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观及度人”[6]321。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又诏令“罢出盂兰盆,不命僧为内道场”[6]326,这显示出德宗初期对佛教所持之抑制弹压的政治态度。此外,德宗企图对佛教教团的规模、财富与活动进行限制,因此,他在态度上倾向于提出类似主张的臣僚。例如,剑南东川观察史李叔明说:“以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粗加澄汰。其东川寺观,请定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人,上观留道士十四人。降杀以七。皆精选有道行者,余悉令返。初兰若道场,无名者皆废。”[6]3579德宗认为,其奏议可以作为处理全国佛教寺院的通例,而不惟局限于剑南地区。彭偃在奏文中说:“今出家者皆是无识劣之流,纵其戒行高洁,在于王者已无用矣。况是苟避征徭,于杀盗淫秽无所不犯者乎?”[6]3580他进而提出整治举措:“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臣伏请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臣窃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6]3581如同对待李叔明之奏议,德宗同样十分赞赏并且支持彭偃的奏议。
然而,由于河朔藩镇长达五年的军事叛乱,并最终引发险致唐朝灭亡的“泾师之变”,唐德宗不得不检讨自己在政治上的冒进举动[注]唐德宗在兴元元年(784年)于奉天行宫中颁布的“罪己诏”中说:“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详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390页。。在此背景下,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德宗为何没有最终接受李叔明以及彭偃整顿沙汰佛教的方案,而是接受了比他们更加谨慎的臣僚们的建议。《旧唐书》记载:“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圣奉之,不宜顿扰,宜去其太甚。”[6]3581针对佛教的举措,不应该像整顿藩镇、财税改革一样的激进或“顿扰”,而应稳健而理性地“去其太甚”的弊病。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敕命“亡僧尼资财旧系寺中,检收送终之余分及一众。比来因事官收,并缘扰害。今并停纳,仰三纲通知,一依律文分财法”[10]379。依照佛教戒律处置亡僧遗物,而不准官府肆意没收。
二、权力的参与:唐德宗对《理趣经》翻译的支持
“泾师之变”以后,德宗对佛教采取“不宜顿扰”的态度,放弃了想要削弱佛教的打算。尤其是贞元二年(786年)叛将李希烈之死,朝廷与藩镇的战争才算结束,“德宗对于佛教这一国家重要势力也变得越来越妥协,并逐渐开始虔信与资助佛教”[12]102。除了阻止地方官府检收亡僧尼的财产之外,在贞元二年(786年),德宗在京师章敬寺从道澄律师受菩萨戒,表明其正式皈依佛法。五月,诏道澄律师入宫,为妃嫔、內侍授皈依戒。同年,德宗还敕命诸寺宣讲佛教经典,并重新恢复建中元年(780年)禁止的盂兰盆法会。贞元四年(788年),京师地震三十六番,德宗诏命迎请岐州无忧王寺佛指骨舍利入内庭供养[注]参见熙仲:《历朝释氏资鉴》卷第七,《卍续藏》第76册,第200页。又据《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贞元四年(788年)正月,京师地震十八次;八月,京师地震一次。这与此处所说略有不同。。直至贞元六年(790年)正月,德宗才下诏送还本寺。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唐德宗对佛教态度的缓和转变,究竟是为纷乱时局所迫使的妥协,还是积极主动地有意迎合?
首先,我们需要通过对印度僧人般若三藏及其翻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以下简称《理趣经》)过程的考察,探讨德宗对佛教态度的转向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佛教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般若三藏,北天竺迦毕试国人,姓乔答摩氏,颖悟天纵,幼年出家修道。随调伏军讽诵四部《阿含经》十万偈以及《阿毗达磨》两万余偈。又至迦湿蜜国,讽诵《萨婆多》《俱舍论》《大婆沙》等小乘要义。又至中天竺那烂陀寺,依从智护、进友、智友等三大论师,受学《唯识》《瑜伽》《中边》等大乘要义,并及《声明》《因明》《医明》《工律论》等世间学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般若游学南天竺,“时闻南天尚持明藏,遂便往诣,谘禀未闻。有灌顶师,厥名法称。受瑜伽教,入曼荼罗。三密护身,五部契印。如是承奉,住经一年,讽满三千五百余偈”[13]891。此后,般若听闻支那国有文殊菩萨道场,遂决定前往中土朝圣并传播佛法。“建中二年,垂至广府。风吹舶破,平没数船。始从五更,洎于日出。或漂或溺,赖遇顺风。所持资财,梵夹经论。遭此厄难,不知所之。及至海壖,已在岸上。于白沙内,大竹筒中。宛若有神,叹未曾有,知《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与大唐国中根缘熟矣。”[13]891般若此行可谓路途多舛,其所持梵文佛典几乎在这次海难中丧失殆尽,惟有《理趣经》完整保存,似乎暗示着该佛典与东土大唐有甚深的因缘关系。
般若于贞元二年(786年)至长安后,在其表亲神策正将罗好心的支持下,初次翻译《理趣经》。由于般若未解唐言、不闲胡语,而参与翻译的景教僧人景净亦未明释教、不识梵文,遂使此次七卷本的汉译未达圆满完善。在上表皇帝请求流通时,德宗“察其所译,理昧词疎。且夫释氏伽蓝,大秦僧寺,居止既别,行法全乖”[13]891。出于教法区分、正邪异类的考虑,德宗于贞元四年(788年)四月十九日,敕命西街功德使王希迁[注]德宗对佛教态度的转变,亦受到其所重用的宦官内侍的影响,如王希迁、窦文场、霍仙鸣等人,他们都是随从德宗奉天靖难的功臣,并且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精选有道行僧,在西明寺组织成立译经院,重新翻译《理趣经》。王希迁奉命所选的译经僧人,皆源于京城附近诸大寺院。译场人员职能的分配:般若宣释梵本,光宅寺利言译梵语,西明寺圆照笔受,资圣寺道液、西明寺良秀、庄严寺圆照并润文,慈恩寺应真、醴泉寺超悟、光宅寺道岸、西明寺辩空并同证义。开题之时,德宗敕命王希迁、王孟涉、马有麟等送梵本经至西明寺翻译,并送钱物香茶等供养译经院。翻译期间,德宗不断遣使慰问译经大德,并不断赏赉供物。同年十月中旬,《理趣经》翻译完毕(共十卷十品),十一月十五日缮写复终,二十八日录表进上。良秀等僧人上表,请求德宗为新经制作序文,并请附入《开元目录》。其序文有言:“六波罗蜜经者,众法之津梁,度门之圆极也……聊因暇日,三复斯经,虽法海甚深,而波流不让,举其梗概,照悟将来。”[14]德宗三复斯经,足见他对《理趣经》的浓厚兴趣。
此经翻译后的贞元五年(789年),德宗敕命良秀、超悟、道岸及智通等为新译《理趣经》修撰疏义。据《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中的记载,贞元四年(78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良秀等奉诏修撰《理趣经疏》十卷,至次年七月一日功毕,参与此事者尚有谈筵、道弘等人。同时,良秀上表请求允许谈筵于当寺赞演此经,并将此新经流布中外。第二部《理趣经疏》(十卷)是由醴泉寺沙门超悟等奉诏完成,始于贞元五年(789年)四月十五日,终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德宗赞其所撰新经疏:“载省科条,兼详体要。发挥既备,嘉叹良深。”[15]763同时,超悟上表请求设置新经院额,“并请抽僧,讲习住持,有阙续填,望为恒式”[15]763。德宗允许了他的请求,赐名醴泉寺本住院为“六波罗蜜经院”,并抽调有义行僧人七人,常令讲习《理趣经》。超悟等迎御赐院额之时,仪式场面宏大,“鼓声才发,陈列威仪,严饰宝车,幡花法事,彩车音乐,诣银台门”[15]763。此后,教坊使、内常侍李嘉兴又奉命“箫韶内教,陈六乐以导前;法事威仪,继八音而列次”[15]763。绕城巡礼之际,“万姓瞻暏,五众争驰。车马骈阗,观斯胜美。两两相谓,庆此嘉祥。咸言善哉,我皇至圣。钦崇佛教,雅尚释门。去岁翻经,今年制疏。特赐名额,垂范千龄。劫石有穷,斯迹无尽”[15]763。此足见德宗对般若等翻经、释经以及讲经的重视与支持。第三部《理趣经疏》(二十卷)是由章敬寺智通以及道岸等人奉敕修撰,始于贞元五年(789年)四月十五日,终于同年九月八日。智通等不仅撰述有经疏二十卷,还附有《理趣经疏义例诀》《理趣经疏义目》等各一卷。和超悟等请赐院额、置院传经的事例一样,智通“因请准例,置院抽僧,永冀传灯,福资圣寿”[15]764。智通希望德宗能够依照前例,允许他们也能够以一寺一院充作“大乘理趣经院”,并请御赐院额,选择有道行的僧人同崇讲诵,并请有阙续填。
从德宗敕命般若三藏重翻《理趣经》开始,其在译场组织、人才选择、财物供养等方面,均进行了慷慨而虔诚的资助。此经翻译完毕后,他又敕命良秀等僧人撰作新经义疏三部,还应超悟等人的要求,设置专门宣讲此经的经院并御赐院额。对于译主般若,德宗更是赏赉有加、崇信异常。贞元六年(790年),德宗“勅罽宾国进梵夹《六波罗蜜经》沙门般若,宜赐名般若三藏,仍赐紫衣”[13]891,这是译经僧人的莫大殊荣。同年,般若三藏又奉命出使天竺,并携回佛像及密教典籍。贞元八年(792年),般若三藏归国,并在德宗护持下继续从事译经活动。我们的追问是,《理趣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经典,以至于德宗对此经之传译、注释以及宣讲进行了如此多样的投入?
《理趣经》的梵本是由般若三藏携来中国,其经题中的“理趣”,即“实相”之义,“实相”即一切法的真如理体,一切法的究竟真实相。因此,一切法的究竟真理之意趣,即谓之“理趣”。此理趣依般若为总依,依大乘理趣而成六波罗蜜多行。波罗蜜多义即到彼岸,理趣则为彼岸之实相。通达彼岸之波罗蜜多行有六种,故称之为六波罗蜜多。六波罗蜜多即是实相,实相即是六波罗蜜多[16]10。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即乘此大乘真如实相之理,进修布施、持戒、忍辱等六波罗蜜多行。此经汉译本有十品。第一品乃十品之根本,初发意菩萨不知由何而入佛法之门,弥勒菩萨代为发问,使初发意菩萨能得入其门,趣向圆满清净的功德;以因地心契果地觉,于世间法建立出世间法,为救世间故有三宝,亦依世间显现三宝。第二陀罗尼护持国界品,总持一切三宝功德,得免灾难而享安宁,为佛果上无漏功德之救生方便,是回果向因义。“陀罗尼咒总持无漏功德,世人受持,即由三密加持而成清净世间。由心净而国土即净以及所行所为无不清净,是为以出世法护持世间。”[16]64第三发菩提心品与第四不退转品,是从因向果的阶段而言,初发意菩萨若要永不退堕,必须发大悲心、精进心以及三种报恩心,如此才能保证菩提心的坚牢永固而不退堕。第五品至第十品,分别是六度行品。菩萨要想圆满菩萨行,就必须要依布施、持戒、忍辱等六波罗蜜多而行,如此才能够达于大乘理趣之彼岸,圆满成就无上佛果菩提。
太虚大师曾指出此经能显四种殊胜:其一,发启殊胜,除第二品之外,皆由一生补处之弥勒菩萨向佛发问;其二,密坛殊胜,密坛即密宗之曼荼罗,“此经以释迦为本尊,即是毗卢遮那遍法界身,一法即一切法,一切法即一法,法法互融无有隔碍,本尊与行人之三业交加相应,则其行愿必圆成也”[16]66;其三,净土殊胜,东方普贤如来净土无尽功德庄严,于诸净土为最胜;其四,次序殊胜,由皈依三宝、清净修行、发心趣向菩提以及进修六波罗蜜多行,开展出由凡夫而至成佛的次序[16]66-67。印顺长老指出,《理趣经》属于密教兴起以后,真常唯心论者从繁密的教学,进而转向精简持行的法门[17]。从本经中对一切佛教之判摄,亦可看出其本身具有的密教色彩。此经将佛教判摄为经律论三藏、般若波罗蜜多藏、秘密陀罗尼藏。传后期佛教之西藏,亦大多采取如此的分判[18]。此经于《皈依三宝品》中将一切佛法摄为五分,尤其强调赞叹秘密陀罗尼藏[注]在《皈依三宝品》中,经文将佛法摄为五分,即素呾缆、毗奈耶、阿毗达磨、般若波罗蜜多、陀罗尼门。将此五法藏分别譬喻为乳、酪、生酥、熟酥及妙醍醐,认为“总持门者,契经等中最为第一,能除重罪,令诸众生解脱生死,速证涅槃安乐法身”。详见般若译《理趣经》卷第一,《大正藏》第8册,第868页。。因此,《理趣经》与注重总持陀罗尼之密教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们知道,般若三藏曾闻南天竺尚持明藏,遂便往诣南天竺,谘禀其所未闻。乌荼国王寺有灌顶师法称,又名达磨耶舍、达磨枳栗多。般若三藏从其受学瑜伽教,入曼陀罗,传三密护身,五部契印。在八世纪,南天竺乌荼国已经成为密教金刚顶派的发展中心之一,“惟印度密教源流,素有中天、南天两派,前者乃大日经宗,后者则成金刚顶法”[19]233。由此可知,般若从法称受学的应当即是金刚顶派密法。从其翻译的经典来看,般若三藏与密教金刚顶派也有着密切关联。根据大村西崖的研究,般若译《本生心地观经》更是南天金刚顶法密教所产,并指出南天密教夙发萌芽于此经,至三十卷《羂索经》而发达[19]309。在研究了般若译《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以后,大村西崖指出:“其金刚城曼荼罗,即殆全同于金刚界。亦是《金刚顶经》出后之密经,与《六波罗蜜经》同味也,皆属南天系统。以故,此经虽有《大悲胎藏出生品》,毫不见带《大日经》之意,又无所存胎藏曼陀罗之趣,是所应尔也耳。”[19]464由此可知,般若携来并翻译的《理趣经》,必是南天金刚顶密法系统下所传出的密教经典。此外,斯坦利·威斯坦因认为,《理趣经》是一部与安邦定国有关的波罗蜜多类大乘经典,是关涉于统治者特别感兴趣的主题[12]105。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德宗对《理趣经》的高度关注,应该是注重于其中的密教金刚顶法之护国思想与宗教仪轨的实践操作[注]般若译《理趣经》第二品为“陀罗尼护持国界品”,在此品中,释迦佛宣说了东方不眴世界的状况之后,又因曼殊室利菩萨的问题而简述受持此甚深经典的功德利益,接着曼殊室利、普贤、观世音诸大菩萨,及诸天王纷纷各说陀罗尼以守护国界及受持此经典的人,并为他们涤除一切障难。。
三、皇帝的信仰:乌荼所献《华严经》与密教佛王信仰
唐德宗对《理趣经》护国功能的重视,极有可能是受其父代宗对《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推崇有关,该经以其完备的护国内容与仪轨,最为突出地体现了唐代密教体系中的护国精神,尤其能说明陀罗尼对皇权的护持之功。然而,德宗转变对待佛教的态度,在国家权力上予以大力支持,难道仅仅只是停留于借其护国助国的层面吗?通过对般若译四十卷《华严经》的考察,我们尝试探究唐德宗在佛教与政治关系层面态度转向的内在动机。
唐译四十卷《华严经》的梵本是由乌荼国王亲手书写之后,遣使奉献于大唐德宗皇帝的。我们知道,八世纪的南天竺乌荼国已经是密教金刚顶派的发展中心之一,大村西崖在谈到南天密教时指出:“抑金刚顶法者,盖成于南天乌荼、摩赖耶、师子等国,想宝觉阿阇梨成其先声,与《大日经》成于中天摩揭陀国那烂陀寺不同,其事数两相所以大异于胎藏法,实在乎兹。”[12]309金刚顶法是迥异于中天竺所传之胎藏密法的另一种印度密教教法,与南天竺乌荼等地区有着重要的关联。就两派的典籍来说,胎藏密法之圣典《大日经》是在中印度那烂陀寺或西北印度编成的,而金刚顶法之圣典《金刚顶经》是在南印度编成的[20]。古正美指出,南天竺密教金刚顶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不空绢索观音佛王信仰[21]184,该信仰是“佛教转轮王传统”在大乘密教化以后发展出来的一种佛教治国意识形态模式。作为南天竺金刚顶密法策源地之摩赖耶国,其国境内就是不空绢素观音的圣山“布呾落迦山”。不空绢索观音与此圣山的关联,在汉译不空绢索观音经典中频繁出现[注]新近关于唐初及中唐密典翻译与不空绢索观音信仰的研究,可参看朱丽霞《唐初密教流布的特征》,载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43-46页。她指出,不空绢索观音信仰的密教典籍源流,在唐前期流行的盛况以及与皇权和国家的关系。。比如,中国最早翻译的不空绢索经典《不空绢索咒经》说:“一时,婆伽婆在逋多罗山顶观音宫殿所居之处。”[22]玄奘同本异译《不空绢索神咒心经》说:“一时,薄伽梵在布怛洛迦山观自在宫殿。”[23]菩提流志译《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说:“若苾刍苾刍尼国王大臣一切人民。幸欲求见观世音菩萨补陀洛山宝宫殿中。”[24]因此,同为密法金刚顶之发源地的乌荼国,自然也成为了金刚顶密教不空绢索观音信仰的策源地,而其特色就是不空绢索观音佛王信仰。密教佛王信仰与早期佛教转轮王传统的最大区别处就是,“在密教的信仰里,因转轮王与佛或菩萨同身之故,以佛教治国的转轮王便能以佛或菩萨的姿态或形象统治天下”[25]。这种转轮王即佛,或转轮王即菩萨的信仰,就是密教“佛王”信仰的特色。对于乌荼地区的不空绢索观音佛王信仰而言,它是将天王观音化或将摩醯首罗密教观音化,其表现之一就是在不空绢索观音的造像法上采取摩醯首罗之造像法,只在其造像顶上画作无量寿佛以示区分。因此,不空绢索观音佛王信仰的传统,就是以不空绢索观音取代摩醯首罗的天王地位,成为观音佛王传统中的“佛王”,也就是说不空绢索即是王,或王即是不空绢索观音。对于金刚顶密教在南天竺成立不空绢索观音佛王信仰传统的意义,古正美论述到:“因为不空绢索观音佛王传统的出现,不但使金刚顶的信仰具有实际的使用价值,能作为帝王治国的意识形态,而且也使金刚顶的发展,因为帝王的使用而广博至印度以外的亚洲各地。”[21]188因此,我们可以说,金刚顶密教不空绢索观音佛王的信仰,自其形成发展、传播盛行以来,就带着浓厚的佛教治国意识形态而被各信仰地域所接受。
南天竺乌荼国与金刚顶派观音佛王传统的密切关系,还表现于乌荼国所集结出的乌荼版《华严经》。此经实际仅相当于唐译八十卷本之第九会《入法界品》,根据印顺长老考证,该品与南天乌荼实在有甚深的关系[注]具体可参看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49页;《龙树龙宫取经考》,收录于《佛教史地考论》,《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1-147页。。我们认为不仅如此,乌荼国所集出的《华严经》是与南天金刚顶密法不空绢索观音佛王传统有关的,是在观音佛王传统的影响下于乌荼国所集结而成的。古正美认为:“传入南天的《入法界品》,因南天密教金刚顶在南天的兴起及发展,便被‘金刚顶化’,而出现了金刚顶版的《入法界品》。‘金刚顶化’的《入法界品》,即是乌荼版的《入法界品》。”[21]211这只要关注此经三种译本所描述的观自在菩萨及其住处即可明白。
与前两种《华严经·入法界品》译本相比,乌荼版在经文内容方面有所不同。晋译之菩萨名为“观世音”,乌荼版作“观自在”;晋译之观世音菩萨住处在光明山之山西阿,乌荼版之观自在菩萨住处在补怛洛迦山西面岩谷中;晋译之观世音菩萨结跏趺坐于金刚宝座上,乌荼版之观自在菩萨结跏趺坐于清净金刚宝叶石上。此“补怛洛迦山”正是不空绢索经典中频繁出现的观自在菩萨住处,而此住处恰在南天摩赖耶国。除所居地点及坐处不同外,相较于晋唐两译,乌荼版在善财童子参访观自在菩萨处还补入了两段用偈颂体写成的经文。第一段偈颂,基本上与《法华经·普门品》所记菩萨善权方便救度世间苦难的偈颂大致相同。第二段偈颂,除描写菩萨大悲救世的内容外,还有大段描绘观自在菩萨形象的经文,此段经文与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慧智所译《赞观世音菩萨颂》的相应经文基本相同,两者都描绘了观自在菩萨顶上真金妙宝冠、伊尼鹿彩作下群、徒以白龙为璎珞、右手执持金莲花等造像特征。根据两者造像特征中都有伊尼鹿彩覆其肩的要素,古正美指出“乌荼版《入法界品》的观音形象,因此很明显地是由南天金刚顶发展出来的不空绢索观音的形象”[21]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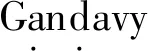
因此,乌荼版《华严经·入法界品》是深受南天密教金刚顶观音佛王信仰而发展的经典,其所含蕴的《华严经》佛王传统,不仅体现在观自在菩萨造像等经文内容上,还体现在本经主尊毗卢遮那佛以及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等大菩萨身上,他们的过去身均被视为佛教转轮王身,这说明他们已经在《入法界品》中被“佛王化”,也就是佛即是王、王即是佛,转轮王能够以诸佛、菩萨的面貌面世或统治其子民。比如,献经的乌荼国王,《贞元录》中就赞叹其为“法王御历,不贵异货珠珍,信重大乘以佛法僧而为上宝”[13]894。国王在《献经愿文》中说:“伏愿书此大乘经典进奉功德。慈氏如来成佛之时。龙花会中早得奉觐。大圣天王获宿命智。瞻见便识同受佛记。”[13]894这也说明乌荼国王崇信大乘佛教,并以“法王”或“弥勒佛王”的姿态统治着他的国家。
总之,由于南天密教金刚顶不空绢索观音佛王传统或《华严经·入法界品》佛王传统的出现,使得金刚顶的信仰具有了实际的使用价值,能够作为帝王以佛教治国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根据古正美的研究,在武则天以后,唐代帝王,如中宗、代宗等,均有与此佛王传统相接触,有明显使用金刚顶佛王文化治国的现象,此佛王传统,几度成为唐代国家信仰或国教[注]参见古正美《从南天乌荼王进献的〈华严经〉说起——南天及南海的〈华严经〉佛王传统与密教观音佛王传统》,载于《佛学研究中心学报》2000年第5期,第214页。另外,有关武则天实施佛王传统治世的研究,请参考古正美《武则天的〈华严经〉佛王传统及佛王形象》,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年版;有关唐中宗实施佛王传统治世的研究,请参考古正美《龙门擂鼓台三洞的开凿性质与定年》,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一千五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82页。。在此背景下,当我们再去审视德宗奉佛态度的转变,尤其是其对具有浓厚南天密教金刚顶法特色之《理趣经》与《华严经》翻译的支持、对具有此系密法之传承的般若三藏的崇敬等,就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时局所迫使的不得已之妥协,或者只是对密教护国功能的一时热衷,而更应该视之为是德宗欲借助金刚顶佛王传统的治国意识形态,这一迥异于儒家治国意识形态的异域思想文化,为其重建李唐王朝中央政权之权威寻求宗教超越层面的合理支持。诚如德宗所明言:“虔奉丕图,保乂蒸庶。思建皇极以升大猷,遐想灵踪期于叶契。而舍城妙说,久祕梵文,徒怀泻瓶,未启遗夹。微言不昧,将或起予。”[9]590佛法微言所能够给予德宗启发的,或许就是“承法王之付嘱,满人心之志愿。持普贤之密印,行天子之正教。浃辰之际,朗慧日于八方。在于顷刻,注洪泽于万物”[13]887。以法王普贤之密意,而行国王天子之正教,即是法王,又是国王。唐德宗转向于佛教者,或许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