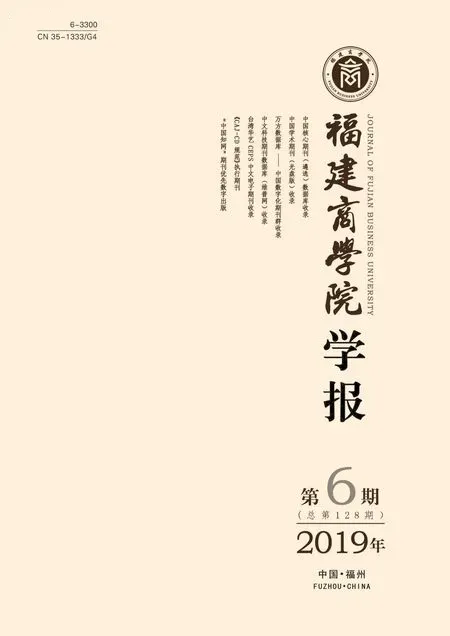明朝海禁政策与闽海士大夫的商贸思想
2019-03-26林春虹
林春虹
(福建商学院 a.通识教育学院;b.闽台与东南亚商贸历史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350012)
明朝海外贸易政策呈现出两大特色,一是推行朝贡贸易制度,二是制定空前的海禁政策。二者是相对应的,即为了排除官方朝贡贸易之外的其他贸易形式而制定严禁一切海外贸易的政策。“朝贡贸易”是明朝特许前来进贡的外国“贡舶”附带一定数量的商品,按一定贡期、贡道、贡船和人数,在贡道所出港口贸易,政府特设市舶司掌管其事。朝贡贸易是明朝前期唯一批准的合法对外贸易。明王沂曰:“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1]明初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三个沿海口岸设立市舶司作为掌管对外贸易的机构,宁波通日本,泉州(后移福州)通琉球,广州(后移高州电白县,最后移澳门)通占城、逞罗及之后的西洋诸国。市舶司制度虽沿袭唐、宋、元制度,但其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而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意义,是为了“通远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用以消衅隙也”[2]。这种象征意义上的贸易往来也因 “倭患起于市舶”之论而宣告失败,嘉靖时期明政府撤销三市舶司并实行海禁。终明一代,海禁政策虽偶有松弛,但一直延续到明末,对明朝整个社会格局产生较大影响。
一、福建海上贸易的不可遏制
明朝在开国之初就定下禁海的政策方向,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明太祖担心“内地奸民”和海上敌对势力相勾结,对政权造成威胁。海上敌对势力的重要一支是张士诚和方国珍的余部,他们不仅控制了江、浙一带,还曾将割据范围扩大到安徽北部和山东西南部,尽管张士诚等人后来被击败,仍有不少残余势力逃亡到东南沿海一带。为杜绝海上势力与外邦相通,明太祖坚决实施海禁政策。实施海禁针对的重点对象之一是福建沿海贸易群体。“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故严禁之。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相交易者,悉治以罪。”[3]明太祖之后,福建沿海始终是朝廷关注的敏感地带。如明景泰帝“命刑部出榜禁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置造军器,驾海交通琉球国招引为寇”[4]。嘉靖时期,福建沿海居民利用朝贡贸易进行私贩活动,又多次牵引朝廷之议。《明世宗实录》记曰:御史王以旗议福建滨海居民每因夷人进贡,交通诱引,贻患地方,宜严定律例;八月甲辰,初,浙江巡按御史潘仿言:“漳、泉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请一切捕治。”事下——兵部议:“行浙、福二省巡按官查海舡,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官吏军知而故纵者,俱谪发烟瘴。” 嘉靖十二年九月辛亥,兵部言:“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阪,因而寇劫;屡奉明旨严禁。第所司玩愒,日久法弛;往往肆行如故,海警时闻。请申其禁!”上曰:“兵部其亟檄浙、福、两广各官督共防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5]卷38,54,154这些证明明朝福建海外贸易已呈现常态化,福建沿海居民私造大船已成规模,是朝廷海禁政策实施的重点对象。
福建海上贸易早在元代已呈现繁荣景象,但明朝海禁政策的实施使闽海地区面临新的历史境遇。种种表象背后隐藏着闽地沿海地区“以海为生”的苦衷。《八闽通志》《泉州府志》《漳州府志》等指出福建背山靠海,可耕之地较少,因而当地人十分依赖航海商渔、对外贸易。在福建巡抚任上的徐学聚、许孚远、金学曾、陈子贞、南居益等人也一而再、再而三上奏朝廷,述说闽南滨海居民靠海为生的现实处境,认为海禁是倭寇祸乱的根源。戴冲霄进一步指出,福建边海之地,贫民倚海为生,以捕鱼贩盐为生存之业,但其利甚微,只有愚弱之人才会从事捕鱼之业,而那些“奸巧强梁者,自上番舶以取外国之利,利重十倍故耳。今既不许通番,复并鱼盐之生理而欲绝之,此辈肯坐而待毙乎!故愈禁愈乱”。戴冲霄又揭露了闽商不走陆路经商而乐于海上贸易的客观原因,“闽中事体与浙直不同,惟在抚之得宜而已。……漳、泉人运货至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脚价银不过三分,陆行者价增二十倍,觅利甚难。其地所产鱼盐,比浙又贱。盖肩挑度岭,无从发卖故也。故漳、泉强梁狡猾之徒,货赀通番,愈遏愈炽,不可胜防,不可胜杀”[6]9118-9119。在明朝文人眼中从事海上贸易的是“狡猾之徒”,但他们都清醒意识到海禁政策与闽海贸易经济的不可遏制,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事实上,嘉靖时期的倭寇大动乱与海禁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樊树志先生等学者曾考证,“所谓倭寇,大多是中国人”,“真倭少而假倭多”,并指出闽人居多,“海寇大约艘凡二百人,其诸酋长及随从,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间亦有徽人,而闽所当者什之六七”[7]。唐顺之认为,“倭患始于福建,福建者乱之根也”,“今也海禁太严,见船在海,有兵器火器者,不问是否番货即捕治之,米谷鱼盐之类一切严禁,虽似犯法,论其情,海船往来,非带兵器火器,无以防海寇之劫夺,不有可原者乎!明乎此则民情得伸,而乱源可塞矣”[6]9125-9126。
可见,海贼并非真倭,有的是带着武器以自卫的沿海渔民,有的是长年在闽浙沿海从事贸易的“剧贼”,而且以闽人占多数。唐枢认为,嘉靖时期海贼的泛滥与海禁政策的严控有密切关联,即嘉靖六七年后,官员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无法谋生,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更严,寇贼也更多。正因为倭寇战争的困扰,明朝曾多次议及开放海禁事宜。在胡宗宪招抚王直期间,胡宗宪曾与唐枢探讨是否赞同王直“开港互市”的请求,虽然唐枢倾向于开港互市,但当时在朝士大夫多数反对招抚及开港,迫于舆论压力朝廷最终下令处死王直。王直于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被胡宗宪诱降下狱,被斩首时间为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之死导致海上倭寇无所皈依,愈加愤恨,遂向南转战,在福建等地发动了更加惨烈的祸乱。史书对此有明确记录,在当时文人集子中也有沉痛记载:嘉靖三十七年及次年,泉州城外数千家被焚,官府、传舍皆为灰烬[8]410;嘉靖三十七年,泉州士绅自发捐赀,请求知府熊汝达建设城墙以抵抗倭寇,熊汝达亲自指挥,晋江知县卢仲佃监督建城之事。(筑城)功未就而寇至。生民之糜烂,庐舍之灰烬者,不堪举目[8]405;嘉靖岁戊午(嘉靖三十七年),倭大寇吾闽,陷福清,长驱至惠安城下,兴、泉振动。……又明年(嘉靖三十九年)夏四月朔,贼结巨艘从海道乘夜袭崇武,戍人不戒,贼入其郛蹂焉,千户钱储、百户王铁死之[9]。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倭寇势力才被消灭,闽地得以渐渐解除倭乱之苦。经历嘉靖倭乱后,朝廷不得不认真研究海禁开放问题,由此产生了在福建漳州海澄县特殊执行的“隆庆开海”政策。朝廷对海上贸易的不可遏制有所觉醒,但碍于明初祖制,只在福建一个小县城开口,这种象征性大于实用性的政策,为明朝后来的海上贸易发展路径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二、闽海私贩贸易集团与海禁政策的抗争
在海禁政策下,除了朝贡贸易之外,任何“互市”行为都是禁止的,即在入贡前提下才允许公对公互市,严禁任何私人贸易。“隆庆开海”的提出使明初以来延续两百年的海禁政策得以部分废弛,但仅以海澄一地作为示范,官方的严海禁立场始终没有根本转变,海禁政策与福建沿海商民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福建海商群体为了对抗官方海禁的制约,找到两种强有力路径,一部分依靠武力化身海盗,甚至诈为倭寇,成为倭寇战乱的祸害之一;另一部分依赖或越过官府,与乡绅土豪、贡使外商乃至官方权贵相勾联,进行秘密私贩活动,逐渐形成私贩贸易集团。私贩活动在明朝初始时期便已存在,虽施行海禁之令亦不能绝。成化之前,朝廷因下南洋活动制造了相对宽松的贸易环境,贸易群体也主要是普通商人,但嘉靖时期,海禁又趋严,贸易主导权便渐渐转到富豪手中。彼时闽南商民结党下海者日益增多,官商勾结、内外蒙骗现象猖獗,闽南豪门巨室亦参与其中,走私之风至嘉靖中期达到极致。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了闽南豪门大族在海禁趋严的情况下“通番”发家之径。豪门巨室与海上走私者互相勾结,从成化、弘治之际的小小享利,到嘉靖时期越发显出弊端来。在巨大利润的诱使下,泉州安海、漳州月港等闽南大镇,当地小民与番徒相勾结,私藏外来商品,为了不使事情败露,往往仰仗大姓宦族之家以得庇护。在豪门巨室的参与下,富家、贫人各取所需,桀骜者、弱小者互相帮扶,贫者不惜委身入赘富家以求得掩护,最终形成一个个私贩集团。因海上强弱相凌现象的产生,有的集团还备有武装以抵御外来侵犯,他们依附强者以为船头,或五十只,或一百只,成群分党,分泊各港。
私贩贸易集团的势力形成过程,实际上是闽海士商与海禁政策相抗衡的过程,正因为海禁政策的执行,才促成了私贩群体的产生。明代福建乃多贤之乡,闽籍朝廷重臣亦多,在福建任职的官员要依赖当地乡贤才能开展工作,因而对于地方乡贤或豪门也颇多迁就成全之举。在豪门势力的庇护下,诸如海防军官、提督市舶太监等甚至与私贩集团勾结,共享福利,若无参与的,也大多不敢过问。明英宗之后,朝廷市舶法令形同虚设,沿海地区的官兵对海上私商贸易不闻不问。但严于执法的官方代表并非没有,嘉靖时期的朱纨是一个典型。朱纨于嘉靖二十六年任提督闽浙海防军务,对闽南一带士商联合的贸易团伙现象深有体会,曾上奏曰:“贼船、番船则兵利甲坚,乘虚驭风,如拥铁船而来;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其不攻劫水寨、卫所、巡司者亦幸矣。官军窜首不暇,奸狡者因而交通媒利,亦势也”。其任职期间严禁乡官的渡船,对林希元等地方官绅十分不满,认为林希元因仕途不遇,赋闲在乡,不惜士大夫名誉,打着林府的招牌,用自己的才学与势力要挟本地官员,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法之上,公然与外番私通,以此成为巨富。“此等乡官乃一方之蠹、多贤之玷;漳、泉地方,本盗贼之渊薮,而乡官渡船又盗贼之羽翼……不禁乡官之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也”[10]。
朱纨的秉公执法给闽海私贩势力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权贵士绅的反击下,朱纨势单力薄,竟以自杀告终。史学家王世贞认为,闽海贵人与朝中大臣谋,定要破坏朱纨的行动,导致朱纨不断上章廷辨,其激烈言语引起大学士的不满。朱纨的自杀是海禁政策在闽海一带受阻的一大信号,甚至导致朝中大臣不敢议论海禁。闽海豪门通向私贩集团的行径越来越肆无忌惮,闽海子民迁居日本、南洋的人数越来越多。朝廷施行海禁却难以真正贯彻,使得闽海私贩集团获得更大利润。如明末郑芝龙乘米禁之机而坐收渔利:“米粟未禁之先,芝龙船仅百只,即禁之后,遂至千艘;未禁之先,仅有芝龙数贼,既禁之后,逐如林姐哥、梅宇六七种。绝贼饷道而贼益多者,何也?我厉禁而漳、泉益饥,益饥则益生贼;我厉禁而芝龙济贫之说益足以收人心,故从贼益众也”[11]2157-2158。
为了对付官府追捕、抵御强盗,闽南弱势海商群体不得不依附于“雄强者”,这些所谓的“雄强者”在很大程度上又带有“海盗”身份,他们聚集成团,控制着海上贸易权。嘉靖时期一些倭寇首领,如闽海李光头、许二、谢和、王靖溪、洪迪珍、吴平等,其实就是私贩贸易集团的首领。在嘉靖抗倭战争的打击下,海盗集团被严重打击,但海上强权者并未消失,随着国际贸易尤其是东南亚贸易的发展,一些拥有雄厚财力与武力的海上贸易霸主相继出现,郑氏集团就是从中脱颖而出的东亚海上第一强。明朝政府既要应付华人海商集团,又要抵制西洋来的海商集团,其军事力量无法与海商集团抗衡。1628年夏,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福建有识之士何乔远的努力下,明朝政府采用了招安郑氏集团的策略,封郑芝龙为海上游击,利用其势力清剿其他海商集团。郑氏集团由此具有了合法身份,并得以不断扩大势力,是海禁政策与私贩贸易之抗衡的最大受益者。
三、闽海士大夫的商贸思想
由于海禁政策与福建地区之间的复杂关系,闽海士大夫在海禁及海上贸易问题上有了更多探讨与思考。
首先在海禁问题上,闽海士大夫大多数认为有着特殊地理环境的闽海地区不宜严海禁,这在明后期历任福建巡抚、福建官员及闽籍士人之言论中有大量记载。在海禁政策上较早开悟的福建巡抚是谭纶。谭纶于嘉靖四十二年至嘉靖四十三年(1563-1564年)任福建巡抚,其时正是受命于福建抗倭的非常时期。嘉靖四十三年,谭纶以福建寇平请终丧得允,回籍守制时上言:自闽中被倭以来,臣经略便宜,自五寨三路之外,已稍稍有绪,然皆救患于目前,而未及久安计也。因陈善后六事。……一宽海禁。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禁之而私通如故,不若官明通之而制之以法。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鱼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宜稍宽其法。……下所司议覆,俱允行推宽海禁[5]卷538。谭纶的建议得到采纳,这意味着当朝对海禁政策的松动,对福建的特殊境况也有所认同。涂泽民乘隆庆改元之机,向朝廷提出开放海禁提议,迅速得到朝廷批准,“准贩东西二洋”,这在明朝海外贸易政策上可谓对于皇朝祖制的大转变。
其次,闽地士大夫在探讨海禁政策与倭乱之间的关系时,并非一味迎合朝中执政者的意见,在商贸活动是否全面合法化问题上形成不同看法。执政者将倭乱归因于海上贸易活动本身,不断限制沿海地区商贸活动。而多数闽士大夫则更倾向于海禁的实施是倭乱的主要原因,倭乱在破坏闽地商贸环境的同时,也严重破坏当地的社会安定,甚至使闽地百姓与朝廷政产生隔阂。正如浙江士大夫唐枢所说:“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衍,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闽之海禁不宜严亦以此。惟其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11]2850。唐枢乃嘉靖时期人,少时师从湛若水,后慕王阳明之学,留心经世之务,讲究躬行致用之学,在海禁问题上有超前而务实的眼光。由于嘉靖时期寇乱正炽,朝廷对海寇、海商一律视若仇敌,唐枢的主张并未获得重视。基于同样原因,福建历任巡抚也将海禁政策的趋紧视为闽地倭乱加剧的一大因素,他们不断向朝廷献策,朝中也有部分官员支持闽省抚臣的提议,但万历皇帝对此始终持怀疑态度,并未能进一步松动海禁。
再次,闽地士大夫也从经济发展与军事发展的角度探讨实施开海政策的诸多益处。海禁的开放力度将直接决定政府税收的增长幅度,不仅有利于当地经济的繁荣,也有助于地方军饷的充实。但朝廷最初批准开海只是从安抚地方的政治立场出发,并未意识到隆庆开海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根据张燮《东西洋考·饷税考》所载,海澄舶税从隆庆六年(1572年)的3 000两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20 000多两,十年间征收额度增长了七倍。福建政府官员是感受这一巨大利益的主要群体,因而也是支持开海、支持合法贸易的主要推动者。万历期间在福建巡抚任上的官员大多支持当地开海,如刘尧诲、周寀为推动商税制度改革积极献策,许孚远、金学曾、徐学聚、陈子贞、丁继嗣等人皆在奏疏中提出闽省不宜海禁的观点。
最后,闽士大夫对开海政策的支持并不限于在任者,除了福建抚臣与闽籍底层官员之外,闽籍辞官居家的乡绅支持开海的亦不在少数,有的甚至是海上贸易的参与者、保护者。嘉靖时期朱纨在其奏章中,曾直接点名参与私贩贸易的闽籍官员达7人,痛诉闽中衣食父母尽在其中,闽海大姓素为倭内主者,对林希元的批判尤为尖刻。面对朱纨的指责,林希元在《与翁见愚别驾书》一文发表了另一番见解,无论其是否亲自参与私贩贸易,但其言论则显示了较为开明的商贸思想:“天下事有义不当为而冒为之,言之则起人疑,不言则贻民害。与其不言而贻民害,宁言之而起人疑,此仁人不忍之心,若今之攻佛郎机是也。佛郎机之攻,何谓不当?……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吾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8]201。朱纨的官方立场不顾闽地边民的现实,引起闽籍士大夫的抗议,最终酿成悲剧。林希元对边民贸易行为的同情与肯定代表了当地士人的普遍心声,其超越正统的通达视野也影响了闽南士大夫的思想。
万历时期,以何乔远为中心的泉州籍士大夫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开明的商贸思想。何乔远在《名山藏》《闽书》中专列《货殖记》《岛夷志》等与商贸相关的章节,在许多文章中也对闽南商人群体表现出积极关切。万历二十年,朝鲜被日本攻破,明朝大臣主张封贡之声较盛,何乔远却激切上疏反对封贡,其缘由之一即来自行走于外番的闽南商人情报。何乔远的好友或弟子如黄汝良、黄居中、蔡献臣、郑之玄、李焻等闽南士人,积极为同乡商人群体作传立言,且能以同情乃至赞赏的态度对待商人阶层。受何乔远影响,到闽地为政的官员也表现出更为开明的贸易思想。崇祯初年,福建巡抚熊文灿招降郑芝龙,使之归顺,招降期间联络郑芝龙的工作由何乔远完成,海盗首领李魁奇猖獗海上,唯一能与之对话的也是何乔远。何乔远的《开洋海议》和《请开海禁疏》两篇文章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商贸思想,既站在普通商民的立场上倡导商贸致富思想,又站在国家政治经济的立场上坚持开海比禁海更有利于国计民生,更有利于增强国家财政实力。
四、结语
闽海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造成了当地以海为生的特殊民情,但明朝政府并未为之提供良性的海洋政策,反之闽地商人群体的正常商贸活动因明朝海禁政策的实施而深受牵制。在海禁政策的反作用力下,闽海私贩集团逐渐形成并不断壮大,一部分成为海盗恶势力给明朝社会带来巨大祸患,一部分最终被政府招安,成为东南海域具有绝对商贸优势的海上霸主。闽海士大夫受闽海商贸环境的浸染,因而对海禁政策有不同于官方意志的认识,这不仅体现在私人言论中,而且在与友人书、为商人传、上疏朝廷等公开议论中皆有体现。以何乔远为代表的闽南有识之士奋力请疏朝廷,为开放海禁而不懈努力,在历史上不失为可歌可泣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