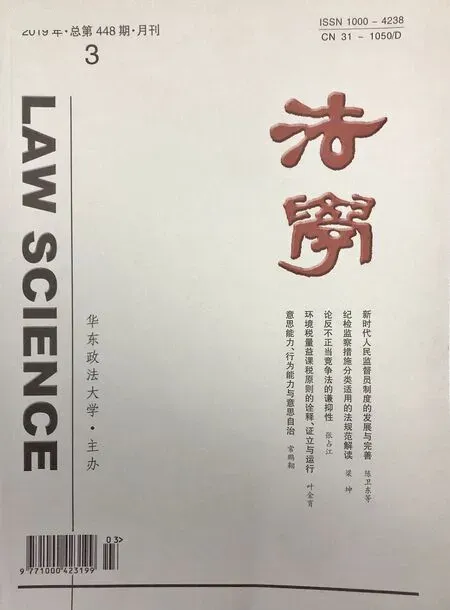明清司法经济对民众诉讼策略的影响
——高昂讼费与健讼风气之悖论的一个分析
2019-03-26尤陈俊
●尤陈俊
明清时期流传着许多讲述到官府衙门打官司之悲惨下场的劝诫文章和例证故事,其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在当时打上一场官司所需的费用,即使未必皆如一些讲述衙门胥吏是如何借机肆意勒索的传闻所形容的那般无比高昂,也必将是一笔为数甚巨的钱财花销,往往会累及涉诉人等因讼罄家。不过,倘若结合更多类型的丰富史料来看,我们将遭遇到一个似乎违反经济理性的“悖论”:一方面,如前所述,明清史料中的一些记载声称,当时打官司所需的诉讼费用居高不下,其开销之巨,甚至足以令普通民众望衙门而却步;另一方面,又有不少文献则显示,不少人到官府频频兴讼,乃至于一些官员认为当地存在健讼之风,并且从一些州县衙门实际所收讼案的数量规模来看,也确实颇为可观。〔1〕参见[日]夫马进:《中国诉讼社会史概论》,范愉译,载《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页;尤陈俊:《“厌讼”幻象之下的“健讼”实相?重思明清中国的诉讼与社会》,《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
管见所及,对于“高昂讼费”与“健讼风气”这两种不同书写之间存在的相互抵牾,迄今为止学界罕见专门的解释,仅有黄宗智、李艳君等少数几位学者曾花了一些笔墨直接论及此问题。〔2〕参见[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188页;李艳君:《从冕宁县档案看清代民事诉讼制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286页。尤其是黄宗智关于清代的诉讼当事人在面对“高昂”讼费时之抉择与策略的精炼讨论,极富学术启发性,不过他主要利用的是来自清代巴县、宝坻和淡水—新竹三地档案中的一些记载,囿于所用资料范围的限制,其得出的那些结论是否可以推而广之用来解释明清时期更多区域的情况,以及是否还存在其他的一些重要应对策略,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力图对上述这种“悖论”专门加以剖析,但并不打算在此着重讨论明清时期的诉讼费用具体是否确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让普通百姓完全不堪承受,〔3〕我将另外撰文专门讨论明清时期的诉讼费用问题。而是对此问题暂时采取折中处理的方式,亦即认为对于明清时期的普通百姓而言,诉讼费用的确构成了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并将这一目前学界已然基本达成的共识作为讨论民众诉讼策略的制约性前提。另需指出的是,先前也有一些学者曾对明清时期民众的诉讼策略或具体手段(例如,运用道德话语为自己塑造“冤”的形象、诬告、缠讼、越诉乃至采取自杀自残、纠众控告等过激行为)进行过讨论,〔4〕例如徐忠明:《小事闹大与大事化小:解读一份清代民事调解的法庭记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6期;胡震:《清代京控中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和官方的结案技术——以光绪朝为例的一个分析》,《法学》2008年第1期;李艳君:《清代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大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杨彦增:《清代黔东南苗侗族民众的联合起诉策略探析》,《兰台世界》2015年第21期;李守良:《清末甘肃循化厅少数民族诉讼策略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但有些遗憾的是,此类研究当中有不少实际上犹如某些并不考虑“交易成本”的经济学分析所做的那样,未能充分兼顾到诉讼费用对诉讼策略的制约性影响。本文旨在利用多种类型的史料记载(例如,目前学界尚甚少有人使用的清末各地诉讼习惯调查报告书),借助“结构/行动者(structure/agency)”的分析框架,着重讨论明清时期的社会大众在面对司法经济中的此种讼费压力时,是如何发展出一些具体有效的诉讼策略来加以应对,进而不仅造成一些地方衙门的实际讼案数量不减反增,并且还在不少地方官员心中加深了所谓当地存在健讼之风的刻板印象。
一、一种需要反思的套路化解释模式:词讼繁滋皆因讼棍胥吏百端煽惑?
面对“高昂”的诉讼费用开销,以及很多官员、士绅们关于打官司将致诉讼当事人钱财耗尽的反复劝诫,明清时期的一些地方缘何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民众来到衙门告状兴讼,甚至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当地民风好讼成习?明清时期的官员们通常将此首先归罪于讼师们的挑唆,认为正是此辈在诱导那些起初本无兴讼之念的无知愚民贸贸然地来到衙门打官司。
这种归咎的话语模式由来已久,早在宋代便已出现。南宋时期的循吏黄榦在任新淦知县时声称,该县“词讼最多,及至根究,太半虚妄,使乡村善良枉被追扰”,而究其原因,“皆缘坊郭乡村破落无赖,粗晓文墨,自称士人,辄行教唆,意欲搔扰乡民因而乞取钱物”。〔5〕参见[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元刻延佑二年(1315)重修本,卷39,“徐铠教唆徐辛哥妄论刘少六”,第17页a。此种话语模式在明清时期更是不断地出现在官员们的笔下。明代万历年间,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杨四知在其发布的一则劝民息讼告示中写道:“闽俗好讼,漳泉为甚,每遇新院下马,无论曲直,群然溷扰,皆因省城聚居讼师,游手好闲,专一兴灭词讼,教唆善良,以此为生。”〔6〕参见[明]黄仕祯修:《将乐县志》,明万历十三年(1585)刻本,卷1,“巡按监察御史杨四知谕民息讼告示二道”,第29页a。到了清代,认为讼师乃是导致词讼繁兴之祸首的论调,更是在官场中广为流传。康熙年间出任福建汀州知府的王廷抡认为,当地民众屡屡兴讼,“此皆讼师之愚弄,或藉蠹棍之引援。”〔7〕参见[清]王廷抡:《临汀考言》,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卷16,“劝谕息讼”,第10页a。雍正十一年(1733)八月,湖南巡抚在一则劝民息讼告示中宣称,“南民刁悍,每以小事辄成大题,砌词越控,一告不准,又敢改名捏词复告……此皆讼棍图利唆拨,以致愚民轻听,自罹罪戾,殊堪痛恨。”〔8〕参见[清]吴达善纂修:《湖南省例》,清刻本,“刑律”卷10,“诉讼·越诉·晓谕刁民架词越控”,第1页。乾隆时期,福建巡抚甚至在同一份文札中反复讲道,“闽省民情刁悍,讼狱繁多,皆由讼棍教唆,以致捏情混控”,“总缘无赖讼师,倚恃刀笔,逞其刁唆之能,遂其诈骗之计”,“闽省民多好讼,皆出一班讼棍遇事教唆”。〔9〕参见《福建省例》(下册),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963~969页。嘉道年间的循吏刘衡断言,“民间些小事故,两造本无讦讼之心,彼讼棍者暗地刁唆,诱令告状。”〔10〕参见[清]刘衡:《庸吏庸言》,清同治七年(1868)楚北崇文书局刊本,上卷,“理讼十条”,载《官箴书集成》第6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97页。下文中引用收入《官箴书集成》的各种古籍时,只写所载《官箴书集成》的具体册数,不再重复标注出版社等信息。道光朝的地方官何耿绳强调:“民间雀角细故,原可平情理释。百姓初无涉讼之心,多因讼师唆弄煽惑,遂尔架捏虚词,牵连无辜,混行呈告。”〔11〕参见[清]何耿绳:《学治一得编》,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眉寿堂刊本,“拟案五则”,载《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678页。光绪年间任山东莱阳知县的庄纶裔,在目睹所谓“莱邑词讼繁多,民情刁健”之景象后写道,“本县推求其故,皆由讼棍包揽主唆”。〔12〕参见[清]庄纶裔:《卢乡公牍》,清宣统三年(1911)铅印本,卷2,“示谕严禁饭店包揽讼事条告文”。一些地方官员还宣称,不乏有“两造均不愿终讼,而讼师欲壑未盈,不肯罢手”,〔13〕参见[清]方大湜:《平平言》,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资州官廨刊本,卷3,“讼师未获须恐以虚声”,载《官箴书集成》第7册,第677页。“当事人既隳[讼棍吏胥]术中,每有欲罢不能之叹”,〔14〕参见[清]刘汝骥:《陶甓公牍》,清宣统三年(1911)安徽印刷局排印本,卷12,“法制科·绩溪民情之习惯”,载《官箴书集成》第10册,第612页。“甚至有[原告]痛哭叩求其息事而不可得者”。〔15〕同前注〔11〕,何耿绳书,第678页。
上述这种将不少地方讼案繁多的现状归咎于讼师挑唆民人打官司的套路化解说模式,并不只是在地方官员之间流传,有时甚至还上达天听。清代雍正年间,河南道监察御史毛之玉向皇帝上奏,提议严厉查禁讼师,其所持的理由,便与上述那些官员们所说的同出一辙:“今查直省各处地方,刁健之风所在而有,告讦之案不一而足,此非小民之乐于成讼,实由讼师之有以导之也。夫讼师本系赋性狡猾之徒,刀笔营生,衙门情熟,遇有户婚田土之事,捏造捕风捉影之词,诱惑愚民,教唆控告,指称线索,包准包赢,一手把持,希图射利,以致薄物细故结讼连年,皆讼师之所为也。”〔16〕参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版,“协理山西道事河南道监察御史加一级臣毛之玉谨奏为请严踈纵讼师之处分以戢刁民以敦风俗事”,第438~439页。
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官场所流行的此类话语模式当中,被认为应当要为词讼繁兴这一让地方官员们为之头疼不已的状况负责的,除了讼师这一所谓挑唆民人兴讼的首恶之外,还有常常被称之为“衙蠹”的另一伙人。“衙蠹”是对官府衙门中那些私下甚至公然贪污腐败、肆意勒索民众的无良胥吏的贬称。在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颁布《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之前,帝制中国时期的中央政府皆未明确定立全国性的法定讼费收取标准并在各地加以统一推行,〔17〕参见邓建鹏:《清末民初法律移植的困境:以讼费法规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6~78页。但这并不影响明清时期的胥吏们在经办讼案的过程中收取所谓“陋规”(有时又称作“规费”),甚至是其他一些完全非法的贪赃所得。由于明清时期的书吏和衙役们能从国家领到的薪水微乎其微,甚至可说是等于没有,故而其只能依靠从民间收取一些被官府默认的“陋规”来维持生计,而在司法诉讼过程中收取的那些陋规,便是各种名目繁多的陋规当中最为主要的类型。〔18〕瞿同祖明确指出,对于明清时期的衙门胥吏来说,“多数陋规费是从诉讼当事人那里索取的”,并且通常是由衙门中的这些人共同分享,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修订译本),范忠信、何鹏、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2~78、100~104页。另可参见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260页。讼民们在打官司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需要向衙门胥吏交纳名目繁多的相应规费,而后者则以此来维持自身生计乃至衙门的日常行政开支。我将这种伴随司法过程而生的钱财流动称作“司法经济”。职是之故,明清时期各地衙门中的胥吏们被认为有很强的动机在此种司法经济中藉由承办更多的诉讼案件来谋取经济利益。而这种动机显然与深受儒家“无讼”思想之影响的大传统诉讼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的追求背道而驰。〔19〕参见尤陈俊:《儒家道德观对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影响》,《法学》2018年第3期。在明清时期的实际案例当中,的确有一些地方衙门里面的无良胥吏希望能让讼案数量保持一定的规模,甚至不惜主动“挑起”词讼,或将民人“诱入”诉讼之中,“尤其欢迎可以任其敲诈的‘好案’”,〔20〕参见伍跃:《必也使有讼乎——巴县档案所见清末四川州县司法环境的一个侧面》,载《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410页。而一些地方衙门(如巴县衙门)里面的各房书吏、差役,为了“公平”分配可以从中收取陋规的案源,还形成了细致的内部规则和程序,当他们之间就某起讼案的经办权发生冲突而争执不下时,甚至还会告到知县那里以求裁断。〔21〕Bradly W.Reed,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00-245.
明清时期的一些官员、士绅们常常怀疑衙蠹和讼师暗地勾结,沆瀣一气,借民人词讼而渔利分肥。乾隆二十九年(1763)八月,江苏按察使钱琦上奏皇帝,主张各地官员应当严厉打击其治境内的积惯讼棍,而他的此番举动,促成了一条专门针对讼师的重要例文随后正式出台。钱琦在其奏折中强调“讼狱繁多,江苏称最”,并声称他自己在彻底推求后认为,此“皆缘有一等狡黠之徒,专以刀笔为生涯,竟藉词讼为行业,如劣监、武生、革书、退役以及训蒙算命等人,类能为之。偶遇乡愚户婚田土以及鼠牙雀角,或本无讼心,从中唆耸,或别施机巧,尽掩真情,百计千方,包告包准,因而勾通书役,设法捺延,且复牵累无辜,故为朦混,总期案使经时不结,俾得渔利,不休乃止。”〔22〕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2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影印本,第448~450页。在钱琦看来,讼师与书吏狼狈为奸,暗中把持民人诉讼,使之经久而不得结案。晚清时期朝廷在组织调查各地民情、士绅办事习惯时,来自安徽绩溪县的报告中声称,当地民情刁健,百姓好讼,而这“其实由讼棍吏胥百端煽惑”。〔23〕同前注〔14〕,刘汝骥书,第611~612页。这种套路化的解释模式,甚至还影响到当代的一些研究者对其基本加以照搬。例如,有学者以清代徽州地区为例认为,“官吏与讼师人等彼此串通肆索陋规贿赂,促使民间尚气好讼、‘健讼’成习”,徽州地区“民情‘健讼’,实与泛滥成灾的陋规以及极度贪婪的书吏和衙役们有着实质的关联”。〔24〕参见郑小春:《清代陋规及其对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的影响:从徽州讼费账单谈起》,《安徽史学》2009年第2期。
我并不认为上述那些将一些地方的词讼繁滋归咎于讼师、衙蠹之挑唆的说法全无道理,但相当怀疑这种话语模式是否足以解释普遍的真实情形。一些巧舌如簧的讼师挑唆民人去打官司,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衙门所收讼案的增多,并且从明清时期的实际案例来看,一些官员前述所说的那种“两造均不愿终讼,而讼师欲壑未盈,不肯罢手”的情况,也并非全属子虚乌有。〔25〕例如清代乾隆朝时发生在江苏宝山县的一起案件便属此种情形。在该案中,陈载恒唆使孙岳廷及其胞弟孙好金诬告他人,当孙氏兄弟急欲息讼时,陈载恒却仍不肯罢休,煽动勉允随行的孙氏兄弟来到对方家中闹事。参见[清]沈沾霖辑:《江苏成案》,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本,卷15,“刑律·诉讼·教唆词讼·唆使诬告照棍徒生事扰害例问拟(陈载恒)”,载杨一凡、徐立志主编:《历代判例判牍》第8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181页。以下引用收入《历代判例判牍》的各种古籍时,只写所载《历代判例判牍》的具体册数,而不再重复标注出版社等信息。但是,我并不认为当时到官府兴讼的民众皆是完全听凭讼师、胥吏挑唆摆布而毫无经济理性之辈(而在上述那些地方官员、士绅们所做的描述中,讼民们实际上被当作是任凭讼师胥吏拿捏、完全被动的无知愚民)。事实上也绝不可能会如此。试想一下,即便其中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倘若每位民众打上一场官司的费用铁定将会导致其倾家荡产,则这种只会让讼师、胥吏从中获利而讼民本人则注定是火中取栗的博弈,将很难长期在整个社会中普遍存续下去。因为在那种情况下,长此以往,通过口耳相传而知晓其后果的民众不仅“屈死不告状”,并且会转而完全求诸民间调解乃至私下复仇之类极端化的自力救济方式,亦即会抛弃打官司这种被他们认为需要付出巨大成本但又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纠纷解决方式。
因此,在讨论民众面临沉重讼费压力的情况下却又出现健讼之风时,我们必须回到那些在前述话语模式中几乎被视作完全被动的诉讼当事人身上,将他们还原为在讼费“高昂”的给定结构中实际上也具有一定的经济理性和能动性的行动主体。从长期的历史趋势来看,讼民们作为一个整体,会在这种给定的结构当中,通过不断地与官府(包括衙门内的胥吏们)、讼师进行博弈,形成一些能够降低自身经济风险的针对性诉讼策略,并借助世代口耳相传,积淀为可被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民间智慧。就此而言,即便是那些为讼民们出谋划策的讼师,在某种程度上也只不过是这些长期以来形成的民间智慧的“更专业”的记忆者和利用者。更何况,明清时期不少所谓的“讼师”,实际上乃是一些其为人助讼的行为在当地官员看来超出了能够容忍的范围,从而被后者贴上该标签意欲治罪的普普通通的下层识字者,〔26〕参见[日]唐泽靖彦:《清代的诉状及其制作者》,牛杰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0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2页。并无足够强大的控制能力让诉讼当事人完全对其言听计从。毕竟,不是每起讼案的背后都会站着一位乃至多位真正的诉讼专家,尤其是在那些琐碎的细事词讼当中。以下将详细讨论明清时期的诉讼当事人所可能采用的几种具有代表性且在相当程度上可谓行之有效的诉讼策略。
二、通过多人分摊讼费来减轻经济压力
黄宗智在对清代一方面打官司费用高昂而另一方面又有不少普通百姓频频兴讼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时,首先强调须将“普通的民事诉讼与含有大笔财产或重大犯罪的官司区别开来”,因为重大诉讼案件的当事人的钱财花销要大得多,他们不仅会更多地求诸讼师帮忙,而且更容易被胥吏们盯上而遭到敲诈,但普通的民事诉讼则相对简单,且不那么花销昂贵。〔27〕同前注〔2〕,黄宗智书,第176页。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不过在此之外,我想再补充同样重要的另一点,那就是还应当将单个民众兴讼从而由其自身或小家庭负担全部诉讼费用的情形,与那些共同参与诉讼的多位当事人每人仅是分担其中一部分诉讼费用的集体兴讼行为区别开来。
从现存的明清史料来看,由众人分担讼费的集体兴讼行为绝非鲜见。这在明代便已常可见到,例如,明代徽州地区张氏族人祖宗坟茔上的树木遭人强行砍伐,在张弘福等人的牵头之下,众族人于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初六日共同订立了一份筹集讼费合同,其中明确写道:“未兑[免]使用盘缠,诚恐子孙推调,独累靠损人难,众议写立合同,各人照依已下丁粮出办,毋许靠损□□□□□照丁粮出办,听从已出之人赍此合同告理,甘罚白艮[银]壹拾两公用,以不孝罪论,仍依照丁粮补出,仍依合同为照。”〔28〕《嘉靖二十六年一月徽州张弘福等筹集讼费合同议约》,载《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2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诸如此类表明众人同心赴讼的分摊讼费合同,在明清时期遗留至今的徽州文书中尚有不少。根据阿风的搜集,现存明清徽州文书中专门以分摊讼费为内容的合同文约,除了上述《嘉靖二十六年一月徽州张弘福等筹集讼费合同议约》外,至少还有《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祁门谢承宪等分担诉讼盘费合同》《崇祯十四年四月徽州黄富祥等合夥出办讼费议约》《康熙四十一年闰六月徽州张为锦等清算讼费合同》《康熙四十五年正月祁门凌君才等公平出费鸣官合同文约》《康熙五十五年祁门许德嘉等均出费用立合文约》《光绪七年元煷公支下光梓等祖堂诉讼前盟约合同》等多件。〔29〕参见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177页。此外,另有多位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也提及现存徽州文书中的其他分摊讼费合同。〔30〕参见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284页;郑小春:《清代徽州的民间合约与乡村治理》,《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例如,据俞江介绍,清代康熙年间徽州百姓叶良之兄弟五人与人构讼,曾为此专门订立了一份齐心诉讼文约以解决诉讼费用的分担问题,约定“官中等事盘费,照股出备,无得独累出身之人”。〔31〕参见俞江、陈云:《论清代合同的类型——基于徽州合同文书的实证分析》,《法学》2014年第5期。在俞江主编的《徽州合同文书汇编》(全1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收录了包括此文约在内的多份以分摊讼费为内容的齐心诉讼合同。
除了讼费分摊合同这种独特的文书类型外,尚有不少来自徽州地区的其他文献同样也反映出当地涉讼民人采取了由众人分摊讼费的诉讼策略。明代徽州府歙县呈坎的罗姓家族与杨干院寺僧围绕该寺庙所在地块的产权归属打官司,从嘉靖七年(1528)开始,一直打到嘉靖十四年(1535)方才尘埃落定。罗姓族人声称杨干院现今所在之地乃是歙县罗氏始祖罗秋隐的墓地,于是不仅多次上控至徽州府,并且还让其族人抱赍上奏位于京师的都察院,最终由都察院转行巡按衙门亲自审理后结案,从而拿回了这块罗氏始祖墓地。这场长达八年的官司之各项开销,总计高达四千余两银子之巨,罗氏族人采取由众家分摊讼费的方式,以应对这笔庞大的诉讼开支。具体而言,罗姓族人各家出资从六百余两到数十两不等,且“其次多寡不同,莫不各随其力之所及、家之所有,乐输以为助,亦难尽悉”。〔32〕参见[明]罗显辑,周绍泉、阿风整理:《杨干院归结始末》,载《明史研究》第15辑,黄山书社2017年版,第282~293页。据清代徽州府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秀才詹元相在其撰写的《畏斋日记》中所记,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一月初五,邻村多名村民来到庆源村尚在封禁之期的山林砍柴,被詹氏族众当场捉拿,两村因此发生纠纷,结果詹氏族众决定到官府打官司,于同月初十召集族众商议好如何分担讼费,并在七天后到当地衙门递交了词状。同年十二月初七,詹元相与被他唤作“瑶叔”“福兄”的两名族人结算打这场官司的花销,共计白银3两2钱7分,“因祠中无银,借出生一公众银暂用”。〔33〕参见[清]詹元相:《畏斋日记》,载《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9~240页。在清代光绪年间徽州黟县一都的余棠控告四都的朱庆春、汪佛金等人抬棺盗占坟地一案中,从汪佛金所记的讼费支用账单中,我们也可看到两位共同被告分担了己方相关的诉讼费用。〔34〕同前注〔24〕,郑小春文。清末徽州婺源县出身于木商世家的秀才詹鸣铎,在其所撰的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中提及,他与族人们为了阻止其家族之九姓世仆中叛变的张姓“混考武童”,于是到县衙打官司,为了凑集讼费,“村内各清明会祀停胙”。〔35〕参见詹鸣铎著,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我之小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不惟徽州地区如此,由多人分担讼费的情形,在其他不少地方亦数见不鲜。在道光十二年(1832)九月十三日的一份堂判中,我们从河南知府李钧笔下获知四十多年发生在当地洛阳县的一桩往事:乾隆五十六年(1791),县民周庠与萧某、王某等人共同筹措费用打官司,结果争得了三十二亩滩地。〔36〕参见[清]李钧:《判语录存》,卷4,“侵吞册费事”,载《历代判例判牍》第10册,第119页。光绪年间的一份判词则透露,浙江会稽县民梁明贵为了争得“未经升科之沙涨地亩,为首纠众敛钱控争”,而受典该沙涨地亩的周屠氏则“出巨款帮助讼费”。〔37〕参见[清]孙鼎烈:《四西斋决事》,卷2,“周屠氏等判”,载《历代判例判牍》第10册,第559页。在光绪末年发生在江苏的一桩官司中,黄堉和黄在沚约定共同分摊讼费,不过黄在沚原先预存的那部分经费后来远不敷使用。〔38〕参见[清]赵幼班辑:《历任判牍汇记》,卷1,“判黄增等覆讯堂词”,载《历代判例判牍》第12册,第161页。甚至在地处边疆的贵州清水江流域,亦有不少以约定分摊讼费为内容的合同文约留存至今。例如,在清代道光年间,当地百姓范文通、姜维新、述圣等人因自家的山木遭人砍伐,于是向官府呈控,并订立同心合字,约定“所有天柱县、黎平府二处之费用,俱照八股均分,范文通占七股,维新、述圣二家认一股,日后不俱[拘]费用多寡,各照股数分”。〔39〕参见陈金全、杜万华主编:《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7页。此份讼费分摊文约,也被收入潘志成、吴大华编著:《土地关系及其他事务文书》,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237页(该书另还收录了其他三份清代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有关诉讼费用摊派或帮补诉讼费用的合同文约)。
尤其是在宗族组织发达而彼此之间又常发生冲突的地区,当纠纷涉及不同宗族、村落的共同利益之时,这种由众人分担讼费的情况就更容易出现。坂上和墩上这两个“相隔里许”的江西村庄,早在雍正、乾隆年间便因汲水灌溉之事而“迭次兴讼”。〔40〕参见[清]沈衍庆:《槐卿政绩》,卷5,“挖毁强车事”,载《历代判例判牍》第10册,第247页。同样是在江西,邻村族居的袁、王、胡三姓,道光年间因王姓众人一再加高堰身,遏截蓄水,影响到其他两姓取水灌溉,以致三姓之间发生讼争。〔41〕同上注,“聚众掘毁事”,第249~250页。诸如此类的官司,其诉讼费用应该都是在全村、全族之中进行分摊。明清时期江西的一些地方,甚至还以合族所建宗祠的祠费来补偿其族人打官司时的讼费开销,以至于清代乾隆二十八年(1763)时,江西巡抚辅德专门为此奏请皇帝予以查禁,而乾隆皇帝不仅对此议准,并且还传谕各地督抚对此类情形留心稽查、实力整顿。〔42〕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页。与江西的情况相类似,在清代湖北黄州黄冈县的孔埠镇,当有族人受到别族欺凌而涉讼时,也会动用宗族公田的收入资助其各项诉讼开销。〔43〕参见张小也:《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在19世纪清廷统治下的台湾北部,更是常常可以见到集体涉讼的当事人形态。在淡新档案中那些现存的诉讼文书里面,我们看到了“金六和”“郑吉利”“吴顺记”之类的合股伙名或堂名。而当它们涉讼之时,往往就是以团体的形态进行应对。〔44〕参见[美]艾马克:《十九世纪的北部台湾;晚清中国的法律与地方社会》,王兴安译,台北播种者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79~180页。这将意味着,打官司过程中支出的各项诉讼费用,是由这些团体或合伙在其内部加以分摊。集体涉讼人在清代台湾的常见,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淡水—新竹衙门的官员们要比那些远在巴县、宝坻等地的同侪们面临着更为沉重的理讼压力。
在明清时期,分担诉讼费用之人,甚至并不限于现居纠纷发生地的那些在地民众。16世纪以来,随着全国市场的日趋活跃,不仅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而且行商坐贾的人数规模也明显见增,甚至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帮”。〔45〕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徽商即为其中最负盛名的商帮之一。那些离家在外、活跃于全国商贸活动之中的徽商,不仅自己常常免不了会因为商业纠纷或主动或被动地涉讼,〔46〕参见范金民:《明清商业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而且当其家乡有族人打官司之时,一些在外营生的徽商还会寄资相助。早在明代中叶,王士性在对徽州地区休宁、歙县两县在外经商之人出资为其乡人助讼的习气加以描述时,便指出江西其他地方的商人对此做法也多有仿效:“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近江右人出外亦多效之。”〔47〕参见[明]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部,载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页。明清时代的徽商之中不乏财力雄厚之辈,他们在遇有其乡党涉讼之时给予后者的钱财资助,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那些涉讼乡民的经济压力。
因此,尽管公堂涉讼时将被胥吏们勒索的陋规种类繁多且数额不菲,但经过团体或合伙之内的多人分摊,以及还有可能会受到来自一些同乡同族在外经商之人的钱财资助,原先或许不堪重负的讼费压力当可相应减轻,从而很可能会降至勉可承受的程度。这种多人分摊讼费的方式,将缩短官府衙门与普通百姓之间原先迫于高昂讼费而被拉大的距离,从而使得告官诉讼并不总是那么令人谈之顿时色变。并且,此类官司由于往往与族众等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且又有众人筹资作为财力后盾,暂时输了官司的那一方很可能会反复缠讼,以图翻案,从而衍生出更多次的告官行为,益发加深了当地官员眼中的健讼印象。
三、采取“官司打半截”的方式以节省诉讼开支
不过,上述所说的这种涉讼一方或双方为团体性诉讼当事人的情况,在明清时期的实际诉讼过程中并不如两家普通民人对簿公堂的情况那么常见。〔48〕在黄宗智统计过的628个清代案例中,出现“团伙性”原告的只有13例(其中巴县3例,淡新10例,宝坻则付之阙如;黄宗智所称的“团伙性”原告,是指原告方为团体、村庄、宗族、行会、商业和生意团伙),在可以辨认出其社会身份的500名原告中所占的比例,不过只有2.6%。同前注〔2〕,黄宗智书,第138页。因此,由多人分摊讼费的诉讼策略,尽管的确会使得一些民众敢于告官兴讼的可能性有所提升,但并不足以普遍解释不少普通百姓面临“高昂”讼费之威胁时为何还能屡兴讼事。分析这一问题的最关键要点或许在于,明清史料中所说的那些诉讼费用,常常都是打完一场官司所需费用的总和。易言之,那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高昂讼费数额,往往是由走完全部诉讼阶段所需支付的各种诉讼费用叠加而成。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原告可能仅仅只是将到衙门告上一状作为给对方施压的手段,未必皆会坚持到堂审、执行等后续阶段。黄宗智曾就此做过简要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49〕同前注〔2〕,黄宗智书,第176、182~186页。接下来我将结合更多的史料,对此进一步展开专门的深入论述。
(一)先下手为强告上一状的可能效果
民人在递交词状与衙门稍做接触后,不待堂审开始便伺机而退,这种做法不仅可能,而且在明清时期或许还相当普遍。在与他人发生纠纷后,如果发觉即便经过调解也将会僵持不下时,为了给对方施加更大的压力,一些精明的当事人很可能会到衙门先告上一状。对于这种诉讼策略,与其一股脑地将之斥为道德评价意义上的“恶人先告状”,还不如将之视为某些具有冒险精神的民众希望借此在后续的纠纷解决过程中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切实手段。
明清时期的州县官们在接到原告递交的呈状之后(即“理”),接下来必须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亦即“准”或“不准”。从官箴书的记载来看,“状不轻准”似乎是当时常见的做法。18世纪的循吏刘衡声称:“状不轻准,准则必审,审则断,不准和息。”〔50〕同前注〔10〕,刘衡书,第195页。他的这一主张,在清代官场上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响应,如方大湜便在《平平言》一书中将此予以引述。〔51〕同前注〔13〕,方大湜书,卷 2,“和息”,第641页。不过,当代的一些研究表明,刘衡此言未必皆与清代各地司法实践中的此方面一般情况相吻合,二者之间很可能实际上相差颇大。梁临霞在研究清代宝坻县的土地债务案件档案时指出,呈词不准的比例相当之小。〔52〕参见梁临霞:《论批呈词——从宝坻档案看清朝土地债务案件的审理》,载中国法律史学会编:《法史学刊》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169页。里赞利用清代四川南部县档案所做的研究也认为,“总体而言,不准的案件在整个州县所受理的案件中是少部分,而且许多案件经过当事人的一再告诉,知县的态度最终也会从不准到准。”〔53〕参见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州县官接到呈词后“准”或“不准”的比例,或许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很难一概而论,且州县官们未必都会在每一起讼案的批词中明确写道“准”还是“不准”,也可能使用了其他一些倾向性难以明确判断的模糊表述,故而即便是借助诉讼档案所做的实证研究,其实也很难说是符合明清时期各地官府之实际处理方式的精确判断。但无论是“准”或“不准”,官员们通常都会作出批词。而这些批词并不止于针对诉讼当事人,它们既可能针对衙门内部的吏役,也可能针对诉讼当事人的族人、中证、约邻、保甲等社会人士。〔54〕同前注〔53〕,里赞书,第157~161页。除了那些明显违反状式条例之要求而“不准”的情况外,〔55〕关于一些状式条例中所规定的案不准理情形,参见邓建鹏:《清代健讼社会与民事证据规则》,《中外法学》2006年第5期;李艳君:《从“状式条例”看清代对书状的要求》,《保定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吴佩林、吴东:《清代州县司法中的“遵用状式”研究》,《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3期。若词状在衙门被“准”,则通常意味着原告暂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当州县官所作的批词表露出对其有利的倾向时更加如此。这种暂时的优势,按照黄宗智的说法,很可能会在由批词所启动的“第三领域”中影响到那些因此更加买力地进行调解的亲友邻里,从而斡旋出一个相比而言更偏向于启动诉讼的原告方的调解方案。〔56〕同前注〔2〕,黄宗智书,第107~130页。
让我们来看一起清代道光年间发生在江西赣州的“猫儿官司”。在这起讼案中,明明无理的张某,却先下手为强,主动到官府挑起讼端,结果后来经过当地士绅的调解,得到了那只原本并不属其所有的母猫。〔57〕详见《器利集》,“诬盗乡村进公呈”与“盗情和息”。原书隐去了张某和王某的具体名字,只留下其姓氏。《器利集》一书现由笔者所收藏,系江西赣州廪生邹列金所编纂的稿本讼师秘本原件,其成书时间为清同治十年(1871)之后。这说明,这种先下手为强告上一状的诉讼策略,有时的确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故而,以到官府衙门先告上一状的方式,向其对手乃至调解纠纷的亲友邻里施压,这种不必等到走完全部的诉讼过程,就可能会在后续的纠纷解决过程中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的方法(一些官员将此做法称作“图准不图审”〔58〕参见[清]李方赤:《视己成事斋官书》,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卷2,“禁打抬讹诈示”,第11页a。),容易成为被某些精明的民众所利用的一种诉讼策略。一旦纠纷通过亲友邻里更加卖力的后续调解而获得解决,调解人可能接下来就会到衙门递交一纸请求和息的呈状,向州县官声请销案,就像前述“猫儿官司”中那位我们不知其名的士绅所做的那样。和息呈状通常是以调解人的名义递交至当地衙门。州县官在收到和息呈状后,通常会准予销案,并要求原被双方向衙门具结,做出“情愿息讼”之类的文字声明。
(二)“官司打半截”的大致诉讼开销
从清末各地上报的诉讼习惯调查报告书来看,当事人向衙门出具甘结、声明以求和息销案,通常需要向官府缴纳一笔费用。对于此点,《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明确写道:“具结完案,亦有必给之手数料,数之多寡,各属不同。兹特录其最多与最少之率于左:(子)状式费,至多者二百四十文,至少者六十文;(丑)写结费,至多者六百文,至少者一百六十文;”〔59〕《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第十项“案费”之“(十七)具结完案之费若干?有无本人不服而勒令具结者?”该书由四川省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股员李先珠编辑,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该报告书的点校整理版,收入张松:《关于清末诉讼习惯资料的初步整理与研究》,《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2012年第1期。后来又被作为附录收入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7~429页。“已成讼案而和息者,当然应缴和息费,以杜起灭自由之弊。至于书差费、堂礼、具结等费付给与否,有不同之点三:(1)有各费全数付给者;(2)有各费俱给半数者;(3)有双方俱不催案、任其拖延者(俗名流案),然非给房费、差费不能。”〔60〕《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第十项“案费”之“(十八)已成讼案两造和息,尚须给书差费、堂礼、具结等费否?”由上述记载可知,尽管状式费和写结费这两项“具结完案”时必给的费用看似不高(总共大约在220文到840文之间),但已成讼案应缴的和息费,实际上往往还包括数额不等的书差费、堂礼费等。因此,和息费的数额实际上颇为不菲。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清代的四川巴县,即便双方情愿到衙门和息销案,也需要各给官府交付2400文钱。〔61〕参见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
《山东调查局民刑诉讼习惯报告书》同样明确列出了原被两造和息时须向衙门缴纳的费用。其中,和息费为“京钱五六千文不等,多者或至数倍”(“大半归于署内门役,少半归房书隶役”),恳息呈费则“与寻常状纸、代书费同”;状纸费为“每纸京钱二三百文不等”,代书费为“每呈一纸,京钱七、八百文不等。”〔62〕参见《山东调查局民刑诉讼习惯报告书》,“民事诉讼习惯”部分第一章“诉讼费用”第一节“关于诉讼之公费”。该书为山东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股员李书田编纂,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当时山东惯称的“京钱”,每两文合制钱一文。
在地处东北的清代奉天地区,光绪三十一年(1905)进行改革之后,该省昌图府收缴的结案费为每案折合银0.33两至0.67两不等。而在同省的复州,光绪三十一年的改革前后所收取的结案费,分别折合银4.16两和3.33两;此外,该地衙门收取的和息费也高达银4两。〔63〕参见张勤:《从诉讼习惯调查报告看晚清州县司法——以奉天省为中心》,《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2年秋季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93~94页。
置身于上述这种收费结构之下,一些诉讼当事人为了尽可能地节省各种诉讼开销,在告上一状后甚至就再也不到衙门纠缠,即便双方之间的纠纷后来在其亲友邻里的斡旋之下得到解决,也不主动到衙门递呈申请销案。于是,该起讼案最终就可能会被衙门不了了之地加以注销。这种情况在当时很可能还颇为多见。例如,清代官员方大湜显然就已经注意到此点,并且还点出了背后的主要原因:“原告无故两月不到,例应注销。一切词讼案件,如被告人传未到,原告又久不呈催,多系两造不愿终讼,或已在乡间私和,其所以未递息呈,特为省衙门费用计耳。此等事应即注销。”〔64〕同前注〔13〕,方大湜书,卷 2,“原告久不呈催”,第641页。
这种将抢先到衙门告上一状作为向对手施压的手段,但并不打算启动后续的全部司法程序的诉讼策略,在明清时期估计颇为常见。正如一条民间谚语所言,“会打官司打半截,不会打的打到头。”〔65〕参见温端政等编著:《中国谚语大全》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页。在黄宗智所统计过的628个清代案例中,约有2/3的案件是在起诉与堂审之间的中间阶段终止其在衙门案卷内的记录。〔66〕同前注〔2〕,黄宗智书,第114页。这显然与倘若采用上述诉讼策略便很可能会节省不少诉讼费用开支有关。
一般情况下,清代的百姓们到当地衙门告上一状,首先需要开销的费用,主要由如下三部分构成:其一,购买状纸的费用,即通常所称的状纸费;其二,请官代书拟写状词(或照自来稿誊写)并盖上戳记的费用,即所谓的代书费与印戳费;〔67〕关于清代一些地方官府规定的官代书收费标准和实际所收费用情况之对比,参见尤陈俊:《清代讼师贪利形象的多重建构》,《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其三,将词状交给衙门承发房时须缴纳的费用,即所谓的传呈费或上号费。从晚清时期山东、四川两省的诉讼习惯调查报告书来看,这些费用在山东大致为京钱880文至3900文(折合制钱为440文至1950文,包括状纸费、代书费和传呈费等三项),〔68〕参见《山东调查局民刑诉讼习惯报告书》,“民事诉讼习惯”部分第一章“诉讼费用”第一节“关于诉讼之公费”。在四川则要稍低,约在1200文至1500文之间不等(包括状纸费、代书费、印戳费、上号费等四项)。〔69〕参见《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第十项“案费”之“(一)纸状、代书、传呈各若干费?各种中有无多寡之分(如禀费少、状式费多之类)?”该报告书还强调:“以上三项,就正式状纸言。至状式与白禀费多寡之比较,大致皆十与二之比例。”来自清末广西的诉讼习惯调查报告书所记载的信息更为详细,具体列举了广西大部分府县的不同收费情况。《广西诉讼事习惯报告书》将民人递呈起诉时所需交纳的各种费用,包括状纸、代书、盖戳、挂号及其他杂费,统称为呈状费,并注明“此种费用在起诉时则取之原告,辩诉时则取之被告,续诉时则各依其续诉之人征取”。据该书记载,这项费用的收取标准,在广西各府县差别颇大,例如,同归桂林府所辖的义宁县、灌阳县两县,一为钱448文,一为1180文,二者相差近750文,但从总体来看,广西各府县对此项费用的收取以800文至1500文的情况居多。〔70〕参见石孟涵辑:《广西诉讼事习惯报告书》,“第四章、诉讼费用”,清宣统二年(1910)铅印本。
由上述三省的情况可大致推断,在晚清时期,民人最初到衙门告上一状的费用虽各地有异,但通常约在制钱800文至1500文之间,往往不到纹银1两。〔71〕杨端六的研究表明,清代咸丰七年到宣统三年(1857—1911)的这55年间,是清代银钱比价回落的时期。当时银钱比价由先前的1500至1600文跌到1100文,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后,才又涨回到1400文,个别地方甚至攀升至2100文。参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179页。另外根据山东、四川两省诉讼习惯调查报告书中的记载估算,如果民人向衙门递交和息呈以申请销案,在山东约需缴纳制钱3000文,而在四川省则要低很多,亦即通常是在220文至840文之间。
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寻常百姓的收入情况。在清末,长工的工价一般在纹银8两左右,月工的收入以800文到1000文为常见。〔72〕参见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191页。并且,城市百姓的收入一般要高于乡民。在天津,皮匠、织花毯工、弹花匠、磨刀匠等下层大众,每日约可得300文;而在上海,独轮车夫每天所得的力钱,大概在130文到350文之间,以一月平均劳动25天计,共可得6000文。〔73〕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7~628页。
上述这种对比意味着,如果民人只是将告上一状当作向对方施压的手段,而并不真正打算使案件再进入堂审等后续程序时,其需要向衙门胥吏支付的费用,其实并没有恐怖得那么高不可攀。在其纠纷通过由原告兴讼而引发启动的“第三领域”中得到解决之后,如果不正式向衙门具结和息,则又可以节省下不少费用(例如,在晚清时期的山东,和息费的数额甚至要超过起诉费用的总和),故而此种做法并非不可能被实际采用。如此看来,采取上述诉讼策略后的经济负担,与将从起诉到出结的全部诉讼程序都走完时所需的费用相比,无疑大为减轻。而这与衙门胥吏所需索的司法陋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差传、堂审等阶段的特点有关。
(三)民众打官司过程中的能动性与被动性
需要承认的是,即使民人采取上述这种“官司打半截”的诉讼策略,也并不能保证其必定能避开差费等数额明显剧增的陋规需索。一些州县官们可能会坚守“准则必审,审则断,不准和息”的司法理念,就像18世纪的名吏刘衡所主张的那样,〔74〕同前注〔10〕,刘衡书,第195页。结果导致很多讼案被一直拉到堂审的阶段。如此一来,挑起讼端的原告小民们照样躲不过各种来自衙门吏役的陋规需索,此前那种“图准不图审”的如意算盘也将落空。但与那种诉讼当事人主动将其讼案一路带到堂审的做法相比,采取前述这种并非不可能的“官司打半截”的诉讼策略,毕竟可以省却不少费用。
此外,在那些斡旋于原被两造之间的亲友邻佑、乡保士绅当中,尽管不乏热心之辈,甚至也可能有个别乡保为求息事宁人而情愿自己出钱来平息他人纷争的事例,〔75〕在乾隆年间发生的一起纠纷中,李氏之女潘完妹被其邻居殴毙,双方私和人命,由曾武臣给苦主李氏3000文钱,此外为双方调解的保正郭天锡还自掏腰包,再给了李氏3400文钱,让她别去报官。参见赖惠敏:《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21页。但这些人未必都会无偿帮忙调解,而可能要就这种“帮助”收取一定的好处。〔76〕清代道光年间的一则记载,暗示了借他人打官司而索要钱财的乡保可能大有人在:“黄土坎儿的保正管地宽,谓包揽官事者也。大约忠实者少,狡黠者多。”参见[清]李光庭:《乡言解颐》,石继昌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保正”,第53页。一些乡保有可能会在为他人私和命案时索取好处,这在赖惠敏对刑科题本、内阁满汉黄册中所收案件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同前注〔75〕,赖惠敏书,第221~223页。清代的一些司法档案透露,在某些情况下,这项费用还并非小数目。〔77〕在乾隆七年(1724)发生的一起两族因争田产互殴而致伤人命的案件中,假借说合之名而行诈财之实的高宗周共得和事钱2000文,另一位同样“帮忙”调解的高守玺则得钱500文,而正遭受丧夫之痛的苦主吴氏却实际只得到对方私下赔付的12000文中的9500文。同前注〔75〕,赖惠敏书,第227~228页。例如,在光绪年间发生于冕宁县的一起讼案中,当事人在书状中罗列自己业已开销的各项费用时,便明确写到此前因央请保长帮忙说话给了其三千文钱。〔78〕同前注〔2〕,李艳君书,第283~284页。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某些通过“第三领域”解决的案件中,当事人支付给那些帮其加劲调解的亲友邻佑的酬劳,可能要比一般性调解中所需支付的为高,因为随着官府批词的出现,将可能有人数更多的亲友邻佑涉入调解,而后者当中人心各异,不排除有个别试图借机发财之人。19世纪末的一本官箴书透露,一旦某些居心不良的贪狡之徒掺入其中,即便两造不欲再讼,也必须厚给讼费,方能请其代递和息呈状。〔79〕参见[清]柳堂:《宰惠纪略》,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笔谏堂刻本,卷1,载《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492页。
因此,民人采取上述那种“官司打半截”的诉讼策略,也并不意味着其所需开销的诉讼费用就必然将会变得完全可以承受。要知道,在清末,天津的皮匠、织花毯工、弹花匠、磨刀匠等人即使终日忙碌,其一月所得的9000文,也只不过能换到大米1公石多,而上海独轮车夫的一月所得还不够一公石米的价格。〔80〕同前注〔73〕,彭信威书,第627~628页。这些下层百姓全赖非常有限的收入养家糊口。不过,与原先那些将全部陋规累加在一起的讼费总和相比,采取上述这种并非不可能的诉讼策略所需负担的经济压力,应当能够减轻不少。正是由于这种可能性,官府衙门与社会大众之间由于那些原先被想象成天文数字的讼费而拉大的距离,可能在现实中又有所拉近。
还需注意的是,即便是衙门吏役需索的那些司法陋规,在一般情况下,其实际数额也可能并没有那些关于吏役们之腐败掠夺行径的漫画式描绘中所形容的那般高昂出奇,亦不似一些民间流传的衙门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全由吏役肆意勒索而当事人对此毫无预期,以至于仅讼费一项就足以将人们阻挡在衙门公堂之外。讼民们完全有可能并非全因老谋深算的差役、讼师之教唆或诱骗才冒冒失失地来到衙门打官司,在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人口增多的时代大背景下,至少在一些经济水平相对富庶的区域,在一些所涉经济利益不菲的纠纷当中,那些司法陋规的需索未必皆能打消每位百姓的打官司念头,衙门公堂实际上亦由此变得并非绝对不可接近,从而造成摆到当地州县官面前的讼案数量有所增长。〔81〕同前注〔21〕,Bradly W.Reed 书 ,pp.241-242。例如,到了清代同治年间,早在乾嘉时期便已被时人认为有着好讼习气的四川巴县,根据夫马进的研究,其时的“诉讼实践,已经不仅仅是‘诉讼社会’一语所能让人联想到的一般形象,甚至已经达到‘诉讼战’的激烈程度。”〔82〕同前注〔1〕,夫马进文,第3页。对同治时期巴县的一个“健讼”案例的专门分析,参见[日]夫马进:《清末巴县“健讼棍徒”何辉山与裁判式调解“凭团理剖”》,瞿艳丹译,载《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95~420页。
此外,各地州县衙门内部关于司法陋规收受的不同惯例,也可能会影响到民众提起诉讼的动力,进而影响到当地衙门所收诉讼案件的总数。清代乾隆年间王有光所写的一则记载颇有意思地展示,青浦县衙门每年收案百余起,而就在与其治境相邻的嘉定县,当地衙门每年所收案件总数竟以千计。而两县讼案数量之所以相差如此悬殊,据王有光所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县衙门的差费归哪一方诉讼当事人承担的惯例不同所致。具体而言,在青浦县,衙门差费系由原被两造共同承担,而在嘉定县,此项费用则只归被告一方承担。因此,青浦县的百姓们可能鉴于当地衙门所收的差费颇为高昂而尽量不去打官司,但嘉定县的民人一旦与人发生纷争,可能就会惟恐成为将来承担全部差费的被告而抢先到衙门告状,从而造成该邑词讼数量远较邻近的青浦县为多。〔83〕参见[清]王有光:《吴下谚联》,石继昌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4,“图准不图审”,第113~114页。关于现代社会中不同的诉讼费用承担模式可能对人们的兴诉倾向造成何种影响,参见傅郁林:《诉讼费用的性质与诉讼成本的承担》,载《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274页。
嘉定县的这种差费承担惯例,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可能相当少见,但在清代的司法实践之中,州县官在审断某起案件时判令其中一方承担另一方的讼费的例子,亦并非罕见。邓建鹏利用清代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判牍中的相关资料,介绍过数起道光、咸丰、光绪、宣统年间发生的一方当事人请求判令另一方当事人赔偿其讼费并最终得到官府判决支持的争讼案例。〔84〕同前注〔17〕,邓建鹏书,第55~57页。而在光绪朝中后期的四川南部县档案中,此类案件其实还有多起。例如,光绪十二年(1886)岳含星冒充武弁一案的判决显示,南部县知县判令“仗恃结盟,唆讼不休”的向开阳“速将岳登文讼费钱文算明给楚”。〔85〕南部县正堂清全宗档案,目录号9,案卷号505,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该判词详见前注〔53〕,里赞书,第264页。而在20多年后同样发生于该县的另一起案件中,据祝明兴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廿四日提交的一份禀状透露,知县先前曾判令邓清泉向其“赔讼费钱十串”。〔86〕“祝明兴禀状”,南部县正堂清全宗档案,目录号18,案卷号1384,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详见赵娓妮、王有粮整理:《南部县正堂清全宗档案选录》,载里赞主编:《近代法评论》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四、结语
本文利用“国家—社会—个体”的视角,再配合以“结构/行动者”的分析框架,立体地阐释了在明清司法经济之结构性约束下,涉讼个体或群体面对“高昂”讼费时可能采用的具体应对策略。概括而言,由于明清时期并不存在法定的诉讼收费制度,涉讼百姓们的确面临着由种种灰色的司法陋规乃至完全非法的勒索盘剥所堆积起来的“高昂”讼费之威胁,但作为并非缺乏经济理性的行动者,他们也发展出并分享着一些能将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降低至自己勉可承受的水平的应对策略,如由多人分摊讼费,又或者将官司只打到一半而非走完全部的司法程序,而商业趋盛、生齿日繁但生存资源又相对紧张的时代背景,也将增大时人利用诉讼作为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的可能性。当时的人们并不都是将到官告状视为绝对不敢踏足的畏途,结果造成一些地方衙门的讼案数量实际上颇为可观。这或许正是我们理解为何明清时期在“高昂”讼费之背景下仍然被不少官员们视为讼风四起的问题关键所在。说到底,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社会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教化之实际控制力等因素发生重要的变化,宋代一些官员当年尚在心中憧憬的那种“讼庭无人鸟声乐”景象,〔87〕参见[宋]黄公度:《三瑞堂》,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3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94页。此时基本上已只能是儒吏们的梦中遥想,而衙门的公堂在现实中最多不过是半开放的“禁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