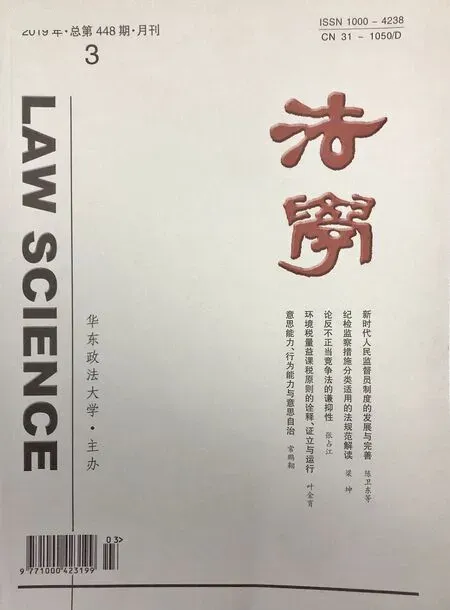前诉与后诉视角下的连带保证人追偿之诉
2019-03-26陈杭平
●陈杭平
在连带责任保证法律关系中,债务人与保证人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也即相对于债权人有外部连带效力,但在内部没有完全的分担效力;保证人可向债务人求偿,反之则不能。故我国《担保法》第31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1〕在连带共同保证情形下,依据《担保法》第12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人在向债务人追偿不能时还可向其他连带保证人追偿。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20条、《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37号)等。如果债权人通过诉讼及取得胜诉判决的方式令连带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而后者又不得不通过诉讼行使追偿权,即面临追偿之诉与前诉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可以拆解为以下两个组成部分。
其一,根据《担保法解释》第126条及债权人的选择,前诉可能形成四种不同的当事人构造:(1)一并起诉连带保证人与债务人,从而构成共同被告;(2)只起诉连带保证人,债务人未参加诉讼;(3)只起诉连带保证人,当事人申请或法院通知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下简称“无独三”)参加诉讼;(4)只起诉连带保证人,债务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2〕可能出现的情形如债权人仅起诉连带保证人,债务人基于确认主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已消灭等“独立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诉讼。对此将债务人定位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似乎更符合逻辑。其中,前三种较为常见,第四种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但在实务中极为罕见,故不予纳入分析范围。这些前诉种类不仅有不同的主观构造,而且案件的诉讼标的或客观构造也有微妙的区别,进而对追偿之诉产生不同影响。
其二,追偿之诉可能在以下四种意义上受前诉及其判决的影响。(1)因为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247条规定的重复起诉而被禁止提起(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也即受前诉判决“消极既判力”(既判力消极作用)的排除。(2)虽未构成重复起诉,但在“积极既判力”(既判力积极作用)的意义上受前诉判决所作判断的拘束,当事人不得否认,法院也不得作出相反判断。(3)不受前诉判决既判力拘束,但受前诉已确认事实预决效力的限制,当事人须提出充分的证据才能推翻。(4)债务人在作为“无独三”参加前诉时受前诉判决“参加效”的拘束。
概言之,对于《担保法》一笔带过的“追偿权”,若通过诉讼主张,其展开过程远为复杂和多样,从而构成民事诉讼法学上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围绕这一实体与程序交织的问题展开研究,也有助于深化对消极既判力、积极既判力、预决效、参加效等判决效力之体系性的理解与把握。有鉴于此,本文将诉讼的主观构造(当事人)、客观构造(诉讼标的)作为两个变量,从债权人提起的具有不同主观构造的前诉出发,逐一识别、辨析其对作为后诉之追偿之诉的判决效力。〔3〕连带责任保证的后诉要更为复杂。比如,债权人只起诉债务人,因债权经过履行及执行未获满足,再次起诉连带保证人,或者相反;债权人只起诉债务人及部分保证人,因债权未获满足,再次起诉其他保证人。为使讨论更为集中,本文暂不予涉及。
一、类型一:债务人与连带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
债权人一并起诉连带保证人与债务人并获胜诉判决,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提起追偿之诉,后诉的原告与被告为前诉的共同被告。〔4〕有疑问的是前诉构成(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还是普通共同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学通说认为构成前者。例如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132页;江伟、肖建国主编:《民事诉讼法》第7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页;李浩:《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但有担保法领域权威法官主张构成后者。参见曹士兵:《中国担保制度与担保方法》第4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427页。而在域外,连带债务要么构成普通共同诉讼,要么构成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还是普通共同诉讼尚无定论。这种独特的主观构造具有双重含义:其一,追偿之诉的当事人包含于前诉,属于广义的“当事人相同”;其二,债务人与保证人虽为前诉的共同被告,但相互间具有主从关系。就前一种含义而言,当前诉法院根据《担保法解释》第42条第1款在判决主文中明确连带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追偿之诉是否因当事人、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与前诉相同而构成重复起诉,或者说受前诉判决消极既判力的排除,便成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即使追偿之诉可得提起,其在多大的客观范围内受前诉判决积极既判力的拘束也不无疑问。就后一种含义而言,域外有理论主张作为共同被告的债务人与保证人之间具有辅助参加的利益,可类推适用“参加效”。〔5〕详见下文注释〔20〕以及正文相关部分的介绍。由此,追偿之诉中当事人所受拘束在性质上属于既判力还是参加效也需要澄清。
(一)消极既判力
若前诉判决依据《担保法解释》第42条第1款,在判决主文中明确连带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是否对追偿之诉产生消极既判力?实务中有不少法院认为此时追偿之诉构成重复起诉。〔6〕参见“云南省江川县龙马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与陈少兴、张海英追偿权纠纷案”,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法院(2016)云0421民初152号民事裁定书;“刘化春与毛旭艳追偿权纠纷案”,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2015)温泰商初字第1206号民事裁定书;“韩汝亮与曹春华追偿权纠纷案”,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5)泰姜张民初字第199号民事裁定书;“山东天翔集团有限公司与朱来富、乔瑞霞等追偿权纠纷案”,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7民终3956号民事裁定书。也即追偿之诉受前诉判决的排除或禁止,保证人只能依据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追偿权对债务人申请强制执行。但这一判解明显有误,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1)关于追偿权的判决不构成已决事项或既判事项;(2)关于追偿权的判决原则上不具有执行力。
其一,追偿权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履行保证债务为事实前提而发生。〔7〕参见程啸:《保证合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原则上这些事实系判决生效后产生的新事实,不属于前诉的审判对象范围,或者说处于判决效力的标准时之后。〔8〕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将“口头辩论终结”当日作为判决效力的标准时,并在案卷及裁判文书中注明。由于我国的开庭审理尚不具有足够的规范性,所谓的“非正式开庭”比比皆是,严格说我国并无与域外“口头辩论期日”相对应的程序设置,也很难将最后一次开庭当日作为判决效力的标准时。但在宽泛的意义上,判决生效后发生的事实不受判决效力拘束。由于保证人有无履行保证债务、履行的数额、债务人有无因保证人的履行而减免债务、保证人的履行有无过错、有无赠与的意思等未经审判,判决明确追偿权仅是对保证人法定权利的重申或确认,并不具有遮断或拘束当事人就相关事实再行争议的既判力。这属于判决主文大于(消极)既判力客观范围的特殊情形。易言之,保证人与债务人之间就这些事实未在程序保障下展开攻击与防御,法院也未在此基础上作出终局判断,“已决”或“既判”的效力无从产生。至于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提起的追偿之诉,依据的恰是前诉判决生效后新发生的事实,按照《民诉法解释》第248条及既判力时间范围的理论,追偿之诉不为前诉判决既判力所及,因而并不构成重复起诉。
其二,关于追偿权的判项并无具体的给付内容,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对追偿权的期待权的确认判决,〔9〕参见郭明瑞、房绍坤、张平华:《担保法》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原则上不具有执行力。保证人据以申请执行,实际上是通过提出证据阐明追偿权的构成要件已满足,追偿权发生并具有请求给付(执行)的具体内容。虽然保证人有无履行保证债务、履行的数额等事实较易审查与判断,但该履行有无过错、保证人有无赠与的意思等仍可能构成债务人的抗辩事由,一旦引起争议须经诉讼程序解决。在“审执分离”原则下,法院执行部门的审查并不能替代审判部门的审理。而且,我国未在执行程序中设置债务人异议之诉,一旦保证人申请强制执行,债务人难以通过异议之诉主张私法上的抗辩权。另外,由于我国不具备德国、日本等立法例的执行文付与制度,即使认为追偿权的判项属于给付判决,也仅具有抽象的执行力,而无法经由执行文付与机关的审查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执行力。〔10〕通过执行文付与机关的审查及付与,使执行名义的执行力现状及范围得以确定,也即对执行力的主观范围、客观范围予以特定。参见[日]田永有利:《民事执行法·民事保全法》,雷彤译,作者2017年印行,第83~90页。
有参与《担保法解释》起草的资深法官在解释第42条的制定目的时指出,法院在审理保证纠纷案件时,可以根据保证人的请求,对保证人的追偿权一并裁决。〔11〕同前注〔4〕,曹士兵书,第162页。换言之,可根据保证人的请求,形成履行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实现追偿权三种诉讼请求的合并,从而对追偿权作出具有既判力及执行力的判决。但是,一方面,保证纠纷审判实务中鲜有保证人会请求这一“诉的合并”;另一方面,即使保证人提出如上请求,如前所述,当事人也无法就尚未发生的事实展开攻击与防御,法院同样不能对将来的事实进行审判。当然,在《担保法解释》第42条第1款被正式废除之前,出于减轻保证人诉累的政策考量,不妨赋予其径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但保证人选择提起追偿之诉的,法院不应以消极既判力或重复起诉为由裁定驳回。概言之,保证人拥有选择申请执行或另行起诉的处分权。应当说,这一理解更符合该款的文义。〔12〕该款后段规定的“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另行提起诉讼”,严格说并未否定前段规定的判决主文明确享有追偿权的保证人另行提起诉讼。恰好相反,其拥有另行起诉与申请执行的选择权。至于前诉判决主文未明确保证人享有追偿权的,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均不应影响保证人提起的追偿之诉。
(二)积极既判力
即使追偿之诉不被前诉判决排除或禁止,由于保证人及债务人为前诉共同被告,其仍受前诉判决积极既判力的拘束。那么,前诉判决究竟在多大范围内拘束后诉,从而使债务人不得为不同主张,法院也不得作出相反判断呢?
传统理论一般主张“诉讼标的的范围=判决主文的判断=既判力的客观范围”的公式,也即以判决主文作为衔接前诉审判对象范围与对后诉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桥梁”。故类型一诉讼的判决主文所包含的针对主债务给付请求、连带保证之债给付请求的判断发生既判力。但很显然,法院判决债权人胜诉是以确认主债权债务、保证合同有效以及可撤销、已消灭、拒绝给付等抗辩事由均不成立为前提的。对于这些“游离”于判决主文之外的前提事项或先决问题,如果允许(广义上)相同的当事人在后诉中再行争议且法院可作出相反判断,既违背诉讼经济、纠纷一次性解决等价值取向,也可能出现矛盾裁判,导致连带保证人无法实现追偿权。根据《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1款第3项后段,相同的当事人在基于相同的诉讼标的提起的后诉中,如果提出实质性否定前诉判决的诉讼请求,构成重复起诉。该项相当于是以消极既判力的面目——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规定了积极既判力的内容,也即拘束当事人在后诉中提出旨在否定前诉判决之前提事项的诉讼请求。即使债务人在追偿之诉中并非以反诉(诉讼请求)的形式,而仅以抗辩的形式进行争议,也应准用《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1款第3项,禁止其进行主张与举证。由此可见,前诉除了判决主文,其判决理由也应当对追偿之诉产生积极既判力。
当然,学理上对既判力客观范围突破判决主文的束缚始终保持克制与审慎。在笔者的检索与阅读范围内,对此持最“激进”立场的学者也仅在有限的意义上将既判力扩张至在前诉中经过充分审理并由生效判决作出明确认定的“基本要件事实”。但导致权利消灭、妨碍权利发生的抗辩或再抗辩事实并不在既判力的射程范围之内。〔13〕参见王亚新、陈晓彤:《前诉裁判对后诉的影响——〈民诉法解释〉第93 条和第247 条解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所谓“基本要件事实”,指的是使某项权利产生的不可或缺或最低限度的必要条件及相关事实。这种观点一方面无疑是受美国“争点排除效”、日本“争点效”理论的影响,将判决已决或既判的效力有限度地向前提事项扩张;另一方面在解释论上与《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1款第3项后段仍未尽贴合。
事实上,《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1款第3项并未区分权利发生事实(或“基本要件事实”)与权利妨碍事实、权利消灭事实,只要基于这些原因事实提起的诉讼请求与前诉的给付判决相冲突,均应被禁止或受拘束。而当事人在前诉中有无实际地展开争议,至少按照美国的诉讼理论并不影响既判力或“请求排除效”的范围。这是既判力规范性的应有之义。〔14〕“请求排除效”有别于“争点排除效”的一大特征是不以争议及裁判的实际展开为前提。换言之,只要界定了“请求”(claim)的范围,处于该范围内的全部事项均因一次诉讼的判决而被排除或禁止再争议。See Wright & Kane,Law of Federal Courts § 100A (7th ed.,2011).转引自Jack H.Friedenthal,et al.,Civil Procedure: Cases and Materials (Compact Eleventh Edition for Shorter Courses),West,2013,p.682.有学者认为《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1款第3项后段有可能强制前诉被告提起反诉,这与我国民事诉讼法未设立强制反诉制度不符。〔15〕参见严仁群:《既判力客观范围之新进展》,《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在一般意义上这种观点或可成立,但就类型一诉讼而言,如债务人不在前诉中竭尽全力就主债务进行抗辩或防御,而在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提起的追偿之诉中予以主张及举证,不仅其行为有违诉讼诚信,而且若因此导致连带保证人难以实现追偿权,对保证人显属不公平。债务人在前诉中已获充分的程序保障,其应承受类似“禁反言”的拘束,不得在追偿之诉中作出相反的主张及举证。〔16〕以当事人先前行为作参照系的效力称为“衡平禁反言”(equitable estoppel),有别于以前诉判决作参照系的“直接禁反言”与“间接禁反言”。See Kevin M.Clermont,Principles of Civil Procedure,Fifth Edition,West Academic Publishing,2018,pp.397-398.在这一特殊情形下,不妨说既判力的扩张及于给付判决的全部必要前提或先决事项。这构成(积极)既判力客观范围大于判决主文的另一种特殊情形,唯此方能与实体法的主流观点保持一致。〔17〕如担保法领域堪称最权威的教科书指出:“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求偿权时,债务人不得以对抗债权人的事由对抗保证人,亦不得以对债权人之债权主张抵销。”同前注〔9〕,郭明瑞等书,第62页。在前诉与后诉的场景下,债务人的各种抗辩权、撤销权、抵销权皆受前诉判决的拘束而不得在后诉中提出。不妨以一则案件为例。
案例一:因诉讼保全受有损害的甲(原诉被告)一并起诉原诉原告乙、在原诉中为诉讼保全提供担保的丙,法院经审理判决乙赔偿甲的损失,丙承担连带责任。丙在赔偿后向乙提起追偿之诉。乙辩称其与丙之间不存在担保关系,《保证书》《担保协议书》等系其代理人未经授权私自签署,并申请对这些文件进行司法鉴定。法院认为丙与乙的担保关系已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对此当事人无须证明,遂不予受理乙的鉴定申请,判决乙向丙偿还代偿款。〔18〕参见“肇庆市新黄河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肇庆市中顺盈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案”,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肇中法民二终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
该案属于前诉判决的事实判断(而非判决主文中的判断)对追偿之诉发生积极既判力的典型例子。后诉法院虽然引用的是《民诉法解释》第93条,但本意应该是不准许乙对其与丙之间的担保关系进行争议与举证,否则按照该第93条第2款的规定,即使已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仍可提出证据予以推翻。考虑到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对积极既判力作出明文规定,这一法律引用并非不可理解。如果该案允许进行司法鉴定,有可能出现相关文书系伪造的认定,从而否定保全担保关系(连带保证责任的基础)的存在,与前诉判决相矛盾。〔19〕实体法上可能涉及表见代理等问题,此处不予展开讨论。乙不在前诉中主张并积极举证,而在丙代其履行赔偿义务之后再提出抗辩,自不应准许。
当然,基于“诉讼标的的范围=判决主文的判断=既判力的客观范围”的公式,为了维护债务人与连带保证人之间因主从关系而存在的辅助参加的利益,似乎也可以考虑前诉判决对追偿之诉类推适用“参加效”。〔20〕例如,日本有学者主张可以在特定的共同诉讼主体之间类推适用参加效或者进行扩张:假如共同诉讼人之间存在辅助参加利益,那么无须实施辅助参加或诉讼告知这样具体的诉讼行为,就认可当然的辅助参加,因此当然地产生参加效。这种学说曾经构成有力说,目前已经衰落。参见[日]三月章:《民事诉讼法》,有斐阁1959年版,第241页。即在追偿之诉中,债务人同时受前诉判决主文及判决理由的拘束,不得针对连带保证人主张前诉判决主文或判决理由错误。〔21〕“参加效”与既判力的异同,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的论述。这样既维持了既判力客观范围的“相对性”(原则上仅限于判决主文的判断),又在类型一诉讼中突破判决主文的束缚对债务人发生拘束力,保障连带保证人追偿权的实现。不过,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参加效”是为了解决判决效力向非当事人的参加人(辅助参加人及受诉讼告知的第三人)扩张的难题而创设的专门概念,且学理上一直存在将参加效视作既判力或者说对二者作一体化理解的主张。〔22〕Vgl.Kathrin Ziegert,Die Interventionswirkung,Tübingen 2003,S.21-22;同前注〔20〕,三月章书,第239页。如将针对当事人发生的判决效力反而理解为参加效,也即扩大参加效的适用范围,与这一学术传统可谓背道而驰。故本文不予采纳。不过,这一理论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有助于解释为何类型一诉讼之判决的理由也具有拘束力。当然,并非前诉的所有判决理由均拘束追偿之诉的当事人,而应限于判决的必要前提或先决事项。
申言之,诸如主合同与保证合同是否成立及有效,有无可撤销的事由,主债务是否因清偿、提存、抵销等原因消灭,是否已过时效等影响给付判决结果的前提事项属于前诉的审判对象或诉讼标的,无论当事人是否确实发生争议并就此展开诉讼上的攻击与防御,或未展开攻击与防御是否出于故意或过失,对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均发生已决或既判的拘束力。在追偿之诉中,保证人与债务人不得作出相反的请求、主张及举证。
二、类型二:连带保证人作为被告且债务人未参加诉讼
在连带保证纠纷中,债权人基于种种原因选择单独起诉连带保证人并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并不罕见。〔23〕例如,债务人下落不明,只能对其进行公告送达,一并起诉严重拖延诉讼进程;基于管辖因素的考虑(如主合同订有仲裁条款而保证合同没有);债务人已处于破产中,债权难以得到完全清偿。如果债权人不同意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且当事人不申请通知债务人作为“无独三”参加诉讼,法院也未依职权将债务人列为“无独三”,对于该类诉讼而言,债务人就成为案外人。〔24〕例外是,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借人仅起诉连带保证人的,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4条。
有疑问的是类型二诉讼的审判对象或诉讼标的的范围。具体而言,其诉讼标的是包含主债权债务,还是仅限于保证合同?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此类诉讼的判决主文仅涉及对保证之债妥当与否的判断。但保证合同在成立、范围和强度、变更、消灭等方面从属于和依附于主债权债务。〔25〕参见崔建远、韩世远:《债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112页。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国际金融、贸易领域出现突破担保从属性、附随性的独立担保,也被称为“见索即付”担保或无条件、不可撤销担保。但我国国内的担保或保证实践未受重要影响。同前注〔4〕,曹士兵书,第42~47页。如果主债权债务未发生、已消灭,或债务人具有拒绝给付、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等抗辩权,法院不应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第20条第1款也规定连带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即使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保证人仍有权行使。可见保证人行使债务人的抗辩权是其固有的权利,并不以债务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尽管债务人相对于该类诉讼主体“不在场”,判决主文也不涉及对主债权债务效力的判断,但主债权债务作为类型二诉讼判决必要的先决事项,仍属审理对象范围。无论债权人还是保证人均在此范围受既判力拘束,彼此间不能围绕主债权债务再行争议,否则违反《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1款第3项后段的规定。例如,连带保证人不能在判令其承担保证责任的前诉判决确定后,以债权人为被告提起确认主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后诉。〔26〕如果前诉尚在审理过程中,保证人依据《担保法》第20条第1款的规定可以提出反诉,或向有管辖权的其他法院起诉确认主合同未生效、已消灭、主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等。《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1款第3项仅禁止前诉判决生效后对其加以否定的后诉,而未禁止并行诉讼。
但就保证人提起的追偿之诉而言,原则上债务人并不受前诉判决既判力的影响,原因在于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债务人未被赋予参加前诉的机会,不能通过合理预测该诉讼将发生既判力的内容及范围而提出足以影响相关判断事项的攻击、防御方法及事实证据。〔27〕参见黄国昌:《诉讼参与及代表诉讼——新民事诉讼法下“程序保障”与“纠纷解决一次性”之平衡点》,《月旦法学杂志》2003年第6期。按照既判力主观范围相对性原理,债务人作为案外人未获得相应程序保障,既判力不得向其扩张。其二,连带保证人是基于其固有的权利享有债务人对主债权的抗辩权,而非替代债务人行使抗辩权,二者不构成诉讼担当。债务人不因连带保证人已在前诉中行使了其享有的抗辩权,就类似“被担当人”受前诉判决拘束。其三,连带保证人享有主张债务人抗辩权的固有权利,意味着其有放弃或部分放弃该权利的意思自由。例如,对于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债务,保证人在前诉中未提出抗辩,不应影响债务人在追偿之诉中进行主张与举证。这是连带保证人与债务人在主债权抗辩权上彼此独立的应有之义。其四,尽管连带保证人可以针对主债权进行防御或抗辩,但其抗辩权主张及实效往往要打折扣。例如,基于不知债务人已清偿部分债务、民间借贷中出借人已将利息先行扣除等原因,保证人会被法院判决超额履行保证债务。在追偿之诉中,如禁止债务人就判决主文认定的债务数额提出不同的主张并举证予以推翻,其可能被迫双重给付。〔28〕因债务人的主张及举证而致连带保证人不能求偿的部分,保证人可向债权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考虑到债权人的资力往往优于债务人,这对保证人而言未尝不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保证属于单务、无偿法律行为,在保证人实际履行保证债务后,应尽量保障其追偿权的实现。出于这一价值判断,追偿之诉中应通过判决效力、证明责任分配等诉讼法机制降低保证人追偿不能的风险。在域外民事诉讼法学理上,如当事人与案外人具有特殊的实体法律关系,前诉判决可有利地或不利地及于案外人,从而在后诉中一并拘束前诉当事人与案外人。该案外人受前诉判决拘束力“反射性”所及,避免就前诉、后诉共通的事项进行重复争议。〔29〕同前注〔20〕,三月章书,第35页;Restatement (second)of Judgments,1982,pp.73-77.类型二诉讼中的债务人可视作具备这类实体法律地位的案外人,在主债务是否存在、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等共通事项上受前诉判决不利的影响。然而,债务人未参加前诉却受判决于其不利之判断的拘束,似乎有侵害其接受裁判权或未审而判之虞,既难以与程序保障原理相协调,也与既判力向债务人扩张无实质区别。〔30〕如在日本,反射效与既判力的异同存在争议,有些学者就以“既判力片面扩张”替代反射效。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11~512页。换言之,债务人就相关事项的争议机会与接受裁判权也应获得保障。基于利益衡量的思路,在受既判力扩张或反射性拘束与不受任何效力影响之间,毋宁说债务人仍处于前诉某种判决效力的射程范围内。问题是其所承受的是何种性质的效力。
在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所构成的广义规范体系下,可援引的是《民诉法解释》第93条的规定。〔31〕对于该条第1款第5项规定的 “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同时,该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关于该条第1款第5项与第2款所组成的“免证”与可推翻之于后诉的效力,民事诉讼法学界多数观点从预决效或预决力的角度理解。〔32〕参见江伟、常廷彬:《论已确认事实的预决力》,《中国法学》2008 年第3 期;李浩:《〈证据规定〉与民事证据规则的修订》,《中国法学》2011 年第3 期;同前注〔13〕,王亚新等文。有少数学者主张该条规定的效力属于仅影响后诉法官自由心证的“事实证明效”。参见段文波:《预决力批判与事实性证明效展开:已决事实效力论》,《法律科学》2015年第5期。另有若干学者从既判力的角度对该条予以批评,或者从证明而非判决效力的角度进行理解,因与本文主题关联度较低,恕不一一列明。一方面,前诉判决确认的事实可在后诉被推翻,因此有别于拘束性的既判力;另一方面,引用前诉判决确认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转由对方当事人举证予以推翻(在消极意义上证明前诉判决的事实判断不成立),如果争点为主要事实(基本事实)且本由引用方当事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相当于发生客观证明责任倒置的效果。〔33〕当事人引用的是前诉判决的间接事实、辅助事实,并不发生客观证明责任调整的效果。不过,仍使对方当事人具有“证明的必要”。关于“证明的必要”,可参见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页。
当然,追偿之诉中债务人据以否定债务承担的事由通常属于权利妨碍事实或权利消灭事实,在诉讼上可以纳入“抗辩”的范畴,本由其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前诉判决对追偿之诉产生预决效,不但未更有效地保障保证人追偿权的实现,反而有违反客观证明责任分配(倒置)规则之嫌。〔34〕按照大陆法系的“规范说”或“法律要件分类说”,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应法定,且主要由实体法规定。但由于我国实体法未从要件事实的角度加以制定,使这一主张并非当然成立。但尽可能由实体法律(司法解释)对客观证明责任作出分配,是应予坚持的努力方向。但是,债务人也可能只是单纯地否认前诉判决所确认的权利发生事实,除非发生上述预决效,否则应由连带保证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而且,为了维护前诉对追偿之诉判决效力体系的完整性,避免类型一诉讼(发生既判力)与类型二诉讼(不发生任何判决效力)之间的落差过分悬殊,也以认可类型二诉讼判决发生判决效力为妥。至于前诉判决效力扩张给债务人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可资平衡。〔35〕如债务人发现前诉判决关于主债权债务所确认的事实存在错误且导致其在追偿之诉中败诉的,在宽泛的意义上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资格。
案例二:债权人甲单独起诉连带保证人丙。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年某月某日甲、乙、丙三方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本金为500万元,二日后债权人甲交付430万元,遂判决丙承担保证责任。丙在履行保证债务后向债务人乙提起追偿之诉。乙辩称《借款合同》约定的500万元未实际交付,交付的430万元非同一借款。法院经审理认为乙未提出证据证明相关主张,判决乙向丙偿还借款。〔36〕参见“兴义市吉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钟国强等与杨平等追偿权纠纷案”,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3民初121号民事判决书。
民间借贷以存在借贷的合意及款项实际交付作为生效要件,款项是否交付由债权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在该案中,假如前诉判决对追偿之诉没有预决效,则乙否认案涉款项已交付的,须由保证人丙对该事实负客观证明责任。尽管丙可以主张前诉判决属于公文书,具备相当的证明力,从而使乙意识到提出相反证据的必要性(承担主观证明责任),但一旦乙提出若干反证使法官陷入真伪难辨的心证状态,仍将由丙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相比之下,如前诉判决具有预决效,则须由乙提出充分的证据推翻案涉款项已交付的事实判断,否则乙就承受败诉的结果。这相当于将该主要事实的客观证明责任倒置给乙承担,提高了对乙的举证要求,有利于丙实现追偿权。法院在引用《民诉法解释》第93条之后,以乙未提出证据证明款项未交付的事实主张为由判决其败诉,相当于认定由乙对该事实承担客观证明责任。裁判的逻辑前提便是债务人受前诉判决预决效影响。
须注意的是,只有债权人与保证人展开攻击与防御且形成法院判断或确认的事项,才发生预决效。如果追偿之诉不受前诉判决预决效的制约,由谁就相关事实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尚有疑问。对此可区分以下三种情形。(1)如果保证人在前诉中对债权人主张的权利发生事实予以自认,相关事项不发生预决效,一旦债务人在追偿之诉中予以否认,基于保证人须对其自认行为负责的道理,应由行使追偿权的保证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此时大致可以将追偿权理解为代位权。〔37〕关于保证人代位权与追偿权的区别,参见程啸:《论保证人追偿权与代位权之区分及其意义》,《法学家》2007年第2期。(2)如果保证人在前诉中未主张主债权消灭、妨碍事实并由法院作出判断,预决效也无从产生,债务人可在追偿之诉中主张,不过仍应由其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理由在于,抗辩权之事实理由的证明由抗辩权利人行使最为方便,也最为妥当。(3)如果保证人未以保证期间届满或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等为由进行抗辩,不妨碍债务人在追偿之诉中予以主张。〔38〕《担保法》第26条规定,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第28条第2款规定,在同一债权上保证与物的担保并存时,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务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于此情形,无论保证人出于故意还是过失未在前诉主张其享有的抗辩权,似乎都不能将由此造成的不利益转嫁于债务人,而以保证人在后诉继续承担相关事实的客观证明责任为妥。其主要理由同上述第二种情形。
不难看出,在上述三种情形下连带保证人在追偿之诉中都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形的风险还很高。就前诉客体而言,保证人就有压力尽其所能地针对主债权及保证债权进行抗辩,而非消极以待。但即使保证人进行全方位的防御,法院所作的判断在追偿之诉中仍可能被债务人举证推翻。为了将风险降至最低,保证人除非与债权人存在合谋,否则可申请法院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或通知其作为“无独三”参加诉讼。〔39〕在实践中法院是否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原则上应征得债权人的同意。在有的案件中,保证人申请追加,但债权人出于债务人下落不明、与债务人合谋等原因坚决不同意,法院不予追加。有法官主张应以债务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通知其作为“无独三”参加诉讼。参见何志:《担保法判解研究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267页。一旦债务人参加前诉,原则上就受既判力或参加效的拘束。通过前诉主观构造的变更,保证人在后诉中所享有的程序保障便从预决力升格为拘束力。
三、类型三:连带保证人作为被告且债务人作为“无独三”
债权人选择只起诉连带保证人,而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依申请或者依职权通知债务人作为“无独三”参加诉讼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在类型三诉讼中,法院只能判决连带保证人承担给付责任,而不应单独或一并判决作为“无独三”的债务人履行债务。〔40〕在个别案件中,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但诉讼请求包括要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直接将债务人当作被告,反而判决债务人承担付款责任,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债权人的诉讼请求,债务人与保证人地位一致,一审将债务人列为原审被告并无不当。参见“李成福与合肥银山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李济深保证合同纠纷案”,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六民二终字第00086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判决明显有违反当事人处分权之嫌。理由很显然,既然连带保证人对债权人负有全部给付的责任,债权人仅选择起诉连带保证人,根据处分权原则,法院不应当一并判决债务人履行债务;而连带保证人的给付尚未发生,法院也不能以债务人承担终局给付责任为由径行判决其单独履行债务。而且,债务人与保证人处于对抗债权人的同一“阵营”,为免于承担终局责任,不仅在理论上会积极进行主张、举证,而且不乏主动申请参加诉讼的情况。就此而言,申请或被通知参加前诉的债务人大致相当于大陆法系的“辅助参加人”或受诉讼告知的第三人。相对于保证人提起的追偿之诉,其具有作为单独类型讨论前诉判决对后诉之效力的必要及意义。〔41〕有学者反对判决对“无独三”产生参加效,一个重要理由是部分“无独三”因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已转型为被告,由此应产生既判力,而非对辅助参加人产生的参加效。参见蒲一苇:《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判决效力范围》,《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但是,由于类型三诉讼中法院不能判决作为“无独三”的债务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一理由并不妨碍本文的分析。
德国、日本等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确定判决对辅助参加人发生一定的效力。〔42〕《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辅助参加人对所辅助的主当事人不得主张本诉讼“裁判不当”;《日本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本诉讼的裁判“对辅助参加人亦生效力”。主流理论主张这是一种有别于既判力的“参加效”。〔43〕参加效与既判力的主要区别在于三个方面。其一,在主观范围上,既判力原则上拘束当事人及其继受人,而参加效传统上仅拘束辅助参加人与被辅助人,当然新近理论主张将对方当事人也纳入。其二,在客观范围上,既判力原则上受判决主文限制,仅在例外情况下扩张至判决理由的判断,而判决理由中的事实及法律判断均发生参加效。其三,辅助参加人可以主张其因正当理由不能充分实施诉讼行为或者被辅助人的诉讼实施行为有瑕疵,从而免于参加效的拘束,但既判力具有绝对性,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主张豁免。当辅助参加人已获得相应的程序保障,在被辅助的当事人败诉后,为避免辅助参加人不受判决效力拘束带来的不公平,应将二者视作整体并相互间受判决所作判断的拘束。〔44〕德国、日本的主流观点认为参加效仅发生在辅助参加人与被辅助当事人、诉讼告知人与受诉讼告知人之间。不过,德国有学者主张为了避免重复诉讼争议,主张在辅助参加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也发生参加效;日本持相似观点的“新既判力说”则已成为有力说。参见陈晓彤:《比较法视角下中国判决效力体系化研究》,清华大学法学院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36~239页。债务人无论是受通知参加还是主动申请参加诉讼,作为“无独三”有权辅助保证人进行主张及举证,或者说获得一定的程序保障;保证人败诉后,如在追偿之诉中债务人不受前诉判决主文及判决理由所作判断的拘束,既可能因当事人重复争议、法院重复判断而造成审判资源的无谓耗费,又可能使保证人求偿而不得,难言公平。故在类型三诉讼中,前诉判决应对保证人、债务人产生参加效。申言之,在追偿之诉中,债务人不得对保证人提出与前诉判决判断不同的主张,或者说不得就主债权债务、保证合同的已生效、未消灭、无实体抗辩权等再行争议。
不过,参加效之所以能向辅助参加人或受诉讼告知的第三人发生,也即拘束力向当事人之外的主体扩张,乃以辅助参加人或第三人已受相应程序保障为正当性根据。就此而言,还不能简单地认为债务人一概承受类型三诉讼判决之参加效。一方面,域外法上的辅助参加人均通过主动申请而参加诉讼,往往期待并在事实上也会竭尽所能地辅助一方当事人对抗另外一方(否则并无申请参加的必要)。相较之下,类型三诉讼中的债务人多数系接受法院“通知”而被迫卷入诉讼,不少并不实际参加诉讼,即使参加也仅作消极、有限的防御。遑论在送达瑕疵、违法送达比比皆是的实践中,有些债务人压根未受合法通知。另一方面,在域外法上诉讼告知的场合,受告知人(主要是具有辅助参加利益之人)哪怕未参加或迟延参加也承受判决的参加效,这是其辅助参加人具有明确的诉讼地位、已获相应程序保障的逻辑结果。辅助参加人虽从属于被辅助人,但原则上可为一切有利于被辅助人的诉讼行为,并具有等同于被辅助人实施的效果。〔45〕例外是不得行使被辅助人享有的私法权利,不得处分及变更诉讼,不得放弃或承认诉讼请求、自认、放弃上诉权等,不得与被辅助人的诉讼行为相抵触。同前注〔30〕,新堂幸司书,第565~566页。但在我国,债务人作为“无独三”的诉讼地位模糊难辨,其反驳、抗辩、举证等诉讼行为的生效要件及效力尚不明确。其诉讼行为究竟视同连带保证人的行为,还是须征得保证人的同意或法院的许可,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付之阙如。法院对此的态度也不甚明确。就诉讼行为对判决结果产生的影响而言,很难说债务人获得了实质的程序保障。
案例三:债权人甲单独起诉连带保证人丙,法院追加债务人乙为“无独三”。乙答辩称,其债务自丙处继受而来,甲持有丙的50%股权,二者有恶意诉讼之嫌。乙提出管辖权异议及申请作为共同被告均未获成功,遂不参加庭审。二审法院判决支持甲的诉讼请求。丙在履行后向乙提起追偿之诉。乙主张其对甲的债务附条件,甲与丙之间构成虚假诉讼,后诉法院以两项主张均缺乏证据支持为由不予采纳。〔46〕前诉参见“福清市三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松原市住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闽民终字第976号民事判决书;追偿之诉参见“松原市飞达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松原市住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吉民终319号民事判决书。债务人飞达公司针对两份二审判决先后申请再审,但均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再审。前诉管辖的依据是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向债权人出具的继续保证承诺书,其中约定可由债权人在其所在地法院起诉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该案债务人乙被前诉法院列为“无独三”,无论其是否实际参加诉讼,理论上均承受判决的参加效。但从乙的答辩意见及申请作为共同被告、提出管辖异议等来看,其主张明显与保证人丙有分歧,认为丙与债权人甲之间有合谋。尽管乙拒不参加庭审有过错,但即使参加庭审,由于不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有些诉讼行为不能作出,有些则可能与丙的诉讼行为相抵触而无效。在目前“无独三”的制度设定下,其行为虽然可能影响法官的内心判断(显然这是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重要原因),但并未获得足以影响判决结果的制度化程序保障。追偿之诉的法院未禁止乙提出与前诉判决相反的主张,而是以其未提出充分的证据推翻前诉判决为由,不予采纳其主张。虽然后诉法院不大可能区分参加效(或既判力)与预决效,但其裁判观点可以说接近预决效而非参加效。这在现行“无独三”制度下可以说颇具合理性。
在立法论层面上,为了使类型三诉讼之判决对债务人的参加效正当化,民事诉讼法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在对“无独三”类型化的前提下,应确定辅助型“无独三”的诉讼地位及对判决结果施加影响的权能,从而提高程序保障程度。〔47〕常见的分类方式有“被告型”与“辅助型”,“准当事人型”与“辅助参加型”,“权利型”、“义务型”与“权利义务型”等。第二,在前者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参加效及其例外。前者是根本,然而非属本文主题范围,故不予展开讨论。就后者而言,参加效虽与既判力同具拘束力,在效力强度上没有质的差别,但在域外立法及理论上均存在可以豁免拘束的例外情形,属于有例外的拘束力。〔48〕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在下列情形下辅助参加人不受参加效的拘束:(1)辅助参加时诉讼的时机导致其不能实施某些诉讼行为(如在二审才申请参加诉讼);(2)辅助参加人的诉讼行为与被辅助人的诉讼行为抵触而无效;(3)被辅助人对辅助参加人的诉讼行为进行妨碍;(4)对于辅助参加人不能实施的诉讼行为,被辅助人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未实施。受此启发,民事诉讼法应规定当事人在后诉中可主张并举证豁免的事由。结合类型三诉讼,可作如下展开。
其一,如果债务人未参加前诉,其在追偿之诉中可以未受合法通知为由主张豁免。如债务人能提供证据阐明债权人或保证人提供的地址、联系方式有误,法院不当适用公告送达致其未获通知等事实,则后诉法院应认定“通知”未经合法送达而未生效,涂销前诉判决拘束债务人的参加效。〔49〕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关于“无独三”的规定被置于“当事人”一节下,因此在实务上一般适用法定送达方法通知“无独三”参加诉讼。当然,债务人仍受前诉判决预决效的制约,须在追偿之诉中对前诉判决所作判断举证予以推翻,相当于具有类型二诉讼的诉讼地位。
其二,如果债务人参加前诉,无论其是否积极进行主张及举证,原则上均受判决参加效拘束。当然,鉴于债务人的诉讼地位具有从属性,如作为被告的保证人不同意债务人的主张或举证,致其诉讼行为不发生诉讼上的效果,或保证人未实施只有被告才可实施的诉讼行为(如提出保证合同已过时效的抗辩、提出反诉),则债务人可以在追偿之诉中主张不受前诉判决参加效的拘束。在其向后诉法院阐明前诉所发生的有关程序事实后,即可从前诉判决的参加效中豁免。当然,其对已为前诉判决确认的主要事实仍须承受预决效;否则,如前所述,根据不同事实类型由保证人与债务人分别承担客观证明责任。
四、结语
判决效力的价值体现在前诉与后诉的关系中。只有在“前诉判决对后诉有何影响”这一视角下,不同判决效力间的异同方能得以呈现。过往的研究大多围绕单一判决效力分别进行分析,但由于欠缺体系化的思维,往往“见木不见林”,顾此而失彼。本文围绕连带保证责任所发生的前诉与追偿之诉,提供了一个可将几乎全部判决效力纳入讨论范围的极佳例证。不同主观构造之前诉对于连带保证人提起的追偿之诉具有不同的判决效力,对作为共同被告、案外人或“无独三”之债务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以此为主题展开的类型化探讨,对实体法上完善连带保证责任制度不无启发,但更重要的是对促进判决效力研究的深入化和体系化具有方法论的范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