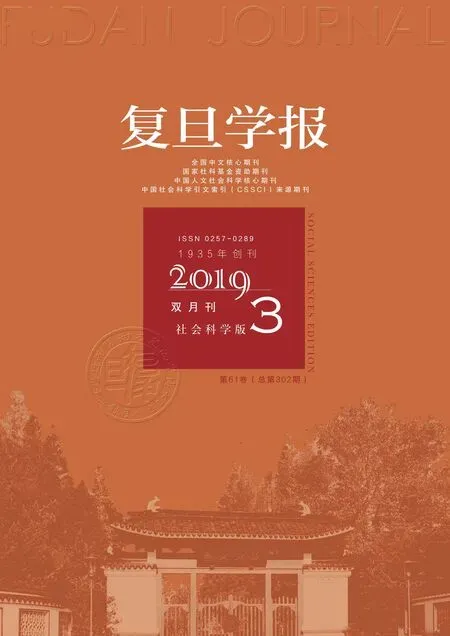《文心雕龙》“才略”意蕴考论
2019-03-25赵树功
赵树功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宁波 315211)
随着才性关系以及文艺创作天人关系认知的深化,汉魏六朝之际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才为核心的范畴系统,这些范畴普遍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才略就是其中之一。关于才略最早、最为系统的论述当属《文心雕龙·才略》。刘勰从这一范畴入手全面考察了历代作家的创作,并将其确立为作家批评的重要尺度——“褒贬于才略”(《序篇》)。[注]范文澜著:《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97-702页。本文相关引文皆出本书,后出者仅注篇目,不另出注。但在如何理解这个“才略”的意蕴上学界却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或以为“才能识略”“文才概略”,或以为“才思”,或以为“创作才华”,或以为“才气之大略”,甚至有学者理解为略论文人的才气等等。[注]参见骆鸿凯著:《文选学》,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第312页;刘永济著:《文心雕龙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4页;詹锳著:《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64页;周振甫著:《文心雕龙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94页;吴林伯著:《文心雕龙义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77页;陆侃如、牟世金著:《文心雕龙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349页。以上诸解各有领悟,也各有偏失,或建立在对于才略引申意义的接纳之上,如才能识略;或建立在才的当代理解之上,如才华才力;或建立在才略体现形态的把握之上,如才思。从文化还原的维度考量,这些理解有将结构性、系统性问题具体化的倾向,有的甚至属于明显的误读(如略论文人的才气)。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汉魏六朝之际的才性理论及才略批评实践,重估才略的意蕴,以期还其本来面目。
一、 才略范畴的发生
“才略”是“才”与“略”两个名词性概念的组合。先秦之际,“才”与“略”均已普遍运用于各种相关文献。“才”与性关系密切,指向主体的禀赋气质与潜能。“略”起初用为动词,如《左传》隐公五年:“吾将略地焉。”僖公十六年:“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宣公十二年:“略基阯。”以上文字中的“略”都是动词,意为经治、统摄。而《左传》昭公七年所云“封略之内,何非君土”则已“借动字为静字”,基本意思为界限、疆界。他如《左传》定公四年“封畛土略”是同一用法,“畛”、“略”皆为疆域,指“自武夫以南,至圃田之北境”。[注]参阅丁福保辑:《说文解字诂林》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3372页。按,其中“经略”杜预注为“经营天下,略有四海”,《说文句读》认为不确。综合“略”的动词名词意蕴,在漫长的文字实践运用过程中,“略”逐步形成了以下几个稳定的内涵:
其一,经画、畺理。这与起初诸侯有其定封的制度相呼应。
其二,由以上引申,经画、畺理的区域由起初的封土拓展为心智、谋划之所能及的范围,其中兼容着经画经治之法术,诸如王略、文武之略等。
其三,从起初土地的经画着眼者,往往关系视域阔大,所筹划者因此多循大体而难以面面俱到,所以“略”之中也便有了简要之意。《孟子·縢文公上》“此其大略也”、《论衡·实知》“众人阔略”之“略”皆是此意。
当然,从经画全局、土地疆域引申,侵夺、抄略之意也便孕育其中。[注]参阅戴侗著,党怀兴、刘斌点校:《六书故》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4页。
“略”与“才”完成耦合,与汉魏人才品鉴将“略”纳为品评一目关系密切。人才评骘依托比类的基本形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诸般品评的条目便产生在物类区划、认识的标准之中,比如度数、容积、空间等等。仅就空间而言,汉魏之际以“宇”、“局”等品目已经普及,器宇、幹局等等皆是,“略”属于这一范围的品鉴纲目之一。东汉建初八年,汉章帝在选举诏书中将征辟者分为四个类型:其一为“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其二为“经明行修,能任博士”;其三为“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任御史”;其四即是“刚毅多略”之才,这类人才要求“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如此则“才任三辅令”。[注]范晔:《后汉书》卷4《孝和孝殇帝纪》,李贤等注引《汉官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6页。可见自东汉开始,“略”已经成为官方人才察举的重要标准。
“略”在汉魏人才品目中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与其时以智术、权谋、诈力经世筹划的群雄竞逐局面不无关系。或为文韬,如:“诸葛亮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注]陈寿:《三国志》卷55《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8页。智慧经画主要集中于人事措置、矛盾权衡、局面规制,其威严心术足以控制影响团结的力量。或为武略,如吕蒙质询鲁肃:“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因为不满鲁肃“临时施宜”的大意无备,随之为其谋划五策以为万全。[注]陈寿:《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1274页。既洞悉全局大势,又能当机立断应变百出。或为兼备文武的盖世之筹度,如赵咨赞孙权:“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自释其意为:“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曹丕),是其略也。”[注]陈寿:《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第1123页。刘备论周瑜“文武筹略,万人之英”也是兼论文武以道其“器量广大”。[注]陈寿:《三国志》卷54注引《江表传》,第1265页。曹羲为曹爽上表论司马懿“包怀大略,允文允武”也是同意。[注]陈寿:《三国志》卷9《魏书·诸夏侯曹传》注引《魏书》,第283页。在以“略”品人广泛流行之际,“才”也同时成为普遍关注的重要概念,从人才察举至九品中正、从政治制度至民间月旦、从哲学研思至文士清谈,才德关注、唯才是举、才性之辨等等都成为当时政治文化的焦点,与主体之才密切相关的才的疆域、边界问题探究由此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才略范畴也随之兴起。东汉文献中才略的应用渐多,如史敞荐举胡广:“才略深茂,堪能拔烦。”张超赞臧洪:“海内奇士,才略智数,不比于超矣。”[注]范晔:《后汉书》卷44《胡广传》、卷47《班超传》,第1508页、第1571页。魏晋之际已经普及,如论桥玄:“严明有才略,长于人物。”论陈登:“忠亮高爽,沉深有大略。”论陶公祖:“本以材略见重于公。”论丁谧:“为人沉毅,颇有才略。”论郑泰:“少有才略,多谋计。”[注]陈寿:《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续汉书》,第3页;卷7《魏书·吕布臧洪传》注引《先贤传》,第230页;卷8《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注引《吴书》,第248页;卷9《魏书·诸夏侯曹传》注引《魏略》,第289页;卷16《魏书·任苏杜郑仓传》注引《汉纪》,第509页。及至刘邵《人物志》,则将其纳入了人才品目理论系统,其中“骁雄”一目便开列了“胆力绝众”与“才略过人”两个条件。[注]刘邵著,刘昺注,梁满仓译注:《人物志》,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9页。
汉魏之际与“略”相关的概念范畴其组合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属于“略”的限定或形容,如将略、雄略、明略、盛略;其二,意义近似,皆指向筹度谋划,如谋略、方略、计略、算略、术略;其三,属于“略”的主体素养源泉的说明,其代表性范畴就是才略。才之为用,一文一武,二者皆与空间相关:文能经国,国大人广地博,其才能足以筹划涵覆,故此称为“略”;武为疆场,变化不尽,其才能足以筹划涵覆,故此也可称为“略”。不仅才堪经画而且才华涵括有余,才略即由此立义,“才”与“略”之间也因此彰显出必然的因果关联。一方面,谋略权术或者经画筹度少不了人生经验的磨砺积累,但主体的禀赋之才对于经画之能往往有着直接的制约,班固盛赞汉武帝“雄才大略”,[注]班固:《汉书》卷6“汉武帝纪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2页。其中便已经包含了才雄则略大的基本逻辑。曹魏时期杨阜将其移赠曹操,名曰“雄才远略”,具体表现为“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注]陈寿:《三国志》卷25《魏书·杨阜传》,第700页。这种过人之处,在时人看来便是“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从“天授”论其才略,才的主导性显而易见。
尽管才略品人风行汉魏,但以才略论文却并不多见,其发端当属于《文心雕龙·才略》。刘勰的才略批评是建立在汉魏六朝才性理论体系之上的。作为禀赋,才的本义之中兼容着潜能与气质性情,一般论述中才、性的意义基本一致,所以又称为才性;但具体语境下时有侧重,这一点早在先秦之际就已经定型。刘勰对于文才的论述基本延续了以上特征,有时侧重于潜能庸俊,而将气质性情的意涵落实在“气”范畴名下,因此有《体性》中“才、气、学、习”的划分,而才与气又归于“性”的辖领,这一点上,刘勰显然受到了晋人“性言其质,才名其用”说法的影响;[注]袁准:《才性论》,《艺文类聚》卷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86页。但有时则依然兼潜能与气质性情研讨文才,《才略》便是代表,而在归于“性”的统领这一点上与其他篇章没有差异。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概括:刘勰所论的才略是主体之才所表现的广度、限度、程度的综合,它是才的体用关系中所有“用”的系统呈现,其中兼容着“才之机权,运用由己”的主体性把握能力。[注]徐增:《尔庵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427页。其意蕴关系到以下三个方面:才之所涵、才之所宜、才之所创。
二、 意蕴之一: 才之所涵的广度
顾名思义,《才略》是研讨作家文才的,但检视本文不免生疑:研讨文才却通篇并非都属以“才”立论。由才直接入手的作家评述当然不少:或显见优劣,如“贾谊才颖”、桓谭“偏浅无才”;杜笃贾逵“亦有声于文,迹其为才,崔、傅之末流也”。或并美等量,如傅玄傅咸“并桢幹之实才”、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或各有千秋,如子建“才隽”、王粲“溢才”、左思“奇才”,曹丕“洋洋清绮”之才、陆机足以“窥深”之才等等。除此之外的作家品目则表现出了丰富的维度:
或言文思。如扬雄“竭才以钻思”、马融“思洽”、祢衡“思锐”、曹植“思捷”、陆机“思能入巧”、左思“业深覃思”。
或言力量。如李尤“才力沉膇”、曹丕“虑详而力缓”。
或言学问。如“(刘)歆学精(刘)向”、王逸“博识”(相当于博学)、张衡“通赡”、应玚“学优”。他如蔡邕“精雅”也是讨论学问之功。这里所谓“精雅”侧重于称道其碑版文章“骨鲠训典”、“词无择言”、“莫非清允”(《诔碑》),如此清正得体、没有遗憾的碑版文章,立体可谓之“精”;而其“缀采也雅而泽”的“雅泽”虽不可脱离禀赋,但“才有天资,学慎始习”(《体性》),体制雅俗,关键还在于平素的学习陶染。
或言识力。如马融“识高”、陆云“以识检乱”。
或言志气。如孔融“气盛”;嵇康阮籍:“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师心”、“使气”二句互文,皆指放纵自我才气情志。
或言情兴。如刘祯“情高以会采”,应璩“风情”、“《百壹》标其志”。
那么文思、力量、学问、识力、志气、情兴范畴与才略之间到底有无关系呢?从才的本然意蕴出发,结合汉魏六朝文才思想实际考察,刘勰笔下的文思、力量、学问、识力、志气、情兴等内容正是才的具体描述。
作为主体禀赋的描述性范畴,才不是一种单独确立、个体运转并发生作用的官能或机能,而是人性诸般的包纳性存在,它以主体禀赋的有机融结为基础,是主体完整心智结构系统及其良性运动状态的呈现,具体呈示为由其决定的“性情气质”与“性能潜质”,并以体用关系的形式融会彰显于情怀、思虑、志气、学力、识度等方方面面。才情、才识、才学、才力、才气、才思等范畴所表达的,皆可以视为主体之才或才性通过其情怀、识度、学养、力量、志气、文思的自我现身。反过来,古人也便经常将富有情怀、识力、学养、力量、志气、文思之能力等视为有才。虽然属于以用论体,却是才的系统性、体用一体性特征决定的。[注]参阅赵树功:《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序编第二章的相关论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文才的这种系统性、体用一体性特征在古代诗学理论中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总结,徐增《尔庵诗话》便是代表。作者首先明确:“诗本乎才。”以才为主体素养之本,为创作的本源与相关理论的逻辑起点。随后又称:“而尤贵乎全才。”“全才”又被称为“才全”,是作者从《庄子》借用的范畴,但庄子论“才全”侧重在物我两忘的境界,徐增旧瓶装新酒,赋予了它崭新的意蕴。在他看来,“才全”就是指“才有情、有气、有思、有调、有力、有略、有量、有律、有致、有格”——这实则就是从批评领域常言的才情、才气、才思、才调、才力、才略、才量、才律、才致、才格中做出的抽象。而以此为“才全”恰恰意味着文才与情、气、思、调、力、略、量、致、格之间是一体化的体用关系(“律”除外)。徐增对此有具体的诠释:
“情者,才之酝酿,中有所属。”情,是使才酝酿勃发的源头,隐蔽于内心,融结于情怀之中。
“气者,才之发越,外不能遏。”气,才发散而出的过程为挟气而行,气是才由内向外显形的动力,这个气裹挟了主体的气质与生命气势。
“思者,才之路径,入于缥缈。”思,才向外显形中所依循的路径、表现出的轨迹,可以及乎缥缈幽微之处。
“调者,才之鼓吹,出以悠扬。”调,本义为才显于外的风采度量,能见自我性质,徐增这里侧重于由声调立论。
“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摇撼。”力,保障才得以稳定完美发挥的支撑,是性之所能的譬喻性说法,禀赋之中已经有其节限,难以变易。
“略者,才之机权,运用由己。”略,能驾驭才、操控才的主体机变。
“量者,才之容蓄,泻而不穷。”量,才所具有的限量,各有大小,但追求其发泄不尽。
“律者,才之约束,守而不肆。”律,约束才之放肆的律条,来自于人力。
“致者,才之韵度,久而愈新。”致,倾向于才所呈现出的个性化的稳定审美特性,经久方成,历久弥新。
“格者,才之老成,骤而难至。”格,才在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运使趋向。[注]丁福保:《清诗话》,第427页。
以上十端围绕着才展开,本源于才(“律”除外),以才的不同运动形式、力量、节奏形成文才不同的用度形态。所论并不周全,具体范畴的解释也有可商榷之处,但其对才的系统性、体用一体性的揭示是富有创见性的。文才正是通过如此广泛的体用形态,在全面呈现其虚灵特性之余提醒我们其系统性的存在形态。《才略》的作家研讨在以才品目之外诸般其他批评维度正是以才“用”显才“体”,属于文才系统的分疏与具体体现。如此描绘历代知名作家的文才,正是从“略”的田土经治意义引申而来,才的疆域或涵括范围之广大即由文才的多维展现中彰显。
如果忽略了才的这种体用一体性与系统性特征,便不容易理解刘勰何以采取如此形式考量才略。当代学者从才识、才思、才气等具体维度去理会才略,道出的也恰恰只是文才系统中的一维。甚至有学者批评刘勰评骘用语甚为错杂,本末未分,而“本末”又指向才略当“以性情为土壤,以学术为膏壤”的一天一人。[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第164页。如此一来,学识、思虑、气力、情兴与文才的体用一体性关系便被模糊甚至颠覆了。
三、 意蕴之二: 才之所宜的限度
从才的系统性而言,只有情、气、思、调、力、量、致、格等齐备且皆能致用方可激发才的最大效力。但文人才分不同,其于以上诸端并非皆能完备或者虽具备致用却力度参差不齐,才的限度由此不可避免。这种限度就总的性能倾向而论有文才与非文才的区分;就文才本身而言,则又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端:体裁有短长、文思有敏迟、运才有敛放、利病融一体。以上特征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都有论述,但学术界罕见关注。
才或者才性并非世外稀珍,而是人人皆有。但大千世界诸般人众的才性潜能并不统一,或长于攻伐,或长于平治,有乱世英豪,有治世奸雄,其他诸如吏才、史才、将才、商贾之才、艺植之才等等名目各不相一,各有偏长。由此而言,如果要在文章事业上有所作为,文才或笔才、诗才的偏长也便必不可少。汉魏之际文人们追溯创作本源而论及的“自然”、“天资”,随后陆机《文赋》中的“辞程才以效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的“因性以练才”等,都与文才的偏宜相关。因此《才略》在展开其相关论述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主线:他所讨论的才不是普泛意义的才,而是文才,是针对“辞令华采”之才的研讨。这一点已有学者明确论及:
如董仲舒和司马迁,刘勰说他们一是“专儒”,一是“纯史”,其所肯定的,并不是《春秋繁露》或《史记》这样的巨著,而是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和司马迁的《感士不遇赋》,认为这才属于“丽缛成文”的创作。又如说:“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王逸博识有功,而绚采无力。”这里,不仅没有混同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反而是有意加以对照,用“富号猗顿”的论著、“博识有功”的学力,来反衬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偏浅无才”、“绚采无力”。这说明,本篇所论之“才”,是专指文学创作的才力,文学家的“才”和学术家的“才”,是各有特点而不可混同的两种才力。[注]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下册,第350页。
体裁有短长。早在曹魏之际,曹丕《典论·论文》就开始直接以“体”概括体裁,文章前有“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之论,继而则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注]曹丕:《典论·论文》,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098页。各种体裁的美学特征不同,对于作家才性的要求也便每有差异,能够兼能通善者并不多见。刘勰对于才有偏长的论述首先集中于体裁短长的界定。就其大端而言,有文、笔的短长。如称桓谭长于著论及讽喻之文而“不及丽文”,是其长于笔而短于文。全篇涉及诗赋之文较多,而于庾元规、温太真则道其表奏、笔记,赞为“笔端之良工”。至于“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则是明确指向了文笔各有“偏美”。就其具体而言,则集中于作家创作体裁的个性化选择与创作优势上,诸如贾谊的议论与辞赋、枚乘的七体、司马相如的辞赋、李尤的赋铭、曹丕的乐府、曹植的诗歌、陈琳的符檄、嵇康的论文等等。
文思有敏迟。自魏晋开始,文学于现实礼仪应酬之中运用广泛,无论公宴还是饯送,诗文竞逐、逞才斗富成为文化时尚,才思敏迟的关注也由此升温。实践的繁盛引发了理论跟进,《文心雕龙·神思》便可谓才思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才略》篇对此也有较多涉及,诸如贾谊“才颖”、王粲“捷而能密”。曹氏兄弟恰成对比:“子建思捷而才隽”、“子桓虑详而力缓”。左思、潘岳与其仿佛,左思“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非自外也”。所谓“非自外也”,正是就其敏给源自内在才性而言。
运才有敛放。徐增论才略已经揭示“略者,才之机权,运用由己”的内蕴。因此,讨论才略,其中也便必然包含才的运使规律与整体的运使状态。运使规律与具体创作中才性、体裁、体制、题材等诸多条件所形成的内在限定势能关系密切,《文心雕龙·定势》由此诞生。此外还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那就是作家运才过程中存在着气有盛衰、思有通塞的状态。《文心雕龙》从道家养生哲学入手,结合文艺创作实践,通过《养气》、《物色》、《神思》诸篇对其进行了充分论述。由于内在限定势能与文思通塞问题是具体创作中的问题,因此刘勰在《才略》篇中基本弃而未论,其关注重点集中在作家之才整体的运使状态上。这种整体运使状态受个体才性影响,彼此相异,大致可分为两类:放纵与敛束。其一为放纵不拘。如“仲宣溢才”,“溢”有充盈漫溢、难以自持的意思,但对王粲而言这是其才高气盛的自然表现,因此下笔“捷而能密”。又如“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师心”、“使气”皆为循遂心性,任纵志气,嵇康玄论精妙,滔滔不绝之中又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锋芒,而阮籍则中心郁结,创为《咏怀》组诗82首,虽然归趋难寻却同样才气如流。其二于文思能够酌量而行者往往表现为才的敛束。诸如左思“业深覃思”、扬雄“竭才以钻思”、曹丕“虑详而力缓”等等皆是。创作的实绩与运才的敛放没有必然关联,因此王粲才“溢”依然可以“文多兼善,辞少瑕累”;袁宏“发轻以高骧”——“发轻”即指随口而发、不事沉吟,虽有偏病却同样可以“卓出”。倒是孙绰创作谨慎,“规旋以矩步”,结果却是“伦序而寡状”——由于循守法度,故而文章有其条流规制却不见精彩。
利病融一体。利病一体是才性的本然特征,如同元气的阴阳二极,虽对立又浑融,不可拆分。这一点在《体性》篇中刘勰已经有所发明,如“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已属利病相合之论。《才略》于此有了更为全面的观照。如论司马相如辞赋“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继承屈原宋玉的传统,将夸艳风格发挥到极致,从而赢得辞宗的声望,但“覆取精意,理不胜辞”,致有“文丽用寡”的批评,二者虽矛盾又集于一体。又如王逸“博识有功”又“绚采无力”、刘向奏议“旨切”却“调缓”、袁宏“卓出”又“多偏”、孙绰“伦序”却“寡状”。更为典型的是陆机,一则“思能入巧”,一则又“辞务索广”而“不制繁”,古人所谓陆才如海又恨其多,正是就此而言。另有“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本处赵壹是与刘向、孔融、祢衡等四人一同被纳入“偏美”一类作家的,刘向《谏营起昌陵疏》、《条灾异封事》等对于奢侈之风与外戚之盛抗言直论,此为其“旨切”所在,但权贵在位不便过显其劣,因而抑扬啴缓,是为“调缓”。联系“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其“盛”、“锐”之中皆有郁结勃发而不事敛束,所谓偏美者显然皆属于利病一体。但赵壹的描述似乎与其他三人不同,其传世的辞赋名作就是《刺世疾邪赋》,刘勰所谓“意繁”、“体疏”是就其称心指斥缺乏辞义熔裁与体制锤炼而言的。[注]参阅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第590~591页。但这篇文章在魏晋六朝文人心中又属于关系世道人心的大著作,其敢于直面浇漓世情、批判败坏风气的勇气与担当又合乎辞赋的本色,对这一点刘勰没有明言,但道其为“偏美”,其用心也大体在此。赵壹的创作因此也同为利病一体了。
如此体裁、文思、利病以及文才运使等诸般独到的特征,便陶铸为作家独到的才能,既融禀赋的涵具,又备才华的运筹策略;既是本能的限度,也是所能的引领。
四、 意蕴之三: 才之所创的程度
依照《文心雕龙·体性》的结论,在文类意义的“八体”习练成熟之后,对于文体根本的塑造力量便源自作家的才性:“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才性与文体之间的这种大体对应关系是《才略》展开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这从以下事实之中可以得到验证:《体性》论述贾谊等十二位文人,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这种上句斥其才性、下句证以文体的法式属缀,而《才略》对同一内容采取的是一致的论述方式。不仅如此,无论才性的描述还是文体的概括,两篇之间也别无二致。诸如《体性》论贾谊:“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才略》即云:“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俊发”为“才颖”的具体情状,“惬”意为得当合适,不在辞繁,故而“议惬而赋清”与“文洁而体清”也基本一致。又如《体性》论王粲:“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才略》则云:“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从才性而论,“溢”指向才华的发散不拘,近乎“躁锐”;“颖出而才果”是就其文才施为的卓荦不群、无所滞塞而言的,这与“捷而能密,文多兼善”等论也基本相同。如果说略有区别的话,也仅仅是文辞略有繁简不同而已。[注]参阅胡大雷:《刘勰论作家个性与风格》,《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魏晋之后才性说尽管有以能论才的趋势,但文化开辟之际形成的以性言才的内涵一直融会其中。我们往往于深刻的文学研讨之中,时时可在“能”之外见到“性”的身影。刘勰的才略论正是如此,其中兼容着以上两个意旨:才之所能、性情所在。而作家才能性情对于文体的建构正是依托才性限度所关系的体裁、文思、利病以及文才运使特点完成,诸端因势凝聚,最终皆可以在文体之中现身。其中体裁、利病等能够见乎文体特征之中比较容易理解,文思敏迟稍微费解。实则齐梁之际论体,既有“伯喈答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等体裁之体、“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的风调之体,同时也有“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的性质敏迟之体。[注]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312页。也就是说,六朝文人认为,才性之中文思的敏迟与其所成就的文体形态之间同样有着必然的关联。
作家才性内蕴的广度与活力、作家才性彼此的限度最终要在文体塑造与总体成就之中形成程度的差异,这是才略自呈的必然路径,刘勰“褒贬于才略”的作家批评正是就此而言。
其一,文体塑造。成体是作家以自我才华为基础、在实践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企及的境界。由一位作家文体塑造的成功与否、影响大小即可确认其才略大概。确认的形式则根据作家造诣略有不同:对于具有一定成绩与影响的作家,往往从其总体创作之中提炼创作体格,如王褒“密巧”、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曹丕“清绮”、刘琨“雅壮而多风”等等,都通过文体的完善自立标示了自我的不凡与才性的归趋;对于体有偏美的作家,则主要从其偏美的体裁入手概括其风调,如陆云“敏于短篇”而“布采鲜净”、张华短篇“弈弈(一作奕奕)清畅”、曹摅长篇“清靡”、张翰短韵“辨切”、庾元规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峤笔记“循理而清通”等等。另有部分作家以标举代表作的形式确认其核心体格,如“乐毅报书辨而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等,其他类似枚乘《七发》、陆贾《孟春》、应璩《百壹》以及冯衍《显志》《自序》、刘邵《赵都赋》、何晏《景福殿赋》等等皆为选文定篇,以篇定体。这其中包容着一些体格创造并不成功的案例,如桓谭的“偏浅无才”直接导致其《集灵》诸赋难以立体;“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也只是“解散辞体,飘渺浮音”,纵才而无检,其创作与体格卓立也便渐行渐远。
在以上较为鲜明的才性体格关系论外,刘勰还关注到影响文体的两个较为隐蔽的现象。
才情激发的形式或发抒的通道。如:“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病蚌成珠矣。”冯衍一生仕途崚嶒,《显志》、《自序》书写其牢愁抑郁,恰能够面目毕显。又如“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刘琨所形成的正直而壮烈的风调,是世积乱离的产物。与其形成呼应的还有“王朗发愤以托志”,与其形成对比的则为“潘勖凭经以骋才”,其中潘勖才华的感激源自经典——尤其《尚书》学习之中获得的灵感,与冯衍、王朗的现实击发正好相反。这两种形式虽然属于影响创作的外在因素,但对于主体才性的成熟、情怀的陶冶以及文体的创构至关重要。
创作之中的才学关系处置。《才略》中云:“自卿、渊已前,多俊(一作役)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这里的“才”特指个体独创的能力,源心发声,无所依傍;“学”则指向既有的经典知识。在刘勰看来,司马相如、王褒以前,文人们创作多役使独到的才能以求尽其意理情志,对于以经典取证无多兴趣。但自扬雄、刘向之后,文章写作往往出经入史、引据典籍,这是文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对于这一客观现象的说明,《文心雕龙》是有着皮里阳秋的:从这一分界前后的代表人物评价来看,司马相如是刘勰直接批评的对象,原因在于“理不胜辞”;王褒虽“以密巧为致”,且“附声测貌,泠然可观”,但与司马相如“洞入夸艳”又有近似之处。扬雄、刘向则不同,刘向的奏议虽调缓却有“旨切”之美;扬雄的评价更高,不仅“属意”为“辞人最深”,而且“涯度幽远,搜选诡丽”,如此的标杆形象与司马相如“理不胜辞”的评价高下判然。其用心所在可谓昭然。从《文心雕龙》整体的思想倾向考量,刘勰是“引书助文”的坚定支持者,一如吴林伯先生所论:
盖本书《事类》肯定以典故证明义理,“乃圣贤之鸿谟”,显示司马相如、王子渊以前之文士,如屈原之《离骚》、相如之《上林》,虽均用典故,究为“万分之一会”;但扬雄之《百官箴》、刘歆之《遂初赋》,以至崔骃、班固、张衡、蔡邕之文、赋,俱多用典故,而“因书立功”,足为后来者的“范式”。[注]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第592页。
才学之间如此的酌量恰恰体现了刘勰才学合一的态度,以学磨砺开掘文才的潜力,同时对于文才过事华藻的冲动加以节制,如此方可实现“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事类》)的创造。从本质而言,才学合一仍属于天人合一。
刘勰以两个较为隐蔽却有着明显理论诉求的现象提醒读者,文体的创造并非仅仅依靠驰骋文才就可以完善,对于文才的把控或者有关文才的经画挥洒,人事勤勉不可缺,时势命运难相悖。
其二,总体成就。才性各异则体格不一,体格难论高下。但在体格之外,才的创造还体现为彼此成就的不同,作家之间的优劣由此彰显。当然,这种优劣的结论都得之于比较。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体裁、体格的掌控能力不同,由此区分出兼才与偏才。这从王粲与建安诸子以及曹魏文人的比量就能清晰体现:
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声;徐幹以赋论标美;刘祯情高以会采;应玚学优以得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
七子之中,刘勰对于王粲可谓极尽夸饰之能事:才华横溢、敏捷细密、诗赋兼能、笔耕不倦。只有孔融未列其中,但前面已经将其纳入“气盛为笔”的“偏美”之列。另外五子则从符檄至诗赋等各得其优,其中徐幹兼能赋、论二体,但无以撼动王粲七子冠冕的地位。其余曹魏文人则笔记、论述各备一技之长,虽有值得称道之处,但所谓“有足算焉”是从前半句延伸而来的,《论语·子路》云:“斗筲之才,何足算也。”刘勰此处无非是说,诸人虽然才具不丰,但并非不足计量称道。言下之意,仍然将其归入了偏才之列。如此评量,自然难以与具有“溢才”的王粲相提并论了。另如“曹摅清靡于长篇,季鹰辨切于短韵,各其善也”等论,曹摅的长篇诗作清新靡丽,张翰的短诗则清晰确当,两人并非通才大德,而是各有其善,自有偏长,同为偏才。
文质协调能力不同,由此区分出创造力的高下。《才略》之中从通赡意义表彰的文人多是文儒两得的大家,这一点体现了刘勰一贯的崇儒思想。如论荀子:“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既为学术大师又精通辞赋,这就是大儒的本色!扬雄与荀子相类,且能“理赡而辞坚”,故有“子云属意,辞人最深”之评,可以说是《才略》全篇最高的评价。又如马融身为鸿儒而能“思洽识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代指其赋颂碑诔等创作既具经论之雅又备文辞之美。另如张衡、蔡邕标以“文史彬彬,隔世相望”,也是赞赏其兼长文章、史传。以上诸家并为兼才大才,其创造之所以杰出关键在于能够立足文质关系运使才能,实现文质并茂。与此相反,质有所不逮,如司马相如“洞入夸艳,理不胜辞”;文有所不足,如王逸“绚采无力”、宋弘“不及丽文”,则均会影响作家的成就及现实声誉。而文质难以协调浃洽又往往是艺术表现力、创造力不足的直接体现,追根溯源在于才赋馁弱。杜笃、贾逵虽“有声于文”,比量傅毅、崔骃的“光采”,两人只堪列入“崔傅之末流”。这一结论便是“迹其为才”的结果,即以其创作实绩所显示的才能做出的判断。
至于“成公子安选赋而时美,夏侯孝若具体而皆微”—— 成公绥撰写辞赋时而可见其佳者,夏侯湛虽有诸般体裁实验却多显羸弱,则是明显的总体成就评估,其间有着直接的才赋优绌态度。当然,如果禀赋近似、控驭才能的法度近似,便往往出现相提并论的现象。如张衡蔡邕“金玉殊质而皆宝”、嵇康阮籍“异翮而同飞”、张载张协“才绮而相埒”等等。
通过文体的塑造与整体的成就,作家的才性特质、才性所宜、才能所及便有了一个感性的呈示,无论才的广度、限度、程度还是运使才华的机权法度,便都可以假此而显形。这就是文学批评之中才略范畴的内涵意义之所在。
当然,《文心雕龙·才略》的篇旨并非讨论才略的内蕴,而是从文学史的脉络出发,以作家才性为尺度,总结历代经典作家的体格风调、创作实绩以及利病得失。因此,《才略》在经典作家创作的总结中又融入了关于作家才能制约因素的思考。这集中体现于时代因素对于作家才能发挥的影响。《才略》通篇评述作家,但篇尾忽发感慨:“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邺都;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汉武帝元封之世、汉魏建安之时,君主文雅且崇尚文学,才士云集,既能施展政治抱负,又以自己的文学才华赢得当世的声誉与君王的垂顾。欲有所作为,这样的时代当然是最值得期待的。言外之意,文人才子处在天人关系之间难以自我把控的末节之上,在时代的不可测度、难以左右面前,作家个人才能的发挥也便增加了太多的变量。这当然不是作者收笔之际忽发感慨,前文冯衍、刘琨等人文体特征的论述之中,实际上已经渗透了这种充满命运感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