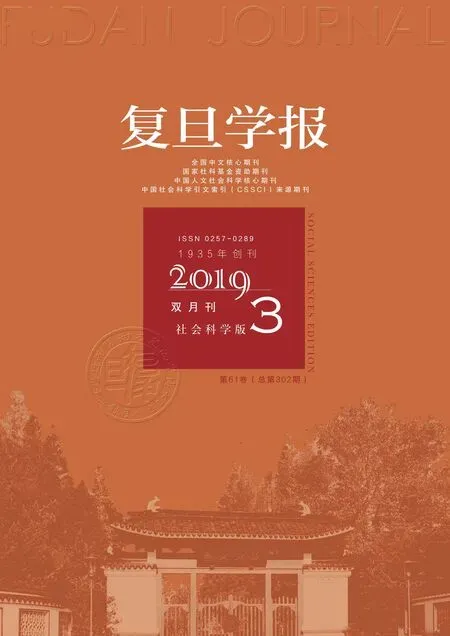地方变迁中的民族主义——基于殖民地广州湾的考察
2019-05-24唐朗诗
唐朗诗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一、 引 言
广州湾是鲜为人知的“非典型”殖民地,但它被殖民统治却长达46年,其时间之长在中国近代史上也相当罕见,然而学界对此却知之甚少。广州湾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上,1899年法国以租借地之名义强占广州湾,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广州湾主权才归还给中国。1946年国民政府将广州湾改名为“湛江市”,隶属广东省政府管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湛江市”的行政区划虽经多次更改,但“湛江市”此一名称仍保留至今。昔日的“广州湾”逐渐被后人所淡忘。
殖民地对民族主义运动与国家构建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种民族主义是如何产生与演变的,它究竟是被“争相奉行采纳”的欧洲式民族主义[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还是本土性的产物?学界对此颇有争议。相比较于当时典型的殖民地(如英占香港九龙、日占台湾、德占胶州湾等),广州湾被时人所忽略。然而殖民地广州湾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答案,它既呈现了法国殖民的冲击及其困境,[注]安托万·瓦尼亚尔著,郭丽娜译:《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也凸显了地方历史与社会结构对民族主义的重要性。
对广州湾地方史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中国民族主义在地方的形成与演变,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在近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何以没有分崩离析,反而在“经历了外国侵略、军阀混战和内战而生存了下来”,[注]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21页。从而深入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独特性。本文采取文本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法,详细讨论了广州湾历史的发展过程,所搜集和分析的材料包括汇编史料、地方志、原始档案、个人回忆录、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等。
二、 民族主义研究范式与争论
在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和现代主义(modernism)是两大相互竞争的研究范式。原生主义论坚信民族性或民族情感是人类天生具有的。[注]Umut Ozkirimli,Theories of Nation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Palgrave Macmillan, 2010) 49.一些受到社会生物学影响的原生主义学者认为,个人之所以结合成同类族群,其动力在于基因的“亲亲性”(nepotism),即个体会选择相近基因的同类人进行合作和结群,而排斥不相似的基因,因此族群就可以看成是具有血缘关系亲属集团的延伸。[注]Pierre L. van den Berghe, “Race and Ethnicy: A Sociobiological Perspective,”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1.4 (1978): 401-411.另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原生主义学说则采取了文化的视角,认为个人相信自己生来就自然拥有“既定的特质”(givens),如血缘亲属关系、语言、宗教、习俗等特质,构成“原生性的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由此赋予了族群认同;[注]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但是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中,这种情感与现代国家所需的“公民的情感纽带”(civic ties)之间容易产生冲突。[注]Edward Shils, “Primordial, Personal, Sacred and Civic Ties,”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8.2 (1957): 130-145.
现代主义学者普遍认为,民族认同是现代社会建构的产物。约翰·布罗伊利(John Breuilly)指出,古代的族群认同是“非制度化的”(non-institutional),因为它缺乏现代民族性所具有的“法律、政治和经济”认同。[注]John Breuilly, “Approaches to Nationalism,” Gopal Balakrishnan (ed),Mapping the Nation(Verso, 1996): 146-174.因此,只有工业社会才打破了古代上层精英所垄断的“高层文化”(high culture),让不同阶层都接受了同质化语言和标准化教育,从而产生出民族认同和公民身份。[注]Ernest Gellner,Nation and Nationalism(Basil Blackwell, 1983): 8-18; Ernest Gellner,Thought and Change(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4): 147-178; Ernest Gellner,Culture,Identity,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5.也有学者强调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上的“不均衡发展”(the uneven development)促使了民族主义的兴起。[注]Tom Nairn,The Break-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Verso, 1977): 316-35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则指出,在“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条件下,民族才得以成为“想象的共同体”。[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46页。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则强调国家建构的角色,19世纪初以来现代国家通过“发明传统”(invented tradition)而建构民族与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于增强政治合法性。[注]霍布斯鲍姆、兰杰编,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00~349页。
西方学者多数是在“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命题”(the culturalism-to-nationalism thesis)中来阐述近代中国的转变。[注]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Jonathan Unger (ed),Chinese Nationalism(M.E.Sharpe, 1996): 1-3; 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作为“非民族国家的国家”(a state without nation)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民族主义化”的过程。[注]John Fitzgerald,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Jonathan Unger (ed),Chinese Nationalism(M.E.Sharpe, 1996): 58-59.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和费约翰等人揭示出,政党通过政治仪式、习俗等象征符号塑造了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党国体制认同。[注]Henrietta Harrison,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7-240; 费约翰著,李霞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1页。现代主义范式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学者,如沈松侨认为,近代民族主义“是被建构出来的人为产物”。[注]沈松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02年第3期。民族主义者或者政党通过传统发明、民族英雄符号、日常仪式来建构历史记忆和民族主义。[注]陈蕴茜著:《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六章;黄东兰:《岳飞庙:创造公共记忆的“场”》,孙江编:《事件·记忆·叙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8~177页;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0年第33期;孙隆基著:《历史学家的经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但是,不少学者指责现代主义范式是以欧洲经验为模板,直接套用到其他国家显然不妥,正如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所质疑:“如果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只能来自于以欧洲和美洲为特定模板的想象共同体,那么还剩下什么能够让他们想象的?”[注]Partha Chatterjee, “Whose Imagined Community,” Gopal Balakrishnan (ed),Mapping the Nation(Verso, 1996): 216; see also Partha Chatterjee,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5.杜赞奇亦认为,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在古代就一直存在着,民族国家体系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注]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因此,笔者认为,在探讨民族主义时需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我们应从长时段视角来探讨民族主义运动在地方发生的历史根源、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构,而不是简单地赞同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如果不联系现代之前的族群纽带(ethnic ties)、记忆和认同,就无法理解现代政治民族主义。[注]Anthony D.Smith, “Opening Statement: Nations and Their Pasts,”Nations and Nationalism2.3 (1996): 358-365.其次,中国民族主义并非变动不居的,毋宁说是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它可以被视为不同叙事或力量相互竞争(contest)和协商(negotiate)的结果,[注]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Jonathan Unger (ed),Chinese Nationalism(M.E.Sharpe, 1996): 31-55.而这正是原生主义论所忽略的地方。最后,可以从微观层面即地方上不同群体尤其是普通民众的视角分析民族主义,而以往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文献太过于侧重精英的视角,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民族’是具有双元性的,它必定是由居上位者所创建,但却也一定得从平民百姓的观点分析才能完全理解”。[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0页。
三、 从边缘到融入大一统: 广州湾的早期历史
(一) 化外之地与政制设置
早期的广州湾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雷州半岛上,它在清朝时期属于广东省高州府和雷州府的管辖之地(见图1)。高州和雷州两地相接,民众多有来往,文化风俗颇为接近,一般并称为高雷地区。

图1 殖民地广州湾地图[注]图中虚线圈为1899年殖民地广州湾范围,作者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清季列强侵占地区图(部分)”绘制。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64~65页。
古人在撰修地方志时,总会将早期的高雷地区视为蛮夷之地,其风俗也与中土殊异,如清道光年间《遂溪县志》一开篇就说雷州府遂溪县“僻在岭南之南”,“昔之瘴雨蛮烟”,经过了宋明以来的儒家教化,才与“中土无殊”。[注][清]喻炳荣等纂:道光《遂溪县志》,《续修遂溪县志序》,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来自中原的士人认为,高雷地区的乡间百姓喜欢用祭神、请巫的方式来治病,唐朝沈既济的《雷民传》记载:人或有疾,即扫虚室,设酒食,鼓吹幡盖,迎雷于数十里外。[注][唐]沈既济:《雷民传》,《龙威秘书》四集第六册,乾隆五十九年(1794)石门马氏大酉山房刊本,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编修《雷州府志》的士大夫感叹:“粤俗尚鬼未有如雷之甚者,病不请医而请巫。”[注][明]欧阳保等纂修:万历《雷州府志》卷十一,《秩祀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早期高州同样被认为是缺乏教化之情况,“在汉晋之时,尚沿夷习,自隋唐之后,渐袭华风”。[注][明]曹志遇等纂修:万历《高州府志》卷七,《风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从秦汉以来,中央王朝已经有意识地在高雷地区设置制度和管理机构。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平定岭南后,分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三郡,高州为南海郡境地,雷州则为象郡之地。汉时期,高州为合浦郡之高凉县,后升格为高凉郡,并增设高兴郡,雷州则属合浦郡徐闻县。南北朝时期大梁兼并高凉和高兴两郡置高州,析合浦郡置合州(后改成南合州),雷州时属于(南)合州。从南朝梁陈之际到隋唐时期,高雷地区被冼夫人和冯氏家族所控制,中央王朝改为招抚地方豪族。唐中期之后,冯氏家族遭受变乱以至衰落,社会陷入动乱中,海贼多次作乱高雷地区。[注][元]脱脱等修:《宋史》卷三十一,《本纪第三十一·高宗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明]曹志遇等纂修:万历《高州府志》卷七,《纪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高雷地区盗、贼、寇的动乱之多,凸显出地方社会与中央政权的松散关系。
宋明以来中央王朝逐渐加强对高雷地区的行政、赋役和地方军事的管控,高雷地区才发生了关键性的社会变革,纳入到王朝行政体制中。[注]贺喜:《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5~17页。宋代朝廷在包括高雷半岛的广西西南诸州推行土丁制。[注][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土丁保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页。明代以来,朝廷设置里甲制,高雷地区“洪武五年定民籍”,[注][明]曹志遇等纂修:万历《高州府志》卷三,《食货》,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地方民众被纳入到编户齐民的控制体系之中。明清时期,高雷两州府制度设置较为平稳,高州府下辖五县一州,分别为茂名县、电白县、信宜县、石城县、吴川县和化州;雷州府辖下有海康、徐闻和遂溪三县。[注][明]曹志遇等纂修:万历《高州府志》卷一,《沿革》,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明]欧阳保等纂修:万历《雷州府志》卷一,《舆图志·沿革》,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地方官和士大夫借助里甲制和平定瑶乱的时机在高雷地区广泛推行理学教化,创办学校,改变地方礼仪风俗。雷州半岛陆续有士子科举高中,明清两代科举人数名列全省中游。[注]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0页。明代万历年间,撰修《高州府志》的地方士大夫终于可以自豪地说:“逮至我朝,休明之化,沦洽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离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虽然语气有所夸大,但至少表明在地方官和士人的心中,他们终于可以融入到中土文化体系。
(二)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整合
1. 宗族制社会的形成
宗族在高雷地区的乡村社会扮演着中心的角色。宗族不能简单地被看成血缘—亲属组织,而是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与地方组织”。[注]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宗族作为一种将民众组织起来的地方制度形式,是在明代嘉靖年间“大礼议”斗争之后才真正确立起来的。华南地区宗族制的发展实践,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改变国家礼仪,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注]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在高雷地区,宗族制社会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就以广州湾的张氏宗族为例。张氏宗族世代居住于高州府吴川县麻斜村,在殖民地广州湾时期曾被改名为“东营”。从明代至今不断续写的《麻斜村张氏族谱》记录了张氏宗族的发展历史。明代的进士、张氏家族第六世孙张光在《张氏创修族谱序》中云:
惟忆我始祖,讳苍显公,字映汉,号河荣,别号陶源,宋进士钦点翰林,原籍福建省莆田县珠玑巷,官授雷州刺史,历任九载。解组时,因胡元扰乱不能携眷回闽,遂卜居吴川麻斜。公生三子,长公讳洞徵,岁进士,任琼山教谕;次公讳洞渊,优贡生,莅文昌通判致仕,卜居遂邑朴扎;三公讳洞玄,郡庠生,卜居茂名蓝溪。…今光与兄讳贞,托荫祖先共叨进士,倘昭穆不彰,是谁之咎?[注]《麻斜村张氏族谱·张氏创修族谱序》,今藏于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麻斜村。
依据族谱叙述,张氏家族从第一代到第五代间并没有建立制度化的宗族组织,其子孙后代也很容易移居到其他地方,这段时期可称为“地方开发期”。到了明代初期,第六代子孙张光及其兄长张贞开始编纂族谱,系统追溯家族的发展史,并强调族谱具有与国史相提并论的重要性,“族自有谱犹国之有史也”。这显然是受到了理学家道德理论及地方实践的影响。
因此,屈大均所描绘的修祠堂、编族谱、置族产、固定时期举行祭祖仪式等标准化的宗族模式在明代的麻斜村已经形成。[注][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七,《宫语·祖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64页。明代之后,高雷地区的宗族也一直致力于维持制度化的过程,以求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依然长盛不衰。
2. 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在广大乡村社会中,也存在着其他多种地方组织,比如以神庙为中心的组织或民间信仰团体。古代中国的民众对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的崇拜是非常普遍的,只有去分析神明信仰的现象,我们才能理解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念,以及民间信仰背后所存在的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注]刘志伟:《满天神佛:华南的神祇与俗世社会》,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岭南历史与社会》,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126页。
不妨继续考察麻斜村的情况。该村最大的神庙就是罗侯王庙,它就建在距离麻斜村码头不远的地方。根据碑刻和方志记载,罗侯王庙始建于元朝末年。神庙供祭的是六位历史人物,包括罗郭佐一门四代五员以及罗仕显部下张友明,皆因讨贼相继死节。因此,朝廷下旨在码头处立神庙,恭祀罗门五节及张友明。这显然符合朝廷的正统观念,将忠君爱国的儒家理念灌输于民间信仰之中。在朝廷对罗侯王庙的敕封中,还包括了麻斜村的张友明,这无疑是提升了张氏宗族在地方上的权势地位。
当然,因为麻斜村临海,村民以海为生,在大多数村民眼中,罗侯王是保护神。所以村民们年例时会抬着罗侯王神像在海面上巡境,意味着它就是海上保护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都通过敕封的神庙维系在一起。正如杜赞奇所言,农业社会里通过神话诸类口头语言和民间信仰的传播使得不同群体加入到“一种民族性的文化”之中。[注]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52页。
因此,制度化的宗族、正统化的民间教派等地方组织,它们所产生的现实影响力,不仅仅是将地方民众团结在一个乡村共同体中,更关键的是,这使得不同阶层或群体融入到统一的身份认同及大一统的国家体系中。
四、 殖民统治下的地方回应与反殖民抗争
(一) 殖民危机与宗族网络的反殖民运动
晚清以来,传统的天下体系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冲击时迅速瓦解。甲午海战之后,帝国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8年法国以租借期99年的名义强占广州湾,使其沦于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局统治之下。法国军队不待清廷与法国政府共同协商划定租地界线,就自行登陆广州湾,并向内陆行军,意图先行扩大占领地范围,以强迫清政府给予认可。
1898年4月,法国远东舰队分队从遂溪县东南部海头村码头登陆。[注]《第六十七号 海军部长柏拿特(Besnard)海军上将致外交部长哈诺德(Hanotaux)先生函》,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页。法军开始在占领地方划界线,除了占有旧营房,还“广挖壕沟,附近庐舍、坟墓惨遭毁挖”。[注]《雷州府遂溪县海头局绅民具禀》,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明清档案,复印件存于湛江市霞山区南柳村吴氏宗祠“南柳人民抗法誓师旧址纪念馆”。在范围划界上,法军与邻近村落发生了直接冲突。在码头附近有众多村落,其中人口较多的是南柳村,且其他多个村都是南柳吴姓宗族之分支。
吴氏宗族竭力支持这次战争,在组织性动员之下,海头一带同宗各村落都被联合了起来。青壮年男丁都被组织起来,成为抗法的主要军事力量,“由祖祠出资,请人打造武器;全族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青壮年男丁,一律参加抗法;为抗法而牺牲者,得劂主入祖祠,分享祠堂同馨祀典,永作纪念”。[注]吴燕辕编:《南柳村》,内部刊物,2001年,第15页。但是1898年底,法国人轻易地击败了南柳村以宗族组织起来的自发抵抗运动,吴氏宗族队伍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法国人继续往遂溪县内陆深入,他们试图将广州湾的界址划得更大,贯穿整个雷州半岛,从而实现与东京湾(即今天的北部湾海域)相联通,但是再次遭到以宗族与团练结合的地方军事力量的沉重打击。
当时遂溪县新任知县李平书着力重振地方公局,兴办团练。士绅们也意识到了法国军队带来的危险,他们集体向李平书呈交禀帖,希望地方官员能够支持他们抗法保家。[注]《据情转请院宪设法保存地方禀》,李平书:《遂良存牍》,《广东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兴办团练得到了全县士绅之支持,其经费主要是来自各个宗族及士绅派捐,“多者递增,少者递减,各大姓祖尝亦同此例”。[注]《遴选绅士办理团练保甲谕》,李平书:《遂良存牍》,《广东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团练机构也是建立在宗族大村,其总部设在广州湾的西北角黄略村潜移书院。黄略村是王姓大村,当时已经有“五六千人”。[注]“王春源口述纪录”(1957年2月6日),《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记录(初步整理稿)》,苏宪章编著:《湛江人民抗法史料选编(1898-1899)》,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团下设六个营,营部分布在黄略、麻章、平石等地,这几个村都是单姓宗族大村。
1899年10月,各地宗族联合起来的团练总部决定对法国军队发起战斗,夺回原本属于遂溪县的境地,当月9日在黄略村与法军对战,竟取得首胜。11月5日法军派军舰到达广州湾,在海面炮轰并派兵进攻,但再次受挫,伤亡七十余人。[注]苏宪章编著:《湛江人民抗法史料选编(1898-1899)》,第8页。法军于是向法国海军部致电请求增援。[注]《第三十三号 法军部长特·雷奈森先生致外交部长得尔卡舍先生电》,1899年11月6日,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法国档案资料选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6页。11月16日,法军准备充分,突袭团练总部黄略村,团练兵员损失严重,黄略上下全村都被毁于一炬。清政府被迫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借给法国,[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929~930页。广州湾彻底沦为法国殖民地。
尽管广州湾抗法斗争最后失败了,但是这场反殖民斗争表明了民众的身份认同是与以往的历史记忆有关。在他们的观念意识中,家乡、地域的认同与国家认同并非冲突或分离的,而是能够相容的。就如一位曾经参加过1899年抗法斗争的村民所意识到的,家乡与国家是密切相关的:“法国鬼过来划地界,占自己家乡,大家说,家乡都被占埋(完全被占),就会做亡国奴,好似元朝被蒙古人霸占一样,大家就不能生存。”[注]“王春源口述纪录”(1957年2月6日),苏宪章编著:《湛江人民抗法史料选编(1898-1899)》,第134页。
(二) 殖民统治下的民族主义认同
1. 城市商人群体的同乡认同与民族认同
法国将广州湾定位为免税自由港,城市被建设起来,行政中心西营、商业中心赤坎等区域也开始变得更加繁荣和商业化,商人及其团体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虽然广州湾的商人有不少可视为城市精英的一部分,但他们多数来自于周围的乡村,依然与乡村宗族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早在被殖民之前,广州湾就已存在同乡会馆等各式传统的商人组织。在1915年创办的广州湾商会是广州湾最大的商会组织,它是众多商家、行会、公会的联合组织,也是建立于同乡会馆的基础上的。[注]蔡挺生等口述、陈基整理:《广州湾的商会回顾》,《湛江文史资料》第九辑,1990年,第108~109页。广州湾商会具有广泛的城市管理权力,设立了调解委员会、治安委员会以及拥有自己的商团(武装)机构,联络和传达殖民当局信息,贯彻执行商业法令,调解商务纠纷,维持商场治安等。但是广州湾商会却选择在国民政府农商部登记立案,自愿受国民政府管理,这无疑反映了广州湾商人群体的民族认同。[注]韦健:《广州湾商业指南年鉴》,香港:东南出版社,1943年;陈国威:《广州湾商会组织结构及其社会功能探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1期。
虽然广州湾商会平时与殖民当局保持沟通合作之关系,但也随时防备着当局对其权力之侵入,它在抵抗法国殖民政府和抗日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6年法国殖民政府试图对商店开征门牌税,广州湾坡头商会首先率领商人举行罢市,南三田头墟商人亦起来抵抗征税,这场运动也发展到了民族主义抵抗运动的层面,最后迫使法殖民当局做出让步。广州湾商会的民族认同在抗日战争期间达到了高潮。广州湾商会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成立救国募捐委员会,给民众提供了各种社会救济,如赈济、平粜等。[注]刘佐泉辑录:《〈大广州湾〉中的赤坎埠》,《赤坎文史》第一辑,2009年,第54~55页。1943年,日本军队侵占广州湾,并试图在广州湾发行伪币,但受到了广州湾商会的抵制,最终没有实行伪币。[注]蔡挺生等口述、陈基整理:《广州湾的商会回顾》,《湛江文史资料》第九辑,1990年,第110页。
传统的同乡认同和民族认同两者并不存在着相互冲突与取代的必然关系。正如顾德曼对上海同乡网络与民族主义的研究所揭示的,同乡情感不一定同民族主义构成矛盾,而是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地方区域认同作为民族的缩影,表明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必然建立在早已存在的团体观念和忠诚之上。[注]Bryna Goodman, “The Locality as Microcosm of the Nation: Native Place Networks and Early Urban Nationalism in China,”Modern China21.4 (1995): 414; 顾德曼著,宋钻友等译:《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可(1853-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八章。
2. 乡村社会的抗税行动与民族主义斗争
1936年广州湾东北部坡头区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民众抗税行动,这次集体行动很快上升为一场民族主义斗争,将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卷入进来。档案表明,1932-1936年坡头区连续遭遇几次大台风和海潮的袭击,民众损失巨大,农田失收。[注]《(府字第3162号)历陈法国勒征人头税、枪杀请愿民众惨案经过及苛政重税请饬交涉》,湛江市档案馆藏,卷宗号1-2-1519-5。在如此艰难的生活状况下,当局依然决定对商人征收“门牌税”,以及在农村开征“人头税”,增加税收,[注]《(府字第3176号)为法国驻坡头营官殷多东率领卢文廷强抽人头税、枪杀民众请谨严交涉》,湛江市档案馆藏,卷宗号1-2-1519-6。自然引起了商人和农民的愤怒。
当地大宗族和商会开始联合起来,并成立“广州湾民众被逼自救会”,动员整个农村地区参与进来,农民抗税组织进入高潮期。[注]郑庆云:《坡头群众被逼自救会》,《湛江文史资料》第二辑,1984年,第110页。若仔细考察“自救会”的动员方式,却发现其基础依然脱离不开宗族。“自救会”实行的是分片动员方式,每一片区由最具有威望的宗族精英来动员族人。[注]李钦编:《吴川、坡头抗法风云录》,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69~70页。因此,各地的农民在宗族组织和民族情感的动员下,于1936年4月23日,一起向坡头公局大楼游行前进,拿起锄头、棍棒、刀叉等武器,并高举着大、小旗帜,上面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义务公役”等标语。[注]苏宪章:《坡头人民反法斗争始末》,《湛江文史资料》第二辑,1984年,第100页。
这场抗税斗争却遭到了法国殖民者的残酷镇压,“肆意枪杀李其福等五人”,[注]《(府字第2709号)为法人拟征人民身税,经民众赴坡头营官处请愿求免竟被枪杀求拯救》,湛江市档案馆藏,卷宗号1-2-1519-1。又继续对“自救会”成员和主要参与者进行大力搜捕。[注]《(府字第3579号)详陈法公使擅捕我国人民经过》,湛江市档案馆藏,卷宗号1-2-1519-7。于是,“自救会”以祖国同胞身份向国民政府发电请求援救:“我全湾同胞三十五万人口,惨受法帝国主义者铁蹄践踏。”[注]《(府字第3418号)详陈法公使戴士多无故将坡头博立村许善甫家产商业劫掠毁灭情形》,湛江市档案馆藏,卷宗号1-2-1519-6。在一系列电文中,“自救会”着重强调了这次抗税的集体行动是一场反抗殖民者的斗争。[注]《广州湾租界陈保等关于法人征收人头税、枪杀请愿群众要求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的报告》,1936年5-9月,湛江市档案馆藏,卷宗号1-2-1519。也正是在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交涉下,最后得到了法国当局的赔款。
在这次抗税斗争中,有五名村民被法国军警枪杀。事后,当地民众将他们以民族烈士身份下葬,其烈士墓及其碑志清晰地表达出一种民族主义的身份认同。广州湾商人和农民群体在殖民地管治中争取城市自主管理权与抗税斗争的一系列行为,都促进了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认同。
五、 政党革命与民族主义动员
(一) 早期革命实践及其失败
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认同感或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体系”,最终表现形式是“国家的一整套以政治体制为核心的制度”。[注]郑永年著:《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第142页。所以,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实现民族主义的制度化,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现代政党组织于是便成为了将民众组织起来建立新国家的最有力手段。
在地理位置上,广州湾属于广东南路地区,早期党团组织成员经常出入广州湾开展活动,且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创建于广州湾。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任命黄学增为南路特派员。在黄学增的组织领导下,南路各县市陆续建立起党团组织。1927年1月中共南路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黄学增被任命为南路地委书记,统一领导南路地区的党组织。[注]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35~38页。黄学增在1926年的实地调查中发现,法帝国主义在广州湾的殖民统治导致周边地区经济衰败,农民处于破产失业、沦为土匪或为娼的悲惨生活境地。[注]《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黄学增研究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页。因此,只有反法帝国主义才能拯救农民,它与农民运动实际上是一体的。但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亦波及南路地区,农民运动迅速凋零,之后的“武装暴动”也完全失败。
广州湾殖民当局与国民党政府达成抓捕和引渡南路地区的共产党员的协定。[注]《中共南路特委给省委的报告(第五号)——关于政治、党务、夏暴及各种会议情况》(1928年6月11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3,广州:广东省档案馆,1989年,第290页。1928年12月底,由于叛徒出卖,驻广州湾的南路特委机关遭到广州湾法国当局的破坏,“此后,南路特委一直未能恢复,南路地区各县党组织也随之相继停止活动”。[注]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5页。一位负责人在反思早期革命斗争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早年革命失败的关键原因是“着重播种,忽视生根”,党组织没有真正扎根于农民群众之中。[注]《对过去南路斗争的总结》,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南路农民运动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0页。南路特委屡次批评下级党组织不发动群众,且指挥混乱,与上级不进行沟通联络,反陷入孤立状态。[注]《中共南路特委关于茂名沙田暴动决议案》(1928年4月26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3,第222页。
(二) 宗族与政党动员的胜利
早期革命的连续失败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动员农民群众参与民族国家建设的革命实际上是一件困难巨大的事情。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动员农民的思维与策略。这种情况在抗战爆发后得到了极大的改变。
1937年冬,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广东省委通过各种途径,先后派遣南路籍党员回到家乡重建党组织,开展抗日活动。[注]《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四月来工作报告提纲》(1939年1月2日),中共湛江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编:《遂溪青抗会》,内部出版物,1988年,第34~38页。中共广东省委于1940年2月重新建立中共南路特委,统一领导南路各级党组织。在沦陷区和敌后根据地,南路党委主张把“民族问题与民生问题结合起来”,即既“广泛发动群众的武装抗日自卫斗争”,又同时“发动群众减租、减粮、减丁、减税等斗争”。[注]《关于南路问题的研究》(1946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9,广州:广东省档案馆,1989年,第19页。中共南路特委的日常动员策略取得了极大成就。抗战结束后,中共南路特委已经建立起一支“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并在距广州湾不到五十公里之处,建立起人口约20万的“人民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注]周楠:《我在中共南路特委工作期间(1939-1945)的几个片段回忆》,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南路人民抗日斗争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8页。
广州湾的乡村宗族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中起到了工具性的动员效果。正如后来中共南路党委在总结以往的革命动员经验时指出:
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入手,即使是封建关系也好,比方宗族关系,我们要搞某条村,就找和某村同姓同族的干部去接洽。…问题是通过上述各种关系深入下层,了解当地具体情况,根据群众要求,积极领导群众斗争,在或大或小的胜利的斗争中,积极去发展力量,壮大力量,并随时注意巩固和改造等工作。[注]《关于开辟新地区的经验总结》(1948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9,第469页。
革命者利用宗族关系进行革命动员的方式主要有三:一是动员同族中的同龄青年参与革命,因为同龄者关系较为密切,沟通较为容易,且青年人易受新思潮之影响;二是动员地方精英,如开明绅士、地主、宗族父老,透过地方精英来动员民众与获取革命资源;三是利用宗族内传统的组织与资源来进行革命活动,比如宗族小学、兄弟会、族产等。
广州湾麻斜村之革命动员正是涵盖了这三种方式。在广州湾益智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创,根据中共广州湾支部指示返回家乡麻斜村开展革命动员工作。张创返乡后,首先动员其伯父张斗文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中。[注]麻斜村委会:《麻斜志》,内部出版物,1996年,第44~45页。当时的张斗文就任麻斜公局长一职,在麻斜宗族中地位显耀。张斗文的女儿后来亦加入共产党,也积极说服她父亲保护共产党的革命工作。因此,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麻斜党支部动员张斗文建立起“白皮红心”两面政权。根据当时麻斜村一位革命者后来的回忆:
做过法国公局长和国民党保长的张斗文,他的女儿张雪英和地下党派来的人都做他工作,所以他对地下党的活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没有上层人物的掩护,麻斜地下党也是站不稳的。[注]“张本(86岁)口述记录”,湛江市霞山区,2014年11月8日。
麻斜村利用宗族的力量组织起抗日同心会和抗日联防保卫队,同时也有不少人在革命动员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路抗日部队。[注]《湛江市坡头区麻斜办麻斜村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史及证明材料》,内部材料,1989年。事实上,在广州湾的乡村中,抗日联防区的队伍常常是驻扎在村庄的宗祠,因为这是村庄共同活动的公共场所。[注]冻山:《南路解放区巡礼》(1946年2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9,第2~4页。
同样据广州湾东北部九有村的历史记载,从1945年开始,钟氏宗祠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据点。中共党员在宗祠里组织群众开会,宣传革命思想,此后建立了长期联络的秘密交通站。1946年后,九有村又在大宗内建立起小学,该村的党员钟志雄、钟亚邦等人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来进行革命活动。革命知识分子利用宗族关系来动员群众,并成功取得了宗族的资源支持,钟氏大宗甚至慷慨地将祖产贡献出来支援共产党的茂电部队。[注]根据2015年1月28日笔者对湛江市坡头区九有村的调研发现。
从麻斜村、九有村等个案可以看出,对宗族关系的利用不仅成为共产党革命动员的有力手段,同时也可以为自身革命活动提供保护网络。的确,对于地下党来说,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保护自身生存的重要因素。[注]黄道炫:《扎根:甘肃徽县的中共地下党》,《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因此,在广州湾的广大乡村中,宗族成为了反对国民党进村“清剿”、保护共产党的有力手段,“对于K的清乡屠杀,则以维持地方治安,维持宗族观念来反对K的借口清乡,实质进行奸淫劫掠,以消极的怠工、阻扰的方式反对”。[注]“K”即指国民党。参见温华:《关于粤桂边根据地的工作报告——粤桂边的形势和当前的方针》(1947年2月24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9,第37页。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已将广州湾主权收回并改名为“湛江市”,随之派郭寿华为湛江市第一任市长。[注]郭寿华:《湛江市志》,台北:大亚洲出版社,1972年,第2~3页。为控制地方社会与打压南路共产党组织,国民党采取了强征人丁充军和过度汲取税收资源等政策,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甚至有民众反过来对抗国民党。“就广州湾市民对征兵态度而言,一般认为K的‘坏政府’比日本仔坏得多,……如果是无办法被抽去打仗的时候,就走到红军那边来,一种想法是因为红军会优待给路费回家,另一种想法是可以掉转枪头痛快的来打蒋军一下。”[注]《二个半月以来国民党军政措施情况——蒋管区军政情况变化、党的组织工作》(1947年4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9,第71页。
由于国民党政权对基层社会资源过度汲取,导致官民矛盾激化,使得置身于官民之间的保甲长进退两难。[注]王奇生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35~436页。尤其是在宗族社会中,保甲长这种两难处境更加突显。当共产党利用宗族关系和以反“三征”的口号来动员时,不少保甲长往往会顾虑到宗族利益而愿意充当“两面派”,表面上敷衍国民党政权,暗中则支持共产党军队。加上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实行的“减租减息”和累进税的政策,也得到了乡村地主阶层和农民的支持。[注]南军:《南路人民当家作主》(1949年5月1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9,第600~601页。
从1947年开始,中共南路党组织决定在已经巩固的群众基础上,作出了“大搞武装斗争”的重大决策,建立了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对湛江市形成了包围之势。[注]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南路党史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7页。到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宣告成立。在野战军南下之前,粤桂边纵队几乎已经攻克雷州半岛各县区。最后在第四野战军的支援下,粤桂边纵队于12月19日攻陷湛江市区,至此,粤桂边区全境宣告解放。
广州湾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过程,说明了仅仅依凭反帝国主义宣传和阶级革命话语不足以动员农民,只有“采取契合农民心理的方法”才能动员农民参与革命。[注]齐小林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46~447页。尽管国共两党都志在建立民族国家,但是两者采取的是“精英民族主义”和“大众民族主义”的不同策略。[注]Zhao Suisheng,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7.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能够嵌入基层社会,将民众真正动员起来参与到革命中。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亦是国家导向的,普通民众被纳入到组织化的政党中,成为建立新国家的主要力量;旧的地方组织被利用与改造,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这种新的地方组织更强调权力集中,比以往的组织更加能将个人与国家紧密联结起来。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动员模式,并将在以后的大众生活中延续下去。
六、 结论与思考
殖民地广州湾经历了从边缘之地到融入大一统、从殖民统治到建设民族国家的历史变迁,可谓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也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变与常。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至少到明代以后,中央王朝利用政制设置、意识形态教化,地方社会通过宗族制、正统化民间信仰,共同将广州湾逐步整合到大一统体系中,地方社会形成了统一的国家认同,具备了稳固的宗族制社会结构基础。在遭遇外来殖民侵略和冲击时,正是这一国家认同和宗族力量为地方民众提供了反殖民抗争的文化和组织资源。中国共产党在重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也需要借助和改造宗族组织、人际关系和传统资源,将个人成功地动员加入到现代政党组织和民族革命事业中,才得以渗透进地方社会并取得最终胜利。
本文对殖民地广州湾历史的深入考察,有助于我们重新检视原生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范式。一方面,民族主义既非现代建构的全新产物,广州湾民族主义与传统的国家认同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性,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仅仅凭借革命者的建构,就可以短时间内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动员起来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不过也必须指出的是,前现代的国家认同也是在长时段历史中由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而逐渐形成的;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亦非一种天然或古老的事物,广州湾民族主义受到了殖民冲击、地方组织或政党动员的影响,而展现为变动和演进的过程。它既是反殖民主义,也是“国家建设”的民族主义(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最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
广州湾的个案也可以让我们理解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是如何在地方上形成与演进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分崩离析,曾经的殖民地也没有在帝国主义强制下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在许多有过殖民经历的后发国家中,其国境线有着“人为塑造”的痕迹,这些国家与“该地区从前存在过的政治实体,两者间几乎没有或者一点没有匹配之处”。[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406页。这种情况与历史上的殖民地划分密切相关,是被帝国霸权强制塑造的结果。广州湾的地方史表明,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虽然受西方殖民所刺激,但它受到过去历史的框限,并非是近代建构与想象的产物,也就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内容与形式,最终没有形成以西方政治经验为模型的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