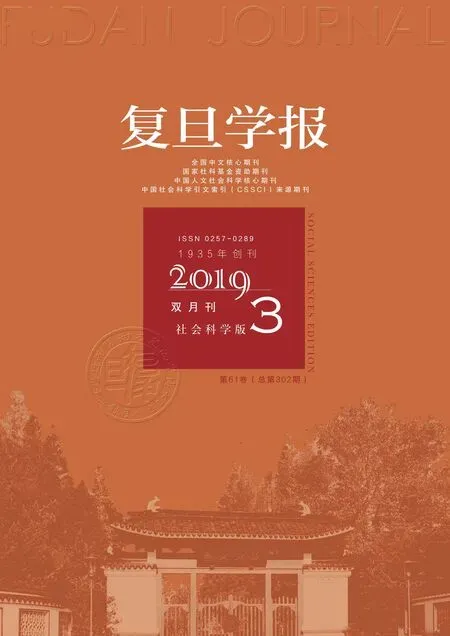法权论是否属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兼论康德在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区分
2019-03-25孙小玲
孙小玲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道德与政治总是互为纠缠,难解难分, 并因此常常难以避免彼此还原的倾向:要么道德被还原为政治,其结果是道德话语完全为司法正义和权利所统摄,对其他德性的追求被边缘化和私人化,这大致是现代西方面临的问题。要么是政治被道德化,被视为追求道德目的的手段,这事实上是仍然不时被怀恋的古典德治之本质所在。作为一个坚定的启蒙哲学家,康德坚决拒绝了后一种还原,并明确指出以政治强制的方式去实行道德的目的将同时败坏政治与道德(Rel,96)[注]本文中关于康德著作的引文均标注普鲁士科学院版的页码,《道德形而上学》标为(MS),《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则标为(Rel)。。但另一方面,康德也拒绝了道德的政治化。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伦理学著作《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最终构建了一种包容了自我发展和完善,以及对他人的仁慈的德性论,因而其德性论不只是正义义务的德性论,并因此区分于法权论。 由此,在《道德形而上学》中,道德学(Sittenlehre)被划分为法权论(Rechtslehre)和德性论(Tugendlehre)两个部分。由于康德的法权学说构成了其政治哲学的主体,而其德性论则可被视为康德伦理学或者狭义的道德学说的“最后赋形”,这一划分同时可以被视为康德在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区分。对于这一划分及其意义,学界一直有诸多争议。争议的一个焦点是:康德的法权论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归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就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传统解释而言,占有主导地位的是一种连续说,即认为法权论与德性论只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建构的道德原则与理念在不同实践领域中的应用。但是,部分地受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在道德与政治之间切割的影响,不少学者开始倾向于一种分离说,认为康德的法权论独立于其道德学说。显而易见的是,这一争论涉及的不仅有对康德的法哲学的理解,而且关涉到对康德道德学说的整体性把握。在本文中,我们将力图拒绝分离论的解释,支持一种关于法权与伦理的间接关系说,以维护康德道德学说的统一性。但是,与传统解释不同,我们的观点纳入了对法权所具有的不同于道德的特殊规定性的考虑,尊重康德在法权与伦理、从而也是在政治与道德之间所做的区分。我们的目的并非只是在两种解释中寻求一种折衷的可能性,而是借此澄清康德在法权与德性、从而也是在政治与道德之间作出区分的独特方式与意义。
(一)
在“德性论导论”开端,康德写道:“伦理学在古时候就意味着一般道德论,人们也将后者称义务的学说,后来人们觉得最好把这个名称只专用于道德论的一个部分,亦即转用于不服从外部法则的义务的学说上。这样,总的义务学说的体系现在就被划分为能够有外部法则的法权论(ius)和不能有外部法则的德性论(ethica)” (MS,379)。 显而易见的是,在法权与德性论之间的划分并不始于康德,而是已经包含于他所继承的古典自然法的伦理传统之中。[注]当然,康德与自然法传统的关系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在此无意介入这一复杂的争论。毋庸置疑的是,康德至少继承了自然法伦理学的基本形态,并与这一伦理传统一样强调法则与责任(义务),尽管康德确实对道德义务及其法则做出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传统自然法理论的解释。因为自然法具有法律的形式,所以,道德首先在与法律类比的意义上被视为道德法(moral law)所规定的义务;另一方面,自然法又被视为超越于所有成文法的道德法。因此,一切具有道德正当性的义务都可以被视为自然法规定的义务,即道德义务。无论其是否为成文法所规定,无论其是否可以被强制执行;也即是说,无论这些义务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政治)义务。由此,道德与法律就具有形态上的同构性,并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共享一套概念系统。[注]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导论第四节“道德形而上学的预备概念”中就提供了法权论与德性论共享的一套构成性范畴。但也正因此,如果承认道德与法权实践的差别,在德性与法权论之间作出区分也就有其必要性;并且这一区分只能是在道德的,即基于自然法的义务理论内部的区分。因为如同我们上面所指出,对于自然法的道德学说而言,义务就其为义务而言,亦即就其具有道德正当性而言,总已经是道德义务,也即是说,总已经是自然法所规定的义务,无论我们将其归入法权还是德性义务的范畴。就康德对这一传统的承继而言,即使在明确地区分法权与德性论之前,法权与德性的区分也可以被认为已经隐含在他的伦理思想之中,比如在为康德基本上接受的完全与非完全的义务的区分之中,因为前者一般被视为法权义务,后者则被视为德性义务。但是,只有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才明确地区分了法权与德性论。
康德首先从立法的角度区分了规定义务的法则和动机两个要素。就后者与法则的关系而言,法则可以使得义务成为动机,也可以使义务不成为动机,而是允许与义务理念不同的动机。前一种立法是伦理学的 (ethisch),其所规定的是德性义务;后者则是法学的 (juridisch)立法,与其对应的则是法权义务。由于与义务理念不同的动机只能是病理学意义的根据,并且因为法律并不依赖奖励,而是通过强制和惩罚而得以施行,所以这一病理性根据也就只能是受制于法律者的反感而非偏好。在之后对法权的进一步界说中,康德更为明确地表明,严格意义上的法权与强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与伦理立法不同, 法学立法必然地借助于外在的强制。这当然不是说这一强制一定构成履行法权义务的动机,我们当然可以伦理地,即以法权立法规定的义务为自己行为的动机。也正因此,所有的义务均可以间接或者直接地被归入伦理的范畴,也即是说,可以被视为内在立法的结果。所以,德性与法权义务的区分标准最终落实为是否可能有一种外在立法或者说正当的外在强制,只有完全不可能被外在强制的义务才是德性义务。康德因此认为对自己本身的义务,就其不可能被外在地强制而言,可以被适切地归给伦理学(MS, 220)。当然,一些外在的义务,即我对于他人的义务(比如我们通常所言的仁慈或助人的义务)也可以被视为德性义务,因为他人并没有权利强制我去帮助他。显然,按照这一区分标准,德性义务主要包括所有对自身的义务以及对他人的不完全的义务,而对他人完全的义务则多半可以被归结为法权义务。当然,这只是非常初步的区分,具体义务及其归属必须依赖于对法权与德性概念的更为详尽的界说。[注]在对德性义务的进一步界说时,康德从质料方面将德性义务界说为同时是目的的义务,但这一界说仍然与德性义务非外在强制性的规定一致,因为正如康德指出,目的不能被外在强制,并因此与任性的自由相容。所以,同时是目的的德性义务必然不能被外在强制。由于区分的关键在于是否可能有外在立法,而不是内在立法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审视的是康德对法权的界说。
值得注意的是,与近代权利论不同,康德对法权的规定所遵循的仍然是自然法的传统路径,即将法权与法则(此处是外在立法的法则及其规定的责任)相关联。这样,法权首先意味着法则所规定的正当,并且尽管外在立法可以是现实的立法,即实证的法则,也可以是自然法则,即在没有现实立法的情况下也能被理性先天地认识的法则,后者才是正当的最终来源。所以,我们首先应当“仅仅在理性”(MS, 230)的普遍规定性中确定行为正当性的法则。这一法则被表述为“任何一个行动,如果它,或者按照其准则每一个人任性的自由,都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就是正当的”(MS, 230)。在此,任性是一个人通过行动实现自己欲求目的的能力(自由)。所以,按照这一法则,不同个体的自由任性只有在可以彼此平等共存的情况下才构成正当的权利。康德进一步指出,这一法则界说的只是不同人格彼此相互影响的外在行动之间的关系,不包括我的任性与他人的愿望或者说需要的关系。换言之,我对他人帮助的需要并不构成我可以正当地强制他人的法权。同时被排除的还有内在的行为(动机), 也即是说,虽然法则要求我不得侵犯他人的正当权利,但并没有要求我将这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视为我行动的动机,后者是伦理而不是法权的要求。
但是,虽然给出了正当(法权)的形式规定,普遍性法则并没有提供法权的内容(质料),所以,在对法权的进一步界说中,康德首先确立了一种生而具有的法权,即平等的自由权利。依据这一权利,每个人在无损于他人同等权利的条件下就有权利做任何他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无需听命于他人任性的支配。这一权利是每个人“凭借自己的人性应当具有的法权”(MS, 237),不同于财产权这样的获得的法权,并且是后者之正当性证明的主要依据。生而具有的法权和获得的法权构成了私人法权,在康德看来,这一法权在公共法律与执法机制缺乏的自然状态下,只有临时的有效性,这就使得公共法权的建立具有必然性,乃至于是每个人的义务。康德的法权论因此主要由私人与公共法权构成。前者确立了他人可以正当地强制我的权利,包括这一权利赋予我的义务,即法权义务;后者则确立了这一权利能够获得保障的公共法律和执法机制,大致囊括了康德关于政府与政制的学说。
(二)
因为康德明确表明法权的普遍性法则是纯粹理性的先天法则,并因此将法权学说归入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即实践理性先天法则的体系,故传统解释一般都认为道德形而上学作为具体义务的学说可以被视为康德的道德法则(即其定言命令)之应用,德性与法权论的差别仅在于定言命令所应用的具体对象与范围的不同。鉴于法权法则与康德在《奠基》中给出的定言命令的普遍性公式之间形式上的相似性,[注]康德在其法权论导论中同时给出了一个具有命令式形式的法权的普遍法则,即“如此外在地行动,使你的任性的自由应用能够与任何人根据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MS, 231)。这一法则就其形式而言与《奠基》中道德定言命令的第一公式具有明显相似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康德随即指出,虽然这一法则赋予责任, 但是,与道德定言命令不同,法权法则不要求动机,也即是说不要求我们以此法则来规约自己行动的准则,正是后者界说了道德定言命令之道德性,同时也展示了意志普遍立法,即自律的可能性。这一解释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定言命令的抽象(即剥离其对动机的要求)与限制(即将其限制于任性的外在关系之中)推导出法权的普遍性公式,从而也就是推导出康德的法权概念。[注]比如Mary J.Gregor 就持有这一观点,参阅Laws of Freedom:A Study of Kant’s Method of Applying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in the Metaphysik der Sitten(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Oxford, 1963) 31, 35-36.
与此相反,伍德(Allen Wood)与维尔西克(Marcus Willaschek)等人则坚持法权论对于康德道德学说的独立性,并指出康德不仅无意从道德的定言命令去推导其法权的普遍化原则,而且也不可能在不依赖于法权概念之特殊规定的条件下做出这样的推导。并且,虽然有一种表面的相似性,法权的普遍性法则与道德的定言命令完全不同,后者必然地将对动机的要求包含于自身,因为正是这一要求界说了其道德性。与此不同,法权法则仅仅确立了外在行为的正当性标准,其所规定的与其说是我的义务,不如说是他人因为我的权利而必须承担的义务。用康德的说法,后者是“一般意志的法则”,而“不必然地被设想为我自己意志的法则” (MS, 389)。所以,维尔西克认为,在此所有的不只是不同的立法,而且是不同的法则,即使两者所规定的义务可能互相重叠。[注]Marcus Willaschek, “Why the Doctrine of Right Does Not Belong in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 On Some Basic Distinctions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Ethics5:205 (1997): 205-227, 210.与道德法则不同,康德的法权的普遍性法则旨在最大限度地保存每个人与他人可以相容的自由行动的权限,[注]博格认为外在自由最大化的目的解释了康德将法权限于外在行动、排除需求与动机要求的理由。Thomas W.Pogge, “Is Kant’s Rechtslehre a ‘Comprehensive Liberalism’,”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Interpretative Essays, ed. Mark Timm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3-158.其所要排除的是伤害他人权利的行为,而不是去规定人们应当做什么,但道德义务却必然包括积极的(比如帮助他人)义务。
但是,主张康德法权与道德法则之连续说的论者也不会否认法权与道德法则具有不同的功能与目的的事实,而是认为法权概念之道德规范性基于康德在《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的道德学说(即其定言命令与自律)的理念。所以,分离说必须显明我们无法由康德的道德学说导出其法权概念。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主张分离说的论者都集中在法权具有的外在强制性之上。按照康德的界说,法权不可以被设想为法则所规定的责任与强制的复合物,毋宁说严格的法权即是强制的权限。 换言之,强制在康德那儿是法权的构成性要素。但是,维尔西克认为我们恰恰无法基于康德的定言命令或自律理念去建构这一强制的合法性。[注]Marcus Willaschek, “Right and Coercion: Can Kant’s Conception of Right Be Derived from his Moral Theo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17:1 (2009): 49-70, 59-61.就康德的普遍性公式而言,准则无法被普遍化证明了该准则的不道德性,但却并不就证明法权强制的正当性,比如我答应某人校对他的翻译却违背了诺言,我的行为准则显然不能通过普遍性法则的测试,但这并不构成法律强制的充分理由,除非我为此与某人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显然,如果法权的强制性仅仅基于道德法则,那么一切违背承诺的行为都应当受到法律的强制,因为并没有在它们之间做出区分的道德理由。与此相同,我们同样无法诉求于道德自律的理念去证明法权强制的正当性,因为如果自律所指的是个体意志的内在立法能力,那么外在强制既不能促进也不能减损我们的自律。所以,维尔西克认为与道德强制不同,法权或者司法强制的根据并不在定言命令之中,而毋宁说是基于法权自身特有的规定性以及人类共存的经验事实。
由于彼此共存之必不可免性,我具有某种权利意味着对他人自由的相应的限制,反之也如此。所以,法权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交互的强制性,并且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所有的权利要求都是同等有效的。正如康德认为,“通过单方面的意志不能强加给他人一种他们自身通常不具有的责任”(MS, 264)。按照弗利克舒(Katrin Flikschuh)的解释,这意味着只有一个不可能被卷入具体法权纠纷的意志,即公意或者说统一的意志(united will)才有权利颁布强制性的法律来限制每个人的自由。在现实中,只有一个国家中的主权意志才是立法意志。也正因此,自然状态中私人法权在康德那儿必然导向公共法权,即主权通过公共法律保障个体公民的权利。这是公民(政治)社会,在这样的公民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法权义务就在于对公共法律的遵从。当然,公民仍然具有在公共法律限制的范围内随自己的喜好做或者不做某些事情的自由,但这一自由却不是自律的自由,因为法则与强制并不源于我的纯粹意志,而是源于外在于我的公意。所以,与自律的内在立法不同,外在立法是非自律的,并因此界说了一个截然不同于自律(道德)领域的法权领域。[注]Katrin Flikschuh, “Justice without Virtue,”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A Critical Guide, ed. Lara Den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1-70, 63-64.
当然,自律及其支持的人性的尊严确实提供了我们尊重他人法权的道德动机,但正如伍德指出,法权法则却不依赖于这一道德的动机,[注]Allen 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Interpretative Essays, ed. Mark Timm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1, 8.并且康德的法权说不仅在动机上,而且在规范意义上同样独立于其道德说。换言之,我们不仅不能由其道德定言命令推导出法权法则与法权概念,而且后者并不需要预设康德的道德原则与自律的理念。就此而言,正如博格(Thomas W.Pogge)借用罗尔斯的术语所说的那样,康德的法权(因而也是他的政治学说)是独立自存的(free-standing),其所基于的并非纯粹理性,而是人们的外在自由的利益(interest)。由此,法权论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以一种可预测和恒定的方式限制每个人自由、并借此保证每个人合法自由的有效的公共法律体系,这一体系构成了康德的公共法权。但是,博格进一步指出,这一法权体系并不需要预设康德的道德学说,因为我们可以同样在霍布斯对和平的追求中找到建构这样一个法权体系的根据。从实践上说,正如康德自己也承认的,尽管出于不同的动机,理性的魔鬼与有德性的人同样可以构建并维持这样一个法权体系。[注]Thomas W.Pogge, “Is Kant’s Rechtslehre a ‘Comprehensive Liberalism’,” p.149.对于博格与其他分离论者来说,这也解释了康德从其严格的法权概念中排除一切伦理要素的理由,以及他对立法主权与政府强制力的强调。也正因此,康德一以贯之地反对以道德的理由推翻政府的行动,即使在政府严重地侵犯到个体权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在分离论者看来,传统解释完全忽视了康德在法权与伦理之间的区分,其结果必然使得个体的权利要求的实现依赖于他人的道德意愿,使得法权(政治)消融于道德之中。另一方面,伍德指出,这一法权与伦理之间的混淆也导致了对康德道德学说的误解,因为康德的道德义务虽然就其内容来说可能具有社会导向,但却完全是关于受到启蒙的个体自律地规范自己生活的学说。[注]Allen 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pp.9-10.与伍德相似,弗利克舒也强调了公共的法权领域与私人的道德领域之间的区别,并认为自律只适合私人的领域。[注]Katrin Flikschuh, “Justice without Virtue,” p.60.当然,分离论者也承认康德确实试图维持法权与德性之间的关系,并因此将法权论归入其道德学说,以确立一种法权的形而上学。但在博格看来, 由于关乎我们外在自由的法权不可剥离的经验性,法权的先天原则不仅无法设想,也是完全空洞与无效的。[注]Thomas W.Pogge, “Is Kant’s Rechtslehre a ‘Comprehensive Liberalism’,” p.147.
(三)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分离论解释成立,那么,正如维尔西克断言,康德就没有理由将法权论归入道德形而上学(即理性的先天法则的体系)。因为对于分离论者来说,法权所关涉的只是现实的法律及其规定的权利,而康德的法权论, 正如博格指出,也只是对现存法律的建构与维系的反思,尽管有抽象性却无先验性。[注]ibid., p.140.但是,在康德看来,一种纯然经验的,即在纯粹理性中没有基础的法权论只能是“斐德鲁斯寓言中的没有脑子的头颅”(MS, 230)。除此之外,分离说主张的公共与私人领域的截然区分也必然使得道德完全被推入私人领域,其所关乎的仅是个体内在的行动。这在波特(Nelson Potter)看来,必将导致一种道德的怀疑主义,与康德道德哲学的意向相背离。[注]Nelson Potter, “Kant on Obligation and Motivation in Law and Ethics,”Jarbuch für Recht und Ethik2 (1994): 95-111, 104.
尽管如此,通过对法权概念在康德法权论中核心地位的强调,分离论者确实有效地拒绝了传统解释,尤其是其所主张的推导论。诚如分离论者所见,无论在《奠基》还是《实践理性批判》中,定言命令都是规定准则(而不只是行动)的法则,其道德性依赖于对动机的要求,所以,剥离这一动机要求就意味着对其道德性的至少是部分的剥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能够推导出法权法则,推导的起点也已经不是传统解释所宣称的道德的定言命令。诚然,康德在《奠基》中已经借助道德命令区分了合法则性与合道德性。按照这一区分,如果一个行为仅仅合乎义务,而不是从义务出发,即完全以义务为动机,则该行为只有合法性而无道德性(价值)。但是, “合法性”在此仅仅描述了道德性(动机)的缺失。换言之,合法性只是对道德性的否定性规定,我们不可能从中推出一个具有自身肯定意义的法权领域。这进一步表明:只有引入法权概念,一种法权的形而上学的构建才有可能。
正如分离论者所见,法权概念不能完全与法权经验相分离,因为外在自由运作的领域是现象的领域。事实上,康德也不否认这一点,并在法权论的序言中表明,“法权概念是一个纯粹的、 建立在实践(出现于经验中的事例上的运用)上面的概念,因而一个法权形而上学体系在其划分上也必须考虑那些事例的经验性的多样性,…… 但对经验性的东西进行划分的完备性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的唯一恰当的表述就是法权论的形而上学的初始根据,因为鉴于运用的那些事例,能够指望的只是接近体系,而不是体系本身” (MS, 205)。[注]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将其德性论也称为德性形而上学的初始根据。就此而言,道德形而上学——无论法权还是德性论——都不是纯形式的道德论,而是形式与质料相勾连的道德学说。同时,也正是在与其经验面的关联中,法权特有的外在强制性才是可理解的。就此而言,分离论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抓住了康德划分法权与伦理之关键,因为正是法权具有的外在的强制性使之区分于伦理学。但这并不就使得伦理学因此被封闭于内在性的领域,因为我们总是可能伦理地,即自由地去履行法权义务,并赋予法权义务一种伦理道德性,尽管这并没有使得法权义务变成伦理(德性)义务。换言之,义务在康德那儿具有一种伦理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义务基于的是纯粹理性(意志)的法则所规定的正当性,而不是任性的需要或者利益。也正因此,在康德那儿,法权(权利)首先由纯粹理性的先天法则而获得规定,生而具有的法权也已经是基于法权的普遍性法则的权利,而不是不受任何法则限制的自由。
事实上,分离说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种对康德法权论的霍布斯式的解读。这一解读暗中引入了霍布斯在法律(lex)与权利(ius)之间的区分,[注]参阅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第98页。由于确立了权利对于法则及其规定的义务的优先性,这一区分颠覆了自然法传统——在这一传统中权利首先由义务(法则)获得其界说,并因此开启了在近代政治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权利论传统。另一方面,霍布斯在法与权利之间的切割消解了权利基于自然法的道德性。在霍布斯之后,洛克一方面认可权利的优先性,发展了权利论的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则重新将权利与自然法相关联,从而赋予权利以道德性。康德的法权论在某种意义上以更为精致的方式继续了洛克的努力。权利由此被等同为个体在自然状态下所具有的不受任何法则限制与规范的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法的规范性则来自对各种互相冲突的个体权利的限制和保障。因为外在自由(权利)自身不具有道德性,对其的规范只能来自于个体之外的法律与立法意志,所以,法律只能被视为纯然外在的强制,而截然分离于依赖于内在强制的道德。与此相应,外在与内在自由也完全被分离。也正因此,弗利克舒认为与其道德哲学不同,在康德的法权论中,任性与意志并不联结于一个人格中,毋宁说立法意志被置于外在于行动者的公意,即主权意志之中,与任性处于一种完全外在的关系中。所以,个体公民不仅不是立法者,甚至不是立法的参与者,而仅仅是受制于法律者(law-receptive citizen)。[注]Katrin Flikschuh, “Justice without Virtue,” p. 68.博格也认为康德的法权论只涉及外在行动的自由,与(道德的)内在自由无关。
基于这一对法权的外在强制性的理解,分离说大多倾向于对康德的法权论的实证主义解读,将法权与严格的狭义法权混为一谈。由于狭义法权被界说为清除了一切道德要素的法权,法权的有效性就完全依赖于外在的强制机制,即一个能够强制的政府,而非法律规定的正当性。法律也因此被等同为实证法律,即某个政治国家的立法,其合理性根据也仅在于该国家的立法意志。对这一法律的合法性的质疑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实存法之外的法律,或者即使有自然法,对外在自由的纯然道德约束在缺乏国家强制力的情况下也没有真正效力。[注]比如霍布斯虽然承认自然法永存,但认为自然法在自然状态或者说在国家强制力缺失的情况下完全无效,其结果必然是自然法及其所基于的非工具性(即纯粹)理性在政治领域完全不起作用。这一对康德法权论的法律实证主义读解完全取消了康德法权论中包含的自然法的规范意义,同时也忽视了康德在法权与严格(狭义)法权之间的区分。与后者,即实证法权不同,前者之正当性源于纯粹理性的法则。这一法则也界说了(正当)权利,公共法权(法律)只有在保障这些权利的时候才具有正当性。所以,正如康德明确指出,即使“可以设想一种全然包含实证的法则的外在立法。也必须有一种自然的法则先行,为立法者的权威提供根据” (MS,224)。
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确实可以在康德的法权学说中见到一些霍布斯的影响,[注]这一影响明显地见于康德对狭义法权,即消除了所有道德要素的法权的界说之中,并且康德始终没有在狭义法权与作为正当的法权之间作出清晰的区分。同时,康德对国家权力的过分强调也明显地表现了霍布斯的影响,这解释了康德何以一以贯之地反对对侵犯权利的政府的反抗。就此而言,对康德的法权论的霍布斯解读并非不能在康德那儿找到某些根据。某种意义上康德的法权论融合了古典自然法和霍布斯所开启的近代权利论的契约论,前者通过法权的普遍法则提供了法权的形式,后者则提供了法权的质料要素。但是,为康德所承纳的更多的是洛克以及卢梭而非霍布斯的契约理论,后两者都在权利与权力之间,从而也是在自由与为所欲为的任意性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注]参阅洛克:《政府论》(下),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第4页;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8~9页。康德则进一步回溯到自然法,即纯粹理性的法则以界说这一区分的基础,并最终落实于个体生而具有的权利。所以,生而具有的权利在自身中已经结合了自然(理性)法与契约论的权利概念。就其与前者,即与先天法则的关系而言,它是被纯粹理性法则规定的正当,并因此属于广义的道德范畴。就其与后者的关系而言,生而具有的权利是“每一个人由其人性而具有的原初权利”,这一权利构成了外在强制的正当性基础。换言之,政治强制的正当性并不基于任性的意志,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体的任性,而是基于生而具有的权利以及可以由其获得证明的其他权利。只有当这些权利受到事实而不是假想的侵犯的时候,政治的强制才是正当的。所以,康德法权论的核心乃是生而具有的权利。这一原初权利,而不只是纯形式的法权的普遍性法则构成了其他一切权利,从而也是康德的法权论的基础。同时,也正是这一生而具有的权利在自身中承载了法权与伦理的关联,因为只有作为普遍立法者,即作为可能自律的存在者,每个人才应当被视为具有平等权利的道德人格。就此而言,道德自律提供了道德人格的基础,法权论所界说的则是平等的道德人格之间的外在关系。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外在自由理解为没有道德意义的为所欲为的(自然)权利,那么,我们将没有理由去尊重他人的平等的权利。[注]所以,并不奇怪的是在将法权视同为外在自由的利益(interest)之后,博格不得不承认康德的法权的普遍性法则并不包含平等的自由权利,也即是说并不能界说康德的生而具有的权利。参阅Thomas W.Pogge, “Is Kant’s Rechtslehre a ‘Comprehensive Liberalism’,” pp.153-156.进一步而言,这一没有道德意义的权利也只能导向没有道德意义的纯然强制性的法律。就此而言,分离说事实上通过取消法权的道德性而达成了法权与伦理,从而也是政治与道德的分离,而康德将法权论置于道德形而上学之中则在事实上肯定了法权的道德性——当然是在区分法权与伦理的前提之下。但是,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指出,对于康德来说,法权与德性论之间的区分是在其道德学说,恰切地说在道德形而上学范畴内部的区分。因为无论是法权还是德性义务,就其所具有的正当性而言,都是纯粹理性法则规定的义务。在这一点上,康德继续了自然法的传统。另一方面,纯粹理性法则在康德那里又被视为(纯粹)意志的普遍立法,即自律的结果,所以,道德最终被归基于自由。当然,自由在康德那儿决非不受法则限制的任意性,而已经是法则,最终是内在于我们的理性的法则所规定与限定的自由。也正因此,唯有通过法则我们才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自由性。所以,伦理的内在自由与法权的外在自由(权利),就其为自由的不同形态而言, 都已经在自身中指向纯粹理性的法则,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注]外在自由在否定意义上可以被界说为不受(尤其他人)阻碍而追求自己目的的自由,但在肯定意义上则已经是被法则——当然是法权法则规范的自由,故而已经是个规范概念,并在此意义上可以被视同为权利。分离论的一个错误是将康德的外在自由视为纯然否定的概念,但在康德那儿,自由作为原因性一开始就被界说为合法则性。换言之,不受任何法则的为所欲为在康德看来并非自由,而是自由的反面。唯其如此,康德可以将法权与德性论都纳入其道德形而上学,即先天法则的体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同推导论所设想的那样,法权(外在自由)的法则是道德定言命令的推导物,康德自己就明确拒绝了从定言命令推导出法权法则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因为法则是纯粹理性在不同经验领域的运用的结果。换言之,只有作为自身特有的对象域的构成性(先天)要素,法则才具有有效性,才可以被适切地称为法权或伦理的法则,而道德形而上学也正因此可以被界说为由不同的先天法则构成的体系。事实上,推导论假设了一种完全脱离人类经验的法则,对于这一法则而言,无论法权还是德性法则都只是其衍生物。但无论康德在《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是否暗示了这样一种与人类生存状况与条件完全无关的道德法则,[注]这一直是康德学界争议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康德在《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对纯粹(实践)理性法则的构建,尤其是康德对作为特殊的,即感性的理性存在者的人之经验层面的排除或者悬搁的意义和功能。我们在此无法展开这一复杂问题。但是,与罗尔斯一样,笔者也不相信人们在世界上的社会状况在康德的道德理论中没有什么作用。参阅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第202页。《道德形而上学》关心的首先是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因为只有对人的经验的不同面相来说,法权与德性领域的联系与区分才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如果说分离论错解了康德对法权与伦理的分离,传统解释则错解了两者的联系。其结果是:前者完全割裂了法权与伦理的关系,并因此导向了一种没有道德性的法和法权; 后者则不可避免地将法权从属于伦理,抹杀了康德在法权与德性,从而也是在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区分。
(四)
在《法权论何以不属于道德形而上学?》一文中,维尔西克认为,法权与伦理的划分是康德以《道德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后期思想中最为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不失为一种公允的评价,尽管我们并不必如他那样将这一划分看作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滑铁卢,以至于只有将法权论“驱逐”出去才可能解救其道德形而上学。究其因由,这一在法权与伦理之间的划分之所以异常复杂,不仅由于其关涉到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概念从《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到《道德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后期作品之间的微妙的变化,而且更多地可被归因于这一划分所具有的政治与道德的双重意向。就前者而言,康德秉承了现代政治哲学的现实主义的视角,并致力于阐释一种至少相对地独立于道德的政治哲学。对于康德来说,虽然人是可能自律的存在者,并因此而应当被赋予其应有的尊严与平等的自由权,但人并不是纯然理性的存在者, 其自然秉性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可能阻抗理性法则的要素。所以,对基于人性的法权的保障就必须依赖于国家(公共法律)的外在强制,而不能仅仅诉求于个体的德性。事实上,在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法律缺失的情况下,不仅个体权利难以获得保障,而且人们之间必要的社会合作也难以维持,这解释了康德何以强调公共法权的必要性以及狭义(实证)法权内涵的强制性。在这一点上,康德与作为现代政治哲学典范的古典契约论一脉相承。与古典契约论相似,康德同样强调平等的个体权利在政治建构中的核心地位,并主张以法治取代德治以确保平等的个体自由权利不受侵犯。在康德看来,这不仅因为德治缺乏政治要求的现实性,而且也因为政治所特有的强制性可能剥夺个体德性形成所要求的自由:对于康德来说,只有自由的行动才可能具有真正的道德性,唯其如此,道德才可以被归基为自由与自律。
换言之,康德在政治与道德之间作出区分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维护政治相对的独立性,同时也是为了保存道德特有的自由性,也即是说为了阐释一种自由的伦理学,这一伦理学,即康德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构建的德性论所要展示的是个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自由地完善自身德性,实现人所特有的道德使命的可能性。当然,德性的形成与完善仍然要求某种强制,但其所依赖的只能是与自由的任性相容的自我强制,而不是政治的外在强制。所以,法权与德性论的区分在康德那儿同时、甚至说在更深的意义上为了在其伦理学说中排除政治的外在强制,以便开出一个个体可以自由地获得自己完善的理论空间,故而已经是具有道德意向的划分。也正因此,康德又借助于自然法传统将法权论——至少就其具有的先天原则而言——包容于广义的道德学说之中。就此而言,这一划分应当被视为法权与德性论,而不是法权(政治)与广义的道德的区分。通过这一划分,康德确实拒绝了政治的道德化,但并不因此而取消政治的道德性。事实上,正如维尔西克承认, 虽然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公民德性,而仅仅依赖于国家强制力的法权在逻辑上是可以设想的,但在经验上却并不可行,并且必然会导向集权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注]Marcus Willaschek, “Right and Coercion: Can Kant’s Conception of Right Be Derived from His Moral Theory?”, pp.57-58.换言之,理智的恶魔或许可以设计一个保障平等权利的公共法律体系,却无法维持之。更何况每个道德的行动者同时又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所以公共与私人、道德与政治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这并不否认政治所具有的独立性与重要性。在一个没有政治公正的体制中,在一个个体权利完全不能获得保障的社会中,其他德性是否能够独存与繁盛也是个问题。但是,政治不能取代道德,也不能提供自身的道德保障。所以,问题是在不彼此还原的条件下,找到贯连政治与道德的方式。康德通过综合传统自然法与近代契约理论在法权与德性之间的划分至少为此提供了一个哪怕并非完美无暇的范例,并将启迪我们对政治与道德关系作出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