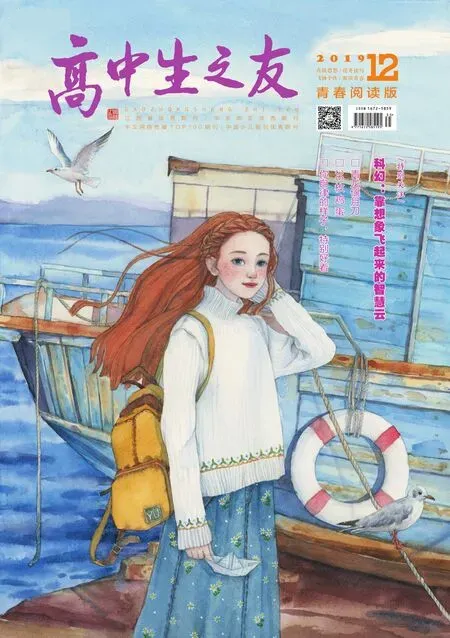与无以名状的虚无对抗
2019-03-25蒋方舟
○蒋方舟
如果不虚无带来的是痛苦,那就把痛苦当作人类的特权。
前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向我分享他看病的经历,他说做核磁共振之前,需要仔细检查身上有没有金属移植物,一看清单,有30多条。他说:“你不会因为戴了耳钉而觉得丧失了0.4%的自我。”
但是如果你的听骨、耳蜗、关节、神经刺激器全是人工的,你会对自我的完整性产生一点儿疑惑吗?
我对朋友说:“这简直像人形的忒修斯之船。”
“忒修斯之船”是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一艘船在大海上航行多年,为了让这艘船不沉,船员就会不停地更换已经腐坏的零件与木板,当所有的零件都被换完了,这艘船还是原来的船吗?
这个命题如果用在一艘船上,有几分思辨的趣味,但如果用在人身上,就有几分“细思恐极”的意味:生命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被人造的?而当我们从外到内不断被人工所替代,我们还是自己吗?
文学家也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主题。
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石黑一雄,在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近10年之后创作了小说《别让我走》。小说中最让人唏嘘的一段,就是克隆人凯西与汤米以相爱为由,试图争取延长他们将器官捐赠给正常人的期限,同时,汤米试图以自己创作的艺术品来说服昔日的学校教师,让其相信他们具有独立且崇高的人格。但他们的努力遭到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因为克隆人不是人,低人一等,所以他们并不拥有生物公民权。
《别让我走》提出了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生命的价值是否均等?谁来决定生命的价值排序?不完美的生命可否被抛弃?而将这些问题往前推进,它们则变得更难以回答:何以为人?何以为生命?何以为生命的意义?
我们生活的世界曾经充满了目的和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下雨、打雷这些自然现象都服从于某些特定的功能,比如他以“大自然厌恶真空”来解释气压。后来,伟大的牛顿让我们认识到自然并没有那么神秘,气压由力学决定,而非因为大自然的情绪。我们身处的自然像上好发条的钟表一样机械运转。自然有法则,却失去了目的,将目的和意义带入自然的是一厢情愿的人类。
在发现自然的规律之后,人把自己从自然的秩序中脱嵌出来,认为人类是不同的,笛卡尔说“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
这种自满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意识到人类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类并没有逃出法则的掌控。
人类因为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独特,没有想象中神秘,甚至没有想象中自由,所以感到了一种价值感的危机。
我们无法按照机械那样彻底程式化地运转下去,这是人所栖居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属性。但是当我们把人看成一个生物学、化学意义上的造物,我们就发现自己好像在认识自己的同时也不认识自己了,在活着的时候感觉不到在活着,在说服自己生命是有意义的同时又忍不住嘲笑和怀疑这种意义。
对这种精神状态的描述,最精彩和深入人心的莫过于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小说中的萨宾娜是一个习惯了否定、习惯了怀疑的人。她否定“刻奇(一种自我感动的情感)”,否定抒情,否定集体,否定浪漫,最后否定了一切意义。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写道:“在科学与技术领域实现了许多奇迹之后,这个‘主人和所有者’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拥有任何东西,而且既非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渐渐撤离地球),也非历史的主人(他把握不了历史),也非他自己的主人(他被灵魂中那些非理性力量引导着)。可是,既然上帝走了,既然人也不再是主人,那么谁是主人?地球在没有任何主人的情况下在虚空中前进。这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对于生活的预言。米兰·昆德拉笔下的“虚空”——或者说“虚无”,是我近几年最常遇到的一种精神状态,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宣称自己是“虚无主义者”。
我试图拆解“虚无”背后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虚无?
虚无经常是无力感的产物。当每天的无力感摧毁了道德体系,便滋生了一种懒惰:懒得取舍,懒得判断,懒得声援,懒得讨论,懒得关注。
为什么会虚无?
因为虚无会显得聪明。无论是离我们很近的新闻,还是离我们很远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只要是押宝,就有押错的风险。总有“过来人”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真心去参与、去支持,因为历史一定会打你耳光,一定会开你玩笑。只要永远不投入真情实感,就可以永远不犯错。
为什么会虚无?
因为一种不虚无的生活让我们痛苦。关心他人的生活让我们痛苦,共情他人的痛苦让我们痛苦;知道一些但不能知道全部让我们痛苦,知道全部但无法判断是非让我们痛苦,明白是非却无能为力让我们痛苦。于是一些人选择把双耳调到听不到痛苦的频率,给双眼加上蔷薇色的滤镜,只看那些让自己舒适的信息,追求享乐——即便那“快乐”是渺小和粗鄙的,相信“幸福”——即便那“幸福”是脆弱的假象。

最后再从生活说回科幻吧,一些脍炙人口的科幻作品,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即人与机器的模糊界限是双向的:当“复制人”“人造人”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时候,人类却都变得越来越像机器。
这些科幻里,人类作为“忒修斯之船”,不断更换掉自己的木板,这些木板是纯真,是正义,是好奇,是勇敢,是相信的能力,是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
机器敏感如人类,人类却麻木如机器。
如果希望科幻中的反乌托邦寓言不成真,我们就应该保持人之为人的一致与本真。更真诚地活着,更充分地活着,更不虚无地活着。如果不虚无带来的是痛苦,那就把痛苦当作人类的特权。
(有删改)
编辑手记
这场演讲的亮点在于它的层进性、延展性和深刻性。演讲者从耳钉引发的“忒修斯之船”疑问开始,一步一步地深入探索,并逐渐把话题引入演讲的核心——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虚无之感的反思。整个演讲过程的引入、过渡和收束都紧密相连,从而形成一条完整的思考链,牵引着听众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