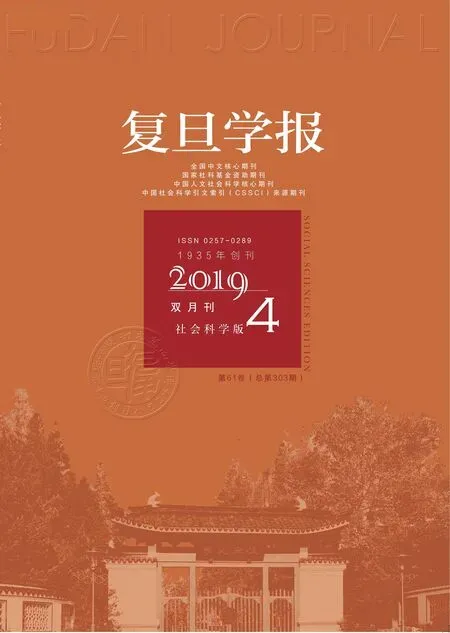语言是逻辑的本能:黑格尔语言观再思考
2019-03-24李钧
李 钧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两百年来的黑格尔研究对语言问题涉及相对较少。近几十年来,英美分析哲学由于自身的语言哲学传统,对黑格尔思想中的语言问题产生了兴趣,引发了这个论题线索的显明,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也有很大深入探讨的空间。
一、 关于黑格尔语言观讨论的状况和问题
英美分析哲学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关注黑格尔的语言问题,他们在其中寻找与英美语言哲学中真理问题看法契合和一致的地方,关注黑格尔关于语言中概念、命题、判断和推理的理论,也关注黑格尔如何用语言来达到他的系统的哲学即客观的真理的方式。这些研究,取用黑格尔的思想资源,助推了英美语言哲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引起人们对于黑格尔以及整个德国哲学传统中语言观的重视。比如加州洛杉矶大学教授麦克卡姆伯(John Maccumber)认为黑格尔的语言观念是可以满足思想和真理的思考,他宣称:“我将证明,黑格尔是一位语言哲学家:是罗蒂说的‘语言学转向’的第一个主要哲学家。像维特根斯坦、摩尔和奥斯丁——实际上,像卡尔纳普、罗素和奎因——黑格尔认为所有的哲学问题是语言问题。它们都可以得到解决,要么通过改革语言,要么通过更好地理解语言。所谓‘更好地理解语言’,我的意思是他认为语言有改革自己的能力:他哲学的目标就是语言的理性提升……”①Maccumber, John, The Company of Words: Hegel, Language and Systematic Philosoph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3)20.
这条线索甚至因此把语言哲学的线索越过所谓的“语言哲学之父”弗雷格往前推进。丹佛大学哲学教授舍伯(Jere O’Neill Surber)对整个德国观念论传统中语言的问题都因此加以强调,他说“德国观念论哲学家不是简单的‘对于语言持天真态度’”,“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有一场‘原初的语言转向’”。以黑格尔为核心的这个“语言转向”的团队包括谢林、费希特,作为浪漫主义者的施莱格尔兄弟、伯恩哈迪(A.F.Bernhardi),以及赫尔德尔、雅各比、哈曼、康德及其后继者,还有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等。②Suber, J.O.ed, Hegel and Languag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1-2.参与这种重构的还有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斯特(M.N.Forster),他编写了两本著作来重构弗雷格之前的英美语言哲学之源,[注]参见Foster, M.N., After Herder: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German Tra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以及Foster, M.N., Germ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rom Schlegel to Hegel and Beyond (Oxford University, 2011).重点关注黑格尔、赫尔德尔、施莱格尔、洪堡等思想家的语言哲学思想。
当他们的成果引起对于黑格尔语言观的关注以后,人们看到,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了黑格尔的语言观,甚至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就已经出现了两本专著:西蒙(Josef Simon)早年的博士论文《黑格尔的语言问题》和波达默尔(Theodor Bodammer)的《黑格尔语言的意义》。[注]参见Simon,Josef, Das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Hegel (Stuttgart: Kohlhammer Verlag,1966). 以及Bodammer,T., Hegels Deutung der Sprach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69).两者都秉持黑格尔把语言当作精神的定在的观念,前者纵论精神发展的几个大环节如对象性、主观性和主客观性中语言的作用和内涵,后者则阐述了黑格尔思想中语言与法权、历史、教化、逻辑、诗、宗教的关系。德国的研究波及英美,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库克(D.J.Cook)在60年代中期也做了关于此论题的博士论文《黑格尔哲学中的语言》[注]参见Cook, D.J., Language In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Mouton & Co.N.V., Publishers, 1973.。他比较重视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在早期文本包括耶拿时期的文本中爬梳材料,在各种论述中寻找语言思考,并阐发其与个体意识、集体意识和绝对精神的论述的关系。这些论著并没有过多地进行自身理论的建构或为自身理论服务,而是更多忠实于对黑格尔语言理论的阐释,对于发掘黑格尔思想中语言观的深度意义有不少贡献。
伴随着研究的进行,一些对人文思想有较大影响的观点也逐渐出现,可惜这些主要是负面的评价。这些观点认为黑格尔的语言观念是有缺陷的,黑格尔不重视语言,因为他要建构的思想是“科学”,是系统性的逻辑思想或者形而上学。相比之下,自然语言是要被超越的。哲学阐释学创始人伽达默尔同时是著名的黑格尔研究者,他于20世纪70年代在其著名的“黑格尔五论”中指出,尽管黑格尔看到了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但是仍然发扬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各斯传统,欲在自然语言中抽取确定而清晰的逻辑结构,以求描述语言之外的“逻辑实在”。他指出:“这项工作无异于谋求在思想中重建在上帝在创世之前的思想——即某种在逻辑上先于实在的实在。”但是,“确然存在于语言之中的’逻辑本能’,……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因此,它也永远不可能通过向逻辑的转化而真正地提高到他的概念。”[注]吕志伟译:《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126、128页。按,伽氏提到的语言的“逻辑本能”,来自黑格尔《大逻辑》第二版序言:“语言……渗透了人使其成为自己的东西的一切;而人用以造成语言和在语言中所表现的东西,无论较为隐蔽、较为混杂或已经很明显,总包含着一个范畴;逻辑的东西对人是那么自然,或者不如说它就是人的特有本性自身。”见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8页。因此,伽达默尔对于黑格尔的语言观是持批评态度的。和海德格尔一样,他倾向于认为语言的内涵比逻辑丰富,所以应该在自然语言对于世界的关系中去理解世界。
这种观念到了法国德里达那里,就变得异常鲜明了。德里达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黑格尔语言观的批判上,在其早期论文《矿井与金字塔》里,他把黑格尔塑造成一个本质主义者。他说,在黑格尔那里,“符号被看做某物或者以某物为基础,以在直观中被看到东西为基础……符号的理论奠基于表现的理论”。因此,符号只是一个充足表现者的替代品,书写(符号)次于声音(表现)。德里达认为,“黑格尔有兴趣于语言‘只是在于把语言看做智力要显现自己的理念于外部中介的意义上的产物’。他并不研究语言本身”[注]Derrida, Jacques,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 Alan Bass (The Harvester Press, 1982)72, 90.。显然,德里达欲以书写来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路,这和伽达默尔走向海德格尔的“通向语言之路”如出一辙。这条线索,大体说来,是把黑格尔的思想看作两分,并且认为黑格尔倾向于抛弃语言而走向逻辑,因此,反对黑格尔的语言观,意图抛弃逻辑,回到语言。
我们看到,尽管对于黑格尔语言观已有不少学理性研究,这种流传甚广的批判仍然出现也是不无道理的。原因就在于,一般的研究,都基本承认黑格尔哲学中有语言与逻辑的两分、艺术和宗教与哲学的两分;都基本承认黑格尔在努力使日常语言上升到哲学语言直至超越语言,逻辑是语言的本性,语言终究要被逻辑改写。在这种研究前提下,语言相对于思想,总是不充分的。英美分析哲学的研究,终究服务于思维的改进;而其他的文本性研究,尽管努力发掘各文本中的闪光点,但基本上也最多把语言提高到平行于思想的高度。在这种总体价值定位下,要么语言消融于逻辑,要么语言就要反抗逻辑,因此,伽氏和德氏的看法有其合理性。
但是,黑格尔的思想是异常复杂的。尽管他的系统哲学表面上设置了这样一些阶级,但由于其基本范畴的涵义已有了深刻的变化,因此,不能仅凭范畴的名义即确定范畴的价值。比如,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认为语言的深度是逻辑,所以黑格尔最终是以逻辑来代换语言的。但他没有注意到,黑格尔语言中的“逻辑本能”发展出的“辩证逻辑”已经不像传统逻辑那样是对语言的抽象,而是深刻地浸染了语言的结构,恰恰体现了语言最本质的运动。它并没有抛弃语言而走向一个创世之前的世界,相反,黑格尔更多地使逻辑具有语言的运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使逻辑回到了语言。与其解释黑格尔逻辑是语言的本性这句话为逻辑超越语言,不如解释这句话为逻辑展示了语言的本性,甚至说语言是逻辑的本性,逻辑作为语言的自为存在就是语言,语言作为逻辑的自在存在就是逻辑,这本来也符合黑格尔相互转换的辩证法。
其实,也有研究者看到黑格尔语言观中语言具有覆盖逻辑的力量。早在20世纪上半叶,牛津观念论传统中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穆尔(G.R.G.Mure)在其名作《黑格尔逻辑学研究》中,为了引入黑格尔的逻辑学,专门写了一章(第一章)来论述黑格尔的语言问题,见解颇为深刻。
他认为,黑格尔哲学论述的是一个精神不断自我纯化的过程,语言问题是这个发展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语言,并不是主观对于康德意义的“物自体”反应或者模仿的产物,而其实是一个精神自我发展的形态。语言是精神的较高阶段对于前一较低阶段的扬弃,是两个阶段的结合。他说:“黑格尔指出的,是康德被……意识所欺骗,把意识的差异性,即主体对于一个异在对象的分离态度,用来描述实际上精神的拥有自己差异性的更高阶段。”他继而指出,精神,包括语言,通过语言的上述高级对低级的包含、扬弃机制,有自我发展的能力,且这种自我发展并没有最终摆脱语言。“在精神哲学的语言原理中,有一个悖论。一方面,语言逻辑地先于思想,思想扬弃语言。作为这一扬弃过程,语言中的感觉要素在减少……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精神的任何阶段里,扬弃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没有话语,思想不能完成自己为一个思想。”[注]Mure, G.R.G., A Study of Hegel’s Log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8, 21-2.也就是说,语言无法被代换掉,与逻辑有着复杂的纠缠关系。语言的自我发展,其实就是精神的自我发展,思想看起来隐于语言之后,其实也可能就是语言本身的形态。
还有思想家也看到黑格尔语言具有自我发展、自我否定的革命性能力,比如法国思想家克里斯蒂娃。克氏在她的《诗性语言的革命》中认为:“黑格尔的否定性……成功地综合了康德的理论和实践秩序……指向生产得以实践的空间……否定性,既没有形成逻辑的运作,也没有形成界限……否定性概念正式提出了一种斗争的状态,强调符号态功能和判定的异质性。”因此,通过理解黑格尔的“否定性”思想在语言中的作用,“我们可以提出一种新的意指实践形式:它在语言中产生,而且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被理解……运用它完成自我意识的重建”。[注]克里斯蒂娃著,张颖、王小姣译:《诗性语言的革命》,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7、2~3页。
因此,黑格尔的语言观正如穆尔所说,其实是有悖论的。一方面认为语言有缺陷,需要从中发展出逻辑来取代它;但另一方面对于语言有着深刻的揭示,这个揭示又赋予语言有自我革命的能力,并且实质上具有能够成为精神本身形态的可能。关于后一方面,在黑格尔研究中是不充分的。
中国的黑格尔研究历史也不短,但对于语言问题还少有人关注。香港刘创馥关于“思辨命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注]参见刘创馥著:《黑格尔新释》,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但此外,国内其他论述并不多,近年来有张廷国、梅景辉、杨玉等发表的数篇论文。[注]张廷国、梅景辉:《形而上学的语言与语言的形而上学——论黑格尔的概念论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哲学研究》2008年第6期;杨玉:《工具抑或存在之本质——黑格尔的语言思想探析》,《求索》2011年第12期。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不多,但都能注意到黑格尔的语言观里,“语言的存在论和工具论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糅合在一起”。[注]张廷国、梅景辉:《形而上学的语言与语言的形而上学——论黑格尔的概念论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哲学研究》2008年第6期。不过,语言作为精神的实存形态是一个黑格尔哲学的鲜明论点,所以,仅见及语言作为精神的存在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对这种存在形态和作为精神形式的逻辑的关系进行探讨。
语言问题其实是黑格尔思想中与辩证法、逻辑学等具有同等重要的核心问题,对黑格尔关于创造性思维的理解以及它对于西方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以前的研究总体上没有突破语言为外层、逻辑为内层,语言为低级、逻辑为高级的观念,随着黑格尔研究的推进,这个观念逐渐显示出有突破的可能。
二、 从黑夜到语法(逻辑):语言产生过程中的三个中项
黑格尔的思想,首先是见及日常现象的虚假性,通过现象中认识的发展,最终超越现象性的认识,达到“科学”的认识,即以“辩证逻辑”所展示出来的世界的系统形式和实际存在。
在这么一个体系中,似乎存在一个对立。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黑格尔自己就说:“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对它作出陈述。”[注]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页。这个判断、理解与“陈述”的区别,表示一种日常语言世界与超语言世界的对立。但是,黑格尔认为,超越其实同时就是回归,他说:“精神的提高固然是一种过渡和中介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对过渡和中介的扬弃。”[注]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7页。“扬弃”并不是抛弃,现象在被超越中保存,并获得了自己的必然性,从而成为真实世界中的环节,因此,“真理就是全体”。所以,黑格尔思想体系与其说是两个世界的对立,不如说是一个世界通过颠倒而呈现真性。语言问题也是如此。确然,黑格尔追求一种“逻辑学”,但这种逻辑并非是外于语言、以语言为工具的特别形式,而正是在语言表面上工具化、中介化面貌的自我颠倒,是语言被遮盖的本性的展示,是语言保持着否定的开放性的自我辩证。
一直以来关于黑格尔语言观的研究,在搜罗、汇集黑格尔各处论说上做了大量工作,但有意思的是,很多研究者却不重视黑格尔关于语言唯一的正式论述,即《哲学全书》“主观精神”中有关于语言的论述。这和20世纪以来黑格尔研究重视其早期思想有关。另外,该段论述的解读也有分歧,影响了它的作用发挥。比如上述穆尔的观点,主要是来自对本段论述的理解,有意思的是,这种重视竟然受到批判。比如库克说:“把《哲学全书》当做理解黑格尔关于语言的概念的基础是危险的,它特别体现在穆尔的《黑格尔逻辑学研究》的第一章里……穆尔受了《哲学全书》里黑格尔明显的系统化、逻辑化的关注点的影响……”[注]Cook, D.J., Language In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Mouton & Co. N.V., Publishers, 1973) 176.其实我们看到,穆尔没有因为重视这段论述而失去对于语言潜力的洞察,对他的这个批评倒恰恰反映了库克对这段论述深意的忽略。我们要问,在这段论述里,语言真的因为黑格尔系统化的体系追求,而被贬为逻辑的外壳和工具了吗?
针对这个情况,本文恰以为对黑格尔语言观的理解,不仅要重视这段论述,而且要以这段论述为基础。毕竟“精神哲学”是其“实在哲学”,即关于世界、这个精神的展开过程的真实的实际存在的正面陈述,在其中语言的定位表示语言真实的内涵。也就是说,尽管在各处都会出现语言现象,但语言的真理其实在此处得到陈述。
关于语言的论述在“精神哲学”的“主观精神”中的“心理学”阶段,在此前,“现象学”表示认识达到了普遍性,于是在“心理学”开始了理性这个普遍性完成它获得实存的过程。“心理学”中的每一部分,其“内涵”都是普遍性、理性、思维。但这个内涵,是不可以独立存在的,它的存在必然是“心理学”的诸样态,即并不存在有一方面是内涵——思维,另一方面是思维的外衣这种情况。语言是“心理学”中完成普遍性内涵完全变成理论形态的阶段,这表示黑格尔认为,人类成熟的语言,只有在人类有了对于世界或者自我的普遍性的认识以后,才是可能的;语言作为普遍性的环节,其本质是普遍性在理论形式上的实存:“主观精神……的产物向外在理论的东西上是言词。”[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7、323、326、322页。言词、语言并不是精神的工具或者模仿,而就是这个精神的形态和实存。
黑格尔对于语言是如何产生并如何成为思想的实存形式的论述,是非常独特而深刻的,应该是语言哲学中独到的成果。在这个论述中,包含着本文主要表达的语言形成逻辑的潜在观点。但是,黑格尔的论述有些含糊不清的地方,造成了黑格尔研究中的一些分歧,需要加以厘清。
1. 黑夜矿井:第一个中项中的潜意识
首先,被认识达到的普遍性,在新的发展阶段,最初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即“感觉”。感觉总是不稳定的,因为感觉作为感觉,就是还没有意识到;但是感觉要成为感觉,又必须被意识到。于是,感觉的内在矛盾要求它发展。发展就是感觉开始进行自我分离。于是,感觉开始自己意识自己,进行自我联系,这个运动被黑格尔称为“注意”和“回忆”。因为感觉本来就是普遍性的无意识状态,所以感觉自我意识为一个普遍性的自我。于是,感觉的一,现在变为分离而相对的二。一边是感觉,一边是自我或者普遍性。回忆是一个双向过程,自我也反过来回忆感觉,并把感觉回忆成(也即对象化为)一个“表象”、一个“图像”。
当感觉一分为二的时候,本来是一体的感觉和自我就其不同,又有了相互外在的意义。对于自我来说,感觉是外在的,而感觉一旦外在,就不再是感觉,而是有了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图像”或“表象”(“理智把感受的内容规定为在自己之外存在着的东西,将之向外投在空间和时间之内”②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7、323、326、322页。)。黑格尔的思想处处隐含着与康德哲学的对话。此处,时间和空间其实是一个对原初无意识脱离的标记,也是康德哲学中经验性存在的标记。
感觉变为图像,意味着感觉反过来在理智自我中被“回忆”,意味着它被理智的普遍性重新塑造为时空维度的外在存在。从原初的感觉中分离出来的理智自我,是感觉对于自己的自我进行寻找而产生出来的。因此,它的主要规定,就是自身联系,是在诸多杂多中的共同性,是《逻辑学》“自为之有”这一节所说的“为一之有”,即在同一个东西的各种属性中为着同一个东西而统一的那个向一性。这个“为一之有”,就是这个在杂多属性之中的那个东西:“自为之有”。自我就是一个“一”,一个简单的同一性,即普遍性。普遍性是分离于原初的,但同时又是表达(回忆)原初的那个分离的层面。“这一力量实际上是理智本身,是与自己同一的我,这种我通过自己的回忆直接赋予图像以普遍性,并把个别性的直观统括在已经使之内在化的图像之下。”③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7、323、326、322页。
可以说,在原初感觉的“注意”这么一种“回忆”行动中,内在地就产生了一个断裂,一个自我否定,一个内在矛盾,一变为二了。这个矛盾驱使感觉自己发展与运动。
感觉被自我“回忆”而成为“表象”④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7、323、326、322页。,所以说表象就可以看作是:我产生(回忆)一个东西,把一个东西放在面前(vor-stellen),是把自我和一个对象联系起来,是那个东西成为自我的对象,在对象化中,那个东西是外在的、存在的。于是,情况就变成:理智自我由原初感觉产生,它被产生后,反过来把原初感觉看作是外在的、在先就已经存在的东西。
此时,我们就进入到一个一般认识论面临的处境:一个主体,面对一个对象(原初感觉),生产出另外一个对象(表象),二变为三。黑格尔的论述让我们看到了这三个看起来独立的环节,其实是来自同一个基础,而且是这个基础内在的矛盾发展出来的。
对于这个情况,黑格尔有理论概括。他认为,任何概念就其整体性来说,都是一个“推论”,也就是一个三要素的结合。关于这个,他说:“在直接推论里,概念的各规定作为抽象的东西彼此仅处于外在关系之中。于是那两个极端,个体性和普遍性,和作为包含这两者的中项的概念,均同样只是抽象的特殊性。这样一来,这两个极端彼此之间,以及其对它们的中项的概念之间的关系都同样被设定为漠不相干地独立自存着……反之,在理性的推论里,主词通过中介过程,使自己与自己结合。这样,它才成为主体,或者说,主体本身才成为理性推论。”[注]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第358-359页。这段话说,任何一个概念,其实都包含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在直接、外在的意义上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其真正关系却是差异性地合一的。而第二个中项,它结合两个极端,同时也具有偏向和合某一极端的意义。
现在我们得到了第一个中项,理智自我是一个独立的项,但它同时又既是来源,又是产物,它是来源和产物的结合体。从根本上说,原初感觉是一切的来源。但是如果理智自我就其是原初感觉的“回忆”来说,理智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代表原初感觉的。所以,黑格尔把一切的来源归于理智,即它是一切直观、表象、图像的来源,因此,它可以说是一个“黑夜的矿井”。[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23、326、327、326、324、326页。所谓“黑夜”,这是黑格尔用来描述最初级的逻辑范畴“存在”的词。一切规定和显示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仅仅是存在,只是有,而无任何内容,这种状态就是什么也看不清的状态,要么是一片光明,要么是一片黑暗,在黑格尔看来,纯光明和纯黑暗都是一样的。[注]参见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第83页。“存在”虽然最初级,但它包含一切。理智自我也是这样,当它作为中项时,来源和产物是一体的。我们最要注意把握的,是这个中项中代表来源的“矿井”,并不在外面和远处,它就是和光明的表象在一起,它是表象的运行的空间。这个空间,因为承载着表象,所以是不被人注意的,是潜意识。
2. 金字塔:第二个中项及想象力的来源
理智自我对象化感觉,将之变成“图像”与“表象”;反过来,理智自我也是图像的对象,它在图像的对比下,也有自己的存在。这个存在体现为各个作为对象的表象所存在的时空平面,也体现为各表象之间的关系上。于是,各表象间的共同的普遍性凸显出来(“各个表象的联想因此也须理解成是把各个个别性的表象统括于一种普遍性的表象”[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23、326、327、326、324、326页。)。这个普遍性,其实就是理智自我在对象方面的化身,黑格尔又称其为理智自我的“独立表象”[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23、326、327、326、324、326页。。于是,表象可以看作是从普遍性而来,普遍性展开着表象,表象从这里涌现。
普遍性,是来源于传输过来使各个个体发生关系的力量,但它又是分离于来源而独立成为一个平台。因此,普遍性可以具有自己的主体,它体现为理智自我,理智自我作为普遍性“本身”。黑格尔进一步指出:“理智在自己那里却不只是普遍的形式,反之它的内在性在自身内是固有内蕴的确定的、具体的主体性。”[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23、326、327、326、324、326页。可以说,主体占有了表象、产生了表象,理智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强力”,一种裹挟和产生表象的强力。因此,理智可以成为“再生的想象力”[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23、326、327、326、324、326页。。
现在,前面提到的表象都是“再生”的,即表象在分离于原初感觉的意义上,对于原初感觉的模仿。
但是,理智自我不仅仅是被动的映照,它一旦有了独立性,它就是一个“主体性”。这个主体其实是原初感觉,但现在这主体是在独立的意义上来说的,所以它本身是不是原初感觉并不重要,总之它现在自己就是一个“黑暗的矿井”。在上一个推理中,大前提是原初感觉。在这个推理中,主体成了大前提。主体既然独立,就必须有它的存在。
主体要存在,存在又必须是图像化的,于是,主体必然是一个将自己图像化的行动,这么一种自我显示,黑格尔称其为“自我直观”[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23、326、327、326、324、326页。。但是,主体自我图像化,其中的图像,主体自己无法变出,它只能借助“再生”的图像来表达自己的存在。
这些“再生”的图像,就是主体本来就已经掌控的那些由原初感觉变成的、已经成为外在物的东西,黑格尔称之为“给定的”、“被接受的”东西。这些东西,就理智自我就是原初感觉本身来说,其实也是自己生产的。但它相对于现在要获得存在的主体来说,是外在的,它是自己过去的生产。因此,对于现在的主体来说,是早就以外在模式存在的东西。所以,它具有“给定”的性质,也因此,按照海德格尔的话说,人“向来已经被抛在世界之内”。尽管这世界本来就是自己的生产,但这一生产,对于现在主动的生产,却是一个环境、一个给定。对于这种给定的存在着的东西,黑格尔又把它称为在主动性生产中的“备料(材料)”。
现在,主体要主动生产,就要借用图像,主体在生产自己的时候把备料敷于自己的独立表象上,让它获得存在。因此,黑格尔说:“理智是支配属于它的各个图像与表象的这种备料的力量,并因此而是自由地把这种备料联结和统括于独特内容的活动。”所谓把备料统一于活动,就是把活动(自我直观)寄托于材料之上的意思。于是,我们看到,理智自我作为主体,它自我生产、自我直观以获得自己的存在,因而产生了一个寄托于材料(图像)之中的独立表象。产品是两者的综合,如果材料是一方,则另一方是它的意义、它的“怎是”,即“形式”。这个生产,其目的就是把自己“规定成存在东西,亦即使自己成为存在,成为事情”。这个活动,黑格尔称之为创造性的想象,“是象征的、比喻的或构思的想象力”。[注]参见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第326、327页。这个想象力,它的主要产物,是“标志(符号)”。
这个标志,是一个图像性的东西,“它不是作为肯定的和表象它自己本身的,而是表象某种他物的……它已把理智的一种独立的表象作为灵魂接纳于自己之内,这即它的意义”。也正因为这样,黑格尔把符号比作“金字塔”。金字塔是一种建立,犹如图像鲜明地呈现,但是,金字塔中却“移入和保存着一种异己的灵魂”。②参见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第326、327页。犹如图像表达独立表象,材料呈现出形式。
在理智自我还只是模仿着原初感觉进行表象时,它是一个双重体:黑夜矿井和表象;现在理智自我作为主体进行自我生产时,它成为符号,是第二个中项,它仍旧是一个双重体:形式与材料。在这个中项中,主体就是黑夜矿井,就是运作图像的力量,因而也就是想象力。这想象力是创造性的,它就是理智,符号产生后,它就成了蕴含在里面的能力和潜意识。
不少学者在研究黑格尔这段文本时,特别关注这个创造性的想象力,有的甚至以之为语言论述的终极内涵。比如库克,他说:“黑格尔以各种形式讨论了创造性想象或幻想,所有它们的独特性质就是通过图像化的方式唤起或表象观念,或者是直接的(象征主义、视觉和造型艺术),或者是间接的(诗)。对于黑格尔来说,表达的最高形式是制造符号的想象……黑格尔在这里的讨论虽然不特别具有源初性,但他对于诗性幻想的喜欢是值得关注的。”[注]Cook, D.J., Language in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Mouton & Co. N.V., Publishers, 1973) 107-8.在他看来,黑格尔讲到符号的形成,关于语言的主要内涵就讲完了,“直接的”和“间接的”都归属于“幻想”这个阶段。看来,对于艺术的偏爱遮挡了他对于黑格尔论述进一步进行阅读和思考,完全不考虑黑格尔关于成熟语言的形成还需要“记忆”这么一个更高阶段。在那个阶段,“间接的”,即脱离图像的,才是成熟的语言。在符号阶段,双重性虽然本质上是一体的,但它由于对材料(图像)的过于借用,这个双重性表现为相异者的双重性,因此,黑格尔才会将之比喻为“金字塔”。
我们也看到,也正因为这种读解,库克才会批评穆尔过于注重《全书》的这些论述,因为毕竟黑格尔关于幻想的论述在其他文本里很多。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穆尔关于语言是“自我差异”而非相异者的差异,因而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观点,与这个观点所暗示的语言本身就可能是精神与逻辑、而非精神与逻辑的工具与模仿的内涵,可能要在充分重视“记忆”这一阶段的基础上才能获得。
对于黑格尔语言观的这种匆忙的阅读与误解,也体现在德里达的论述中。德里达仅仅在“金字塔”阶段就总结了黑格尔的语言观,因而得出黑氏只是把语言当作“中介”的结论。如果他继续阅读下去,他可能会发现黑格尔关于语言的论述,和他自己要建构的书写理论竟然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黑格尔本人明确认为想象力还没有完成使主体达到存在的目标,“想象乃是理性,但却只是形式的理性,因为想象之为想象所具有的内蕴是不相干的,可是理性之为理性却把内容也规定成真理”。[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27页。想象的成果仍然是一个相异者的结合(漠不相干),因为被动的自我属于一方面,主动的自我属于另一方面,思维和存在、自我和对象还没有统一,因此,形式还不是质料,符号还只能是两个不同东西的综合。此时,整个精神因为还没有解决自己内部的主体与对象的对立问题,它还是努力和对象结合的主体,它总体上就是“形式”的、主观的。
但是,精神在这一阶段还在努力,语言还在形成中,语言在为了让精神、也是让自己进一步得到存在,还要走到自己的极致,从而形成自己,并在自我形成中达到自己的终结。这下一个阶段就是“记忆”。
3. 记忆:第三个中项把“黑夜”铺展为逻辑
符号是作为金字塔而存在的,金字塔的要义是:一个图像里面含着异己的表象。在日常的观念里,语言也就是金字塔了,即语言是一种模仿,它用图像性的形态,来表达“真实的”内容。
黑格尔的语言观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反对这种金字塔式的模式。因为他认为,语言是理智主体的实存,语言不表达别的实存,语言这个实存就是真理的实存。
达到对语言的这个理解关键在于这下一步,即符号的自我否定。前面说过,金字塔是一个图像,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表达异己的东西。于是,这个图像的本质其实就是这个图像的否定,金字塔的存在就为了自己的崩溃。真正要存在的,其实是相对于静止的消逝的东西,这东西,黑格尔认为是“时间”:“一种标志的直观所具有的更真实的形态是在时间内的一种定在……是定在的一种消逝活动。”[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28、328、329、331、328、329页。时间就是无形的主体在实存世界的维度。当然,消逝本身(时间)是无法有形态的。如果要给消逝以形态,那么最切近的形态就是“声音”,声音是出现即过去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声音代表的消逝,才是语言的本质。当声音与主体关联起来,声音就不再仅仅是声音,它会因为这关联而分化并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意义单元和它的系统,就成了语言。
语言因而是一种特殊的实存,它比图像对真实的模仿,是更加直接和切近的模仿。因为其形态的特殊性,这种模仿甚至不是模仿,而是贴合到真实上面,几乎做到让真实直接出现。因此,黑格尔把语言称为“第二定在”,而把以模仿方式存在的图像等作为“第一定在”[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28、328、329、331、328、329页。。第二定在对于真实的表达是几乎没隔膜的。
原本理智自我、主体借了给定的图像来表达自己这种存在,因为给定的东西,是外在性的、直接性的、异己性的东西。对于这种东西,黑格尔称之为“感性”的,所以,原本理智自我其实是通过“感性”而显现。这感性的东西是会遮挡和歪曲它要表达的东西的,也因此,它是金字塔模式即相异的表达的模式。
所以说,在黑格尔这里,语言的成形之最重要的,是原来模仿模式中被模仿者克服模仿者直接出现。也因此,黑格尔要求语言要尽量去掉符号中原来材料(即表达理智的图像)里面固有的内容。他说:“在语言的元素性质料方面……模仿的原则已限定在自己微小的范围……他们作为感性的直观本身被减弱成标志,而这样一来它们固有的原初的意义就被萎缩和被抹去。”[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28、328、329、331、328、329页。于是,语言这种特殊的符号“作为一种存在单独并不使人想到什么,而只是具有一种规定:指谓单独的表象本身,和感性地介绍这种表象。”[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28、328、329、331、328、329页。语言的这么一种和理智自我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内在表达在某一个层面上的极致,“表象的这种最高回忆内化,是理智的最高外化。”内外呼应可以做到的极致接近,就在语言这里完成了。
现在,以声音为形态的语言,尽量以忽略异己的意义而存在,所以能够直接表达思想。它就是思想。因此,黑格尔认为,它“一般地给以一种在表象活动领域有效的实存”[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28、328、329、331、328、329页。,即给思维以实存。
在黑格尔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会注意到黑格尔对于口头语言的重视,原因就在于他对于声音这种“变”——在消逝中存在的性质的理论化。德里达批判黑格尔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黑格尔试图用口头语言实现真理的现实出现是过于简单地处理真理问题。不错,黑格尔是重视声音,但是,如果认为黑格尔的语言观的要点最终只是一个声音,那就错了。声音只是实现真理出现的第一步:去掉材料的隔膜,但黑格尔从来没有认为真理简单地体现为声音,因为,他文本中还有很多需要我们注意而几乎所有的研究者们几乎都不注意的地方。
于是我们要接触到黑格尔语言观中最为深刻的观点。黑格尔认为,因为语言是思维几乎本身的存在,所以语言是系统的,语言是一个言语体系。符号是没有体系的,声音也是没有体系的,而语言是一个体系,语言是声音加体系。语言通过声音去除了与思维的隔膜,思维于是就来到实存中,但思维来到实存中,并不仅仅是声音,它铺展为声音的体系,即语言。所以,思想变成语言,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在变成外在的问题,而是内在走到外在后,外在成为一个复杂的东西,这个东西里面有变化与发展的性质和机制。所以,黑格尔会把体系内在关系的“语法”也当作思维自身的展示,他说:“不过语言中形式性的东西是知性的作品,知性把自己的各种范畴内建到语言内去,这一逻辑性的本能产生出语言的语法的东西。”[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28、328、329、331、328、329页。
这些文本向来不受重视,但它在黑格尔的思想中有隐然的重量,因为它和黑格尔关于“记忆”的思想联系在一起。黑格尔在语言的成形中,专门强调“记忆”的作用。“记忆”这一节看起来是有些奇怪的,很多人不能理解它对于黑格尔关于语言性质的意义,所以大多一带而过。黑格尔研究中的名著《黑格尔再考察》是对黑格尔的一流研究成果,在阐释这节时,芬德莱说:“于是我们从想象过渡到正确记忆(不清楚为什么黑格尔这么古怪地用这个词)的环节,……这里,黑格尔认为,思维这样主动性地操控语词对于它是本质性的,……认为这是知性的控制中更高级的一步,思维在把自己的思想铭记在口头符号之后,可以机械地重复这些符号,而不必受到它们的感性涵义的干扰。”[注]Findley, J.N., Hegel: A Re-Examinati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8) 304.芬德莱把“记忆”这节的意思,理解为记忆把意义铭记在符号上,这样,符号就可以忽略自己的感性涵义,直接代表意义。于是,思维就可以更好地使用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思维直接出现在语言中。在这个理解中,似乎思维本来就是有形式的,现在无非是这个形式直接出现在语言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语法”等与语词关系和系统的意义,也因此,他也没有充分理解黑格尔用“记忆”这个词的深意。“记忆”表达的是如是坦呈,而非隐喻外指的意思,它绝不仅仅是机械地把意义固定在符号上这么点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那么,可以代替这个术语的词多得是。应该是没有注意到这个词的深意,所以芬德莱觉得黑格尔用这个术语“古怪”。但是黑格尔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甚至说:“精神学说内至今完全没有得到重视,而事实上也最困难的一点是……把握记忆的位置和意义。”[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36、334、333、333、334、335页。因此,要充分重视记忆的意义。
在黑格尔看来,记忆是语言成型的最后一步,只有通过记忆,理智的“外化”才能实现。它的意义在于:第一,记忆使理智自我和声音性的名称(标记、符号)合一,它造成“意义和名称间那种区别的扬弃”。[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36、334、333、333、334、335页。第二,这整一的东西是外在化了的,它完成了理智的存在运动。“名称作为从理智产生的直观,它的记忆同时是外化,在这种外化中,理智在自己本身之内设定自己。”[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36、334、333、333、334、335页。
记忆分为三种:保存的记忆、再生(再创造)的记忆和机械性记忆。保存的记忆指名称和内容的联系固定下来,它是两者合一;再生的记忆是能够自如地使用那种联系,也就是说,通过它,名称就是一个“实事”,它独立运用,“而无须直观和图像”[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36、334、333、333、334、335页。。机械记忆才是记忆的本质,因为按照黑格尔的理解,记忆虽然内涵复杂,具有又是内化又是外化的双向关系,但它根本上的意义就是被记忆的东西的直接出现,记忆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记忆这个样子,它这么存在着,它和同样的其他东西的关系也有固定的秩序,这个固定的秩序也是记忆赋予的。此时,并不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理智来支撑这个记忆的东西,因为内在的理智已经走出来在记忆里面了,记忆就是它要表达的东西了。记忆不依赖别的来定位,而就是依自己来定位,即黑格尔说的“整个的外在性”,这种记忆是机械的。[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36、334、333、333、334、335页。机械记忆的要点,就是理智整个地外在化了,“理智作为机械记忆一体地就是那一外在的客观性本身与含义”。相应的,机械记忆也就可以说是完全的内在,“记忆就是往思想活动内的转化”。于是,内外的分离扬弃了,“主体的东西不再是一种和它的客观东西相异的东西,正如这一内在性在其本身就是存在着的(实存的)”。[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36、334、333、333、334、335页。
黑格尔对于记忆的论述是很独特的。记忆是比想象力更高的东西,想象力还是把内在借用相异的外在来表达,但记忆之为记忆,哪怕记住的符号名称无可避免还是一个直观,但它的要义是内在直接外在出现。因为出现了,所以说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别的理由,故而机械记忆是最高的。这无非是表示语言把理智自我带到实存中,给理智自我以存在的形体的意思。
至此,语言才完成了自己产生。语言的出现,给了原本主客观分裂的精神的状况一个新的可能,那就是:主客观分裂是可以克服的。语言即是一个体现。在语言里,普遍性的这一端(内在、普遍)和普遍性的那一端(外在、个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主观的可以是客观的,而客观的,因为它是为了自我扬弃而是客观的。精神,在普遍性的层次上,占有了原本和自己分离的外在性。关键在于,我们看到,精神在对外在性占有的语言中,第一次有了关系。唯此,才有了“逻各斯”,有了逻辑规则的雏形。
三、 语言是逻辑的本能
黑格尔这个文本展示的语言观,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不无瑕疵,至少有混淆语言和文字之嫌。不过,他对于语言作为思想本身自我发展的形态、图像和意义之间相互异在,以及语言展开为一个系统的观点,却也比较深刻地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语言的结构性、任意性和时间性)做了一个哲学注解,同时也涉及一些自己理论的重大问题。
首先,语言就是思想,其以否定为机制自我生发。
语言就是作为普遍性自我的思维自我外化而取得的外在性,这是黑格尔明言的。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任何概念都有自在(直接的无意识的存在)、自为(寄寓于他物、以他物为自己的内容的存在)和自在自为(在他物中意识到自己并把他物作为己物,从而完成一个完整的存在)。语言,在某个层次上是思想的自在自为的存在,因为思维首先外化,同时在外化中完成回归性自我指向。
在思维的这一运动中,外化的力量并非是异己而来的,而是思维本身内在的力量。思维在其直接状态中,是一个没有意识的原初感觉,这是一个肯定性的状态,但是,这个肯定性并没有意义,因为它没有自我意识,它要获得存在,必须同时要有规定,要被自我注意到。因此,“注意”给了这个直接的肯定性一个否定,注意让原初感觉注意到自己,而对自己的注意让自己产生分化;这个分化,把原初的感觉外在化了,推入了一个以时空为维度的普遍性空间,成为图像。图像又被自我否定,变成普遍性主体的确立;普遍性主体的确立又引出一个否定,即普遍性要在自己的表象中获得存在,即普遍性就是外化。最后,普遍性再次对于外在进行否定,以一种最少外在性的外在物的形态出现,成为语言。到了语言,似乎这个内外否定的运动停止了,但语言却因此成为另一种关系,否定转而发生在语词之间。到了这里,我们似乎开始看到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影子。
其次,语言终究无法被替换。
黑格尔认可在语言的产生过程中有“模仿模式”的存在,这个模式主要出现在以“金字塔”为喻的符号阶段中。符号,就使用外在的、已经定下的、被发现的图像来使“独立表象”(主体的定在)获得自己的形体。因为图像具有外在性、固有的特殊性,它对于独立表象是有歪曲或者遮盖作用的。模仿模式形成最根本的原因是外在性中固有的特殊性不能消除,这样,就有了外在性与内在性的分离。语言从符号中否定而出,为的是否定这个模仿模式,但其实根本上没有让内外的差距消失。我们看到,声音并不就是消逝,而是最接近消逝的定在而已。黑格尔尽可能去除掉质料的固有含义,使之成为一个尽可能空的标记,在其之上自我的内在性可以栖居。但是,一个以声音为质的语词,不管如何回避固有的特殊性,它仍然是一个表象(存在、定在),语言的这个基本的符号特征是要看明白的。
正因为声音无论如何有自己的定在,于是,内在性变为外在性时,就好像被声音里面的定在这个最终无法消解的石头绊了一跤,它无法仅在某个声音里完全外化自身,从而把自己铺开在外在里,形成声音与声音的关系,这才是语言。所以说,语言,是用横向的关系来代替符号这个中项里的纵向关系。横向关系里的差异,才是语言的本质。而承载声音与声音之间关系的,是一个普遍性,一个承载着外化的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横向差异或者纵向差异,直到绝对理念的最高处,也没有消失(在黑格尔这里,绝对理念是精神的自身出现,但它的模式最终是“扬弃”模式,即精神通过全包现象因而能透过现象出现的,这种出现模式是造成黑格尔哲学“真理即是全体”这个特征的根本原因)。而只要差异存在,就意味着实存这种外在性根本上在其中起着作用,而没有被消解。于是,这也意味着,语言在理论上无法被超越和摆脱。
再次,语言在形成时就产生逻辑。
语言在外在性中,把自身铺展为一个内涵关系的系统。黑格尔明确把这种语言中的差异与关系(他归为“语法”一类),当作是语言“逻辑的本能”所产生的。这么说来,似乎有一个被语言遮盖着的“逻辑本能”,然后,语言对它进行模仿。但这个结论符合黑格尔理论中蕴含的深意吗?显然不符合。因为在语言形成之前,或者在语言的下面,并没有已经有形式的所谓实体,而只有等待着被自我赋形的一个冲动,比如说“主体”、“独立表象”,或者干脆说“黑夜的矿井”。
这里有众多研究者都不注意的论述。黑格尔说:当此之时,主体(自我)“把自己设定为存在,设定为各个名称之为名称、亦即无意义的语词的空间。其实这种抽象存在的我,作为主体性同时是支配不同名称的力量,是那种在自己内把它们的系列固定下来,并使之保持在固定次序中的虚空维系。”[注]黑格尔著,薛华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第334页。这段论述,已经直接把外在的差异性以及承载差异的普遍性(虚空)当做是主体的外化了。
在前面,当原始感觉被外化时,分离出来的自我给外化的感觉提供了一个时空维度,使感觉被外化成时空性的图像。在那个时候,时空图像对应着一个意义,就好像修辞中的隐喻模式。隐喻模式孤独地成立,不存在与别的图像发生什么关系的问题。此时,时空本身不是时空性的图像,那些固有的特殊性遮盖了时空本身,因此,作为给出时空维度的时空本身的自我,对立于这些时空图像。现在语言中,时空图像自我超越和否定,它努力走向时空本身,于是时空本身走进了语言。在时空本身走进语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尽管语言已经尽力去除各种固有特殊性,但是,就算所有特殊性去除了,但特殊性本身是去除不了的,某一个时空中的东西去除了,但时空的“这一个”是去除不了的。于是,时空本身走进语言的时候,就化成一个个“这一个”的联系,从而隐喻关系转化成了转喻关系。
这会造成什么效果呢?那就是,一般的符号之间,它们不会是必然互相联系的,而语言这种特殊符号,它必须是一个多元联系的“系统”。因此,黑格尔说,声音会分化为体系,而且这一体系中的内在关系“语法”,体现了“逻辑的本能”。黑格尔认为,正是语言比较好地让思维出现,所以思维把自己逻辑本能放置进了语言里。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思维在语言形体获得以前,并不是逻辑的,而恰恰是在它变成了语言的时候,才是逻辑的。没有语言,思维没有逻辑这件事。在思想史上,逻辑向来是超越时空的存在,但是,黑格尔不自觉地让我们看到,没有时空的出现,逻辑作为一种时空本身性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在描述语言的时候,可以讲述一个“逻辑的本能”,但是如果要讨论逻辑,则应该看到逻辑有个“语言的本能”,这才是“逻辑”作为“逻各斯”的本意。关于这一点,恐怕是我们在黑格尔的语言观中收获的最重要的发现。
黑格尔的这个思想,是其语言观中不可轻视的要点。这个要点,只有在《精神哲学》这段论述中表达得最清晰和深刻。虽然它的表达显得艰涩而不诗意,但它显示出语言是逻辑、思想的基础的意义,是所有关于语言诗意地使用的最坚实的支撑。而且,这并不是黑格尔偶发的思想。黑格尔引人注目的另一个论述,不仅是这个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根深蒂固的佐证,且具有直接关系,这个引人注目的论述就是黑格尔关于康德“物自体”的论述。康德在其知识论中,认为我们的知性知识都是来源于“物自体”的。这看起来,我们的知识都是对于“物自体”非常曲折的模仿。但黑格尔看来,这个“物自体”是毫无必要的设立,因为它是一个幻像。他说:“物自体……只是一个极端抽象,完全空虚的东西,只不过是思维的产物,只是空虚的自我……的产物,这个空虚的自我把它自己本身的空虚的同一性当做对象,因而形成物自体的观念。”[注]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第126页。这就是说,知识本身并不需要一个外在的对象,因为这个对象已经进入了知识。但它在知识里,除了是一个个有形的在运动着的表象以外,还更深地是那些表象运动于其间的关系和“虚空”。这个“虚空”,在康德认识论里被称为“统觉”,被称为“先验自我”。在康德那里,“统觉”给出了知识生成所需要的想象力、范畴以及表象运动的空间。把握住这个蕴含各种关系和力量的虚空,是消解康德“物自体”的要点。
这段论述可以反过来讲述语言,那就是:思想已经进入语言,语言不再是对于一个更深、更高的思想的模仿。语言就是思想的身体,作为思想形式的内在各种关系以及动力,就在语言作为一个诸定在具有相互关系因而成为语言的本性里,语言是思想关系的提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