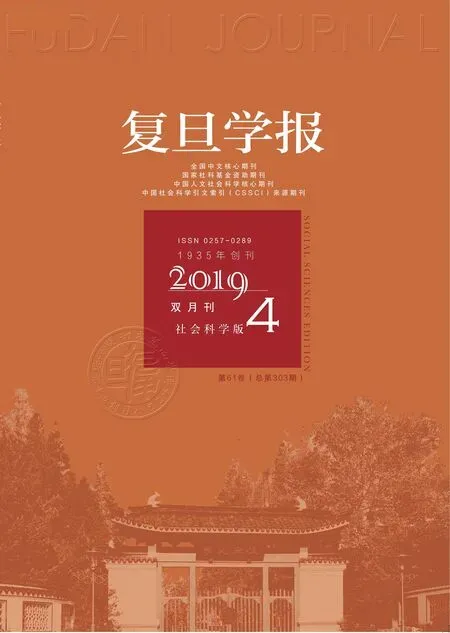感应与调适:元明易代两起祥瑞的文学意义发微
2019-08-06饶龙隼
饶龙隼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至正二十年(1360)春某月日,在西昌石塘萧氏故居之旧址,于蓬蒿瓦砾中突产瑞芝二本;也正是在这一年春二月某日,金华硕儒宋濂应聘将赴金陵,临行前自占得“文物之祥”。两起祥瑞,同时并出,一在江西,一在浙东,看似偶然,实为灵应。当元末衰乱之世,此类祥瑞的出现,不知是亡元的回光返照,抑或是新朝的瑞应发祥;这让劫后余生者颇生疑惑,也让向往太平者满怀遐想。今考旧文遗迹,追缅人物情景,其所蕴涵的政治气运与文学意味,仍然彰显着奇丽的历史人文气息。兹将透过这两起祥瑞的表象,对其文学意义作深切之发微。
一、 对两起人文祥瑞的叙咏与解读
世当元明易代鼎革之际,社会与人生均遭巨大变故,难免发生许多灾异、祥瑞之事,其中有两起祥瑞同时异地并出,颇引起东南士绅的关注,亦激发相关叙咏与解读。
其一起是萧氏瑞芝。至正二十年(1360)春某月日,石塘萧氏故居之址产芝草二本。①刘崧:《槎翁文集》卷五《萧氏芝草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这引起西昌士绅的关注与极大兴趣,有十名贤应萧斯和之邀作瑞芝诗文,既表达对萧氏积善累仁之祥庆,也因以抒发对世变运会的感想。大约半个世纪之后②杨士奇曾馆萧氏家塾,与萧氏兄弟交谊深厚。萧应之祖斯和、父安正,在洪武初相继长区赋,嗣后萧应(字德聚)继承父祖职事。他每次运赋到京城,均要与杨士奇相聚。其具体次数和年份不可详考,但大致时间范围仍可以考定。杨士奇曾说:“余仕两京,德聚以督赋屡至,竣事,必过留一再宿。”(《东里文集》卷十六《萧德聚墓表》、卷九《题萧氏瑞芝诗文后》)杨士奇于建文二年(1400)被荐入京,朱棣迁都北京在永乐十八年(1420),则萧应与杨士奇在京师相晤,大约在1400年至1420年稍后。如此,从出芝草之1360年算来,已跨越40至60多年了。安正,名廉,号凌云居士;德聚,名应,别字聚学。,其孙萧应运赋来京,出其父萧廉所录诗文九首,请杨士奇鉴赏并题写跋语。杨士奇从《杨氏家集》中,又辑录出《瑞芝记》一首,乃其伯祖杨望之所作,恰足成十首以为完帙。该十首瑞芝诗文,今多方搜讨暂得:文一篇,即刘崧《萧氏芝草记》,见载《槎翁文集》卷五;诗六首,即欧阳铭《瑞芝》、王沂《咏桃源萧氏瑞芝》、王佑《题桃源萧氏瑞芝》、杨卓《瑞芝》、邓尚《瑞芝》、张虎《瑞芝》,分别见《泰和诗征》卷五、卷六、卷八、卷十一。
据刘崧《萧氏芝草记》所述,萧氏瑞芝产出情形及姿态为:
岁在庚子,余读书武山之阴,闻有异草二本,生于石塘萧氏故居之址。萧氏,故文献家也,则异草之生固宜。余他日过而见之,则连蜷轮囷,大者如叠鳞团凤,小者如羽盖,如金支,其茎干皆赤黑,坚莹如质漆。其状质之美,盖又有过于余西江所见者。而识者亦谓之芝焉。[注]刘崧:《槎翁文集》卷五《萧氏芝草记》。
这里交代了芝草产出的时间与地点,并简要点明芝草主人为文献故家;还描述了芝草的数目、形态与色泽,而且判定萧氏芝草有“状质之美”。
至于文中“有过于余西江所见者”云云,则是照应了早前一起旁邑所产瑞芝事。此处前文曰:“当至正丙申春,临江山谷之民得异草,以上于县;县异之,以为芝也,送于郡;郡送于省若宪。时袁州盗犹负固,有大官奉旨,以赣兵讨之而未发者。省命图其状以送之,且言其将为偃兵兆也。当时游谈之士以诗文相颂美者,无虑百数矣。明年,楚以乡贡江西,将赴春官,适省中贵人以前《芝草图》相示,余因得见之。信乎,其秀且异也。孰知不三四年,兵祸迭作,而事乃有大不然者,吾未尝不慨然为斯草三叹也。其在当时,虽容有好奇之过,而诸公惓惓思治之心亦可悲矣。然又窃自思,以为祸变之作,未有甚于斯时;则天地间和气之剥蚀消歇者,又宁不有熏蒸凝液之潜复者乎?”这就与萧氏瑞芝形成对照,清江所出芝草作为瑞应物,并未成为太平偃兵之祥兆,而接下来的“兵祸迭作”,反让此地官绅滋长悲观情绪,其“惓惓思治”便徒成空想;而四年后西昌萧氏瑞芝的出产,恰慰藉了当地士绅的怅望渴想。
此类怅望渴想既有共通的丧乱思治意绪,却也是观赏者基于身世之感的多重解说。这解说的详情细节如何,今天恐难以尽复其原貌;但从现存萧氏瑞芝诗文中,还是可以窥探其情致意趣。如欧阳铭诗《瑞芝》以“嘉祥符积庆”相歌贺,王沂诗《咏桃源萧氏瑞芝》以福善慎修相劝勉,王佑诗《题桃源萧氏瑞芝》以避世高蹈相呼召,杨卓诗《瑞芝》以美人仙侣相倾慕,邓尚诗《瑞芝》以桃源人家相吸引,张虎诗《瑞芝》以太平休战相期待。与这些诗篇的情思意趣相比,刘崧文的命辞立意更为高妙。它以家国将兴、必育祯祥来阐发,预言了元末乱世社会政治之趋向。后来杨士奇撰《题萧氏瑞芝诗文后》,追述萧氏瑞芝事并解读这组瑞芝诗文,就是接过刘崧的这一话头,因以揭举其文明发祥之义。
另一起是宋濂占祥。也是至正二十年春二月某日,金华硕儒宋濂应聘将赴金陵,临行前自占得“文物之祥”。当时的情势处境是: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军队攻取婺州,嗣后袭取青田、处州诸郡,浙东地渐为朱氏武装掌控。为躲避战乱而匿居的士绅[注]朱元璋攻取集庆路、太平路,随后便挥师南下,直逼浙东。这就给浙东形势更添恐慌,浙东文人纷纷作出反应。至正十五年春,即朱元璋军队渡江前夕,王袆早一步隐居青岩山,买地结屋而住。至正十六年七月,朱元璋自奉为吴国公,越三月宋濂隐居小龙门山著书。至正十八年三月,朱元璋军队攻取睦州,宋濂先遣家人避居诸暨勾无山;及至六月,朱元璋军队攻取浦江,宋濂也随后避兵勾无山。该年十二月,朱元璋军队攻取婺州,王袆避兵凤林、香溪间。同时,戴良也避兵万山深处。,如宋濂、王袆、戴良等人;为保境安民而抗敌的志士,如刘基、胡深、章溢等人,都陆续返回原居住地,并接受朱元璋的保护。朱元璋为了安抚人心,也为赢得读书人支持,竟能礼贤下士,悉心咨访儒学。
然而因朱元璋出自草莽,面对他的降尊优礼,婺州儒士犹存忧惧疑虑,故大多不肯贸然归附之。比如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辟范祖幹、叶仪,咨问二人“治道何先”,范祖幹以《大学》敷陈;朱元璋迎合他们说:“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这当然赢得了范、叶及其同类的认同。但当朱元璋命二人为咨议,他们各以亲老、疾病推辞。[注]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六,至正十八年十二月“辟儒士范祖幹、叶仪”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又如至正十八年十一月,郡太守聘任宋濂为郡学五经师,宋濂作《答郡守聘五经师书》,以多病、亲老、性懒、朴憨固辞,拖至次年正月才接受五经师聘任。宋濂能够最终接受聘任,应是对朱元璋有所认同;但也不排除迁就之计,冀不激怒朱元璋杀心。宋濂还不能简单断定,朱元璋可否倾心归附;因为他此时还缺乏安全感,不久便举家迁回潜溪故居。但是到至正二十年初,朱元璋礼请他去南京;宋濂经历一番游移,最后还是决定赴命。其“文物之祥”,就是为此行而占。
此番占卜之事出自宋濂自述,见其《赣州圣济庙灵迹碑》:
濂初被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祥,后果入翰林为学士,心久奇之。今故特徇祝史韦法凯之请,为撰《灵迹碑》一通,使刻焉。[注]宋濂:《銮坡前集》卷五《赣州圣济庙灵迹碑》,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34页。
此记述明文可征,盖可以确信无疑。但在现存的宋濂几百万文字中,仅此一处载述该文物占祥之事;而此事关乎宋濂及朋辈出处大义,其记叙文字如此之少颇令人寻味。且更隐讳的是,如此祥耀之事,竟在后来记述宋濂生平行谊的大量传记类文字,如郑楷《潜溪先生宋公行状》等文中绝无影迹。
此为一种奇异的文学现象,其所含人文意味有点诡魅。对宋濂本人来说,或许是确有某种隐衷,故在生平文字中仅一笔提及之;在郑楷之辈来说,则是为尊者贤者讳言,盖因宋濂不得善终而不忍语之。当宋濂初受聘而迁延畏惧之时,他用推卜来占断赴金陵之吉凶,此为士人出处决疑之常举,因得“文物之祥”而应命。他既得此祥占,便感心理稍安;所以他抵达南京之后,能做到泰然无芥于心。对此中情节,刘基曾叙云:“庚子之岁,予与金华宋先生俱来京师。时上渡江未久,浙东方归附。先生与予、同乡叶景渊、章三溢同居孔子庙学,惟日相与谈笑,能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无芥于心,惟先生泰然耳。”[注]刘基:《诚意伯文集》卷十五《送宋仲珩还金华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宋濂的态度既是出于对占祥的自信,亦何尝不是对自己政治前景之文饰。后来,宋濂官江南儒学提举,两度任《元史》总裁,教导皇太子十余年,荣膺开国文臣之首,果应验了早前的吉占,诚可谓“文物之祥”。
然而,宋濂入朝后所见同僚朋辈屡遭残害,自己也动辄甚或无端遭遇多起罪罚。如洪武二年八月以“失朝”,宋濂由翰林学士被降为编修;洪武四年“坐考祀孔子礼”失时,宋濂由国子司业贬谪为安远知县;洪武十年宋濂以年迈致仕还乡,闭居容膝之静轩却仍被人监视;终至洪武十三年十一月,以长孙慎坐胡惟庸党案,宋濂虽获减罪被徙置茂州监管,但次年七月逝于夔州旅次僧舍。从宋濂遭受的一系列困厄来说,其命运实与“文物之祥”相悖。[注]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二十四史》缩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因之,宋濂的心理极度失衡,由信赖占祥转成悔恨。当祖孙连坐系囚,老少有一番对话,据载:“宋濂同孙慎被执。慎曰:‘祖读万卷书乃有今日。’公曰:‘为我读书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读书何罪?’”[注]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文学》,《明代传记丛刊》本,台北: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这当然是激愤之辞,既然不能明哲保身,则读书即便无罪,也未必能发祥吧!
正因该祥占与宋濂等浙东文人不幸遭遇相悖,故其“文物之祥”占语在后世未获充分解读;这不仅使宋濂、刘基、戴良等浙东文人出处大义隐晦不明,而且使浙东文人群落在入明前后文学活动的意义隐微难显。
综观之,这两起祥瑞虽逢共同的天下形势,但当事人的政治境遇又很不相同。其共同者,元末战乱,天下失控,两地文人都丧失所天,得不到元朝政权庇护。其不同者,西昌文人没有卷入割据政权,因而在政治上始终保持清白,其被征聘入明的身份,是为元末乱世之顺民,故与朱氏政权没有特别恩怨,易于顺利归化为明朝的臣子;浙东文人率先投附朱氏政权,因而在政治上处于特殊境地,其辅佐创立大明新朝,虽膺开国文勋之赞誉,但毕竟对亡元旧朝有亏臣节,且与朱元璋的恩怨纠缠不清。这使得两地文人政治际遇,亦呈现为前后盛衰之不同:西昌文人入明之初虽官位不够隆显,但愈往后愈表现出强劲的政治命运;浙东文人归附之初即获致位高权重,但愈往后愈遭受铲除终至群体消灭。即以江右大儒陈谟、浙东儒宗宋濂来说:国初,陈谟以老迈之躯,犹被征舆曵就道,及入朝见驾,所论又不合,乃以老病辞,而命驾还山。[注]陈谟:《海桑集》卷首“四库馆臣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实,陈谟不得其用,应与宋濂有关。盖因宋濂归附朱元璋更早,以浙东儒宗已为文臣之首;而陈谟属后来,已无合适位置。既然无所容身,不如命驾还山。像陈谟这样命驾还山,虽受折腾而落寞失意,但得以寿考善终,实属不幸之万幸。而宋濂宠极文臣,虽应文物之祥,但最后不得善终,实属万幸之不幸。此人群升降及人生际遇之幸与不幸,恰深切揭示了解读两起祥瑞的背景。
二、 西昌十名贤对文明发祥的感应
如前文所述,刘崧《萧氏芝草记》以家国祯祥之命意,阐发并预言了元末乱世社会政治之趋向;半个世纪后,杨士奇《题萧氏瑞芝诗文后》承其绪论,因以阐扬萧氏芝草呈瑞及文明发祥之义。如果说杨士奇以馆阁重臣来领袖风雅,其解读瑞芝诗文有阐扬乡邦文献之意;那么刘崧于衰亡之际预见家国祯祥,则是对风俗教化和家国气运的感应。这感应出自瑞芝叙咏参与者的天属,是自然情性的抒发而非刻意之矫饰。
据相关资料显示,因常遭流寇侵扰,当地士绅长年窜伏山林,很难有雅集酬唱的机缘;故西昌十名贤之叙咏萧氏瑞芝,并不是同一时间聚齐萧氏故居,而是先后慕名过访萧氏桃源里,得观赏瑞芝而各以诗文叙咏之。此十名贤的基本信息,可列表综述如下:[注]该“西昌十名贤(附萧斯和)基本信息分析表”之编制以杨士奇《题萧氏瑞芝诗文后》为标本。

十名贤学承交游出处儒行文品康震字宗武号匡山先生师从吴澄齐鲁关陕之士多从之游庆洲书院山长/退隐乡里学行醇实阙杨望之字公望号望之先生承待制公家学受虞文靖、欧阳楚文诸公推许隐处操行之峻洁文学高古刘楚字子高号槎翁后更名崧阙阙隐处/入明仕至权吏部尚书尽诚敬以事上,谨于职任,务当大体阙王沂字子与号竹亭阙阙隐处/入明征授同知福建盐运司,未赴任矩度严肃,学者敬而亲之辞气温裕王佑字子启阙阙隐处/入明授监察御史等官锄奸植善,风概凛然阙欧阳铭字日新又字仲元阙阙隐处/入明为临淄令其政宽简,而重礼教,有古循吏风阙杨卓字自立又字子渊号退庵阙阙隐处/入明为吏部主事、杭州府通判罗性字子理阙阙隐处/入明为德安府同知邓尚字彦高又字崇志阙阙隐处/入明为四川盐运司经历砥砺踔绝,冰蘗不过,不怍古人,造次隐微之际,必在于所学,卒时不蓄一钱阙阙阙张虎字子召阙阙隐处/入明为丞于蜀治民以平易,而持己介然阙萧斯和阙阙隐处富而好礼,积而能施,以保障其乡自任阙
从这个分析表可知,杨士奇撰《题萧氏瑞芝诗文后》,论述了十名贤及萧氏的儒行文品,特看重德性与艺文双修之特征,而于诸贤的儒行学术尤致意焉;西昌十名贤大多宗尚儒学,是一个有隐逸情怀的文人群体。
总之,这次萧氏瑞芝诗文叙咏,实为西昌文学活动大事。它不仅吸引当时西昌十名贤参与创作,后来还引起馆阁文学领袖杨士奇重视。其精心结撰《题萧氏瑞芝诗文后》,就从多层面阐述该事件的文学意义。
(一) 西昌十名贤率先感应到了时世运会。文曰:
当元季兵乱,四方涂炭之际,安正之父斯和,富而好礼,积而能施,屹然以保障其乡自任。卒之,其乡无寇盗攻剽之患,父子夫妇相保聚如平时。此芝所以发祥,而先生君子所以作为文章,称述咏叹,累累其盛如此也。其光远而信后,岂有穷哉?[注]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九《题萧氏瑞芝诗文后》,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0、130~131页。
“元季兵乱,四方涂炭”云云,包含西昌小环境与天下大环境。小环境,指西昌境内的骚乱;大环境,指大江南北的战乱。
从至正十七年(1357)开始,陈友谅部将熊天瑞侵扰江西,次年攻陷西昌,士绅转徙避乱。文中说,萧斯和“以保障其乡自任”、“无寇盗攻剽之患”、“父子夫妇相保聚”,指的就是在这次寇乱中,西昌故家旧族如何自保。然而,这只是西昌某乡某姓的特例,士民所受冲击实际是巨大的。如刘崧至正二十二年(1362)八月,与兄弟三家避乱长坑、里良等地,病疟流徙岩谷间,二子又相继死去;后又避兵南富、阆川、富田等地,迁延至二十五年(1365)明兵入据,才返故庐,重理旧业。从西昌小环境来看,刘崧等人是不幸的。
但从天下大环境看,西昌文人何尝不幸?当元末汝颍始乱,迅速波及江淮间,并蔓延东南数省。各地文人,骤遭世变,凄凄惶惶,不可终日。为自保图存,或身陷行伍,如淮西李善长辈,参谋朱元璋麾幕之下;或屈身事人,如吴中高启之流,投靠张士诚伪政权中;或委曲逢迎,如宣徽儒陶安等,诱导朱元璋仁武不杀。当各方势力攘夺之际,鹿死谁手未卜之时,与任何政权发生关系,都要冒极大的风险。而西昌文人除了躲避流寇侵扰,并不曾受胁迫来承担这种风险。特别是西昌相对僻静,又不当四战必争之地,故不必像浙东等地文人那样,必须面对极严峻险恶的形势。
当然,西昌文人其时未必意识到,自己处在相对安全的境地;但他们世世代代长养于此,对其处境实有天然的感应。故当江西盗起,各郡望风瓦解;而泰和的长官守将,能以忠义倡民固守。西昌因此号忠义之邦,而康震撰文纪颂之曰:“嗟尔丑类,胡然致寇。熊咆豕突,窥我江右。既陷九江,袁筠继之。惟我庐陵,有弗克支。桓桓西昌,屹乎其东。”[注]王琨辑:《泰和诗征》卷四康震《忠义之邦碑颂》,清光绪甲辰年孟秋萧氏闲余轩刻本。所以,尽管四境未绥,流寇还将再来;但只要贼寇稍稍退去,他们就回复原有状态。西昌十名贤的萧氏瑞芝叙咏,正反映了兵燹下的生存状态。
不仅如此,十名贤参与萧氏瑞芝叙咏,还表现了西昌的文化自信。杨士奇文说,芝之发祥与文章之盛,将光远而信后于无穷,这不是对萧氏及十名贤的简单溢美,而是对西昌文化价值的默会与认同。恰好刘崧在早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凡阴阳之和,委于物而自行,固将无所择地而出也。然亦有非偶然者矣。今斯草……独由然与蓬蒿瓦砾偕处于林泉寂寞之滨,而得以全其天和,将非幸哉?”说芝草因处林泉,而得以全其天和。至若芝草比况人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国家将兴,必有祯祥。……是天将兴其家,而未艾也。夫为孝子而瑞于家,为良臣而瑞于国,萧氏其必有当之者矣。君其仁以滋之,厚以培之,必有钟和蕴秀以济太平之运者,岂徒为草木之美观而已哉?”[注]刘崧:《槎翁文集》卷五《萧氏芝草记》。
这类似的话,同样的思致,在当初刘崧,是为一个预言;而在杨士奇,则是一重认证:西昌十名贤虽身居乱世,却率先感应了时世运会,预言将有家国太平之兴,而士当为孝子良臣之用。
(二) 西昌十名贤的儒行及文学活动心态。《题萧氏瑞芝诗文后》又曰:
夫事以文显,文以人传,不知其人,读其文,而欲信之不疑,难矣。当是时,江右文物盛于吾州,诸先生君子或仕而既退,或隐而未出,旦暮聚处,相与磨切颉颃,所自树皆不肯苟且在古人下。……夫惟不言,言必有征,萧氏斯文之著,夫岂偶然之故哉?余少时亲睹刘先生以下数君子与安正往还契好甚厚,每游桃源山中,必过凌云轩,留止数日,极欢然后去。要之,不独文字之交而已。然则,览斯文者,萧氏先德之征,西昌名贤之众,安正交游之盛,概可见矣。④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九《题萧氏瑞芝诗文后》,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0、130~131页。
此所云“事”是指萧氏产瑞芝,“文”是指《瑞芝诗文》十首,“人”是指十名贤与萧氏祖孙。即事成文,而事以文显;文以人传,需知人论世。西昌文人之立身处世为文,于十名贤及萧氏可见大概:
从出处来看,他们多隐而不出,或既仕而后退,因而安居乡里,栖心游于道艺。这种隐处超脱、不求仕进的态度,既能坚守西昌人士耕读自守的志业,也能适应蒙元政权种姓制度之压抑。所以康震赞曰:“惟此西昌,如适乐土,桑麻蔽野,多稌多黍;惟此西昌,父子兄弟,岁时伏腊,优游田里。”[注]王琨辑:《泰和诗征》卷四康震《忠义之邦碑颂》。而十名贤《瑞芝诗文》,亦多以仙隐修德相劝勉。[注]有诗为证,如欧阳铭《瑞芝》:“私缘仙隐出,端许歌乐传。羡汝阶庭秀,相看共郁然”;王佑《题桃源萧氏瑞芝》“我亦逃名避世喧,种桃久拟觅桃源。明月还共吹箫者,手把灵芝倾玉樽”;杨卓《咏桃源萧氏瑞芝》:“怅令德兮弥修,俨神盼兮欲留。揽月袂兮披云裘,仙之徒兮从尔游”(以上分别见《泰和诗征》卷五、卷六、卷八)。
从交游来看,他们有深厚的家族文化底蕴,因而居处交往能够数辈同乐,而又秩序井然,不曾非分越礼。即以十名贤辈分来说,若依杨士奇行辈推算,有曾祖辈康震、杨望之,祖辈王沂、王佑、刘崧,父辈欧阳铭、杨卓、罗性、邓尚,而张虎“后出”在父辈与同辈间。考十名贤之来源,多出自故家旧族。其家族之间多世通婚姻,而成员之间亦递相师友;所谓“先德之征”“名贤之众”“交游之盛”,说的就是这种有故家旧族文化背景的交往实况。如欧阳铭为康震与杨望之私淑弟子,则是师徒共同参与萧氏瑞芝笔会了。[注]参见杨士奇:《东里文集》卷四《康氏族谱序》、卷十一《书欧阳临淄传后》。
从志尚来看,他们流连诗酒,好以文字交欢;还能涵泳德性,恒以道义相尚;更兼递相师友,共期进德修业。如十名贤中的杨罗邓,“三先生布衣时,为金石交,时称‘杨罗邓’,砥砺踔绝,冰蘗不过。其将仕也,相与约曰:‘吾徒幸获事明天子,行或纤介有怍古人,复何颜相见哉?’其后,杨先生自吏部主事四迁,通判杭州府;罗先生为德安府同知;邓先生为四川盐运司经历。三先生居官,虽造次隐微之际,必在于所学,其卒也皆不蓄一钱,以遗其家。”[注]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九《题萧氏瑞芝诗文后》,第131页。又如王沂:“幼读《孟子》,即知辨于义利”,“自六经至于周、程、朱、张之书,靡不深究,及子史百氏,咸旁通博考”;故时贤赞曰:“使及门孔氏,则风雩之咏归,端章甫之礼乐,固将进退绰然,而特视其所合。”[注]杨士奇:《东里文集》卷十八《王竹亭先生墓志铭》,第258、259页。
(三) 西昌十名贤所表率的雅正文学风范。《题萧氏瑞芝诗文后》一文,还论述了十名贤的儒行文品。论儒行,则有康震之“学行醇实”,杨望之的“操行之峻洁”,刘崧之“尽诚敬以事上,谨于职任,务当大体”,王沂之“矩度严肃,学者敬而亲之”,王佑之“锄奸植善,风概凛然”,欧阳铭之“其政宽简,而重礼教,有古循吏风”,杨罗邓之“砥砺踔绝,冰蘗不过,不怍古人,造次隐微之际,必在于所学,卒时不蓄一钱”,张虎之“治民以平易,而持己介然”,萧斯和之“富而好礼,积而能施,屹然以保障其乡自任”;论文品,则有王沂之“辞气温裕”,杨望之的“文学高古”。
再从其他相关文字记述来看,西昌十名贤都宗尚雅正文风。如刘崧“为文雅粹,为诗有唐人风韵”[注]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五十五《侍郎刘崧》,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倡言“雅道今如此,古人端可师”[注]刘崧:《槎翁诗集》卷四《示刘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沂“以商确[榷]雅道为己事,温厚和平出于自然,而音调格律之严必合于典则”[注]梁潜:《泊庵集》卷八《竹亭王先生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欧阳铭“为文清丽典赡,思若决河”[注]王直:《抑庵文集》卷十一《故临淄知县欧阳府君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更为重要的是,十名贤志尚高雅,他们除了相互交流协作,还组成多层次文人圈属;因而实际领导着当地文学活动,来共同推进西昌雅正文学创作。比如,康震有二弟能文,是为康氏三贤才;刘崧与兄弟并称“珠林三杰”,又与欧阳铭并称“江右二贤”;王沂与弟王佑,并称“二妙”;杨卓与罗性、邓尚,并称为“杨罗邓”;萧斯和与子廉、孙应,并称为“萧氏三贤”。
更可以萧氏瑞芝诗文印证之。王佑《题桃源萧氏瑞芝》云:“琬琰何烦种植工,生成应见陶钧力。夷齐不足夸采薇,楚皋猗兰安可希?轻芬飘翩逐风去,凡卉讵敢含华滋?商山岹峣峙云峤,四皓云遥三秀燿。避世狂歌自有神,千年高躅谁同调?我亦逃名避世喧,种桃久拟觅桃源。”[注]王琨辑:《泰和诗征》卷六王佑《题桃源萧氏瑞芝》。当元末乱世,不可有作为,乃欲觅桃源,以逃名避喧;当开国兴治,则承运而起,乃效力君国,使文明发祥;故杨士奇叙曰:“江西既内附,先生(王佑)首举教官,吏部试中经义,偕十八人者入见。是日,太史奏星相文明之祥;太祖皇帝喜,皆除监察御使,赐袭衣,又赐宴御使台。”[注]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二十二《王先生传》,第332页。
如上三方面文学意义,概言之就是文明发祥。这在元末西昌十名贤那里,或是出乎各人天性的感应;而在入明的刘崧、杨士奇辈,则是接引西昌雅正文学风范,通往馆阁而创新台阁体,因以主导明初文学走向。这不仅带动此方文士络绎进入馆阁翰苑,而且以其典雅平和气度来修饰盛国气象。[注]参见饶龙隼:《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西昌雅正文学的生长历程》,《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饶龙隼:《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图表十八 明初浙赣(泰和)籍文人出任翰林院及馆阁官职统计分析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357页。
三、 浙东文人入明后的文学观调适
如前所述,宋濂占祥,固出于决一己之疑,却也表露一种意绪。这种意绪在若隐若现之间,表面上是对己境遇的回应,深层却有其生命哲学根源,是他人生困惑的诗性表达。
宋濂曾撰《禄命辨》,论人生富贵寿夭之理,认为万物皆出于五行,五行之外则别无所主;故不信占卜、推测之事,而于禄命之说一概摒绝。其文曰:
人之赋气,有薄厚长短,而贵富贱贫寿夭六者随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测也。蹈道而修德,服仁而惇义,此吾之所当为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后知之也。予身修矣,倘贫贱如原宪,短命如颜渊,虽晋楚之富、赵孟之贵、彭铿之寿,有不能及者矣。命则付之于天,道则责成于己,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注]宋濂:《銮坡后集》卷六《禄命辨》,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674页。
该文是为告示江西刘永之而作,故颇引起江西大儒陈谟的共鸣。[注]佚名编:《潜溪录》卷五陈谟《书萧执所藏宋景濂〈禄命辨〉后》,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2571页。但他在《赣州圣济庙灵迹碑》中却说:
濂稽诸经,国有凶荒,则索鬼神而祭之;士有疾病,则行祷于五祀。先王必以神为可依,故建是祠祝之制也。世之号为儒者,多指鬼神于茫昧,稍与语及之,弗以为诬,则斥为惑,不几于悖经矣乎?有若神者,功在国家,德被生民,自汉及今,孰不依之?虽近代名臣若刘安世、若苏轼兄弟、若洪迈、若辛弃疾、若文天祥,亦勤勤致敬而弗少怠。是数君子者,将非儒也邪?何其与世人异也![注]宋濂:《銮坡前集》卷五《赣州圣济庙灵迹碑》,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434页。
该段下文即接宋濂自占得“文物之祥”语,可见他又信“入翰林为学士”是出于禄命。这显然是与《禄命辨》相矛盾的,故知宋濂诚如朱元璋所说非纯儒,虽平常不信禄命之说,但亦非一概排斥占祥。因之亦可以说,这“文物之祥”占的适时呈现,恰为宋濂人生忧危困惑的表象;也可反过来说,宋濂所遭遇的人生忧危困惑,有赖“文物之祥”占来慰藉。
身处元末乱世之危难局势,浙东文人做梦也不曾想到,枭雄中竟会有“明主”,能诱使他们委身而事之。然而期待明主以事之,这是儒士的常规志愿,浙东文人不例外,宋濂也不会例外。寻想宋濂正值壮年而遁迹退隐仙华山时,戴良撰《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并举用、晦二义,来婉讽他的避世。宋濂作《龙门子凝道记》回应之,其书卷上《终胥符第三》申辩曰:“我岂遂忘斯世哉?……予岂若小丈夫乎?长往山林而不返乎?未有用我者尔,苟用我,我岂不能平治天下乎?”[注]宋濂:《龙门子凝道记》卷上《终胥符第三》,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1761、1762页。这是说,若有“用我”者,他就能平治天下。宋濂曾作《诘皓华文》,称士不当图一己之安乐,而应忧世艰、民瘁、道坠,以救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注]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二十五《诘皓华文》,《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这似乎在说,归附朱氏乃责任感使然,故不太介意人主的品性。其实就在此前不久,他领略过朱元璋嗜杀[注]刘辰:《国初事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据该书载,朱文忠在金华时,用儒士屠性、孙覆、许元、王天锡、王袆干预公事。朱元璋闻之,差人提取屠性等人到京, 命王袆、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写,而诛杀屠性、孙覆二人。;只因他的一厢情愿,而不多加考虑罢了。而“文物之祥”占语,恰满足了宋濂的心愿。可见,归附之心一旦萌动,宋濂便不能自已了;而为了释除前疑,便以神物证成之。也是因这一厢情愿,他已不听戴良忠告:“云路多鹰隼,烟波有虞机。”[注]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十《寄宋景濂三首》之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但浙东文人自居理学正宗,其立身用世还有特立之处。他们愿否委身忠心事主,仅逢“用我”者还不够;这“用我”者除了必须是明主,还要用我所怀之道以使我悦服。如刘基见乱不可为,乃隐居入青田山中,著《郁离子》以明志,其《枸橼》即这样说:“鸟兽以山薮为家,而豢养于樊笼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驯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无违也。……人与人为同类,其情为易通,非若鸟兽之无知也。而欲夺其所好,遗之以其所不好;绝其所欲,强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从,其果心悦而诚服耶?其亦有所顾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悦诚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国,徇吾事;则尧舜亦不能矣。”[注]刘基:《诚意伯文集》卷十八《郁离子·枸橼》,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台北:台湾世界书局,1988年。
所以,宋濂是表率浙东文人群体,以其所抱持浙东“正学”、深藏难掩的择主心态,来投附假想的明主朱元璋。其“文物之祥”不是对皇明文治的感应,而是对理想国度和假想明主的心理调适。与萧氏瑞芝诗文感应文明发祥相比,这种心理调适有先天的缺陷和不足:(一)宋濂及其同人心有所主,就不容易做到委弃自我;(二)不能委弃自我就会自是,以固执己见而触犯主怒;(三)一旦触犯主怒就被不容,以致被君疏远终至铲除;(四)人既铲除主体性就消失,其“正学”便遏塞消歇。正是在宋濂同人自我调适的愿景下,其所表彰的浙东文学观也有所调适。故而,尽管金华文学有丰富的思想资源、深厚的绵延不绝的艺术内涵,但在丰厚绵延之中,亦非执着一成不变,特别是在以群落归附新朝后,为修饰皇明政权而有所调适。
就在至正二十年(1360)赴南京前夕,宋濂已开始自我反思早前的文学观点。他说:
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至三十时,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及逾四十,辄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时复一践之。五十以后,非惟悔之,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自以为七尺之躯,参于三才,而与周公、仲尼同一恒性,乃溺于文辞,流荡忘返,不知老之将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毁笔研,而游心于沂泗之滨矣。[注]宋濂:《銮坡前集》卷十《赠梁建中序》,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558页。
以此看来,宋濂似乎自十七八岁开始,就不断调正他的文学思想;但实际上,这只是后来追述的堂皇之辞,目的是为适应新朝而作铺垫。因为就在该文写作稍后,即当年的三月一日,宋濂等浙东四先生被礼聘至南京,应验了行前所得“文物之祥”占;故知,宋濂撰写该文,绝非随意巧合,而是有深刻的理论预见性,为迎合皇明大雅自我调适。由宋濂三十岁“悔之”,再到四十岁“大悔之”,终至五十岁“大愧之”“大恨之”,其调正文学观之事或早已悄然发生,但他一直似无清醒的知觉,需到入明前才有明确认知。由摹研文辞句法,到为文能有自得,再转向深研儒家理道,终至于游心圣贤境界,这既是宋濂文学思想逐步成熟的过程,更是对将以文学修饰皇明文治之趋迎。
宋濂入仕新朝,可谓如期而至;宠为文臣之首,亦为如愿以偿。当国家初立、百废待兴、人心不稳、纲常未立之际,急需整顿社会秩序,振兴文化价值,重建道德规范。为了适应这样的社会文化需要,就须摒弃元末绮弱哀怨的文风,倡导适应胜国气象的新文风,这就是明初文臣的首要任务。宋濂作为文臣之首,当然要为翰苑表率,“立心制作”以推行文学革新,促使辞藻之文向治道之文转变,希望通过弘扬儒家正统诗教,来建立敦大和雅的盛国文风。故宋濂入明以后所作诗文,大多雍容典雅、纯和冲粹。[注]参见宋濂:《潜溪后集》卷四《答章秀才论诗书》、《銮坡后集》卷一《见山楼记》,均见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这也表明,入明之后,宋濂调适文学思想,已取得初步的成效。但这调适只是初步的,还不够彻底。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三重原因:(一)元末的旧文风积弊太深,非短时间所能克服,而有一个新旧交替消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不断摸索与尝试;(二)明初各地文人以群落归附明廷,共同汇聚新朝而呈多元并存局面,各地文学风尚就被带入朝堂,而非金华一地文风所能掩抑;(三)开国之初庶务丛杂,未遑文雅制作之事,一时还不确定新文学风尚如何,故对文学变革仍缺乏强力推动。
正是基于特定的文学环境,宋濂才调适金华文学思想,而不曾高调推行文学革新运动,亦未以金华文学思想强加于人。因之,宋濂的做法是理智而节制的,他只做文臣之首所能做的事,一边调适自己的文学思想,一边对文学多样表示宽容。当时朝中词臣及草野文士论文,好为“台阁”“山林”之区分,“台阁之文”代指庙堂文学趋尚,“山林之文”代指地方文学习气。宋濂虽亦认为“山林枯槁”,但他并不排斥“山林之文”。[注]参见宋濂:《翰苑别集》卷三《佛真文懿禅师无梦和上碑碣》,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他曾说:
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惟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濂尝以此而求诸家之诗,其见于山林者,无非风云月露之形、花木虫鱼之玩、山川原隰之胜而已,然其情也曲以畅,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处台阁则不然,览乎城观宫阙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故不发则已,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而镗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注]宋濂:《銮坡前集》卷七《汪右丞诗集序》,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481页。类似的论说,还见于另文:“予闻昔人论文,有山林、台阁之异。山林之文,其气瑟缩而枯槁;台阁之文,其体绚丽而丰腴。此无他,所处之地不同,而所托之兴有异也。有立以粹然之学,位居柱史,日趋殿陛,濡毫螭坳,回视山林,不翅有仙凡之隔。故其见于辞者,云锦张而春葩明,钟簴奏而音律谐,体制正而局度严,诚可以传诸当今,而垂于久远者也。”(《翰苑续集》卷四《蒋录事诗集后》,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
后人区分宋濂入明前后的文学思想,往往以《汪右丞诗集序》为转折点,认为入明前所作是“山林之文”,入明后所作是“台阁之文”;宋濂入明之后,受朱氏皇权压迫,其文学生涯进入低谷,因而所作多“台阁之文”。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未切宋濂持论之心意。宋濂之所以比较“山林之文”“台阁之文”,导出“所居之地不同……发于言辞之或异”,旨在说明两种文学体格之异,乃因于作家所处境遇之不同。其“所居之移人”云云,既是讲入明的各地文人,也是讲入明的文风新变。这种文风新变,既关乎文学的题材、主张、宗旨等,还关乎体国经邦、教化民俗之功用。宋濂这么说,只是表明文学应该适时而变,并非褒“台阁”贬“山林”。
正是基于这种理智而节制的认识,他才援引《诗经》三体来比附之:
虽然,诗之体有三,曰风,曰雅,曰颂而已。风则里巷歌谣之辞,多出于氓隶女妇之手,髣髴有类乎山林;雅、颂之制则施之于朝会,施之于燕飨,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为,其亦近于台阁矣乎!轩之使弗设,而托之于国风者,若无所用之;皇上方垂意礼乐之事,岂不有撰为雅、颂,以为一代之盛典乎。[注]宋濂:《銮坡前集》卷七《汪右丞诗集序》,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482页。
宋濂之意,并不认为台阁之文独尊,可以掩抑消泯山林之文;而是认为山林与台阁并存,不可崇此抑彼而有所偏废。只是当皇明开国之初,朝廷未遑设轩之使,而注重礼乐之事罢了,因使“台阁之文”为“一代之盛典”,而“山林之文”暂时“若无所用之”。他这样保守节制地衡文,实为“山林之文”留地。因为,他很清楚明初朝堂多地文学并存局面,而作为开国文坛领袖就不能漠然视之;所以,宋濂只调适自己的文学观点,而非轻妄推行金华文学思想。这种态度与策略是切实妥当的,照顾到明初文坛混杂的状况。既为入明各地域文学保留适度空间,又守护了自己抱持的金华文学理念。这就使金华文学思想的调适,竟不由自主地走向二元分裂。
由此可知,金华文人群落入明之后,游移在乡邦与朝堂之间,不仅身心陷入进退两难境地,其文学思想也经受二元分裂。所以,一方面,宋濂为倡建开国文风倾注心血,时常为之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他又对参预文学侍御感到厌倦,不时因之黯然神伤。他虽撰写了许多“台阁之文”,如有轰动朝野的《平江汉颂》,是谓“廊庙之文,所以异于山林也”[注]王崇炳编:《金华文略》卷十九《平江汉颂》附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但他又对此类馆阁制作大为不满,仍怀念早年伏居乡间的山林之作。他曾痛心自省曰:
窃自叹赋才暗劣,规规方圆中,日蹈古人轨辙,不敢奋迅吐一奇崛语。虽见诸简牍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无气人。作文固当如是邪?[注]宋濂:《銮坡前集》卷七《詹学士文集序》,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483页。
综上所述,两起祥瑞,一出于感应,一出于调适。感应者,能够心无所主,纯乎天性,随顺委蛇,虚怀纳物;这在人生出处上,就表现为不择主而事、不择地而居、不择官而处,而在明初极端皇权政治高压下拥有更强的适应性。调适者,恒常心有所主,动依理道,坚守己见,触物皆忤;这在人生出处上,就表现为欲择主而事、欲择地而居、欲择官而处,而在明初极端皇权政治高压下缺乏更强的适应性。故而,陈谟与人主不合,而甘愿息心命驾还山;刘崧以廉慎所历多官,而终以老迈荣膺恩宠;杨士奇每每化险为夷,辅弼五朝而终致太平。然则,宋濂侍奉假想的明主,宠遇愈隆而危机愈深;又倾其所学教导太子,竟使得太子过于仁柔;方孝孺以周礼诱导幼主,终使建文帝庸弱失国。
此两地文人行为之差异,乃在于各自的思想根源有别。宋濂、方孝孺等浙东文人自居理学正宗,企图用自己所抱持的浙东正学修饰皇权,不论是假想朱元璋为明主,还是将太子朱标教得仁柔,抑或诱导建文帝修复周礼,其奉御的方式虽不断翻新,却都是用理道约束人君的尝试,实质上流露出深层的择主心态。这择主心态根深蒂固,以至终身都难以消释。宋濂《绝命词》曰:“平生无别念,念念在麟溪。”[注]佚名编:《潜溪录》卷一郑柏《宋潜溪先生遗像记》载录,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2304页。其所执念的这“麟溪”,是浦江郑氏义门的象征;宋濂入明前长期主讲郑氏义门塾学,平生唯在此得以大力弘扬程朱理学。方孝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注]张廷玉:《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载录,《二十四史》缩印本。方孝孺抗辩朱棣篡位,宁诛十族亦不肯草诏,则其择主之心志,至死仍执迷不悟。
与浙东文人执意择主不同,西昌文人是秉承另类儒学,援引庄子道旨入儒,不以己学强非其君。陈谟撰《通塞论》,其文开宗明义畅言:“知通而不知塞,贪宠之民也;知塞而不知通,执一之见也。然则孰为近?曰:塞而知其通焉,不胶于塞;通而知其塞焉,不流于通,斯近矣。”[注]陈谟:《海桑集》卷三《通塞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此可知,陈谟命驾还山,其高明处在于:“知塞”而能“不胶”,“不胶”适为求“通”。这就难怪同样面临朱棣靖难造成的变局,杨士奇会作出与方孝孺完全不同的政治抉择。盖杨是陈谟的外孙,自当领教通塞之论。从陈谟命驾还山到杨士奇历事五朝,西昌文人拥有对政局更强的适应性。
也正是得益于自身更强的适应性,西昌文人在政治高压下保有后劲;并因着此方文学主体的延续,将西昌雅正文学接引入馆阁;又因着宰辅杨士奇的大力阐扬,而将馆阁文学风范推广到朝野。也正是受累于自身更弱的适应性,浙东文人在政治高压下缺乏后劲;并因着此方文学主体被掩抑,而使其调适过的文学观失效;又因着方孝孺抗命株连十族,而使浙东文学传统顿然消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