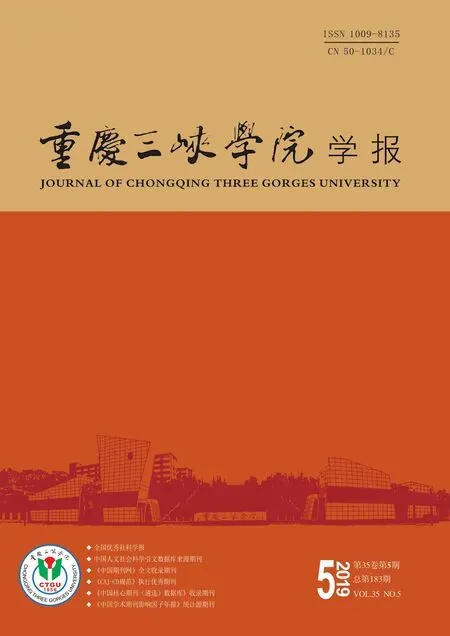民俗控制性叙事、角色形塑与壮族师公叙事传统
——以广西凤梧镇韦锦利师公班为例
2019-03-22王志清
陈 曲 王志清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404020)
壮族师公叙事传统是以壮族师公在受戒、丧葬等仪式的民俗系统中进行叙事活动的文化传统。其以传承谱系作为叙事背景框架,以师公教信仰及行为实践作为叙事动力,以“阴泰阳安”观念作为内在的文化逻辑。叙事传统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源于过去而又不断地作用于现在,具体的叙事实践以民俗控制性叙事作为主要内容及表现形态,以具体的民俗链作为叙事表达单元,将某一师公组织的具体活动范围作为叙事论域。纵观师公传承历史,叙事传统成为建构师公身份的一种文化标志,其中民俗控制性叙事成为形塑师公角色的主要手段。师公叙事传统在师公班这一具体组织内进行传承与展演。师公班主要是以当地某一位较有威望的师公牵头,通过师徒关系、亲属关系等缔结而成的具有合作性质的团体,根据丧葬、打斋等仪式的规模大小、耗时长短、耗资多少等不同情况,随机组合成6、7、8 或12人的团队进行相应的民俗活动①文中所引用的田野调查资料均来自笔者的实际访谈,如有不妥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笔者曾作为“第三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工作坊(VRFW)”的成员于2016年7月15日至8月1日在广西平果县凤梧镇的韦锦利师公文化传承基地进行专题田野考察,并借鉴辽宁大学江帆教授多次追踪研究民间故事家谭振山的专项田野调查方法[1],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期间同师公韦锦利进行多次通话访谈。笔者参考“感受生活的民俗学”②“民俗,不只是研究对象的集合性概念,还指明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根本视角。这就是要求通过民俗来观察一定地域和人群的生活,考察他们在那里一代代传承的文化。艺术家是借助某种模式化的艺术来感受生活,而民俗学者则经由模式化的民俗来感受生活。民俗的传承与变迁从来都是与具体的人群、个人连接在一起,同时又与时代社会背景紧密联系,所以民俗志研究可以将问题、事件、人都凝结于富有弹性变化的表达与呈现之中,这是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所以该追求的。”参见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的理论观点,依据现场参与观察及韦锦利等多位师公提供的口述、文献资料,分析韦锦利师公班中民俗控制性叙事与形塑师公角色的有机联系,阐释地方性知识如何形塑师公行为方式的文化惯习,深度理解作为当地文化持有者的师公如何感受师公组织的语言叙事与行为叙事,通过一系列“体化实践”[2]建构壮族师公叙事传统。
一、“子承父业与父不为师”——家传与师传的有机融合
关于如何确定师公人选即个体如何加盟师公组织问题,我们访谈了多位韦锦利师公班成员。综合访谈资料了解到当地确定师公人选有两种类型:一是“命定说”,具体情境为某人经常遭遇病患,久治不愈后就会向巫婆咨询,经巫婆测算后方知此人生辰八字契合师公命,须做师公才能摆脱患病厄运;二为“子承父业”说,当地师公组织有约定俗成的行规,师公之家须至少有一位后人担任师公,否则有师公宿命的后人会多灾多难。当下加盟师公组织的方式与昔时相比略有变化,更具宽容性,即80后、90后的青年人若有意愿做师公者可以直接拜师学艺,不再过分强调其家庭出身。不过此种情况属于小概率事件,几乎可忽略不计。
考察韦锦利的师承谱系以及师公班成员,以“子承父业”类型居多。通过访谈了解,韦锦利的大师兄兰瑞珊于1982年拜师受戒,系兰家第二十代师公;韦锦利的徒弟卢海堂是20世纪70年代生人,为卢氏家族第三代师公。据韦锦利介绍,其师傅兰安基生于1932年,14岁继承祖业当师公,是兰家第十代师公,其子兰毓风、兰毓东均继承祖业,成为兰家第十一代师公。韦锦利20岁时接受受戒仪式成为师公,系韦氏家族第十六代师公。“韦家的师公直系传承为:第一代法丹师傅→第二代法应师傅→第三代道总师傅→第四代承印师傅→第五代文贵师傅→第六代文行师傅→第七代文学师傅→第八代应法师傅→第九代接教师傅→第十代承师师傅→第十一代授教师傅→第十二代理明师傅→第十三代秀松师傅→第十四代承德师傅→第十五代秀珊师傅→第十六代接印师傅(韦锦利)。”[3]17-18连亘的韦氏家族传承谱系足以说明师公组织“子承父业”传承模式的悠久历史,但该谱系并不能说明师公的师承关系。也就是说,父子之间在名份上并不存在师徒关系,即“子承父业,父不为师”。当地师公的解释是“遵守老祖宗传下来的三代之内不能直接给后人当师傅的说法”①源于作者田野访谈笔记。访谈对象:韦锦利;访谈时间:2016年7月23日;访谈地点:韦锦利家。。作为师公的父亲可以给儿子实际传授师公技艺,但二者绝无师徒名份,儿子必须在父亲同行中拜师受戒,确立师公身份。师公韦世松引用富有生活经验的俗语“牛尾打牛,牛不动”②源于作者田野访谈笔记。访谈对象:韦世松;访谈时间:2016年7月23日;访谈地点:韦锦利家。解释“父不为师”的原因,认为父子之间如果是师徒关系,必然会造成双方因为过于熟悉而出现授业不专、学艺不精的后果,不利于师公整体的良性传承和发展。
选定师公人选的传承活动在现实中往往呈现为“子承父业”与“命定”两种类型有机融合,即以“命定”说的观念作为基调,以“子承父业”的形式为主流。例如韦锦利讲述了个人的从师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得大病两年,那时候我家生活贫穷,无法去医院留医,只是请巫师来消灾。病也不好,越来越严重,结果去求巫娘。巫娘说,我公公(爷爷)要给我接祖师香火。后来我真的决定做了,又到神台前为祖师奠酒、认错,病渐渐好了。我于1986年拜师受戒,当师傅了。至今我有徒儿18人。”①源于作者田野访谈笔记。访谈对象:韦锦利;访谈时间:2016年7月23日;访谈地点:韦锦利家。韦锦利的“患病不愈——问巫指路——命交华盖——入门免灾”的从师过程在当地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模式。韦锦利还列举其徒弟韦承新的从师经历予以佐证。
韦承新是平果县凤梧镇龙林村弄屯人,小学毕业后就去广东打工。期间经常生病,于是他家人就找巫婆卜问。巫婆说因为他爷爷是师公,命中注定他是师公传人,经常患病的原因是当过师公的去世祖先在提醒他,抓紧举行受戒仪式成为师公。按照我们师公教从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祖上只要有人当过师公,后人就必须有人接班做师公,不能让师公坛的香火灭了。韦承新的父亲虽然一直干师公的活儿但始终没有受戒,不能算真正的师公。受戒对师公过关的要求很高,很多人都达不到要求,这种情况比较普遍。韦承新只有向去世的祖宗承诺当师公,这辈子才能身体健康,否则就会灾病连连。他家人后来又接连去找好几位道公给他算命,有道公告知他命带“华盖”,命中注定要继承祖上的师公身份。也有道公直接告知他这辈子就是和尚命,必须受戒做师公才能避免生病。于是韦承新也认为自己“命中注定”,就通过巫婆转告祖宗,承诺会受戒做师公。通过巫婆转告后没多久,他的身体就慢慢好转起来。他病好后就去广东打工赚了一笔钱,然后赶紧回家拜师做受戒仪式,所赚的钱用于受戒仪式的各项开销。2007年底,也就是他30岁那年从广东回来受戒当了师公。②源于作者田野访谈笔记。访谈对象:韦锦利;访谈时间:2016年7月23日;访谈地点:韦锦利家。相关事件介绍亦可参见陆秀春:《平果县凤梧壮族师公信仰习俗研究——以韦锦利师公班为例》,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可见,“子承父业、父不为师”“牛尾打牛,牛不动”等叙事并不是孤立地讲述事件,而是累积建构成民俗控制性叙事传统,而叙事传统又彰显“监测型、规约型民俗控制”的现实效用。例如“子承父业”就是师公组织内部带有强制执行特征的规约型民俗控制,即“以俗民群体制定约束成员行为的各种约法条例为标志的控制手段。这些约法条例的产生往往出自权威代表的决定或俗民群体公议制订,其表现形式或口头约定,或立据为证,形成条文。这约法条例的规约常被称为‘习惯法’。”[4]185而“父不为师”“牛尾打牛,牛不动”“巫婆(道公)指路——入门免灾”等则有监测型民俗控制的意味。监测型民俗控制“是有针对性的对民俗角色行为的或明或暗的日常管理,也可以明确地把它称之为习俗环境中的社会监控。这种监控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手段,既是一种机制,其本身也是一种惯习。这种监测可以形成一种习俗氛围或习俗压力”[4]180。
“子承父业”是发生在师公家庭内部的民俗控制性叙事。被外界视为神秘文化的师公文化在家庭中以常态化呈现,对于师公子女而言,耳濡目染的家庭氛围为其学习与师公相关的知识技能具有天然优势,提供现成基础。从事师公职业的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承担着师公做法等民俗行为的示范者、师公角色各项禁忌等民俗规范的监测者、师公唱本与演述等民俗知识的传授者等多种民俗角色,以师公教信仰为依托、以“阴泰阳安”观念为价值观基础的师公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的习俗化过程。“父不为师”与“牛尾打牛,牛不动”等事件中的师公个体与师公组织的互动联系,则彰显监测型民俗控制的测量和调适效用。通常一个师公班至少需要6人参加,因此要求组织成员必须进行集体性协作。基于这种现实需要,师公技艺传授必须克服“祖传秘方、绝不外流”式的保守性、封锁性传承,成员之间要通过父子血缘、师徒业缘关系的有效衔接建立起师公班这一共存共生性组织。
“巫婆(道公)指路——入门免灾”等叙事则体现出道公、巫婆等角色发挥着监测型民俗控制的监测和指导作用。任何来自师公家庭的子女都要面对当地民间信仰从业者群体的期待,传承弥久的“子承父业”这一“不成文法”的规范。道公、巫婆、师公在确定师公角色的习俗化过程中各司其职又通力合作。综合分析三者的职能及关系,可以了解当地各类民间信仰从业者交叉共生的社会事实,了解当地民间信仰体系的运行模式和文化逻辑。他们的合作方式是通过借助超自然力禳灾解惑的方式,使壮族民众“阴泰阳安”观念得以表达,有效维护当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鬼神(超自然)之间的既有秩序。
二、呈现互文性的口头演述与仪式展演
师公组织的受戒仪式是一次通过模拟人的诞生让公众认可师公身份的习俗化过程。对此,当地人的共识是某人经历受戒仪式后被民众承认终身拥有师公身份。有学者分析评述广西平果县壮族师公受戒仪式的特点,认为“整个受戒仪式都有道教的因素存在,内容涉及道教范畴的众多。当地民间宗教和道教的融合,并不是一味地向道教靠拢,而是积极地从道教中吸取有用的先进的内容为自己所用,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5]。田野调查期间,师公韦锦利依据师公唱本向笔者讲述了受戒仪式来历的传说。
师公们的祖师爷是鸿钧老祖,很早的时候他创立了一个教派,徒儿是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是道教的始祖,也就是我们师公所说的青都先生。太上老君的徒儿做法事时总出问题,于是他向鸿钧老祖询问原因。鸿钧老祖回答:“是因为凡人身体原有污秽不洁净,故不得投生换骨,令后生即成道(师)也。”太上老君又磕头继续问:“如凡人投胎,死去何以复生呢?”鸿钧老祖又答:“作为凡夫俗子的普通人,想要成为师公或道公,要在受戒前21天内的农历初一或十五这一天,准备一只公鸡、一碗米、一瓶酒、三百六十个铜钱,到师公或道公家拜师。到师傅家后徒儿把公鸡杀了收拾好,在师傅的师龛前拜祭各位阴师,然后破鸡胆,放到二杯白酒里和师傅对饮。师父每饮一杯酒就念道,‘今日受胎(受孕),弟子在腹内也’。离受戒还有9天时,徒儿又要拿着公鸡、酒和米再到师傅家去报龛,向诸位神像汇报。受戒剪头发的时候,师傅就要讲受戒九个月后换骨复生,这个徒儿就成为师公(道公)了。”①源于作者田野访谈笔记。访谈对象:韦锦利;访谈时间:2016年7月24日;访谈地点:韦锦利家;资料来源:韦锦利珍藏的师公唱本。
该传说文本中半文半白的语言讲述风格与攀经附典的文言文痕迹,体现的是作为师公的讲述者所强调的“语出有据”的效果。师公通过传说内容努力建构并说明受戒仪式的古老历史渊源,又通过叙事功能和内容着重强调此传说乃是“老祖宗的规矩”。就其结合壮族师公教悠久的历史渊源与引用道教始祖的托名言事的叙事策略来看,受戒仪式需要传说解释其合法性存在。亦如李亦园所说,“传说神话的出现应该属于比较晚的事,而很明显的传说神话的出现是用来支持仪式的执行”[6]。在学术界,“神话(传说)——仪式学派”所争论的先在性现象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热点论题,在此暂将该论题予以悬置,仅从民俗学维度分析论述民俗控制性叙事与师公角色形塑方面的关联性。现将韦锦利撰写的受戒仪式记录文本列举如下。
韦全福(我儿子)出生于1992年9月,受戒于2016年10月,法名为韦法亮。韦全福的戒度师傅是卢海堂、监度师傅是韦忠平、传度师傅是韦志德、职箓师傅是道公唐秀伦、坛越师傅是李建灵。韦全福求师拜师受戒的原因主要是受到我的影响,本人有继承师公文化的决心。他会画画、会雕刻、会使用师公需用的法器、面具、神像、服饰等,在师公活动中会唱、会打、会跳。我希望他做好师公文化传承,使我们韦家宗祖师香火坚持永远传承下去。
韦全福通过受戒仪式后就成了大家认可的师公师傅。2016年农历九月十五日,韦全福带着礼物去各位师傅家求师拜师。十月十日下午2点,各位师傅到齐,正式活动开始。安正坛、写疏表、挂神佛,准备好备用的物品(每一位师傅有一只马鸡——凤凰鸡)。下午4点开始“请水”,一位大师与道士一同到泉水边取五龙水,目的是取得五龙水后拿回来洗净弟子及各种新法器、新衣物等。晚上7时30分,受戒仪式入坛,道公师公合作、发鼓、禁坛(禁凶神恶鬼来骚扰这个活动场面)。晚上9时,一位师傅穿红衣红帽,恭请各位大神下降,目的是请大神驱邪恶魔、保佑场面平安。夜里12时,韦全福给各位大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及房叔兄弟姐妹们各敬酒一杯。诸位师傅们异口同声地问到:“各位老丈人们、房叔兄弟姐妹们,现在我们要弟子韦全福去做我们祖师的大徒,三元大神的龛位,你们同意不同意?”诸位亲戚大声回复:“同意”。问答环节结束后,两位大师把韦全福引入受戒考场中,通过各位大师的“清心”,围着考场唱经文。两个小时后,韦全福出来,师父们给他剪发“脱生”,清洗干净后他就成为师公了。从今以后可招收徒儿、做法事,秘法更可靠了,自己可以为民消灾解难了,法度也灵了。清晨4时,师傅们又给韦全福穿红衣红帽,又跳又唱地教他开师请神。清晨5时30分,诸位师傅又打着锣鼓带韦全福去山脚下庙亭拜庙、叩求,告知庙神和土地神。返回后,诸位师傅在神龛前告知韦全福师公的法度和未来四个月中的修身禁忌。受戒仪式的最后环节是散坛,韦全福在神龛前叩首、“化财”①依据韦锦利提供的手稿资料编写,2017年3月21日。。
对比分析韦锦利提供的两则材料,“投生换骨”的主题以及仪式的步骤环节、民俗符号的应用等在二者之间逐一映射。鸿钧老祖传说与师公受戒仪式之间呈现出“互为话语”(interdiscourse)的关系,即互文性。“‘互文性’一词,指的是一个(或多个)信号系统被移至另一系统中,就文本而言,就是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7]20依据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该民俗事件中所有在场的各种因素都在陈述。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没有一个陈述不是以其他陈述为前提的;没有一个陈述的周围没有一个共同的范围、序列和连续的效果、功能和角色的分配。”[8]受戒仪式与鸿钧老祖传说各自彰显其张力,将一代又一代置身其中的师公编织进一个既定的空间意义框架,通过沟通、互动与扮演,促进组织成员对师公身份的理解与记忆。“讲述人和听众相信与否的态度,不是对历史或科学的事实,或任何对真实或虚假的最终判断。……这是个主观判断,它建立在报告者的观念上,并非建立在客观事实上。”[9]师公组织成员秉持“阴泰阳安”观念的文化逻辑。鸿钧老祖传说在师公组织中作为规约型民俗控制性叙事规范着仪式的步骤与内容,指导组织成员顺利完成角色转换、身份标识和价值塑造。传说与仪式之间经过无数次的辐射和反馈、被选择性修正与强化后达成有机融合。作为一种认知性记忆的鸿钧老祖传说,实践作用于习惯性记忆的师公受戒仪式,形成仪式与传说的良性循环,推动师公组织持续性地进行富有生命力的传承。
三、结语:层累的习俗化活动与壮族师公叙事传统
“民俗是为一时一地的所有生活需求而设。它们是一致的、普遍适用于群体的、强制性的和恒常的。”[10]师公教作为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必然适应其特定族群与区域,师公作为成员必须扮演、承担其具有社会期望的规定性民俗角色。师公如何应对角色期待和行为要求?如何遵循职业上的习俗惯制,以他们特有的习俗行为模式显示身份?壮族师公叙事传统如何参与建构师公角色的形塑过程?在理论层面,民俗学的核心概念——习俗化,可以回应上述问题。“习俗化(conventionlization)是指任何个人从他所出生的环境中开始对习俗惯制的适应过程;也是群体对他们的成员个体施以习俗惯制的养成过程,即‘使习俗化’过程;同时也是个人在习俗体系中学习并增长习俗知识、培养习俗意识和能力的过程。这是民俗养成的最为重要的过程,也是任何人终生必不可少的习俗实践过程。”[3]72韦锦利师公班的师公角色建构机制即习俗化过程,师公们“子承父业与父不为师”的经验叙事、“牛尾打牛,牛不动”的日常俗语、家传与师传有机融合的叙事模式及作为解释性话语的鸿钧老祖传说与互文性的受戒仪式展演等一系列民俗控制性叙事,共同构成了师公角色形塑的习俗化过程,诠释了师公传承的“惯性”和从来如此的“如实性”(thus-ness)[11]。韦锦利等师公在不断的习俗化过程中约定俗成地形成师公谱系,层累地建构、丰富着壮族师公叙事传统,同时不断感受着叙事传统从而实践师公的传承机制,促使师公叙事传统成为师公身份的一种文化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