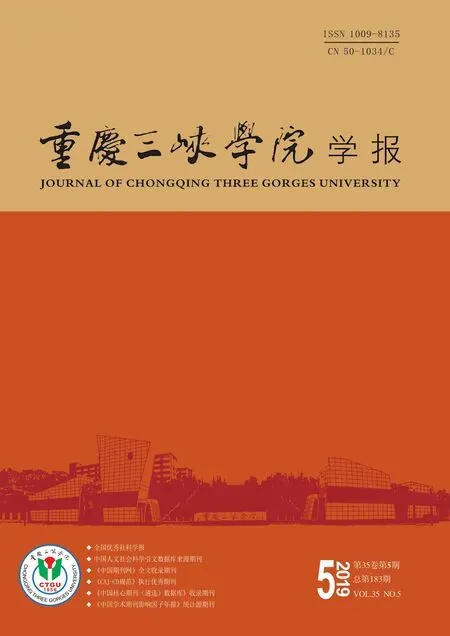中德美学之“意境”与“气氛”比较研究
2019-03-22王诗雨
王诗雨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西美学都十分关注的话题。中国古典美学历来崇尚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意境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是艺术家个体生命在自然中的对象化观照,是主体感性思维在特定情境中的诗意言说与诗性阐发,是天人合一、主客一体、时空结合、象内与象外之境的高度统一。气氛美学是德国美学家格诺特·波默在新现象学气氛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美学,是对当下美学片面注重理性判断的反叛。自康德、黑格尔以来,西方近代美学由鲍姆加通重视知、情、意,强调情感与想象在艺术创作中作用的感性学—美学逐步转变为判断美学,成了艺术批评家手中的理论工具。波默认为,这一转变是美学的狭隘化趋向,有必要对其加以扭转和改变。为此,波默从现象学、身体哲学出发,以人对自然的感性体验以及人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为切入点,主张美学回归鲍姆加通注重感性知觉的感性学—美学传统,将美学从精英阶层中解救出来,为日常审美辩护,呼吁艺术平等,把审美的权利归还给普通大众,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气氛”是气氛美学的根本概念,亦是其研究对象。从理论层面上对“意境”与“气氛”进行梳理和比较,有助于了解和把握中西美学在艺术时空、生态平衡、美学走向等问题上的特点和差异。
一、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范畴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范畴,亦是中国传统艺术着力追寻的艺术境界。“中国艺术家面对的是一个气化的世界,他与气化世界相优游,又以艺术表现这个世界。”[1]在这个气化世界中,“气”作为一种物质形态贯穿于宇宙万物之中,是宇宙万物与文学艺术的生命。人与物皆气化而生,因此,主体生命之气与自然万物之气得以相通相感。“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四时景物之变迁、人生际遇之沉浮,经过人的身体性在场投射进主体,触动人的心灵,激越情感波荡。气介于形与神之间,是意境生成的中介,“在物的层次结构中,它是由形而神、由实而虚、由感性而理性的中间环节”[3]。气腾而势飞,气融而意成。“从审美活动(审美感兴)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领悟和感受。”[4]中国传统艺术以取境为胜,讲究形、神、意、韵,虚实相生、有无相成、天人合一、主客相融,诗有诗境,词有词境,书有书境,画有画境,乐有乐境,小说有小说之境,建筑、雕刻亦有建筑、雕刻之境。情与景是意境得以生成的内在基础,“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5]。情与景会,意与象通,意与境谐,浑然圆整而意境生。
王昌龄在《诗格》中将诗境分为“物境”“情境”“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6]172-173此三境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步步加深,王昌龄在提出时虽然只局限于诗境,但揭示了中国艺术之境的次第层深,指出了意境生成之不可或缺的情与景、意与境、主与客之间的相互融合。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王昌龄在此还格外强调了空间与身体的在场经验对意境生成的基础性作用。“处身于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这里的“身”,指“意”之身心合一的主体,“是灵与肉浑然无间的主体性存在”[7],而境即是外在空间、自然环境。在《诗式》中,王昌龄多次谈及“身”的重要性,“夫诗,一句即须见其地居处。……若空言物色,则虽好而无味,必须安立其身”[6]163,认为诗人安立其身不仅是作诗的基础,而且是决定诗歌韵味的关键因素,并列举了“明月下山头,天河横戍楼”一诗作为身体缺席的山水诗反例,以论证身体之于诗歌意境生成的重要作用。“凡诗人,……皆须身在意中。若诗中无身,即诗从何有?若不书身心何以为诗。是故诗者,书身心之行李,序当时之愤气。”[6]164身心与物相融,情感产生波荡,诗歌才能言之有物,进入象外之境,达成味外之旨。“夫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闻于耳,见于目,录于纸。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寸。”[6]162身心耳目对文章兴作之意象生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意境须经由身体的感性知觉进而才能得以精神的超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强调了诗人对宇宙人生的切身观察与深入体会,“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8]。由此可知,意境的生成不仅需要在有限空间中身体性在场的感性知觉,而且还需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精神层面上的升华、超越。
意境范畴肇始于唐代,从盛唐王昌龄的诗歌三境、中唐皎然的“神旨”与“意冥”、晚唐司空图的“象”“景”与“妙悟”,经由南宋严羽的“气象”与“兴趣”、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至清末王国维的“境界说”而臻于成熟。后人对意境范畴的钩沉爬梳、阐发研究,为意境理论的建构与完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学界历来对意境主体的认知,正如张晶教授所言,多基于西方身心二元的哲学思维,“将其视为纯粹的精神主体,而无关乎身体”[7]。然而,通过对王昌龄等人有关“身”的论述我们发现,古人对身心的认知是浑然一体的,精神层面的升华与超越离不开身体的在场经验。个体生命以身体存在于时空之中,以身为度是中国古代感受时空的原初方式。艺术家处身于境,自然也是先以身体为基准对周围的空间环境进行感知,通过眼耳舌鼻身等感官感知物象的形色声状之整体面貌。仰观、俯察而始作八卦;极视听之娱,宇宙万物方了然于心,进而由形入神、取之象外,如张旭常观公孙大娘舞剑而后草书日渐精进,“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9]。在审美意象方面,艺术家也常从身体中寻求灵感,如“字有筋骨、血脉,皮肉、神韵、脂泽、气息,数者缺一不可”[10];“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成为书。”[11]在审美批评方面,亦多借助视、听、触、味、嗅等主观感觉对文学艺术进行鉴赏批评,如“品”,品藻、品鉴、品评;如“味”,体味、韵味、滋味等。此外,“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线”[12]。通感的灵活运用可以克服知觉感官的客观局限,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之视听相通;“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之以声类声;“状似流水,又像飞鸿”之听声类形,不仅能够使艺术家更好地把握审美对象,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艺术的意境表达和审美感受。
二、气氛美学中的“气氛”概念
“气氛”原非美学范畴,中国古代已有“气氛”一词,汉代刘向在《说苑·辨物》中有“登灵台以望气氛”之语,“气氛”在此意指显示吉凶的云气。波默将“气氛”引入美学范畴,超越了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认为“气氛表达是某种独特的居间现象,某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东西”[13]91。波默对“气氛”的概说,建立在瓦尔特·本雅明的“灵气”和赫尔曼·史密茨哲学中“气氛”概念的基础之上,由此确立了“气氛”的空间特征和身体性在场。随后,波默又将“面相”引入到气氛美学之中,以论证气氛的整体性与可感知性特征。
(一)本雅明之“灵气”
本雅明引介“灵气”概念,意在阐释萦绕在艺术品原件周身那种独特而颇具距离感的气氛,并希望借此点明艺术品原件与复制品的差别之所在。“灵气到底是什么?由时、空交织而成的奇特编织物:……某个夏日午后,静静地追随着地平线上的群山或一根将其影子投射到休憩者身上的树枝——这就叫群山或这根树枝吞吐着灵气。”[13]15本雅明关于“灵气”的定义,首先强调了灵气得以生成的两大因素:时间与空间。“空则灵气往来”[14],空间是灵气生成的基础,有了空间,灵气才得以空间上的存在和时间上的往来延续。其次,本雅明通过对自然场景的描述进一步阐释了“灵气”产生的客观条件,认为灵气来自自然之物,是自然物在空间中的自然流露,而人置身于空间之中“呼吸”着灵气。波默从本雅明对“灵气”概念的描述中汲取了三个关键信息:一、空间是灵气得以生成的一大因素;二、“灵气”并非只存在并局限于艺术品原件之中,也并非只有在艺术品原件中才能被察觉到;三、人对艺术品原件以及自然物“灵气”的察觉和经验,又赋予了“灵气”概念以身体性在场。本雅明的“灵气”概念,为波默美学范畴中的“气氛”概念界定奠定基础,波默在此框架中进而与赫尔曼·史密茨身体哲学中的“气氛”概念相联系。
(二)史密茨之“气氛”
在赫尔曼·史密茨的身体哲学中,史密茨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将“气氛”引入其身体语境之中,着重论述了气氛在空间上漫无边界、居无定所即无法定位的不确定性特征,认为气氛“是侵袭着的感染力,是情调的空间性载体”[13]17。而人或物的身体性在场,使“气氛”在主客体二元论下呈现出的那种不确定性得以消除。不同于本雅明“灵气来自自然之物”的观点,史密茨认为“气氛”是独立于物的外在存在,气氛与物无关,也并不通过物而产生,气氛只是萦绕在物的周围。在史密茨看来,物之于气氛,最多不过是起到了开启气氛的作用,甚至物反过来成了“气氛”的审美再造。而史密茨对气氛独立于物的过分强调,又从侧面愈加凸显了主体的身体性在场即知觉感受对经验气氛的重要性。在史密茨的身体哲学中,“感受是‘没有定位地涌流进来的气氛,即以情感波动的方式侵袭着其所植入的某个身体的气氛,这样,这种情感波动就抓住了被侵袭的形体’”[13]18。波默对史密茨有关“感受”的这一观点十分赞赏,认为这是对传统美学理智主义的反叛,是新美学的开端。但波默并不十分认同史密茨“气氛独立于物”的观点,认为史密茨夸大了“气氛”的独立性。气氛的经验确实离不开主体的身体性在场,但外在环境以及环境中的物对气氛的生成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气氛得以生成的另一必要条件。
(三)“面相”之整体性与可感知
为了论证气氛空间的整体性与可感知性特征,波默将“面相”引入到气氛美学之中。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面相学地认知某事物,意思就是,通过其面相来认知该事物”[13]194。但波默的分析则不然,在他看来,面相学认知首先是通过对气氛的觉察,其次在于将气氛主要经验为某事物的确定的在场性,某事物通过自己所散发的气氛而被外界知觉到[13]195。而气氛,就是某一环境或空间经由其身体性在场经验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即面相。气氛作为面相而显现的这种可感知性,即鲍姆加通所强调的感性认知。波默认为,自然之所以可以被感知,是因为建立在可感知性的基础上,而自然的这种可感知性,不是康德美学中所指的感官在受到外界刺激后而产生的感性直观质料,而是人们在面对自然时的第一情感知觉,是人对自然面相的整体感知。物通过自己属性的在场而从自我中走出,将自己的整体面相呈现于他者而被察觉感知,从而实现物的在场。
波默在对本雅明之“灵气”、史密茨之“气氛”以及面相学中“面相”的论述中,逐步确立了美学视域中“气氛”概念的理论框架和基本特征。波默的气氛美学,微观上是一种自然生态美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宏观上则是致力于改变当代美学走向的感性学—美学,引导人们寻回消失了的“身体”与“感性”,使美学回归感性知觉。
三、意境与气氛之迥异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15]美学视域下的气氛与意境,尽管分属于不同的美学领域,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错位,但二者在空间与身体性在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方面的共同之处,使其能够跨越时空进行对话与交流。不过,“艺之为术,理以一贯,艺之为事,分有万殊”[16],就本体而言,意境与气氛汇通之余又彼此迥异。
(一)“境”与空间
从生成论角度看,意境与气氛都注意到空间的基础性作用。但波默的气氛美学只强调空间的重要性,而且气氛美学中的空间是指气氛的载体——物或人身体上的在场。也即是说,气氛的载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而这些带有某种感受质的人或物的在场就是气氛的空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历来主张时空一体,映射到艺术创作之中亦是如此。且仅就意境之空间而言,无论是生成前的外在环境还是生成后的精神空间,较之气氛空间都更为广阔而深远。
“自然宇宙的一切秩序匀称,到底是否有目的而设,还是无情思而生,古往今来多少中外大哲学家、科学家都曾经苦苦探索思考过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西方宇宙学和宗教的一个热门话题。”[17]236可以肯定的是,艺术范畴中的时空秩序,是基于客观存在的有目的而设,是对现实时空的艺术化处理与再造。意境作为中国传统艺术所着力追寻的诗意时空与精神境界,有象内之境与象外之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分。象内之境即是意境得以生成的物质空间基础,宏观上一般指大自然,中国传统艺术如“夫书肇于自然”[18];“诗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不及”[6]166;乐之“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19];国画之“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其画所以称独绝也”[20]859等,作品之意象皆源自自然之物。象外之境则是主体对外在有限空间环境的精神超越,如山水画之“扫千里于咫尺,写万顷于指下”;传统戏曲之“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古典园林之“纳千倾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21]。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意境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也。”[22]有我之境,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即是缘心感物、物被人化之情境;无我之境,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是主客相融、天人合一之境界。
在波默气氛美学中,空间是气氛得以生成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气氛显然是通过人或物身体上的在场,也即是通过空间来经验的。”[13]19气氛具有明确的空间性,当我们进入某一空间,便会被该空间中或热闹或冷清或喜庆或悲痛或平和或紧张或晴朗或阴郁的氛围所包围。就存在论而言,气氛具有不确定性,不同的空间所呈现出的气氛不尽相同,而身处空间中的个体并不能确定该气氛是源自客体的空间环境、主体的经验在场,抑或主客体之间的交互关系。然而就其特征而言,气氛又极为确定,我们可以根据感知而将气氛描述为明快的、沉重的、崇高的、颓废的、激动人心的、肃然起敬的、轻松惬意的、紧张压抑的等等。商场营造的是使人产生购物欲望的气氛,教堂则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博物馆是历史厚重空间之所在,图书馆是安静博学之场所……波默以建筑为例,指出气氛的生成离不开空间的支撑,不同的空间所营造出来的气氛及其带给人们的切身感受亦不尽相同。不过,波默的气氛美学过于强调空间性而忽略了时间因素,依然没有走出时空二元对立的窠臼。
(二)“象”与气氛之物
意境的生成离不开意象,气氛的营造也需要气氛之物的参与,意境和气氛都意识到意象和气氛之物对诗歌、艺术的重要性。中国美学重视意象的选取与创造,目的是为了达到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而波默对气氛之物的引入却是为了说明气氛的可营造性,以及被经验的自然与被艺术化的自然之间的关系。
“自天地一阖一辟而万物之成形成象,无不由气之摩荡自然而成。”[20]859观物取象,窥意象而运斤,立象以尽意。意象是艺术作品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天地自然之象”与“人心营构之象”[23]的统一,神与物游,神形兼备。“物的体用,象的虚实,皆适于词章谈艺。”[17]62物象通过感性知觉、情景交融内化为意象,而意象又凭借艺术家的艺术手法外化为以文字、言辞、线条、音符、笔墨等为物质属性的客观实体,从而生成各类艺术作品。以书法为例,“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萧子云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24]。艺术创造是化实为虚、以虚为实、由实入虚、虚实相生的过程。这虚实之间,意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即是客观物象,是意象的客观实在,是生成意境的物质基础。化实为虚、由实入虚,即是将具体可感的客观物象意象化,由形入神,由仿象、兴象至超象、抽象,由有限的时空进入无限的境界。诗歌以有尽之言表达无穷之意,国画中擅用留白的手法计白当黑,戏曲演员通过唱念做舞等虚拟表演以赢得舞台上的时空自由,均是艺术家运用审美意象由有限时空向无限时空的艺术转化,是言外之意、象外之境、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是超越了现实时空的超时空经验与艺术境界。
在波默的气氛美学中,如何对物进行定位,是气氛概念能否得以合法建构的关键。在传统的物存在论中,物的形式、颜色、气味等属性“被理解为该物与其他事物得以区别的东西,被理解为向外为该物划界、向内使该物成为该物的东西”[13]19。在波默的气氛美学中,物本就是在空间中在场的,物的属性如颜色、气味等的在场则是物在空间性的在场得以被察觉的决定因素,物的属性是物在场的方式和表达。波默将物冲破传统物存在论走出自身的方式称为“物的迷狂”。波默通过松尾芭蕉的一首三行俳句诗,将气氛之物引入到论述之中。波默认为,气氛之物源于自然。“钟声渐去”,但“花香漫起”,诗人通过两组对立的物象趋势而凸显,营造出“现在是傍晚时分”的气氛,“确定的是,气氛之物属于自然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13]55。从自然物或环境的角度来看,被经验到的东西首先是自然物、环境所散发出来的气氛。松尾芭蕉诗中通过语言对气氛之物的选取和编排,使波默感受到语言对于诗歌的重要性,认为气氛是可以像布景师设计舞台那样通过语言来营造的。这一点,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早已有此认知,而且较之更为深刻。“意以象尽,象以言著”,王弼在言意之辨中不仅认识到言象对尽意的基础性作用,而且指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融入现实时空观物取象,而后又从具体形器中超脱出来,才能真正达到精神上的超越,进入无限的时空之中。
(三)“意”与身体性在场
意境与气氛都需要身体性在场。就“气氛”的生成而论,波默虽然认为“气氛”可以被创造,却更强调“气氛”的空间特性,人的身体性在场经验不应有过多的情感介入。而中国美学语境中的“意境”则更侧重空间中人对物的主观能动性,需要感性知觉的同时亦注重主观情感的介入。再者,气氛的生成需要营造者与接受者的身体同时在场,而意境的生成需要的则是创造主体即艺术家的处身于境。
中国传统语境中,意境的生成主要在创造主体,“意”之主体是人,是身心合一、灵肉浑然一体的艺术家。“意在笔先,神超象外”,艺术家在取象造境之前内心已预设了“意”,这“意”不仅对“象”有情感的介入,而且具有决定性作用,象由意而生。意象的选择,需要艺术家具备相“几”的能力,即敏锐的感知力与形象思维能力,且富于想象、联想,善于直寻、妙悟。“‘几’,先秦之后亦作‘机’字解用,即事物的隐微、迹的初露与未露。也是《老子》中讲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形未动,意先驰,引而不发,聚力作势。自然与社会的恍惚形态,为文学造就幻想、朦胧美。”[17]248艺术家擅于相“几”,方能在万物中选取恰当有效的物象,进而通过联想与想象将其诉诸情感而意象化。“艺术家所提供的是这样一些因素,它们使我们意识到在整体感性空间连续中相关的形式。所有的强调和选择,以及对物体、实际形式的完全失真和根本背离,都有着使空间可见、使其连续可察觉的意图。”[25]这里所说的强调和选择,是艺术家对物象的把握方式,即艺术家对外在空间环境中物的意象化过程。该意象化以艺术家的美感为依托,对自然之物进行选取与再创造,使其成为审美时空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家不仅仅法天,而且可以把自然的疏忽弥补过来——胜天,还可以达到天艺溶化的更高境界——通天。”[26]艺术家的能动作用,不仅在于模仿自然,从自然中选取特定的物象,而且可以通过艺术创作弥补自然的缺失,使艺术与自然完美融合,达成相得益彰的通天境界。在中国美学的意境范畴中,物境和情境相对易得,而意境则较为难寻,有时刻意营造、着力追寻,作品却意境全无。意境是创造者在空间与身体性在场的经验基础之上的精神超越。意境的生成,不仅需要特定的空间和身体性在场,而且需要艺术创造者深厚的艺术素养、文化底蕴与审美能力。
在波默的气氛美学中,接受者的身体性在场是气氛得以生成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相较于中国美学范畴中的“意境”之幽深难寻,西方美学语境中的气氛显得寻常易得。在波默气氛美学中,气氛的载体可以是自然物也可以是人,气氛经过营造可以普遍存在,抑或可以说,只要有特定的空间以及人的身体性在场经验,就会形成一定的气氛空间。对于创造者而言气氛是一种审美空间,对于接受者而言气氛是一种处境空间,气氛的生成是创造者与接受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接受者的身体性在场只需对创造者营造出的空间感受质进行直接而整体的第一知觉,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的情感介入。“身体是似主体的(subjekthaft)东西,属于主体,就气氛在其身份性的在场中是通过人来察觉的而言,就这个察觉同时也是主体在空间中的身体性的处境感受而言。”[13]22这里的人指气氛的接受者,如果没有接受者的身体性在场经验,气氛这种“空气中流入的某种不确定的感受质”[13]16,只是一团来自“自然物的模糊不定的气”[13]91。气氛美学的居间性超越了西方传统美学中的主客二元对立,将主、客体有效融合在一起,而通感则是气氛得以生成并连接主客体的中介。波默在通感问题上,首先通过歌德的颜色学说加以说明,而后挖掘出知觉的哲学背景——感觉基础主义,这种感觉基础主义在认知理论中的统治地位打破了不同感官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随后引出史密茨哲学理论中的通感特征——自身性的察觉,而这种对自己身体的察觉也即通感,正是人们能够知觉气氛的关键途径之所在。
波默气氛美学视域下的“气氛”,重空间与身体性在场经验,具有整体性与可感知性等特征,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些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范畴交相应和。但二者之间的不同也十分明显,意境是时空一体,而气氛偏重空间;意境不仅重感性知觉,而且还力求在此基础上升华与超越,以期进入无限的审美时空,而气氛则只强调感性知觉,企图以此来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名,呼吁艺术平等,将审美的权利归还于大众;意境追求的是幽深难寻的艺术境界,气氛则为日常审美化代言。也正是这些差异,为二者提供了互通有无的潜在空间。从气氛美学的视域看中国的意境范畴,意境可视为一种气氛;但从中国美学的意境范畴看气氛,气氛则对应着三个次第层深的不同阶段——物境、情境、意境。其中,气氛与物境最为接近,都属于感性知觉阶段,而情境与意境则是气氛在感性知觉基础上的升华与超越。波默认为,气氛可以发挥其审美领域内的批判功能,以气氛的可塑造性与传播为突破口,从内在根源上打破气氛的诱导性力量,对艺术庸俗化进行内在批判,而且相较于阿多诺“文化工业”等外在批判而言,气氛的批判力度更为强劲。但应该警惕的是,气氛美学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平反,又极易重新导致审美的庸俗化、低俗化走向。对此,中国意境范畴对气氛的升华与超越或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气氛对感性知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我们反思人与自然的现有相处模式,审视中国美学的当代走向,进一步发掘古典美学中的生态智慧与诗性思维,促进中国当代美学的自我建构与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