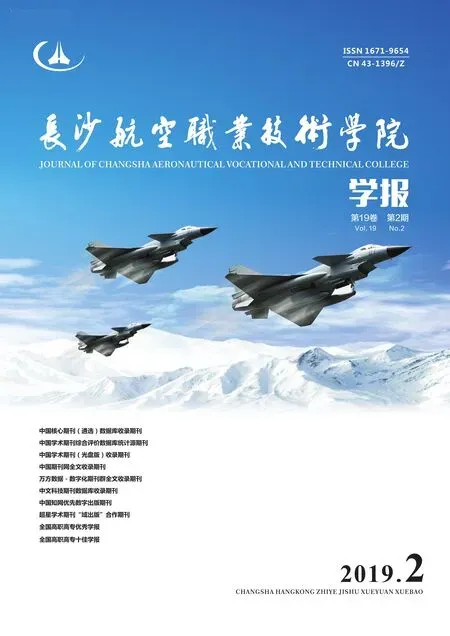量词“盏”的认知分析
2019-03-22张万禾
文 西,张万禾
(1.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近些年来,学界开始将认知理论广泛运用于语言学领域,其中有关量词的认知方面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有大类量词的认知分析,如黄璜[1]、葛松[2]等,也有认知视角下的个案研究,如赵景宇[3]、袁静[4]等。然而,在这些著作中,前贤们主要择取特点突出的典型量词作为它们的分析对象。
“盏”,最早见于春秋,本义指“浅而小的杯子”,用作名词;东汉时借用为计量“水”“酒”的容器量词;现代汉语将“盏”归为计量“灯”的个体量词。
目前关于量词“盏”的研究,除阳盼[5]对“盏”的称量对象做了一个详细的演变梳理外,其他都只是在分析专著中某一类型的量词时稍带提及,如周建民[6]、陈跃[7]等。因此,关于量词“盏”的专门性研究,尤其是认知方面的分析,目前还尚未有人进行。
本文在前贤的基础上,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对量词“盏”的称量对象和认知模式进行详细的叙述与分析,以求对量词“盏”的研究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一、量词“盏”的称量对象的分析
王力[8]认为“盏”是一个计量范围发生了转移的单位词,由原先计量“酒”转为计量“灯”。然而,任何现象的转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经历一个两种现象并存然后其中一种现象消失的过程。阳盼[5]对量词“盏”的称量对象做了一个历时的演变梳理,认为量词“盏”的称量对象经历了一个由个别到一般,最后专职化的过程。从其演变梳理过程来看,可以知道:量词“盏”称量“水”“酒”的现象和称量“灯”的现象虽然出现时间有早晚的差异,但从其称量“灯”的用法的产生开始,一直到明末清初,量词“盏”都处于两种计量用法并存的状态。本文首先将这一并存阶段中量词“盏”的两种称量对象分别记为A、B两类,然后对A、B两类称量对象以及二者与“盏”的具体关系进行分析。
(一)A类称量对象及其与“盏”的关系
“盏”借用为量词的用法始见于东汉,当时其称量对象单一,因此A类称量对象主要指“水”和“酒”两种液体,后来随着“盏”作为容器的大量使用,其称量对象也随之扩大,发展到明代时,A类称量对象主要有“水、酒、茶、油、药、牛奶子、汤、粥、饭”等。例如:
(1)言讫,取出钵盂一具,盛水一盏,焚香诵咒。(《两晋秘史》)
(2)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元散曲》)
(3)吃过了一盏茶,便开口问道:“秀才官人,几时回家的?甚风吹得到此?”(《初刻拍案惊奇》)(4)烧热了,放上半盏香油。(《老乞大新释》)(5)吃了他头一盏药,还不见动静。(《金瓶梅》)(6)只见画童儿拿了两盏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金瓶梅》)
(7)丫环捧着雪花白米饭,一吃一添,放于秦重面前,就是一盏杂和汤。(《今古奇观》)
(8)妇人且不梳头,迎春拿进粥来,只陪着西门庆吃了半盏粥儿,又拿酒来,二人又吃。(《金瓶梅》)
(9)但见一个妇人,身穿重孝,左手托一盏凉浆水饭,右手执几张烧纸黄钱,从那厢一步一声哭着走来。(《西游记》)
在这些称量对象中,“水”“酒”“茶”的用例最多且用例时间也最长,“牛奶子”“粥”“饭”的出现频率最低,都只出现个例。周建民[6]认为,当“盏”用来计量“粥”“汤”“药”时,“盏”已不再指“浅而小的杯子”,而是一种类似于“盏”的小碗了。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盏”的称量对象扩大的原因之一,但若从其所称量的对象的特征来看,A类称量对象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它们指称的事物都是[+可被容纳的] [+无边界的] [+不可数的] ,而“盏”是[+可容纳的] [+有边界的] [+可数的] 。因此,在称量这些物质的时候,“盏”恰好是一个具体的可反映一定量的称量工具,与称量对象之间构成“容器”与“容纳物”的关系。再加上“盏”的长期使用,以及当时“碗”“杯”等容器的称量功能还未占优势,因此凡具有上述特征,且被盛入“盏”或类似于“盏”的容器中的事物,都可以用“盏”计量。
(二)B类称量对象及其与“盏”的关系分析
相对于A类称量对象,B类称量对象则比较单一,只有“灯”和“灯笼”,其中,计量“灯”的用法出现于唐朝,而计量“灯笼”的用法则到明代时才出现。但二者用例多,使用频率高,且其计量“灯”的用法一致延续到现代。例如:
(10)初夜,台东隔一谷岭上空中,见有圣灯一盏,众人同见而礼拜。(《入唐求法》)
(11)夜则放炮三个,卓起双灯笼二盏,在城前项人等一照白昼事例上城。(《纪效新书》)
(12)还是每人四盏灯笼。(《醒世姻缘传》)
此时,“盏”指的是“灯”或“灯笼”中用以盛油的部分,即“盏”为“灯”“灯笼”的组成部分,因此“盏”与其称量对象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二、量词“盏”的认知模式分析
Lakoff[9]认为“转喻是基于概念邻近性的一种认知过程,是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认知通道的过程”。也就是说,转喻也是一种认知机制。前文,已指出“盏”与其两类称量对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两种关系反映的是人们运用的两种不同的转喻机制,即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
(一)“容器”转喻“内容”的认知模式
黄璜[1]认为“人们认识事物所依据的原则是邻近原则”,认为“由于在认知中,距离相近的事物常常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因此会出现用一种事物的空间来计量另一事物数量的现象”。换句话说,在计量容器所容纳的物体的量时,人们会根据邻近原则,把容器的大小、边界等同于容纳物的大小、边界,用容器的空间来计量所容纳物的量,即用“容器”转喻“内容”,以此形成对物体“量”的认知。量词“盏”在计量A类称量对象时,所运用的就是这种认知模式。例如:
(13)如一碗水,分作十盏,这十盏水依旧只是这一碗水。(《朱子语类》)
(14)八里庄梁家花园里做来,我也那一日递了手帕之后,吃几盏酒,过两道汤,便上马出来了。(《朴通事》)
(15)便浓浓的点两盏姜茶,将来放在桌子上。(《水浒全传》)
(16)宋四公劝了,将他两个去汤店里吃盏汤。(《喻世明言》)
(17)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白居易诗全集》)
(18)武大再呷第二口时,被这婆娘就势只一灌,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水浒传》)
例(13)—例(18)中,“盏”依次计量的“水”“酒”“姜茶”“汤”“粥”“药”,它们都被盛入“盏”中,且没有固定形状、没有边界以及不可计数。但是,“盏”是一个有边界、有大小、有一旦体积的容器。因此,根据邻近原则,可以借助“盏”的体积来估量“水”“酒”“香油”“汤”“粥”“药”等事物的量,即用“容器”转喻“内容”。
另一方面,当人们看到物体时,最先感受到的是它的空间构成,因此空间在人们的脑海里最为突出。而在人的认知中,突出的事物显著度也更高。所以,在“容器—内容”这个认知框架里,“容器”比“内容”的显著度高。也就是说。“盏”相对于其A类计量对象而言,“盏”作为具有一定体积的容器,因其显著度高的缘故。人们在称量时也更倾向于用它来量称其所盛物的量,即用“容器”来转喻“内容”。
(二)“部分”转喻“整体”的认知模式
赵艳芳[10]认为“一个物体、一件事情、一个概念有很多属性,而人的认知往往更多地注意到其最突出,最容易记忆和理解的属性,即突显属性”。因此,黄璜[1]认为“在‘整体—部分’这个认知框架里,‘整体’的显著度比‘部分’的显著度高。通常情况下,人们习惯用‘整体’转喻‘部分’”;另外,他还指出容量量词暂未发现“部分”转喻“整体”的例子。的确,当“盏”计量A类称量对象时,它不具备用“部分”转喻“整体”的特性。但当其计量“灯”“灯笼”时,运用的正是“部分”转喻“整体”的认知模式。例如:
(19)当夜,军师扶着一军,左手把印,右手提剑,披头,点一盏灯,用水一盆,黑鸡子一个,下在盆中,压住将星。(《三国志评话》)
(20)岂知事不可料,冤家路窄,那一盏红灯纱笼偏生生地向那亭子上来。(《二刻拍案惊奇》)
后来,随着“电灯”的出现,“盏”的语义开始发生变化,由“盛油的浅盆”变为“灯的底座或灯最下面的盏托”,即仍然属于灯的一部分。例如:
(21)办公室放著两盏台灯,夫妻各一盏。(三毛《滚滚红尘》)
(22)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桥上的44盏路灯,一直不曾亮过,给夜晚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带来诸多不便。(《人民日报》)
三、结束语
本文以量词“盏”为分析对象,将其称量对象分为A、B两类。其中,A类称量对象所指称的事物都具有[+可被容纳的] [+无边界的] [+不可数的] 的特征,“盏”与它们是“容器”与“容纳物”的关系;B类称量对象只有“灯”“灯笼”两个,且“盏”与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另外,“盏”与这两类称量对象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容器”转喻“内容”的认知模式与“部分”转喻“整体”的认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