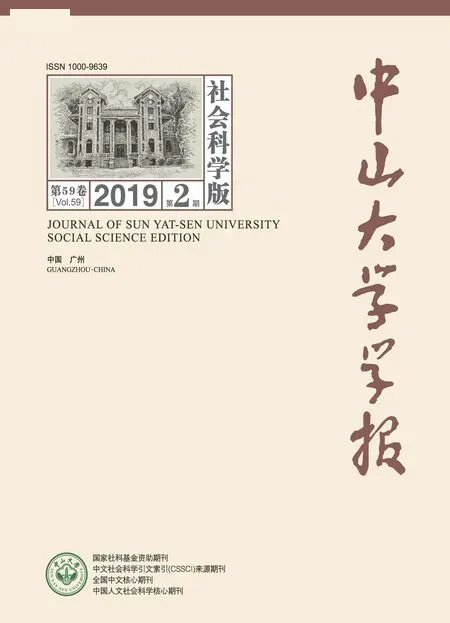新史料中所见札八儿火者史事及其时代背景*
2019-03-22邱轶皓
邱 轶 皓
引 言
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以前,来自东部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就已经活动于各部落之间,从事长途商业活动;而在其早期征服活动中,也能够看到少量穆斯林追随者的身影。不过和蒙古人第一次西征(1219—1224)之后开始系统性地利用穆斯林管理国家的做法不同,这些早期的追随者大多是通过为成吉思汗个人提供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服务而被吸纳进其亲信群体的。

正因为相关史料比较丰富,所以围绕这些文献而展开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如杨志玖先生很早就结合汉、波斯语文献对相关史事作过考证。另外,党宝海和本人也分别从不同角度撰文加以考述*杨志玖:《补〈元史·札八儿火者传〉》,《元代回族史稿》,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63—369页;《〈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元代回族史稿》,第370—377页;党宝海:《外交使节所述早期蒙金战争》,姚大力、刘迎胜编:《清华元史》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59—187页;Yihao Qiu, “Jafar Khwāja: a Sayyid, Merchant, Spy and Military Commander of Chinggis Khan”, Along the Silk Roads in Mongol Eurasia: Generals, Merchants, and Intellectuals, Michal Biran, Jonathan Brack, Francesca Fiaschetti (eds.), 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forthcoming)。。不过近年来在伊朗新刊布的一种阿拉伯语蒙古史书,难得地为我们展示出同时代的波斯人对札八儿火者其人其事的看法。因此本文尝试从对新史料的译注切入,不仅对其传记信息加以增补,同时更进一步讨论历史记述者自身的宗教身份是如何影响甚至重塑历史图景的。
一、札八儿火者史事译注
(一)文献介绍
2015年,德黑兰大学历史系教授贾法里扬(Rasūl Jafariyān)刊布了一部题为《蒙古—鞑靼君王纪事》(Awālmulūkal-tatāral-mughūl, 下简称《纪事》)的阿拉伯语史书。题目为整理者所加,同时贾法里扬强调该书为巴格达陷落后最早的一批历史记录。

贾法里扬在评价巴惕惕的阿语译文时称其“阿语水平并非一流”,理由是译文中有不少拼写错误。不过他也认可巴惕惕的译文时而展示了对古典风格和文学修辞的了解。《民智启蒙》原书共26章,而《纪事》恰好收录于巴惕惕所续写的第27章。贾法里扬认为本章内容和风格独立于全书之外,意在记述史事而非表彰宗教。而我们对巴惕惕生平的了解,基本上就来自《民智启蒙》的译本和补编以及少量什叶派学者的传记汇编。



(二)《蒙古纪事》中的札八儿火者事迹
《纪事》中和札八儿火者有关的段落全文迻译如下:
成吉思(Jinqiz)成为大汗(khānānkabirān)和有名的异密之后,其权势益著,部众日增。因此他将目光投向了更为遥远的地区。商人们前往他那里,而那些了解[那些地区]的人也同样如此。他们告知他关于远方各国的信息,于是[成吉思汗]决意进而攻占契丹境内的每一片地区。
契丹的统治者之一阿勒坦王(Altūn Malik)进行了抵抗,因此他(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对之进行长期围困,但后者的策略未能奏效。
此时,他的军队中有一名极为机智聪明之人,此人为一品行端正的什叶教徒,为阿拉伯裔并操阿语(minshīasadīdaArabīal-nasabwa’l-lisān),名为札八儿火者。某日,他来到成吉思[汗]跟前说:“若我能助你攻下该城,你将如何奖赏我?”——[该城]即“汗八里”(*Khām-Bāligh)。
[成吉思汗]说:“若假你之手使我们顺利[攻占此城],你将会得到阿勒坦王的财富、妻子和王座。”

(三)考释
《纪事》的行文风格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口语特征。如文中称金朝皇帝为“阿勒坦王(Altūn Malik)”而非当时波斯语史书(如志费尼、术札尼著作)中习见的“阿勒坦汗”。这应该是转述者为了便于听众理解而作的处理。与之类似的案例可见马可波罗所著《行纪》,作者在书中称金朝皇帝为“黄金王”(Roi Dor)。此外,《纪事》中的蒙古人名、地名的拼写也稍异于此后通行的写法。例如,成吉思汗被写作“Jinqīz”,而非大多数文献中所见的“Jinkīz”;“汗八里”则被写作“Khām-Bāligh”,而非“Khān-Bāligh”等。这应该是讲述者本身的口音差别在文献中的反映。
更值得注意的是,称金朝都城为“汗八里”,而我们确知自金海陵王贞元年(1153)后即改燕京为中都,到金贞祐三年(1215)金帝弃城南奔后,新据此地的蒙古人复改“中都”为“燕京”,至元九年(1272)并金旧中都入新建的大都。“汗八里”则是“大都”一名的突厥语翻译[注]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页。而即使在中都改名之后,回鹘语和波斯语文献中仍常见以“Jūnk-dū”旧名与“汗八里”并称的用法。邱轶皓:《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国遣使元朝考:法合鲁丁·阿合马·惕必的出使及其背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1分,2016年,第93页。。故据“汗八里”一名,可判断现存《纪事》文本并非如整理者所认为的那样,完成于1260年。相反,它有可能在1272年之后经过了增补或改写。

巴惕惕书中所提供的最具价值的信息,是关于札八儿火者的族属和宗教派别的资料。称札八儿为“阿拉伯裔并操阿语”,这和《元史》本传称其为“赛夷人”(Sayyid)可以相勘合[注]宋濂:《元史》卷120《札八儿火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960页。。按,赛夷原本被用来指称穆罕穆德后裔,特别是指那些出自阿里和法蒂玛两子哈桑和侯赛因的子嗣,因此具有“赛夷”身份就相当于承认某人具有阿拉伯血统。而在蒙元一朝,蒙古统治者普遍有重视“根脚”(huja’ur)出身的习惯。据《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对具有贵族血统的人,即便是世敌之子也往往能加以优待[注]陈得芝:《程钜夫求贤江南考》,《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94页。,因而札八儿火者圣裔身份无疑有助于其得到成吉思汗的重视。
而当蒙古人在进入中亚地区后,也将草原部族传统的身份观念和“根脚”意识带入当地,甚至部分强化了中亚本地穆斯林精英对族裔、血统的认同。穆明诺夫(Muminov)在一篇讨论中亚贵族和圣裔的论文中指出:在经历蒙古统治之后,本土的宗教家族更倾向于强调甚至杜撰自身的圣裔血统(即阿拉伯族源)[注]Ashirbek Muminov, “Dihqāns and Sacred Families in Central Asia”, Sayyids and Sharifs in Muslim Societies: the living Links to the Prophet, Morimoto Kazuo (ed.),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198-209.。巴惕惕写作的时代虽然较早,但作为一位从蒙古西征开始就较积极与后者合作的什叶派学者,强调札八儿的阿拉伯身份应该来自和蒙古实际的交往经验。
我们更可以参考汉语、阿语的记载,进一步推考札八儿火者的原居地。《元典章》有一条,引述成吉思汗时期旧例,将汉儿民户事务交由“近都不儿、探木呵、大西札发儿和尚根底也相参委付了来”[注]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第一册)卷8《吏部·官制二·选格·色目汉儿相参勾当》,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46页。。据洪金富考证,上揭文字中提及的三人即指不只儿(Bujir)、撒木合(Samghar)和札八儿火者[注]洪金富:《元典章点校释例续》,《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8页。,别号“大西”可能是记录者用来表示札八儿火者原居地。考虑到传统汉文文献一般称突厥斯坦和中亚地区为“西域”,则札八儿火者名字前的“大西”(“大”当读如“泰”)意为“极西”,所指或为伊朗东部。
关于札八儿火者前往汉地时的身份,《元史》本传和波斯文史料的记述均强调其受成吉思汗之命以使节身份前往金国,并乘机侦知绕过金人防守的小路[注]英译本作:效力于那些人(蒙古人)的……札八儿以经商为名来到阿勒坦汗军中(Jafar, who was among that people [the Mughals], among the force of the Altūn Khan under semblance of traffic)。不过据波斯文本当作:“以遣使为名派往阿勒坦汗处”(ba-vajh-i risālat ba nazdīk-i Altūn Khān firistād)。Tabakat-I-Nasirī, vol. 2, pp. 953-954; abaqāt-i Nairī, vol. 2, pp.100-101。。而他的使节身份同时也体现在《金史》径直以“乙里只”称之而不具名。甚至远在埃及的马穆鲁克历史学家答瓦答里(Ibnal-Dawādarī,写作年代为1309/10—1335/6),通过经阿哲儿拜占人(Azirbāyjānī)带到叙利亚和埃及的信息,在其编年史中也提到成吉思汗派遣一名“使者”(īljī)——札八儿火者前往金朝谍取情报的故事[注]al-Dawādarī (Abū Bakr b. Abd-Allāh b. Aybak), Kanz al-durar wa-jāmial-ghurar, Ulrich Haarmann (ed.), Cairo: Deutsches Arch?ologisches Institut Kairo, 1971, Der Bericht uber die fruhen Mamluken, vol. 7, p. 235; Ulrich Haarmann, “Altun Hān und ·ingiz Hān bei den ägyptischen Mamluken”, Der Islam, 1974, vol. 51, pp. 29-30.。
但《纪事》却称札八儿火者曾多次前往汉地行商(kānayatjrailayhā)。这则信息虽有异于上述记载,却能在史料中找到相应的证据。对于什叶派穆斯林从事前往中国的长途贸易,12世纪的作者马卫集(Marwazī)就曾记载道:早在倭玛亚王朝时期(r. 661—750),阿里派(什叶派)教徒为了躲避倭马亚人的迫害而逃往呼罗珊,并从那里前往中国。他们在中国学会了汉语以及其他来到中国的人的语言,并在商队与贸易者之间做中间人[注]Shiraf al-zamān Tāhir Marwazī, Sharafal-Zaman Tahir Marvazi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V. Minorsky (ed. and tr.), Frankfurt am Main: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rabic-Islamic Science at the Johann Wolfgang Goethe University, 1942, pp. 17, 66. 根据洛杉矶图书馆和伊朗议会图书馆两个新抄本的翻译,见[伊朗]乌苏吉(M. B. Vosoughi)撰,王诚译,邱轶皓审校:《〈动物之自然属性〉对“中国”的记载——据新发现的抄本》,《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5页。。继倭马亚王朝之后,阿拔思哈里发(r. 750—1258)和由迁居河中的突厥部落建立的塞尔柱王朝(r. 1037—1194)仍然延续了对什叶派的不宽容态度。因此,什叶派教徒因躲避宗教迫害而从伊斯兰核心地区东迁并进入汉地,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应该是凭借自己的经商才能谋生的。
而对于地处欧亚贸易网络东端的金朝而言,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商人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0世纪以降,随着高昌回鹘、西夏、西辽和花剌子模等区域性政权的兴起,将原本连贯为一体的陆上丝绸之路分割为各个区域性商业网络。随着商业网络的复杂化,越来越多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商人逐渐参加到与金朝的贸易活动中来,尽管直到12世纪回鹘商人仍然控制了丝路东段大多数的商业份额,如大定中(1161—1188)来自虎思斡耳朵(Ghuzz Ordo)的“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注]脱脱:《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37页。。
与此同时,对于草原上的蒙古诸部来说,中亚商人则适时填补了因金朝出口限制(如铁器)而造成的物资短缺。同时从中亚输入的日用品,例如衣服等,也是游牧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商品。伊本·阿昔儿(Ibn al-Athīr)就曾经记载说:因为花剌子模沙从西辽手中夺取河中地区的战争暂时切断了前往东方的商路,随即便导致了蒙古草原上服装的奇缺[注]Ibn al-Athīr, The Chronicle of Ibn al-Athīr for the Crusading Period from al-Kāmil fi’l-ta'rīkh, D. S. Richards (tr.), Burlington: Ashgate, 2007, vol. 3, p. 205.。而曾经出使蒙古草原的南宋使节彭大雅也称“鞑人所需”大多为“汉儿及回回等人贩入草地”[注]彭大雅著,许全胜校注:《黑鞑事略校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4—85页。。
除了从事长途贸易,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商人的语言能力也使他们受到蒙古人的重视。如马卫集称,来到东方的什叶派穆斯林很快学会了汉语及其他语言,彭大雅则称回回“多技巧,多会诸国言语”。擅操语言和行商于各地的特点,使得蒙古人也常常利用穆斯林充当侦查汉地情报的间谍。据赵珙《蒙鞑备录》所记,当时故金地区还流传有田姓回鹘商人“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具言民物繁庶,与乣军同说鞑人治兵入寇”[注]赵珙撰,王国维笺证:《蒙鞑备录笺证》,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叶14a-14b。。
二、札八儿史事西传的网络

阿思塔剌八忒靠近祃赞答儿和里海,是朱里章第二大城,其规模仅次于地区首府朱里章城。雅库忒·哈马维《地理词典》一书称阿思塔剌八忒以汇聚各色技艺的才智之士而知名[注]Yāqūt b. Abd Allāh al-amawī, Mujam al-buldān, Beirut: Dār ādar, 1977, vol.1, pp. 174-175; Yāqūt ibn Abd Allāh al-amawī,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Barbier de Meynard (tr.),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61, p. 32.。除此之外,当地也出产各类谷物、水果和丝织品。甚至直到伊利汗后期,该地仍需定时缴纳丝织品充当贡赋[注]amd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 al-Qulūb, G.Le Strange (tr.), Leyden: Brill, 1919, p. 156; Abd Allāh b. Muammad b. Kiyā al-Māzandarānī, Die Resālä-ye Falakiyyä des Abdollah Ibn Moammad Ibn Kiyā al-Māzandarānī. Ein persischer Leitfaden des staatlichen Rechningswesens (um 1363), W. Hinz (ed.), Wiesbaden, 1952, p. 155.。
在伊斯兰征服时期,朱里章地区(包括阿思塔剌八忒)信仰琐罗亚斯特教的波斯居民曾在阿拉伯人入侵初期频频发起叛乱,最终皈依了什叶派,并逐渐发展为伊朗东部较有规模的什叶派聚居地。据穆思妥菲(Mustawfī)称,朱里章城以有被称为“红色的墓”(Gūr-i Surkh)的什叶派圣墓而闻名。据说墓主人是阿里后裔之一第六代伊玛目贾法儿·撒底黑(Jafar al-adīq)及其子摩诃末(Muammad),均葬在距阿思塔剌八忒不远的朱里章城,并成为什叶派信众中有影响力的圣墓[注]amd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 al-Qulūb, G. Le Strange (tr.), Leyden: Brill, 1919, p. 156.。不过在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出身于突厥部族的统治者属逊尼派,并对什叶信众持敌视态度。例如,《治国策》作者内扎米·木勒克记述道:如果有人提出要为突厥人服务,若他说自己是来自库姆(Qum)、卡尚(Kāsān)、阿巴(}bā)或雷伊(Ray)的什叶派,就会遭到拒绝并被告知:“走吧,我们是杀蛇的而不是养蛇的。”而在另一节里,和内扎米·木勒克交好的哈纳斐派法官穆沙塔伯(Mushab)说:“如果你看到一个诨名为拉斐迪(Rāfióī, 即什叶派)的人声称信仰伊斯兰教,就杀死他们,因为他们是多神论者。”[注]Khwāja Nizām al-Mulk, Siyar al-mulūk (Siysāt-nāma), Hubert Darke (ed.), Tehran: Intishārāt-i Bungāh-i Tarjamah va Nashr-i Kitāb, 1981, pp. 216, 219; Nizām al-Mulk, The Book of Government, Or, Rules for Kings: The Siyar al-Muluk, Or, Siyasat Nama of Nizam al-Mulk, Hubert Darke (tr.),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160, 162.也正因如此,在蒙古兴起之前,故阿思塔剌八忒的什叶派社群在波斯语文献中显得籍籍无名。


对当时生活在中亚、蒙古以至汉地的什叶派穆斯林而言,阿思塔剌八忒也成了他们和伊朗本土联络的重要节点。因征发赋税和稽核账目的需要,大汗的使节常往返于哈剌和林与阿思塔剌八忒之间[注]Juvaynī,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p. 495;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第553页。,同时也应有不少本地的穆斯林前往大汗斡耳朵供职。巴惕惕序中提到的两位信息提供者即为一例。札八儿火者应该也和当时许多移居汉地的穆斯林一样,通过家族和宗教的网络与中亚、波斯的什叶派社群保持着联系。这也能解释为何《纪事》所述札八儿火者在征金过程中的作用,可以与汉文史料相互印证。

阿思塔剌八忒事实上也是伊朗东部逊尼、什叶和亦思马因等数个教派相杂居的地方。伊本·阿昔儿在塞尔柱统治时期唯一一次提及该地是在554H/1159 年。因为当年阿思塔剌八忒的什叶派居民和当地的沙斐仪派支持者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多名沙斐仪派教徒被杀。由于塞尔柱君主在宗教上的倾向性,什叶派居民遭到镇压,许多人不得不亡命他处[注]Ibn al-Athīr, The Chronicle of Ibn al-Athīr for the Crusading Period from al-Kāmil fi'l-ta'rīkh, D. S. Richards (tr.), Burlington: Ashgate, 2007, vol. 2, pp. 109-110.。志费尼则记载道:1245年前后盘踞在厄尔布尔士(Alborz)山区的“异端”——亦思马因派徒众烧杀并摧毁了迦布德扎马、阿思塔剌八忒、阿模里(Amul)等地[注]Juvaynī,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p. 542;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第603页。。而阿思塔剌八忒当地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冲突,甚至一直延续到伊利汗国统治瓦解后。由异密·外力(Amīr Vālī)领导的什叶派武装和支持逊尼派的撒八儿答儿(Sarbadār)政权仍然围绕着阿思塔剌八忒争斗不已[注]John M. Smith, The History of the Sarbadar Dynasty 1336-1381 A.D. and its Sources, Hague: de Gruyter-Mouton, 1971, (Publications in Near and Middle East studies. Series A, Monographs), pp. 85-86.。
三、札八儿火者史事西传的什叶派背景


从《蒙古纪事》一书写作的时代背景来看,什叶派等宗教少数派主动选择和征服者合作,充当后者的智囊和耳目,恐怕是当时中亚、西亚伊斯兰社会面对蒙古风暴的一种普遍性焦虑心态的反映。这点在札八儿火者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汉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史书均聚焦于他在征金事件中的作用。不过和《蒙古纪事》中的正面形象不同,从来自坚持抵抗蒙古入侵的德里宫廷,且持敌视什叶派立场的术兹札尼看来,札八儿火者无非是鼓动蒙古人入侵周边政权的帮凶。如果说在札八儿火者的故事里,因为受害者是“异教”的金朝政权,术兹札尼未曾明确表露其态度的话,那么在同书的“窝阔台纪事”中,术兹札尼就用一种刻板的笔调描写了一个来自不花剌的伊玛目札马鲁丁(Jamāl al-Dīn)。后者据称“经常祈祷让蒙古人前去入侵剌火儿(Lahor)”[注]Jūzjānī/Raverty, Tabakat-I-Nasirī, vol. 2, p. 1142.。
随着蒙古人兵锋继续西进,越来越多类似的报道见诸同时或稍后的穆斯林作者笔下。而在这种主体族群(或主流宗教群体)对少数宗教教徒越发猜忌的心态影响下,当地社会的教派矛盾愈演愈烈,事实上也削弱了对蒙古人的抵抗实力。如在阿拔思王朝覆亡前夕,身为末代哈里发宰相的阿里合迷(Muayyad al-Dīn b. al-Alqamī),因为是什叶派教徒就成为众矢之的。据称,他借职务之便大肆扩大什叶派的势力,遂招致逊尼教徒的不满。双方冲突的结果是什叶派落败,一些人被杀而另一些遭劫掠。阿里合迷于是暗中写信联络旭烈兀,表示要献城出降。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在德里的术兹札尼和埃及的马穆鲁克作家答哈必(al-Dhahabī)各自提供了一个相似的版本[注]abaqāt-i Nasirī, vol. 2, pp. 1228-1234; abaqāt-i Nasirī, vol. 2, pp. 190-192; Muammad Ibn-Amad al-Dhahabī, Tarīkh al-islām wa-wafayāt al-mashāhīr wa al-alām, Umar Abd-as-Salām Tadmurī (ed.), Beirut: Dār al-Kitāb al-Arabī, 1997, vol. 56, pp. 33-39.。而在报达陷落后,什叶派和基督徒(Erke’un)受到蒙古人事实上的豁免,也不免让旁观者进一步坐实了这种猜忌[注][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三卷,第69页。Biran比较并列举了波斯、阿拉伯、叙利亚语文献中所记载的得到豁免的不同宗教派别。Michal Biran, “Music in the Mongol Conquest of Baghdad: afī al-Dīn Urmawī and the Ilkhanid Circe of Musicians”, The Mongols’ Middle East: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Ilkhanid Iran, Bruno de Nicola, Charles Melville (eds.), Leiden: Brill, 2016, p. 141, note 27.。有趣的是,当效力于伊利汗的阿拉伯语作家伊本·法瓦的(Ibn al-Fawaī, 1244—1323)在其编年史重述这个故事时,却删去了所有不利于什叶派的指控[注]Hend Gilli-Elewy, “Al-awādit al--āmīa: A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he Mongol Conquest of Baghdad, 656/1258”, Arabica 58, 2011, p. 368.。这也许和伊利汗宫廷中什叶派的得势有关。
这种猜忌心态同样也体现在带有“官方”色彩的波斯语史家笔下。如《世界征服者》的作者志费尼(其家族为逊尼派)所记述的负面的穆斯林形象多为什叶教徒。如企图骗取窝阔台财物的阿里后人察儿黑(Chargh)以及在脱列哥那朝扰乱朝政的失剌(Sīra)等人[注]Juvaynī,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pp. 224, 245;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第244—245、270页。。由于志费尼书在早期蒙古史中的权威地位,他对于宗教派别的差异态度也影响到了后世的大多数作家。
正如Stephan Conermann在讨论马穆鲁克编年史的书写传统时所作的评价:“一般说来,马穆鲁克的编年史是虚构和史实参半的作品。”[注]Stephan Conermann, “Tankiz ibn Abd Allāh al-usāmī al-Nāirī (d.740/1340) as Seen by his Contemporary al-afadī (d.764/1363)”, Mamluk Studies Review 12: 2, 2008, p. 4.而历史主题(topos)或许真实而有所本,其作用则是将记述者的各种主观意图牢牢锚定在真实的历史参照物上[注]Albrecht Noth, Lawrence I. Conrad, The Early Arabic Historical Tradition: A Source-Critical Study, Michael Bonner (trans), 2nd ed. Princeton: The Darwin Press, 1994, p.109.。同样,我们也可以将相似的评价加诸波斯语,或加诸伊利汗国境内编写的穆斯林蒙古史书身上。从前揭札八儿火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至少我们在讨论《蒙古纪事》这部作品时,应该考虑到该作品是历史本相和写作者意图结合的产物。写作者试图按照自身的立场和情感好恶重塑历史叙事的努力,恰好折射出其所身处的时代和社会本身所存在的各种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