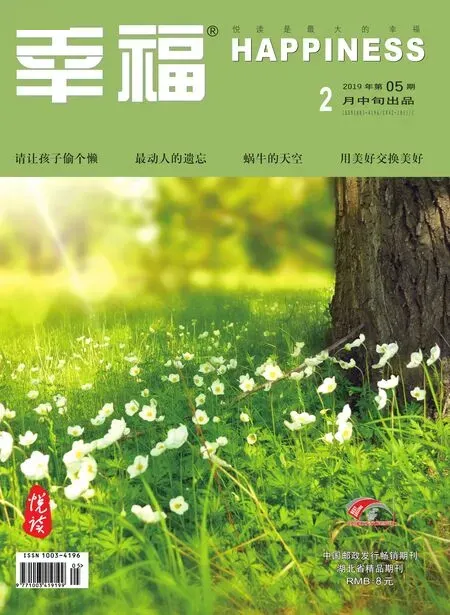飘香
2019-03-22肖静
文/肖静
记忆中,童年的生活充满艰辛,那时物资贫乏,儿时的我们,从不敢奢望有什么零食可吃,更谈不上大肉大鱼……只有眼巴巴地盼着过年,过大年,才有诸如花生、瓜子、蚕豆、翻饺、糖果等供我们解馋。年饭桌上也少不了一些素常难以见到的荤腥大菜,如寓意团团圆圆肉丸子。
我家的年饭一般都在腊月二十九的傍晚吃,母亲掌勺,一家老小围着八仙桌,吃一年中最大的一餐。
我们住的职工宿舍只有两层楼,在晚餐过后的二三个小时时间,楼上楼下家家户户纷纷响起剁肉声,就像一首单调而喜庆的春节奏鸣曲。这首令我们期待已久的曲子有时会响到凌晨。这便是各家各户忙年的节奏。
母亲经常会大声喊我们帮忙。那时,我才十岁多,能帮什么呢?母亲准备的年货,无非是炸藕夹、削荸荠、剁肉末、炸肉丸、煎鱼块、蒸糯米、做“翻饺”,我们几个孩子充其量打打下手罢了。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削荸荠和炸丸子。母亲做肉丸子,不仅要掺入鸡蛋和鱼红,还要放些荸荠。母亲说,这样做出来的肉丸子,泡,嫩,口感好。
削荸荠的任务总是交给我。平时我们难得吃到荸荠,见到荸荠,很是口馋。我忍着寒冷,用清水把一小盆子荸荠一个一个洗净,然后拿一把小刀,像削苹果那样,将紫红的皮去掉。削着削着,忍不住便将削好的荸荠直接塞进嘴里,脆嫩,清甜,好吃极了。现在想来好笑,原本不多的荸荠常常越削越少,母亲很快就发现了,她知道是我嘴馋惹的。每到这时,母亲什么话也不说,只笑着用眼睛斜睨着我。我对着母亲吐吐舌头,起劲地削,再不敢吃。
待我削完,母亲就将白嫩的荸荠,用菜刀拍扁,切成细细的粒子,放到剁好的肉碎碎里,一起盛入菜盆。然后,母亲撸起袖子,左手扶着盆边,右手伸进盆里,用力搅拌。母亲划着顺时针,边搅边说,搅拌是有窍门的,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搅的时间越长越好,做出来的丸子才有韧劲,炸出来就泡。不知过了多久,盆里的肉碎碎充满了气泡,肉碎碎好像变多了,慢慢快溢到盆边,母亲再在上面撒上各种佐料,拌匀。
一切准备就绪。之前早已架上炉子的大锅,里面满满一锅油,此时已经沸腾起来。母亲将盆子端到炉子跟前,放在一张板凳上,然后取一只白瓷调羹,舀着肉碎碎往油锅里放。转眼,圆滚滚的肉球,扑腾着,活脱脱一群小鸭子在游泳。不多一会,在油的翻滚下,丸子渐渐变黄了,然后金黄,一股子肉香味飘散开来,直钻到鼻子里,沁入心扉。母亲用漏勺将丸子从锅里一网打尽,搁进另一个抹得干干的菜盆里。
我和姐姐弟弟围在母亲身后,你挤我,我挤你,争相看丸子。一年的等待太长,小时候的我就是盼过年,能吃上香香的丸子,这大概是我孩提记忆里颇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最好吃,手端小碗排在第一位。母亲不紧不慢地将丸子从油锅里打捞上来,并不让我们马上吃。我咽着口水,眼巴巴看母亲将很少的一部分留在锅里,让它们多炸一会。原来,之前的丸子并没有完全炸透就捞了出来。母亲说,丸子不能炸得太透太老,吃的时候还要回锅,如果现在炸透,再回锅就不泡了。她还说,这些丸子要管够五天过年,要省着点吃。
我的小碗里很快就有了两三粒乒乓球大小的肉球,它们金黄欲滴,冒着热气,散着香味。我根本顾不上烫嘴,立即塞进小嘴巴里,哈着气,嚼呀嚼,足以将整个味蕾融化。那样的一种美好感觉就是让我觉得,不枉等了三百多天的“年”终于幸福地到了。母亲不让我们吃够,她怕我们吃坏了肚子,用她的话讲,要“欠”着吃。实际上,母亲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就没有多的丸子供我们随意吃,我们平日油水不多的小肚子也经不住猛吃,不欠着吃也不成。
时光如白驹过隙,过了若干年,生活物资变得丰富起来,我们想吃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大大小小的菜市场和超市随时都摆着肉丸子,在买的时候,我们还挑肥拣瘦。母亲上了年纪,精力大不如从前,几个子女长大成人,各自忙工作忙小家,也不可能像小时候那样帮她打下手,她也就不再自己炸丸子了。听弟弟说,年迈的母亲其实又炸过一次丸子,那一次,没有我们端着小碗围在身边,上演偷着吃争着吃的小戏,她仿佛就没了灵感似的,忘记放荸荠,买的肉瘦,搅拌肉碎碎的时间短了,结果,出锅后的丸子吃到嘴里,像渣子一样。
不知从哪一年起,我家的年饭改到酒楼吃了。儿时一幕幕往事像电影似的回放时,我时常感叹现代的生活削去了浓浓的过年气息,越发想念在家里吃年饭的味道,怀念温暖的厨房,幸福的油烟,飘香的丸子,袅袅的水气,孩子们在狭小厨房挤撞着争吃的情形。只是,很多年过去,很多年也过了很多“年”,而小时候飘香的丸子味道好像再也没有尝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