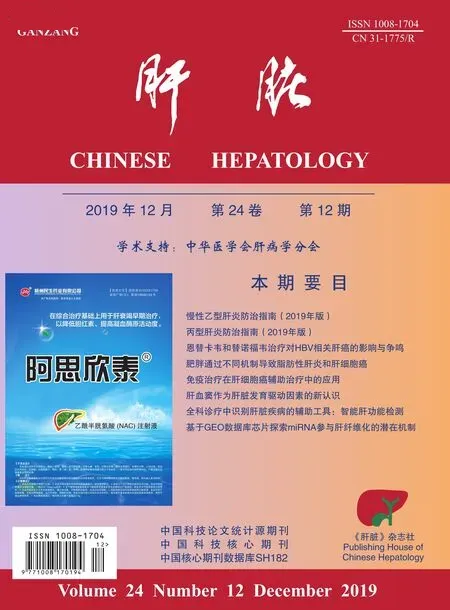恩替卡韦和替诺福韦治疗对HBV相关肝癌的影响与争鸣
2019-03-19邓芮孙剑
邓芮 孙剑
由于口服核苷(酸)类似物能有效抑制HBV DNA并降低肝脏终点事件包括肝细胞癌(HCC)的风险,当前国内外指南均建议具有抗病毒指征的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接受核苷(酸)类药物治疗,其中具有较高耐药屏障和安全性的一线抗病毒药物包括恩替卡韦(ETV)、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和替诺福韦艾拉酚胺(TAF)。尽管长期口服核苷(酸)类抗病毒药物已大大减少CHB患者肝脏终点事件的发生,但并未完全消除HCC的发生风险。近年来多篇相关研究就一线抗病毒药物ETV和TDF在降低CHB患者的HCC发生率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2019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在Gastroenterology杂志在线发表的一项全港队列研究回顾性比较了28 041例经ETV治疗的CHB患者和1 309例经TDF治疗的CHB患者的诊疗数据,其中TDF治疗组只有8例发生HCC(0.6%),而ETV治疗组中则有1 386例HCC发生(4.9%)[1]。考虑到两组样本量相差悬殊,再加上基线特征不均衡,故研究者采用倾向性评分逆概率处理加权法(IPTW)、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结果表明,ETV治疗和TDF治疗两组基线特征均衡可比,TDF在降低HCC发生风险方面优于ETV(风险比HRs: 0.33~0.39)。
这与2018年韩国Choi教授等在JAMA Oncology杂志报道的结果一致[2]。他们回顾性分析了韩国健保系统的24 156例初治CHB患者(全国队列,其中11 464例接受ETV治疗,12 692例接受TDF治疗),以及一家教学医院的2 701例初治CHB患者(医院队列,ETV组1 560例,TDF组1 141例)的诊疗数据,首次报道TDF降低HCC发生风险优于ETV。这一结果在肝病学界引发热烈讨论,多个研究团队对该论文的数据和分析提出建议,此后Choi教授等修订了部分数据,并于2019年4月25日替换原文章。修正数据后,接受TDF治疗和接受ETV治疗的两组CHB患者全因死亡率或移植风险并未存在显著差异(HR: 0.89,P=0.22),但TDF治疗组的HCC发生风险仍低于ETV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Rs: 0.61~0.68)。
然而,同样来自韩国的Kim教授等2019年4月在Journal of Hepatology上发表的文章却提示,TDF与ETV在减少HCC的作用上无明显区别[3]。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从韩国4所教学医院共纳入了2 897例CHB初治患者,通过PSM和IPTW等统计学方法比较了ETV和TDF两组患者在抗病毒治疗5年内HCC及死亡或肝移植的累积发生率,结果发现,两组患者在HCC等临床终点事件发生方面没有差异,其中代偿性肝硬化患者的HCC年发生率分别为4.3%和3.4%(校正后HR=0.83,P=0.25),而对于无肝硬化的患者,其HCC年发生率分别为0.58%和0.76%(校正后HR=1.60,P=0.07)。2019年4月的EASL大会上还报道了一项来自美国的纵向慢性肝炎队列研究(CHeCS)[4]。该项多中心研究涉及822例CHB患者(ETV治疗组407例,TDF治疗组415例),结果显示在整体人群、核苷(酸)类似物初治亚组人群及亚裔或非亚裔人群中,ETV与TDF治疗两组间的HCC发生风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理论上来说,韩国Kim教授报道的患者应该来源于韩国Choi教授报道的全国队列人群,为什么结果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一种可能是患者的具体纳入排除标准不同。具体有以下几方面:(1)Kim教授的研究只排除了在治疗开始后6个月内发生HCC的患者,而Choi教授的医院队列排除的是治疗开始后12个月内发生HCC的患者;(2)Choi教授的研究纳入了失代偿期肝硬化的患者,而Kim教授的研究则没有包括该部分患者,这是该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局限,因为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是HCC发生风险很高的人群;(3)Choi教授的全国队列中接受ETV和接受TDF治疗两组患者的重要基线变量如HBV DNA和ALT水平不匹配,而这些是HCC发生风险的重要预测因子;(4)Choi教授的文章中,HCC的累积发生率曲线走向模式不好解释:在全国队列中,治疗2年后ETV与TDF的HCC累积发生率曲线开始分离,但在治疗后2.5年至4年期间,全国队列中TDF组几乎没有新的HCC发生;在医院队列中,由于排除了治疗开始后12个月内确诊HCC的患者,ETV组的HCC累积发生率在12个月后即开始增加,但TDF组患者约16个月后HCC发生率才开始增加,这3到4个月的延迟现象难以解释。而且,从HCC发生率开始增长的时间点到最后一个观察时间点(即第4年),两组的HCC累积发生率曲线几乎保持平行。
在比较长期接受ETV治疗与接受TDF治疗患者的HCC发生风险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目前ETV与TDF两种药使用情况不对等的问题。在TDF上市前几年,ETV就已在亚洲众多国家广泛投入使用,因此医生倾向于在肝功能状态更差的患者中使用ETV而非TDF。而在TDF正式上市以后,由于担心其对肾脏和骨骼安全性的潜在风险,医生可能也会优先考虑使用ETV而非TDF治疗肥胖、糖尿病及老年CHB患者。这一策略可能会使得具有其他HCC危险因素的患者被人为集中在ETV治疗组,造成偏倚。采用一些统计方法只能尽量减少这些重要混杂因素的作用,保证纳入患者的可比性,但事实上并不能完全消除混杂因素的影响。按肝硬化对研究对象进行分层分析仍有重要意义。
尽管目前的研究对这一问题还仍未有定论,是否存在潜在的机制来解释为何TDF能降低更多的HCC发生?从抗病毒治疗应答方面来看,Choi教授团队的报道显示,接受TDF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ETV治疗的患者有更好的病毒学应答[2]。TDF也可能在降低HBsAg方面较ETV更有优势[5]。Choi教授的报道还显示,治疗1年时,TDF组ALT复常率高于ETV组[2]。而过去已有研究报道显示,抗病毒治疗1年时ALT复常率与HCC发生风险相关[6]。从免疫机制来看,TDF和阿德福韦是核苷酸类似物,而拉米夫定和ETV属于核苷类似物,前者能诱导更高的血清干扰素λ3(IFN-λ3)水平,而IFN-λ3在动物模型上发现其具有抗肿瘤活性,这可能部分解释了TDF组HCC发生率低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关于ETV和TDF治疗对HBV相关肝癌发生影响的争鸣尚无定论,因此暂未有足够证据修改现有指南,仍应同时将ETV与TDF作为核苷(酸)初治CHB患者抗病毒治疗的一线推荐药物。需要开展更多的观察性研究,在基线相对均衡的人群中(包括肝脏疾病状态、病毒学应答、依从性等方面),比较ETV和TDF治疗在减少HCC方面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