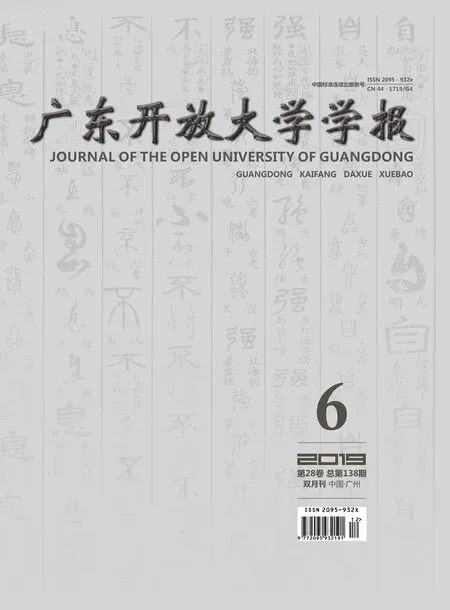潮剧在泰国的传播与发展小议
2019-03-18陈子
陈子
(广州图书馆,广东广州,510623)
潮剧源自南戏。南戏于南宋期间发轫于温州,以宋代南曲戏文为基础,随后在江浙及闽南地区流传[1]。明时南戏传入潮汕地区,以潮汕地区出土的夹杂潮州方言的明朝抄本《金钗记》、《琵琶记》为证。简而言之,潮剧就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南戏,是南戏向潮汕地区传播过程中地方化的结果。
陈毅称潮剧为中国八大出国剧种之一,这与潮汕地区的移民传统分不开。移民促进文化传播和交流,逐渐形成“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剧”的现象。潮剧在海外的传播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地区。其中,泰国是其在东南亚传播的中心之一。“马来西亚40多个潮帮都不能培养或维持自己的潮班,各地潮帮需要演戏时,邀请泰国的潮班为多。”[2]因此,泰国又有潮剧第二故乡之称。
一、地方移民传统与潮剧在泰国的传播
潮汕地区频临南海,素有贩海为生的传统,在这过程中潮人逐渐向海外发展。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有林道乾率领武装集团到南洋,并定居于暹罗南部北大年。18世纪,随着清政府大力鼓励与暹罗进行大米贸易,该地民众利用地理环境之便,纷纷出洋贩米,并带动潮汕与泰国民间贸易的发展。汕头在1860年开埠后成为粤东地区重要的对外口岸,开启了潮汕地区出洋的高潮。泰国是主要的流向地之一,是东南亚地区潮汕人最为集中的国家,在泰国华人各方言群中潮州人占了一半以上的比例[3]。潮州人凭借其善于经商,财力较为雄厚的优势,在泰国华社中有较大的影响力。
随着在泰国潮州人人数的增加,大约在17世纪中后期至18世纪初期潮剧开始在泰国落地生根,“每逢当地华侨举办酬神赛会就已经有来自广东、福建的艺员进行大锣鼓表演和戏剧演出。”[4]20世纪20~40年代,随着来自潮州地区新移民的不断激增,潮剧在南洋尤其是泰国进入繁荣发展期。当时著名的华人聚居区——耀华力路有五大剧院和五大戏班,每个戏班有一个固定演出的戏院,各有名角和艺术特色,时人概括为“中一服饰、赛宝曲、怡梨鼓、梅正嬷”。20世纪30年代,泰国以潮剧为生的人数多达数万人[5]。20世纪40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地潮剧戏班逐渐解散。二战结束后,潮剧在东南亚地区有所复苏。首先是“来自潮州地区农村的大量新移民源源不断涌入泰国。大量潮州人的存在,加上潮剧的内容大多以历尽艰辛、否极泰来、飞黄腾达、家眷团圆为模式,这对于远离桑梓,在异国他乡艰苦创业,企求日后发达的潮州人来说,很容易产生共鸣。”[6]进入50年代潮剧在泰国呈现出低迷的趋势,传统潮剧班的生存也日渐困难。20世纪60至70年代末因“文化大革命”,海内外潮剧的交流几乎中断,由于缺少母体——中国潮剧的滋养,泰国传统潮剧市场大大缩小。
1979年广东潮剧院一团到泰国的演出首先打破了僵局。该年10~11月广东潮剧院一团应泰国泰中友好协会的邀请,一行65人在泰演出22场,姚璇秋、蔡锦坤、李有存等著名演员参与了此次访问。时泰国有评论道:“广东潮剧团此次来泰演出,除完成慈善义举之外,也给当地人士对新的潮剧,新的中国面貌,有着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给此间日走下坡的潮州戏班新的启发,输入新血,重新振作。”[7]自此之后,来自中国的潮剧团多次访问泰国,如广东潮剧院一团、澄海潮剧二团等。其中澄海潮剧二团以华侨过番为题材创作的潮剧《红头船》获得海外乡亲的极大关注。2014年10月澄海潮剧二团受泰国潮州会馆的邀请携《红头船》等剧目到泰国演出并在当地华社掀起了“一股潮剧热”,“连演5夜场场爆满,每场演出结束后仍有许多观众意犹未尽,要求加场演出。”[8]泰国澄海同乡会陈灿泰理事长对澄海潮剧二团的评价是“为弘扬家乡传统文化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亦是吾旅泰澄籍之光!”[9]泰国的潮剧团也积极到侨乡参加演出交流活动。“1993年1月,汕头举办首届国际潮剧节,泰国国内的31个职业和半职业的潮剧团,组成了演员队伍壮大的‘泰国潮剧团’参加大会”[10]。
然而,潮剧的黄金时代已逝,它在海内外都面临着受众减少的困境。海内外的有识之士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积极采取帮扶和提振的措施,“2007年5月23日,中国汕头市成立了潮剧改革和发展基金会,来自泰国的庄美隆先生等海外潮剧爱好者提供了资金、技术、宣传等的帮助。”[11]
二、跨国互动中潮剧的革新与发展
以潮剧为载体的人员跨国往来,推动了中国和泰国潮剧的革新与发展,主要表现为:
首先,制度上的革新——废除童伶制,保护儿童权益。20世纪50年代以前,因为童声较为清脆,潮剧中的生、旦、小丑角色一般由儿童扮演。扮演这些角色的儿童多为贫苦人家的小孩,他们卖身给戏班的年限一般是七年十个月,即从十岁到十八岁,变声期一到,或意味着从艺生涯的结束。儿童在戏班学艺十分苛刻辛苦,稍有差错,常会受到惩罚甚至虐待,这对于他们的正常成长,身心健康是极为不利的。与潮剧的发源地潮汕一样,泰国的潮剧班最初也实行童伶制。“有的潮剧班子到了曼谷以后,又与当地聘请公司合伙,从潮汕招买童伶,作短期训练,然后组成新的班子,挂牌演出。”[12]此现象存在一段时间后,“30年代中期,有人向当局密告潮剧班虐待童伶。1937年有名乌衫‘一鸣’在和乐戏院跳楼自杀,引起当局的重视,下令拘捕班主及教戏先生,并驱逐出境。政府命令禁止潮剧班使用十六岁以下的童伶。”[13]泰国政府的严厉措施使童伶制在泰国的潮剧班中失去生存的根基。
泰国废除该制度对后来潮汕侨乡童伶制的废除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张长虹认为“20世纪30~40年代,泰国潮剧演员、编剧家、教戏先生们相继返回中国,彼此交流,也不断地将其锤炼出的潮剧新精神与新形式传回了故土。”[13]笔者也倾向于此说法。人员的往来使泰国废除童伶制的消息传递到侨乡并推动侨乡废除该制度。20世纪50年代,潮汕本土的潮剧进行了改进,其中之一就是废除童伶制。废除带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色彩的旧制度,一方面保护了儿童,另一方面,使大批女青年被招进戏班,著名潮剧演员姚璇秋就是在该时期从艺,这有利于提高女艺人的地位。
其次,探索潮剧表演的新内容和新形式。潮剧在传入泰国后,也在不断地谋求发展。一是因为泰国的潮剧戏班与祖籍地的潮剧团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竞争关系,因此泰国潮剧戏班必须积极改良潮剧艺术才能赶超祖籍地的艺术水平;二是融入住在国的需要,以使潮剧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泰国潮剧的革新主要表现在:
(1)学习新经验。20世纪20年代,泰国的潮剧进入改良期,以澄海人陈景川为首的“青年觉悟社”在潮剧改良上成效显著,他们当中就有把中国的改良经验带到泰国的移民。如谢吟于1927年到曼谷,“他们受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仿照当时国内一些影业公司(如明星公司等)拍摄的电影,以编演时装新剧作为改革艺术的尝试。”[14]
(2)学习新剧目。“1981年秋,广东潮剧团在香港演出《春草闯堂》,香港一家公司录制的录像带很快就传到泰国。曼谷的怡梨兴潮剧团买到录像带后,演员就根据录音练唱。半年后,当广东潮剧团来曼谷演出时,《春草闯堂》早已搬上泰京舞台了。”[15]从这个例子可见泰国潮剧团的进取心,亦可窥见香港-泰国-潮汕三个区域之间潮剧的互动网络关系。
(3)泰语潮剧:中泰文化交融的结晶。泰语潮剧的产生与泰国当地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庄美隆先生的努力分不开。庄美隆先生1941年生于泰国,从小因母亲常带他看戏而与潮剧接下情缘。他在16岁时返回汕头,在这期间学习了大量的潮剧知识,1973年返回泰国后,发现潮剧在泰国发展空间日益缩小,“我在参加剧团演出时观察到,有不少泰国人和潮人新生代也喜欢潮剧,但却看不懂听不懂。”[16]因而在潮剧表演中引入泰语,形成了泰式潮剧。泰式潮剧诞生后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如电视、义演,得到当地的关注,并引起了王室的注意。“在泰国乐达那歌信皇朝建都200周年时,庆祝活动上演出了潮调泰语剧《包公铡侄》,泰皇拍贴诗琳通公主为其主持开幕仪式,并多次出席义演,成为坐上宾。诗琳通公主声称本人也是中国戏迷,力倡发扬泰式潮剧为泰国国粹[17]。
2006年潮剧文化周期间,泰国潮剧代表团于广州友谊剧院表演泰语潮剧《包公铡侄》、《包公会李后》。“舞台上的《包公铡侄》,一派潮剧唱调、潮剧锣鼓、潮剧表演、潮剧装扮、演出形式与潮剧完全一样,但它应用泰语演唱,倒让潮汕观众只听着熟悉语调,却听不懂演员唱念的语音,这种熟悉又别开生面的潮调泰语剧,便成为这次潮剧国际文化周艺术交流的热门话题。”[18]
泰语潮剧的产生在中泰潮人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或持支持意见认为顺应形势变潮剧“中为泰用”,“可以争取中青年广大观众,能作为泰国的一个剧种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20];或担心潮剧将在泰国消失。虽有此担心,但泰语潮剧是当地华人移民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使潮剧在泰国得以加入新元素,焕发新的生机。泰语潮剧的产生在丰富潮剧表现形式的同时,亦增强了泰国民众对华人及其族群文化的了解。
三、结语
潮剧作为地方戏种,是海内外潮州人亚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潮州人对潮剧的深厚感情,推动了以潮剧为桥梁的跨国互动。在互动中泰国移民得到心灵慰藉,获得了亚族群文化认同;祖籍地潮剧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丰富。不过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潮剧在泰国的发展却陷入困境,笔者认为泰国华人的代际更替是主要原因。20世纪50年代左右銮披汶政府对华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速华人的同化,其中移民配额大为减少,由每年大约三万名减少到两百名,标志着大量中国人移居泰国时代的结束,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潮汕地区。泰国华人逐渐完成了由“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变。现时对潮剧有感情的群体多以20世纪上半叶移民泰国的老华侨华人及他们的子女为主,他们或受家庭的熏陶,或年少时有过家乡生活的经历。但他们多年事已高,而后代缺乏祖籍地生活经验,潮剧难以引起他们的共鸣,因而潮剧在泰国进入困境难以避免。当然,潮剧的衰落原因复杂,是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代际更替是主要原因。
不过,重振并非毫无机会。据笔者的了解,第四代华人并没有如施坚雅所预测的那样完全同化于泰人社会,有的华裔身上还保持着一定的华人特征。这主要是受祖父母辈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给泰国带来贸易商机。现时泰国的“华文热”即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商机的反应。中泰两国潮剧的有识之士和相关团体应当借力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借助潮剧的文化纽带作用,加强交流,推动潮剧的改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