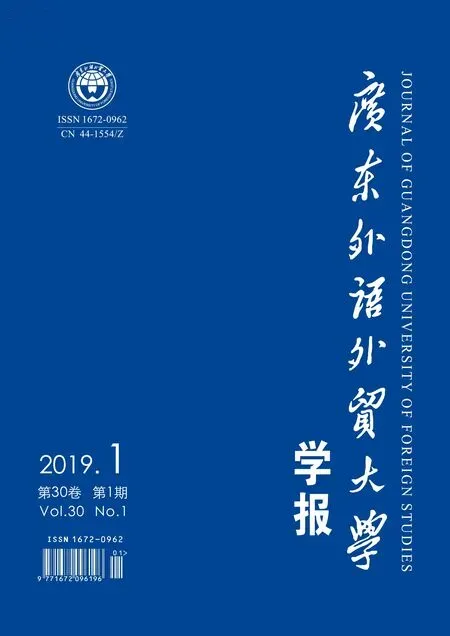后殖民视域下张爱玲与林语堂的跨文化写作研究
2019-03-18蒋美红
蒋美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人文与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 佛山 528000)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登文坛的张爱玲就在其散文《私语》里表达了对跨文化学者林语堂的倾慕:“我要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张爱玲,2012:121)。其时的林语堂已于1935年在美国出版英文著作《吾土吾民》,风行一时,是张爱玲追赶和超越的目标。张爱玲在上海短暂而辉煌的文学生涯之后,张、林二者生活轨迹和创作经历越来越展示出某种相似性:均掌握娴熟的英语,能够进行双语创作;均离开故土来到美国长期生活;均英译了各自心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经典著作;均以英语为创作语言书写中国经验与故国风物……不同的是,张爱玲的英语创作不断遭受挫折,接连被英国、美国出版社退稿,好不容易发表的作品也受到英美主流评论界的冷遇;不仅与林语堂在英美文化界持续的炙手可热形成鲜明对比,也与自己早年在上海巨大的成功形成强烈反差。
在华语文学界崇高地位的光环烛照下,张爱玲在美国“水土不服”的后期创作生涯越发显得黯淡,以致不少当代研究者认为张爱玲创作力萎缩,根源在其“英文写作、处理口语时,时见力不从心”(刘绍铭,2016: 159),文字再不能像汉语写作那样可以兀自燃烧,认为如果她生活无忧,把精神和精力全放在中文书写上,该多好!张爱玲的英语即使不能与自己的汉语表达相媲美,但在同一个向度我们也可以说,林语堂的英语未必就一定比其自身的汉语好,毕竟在英语世界里,林语堂远不如狄更斯、奥斯丁那样的文体家。客观来讲,张爱玲也不是没有支撑其成为林语堂式英语作者的英文能力。著名学者夏济安、夏志清兄弟都曾赞佩张爱玲有着随心所欲中英文互译的本领,美国新闻处处长Richard M. McCarthy多年之后谈及他于20世纪50年代初读《秧歌》时的惊异佩服,认为自己写不出那么好的英文,既羡慕也忌妒张的文采(刘绍铭,2016:156)。可以看出,林语堂、张爱玲的英译及英语作品当时在美国市场上一冷一热,与其各自英语水平关系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自身对林语堂的评价也存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如果说早期张爱玲做过“林语堂梦”,但在美国,此时“得意”的林语堂却在“失意”的张爱玲心中褪色。张爱玲不仅在其生前发表的《忆胡适之》里绕了一笔感慨胡适“竟没有林语堂有名”,言下大不以为然,在其身后出版的信件中,更直言“妒忌”林语堂,觉得他“不配”( 张爱玲,等,2011:60)。与其说此等略显尖酸的评语是张爱玲面对林语堂在美国市场成功的酸葡萄心理(刘绍铭,2016: 156),不如说是心高气傲的张爱玲对自己文学理念及跨文化写作的自信。确实,几十年后的今天,类似于张爱玲在中国大陆由被遗忘到备受追捧的再经典化,张爱玲的英译和英语创作地位在其曾备受冷落的美国文学场也呈上升之势,在太平洋两岸重新燃起一波对张爱玲其人其作的研究热潮(Nicole, 2016:220)。
可以说,当年张、林的英译及英语创作在美国的一冷一热及几十年后的升降易位,涉及张、林二人在跨文化写作中不同的文化本位和翻译策略选择,涉及文本背后复杂的中西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为我们考察后殖民语境下跨文化写作的历史条件和权力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
一、场域的影响:进入美国文学场的不同机缘
20世纪80年代初,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是张爱玲在大陆再成热潮的重要批评文章,其中的论述也被一再征引。“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柯灵以为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香港”改为“上海”、把“流苏”改为“张爱玲”,简直天造地设。“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柯灵,1989)。虽然彼时“文学场”的概念尚未引入中国,但柯灵的论述暗合了“场域”的概念(Bourdieu,1992:80-97),作家仅为文学场的一个“行动者”,其作品的出版、接受和流通要受整个权力场的制约。虽然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的文学才华,但如果没有上海沦陷这一外在的社会情境,张爱玲未必能够如此迅速地进入文学场最中心的位置,在上海红得发紫,风头一时无两,取得强有力的“文化资本”。
类似于张爱玲进入上海文坛,林语堂进入美国文学场也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其初入美国文坛是1935年,此时的西方一战阴影尚未从记忆中退去,空前经济危机又使二战的阴云形成惘惘的威胁,加剧了西方文明的不安全感。在此背景下中国因其战略位置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西方世界需要深谙中国文化又能用西方语言和思维方式来讲述的论者。而拥有西方博士学位,又获当时西方最负盛名、于1938年凭中国题材《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本土女作家赛珍珠强力推荐的林语堂便成为“古老神秘幽远的东方”最合适的讲述者。博士学位本身即为西方文化体系认可的文化资本,赛珍珠对林语堂的介绍“实际上又使林语堂从中国文化中携带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能不贬值地直接进入英语市场”(杨雪,2010:151)。多种因素的合力,林语堂的《吾国吾民》1935年由赛珍珠主持的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一经问世便在畅销书上名列首位,迅速在欧美市场打开知名度。
张爱玲则晚林语堂近20年来到美国,此时已势与时移。冷战使中西关系处于最为紧张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更使美主流社会对中国既警惕又居高临下。“处于内忧外患的美国文学场中,来自中国大陆女作家张爱玲要想跻身主流文坛可谓举步维艰”(游晟、朱健平, 2011)。张爱玲没有西方的学位,昔日在中国大陆的巨大成功又无法转化为美国文化场的文化资本,孑然一身到美国的张爱玲只能从头再来。她将自己在中国最获成功的《金锁记》改译为theRougeofNorth,转战美国市场,却发现没有一家美国书商有兴趣。至60年代后期美国由于民权运动的影响,少数族裔取得应有的关注并日渐进入主流,美国文化场才开始再度接纳亚裔作家。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以《女勇士》一书在美国文坛取得巨大成功,已经是1976年的事了,而此时张爱玲在美国的英语写作已基本停止,只从事学术领域的英语翻译。如果说张爱玲在上海进入文学场是“过了这村,没有那店”(柯灵,1989),则其进入美国文学场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半个世纪之后,张爱玲的英语作品又重新在美国得到重视。究其原因是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中国的再度崛起使美国再度掀起研究热潮,而在中国早已被经典化的张爱玲自然是关注的对象。美国重新出版了theRiceSproutSong(1998)和RougeoftheNorth(1998),她的汉语创作如LoveinaFallenCity(2006)和散文集WrittenonWater(2005)等也被译成英语出版。随着对张爱玲再经典化出力最多的美国著名华裔教授夏志清在美国文学场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张爱玲得以重续其符号资本在英美文学场的兑换和传递,这是张爱玲的跨文化写作得以重新进入当代英美文学场的深层原因(杨雪,2010:155)。反之,随着美国人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可能会发现,当初林语堂介绍的中国与现代中国相去甚远,且来自中国本土的文化评价也将稍稍减去当初美国人赋予林语堂身上那神圣的光环。毕竟,翻开任何一本中国文学史,张爱玲都是更为重要的作家。虽然不能就此否认林语堂曾经在美国文坛的影响力,但可以说,在当代的美国,曾经失意的张爱玲实现了一次逆袭。
二、英译文本的选择:平淡而近自然与神秘的东方
如果仅从数量上来看,张爱玲在美期间出版的英译及英语创作文本实在不多。除1955年发表的长篇英文小说《秧歌》(theRiceSproutSong)之外,就只有一篇英语短篇《五四轶事》(1956年),然后就是跨度十余年对《金锁记》的四度改写改译和翻译(1956年首个英语改写版thePinkTears遭退稿,1967年再改写为theRougeoftheNorth于英国出版,回译为汉语版《怨女》,1971年再应夏志清之邀将其翻译为theGoldenCangue)。译作方面,1961年张将自己的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译为Shame,Amah发表之后,也不再有重要的英译作品,1967年开始英译《海上花列传》,但迟至其逝后的2005年才发表。
从中可以看出张爱玲在美国的窘迫——这样的创作数量和题材,即便在中国也难以用版税养活自己。可也不难看出张爱玲意在以平淡而自然的写实艺术、以高雅作家的身份在异域赢得尊重,而不是成为美国人喜欢看的东方传奇的作者,成为“被凝视”的对象。
《金锁记》是这些文本中最具戏剧冲突的,但其叙事重心聚焦于人性的弱点和金钱对人性的异化,这一主题其实非常具有现代性,一点也不“东方”。即便如此,张爱玲还是在不断的改写中,去除《金锁记》戏剧化的部分,从七巧到银娣,人物形象更接近自然。《桂花蒸阿小悲秋》的情节因素也弱化到近乎于无,通过不同人物的穿插,展示女主人公的日常生活。《秧歌》不仅是现实主义题材,行文细节中体现出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更为行家所称道,胡适就言最佩服文中写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夸嗤夸嗤,响得那么厉害”。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为一般读者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张爱玲,2012:17)。“平淡而近自然”的艺术追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可能都难以见容于一般读者,难以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即使如《金瓶梅》,读者多不喜欢西门庆死后的后半部分,究其实质,“还是因为很少人耐得住小说后半部扑面而来的灰尘与凄凉” (田晓霏,2003:315)。
张爱玲在美国遭遇的,还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艺术与市场的两难,而是西方对中国的兴趣与实际的中国存在严重的错位。西方感兴趣于一个他们需要的东方,或者一个想象的东方。正如萨义德所言,这一想象的东方才是东方的原型(王东风,2003),是异国情调的、辽远神秘幽玄的。同时,“对于那些深怀焦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或退路”(史景迁,1997:186),用如田园诗般和平安宁的中国文化救赎欧洲的精神文化危机,这才是他们需要的东方和中国。对于急切找寻社会差异的美国读者而言,张爱玲所描述的中产阶级社会对他们来说似乎太熟悉、太平常了(金凯筠,2003:216),与西方对田园牧歌式的中国想象大相径庭。
张爱玲所拒绝的正是林语堂所给予美国人的东方。林在美国打响头炮的作品《吾国吾民》(1935)及《生活的艺术》(1937年),严格意义上都不是原创的著作,而是利用自己的学识,从中国古籍里选取各种能够代表归隐自然、与世无争等具有东方色彩的段落,翻译成英文再连缀而成。在文本选择上,林语堂明言“乃写与西洋人阅读,故选择与重编皆受限制,……致使甚多名作无法重编故未选入”(林语堂,1994:1)。在汉语源文本里是否名作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目标读者(西方大众)能否接受。林语堂敏锐感到当时西方在工业化的压力下普遍存在着对人性异化的警惕和对自然的回归之情,不无机智地从中国文化中选择田园、自然、隐逸的元素进行翻译、改写,满足西方读者的期待。沿着这条路子,林语堂先后编译出版了《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苏东坡传》等,翻译了清朝沈复反映闲适生活的作品《浮生六记》,从《太平广记》《聊斋志异》《清平山堂从书》等古本中选择20篇故事,集冒险、爱情、鬼怪、讽刺和幽默于一体,汇编翻译而成《中国传奇》等等,在美国打开市场之后,林语堂又用英文创作了《京华烟云》(1939)、《风声鹤唳》(1941)、《朱门》(1953)等反映中国风俗人情的系列文化小说,均取得不错的反响。
综合来看,林语堂编译作品的选取,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西方对神秘东方的好奇,所创造的整体中国形象与西方读者期盼视阀相符合,符合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曾尔奇,2010),从而赢得市场。其创作的英文小说,从最为成功的《京华烟云》来看,并不着力于人物的性格塑造,而是“用小说的形式阐释道家文化精神”(王兆胜,2007:61),除特意翻译《庄子》作题解之外,正文更多处引用老庄,并借书中人物之口弘扬道家思想。
有论者言,如果说张爱玲对《生活的艺术》一类的书可以接受,对林著英语小说则肯定不以为然,两人写小说的路数相去太远。张爱玲写她对人世生活的观察和感悟,林语堂则倾向以小说做介绍中国的工具。林语堂笔下的人物常是观念的演绎,小说过于理念化;张爱玲最讨厌抽象的理论,其小说充满丰盈的感性(余斌,2009)。就介绍中国这一点来看,林语堂所着力塑造的那种古老幽玄的文明、前工业时代田园牧歌似的生活以及微妙的情调正是西方所喜欢的东方,却也正是张爱玲想揭穿的东方。
三、译写策略:对西方读者的强硬与顺应
综合来看,林语堂与张爱玲的跨文化写作都表现出流畅的能动性和自由度,但相形之下,张爱玲虽不无顺应策略做出融入西方的种种努力,总体来讲却“对西方读者十分强硬”(王一凡,2012);而林语堂则“以其一手极流利漂亮的英文,从事文化上的出口事业,自是出色当行”(余斌,1989)。叙事及翻译策略的不同追求是二者跨文化交际实际效果不同的重要原因,也体现了复杂难言的强势文化对异质话语的压制,以及异质话语对霸权的抵制和纠正。
张爱玲是一位忠实于创作、注重作品文学价值的作家和翻译家,她的英语作品主要是自译及同一故事原型的双语写作,而英译的《海上花列传》在源语中又是其十分重视和喜爱的作品,故张爱玲的翻译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文化本位,她在英文创作及英译中,对于中国文化意象及表达习惯的传递几乎到了顽固的程度。有论者统计,张爱玲在《金锁记》的自译文本TheGoldCangue中,忠实套用中国古典小说对白的表达方式,“笑道”译为“said, smiling”达55处,“如此不厌其烦地表现原文中反复出现的套用语,表明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手法极为尊重”(陈吉荣,2007)。甚至在语气词这一看似极为琐碎的细节上,张爱玲也相当认真地用音译的方式,试图传达出汉语的韵味,而不借用英语中既有的、已被英语读者所熟悉的语气词来表现。如TheGoldCangue中,七巧出场的一句“哟”,在汉语中,人们难免会想到王熙凤,而张爱玲未必对西方读者有这个信心,但仍然音译为“Yo!”并用斜体标出,试图凸现这个语气词独特的个性色彩和语言文化色彩(杨雪,2010:114)。在涉及关于婚俗礼仪、谚语等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词汇“翻译”时,张爱玲更是费尽周折,如在婚礼的描写上,TheRougeoftheNorth中充满丰沛的细节,“姑爷姑奶奶吃青果茶,亲亲热热”一段,张爱玲的英文处理堪称经典:“Have tea, Gu ya and Gu Nana Bingfa’s wife used the polite terms for the son-in-law and the married daughter of the house, called Master of Miss and Madame Miss. She offered them tea with a green olive on the lid of the cup and quoted the well-wishing phrase that puns on ching guo, green olive, ching ching jurh jurh, billing and cooing”(Eileen,1967:25)。姑爷姑奶奶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称呼,张舍弃son-in-law和daughter这种既有的表达,而是直接用威妥码拼音法音译过去了,当然她巧妙地在文中通过解释其含义的方法加以补充,但英文文本劈头而来如此生拗的异质语言,当时习惯于“透明的翻译”的英美读者确实难以习惯,即便在现代翻译上这种处理也是较为少见的。但在张的英语文本里,这样的阻抗式翻译却比比皆是。如将“亲亲热热”译为ching ching jurh jurh、 billing and cooing,将“甜甜蜜蜜”译为Tien tien mi mi! So sweet on each other,将“早生贵子”译为Dzao sheng gwei dze, give birth soon to a son who will be a high official等等,刻意用音译处理,再用意译复述,试图在译文中忠实地保留独特的中国文化意象。公平来讲,张的译文中保留了汉语词汇原来的读音,又刻意保留了大量的东方人文风俗形象,试图忠实地传达出中国文化所独有的美学特征,这既可造成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又能够使英语读者在宏观和微观上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不失为一种极有价值的探索和尝试。但正如论者借用张爱玲“打破砂锅纹(问)到底”Break the pot to go to the bottom所生发的议论,“不知有汉的洋读者,打开书才三两页就搞昏了头,是决不肯Break the pot的”(刘绍铭,2016: 160)。如此一来,可读性的牺牲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而林语堂的英语,更多的评价是“地道”。林语堂并不讳言其在西方的创作是以西方人为隐含读者的,这也使得他尽可能地顺应英语文化的认知习惯,尽量不去挑战读者的阅读惯性,以便于读者理解来选择翻译策略。为此,他常常在翻译中对汉语原文中相关的文化因素进行修饰、替换甚至删减。由于林语堂是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中西文化均造诣甚深,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兼才优势,又使其在做出这种修饰、替换和删减时,十分巧妙和妥帖。
如《京华烟云》的女主角木兰,林是这样介绍的“Mulan was the name of a Chinese Joan of Are, celebrated in a well-know poem, who took her father’s place as a general in an army”(林语堂,1999:17)。在这里,“木兰”这一中国经典中闻名的女英雄被修饰为“中国的贞德”,不能不说这两个形象在中西各自的文化传统中确实具有外在的对应性,能够让西方读者在接触到Mulan这一十分拗口的东方姑娘名字时,迅速调集起自己熟悉的文化记忆来理解木兰这一形象的美。当然,由于贞德这一形象在西方读者心中所拥有的强大的文化原型力量,势必会改写、排挤木兰这一东方形象所包含的诸如忠、义、孝以及家族观念、向往田园的隐逸传统等文化元素。此类的翻译策略在林氏英文创作中多有,如《京华烟云》里,“和尚”译为“monk-priest”,其进行的“超度亡灵”直接为“mass(弥撒)”所代替,“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译为“men contrive, but the gods decide”,中国的天道为西方的上帝所代替;在林的另一部重要译作《浮生六记》中, 中国的“姑射仙子”也被译为希腊神话的自然女神“nymph”。
谁也不能否认,让西方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林语堂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那时弱势的中国文化翻译为强势文化的语言时,翻译技巧的选择客观上减少西方读者接近中国的障碍,并由此了解到更多的中国文化,毕竟只有先让人家“打破砂锅”才有机会“问到底”。但由此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排挤和改写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在林语堂普遍存在的文化改译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其在《中国传奇》中对《碾玉观音》的改写。林语堂借用了原故事的前半部,男女主人公因爱私奔,在原著里二人被捉回后女主人公秀秀被活埋,后化厉鬼寻仇。而林氏则按西方“艺术与自我的关系”这一主题进行改编,私奔后男主人公为逃避追捕,被迫放弃自己的玉匠艺术,但终于欲罢不能而再度创作,被通过流落在外的作品为线索被抓。虽然林氏的改译在西方获得了市场上的成功,但许多研究者不免质疑,“林语堂对西方读者的胃口是否迁就太过?”因为“来个低度‘茅台’,西方人喝了也许更觉顺口,只是那已不是真正的‘茅台’了”,对中国的文化意象“牺牲太大,让人觉得冤枉”(余斌,1989)。
四、结语
从跨文化写作的历史来看,相对弱势的中国文化要想与强势的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绝非易事,也非一朝一夕之功。20世纪30年代至1966年,林语堂在美国长达30年的英语创作,其市场上的巨大成功对西方主流文化了解和认知中国起到开拓性的积极作用,但林氏在英语创作及译作中,过于强调译文读者的需求而对源语文化的弱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汉语文化元素被修饰甚至改写,也是客观的现实并越来越引起争议。张爱玲则有意坚守中国小说的传统,坚守写实的艺术,采用保留汉语特色的杂合手法来抗拒英美强势文化的压制,“彰显了中西诗学碰撞中东方文化自尊自信的姿态”,但这种与美国文学场相悖的行文特征与诗学观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她在异乡前行的脚步(游晟、朱健平, 2011)。时至今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当时市场的成败和影响力来判断林、张在艺术、翻译甚至英语能力上的高低,也许林语堂这种世俗上的成功正是张爱玲所不屑的,张爱玲“选择的是偏离了主流的岔道,不会被同时代的多数人所喜欢”,但历史的发展跳过某个阶段,“许多人是时间愈久愈被遗忘,张爱玲则愈来愈被记得” (刘绍铭,2016: 48),也许这句论述张爱玲华语创作的评语在冥冥之中也切合了对她英语翻译和创作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