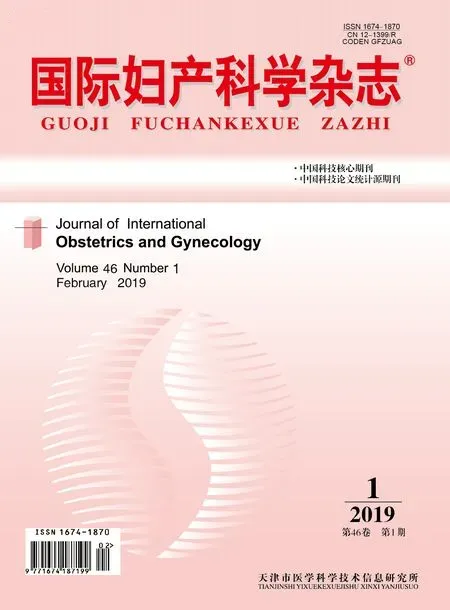母胎免疫中巨噬细胞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2019-03-18黄金花梁梦晨姜梦琦刘悦丁之德
黄金花,梁梦晨,姜梦琦,刘悦,丁之德
近年来,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的不孕不育患者持续增加,我国每年实施的辅助生殖手术平均达到70万例[1]。随着促排卵技术和体外受精技术不断提高,优质胚胎的获取变得相对容易,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成功率却仅有30%~40%。这是因为成功植入除了要求胚泡有侵入子宫内膜的能力外,还需要母体子宫处于能够接纳胚泡植入的正常状态。对于母体来说,胚胎的基因一半来自于母方,一半来自于父方,属于一种特殊的半同种异型移植物。在正常妊娠过程中,胚胎能够在母体子宫中存活、发育成熟并且不产生免疫排斥,依赖于母体对胚胎产生的特殊免疫耐受机制。由于血-胎盘屏障的存在,胎儿来源的细胞和母体来源的细胞仅在母胎界面处有直接接触,因此母胎界面是免疫耐受的关键部位。母胎界面的免疫细胞主要由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巨噬细胞和T细胞构成。巨噬细胞的数量是仅次于NK细胞的子宫内膜白细胞群体,并且还是主要的子宫肌层白细胞群体[2]。巨噬细胞在未妊娠子宫内膜中参与月经周期子宫内膜的分解、再生和修复;妊娠时则在胚泡植入、胎盘形成以及胎儿发育和分娩中发挥重要作用[3],而巨噬细胞功能障碍与妊娠并发症有关,如子痫前期(pre-eclampsia,PE)、复发性流产和早产等。
1 母胎界面巨噬细胞的来源
机体绝大多数组织的巨噬细胞主要有两种来源:一部分来源于造血干细胞,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卵黄囊。目前关于母胎界面巨噬细胞来源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造血干细胞途径。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s,HSCs) 经历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形成单位(colony forming unit of granulocyte macrophages,GM-CFUs)、单核细胞集落形成单位(colony forming unit of monocytes,M-CFUs)及原始单核细胞等几个阶段分化为幼单核细胞,随后幼单核细胞入血成为成熟的单核细胞。国际免疫学协会联合会命名委员会规定,根据脂多糖受体(CD14)和Fcc-Ⅲ受体(CD16)的表达模式将单核细胞分为3个亚组,分别是经典型单核细胞CD14++CD16-、非经典型单核细胞CD14+CD16++和中间型单核细胞CD14++CD16+。三类单核细胞均可分化为巨噬细胞。然而,母胎界面的巨噬细胞是由哪类单核细胞分化?是单核细胞分化为巨噬细胞后迁移至母胎界面,还是单核细胞到达子宫后,在胎盘微环境作用下分化为不同的巨噬细胞亚群?目前具体分化机制等一系列问题仍无定论。有研究推测,滋养层细胞可诱导免疫细胞分化为滋养层支持表型(trophoblastsupporting phenotype)。Mor等[4]发现来自滋养层细胞的条件培养基能够诱导人单核细胞白血病细胞1(THP-1)分泌对滋养层发育和功能有益的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6(IL-6)、IL-8、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和生长调节致癌基因 α(growthregulatesoncogenes,GRO-α);建立在三维构象体外培养系统中的绒毛状结构能够吸引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并在滋养层衍生的结构周围募集该类细胞。Aldo等[5]发现滋养层细胞通过分泌IL-6、IL-8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等诱导单核细胞发生形态学改变,分化为CD14+/CD16+巨噬细胞,且这些巨噬细胞高表达IL-1β、IL-10以及趋化因子配体 10[chemokine(C-X-C motif)ligand-10,CXCL-10]等因子且拥有更强的吞噬能力。
2 母胎界面巨噬细胞的分类
组织中的巨噬细胞可以分为2个亚型:经典激活的巨噬细胞(classically activated macrophages,简称M1型)和替代激活的巨噬细胞(alternatively activated macrophages,简称M2型)。巨噬细胞的分化与Th1/Th2型细胞因子的比例有关。当巨噬细胞被Th1型细胞因子γ干扰素(IFN-γ)单独刺激或被IFN-γ 与细菌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共同刺激后会产生一氧化氮(NO)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引发并促进炎症性反应,杀灭病原体。巨噬细胞以该方式活化后被称为M1型巨噬细胞[6]。M1型巨噬细胞表面高表达CD80和CD86等,可产生TNF-α、IL-12、IL-23等细胞因子,并在Th1型免疫应答中起重要作用,在微生物感染、肿瘤和移植器官等发挥细胞毒效应。M1型巨噬细胞有较强的抗原提呈功能,并能分泌大量活性氧中间体[7-8]。另一方面,当巨噬细胞被Th2型细胞因子IL-4、IL-10、IL-13及免疫复合物、糖皮质激素、开环甾类激素等刺激发生分化时,则被称为M2型巨噬细胞。M2型巨噬细胞高表达CD163、CD206和CD209等,具有免疫抑制特性,并高表达抗炎因子,如IL-10,参与凋亡细胞的清除和组织重建等过程[9-10]。M2型巨噬细胞包括M2a、M2b、M2c和M2d 4个亚群,这4类细胞均具有免疫抑制功能[11]。
此外,有研究发现M1型及M2型巨噬细胞均存在于正常母胎界面,初期以M1型为主,之后一直到分娩变为M2型为主[11]。在特定的环境下,M1型和M2型可以相互转换。体外研究证实,在IFN-γ或Toll样受体配体的刺激下,M1型可以分化为M2型,反之亦然[12]。不同妊娠时期,不同巨噬细胞亚型的比例及分泌的细胞因子数量均有变化,当妊娠期间发生微生物感染、糖尿病和过度节食均会影响M1/M2型巨噬细胞和细胞因子之间的平衡,并对妊娠产生破坏作用[13-14]。
3 蜕膜巨噬细胞(dMΦ)在妊娠中的作用
巨噬细胞存在于机体绝大多数组织,不同组织中的巨噬细胞具有不同的组织特异性功能。dMΦ的吞噬作用可以识别、清除病原体、凋亡细胞的碎片等有害物质,保护子宫不受病原体的入侵,维持子宫组织环境的稳态,并且dMΦ可以抑制炎症反应的发生、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保证母体及胎儿的健康。同时,dMΦ是子宫中重要的抗原提呈细胞,并能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包括与免疫调节有关的细胞因子如IL-4、IL-10和TNF-α,与血管生长相关的因子如血管生成素、角化细胞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1)、MMP-2、MMP-7、MMP-9、MMP-10 等,在血管生成、宿主防御、免疫应答、组织发育、代谢、重建和修复以及维持体内平衡中均发挥重要的作用[15]。在胚胎种植期,母胎界面巨噬细胞以M1型激活为主;当滋养细胞侵入到肌层时,则为M1/M2型共同调节模式;直到充足的胎盘-胚胎血液供应系统建立以后,转为以M2型为主,直至临产[16]。
3.1 免疫调节作用作为子宫蜕膜重要的抗原提呈细胞,dMΦ的一个主要功能是维持免疫耐受与免疫应答之间的平衡,特别是对T细胞活化的调节。在妊娠早期,dMΦ低表达共刺激分子(co-stimulatory molecule)CD80和CD86,提示dMΦ可能有抑制T细胞激活的作用。此外,dMΦ还产生IL-10、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TGF-β和吲哚胺双加氧酶(indoleamine dioxygenase,IDO)等免疫抑制分子,低表达转录因子干扰素调节因子5(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5,IRF5)。IDO能够抑制T细胞激活并诱导调节性T细胞分化[17],而IRF5是典型的M1型细胞因子,可以促进Th1和Th17应答[18]。因此dMΦ可能通过抑制T细胞激活表现出免疫抑制作用,从而维持母胎界面的免疫耐受。有研究显示,dMΦ表现出的M2型巨噬细胞特点并非由Th2型细胞因子诱导而来,而是由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M-CSF)和IL-10诱导分化而来[19]。dMΦ对胚胎的免疫耐受作用也可能由胎盘滋养层细胞诱导而来。Svensson-Arvelund等[20]利用条件培养基加入妊娠早期胎盘组织培养单核细胞并诱导其分化,得到的巨噬细胞表现出dMΦ的特点,即高表达CD14,CD163,CD206,CD209,低表达细胞间细胞黏附分子3(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3,ICAM-3),且表现出与加入胎盘组织量的依赖性效应;同时,抗炎因子IL-10以及在dMΦ中典型表达的趋化因子配体18(chemokine ligand 18,CCL18)其表达量也显著上升,而诱导Th1和Th17细胞的M1型细胞因子IL-12和IL-23其表达量未见改变,说明胎盘滋养层细胞可能具有诱导巨噬细胞向M2型分化的能力。
3.2 在螺旋动脉重塑(spiral artery remodeling)中的作用子宫螺旋动脉重塑是在胚外滋养层细胞、子宫NK细胞以及巨噬细胞等一系列细胞共同作用下,受到精确的时空调控的过程[15]。在子宫螺旋动脉外膜和血管壁中都有白细胞分布,且分布于血管外膜的白细胞更多,而巨噬细胞是其中数量最多的白细胞亚群。有研究发现,在子宫螺旋动脉重塑过程初期滋养层细胞还未长入时,巨噬细胞已经聚集在子宫螺旋动脉周围[21],可能为帮助螺旋动脉进一步接受重塑做好准备。一项针对从妊娠早期蜕膜中分离出CD14+的巨噬细胞研究显示,dMΦ并不具有诱导胚外滋养层细胞向螺旋动脉侵入生长的作用,也不影响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分化状态,但可以诱导细胞外基质的降解,并能吞噬凋亡的血管平滑肌细胞[15]。在螺旋动脉重塑过程中,也会有一定数量的滋养层细胞发生凋亡,dMΦ能够及时吞噬清除凋亡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和滋养层细胞残骸,防止炎性物质释放到组织即阻止蜕膜炎症反应的发生。动物实验表明,小鼠在围植入期(peri-implantation period)子宫中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的表达显著上升,提示子宫巨噬细胞通过上调iNOS的表达增加NO的分泌[22],NO不但可以促进子宫内膜的蜕膜化和血管的新生,而且可以增加血管的通透性,从而促进血液循环和营养物质之间的交换,有利于胚胎发育[23]。另有研究显示,在子宫螺旋动脉重塑的过程中,巨噬细胞也影响胚胎滋养层细胞的生长,Buckley等[24]在体外培养滋养层细胞时分别加入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的培养基,与后者相比,前者滋养层细胞的运动性降低,裂解的半胱氨酸蛋白酶3(Caspase3)表达量显著升高,在人工基底膜上形成的网状结构短而分支多,由此提示M1型巨噬细胞可能会降低滋养层细胞侵入子宫内膜的能力,并诱导滋养层细胞凋亡,导致子宫螺旋动脉重塑的效率低下。
4 巨噬细胞与病理妊娠
4.1 PE是指妊娠20周后孕妇出现高血压,并伴有蛋白尿或全身性疾病,常累及肾、肝、脑、肺等多个器官,导致急性肾衰竭、肝破裂、脑血管意外、肺水肿等,这是孕妇妊娠期和围生期死亡的主要原因[25]。PE的发生发展与滋养层细胞的入侵以及子宫螺旋动脉重塑的缺陷有关。当正常妊娠开始的时候,母胎界面的巨噬细胞水平升高,起到局部免疫、促进滋养层细胞入侵和螺旋动脉重塑以及血管生成的作用[26]。正常妊娠中期后母胎界面主要是M2巨噬细胞,有研究报道PE患者母胎界面M1巨噬细胞水平升高,提示M1/M2比例异常将影响胎盘的正常发育[27]。Milosevic-Stevanovic等[28]的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滋养层细胞入侵水平差的PE患者其子宫dMΦ浸润水平显著升高,异常的巨噬细胞浸润水平对滋养层细胞入侵起到一定抑制作用,激活的巨噬细胞可诱导滋养层细胞发生凋亡;而Reister等[29]在多年前就已发现PE患者子宫螺旋动脉周围巨噬细胞水平升高,这会对滋养层细胞入侵产生不利影响。另外,PE的发生还与母体异常的炎症反应有关,PE孕妇表现出炎症反应水平升高,促炎症因子如TNF-α、IL-6、MCP-1等在全身及胎盘局部的含量上升。Cotechini等[30]通过家兔动物模型实验,发现用LPS诱导妊娠雌鼠发生炎症反应会提高子宫胎盘活化的CD68+巨噬细胞水平,影响子宫螺旋动脉的重塑,进而导致胎盘灌注不足,引发PE。与此同时,Cotechini的研究团队还发现子宫螺旋动脉重塑缺陷及胎盘灌注不足主要与TNF-α相关,而活化的巨噬细胞是最先产生TNF-α的细胞。上述结果提示巨噬细胞被活化后大量分布于胎盘附近,分泌TNF-α抑制了子宫螺旋动脉的重塑过程[30]。
4.2 复发性流产巨噬细胞是胚胎免疫耐受的核心细胞,也是天然性免疫和获得性免疫之间的桥梁,其可通过识别并耐受胚胎抗原直接影响妊娠结局。巨噬细胞功能异常是导致母胎耐受异常、引发流产的重要原因[31]。有研究证明流产患者中巨噬细胞的增多并活化是导致流产的主要因素之一[29]。也有研究证实在流产病例的蜕膜组织中其M1型巨噬细胞的自噬处于激活状态,提示巨噬细胞活化后自噬功能也相应增强以维持巨噬细胞的功能,而当这个平衡被打破后就会影响母体的免疫耐受,进而引发母体对胚胎的免疫排斥反应,导致流产的发生[32]。但也有临床研究报道,在不明原因的自然流产患者中,子宫蜕膜单核和巨噬细胞数量并无显著变化,而CXCR6+单核和巨噬细胞其表面分子CD206的表达水平明显降低,CD80表达水平明显升高,提示CXCR6+单核和巨噬细胞可能涉及自然流产的病理过程[11]。
4.3 早产巨噬细胞参与早产相关的炎症反应,但具体的作用目前还不明确。研究表明,与足月分娩的孕妇相比,早产的孕妇基蜕膜与壁蜕膜中M1型巨噬细胞的含量较高,而基蜕膜中M2型巨噬细胞含量较少;壁蜕膜中M2型巨噬细胞在二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别,但早产孕妇蜕膜高表达TNF和IL-12,低表达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PARγ)[33-34]。M1型巨噬细胞被活化后,会产生大量炎症因子。在自然分娩以及早产过程中,尽管生殖系统以及母胎界面均有一些M1型巨噬细胞的分布,但早产过程中含量更高,这提示早产孕妇蜕膜M1型巨噬细胞浸润程度升高,导致母体免疫耐受异常,这可能是早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研究还发现,有些M2型巨噬细胞也会表达TNF和IL-12,与足月分娩的孕妇相比,早产孕妇体内M2型巨噬细胞表达TNF与IL-12的水平也较高[33,35]。因此,可以推论巨噬细胞活化可引发炎症,进而影响母体免疫耐受且与早产密切相关。
4.4 弓形虫感染弓形虫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且是人类体内常见的寄生虫之一,妊娠期感染弓形虫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包括死胎、流产、先天畸形等[34]。有研究发现白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亚家族B成员4(leukocyte immunoglobulin-like receptor subfamily B member 4,LILRB4)受体基因敲除的妊娠小鼠感染弓形虫后,与野生型小鼠感染弓形虫后相比,更容易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同时该研究还发现,LILRB4受体基因敲除小鼠与野生型小鼠在弓形虫感染后,子宫dMΦ的分布水平均显著上升[36]。另一方面,与未受弓形虫感染的孕妇相比,感染弓形虫的孕妇其子宫dMΦ的LILRB4受体表达水平下调,M1型巨噬细胞的比例显著上升,并伴随着M2型巨噬细胞的比例显著下降[36]。LILRB4受体主要表达于巨噬细胞,作为内源性巨噬细胞活化的负调节因子,在妊娠期特殊免疫耐受的维持方面起到关键作用[37],由此推测弓形虫感染后巨噬细胞LILRB4受体的异常表达及M1/M2型巨噬细胞比例的失调是弓形虫感染后诱发严重并发症的重要病因之一。
5 结语与展望
子宫巨噬细胞在妊娠期母体免疫耐受的建立与维持、滋养层细胞侵入与胎盘形成、子宫螺旋动脉血管的重塑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M1/M2型巨噬细胞在子宫中的数量、比例、功能是否正常与妊娠的发展以及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密切相关,一旦出现异常就会通过促炎症因子的释放、自噬等途径对母体与胎儿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先兆子痫、早产、复发性流产等。
然而,对于子宫巨噬细胞出现异常并影响正常妊娠的具体机制目前还尚未完全明确,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另外,在妊娠的特殊时期,子宫中各种免疫细胞在正常妊娠状态的维持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综合了解子宫中多种免疫细胞及免疫因子构成的免疫调节网络,必将会对巨噬细胞在母胎界面的作用有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