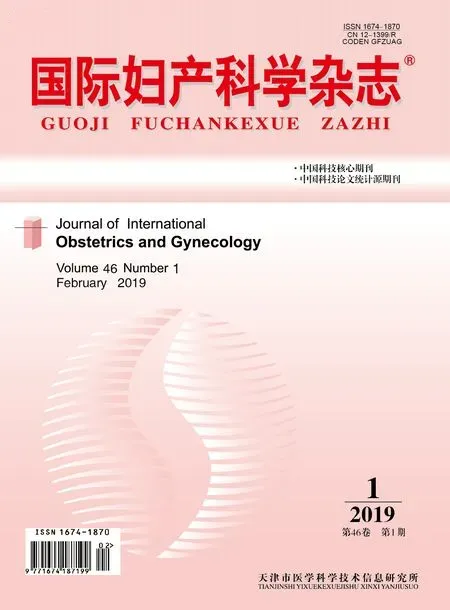宫颈腺癌的病因学研究进展
2019-03-18黄艮平栗宝华
黄艮平,栗宝华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组织学类型主要有鳞状细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SCC)和腺细胞癌(adenocarcinoma,ADC),其他少见类型包括腺鳞癌、小细胞癌和未分化癌。其中,宫颈鳞癌约占80%~85%,宫颈腺癌约占10%~15%[1]。宫颈腺癌起源于宫颈管柱状上皮细胞,包括黏液腺癌(肠腺癌和印戒腺癌)、子宫内膜样腺癌和非黏液腺癌(透明细胞癌和浆液性细胞癌)。尽管宫颈腺癌的发病率明显低于宫颈鳞癌,但近年来呈明显上升趋势。学者们致力于宫颈癌早期筛查的研究,提出“宫颈癌细胞形态学评估”与“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检测”相结合的筛查策略[2]。该策略对于宫颈鳞癌的早期检出率很高,所以鳞状细胞癌的发病率呈下降趋势;但是对宫颈腺癌及其前体病变原位腺癌的筛查作用十分有限[3],宫颈腺癌发病率有所上升,这在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和年轻女性中最为明显[4]。Eduardo等[1]认为,由于宫颈腺癌前体病变通常位于宫颈转化区内侧面凹陷较深处,病变组织难以脱落,以致有效标本获取困难。目前尚缺乏有效的宫颈腺癌筛查策略,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性观念的改变,宫颈癌患者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宫颈腺癌患者年轻化趋势更加显著,严重威胁年轻女性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相较于宫颈鳞癌,宫颈腺癌恶性程度及预后均较差,具有相对较强的侵袭性生物学行为,主要表现为腺癌细胞体积大、肿瘤病灶大、预后差、局部浸润早且淋巴结转移迅速。由于宫颈腺癌具有远距离传播的趋势,以及其对放疗和全身化疗的抵抗性,因此,对于宫颈腺癌的治疗具有挑战性,迫切需要对宫颈腺癌的病因进行深入了解,制定更好的预防措施。现对宫颈腺癌病因学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从事宫颈腺癌研究的学者提供参考,从而根据宫颈腺癌的病因制定出更加完善的预防措施及筛查策略。
1 病毒因素
HPV是一种双链DNA病毒,属于乳头瘤病毒家族。大量研究表明,HPV持续感染在宫颈腺癌的发病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参与宫颈腺癌发病机制的HPV主要是高危型HPV(HR-HPV),并且HPV的型别可能影响侵袭性宫颈腺癌的组织学亚型。在宫颈鳞癌中,HPV阳性率几乎可达100%;但是在宫颈腺癌中,HPV阳性率仅为62%~100%,具有地理区域差异,并且HPV阴性ADC主要是某些特殊亚型[5]。Chen等[6]研究收集了中国7个具有代表性区域性癌症中心确诊的1 051例宫颈腺癌患者感染组织标本,结果显示符合条件的组织标本中HRHPV阳性率为74.5%,其中神经内分泌癌HR-HPV阳性率为100.0%,经典宫颈腺癌为82.2%,非经典宫颈腺癌为40.0%,子宫内膜样腺癌为33.3%。Chen等[7]研究通过对比分析SCC和ADC的HPV类型,发现虽然HPV 16是宫颈癌中最常见的HPV类型;但是在ADC中HPV 18所占比例更大,HPV 18在神经内分泌癌中占比58.3%,腺鳞癌中占比40.2%,非典型宫颈腺癌中占比40.9%。Mabuchi等[8]研究发现HPV 18可以作为评估宫颈腺癌预后的预测因子,HPV 18阳性的宫颈腺癌具有更强的生物侵袭性,且预后相对较差。
长期持续的HR-HPV感染是导致宫颈腺癌的重要机制,从最初感染HPV至发展成为浸润型宫颈腺癌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一般来说,大多数女性由于生理屏障的保护机制,虽然感染了HPV,在未来1~2年内没有任何干预措施HPV也会自然消退,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影响。只有一小部分感染的女性HPV会持续存在,最后发展为浸润型宫颈腺癌。大多数早期常见的ADC肿瘤细胞可检测出HPV阳性,但HPV可能在肿瘤晚期消失,HPV阳性患者平均年龄比HPV阴性患者小约6岁,临床分期也相对较早[9]。近年来,针对HPV研发的宫颈癌疫苗在中国广受欢迎,可见宫颈癌的预防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也暗示着宫颈癌患者群体的庞大[10]。针对HPV阳性宫颈腺癌的预防策略已卓有成效,HPV阴性宫颈腺癌仍是一个挑战,可能需要发展新的分子检测技术。
2 分子生物学因素
2.1 表观遗传变异表观遗传学是指由调控机制引起的基因表达的可遗传变化,特定的表观遗传过程包括DNA甲基化、染色质重塑、组蛋白修饰和微小RNA(miRNA)调控[11]。通过分析特定的表观遗传变异,可以绘制出能表达相应病理特征的甲基化图谱和组蛋白修饰图谱,使之成为有力的工具,应用于宫颈癌的筛查、早期诊断和预后标记。基因的表观遗传沉默或去沉默可能产生类似于基因突变的作用结果,使宿主的上皮细胞转化和永生化,与基因突变不同的是,表观遗传变异具有可逆性,这一特性为癌症的表观遗传治疗提供了机会[12]。表观遗传变异具有促进原癌基因或抑制抑癌基因表达的能力,肿瘤抑制基因的表观遗传失调可作为人类疾病和恶性肿瘤诊断和评估预后的标志,例如SFRP基因家族的SFRP5在宫颈腺癌组织中高甲基化,而宫颈鳞癌的大部分基因都没有甲基化[13]。Kang等[14]研究了92例宫颈癌(62例SCC和30例ADC),ADC中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3(tissueinhibitorsofmetalloproteinase 3,TIMP3,53.3%)、死亡相关蛋白激酶(death-related protein kinases,DAPK,46.7%)、钙黏蛋白 1(cadherin 1,CDH1,43.3%)、螺旋酶样转录因子(helicase-like transcription factor,HLTF,43.3%)和细胞分裂后期促进复合物(anaphase promoting complexes,APC,40.0%)均存在较高频率的甲基化,Ras相关区域家族1A(ras association domain family 1A,RASSF1A,33.3%)和凝血酶敏感蛋白1(thrombin sensitive protein 1,THBS1,23.3%)均存在中等频率甲基化;与SCC相比,HLTF、TIMP3、RASSF1A 和 APC 在 ADC 中表现出更高频率的甲基化。
2.2 基因突变基因突变是基因在结构上发生碱基对组成或排列顺序的改变。基因虽然十分稳定,能在细胞分裂时精确地复制,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在ADC中基因突变的靶点很多,故基因致癌突变率较高。
2.2.1 TP53基因Tornesello等[15]研究表明TP53基因DNA结合域在宫颈腺癌的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20%的宫颈癌患者检测到TP53基因突变,宫颈腺癌的突变频率高于宫颈鳞癌,宫颈黏液腺癌的频率最高,达54%。另外,HPV 16阴性的宫颈腺癌患者TP53突变率高于HPV 16阳性患者。
2.2.2 PIK3CA基因Ojesina等[16]通过查阅癌症细胞突变的目录,发现11%的宫颈腺癌患者PIK3CA基因突变。Forbes等[17]通过对宫颈癌基因组序列整个外显子进行排序,发现12.5%的宫颈腺癌患者发生PIK3CA基因突变。Wright等[18]采用基因分型平台对宫颈腺癌样本进行分析,通过正交实验发现25%的宫颈腺癌PIK3CA基因突变。无论采用何种检测方法,均证实PIK3CA基因突变与宫颈腺癌的发生密切相关。
2.2.3 RAS基因HPV阴性宫颈癌细胞中出现RASSF1A启动子高甲基化和转录缺失,而在HPV阳性宫颈癌细胞系中没有此类发现。RASSF1A启动子甲基化在10%的鳞状细胞癌、20%的腺癌和45%的腺鳞癌中均有发现,提示RASSF1A沉默可导致宫颈腺癌的发生。Wright等[18]利用基因分型平台对80例宫颈癌样本进行分析,发现KRAS基因突变只发生在宫颈腺癌中,17.5%宫颈腺癌中可以检测出突变基因,而且,KRAS基因突变的宫颈腺癌患者预后较差。
2.3 细胞凋亡细胞凋亡(细胞程序性死亡)是正常组织和肿瘤组织中细胞转化和发育的基本特征。宫颈肿瘤的发生和进展可能与细胞凋亡的改变、免疫监测的紊乱、细胞生长增加或生长抑制功能丧失(不受调控的增殖)有关。基因表达谱分析发现,细胞周期失调是宫颈癌的主要标志,与宫颈癌患者的不良临床预后有关[19]。宫颈腺癌细胞增殖活跃的特性能激活细胞快速更新,高频率的有丝分裂和细胞凋亡增加了细胞周期失调的发生率,所以宫颈腺癌比宫颈鳞癌进展更快、复发频率更高。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s factor,MIF)作为一种多功能细胞因子,与肿瘤的关系密切。MIF表达与ADC的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等临床病理特征呈正相关。研究证实,MIF在ADC组织中过表达,其机制包括抑制细胞周期蛋白和诱导凋亡蛋白表达。MIF敲除导致ADC细胞周期G1/S阻滞,p21、p27和促凋亡蛋白(Bax、caspase-3、cleaved caspase-3、cleaved-PARP)表达上调,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cyclin-dependent kinase 4,CDK4)、Cyclin D2、Cyclin E2和抗凋亡蛋白[Bcl-2、磷酸化蛋白激酶B(pAkt)、p53]表达下调,说明MIF敲除可抑制ADC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20]。
3 炎症因素
一直以来慢性炎症都被认为是癌症的重要发病原因[21]。肿瘤微环境中的炎性反应是肿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肿瘤形成的重要标志。大多数肿瘤微环境由肿瘤细胞、周围基质、免疫细胞和炎性细胞组成,这些细胞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和黏附分子密切相互作用,促进肿瘤的发生和转移。在这一环境中具有特殊相关性的是促炎性细胞因子,其是慢性炎症反应的重要媒介,对恶性肿瘤发生过程有重要的影响。宫颈癌主要发生在宫颈上皮转换区,该区域是宫颈炎最常发生的区域。宫颈上皮转化区细胞直接或通过全身循环暴露于炎症介质中可增加宫颈癌的风险,肿瘤微环境中的炎性反应涉及大量的生长因子、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脂质介质,特定的炎性因子启动组织再生和修复机制,改变血管的功能,增加血管通透性,促进炎性因子聚集于肿瘤微环境。促炎性细胞因子是慢性炎症的重要介质,对恶性肿瘤的发生有重要作用[22]。Zheng等[23]通过回顾性分析795例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宫颈癌全身炎症评分(cervical cancer systemic inflammation score,CCSIS)的预后价值及其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总生存期(OS)和无病生存期(DFS)的关系,发现炎症与宫颈癌细胞增殖、浸润、转移和预后密切相关。与正常宫颈组织相比,宫颈癌组织中白细胞介素8(IL-8)水平显著升高;与未处理的HeLa细胞相比,外源IL-8处理的HeLa细胞迁移和增殖效率提高,IL-8能够下调HeLa细胞内吞转导蛋白的表达,上调A型IL-8受体(IL-8RA)、B型IL-8受体(IL-8RB)和细胞外信号调节蛋白激酶(ERKs)的表达,提高HeLa细胞的致癌潜能[24]。Sutherland等[25]研究表明,精液中含有多种促炎性细胞因子,包括细胞因子、血管生成因子、前列腺素、蛋白酶、蛋白激酶和转运体,这些因子被认为是肿瘤生长的调节因子。研究人员利用宫颈腺癌细胞系作为研究载体,发现精液可以与宫颈上皮细胞相互作用,激活免疫系统,促进免疫细胞(如树突状细胞、中性粒细胞等)流入,促进免疫耐受,加快肿瘤微环境的形成。在性活跃的女性中,如果缺乏屏障避孕的保护措施,精液直接与宫颈细胞接触,反复作用于宫颈上皮转化区细胞,可导致宫颈炎症,从而促进宫颈腺癌的发生。精液还可以促进基质金属蛋白酶的释放,促进癌症的恶性生物学行为,如浸润、转移、促进炎症介质释放,调节肿瘤微环境。
4 个人因素
外部环境对宫颈腺癌的发生起着重要作用,但个体情况不同,外部环境的耐受性也不同,这些个体异质性主要体现在性行为、激素水平和生育因素的差异。
4.1 性行为性行为因素主要包括初次性交年龄和性伴侣数,这与部分女性性生活开始时宫颈局部发育尚不够成熟、性行为的频繁刺激、创伤和感染有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性观念的转变,女性初次性交的平均年龄不断提前而结婚年龄不断延后,婚前更换性伴侣越来越普遍,因此宫颈腺癌发病呈年轻化趋势。国际宫颈癌流行病学研究协会(ICESCC)从12项流行病学研究中汇集并综合了1 374例浸润性宫颈腺癌女性和26 445例正常女性的数据,发现浸润性宫颈腺癌的发生风险随性伴侣数的增加、初次性交年龄提前而增加[26]。研究表明,首次性交年龄是宫颈腺癌相对较强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首次性交年龄在17岁以下女性患宫颈腺癌的风险比20岁以上女性高2~3倍;拥有超过3个性伴侣的女性患宫颈腺癌的风险是无性伴侣女性的2倍。
4.2 激素水平激素的影响来自内源性激素(肥胖)和外源性激素(口服避孕药)。Smith等[27]研究发现,目前正在使用口服避孕药的女性患宫颈腺癌的风险较从未使用过口服避孕药的女性高3倍;使用口服避孕药超过6年,宫颈腺癌的患病风险增加约2倍,且与使用时间呈正相关;就年龄而言,17岁之前使用避孕药患病风险最高,是非使用者的2倍。肥胖与内源性激素水平呈正相关,使肥胖在激素依赖性肿瘤中的作用引起关注[28]。外周脂肪组织可将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所以肥胖是血清性激素水平升高的标志,尤其是绝经后妇女。近年来肥胖者宫颈腺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Lacey等[29]进行了精细地筛查和统计学分层,尽可能屏蔽混杂因素(任何癌症史、活产数、年龄、性伴侣数、更年期和吸烟),发现肥胖妇女[体质量指数(BMI)>30 kg/m2]患宫颈腺癌的风险是正常女性的2倍,且BMI、腰臀比(WHR)与宫颈腺癌发病风险呈正相关。
4.3 生育因素生育因素主要包括初次生育年龄和总生育次数,与初次性生活年龄早、分娩宫颈创伤等有关。生育次数的增加,特别是经过多次阴道分娩的妇女以及发育尚未成熟的女性宫颈在性交时容易导致多次创伤,在修复过程中新生成的上皮细胞抵抗力弱,对致癌因素HPV感染较敏感,宫颈发生异型增生,最终引起癌变。Green等[30]对180例宫颈腺癌患者和923例无宫颈腺癌女性的研究发现,宫颈腺癌患病风险与初次生育年龄密切相关,初次生育年龄在15~19岁的女性患宫颈腺癌的风险是初次生育年龄在25岁以上女性的2倍;生育女性(≥3次的活产或足月妊娠)比未生育女性患宫颈腺癌风险高。
5 结语
近年来宫颈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并且发病人群趋于年轻化,是病因较为复杂的恶性肿瘤。临床容易忽略诸如初次性交年龄、性伴侣数、生育因素、外源性激素及肥胖等致病因素,从而使宫颈腺癌发病风险增加。明确宫颈腺癌的病因并探寻其预防机制将有利于降低宫颈腺癌的发病率并改善其预后,从而使宫颈腺癌有望成为可以被控制的恶性肿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