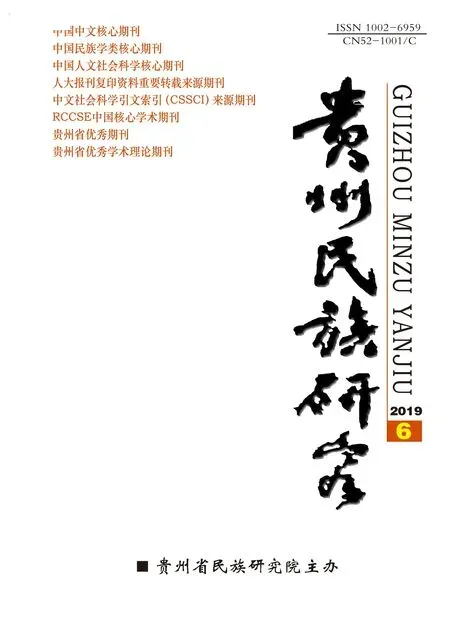凉山彝族社会礼物的契约性交换
2019-03-18吉克曲日
吉克曲日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 610000)
纵观人类学对礼物的讨论,几乎都是顺着莫斯提出的“礼物中有何力量使得受礼者必须回赠礼物?”[1](P3)的问题在展延,莫斯则借用了当地人关于礼物之灵“惑”的解答,但是这一观点很快被互惠原则所取代,尤其是在经过萨林斯等人的发展之后,互惠原则更是作为礼物交换的普遍公理大行其道,但在之后对亚洲等地的礼物考察中,发现互惠并不能解释单向馈赠的不求回报或不能回报的交换类型,因此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均衡互惠或非均衡互惠的弥补方案,也有称之为对称或不对称的互惠。可惜的是这种弥补性的理论不但未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使互惠理论处于一种流于表象描述的境地。因此,韦娜提出礼物“不可让渡”的新观点来批击互惠原则是西方经济化的产物,她也由此重提了莫斯礼物之“灵”的意义所在[2](P11)。其次,“不可让渡”的观点涉及到礼物的“即赠与同时保留”[3](P32)的双重性问题,而对这一双重性的讨论则引出了古德利尔关于社会起源于契约的阐述,因此在他的《礼物之迷》一书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出现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契约性的交换,另一方面是非契约性的传承”,他虽然没有阐明契约在礼物交换中的具体细节,但他把礼物视为一种契约性的交换的理解,为人类学的礼物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凉山彝族社会里,有三类不同的礼物交换形式,其概念、类型、场景、回报等均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礼物交换现象并存,如果按照以往互惠的视角,很容易笼统地将之归为均衡或非均衡的类型,这就掩盖了当地礼物所表现出的不同特性。其次,当地人对礼物概念的理解和多变的交换形式,透露出契约的某些特性,正好作为合适的研究对象进行礼物与契约方面的讨论。
一、礼物的契约性理解
2016年,笔者对凉山美姑县瓦乌村的礼物交换进行调查后,发现除以往学者提到过的“卡巴(ka33ba33)”和“尔普(lɿ33phu33)”外,还有一种没有特定称呼的交换形式,当地人经常用“洛尔”一词来做解释,所以笔者暂且以“洛尔(lo33l ɿ55)”来称呼这类交换。首先从概念入手,因为概念是对某一类事物特征、含义的浓缩,它包含了当地人对该礼物交换的不同方面的理解和概括,因此对礼物契约性的理解离不开对这些概念的剖析。“卡巴”在三种类型的交换中,其交换形式最为复杂、交换的场合也最广,而且在不同场合下的“卡巴”,其理解也有不同的偏向,如过年“卡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奖赏的性质,婚礼“卡巴”体现为一种酬谢,小孩满月“卡巴”则体现为一种慷慨等。在这里重点分析婚礼场合下的“卡巴”礼物,因为这里的“卡巴”直接点明了一种契约关系的成立。
在美姑县有“卡巴洛萨(lo55sa33)”的搭配说法,据当地的曲比毕摩讲:“‘卡巴’广义上定义为辛苦费。在很早以前女方出嫁时不可能自己独自前往男方家,自己的父母又不能送去,只好请女方的舅舅、叔叔等亲戚和其他邻里送到男方家,男方对这些送亲的人表示感谢,分等级分级别给予的辛苦费,就叫做‘卡巴’。而‘洛萨’一般是印章之意,就是指男方给了女方各种‘卡巴’后这种婚姻关系正式成立,‘卡巴洛萨’就代表婚姻的印章确认之意。”从毕摩的解释来看,“洛萨”(印章)其实是对“卡巴”所具有的类似契约性保障的一种描述。因此,在婚礼场合中只要“卡巴”给与并接受了,便标志着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的正式确立。这一印章确认的说法很容易联想到纸制形式的契约或合同也是在最后的签字或盖章后才正式生效。可见,这里的“卡巴”的交换形式是符合契约性质的。
“尔普”理解为“协商的价格”和“交换的价格”[4](P60)两种,从当地人的分类来看“尔普”是规定好的、专用于丧事和赔命金的、共同承担的费用,最大的特征是以强制的手段来维持每个成员的义务,这点尤其是以家支团体中的“尔普”最为明显。在家支“尔普”里,同家支的人才有资格和义务交纳“尔普”,而回报则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同和家支庇护,但如果拒绝交纳“尔普”则有被消除家支身份的危险,这一惩罚意味着在当地将无法立足。可见,“尔普”交换类型的强制性和约束性特征已与现行的契约的法律效应相差无几,而且为了保障成员能履行“尔普”义务,它还以惩罚的手段作为保障,这都是一种契约性的表现。
“洛尔”礼物主要指婚礼场合中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送去的礼金,最大的特征是这类礼物在回礼时不能等于和少于之前所收到的礼金,如果没有按照这一原则回礼,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洛尔”从词源上看,“洛”有“手”之意,而“尔”则有“灵”之意,合起来便是“手的灵”的意思,这和上述“卡巴洛萨”的印章性质极为相近,因为“手的灵”在某种情况下可表达“手的印”之意,从“灵”到“印”都是对“手”独特性标识的描述。这点也可以从当地人的解释中得到理解。吉克毕摩在解释“洛尔”时,作了个很生动的举例,他说:“比方在之前我儿子结婚时你给过我礼钱,我这里就有了你的‘洛尔’,到时候你儿子娶媳妇时我就把‘洛尔’还给你,给的时候数额要多于之前收到的金额。”吉克毕摩在用彝语描述“洛尔”时用到了“立(ȵI33)”,有“坐,存在”之意和“则(ʦe33)”,有“偿还”之意,来分别描述“洛尔”存在于“我”这里和“洛尔”的偿还属性。从这一理解中发现,“洛尔”成了附加在礼物上的一种独特标识,一个人在接受礼物后,便说对方的“洛尔”在我这里,表示还得在将来某个时候进行归还。礼物在赠出的时刻就好像被打上了特殊的标识一样,而通过每个人的独特“洛尔”就能进行一一回报,这好比签署契约的手印,每个人的独特手印对应相应的契约,以明确契约双方的当事人。
通过以上从概念层面的梳理,已分析出“卡巴”“尔普”“洛尔”三类礼物交换都带有契约的某些特性。三者相比下,“尔普”的契约形式与其他两类更为直白,从成员构成来看大致可将“尔普”分为两类,除最常见的家支“尔普”(由亲兄弟、堂兄弟或同一家支成员组成)外,还有新近出现的非家支形式的“尔普”(由同乡或同事或同学等组成),两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赔命金的规定,而后者没有。这些不同团体的“尔普”尽管其成员和义务有一定的区别,但他们的成立都是事先经过共同协商后将义务规定下来的,所以在当地很多团体都有书面形式的“尔普”协议。而反观“卡巴”和“洛尔”,它们的契约性则要隐晦得多,更有趣的是这两类交换关于“章印”和“手印”的说法都涉及到了韦娜的“不可让渡”的观点,尤其是在对“洛尔”的契约的理解中,它更体现为一种不可转让的所有权属。礼物因具有手印标识的“洛尔”而始终使对方知道礼物是谁赠与的,而且这一所有权属并没有在礼物赠与对方后消亡,对方回报时也只是将其归还给赠与方。这样看来,这一不可转让的性质似乎保证了契约交换的顺利实现,这就引出了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关于礼物交换的契约保障问题。
二、礼物的契约保障
韦娜关于“不可让渡”的观点,从契约来看就是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在当地这一不可转让性体现为独特的“手印”或“章印”,它们是契约生效的重要保障。从之前“洛尔”礼物的赠与和回报的过程来看,“洛尔”只是通过礼物的赠与进行了转移,这一过程和莫斯关于“惑”通过礼物的赠与而转移到对方的描述极为相似,这也难怪韦娜会重提莫斯的礼物之“灵”,并认为“莫斯关于毛利人之‘豪’的论述是正确的:‘作为某种充盈于人的生命力,被传递给了人的所有物,并因而赋予物品以不可让渡的价值’”。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发现,韦娜对“惑”的理解与莫斯并不一样,莫斯是将“惑”视为一种回礼的力量,韦娜则揭示了“惑”所赋予的“不可让渡”的属性,这一属性让韦娜看到了礼物“赠与同时又保留”的一面,而这双重属性中的保留在古德利尔看来与一种神圣性有关,他说道:“……交换并不是这些氏族存在下去的唯一条件。还有另一个条件……它一直处在背景之中。这个条件就是每个氏族必须自我维持的一些联系……每个氏族在复制自身身份时所做的种种努力……当那些交换之物品接触到这一点时……就不再是活着的人之间的交换了,而是活着的人与他的神之间的交换了。贸易物品就成了神圣之物。”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保留性就是那不可转让的“自我身份的复制”,它对交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从大量的人与神之间的交换(献祭)上去解读这一神圣性的起源。依照这种理解,在当地有一个关于人神之间礼物交换的案例,也许也能提供更多的细节。
在美姑县当地的彝族家庭里,每年都要举行冬季惯例性的“席尔布” (意为做法事)仪式,在这个仪式里有个很有趣的过程:在仪式开始不久后,主人家的所有成员要先经过一个名为“洛偌(lo33zo55)”的小仪式。在这个小仪式里,毕摩的助手拿来一个盛着清水的碗,让主人家的所有成员,以男左女右的原则,用手指轻轻蘸下碗中的水……(据毕摩讲“洛偌”是表示向神灵等告知今天的作毕仪式有哪几位,因此有人将之理解为“纳员仪式”或“点名仪式”。当仪式进行到一半后,来到最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往往决定整个仪式的成败。)……在场的人屏住了呼吸不敢说话,毕摩一手拿着碗,一手拿着‘神枝’蘸出碗中已‘洛偌’了的水,缓缓从绵羊的头部洒遍全身,毕摩口中不停地念着经文将绵羊献祭给神灵祖先,绵羊开始抖动身子,抖落身上的水,在场的所有人瞬间大喊‘哦……嗡喂!’,紧绷的气氛终于得到舒缓,献给神灵和祖先的绵羊已被接受,预示着主人家将吉祥如意(在当地很多仪式不成功的案例中,即使绵羊全身湿透也不见绵羊抖水,人们就会尽量排除各种原因,如牵羊人的站姿、主客位置等以此再重复,如果始终不见抖水,这就预示着主人家会有不好的事情降临)。
这段内容记录的是当地比较普遍的一个阶段性仪式,当地彝语称为“依次(ʑɿ33ʦɿ55)”,常译为“赎魂”仪式,意为通过绵羊的献祭向祖先神灵赎回灵魂。如果将这个仪式放入礼物交换中去理解,便会发现有趣的象征过程。绵羊是主人家祭祀给祖先神灵的,但是不能用嘴来说这羊是谁的,于是就创造了“洛偌”这一仪式。“洛”意为“手”,“偌”意为“(说、打)中、碰触”之意,“洛偌”便意为“手已碰触过了”,从词源上看,这与之前分析过的“卡巴洛萨”和“洛尔”又如出一辙,可直指“手印”,深层来讲都是对身份的强调。而仪式中的“洛偌”其意义在于将每个人的手印通过“蘸水”而附在水里,再由毕摩将带有手印的水施在绵羊身上,如此,附在水上的手印便转移到了绵羊的身上。整个蘸水过程就是一个有趣的象征,这是把绵羊的归属权仪式化的过程,或者说是将人的所有权赋予绵羊的过程,其结果是用仪式来告诉神灵,这是主人家所有成员的羊。紧接着更有趣的现象出现了,绵羊抖落身上的水,意味着祖先神灵接受了主人家的献祭。绵羊身上的水代表人的印记或所有权属性,但羊把水抖落,意味着主人家的所有权的消除,预示着神接受了绵羊,绵羊成了神灵的物品,与神交换的契约也在抖落水的象征中得以达成。
从整个仪式来看,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抖落手印的一瞬间,这和我们之前讨论的“洛尔”在赠出去时“不可让渡”的手印只是随礼物转移到对方而并未消失的情况有些不同,但从仪式抖落的水来分析的确是一种被消除的表征,因为在“抖洛”水之后也没有别的预示转移的象征出现,手印保障的消除是否意味着契约的无效。按此来分析,似乎支持了古德利尔的观点:“在那些伟大的神与人之间就不会有真正的‘契约’问题……不认为从根本上讲献祭是人与神之间的一种契约。”他的理由是人与神之间的不对等关系造成的,人生来就“欠”神的债是没有任何回报能平衡的,人也不可能通过送礼而改变人神之间的差距。人和神之间的交换的确是不对称的,但如果人与神之间不能形成契约交换,那仪式中蘸水和抖水的象征就显得多此一举,应该有别的可能性,才能解释当地人为何花心思创造这样一种象征。在人与神的整个交换中,神一直是处于“不言语”的沉默状态,一切都是人的自编自导,而对于礼物被神接受与否,人们也选择了以最直观的抖水方式来进行展演,这一切都是一种人为的赋予,这是带有目的性的,所以人们创造这一象征就是为了和神进行一种契约性的交换。如此,抖水使手印消除还有一种可能,便是契约已经完成,这一保障性的手印也就没有存在意义了。回到仪式上,在抖水的那一刻,神便做出了承诺或回报,我们可从绵羊的食用者上得到理解,绵羊通过献祭给羊,成为神灵的羊,而最后享用的却是人,更应该说人享用了神灵的绵羊,可见,在抖水的瞬间神就完成了接受与回赠,因此,人们享受神灵的绵羊受到神灵的祝福,这也可以从其他文化中将食用供过神灵的食物视为一种祝福的现象中得到理解。
从人与神之间的交换中已看到手印作为契约性的保障的重要性,这一手印标示了礼物的归属权问题,而每一个手印代表的是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人自身,似乎人的唯一的身份才是礼物“不可让渡”的真正来源,这点可以从当地人的婚姻交换中找到线索。首先有个前提,便是要将婚姻视为一种交换,才能以此展开讨论。从之前曲比毕摩对“卡巴洛萨”的解释中,可以知道“卡巴”的给与是婚姻成立的重要过程。给与“卡巴”这一风俗还一直延续着,在婚礼当天女方家属送新娘到男方家完成仪式,在仪式结束后便是给与送亲队伍各种“卡巴”,有“舅舅钱”“叔叔钱”“族叔钱”等等,最重要的就是“舅舅钱”的给与,在给与时经常会讨价还价,如对方觉得少,男方家只能不断往上加钱,因此只要将“舅舅钱”谈妥后,其余的“卡巴”就逐次减少500-1000左右进行给与。但如果谈不妥,对方不愿意授受“卡巴”,则婚姻便有取消的可能,这样的情况在当地是有案例的。从表面上看婚姻是以各种“卡巴”和“身价钱”来换取女人的契约交换,也看不出任何类似契约保障的特性,但是当这一婚姻关系破裂(违约)时,隐藏在交换之物(女人)的“不可让渡性”便突现了出来。
在当地的婚姻中,如果女方提出离婚,那就要把男方之前所给的“身份钱”“卡巴”,以及背的过年肉等等一切所有用在女方家的花费全部还回来,往往算的时候会以2到3倍的价进行计算;而如果是男的提出离婚,男方之前给出的所有钱财都不作数,还要用高额的价钱将她风光地送回娘家。在这种婚姻关系中,一旦婚姻破裂,女方便被她的家支要回,男方则被处以高额的赔偿,同时与女方所建立的姻亲关系也到此为止。此外,还有一种更为极端的例子,如妻子与丈夫发生矛盾纠纷而死亡,妻子的家支方便会向男方索要赔命金。这些现象说明在当地彝族社会,一个女性代表的是她背后的家支群体,这一家支身份在婚姻交换中就是一种“不可让渡”的印记或标识。女性在嫁入男方家后是没有名字的(平时生活中被称为某某的媳妇,结构表现为:男方姓氏+媳妇,如吉克“西莫(ɕi33mo21)”、古次“西莫”等),女性的这一身份标识被隐藏了起来,但是在契约被打破后,这一标识便突现了出来,女方的亲属便依据此标识将之收回并惩罚对方的毁约行为。从更广的层面来讲,家支身份在当地是一种归属和自我的确认,它确定了一个人在所处社会的位置,并由此区分出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这种独特性还来源于对同一血亲的强烈认同,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而祖先的来源总是神圣的,在很多的神话故事里,包括当地彝族的神话中,人类的起源都来自神,神赋予了人以灵性,人从神灵处继承或获得了神的(血脉)印记,这是一种神的恩赐,这一神性是一种不可转让的,而人对神灵的崇拜与模仿,使人也给物赋予自己的印记和标识,物便继承了人的某些属性或意义符号,这就是物的人格化过程。而这一物的人格化属性,在礼物的契约性交换中体现为“不可让渡”的属性,因此,才能成为契约交换的重要保障。
三、单向的隐性契约
从之前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在“卡巴”“洛尔”的交换中,“不可让渡”起着一种契约的保障作用,而在契约关系明朗化的“尔普”里,“不可让渡”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资格和条件,在这里人的身份是能否参与“尔普”契约的前提条件。这一不同源于“卡巴”“洛尔”的交换形式的不同,与“尔普”相比要隐晦得多,可以说它们的交换是一种隐性的契约交换,这应该也是礼物最常见的交换形态,因为在普遍的礼物交换里,几乎没有哪类礼物是像“尔普”一样直接说明要交换什么的,大家都是处于一种默契的状态下达成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送对方礼物只是为了增进彼此的友谊,那就意味着接受方的友好关系才是他想要的回报,但如果这个人送礼物的目的只是向对方表示感谢,又或者说送礼物是因为下午的选举会议需要支持等,那契约内容和交换结构也会相应发生改变。因此,只有从契约性视角出发才能真正看到两人所交换的是什么,才能找到礼物真正的交换结构。当然,契约的建立意味着双方都应知道送礼者的动机和意图,但是事实上在实际的礼物交换中,双方不一定都能明了对方的心思,但是契约关系还是能达成,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契约,也正因为此才被称为一种隐性的契约。
礼物交换的单方面性的契约可以通过之前提到的关于献祭绵羊的案例来进行论证。在当地的赎回仪式里,人们通过象征性的手法将人格化的水撒在绵羊身上以示绵羊的归属权,其后通过绵羊抖落身上的水,来表示神灵已接受了礼物,契约已达成。从整个过程到结束,并没有对方的参与,一切都是赠与方自编自导的意向性所为,因为神灵也不可能现身出来与人进行协商。所以整个仪式下来,我们可以发现契约的达成完全不需要有对方出来说一句话,只需保持沉默即可,赠与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便是对方接受礼物,这才是对方唯一需要做的事情,而接受便意味着自己所想的契约的达成,便等待着对方的回报。也正因为这一单方面的隐性契约的原因,礼物的馈赠常会造成三种情况:一种是对方完全理解送礼物的含义或意图;一种是会意错了对方的送礼的意图;还有一种是不明白送礼物者意欲何为。首先分析第一种情形,如果双方都知道送礼的意图,那双方在契约上便是一种统一的交换结构,接受方只要按照契约履行自己的承诺便能完成这一结构的回报。比如当地常见的“卡巴”“洛尔”“尔普”的交换,因其约定俗成的回礼规则,交换双方心里都十分清楚契约内容是什么。但在“卡巴”的某些情景下,它的交换结构也会因对象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以过年“卡巴”为例,通常见到的是晚辈背肉送给亲属长辈获得“卡巴”,交换结构便是:送肉(赠与)———“卡巴” (回报)。但如果对方换成领导或教师后,其结构便可能变成:送肉(赠与)——“卡巴” (附带或利息)——好的关系(回报)。
背肉给教师或领导的,从送礼者的角度来看,学生或阿依想要的真正“卡巴”是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或好处,出于这种心态,对方回报的“卡巴”并不能满足他们送礼的初始,此时,教师给的“作业本”和领导给的“钱”,似乎只是起着利息的作用。但是从回报“卡巴”者的角度来说,他应该完成了回报的偿还,但是为什么之后还是会给别人好处?为什么他会默许这样一种结构的改变,双方是如何达成这种默契的?这只有一种可能,便是在送礼的那一刻,对方便知道他想要交换什么东西,而中间的“卡巴”只是一种随俗的行为,由此两者才能在交换结构上达成一种共识。这是可以论证的:过年送肉一般只在亲属间,他们之间的亲属界线很明显,然后将这一只在亲属间运行的礼物交换放在其他人际圈子,其动机显而易见,也就达成了在接受礼物的那一刻就重塑了这一交换结构。然而双方的期望形成一种误解时,那就会造成结构上的冲突。这就讨论到了第二种情况:误解对方送礼意图,其结果就是认为其中一方没有履行义务。比如两位同学他们之间同时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下级向上级送礼,按正常的人来理解,便认为这个下属一定是有求于领导,通过送礼来达到某一目的,而作为上级,他从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考虑,完全有可能想象对方可能是想需求什么。由此,在领导一方所形成的就是:礼物(赠与)——给与工作上的便利(回报)的契约结构,而对于送礼方的下属如果他只是出于一种同学的情义而送礼,那他所形成的契约结构便是:礼物(赠与)——增进同学情谊(回报)。如此一来,两者在结构上并不一致,就会造成双方的冲突。如果领导按着他所理解的结构给与了对方工作上的便利,那对方可能会觉得自己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人,觉得这是对自己品性的曲解。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地位的悬殊经常会给送礼套上功利性的特点,所以下级向上级送礼很少会有此类误会产生,但在平时的交往中人们之间因为误解对方送礼意图而发生不愉快的事是常有的,其原因在于单方面的契约所造成的结构不对称或冲突。其次,是第三种情况,送礼者没有明确的意图,或者说接受礼物者摸不清对方的意图。这种情况下,常常会给接受礼物的一方带来极大的焦虑和困扰。因此,受礼者会想方设法地从各种可能性上去判定赠送礼物者的意图,如果不太熟的人,便会直接问清送礼者的意图,而如果是较为亲密的,便会用试探性的方式来揣摩对方的心思,原因在于如果当面询问就会使赠送方觉得自己的人品遭受怀疑,觉得别人把自己的好意视为一种功利心的目的,这很容易给对方造成情感伤害。因此人们为了避免这类情感伤害一般不会明言而只能意会,这也是造成人们在礼物交换中形成这种单方面契约的原因所在。可见,礼物不仅传递着自己的意图,还常受双方主观性意愿左右。
礼物单方面的隐性契约突显的是一种人的主观性,这一主观性还与交换场合和人的先天权衡有关。一个人给的礼物可以是“卡巴”,可以是“洛尔”,也可以是“尔普”,它因场合不同而变换其交换结构,而且同一类型的礼物只能在同一场景里进行回报。其次,在实现生活中,我们往往会发现礼物的给与不一定都能使对方产生理亏心理,有时反而让对方感到不愉快。在接受方的眼里,如果一件礼物的价值低于对方所要交换的东西,那他是不会承认这一契约关系的,比如一个人送了两瓶酒,想让对方帮他搞定工作上的某件事情,但是在对方眼里他那两瓶酒根本不值帮忙的价,因此对方要么就是拒绝,要么就是不进行回报。从这种现象来看,在契约结构成立之前,人似乎有一种先天的权衡现象,这也是礼物交换中主观性的一个体现,一个礼物是造成亏欠,还是不快,这取决于对方对所送礼物价值的衡量。因此,人们在接受礼物时,心里便有了一种价值判断,而这一价值判断也决定了契约是否会被对方履行或接受的问题。可见,契约是一种灵活性的,它因人的不同交换诉求而变得不同,也可以因不同的赠与人和不同的场合进行调整。但是我们也可看到礼物的交换都是在二元的结构之上进行的,深藏在人类意识里的二元结构观随时都在左右着事物的形成,包括契约也是一种二元观的驱使,只不过在礼物交换的层面,我们应该明白二元结构形成的前提是什么,不能直接拿出一个二元结构来对礼物交换进行套用,而是应该先考虑二元交换结构之上的契约关系,也就是要弄清双方真正交换的是什么东西,只有将这一关系弄清楚后,才能得到真正的二元交换结构,才能真正的理解礼物的交换意义。因此,可以说契约在交换结构上,或者说契约先于交换结构,契约一旦达成,其交换结构便会瞬间形成,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礼物那变动不居的交换结构。
四、结语
通过梳理,发现当地“卡巴”“尔普”“洛尔”类型的礼物十分符合契约性交换的描述,尤其是对“洛尔”的“手印”之意的讨论,它是契约得以生效的印章,它在礼物交换中的转移过程与莫斯提到的礼物之灵“惑”相似、在回礼方面则与韦娜的“不可让渡”的特性一致。由此,便可明白礼物之“灵”的真正意图并不是指迫使回礼的力量,而是指礼物中“不可让渡”性质的神圣性。从当地献祭绵羊和婚姻交换的案例中,分析出礼物的“不可让渡”来源于人对自我独一无二身份的复制或人格化的赋予,而这一身份的神圣则体现为一种对神的血脉传承,这也正好应合了古德利尔关于保留之物来源于神圣性的观点。其次,从当地因不同场合、不同的主观意愿对交换结构的影响来看,通常的礼物交换是建立在一种单方面的隐性契约之上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突显参与礼物交换双方的主观性意愿,才能看到礼物交换的真正结构。
以契约的视角来理解礼物交换,是有着一个前提的:一切礼物馈赠都是有动机的。因为作为契约性的双方,要有明显的意图才能形成契约,这也就否认了存在单方面馈赠的礼物类型。尽管布劳不赞同将只出于良心而不指望得到任何形式的感激的馈赠纳入交换的范畴里,但他自己也认为“可以被看成是用他的钱来换取超我的内在赞同”[5](P156)。其实,不管回报是不是内在的赞同,只要存在一种主观性的判定因果,它就形成了一种契约结构,而且这一契约会因主观的判定而改变其结构。因此在分析不求回报或无法回报的经典案例中,总能找到一种契约关系:印度的“檀施”和日本的“恩”,这在契约看来印度的“檀施”礼形成的并不是表面上的高等级向低等级的交换,其真正的结构是送礼者换取声望的契约关系,这类似于布劳对“捐赠是为了换取社会赞同”的分析。而日本的“恩”并不是无法回报而应是未完成的契约,从当地“卡巴”“尔普”“洛尔”须按同一场合进行回报的原则看,对“恩”的回报需依赖于合适的契机(受恩时相同或相等的场景出现),否则受恩者的持续性的感恩之情和忠义只能作为回报时间间隔的利息而存在,并且是否完成了等价的回报与人的价值判定有关。
综上可见,如延用以往对称或不对称的互惠来理解这类礼物交换,则会遗漏礼物交换中的诸多细节。虽然互惠是社会交换的普遍原则,但在礼物交换里却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互惠的理论偏于一种理性的计算,而礼物所附带的情感、义务、行为等是无法计算的,这使礼物多样性的交换趋于单一化。二是互惠只是回礼原则,并不等同于回礼原因。原则只是一种规则描述,而且它是对礼物交换双方的结果进行利益得失计算后的描述,始终不能作为礼物之迷的解答。反观契约性的描述则更符合礼物交换中那变动不居的人观因素。据此,似乎不应说礼物的交换产生了名声、地位、情感等,而应说双方通过契约性的约定来交换名声、地位和情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