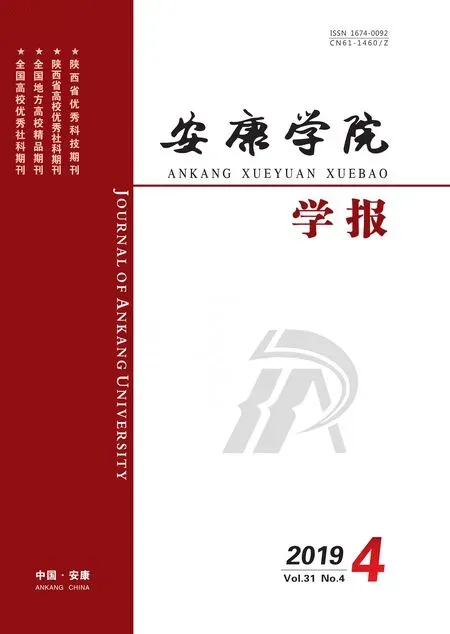移民语境下的翻译
——《翻译与移民》述评
2019-03-15朱斌
朱 斌
(四川外国语大学 商务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在西方,移民(migration)向来是个热点话题。在公共领域,它是政客政治选举、政治辩论绕不开的议题;在日常的新闻报道和交流中,由它而产生的语言政策、难民政策、庇护政策等相关讨论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学术界,学者们对移民的研究逐渐深化,注重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如Russell King和Nancy Wood[1]研究了移民和媒介的多界面相互影响;Collins et al.[2]和Canagarajah[3]探讨了移民与语言政策规划、二语习得之间的关联。近年来,翻译和移民,与其他话题“嫁接”的相关议题也走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比如,Polezzi[4-5]认为学界过度关注翻译与旅行的研究,忽略了与空间和语言变动相关的社会、再现现象的复杂性,如移民现象;Paul F.Bandia[6]探讨了后殖民话语实践中与移民、离散和文化迁徙相关的翻译现象。全球化背景下,持续增加的移民和翻译的多界面互动是我们不可忽视的现象。2017年,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翻译研究主任莫伊拉·英格拉里(Moira Inghilleri)的专著《翻译与移民》 (Translation and Mi-gration)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属于“翻译与口译研究新视野”(The New Perspectives in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丛书。该丛书收录了学界知名学者就新兴和流行话题展开研究的相关著作,旨在解决口译和笔译研究领域不断变化的需求。《翻译与移民》研究路径多元,多学科融合,从第一手资料出发,论证充分合理,是翻译、文化、社会学和移民等诸多领域研究者不可多得的力作。
一、《翻译与移民》的内容简介
《翻译与移民》一书除插图、目录、致谢和索引外,共有六个章节,分别是移民、流动性和文化(Migration,mobility,and culture)、好客的多元意义(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hospitality)、翻译与劳工移民(Translation and labor migrants)、翻译景观(Translating the landscape)、从上到下的跨国主义符号 (Signs of transnationalism from above and below)、构建和质疑年轻移民的身份(Constructing and contesting young migrant identities)。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历史、社会、哲学和地理条件等因素对移民和不同形式的多元文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和碰撞,这一切与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密不可分。首先,作者从人类学和后殖民视角入手,结合丰富的史料,重点阐释了移民(migration)、流动性 (mobility)、景观 (landscape)、移居(departures)、永久迁徙(permanent displacement)等重要概念。其次,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翻译和移民之间的交叉和互动进行阐释:一是流动(fluidity)、杂合(hybridity)、身份(identity);二是重构“我们”(us)和“他们”(them)(主客关系);三是翻译和好客(hospitality)[7]18-31。最后,作者指出人员的流动迁徙必然涉及一个人在新地方翻译和被翻译的经历。“移民绝不是某个单一方向的简单再现,总是涉及大量散布、挪用、吸收、抵抗和持久的矛盾。翻译作为一种交互影响的形式,在重要的话语空间发挥作用,在不同的认知模式中得以协商、挑战和重构。”[7]34总之,本章侧重主题引入,为后面章节的展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知识背景和素材。
第二章围绕移民过程和移民在多元文化社会的生活境况,从语言层面探讨好客行为的存在和缺失,以及翻译在公共和政治层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作者通过分析移民作家的多部作品及移民在埃利斯岛(Ellis Island)和天使岛(Angle Island)的生活状况后指出,好客行为是有条件的,译员在两个不同世界和新兴的政治现实面前将会遭受两难处境——道德“个人”和伦理“专业人士”的紧张关系,而这样的矛盾现实在过去和当下的移民社会中都不可避免。在有潜在的不好客的交际环境中,一些人的权利受到限制,或者需要协商,这时翻译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促进语言的好客和包容的交际至关重要[7]45。作者还指出,翻译作为一种伦理行为,绝不是移民和全球化语境下才有的产物,它自古便有之。正如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会受特定的政治、社会和伦理语境影响,译者和翻译行为也处于强大势力(有时是危险势力)的十字路口。从这个意义上讲,译或不译并不是可译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或政治问题[7]65。
第三章结合“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的概念,从移民的原因以及全球化与翻译的关系入手,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移民人群在对象国或地区从事工作时,翻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翻译缺失对其产生的影响。作者阐述了四类劳工的不同遭遇,国外的合同工、男性合同工、被贩卖的劳工及国内移民(中国工厂的女性工人)。劳工因自主翻译能力和被翻译能力的不足或“缺位”,往往遭受雇工剥削及一些法律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误解。作者在本章中介绍了国内外的一些权利支持者通过成立专门组织、建立网站等方式试图为移民工作者提供翻译服务的例子,并对性工作者的移民进行了关注。她以泰国的性工作者为例,讨论了这些移民群体因为合格翻译者的缺位,有意或无意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人权未得到应有的保障。
第四章借用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提出的“给出”(give) 和“流露”(given off)概念,探究了移民适应新的景观和帮助塑造新的景观的方式。以爱尔兰劳工和中国劳工在英美两国修建铁路为例,作者通过解读关于他们的政治漫画、照片、宗教和其他文化符号后指出,这些符号具有社会功能,关涉互动秩序(interaction order)的再建和移民与多元文化的公共想象[7]108-109。作者发现,移民个人或群体为宗主国创造景观的贡献未受到应有的承认甚至被忽略,这与宗主国的政治、文化密不可分。作者通过事例从人类学的角度介绍了移民个体在新的地方如何定位自身以及如何创造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从文化地理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分别对景观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第五章聚焦公共场所视觉符号,探讨了这些符号的社会和互动功能,以及它们对预测和判断多语社区中个体身份的解释力。作者借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语言学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概念,讨论了既定景观中不同语言社区的存在和角色。接着研究了纽约和洛杉矶韩国城(Koreantown)的公共标识的呈现方式及背后潜藏的社会学意义。在作者看来,商店等公共场所前“被翻译的标示牌、广告牌和通告以某一特定的语言形式出现,可以将‘外来者’(outsider)身份从一个群体转换为另一群体,强调一个社区中目标群体的‘另一性’(otherness),从而标记那个地方的最新居民”[7]149。作者认为,实际上,像纽约和韩国城这样的城市语言景观符号在流动人口和社会物理世界之间创造了一个动态的空间。
第六章重点论述了多元文化社区中内外群体(ingroup-outgroup)的多元化和社会凝聚力,以及年轻移民者的身份的创造、协商和质疑等相关议题。首先,作者重新审视了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的研究者关于年轻移民群体的四个民族志研究,“旨在突出当代年轻移民在特定地理、机构和社会环境中协调他们的身份时个人层面所呈现的‘跨国性’和‘世界性’特性,以及引起对不同形式的翻译的关注”[7]181。其次,作者考察了韩裔美国移民在同一种族内部自我归属(self-ascription)和他者强加(other-imposition)之间的关系。最后,作者指出不同形式的翻译在不同的社会和地理环境下都对文化意义和历史关系的改变发挥了核心作用,且在移民身份构建和文化融合过程中继续发挥中心作用。
二、《翻译与移民》的主要特点
从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了“文化转向”以来,翻译学科与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等多种范式结合,繁荣了当下的翻译研究,并拓展了研究的领域,使其呈现出开放性、多元化的特点。《翻译与移民》结合多种理论范式,探讨了移民语境下翻译的不同形态,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
(一)研究路径多元
1959年,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翻译活动分为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人们讨论翻译时,通常指的是第一种语际翻译,后两种因其特殊性很少进入翻译研究者的视野,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翻译与移民》一书中,作者所讨论的翻译形态基本涵盖了上述三种情况。她视翻译为一种社会活动,不仅考察了严格意义上的语际翻译,也将阻碍或影响交流的各种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如第二章中,作者阐述翻译对于来自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移民在同一城市空间汇聚时的重要作用,讨论了翻译的“在场”或“缺席”对人们在移民城市空间生活的影响。此时,研究对象是一种存在状态,即移民是否具有自主翻译能力和被翻译的能力。一方面,翻译可以帮助移民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更加自如的生活;另一方面,“误译”或“翻译缺位”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即也许是移民个人形象的毁坏、财产的损失,甚至是生命的危及。符际翻译常常出现在人们经常打交道的许多不同文本和媒介中。如第四和第五章对标牌、广告、标识语等在公共领域的呈现方式和解读就涉及符际翻译。语内翻译则贯穿于各章,如作者在第二章中讨论了在广州工作的外来移民(务工人员)因普通话、方言、广东话之间的相互混杂而导致语内翻译不畅或缺失的相关例子。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是翻译研究应关注或被忽略的问题,本书将这两种翻译形态纳入研究视域,拓展了我们翻译研究的思想疆界,为翻译讨论提供了多元的研究路径。
(二)多学科交融
不同学科的交融与邂逅既是人文学科发展的必然之路,也是不易之路。《翻译与移民》借用社会学、人类学、社会语言学、后殖民理论的相关成果将翻译研究和移民研究有机融合在一起。文化翻译思想就是很好的体现。在人类学中,它是用于描述社会人类学主要任务的代名词。其中的核心概念“翻译”并不是指语言层面的文化翻译,而是指“读者阅读另外一种生活方式”[8]。在后殖民研究中,文化翻译“被当作一个隐喻来指向后殖民语境中宗主国和前殖民地的文学文化冲突和矛盾”[9]。换言之,文化翻译超越了以文本为载体的翻译形式。它关注的是一般的文化过程,而不是有限的语言产品,就是“没有译本的翻译”(translation without translations)[10]。《翻译与移民》一书中的六个章节关联度看似不大,但作者尝试将各章节讨论的话题与文化翻译的核心思想紧密联系。移民从源语语言和文化环境移动到目标语言和文化环境,翻译由此产生。“一是身体层面的位移或者移动;二是象征意义层面的一种讲述、书写和阐释世界的方式向另一种讲述、书写和阐释世界的方式的转换。”[11]作者在文中对翻译做了如下定义:“说翻译,我并不是指阐释它们的文化或语言学意义的任务,虽然这也是此过程的一部分,我所指的是通过结合智力的和本能的行为理解‘给出’符号和‘流露’符号之间动态关系的更复杂任务,这个任务激发了不同个体或群体在某一特定环境内自身的反应。”[7]155翻译工作主要功能并不是表达信息,而是在一个仍不熟悉的空间寻找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主要是关于“将自己翻译成地方”(translating oneself into place)[7]164。显然,文中所指的翻译是指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翻译。“文化翻译”的宽泛概念是当今多角度研究的结果,是跨文化研究范式的体现,可以用来解决后现代社会学、后殖民、移民、文化杂合等多领域的相关问题。不同的视角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和阐释依据。因此,翻译研究应该跳出传播的语文学研究模式,借鉴学科之外的研究范式,将翻译纳入新的语境,必然会对原有领域产生新的启示,进而获得新的特点。
(三)从第一手资料出发
有学者曾评价,中国许多翻译研究者缺乏啃硬骨头的功夫,对二三手资料过度依赖,“同时颇爱引用名人评语,很少再加考证或思考”[12]。然而,通读《翻译与移民》,我们可以发现该著作的另外两大特点,一是一手资料充分占有。翻译研究视野宏大,所涉资料繁复,要获取众多原始资料并不容易,但作者从海量的文学作品、民族志研究、图像和历史史料中梳理了众多的一手资料,用于论点的支撑和阐述。从空间跨度来看,包括中国、英国、美国、印度和非洲等国,几乎遍及世界;从时间跨度来看,包括18世纪的早期移民到21世纪的现代移民现象。《翻译与移民》正文中附有图片30张,包括作者通过田野调查方式实地拍摄的图片,以及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申请扫描的图片。这些珍贵的图片作用不可小觑,可以引导读者更清楚直观地理解作者的表达意图。二是言说有理有据,论证充分。文中作注多达92条,努力做到每一条信息给出后,用与它相关的情况加以必要说明,做到既见树木,也见森林;参考文献达200多条,尽量用详实的材料“说话”。总的来讲,各种丰富可信的史料和严谨的作注方式为相关学者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和线索。
三、结语
当然,本书不免有一些瑕疵,如章节缺乏开头的引言和结尾的总结性话语,可能会给读者的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又如72页的13 billion dollars误写成13 million dollars等。但瑕不掩瑜,《翻译与移民》一书博采百家之长,广泛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系统地将跨学科的研究范式融为一体,讨论了当下跟移民相关的热点问题。其视角新颖、论证充分、研究范式创新,是与其他学科深度融合的又一力作,可以为翻译、文化、人类学和移民等诸多领域研究者提供研究路径上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