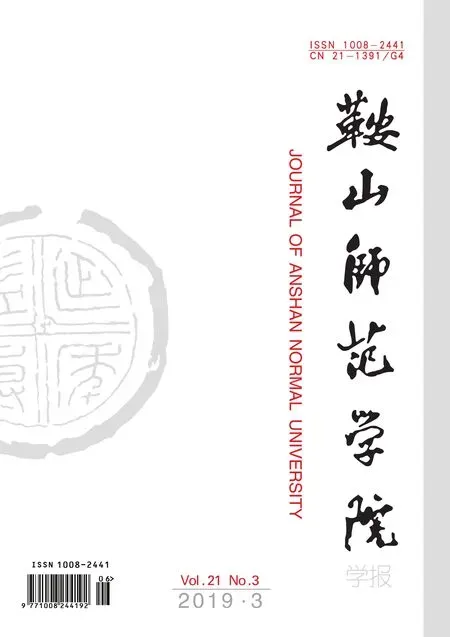《接骨师之女》中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2019-03-15程宇飞
程宇飞 邱 畅
(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殖民主义对当地国家和人民的影响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与层面,旧殖民主义更多体现的是对政治、经济上的影响,而后殖民主义则更多表现于前宗主国对前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后殖民主义对前殖民地文化的影响程度,研究从后殖民女性的视角,以《接骨师之女》为例,揭示华裔女性受到双重压迫的窘境,从而更清晰地呈现出后殖民女性主义对文化的影响状态。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文化影响
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批判色彩的文学理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讨论前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现如今,后殖民主义已经成为西方重要的批判理论之一。论及后殖民主义,此三人影响尤甚。其一是当代后殖民主义之父弗朗茨·法农。他于1952年发表了《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主要探讨了后殖民主义的一些关键性概念;在1961年的《大地上的受苦者》一书中,他认为要让被殖民的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建立自己的身份从而认清本民族过去历史。
其二是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深深影响着后殖民主义,“文化领导权”即“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指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支配,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文化领导权渗透到大众的意识中,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们的心理,并产生深远的影响。资产阶级通过文化领导权取得对人民群众教育上的文化霸权,使人人都得服从集体。正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通过风俗的衍化、思想和行为方式以及道德风尚等产生客观效果[1]”。这是一种有关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并通过大众认可进行统治,它强调了文化上的霸权。
其三是代表人物福柯,他着重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的学说研究,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福柯认为:“权力是透过话语发挥作用的东西,话语不仅仅是一套功能符号和语言表征,更重要的是在话语的背后存在着一套权力关系[2]。”在《权力的眼睛》一书中,福柯认为:“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3]。”由此可见,在整个文化话语体系中,宗主国的文化,即西方殖民国家的文化起着支配作用。
从上述三个代表人物的观点中可以看出,被殖民地的人民经历了来自宗主国的文化侵袭,他们的文化身份产生了变化,一半是自己的国家文化,一半是宗主国的文化。[4]当国家独立后,被殖民的人民已经受到了双重文化的洗礼,他们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继而开始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与下一代未被殖民的人们交往时,文化混乱与冲突就此产生。
女性主义则起源于20 世纪 60 年代欧美妇女解放运动理论,不管是以激烈的行为来抗争,还是以温和的方式来讨论,它都是建立在女性受到不平等对待的基础上的。女性主义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关心女性群体,确立女性身份地位,从而实现女性解放,并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女性主义强调削弱男性主导地位,解构父权等级模式,解放女性。许多思想家和文学家投身于这场反对父权压迫的斗争,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她的作品《第二性》充分讨论了从古代一直到现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处境情况,探讨了性别差异问题。
后殖民女性主义是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后殖民女性主义结合了对女性主义的思考以及对殖民理论的批判,它要挑战的是西方话语下对第三世界女性形象的歪曲[5]。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看女性受压迫不仅是因为她们是被殖民地人民,还因为她们是女性。这与主流文化中主要关注性别歧视的女性不同,被殖民地女性面临着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
二、父权文化的压迫
虽然现代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劣势地位,长期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与压迫。在《接骨师之女》中,主要人物是包括露丝在内的女性,她的母亲茹灵,她的阿姨高灵和她的祖母宝姨,围绕这些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不可避免地要从性别的角度来做研究。在古代,人们总是把男人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女人,称女人是“祸水”,如商纣亡国是因为妲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是因为褒姒;唐玄宗遭遇安史之乱是因为杨贵妃等,这就无形中把女人当作政治的牺牲品,成为人们谴责的对象。另外,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被要求“三从”:在婚前服从她的父亲,婚后是丈夫,丈夫死后是儿子。
无独有偶,在古代西方,女人的地位也一样不高。根据圣经,女人属于男人。夏娃是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来的,女人来自男人,又是因为夏娃被蛇诱惑偷吃了禁果,所以亚当和夏娃才被逐出伊甸园。在古罗马社会,父亲是家中的主宰,并且有权拥有决定他刚出生小孩的生死。如果新生婴儿身体上有缺陷或者是女孩数量已经足够,孩子就会被遗弃。
综上所述,在古代,国内外妇女的地位都相当低。目前,虽然妇女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但她们仍然是弱势群体,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如女子读书无用论的盛行、女婴被弃现象屡见不鲜、对女司机固有的不良印象以及女性面临就业方面的歧视问题……正如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和美国女权运动先驱夏洛特·泊金斯·吉尔曼笔下疯女人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女作家所处的困境和对现实的反叛,女性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没有任何权力,只能选择依附男性。[6]
斯皮瓦克是当今著名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家,她主要对第三世界妇女进行描写,她们受到双重权力话语的压制——殖民主义和男权主义。她的作品《副领事》中的东方女性不仅受到男权的压迫,而且一直被西方白人女性忽视。[7]根据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在那些被白人文化和性别歧视主导的社会里,第三世界的女性位于从属地位,为次等公民,通常处于“失语”的状态。[8]她们的真正价值从来没有得到承认。因此,后殖民主义女权者坚持认为,是时候让这些女性为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斗争了。她们是被忽视的群体,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取平等,所以,当她们面对压迫时,她们不愿意保持沉默。
后殖民主义对被殖民地人民的影响在《接骨师之女》中首先体现在父权文化的压迫上。后殖民主义强调话语权的问题,而女性长期处于话语权被压制的境地。主人公露丝面对男友亚特时常常妥协和退让,无论是由谁抽出时间请工人修理水箱,还是做饭要迎合谁的口味,露丝都要委屈自己。“话语”等同于“权力”,在父权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中,女性的发言权是较小的。露丝的外婆宝姨自杀被救活后,她的身份地位一落千丈,变成了女儿的保姆。原因在于她失去了丈夫,就失去了发言权,她没有办法帮自己争取应有的地位,加之本身是沉默的人,她失去了做主的权利。
在露丝的记忆中,她的母亲茹灵曾经抱怨她为什么是女孩而不是一个男孩,就因为自己是个女孩,所以才没有得到祖父母的遗产,而大多数的遗产都给了叔叔艾德蒙,因为他有一个儿子。茹灵说到“只给我这么一点点,就因为你不是一个男孩。”在露丝还小的时候,她把男人的尿液看作是标记,这体现了父权对女性的压迫从童年就已经出现端倪。露丝的表哥比利常常欺负露丝,十足的霸道嚣张。在上卫生教育课时,教师找来帮忙的视听部男孩在看到女生对性教育流露出的羞涩后,大模大样地出了教室,得意扬扬,活像是看到了全体女生的裸体。在和白人丈夫亚特讨论修理热水箱时,亚特强调自己有多忙,忽视了露丝也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最终露丝还要尽力心平气和,亚特还说露丝把每件事搞复杂,从中可以看出露丝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亚特当着孩子的面说露丝总是无事生非,她的孩子们也看不起这个华裔继母。当露丝和好友温迪在一起讨论时,总是大倒苦水——社会对女性越来越不公平了。亚特在与露丝刚开始交往时就提出不想结婚这个念头。当露丝因为母亲生病不能与亚特一起去夏威夷度假时,亚特问她“你打算怎么办”而不是“我们该怎么办”。露丝还发现把亚特和她当作收信人的邮件很少,大部分的修理账单都是露丝签收,因为亚特始终没有把露丝当作一家人。
母亲茹灵的笔记记叙了亲生母亲宝姨和自己颠沛流离的故事。宝姨,茹灵的亲生母亲,在婚礼当天,她的父亲和她的丈夫虎森双双被恶人害死,她选择了吞下一碗热墨水自杀,但是后来为了腹中的孩子,宝姨只得做孩子的保姆,才能陪伴孩子长大,因为没有了丈夫她根本无法在刘家立足。宝姨的父亲是一名接骨师,需要寻找龙骨为病人治病,在周口店寻找龙骨时,如果是女人找到的,也得说是男人找到的,因为女人找的不值钱。宝姨曾说:“父亲竟把我宠坏了,任由我像男孩子一样为所欲为,叫我识字读书,勇于发问。”那时老人们都说纵容女儿是不好的行为,让宝姨的父亲给她裹脚。从宝姨的经历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父权文化对女性的荼毒与迫害。除了宝姨的悲惨经历,茹灵也深受父权文化的压迫。茹灵在儿时发问裹脚的事情时,茹灵的养母和婶子们都皱起了眉头,认为茹灵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下谈女人的私事。后来,茹灵的养父和叔叔的油墨生意失败了,所有人都认为是宝姨的错,茹灵是应该承担责任的,所以茹灵被养母遗弃,送往育婴堂。接受这个决定是茹灵唯一的选择,她在父权社会中没有任何决定权,她应该做的是服从父权权威的命令。茹灵第一任丈夫的父亲潘教师对茹灵说过,她要是托生成个男孩,准能成为大儒。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女子即使再富有学识,也不可能像男人一样出人头地。茹灵的妹妹高灵所嫁之人张福男,抽大烟赌钱背债,但在高灵面前却颐指气使。育婴堂的于修女的姐夫拿钱买了鸦片却不给她姐姐治病,导致姐姐病死,她恨透了那个恶棍,当高灵辗转来到育婴堂后,二人成为好朋友,她们一起咒骂男人,说他们品行连蛆都不如。当高灵先一步去了美国后,茹灵去了香港当英国人帕蒂小姐家的帮佣,帕蒂小姐也说过她家的那只鹦鹉跟男人一样坏,帕蒂小姐的母亲英娜夫人一听有客人就一定要坐得笔直,保持淑女风范。由此可见,无论在何种文化下,女性都要约束自己,不仅中国女性受到父权的压迫,西方女性也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
三、异质文化的压迫
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存在已久。自从1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北美大陆定居下来后,他们相信他们的国家是最好的,他们的文化优于任何其他文化,其他种族是劣等种族,这种严重的排他性导致了现在美国社会对非裔、拉丁美裔和亚裔的歧视。
白人文化对华裔歧视由来已久。第一批到达美国的华人是在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期间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在淘金热时期,中国人被白人排斥,他们只能开采价值更低的矿藏。19世纪60年代初,华人同胞投入加州铁路的开建工程。然而,他们的美国梦太难实现了,他们只能获得最低的工资。而美国华裔女性的情况更糟,她们中的许多人只能找到保姆工作。一些偏见问题随之而来,1882年的《排华法案》出台后,中国劳工被禁止来到美国。《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特定族裔为目标的歧视性法案,使华人成为不能向美国自由移民的唯一民族群体。[9]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中美两国的联盟,美国开始允许中国人移民美国,可以加入美国国籍。由于种种原因,尽管许多中国移民已经在美国定居,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已经接受美国文化的教育,并试图融入其中,但他们仍有隔阂和受到歧视的感觉。其根源在于白人文化优越是根植于美国人心中的,而华裔文化被认为是不合群的。美国主流文化认为他们的文化是文明先进的,而其他国家的文化包括东方文化和黑人文化是野蛮的、落后的。
后殖民主义对被殖民地人民的影响在《接骨师之女》中还体现在异质文化的压迫上。
后殖民主义强调文化领导权,前宗主国或者国力更强的国家的文化是处于凌驾地位的,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迫。主人公露丝在上幼儿园时期就被排挤,到现在工作了也被人轻视,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华裔的身份。甚至在家庭聚会上,作为露丝亲属的美国白人也对中国的食物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厌恶之情。男友亚特的两个女儿都瞧不起露丝这个华裔继母的中国式习惯和饮食风格,对露丝母亲茹灵更没有什么尊重可言。称中文为“黑话”的行为深刻映射出美国华裔和美国白人之间有一道深深的文化沟壑,美国白人文化是站在俯视的角度看待中国文化的。
在《接骨师之女》中,露丝的经历最能体现出白人文化对华裔女性的压迫。主人公露丝的母亲茹灵是20世纪40年代的华裔移民,因为中美文化的差异,这对母女之间经常爆发冲突。茹灵的丈夫在女儿露丝只有两岁的时候因车祸去世,由于生活的残酷,她必须努力工作。自从露丝在幼儿园起,就因为中国移民身份被同学排斥无法融入群体,后来又搬过八次家。除此之外,这对母女在个人隐私上也产生了争执。从中国父母的角度来看,子女不应该对父母保守秘密,父母有权利了解孩子的隐私;而美国人要保护他们的隐私,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个人的隐私权,父母也不例外。对于茹灵来说,翻看女儿的日记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露丝知道母亲擅自读了她的日记后,她十分生气。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茹灵无法得到女儿的理解。
露丝,一个典型的美国华裔女性,出生在美国,接受了美国的教育,却始终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与她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男友不愿意和他结婚,他的前女友生下的两个女儿说露丝爱吃的腌萝卜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在冰箱里放的屁”。作为代笔作家,“露丝·杨”这个名字以小号字体印在主要作者的后面,或者直接不出现。在庆功宴上,露丝只能坐在后面默默地看着别人获得祝贺。她的经纪人吉蒂恩这么评价露丝:“客户傻话连篇你也乖乖听着,不管他们如何自大,怎样丝毫不把你放在眼里,你都会照单全收”。在带母亲去看医生的医院里,露丝发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谢顶白种人,他的尴尬是因为他的一个类似华裔的姓氏而被分到了这个专门为华裔看病的医院。露丝的继女菲雅和多丽称中文为“黑话”,把对茹灵“外婆”的称呼,只当作是外号。除了菲雅和多丽,周围白人比如露丝男友亚特的父母卡门夫妇也不是非常欢迎露丝。卡门夫妇把家传的银器、瓷器和圣经都给了亚特的前妻米莉安。在中秋节聚餐上,亚特、米莉安和露丝的好朋友温迪坐在一张桌子那边,温迪还调侃道:“我们这里是白人专区还是怎么的”;上菜后,白人亲友对于中国式的菜品都露出了怪异的表情,多丽还称海蜇为虫子,亚特直接把一整盘海蜇都递给露丝的行为更让露丝头疼。在生活中,露丝对他男朋友宽容忍让,即使她有工作,她在家庭中也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她要做家务,要自己付账单。她把时间花在家庭的事情上,但没有人对她心存感激。总之,因为非白人的身份,露丝不管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处于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状态。
四、结语
《接骨师之女》被认为是作者谭恩美的自传,灵感来自她的母亲和祖母的故事。谭恩美的小说以母女关系为主线,往往带有文化冲突色彩。在这部小说中,她增加了许多自己的经历。《接骨师之女》成功地说明了种族、性别和文化在影响人物性格方面的重要性,表现了她对华裔女性身份困境的关注。主人公露丝作为在美国出生的女性,受到了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主流白人文化的双重教育,同时也长期受到父权文化和白人社会的极大压制。在《接骨师之女》中,谭恩美成功地刻画了两对母女的智慧和勇敢,虽然她们一度受到压迫,囿于困境,但是她们从不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反抗歧视,不做命运的沉默者。谭恩美以母女关系为切入点,向读者们展现了华裔女性面临的父权文化、异质文化的压迫与被边缘化的现状,以及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揭示了美国社会中华裔女性生活的艰辛,应和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