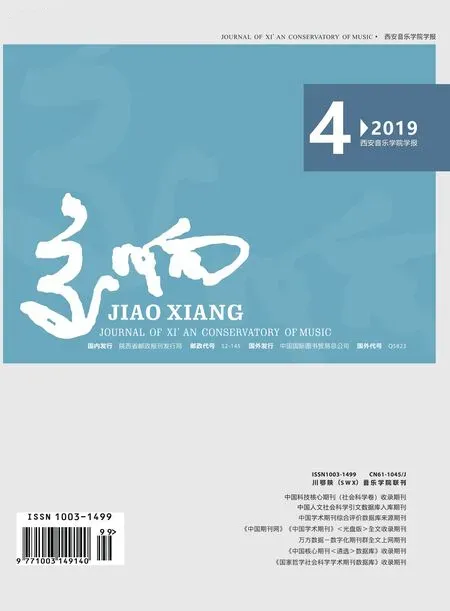《党的女儿》“桂英”形象塑造与演出体会
2019-03-14
(西安音乐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党的女儿》是1991年由阎肃、王俭等编剧,王祖皆、张卓娅、印青等作曲,彭丽媛、孙丽英等主演的一部革命题材的大型民族歌剧。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师生将这部歌剧重新搬上了舞台,20多年后经典民族歌剧辉煌再现,很多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师生以其雄厚的专业实力,将歌剧中的每个角色都塑造得有血有肉。
该剧讲述的是1935年,江西苏区杜鹃坡陷入白色恐怖。共产党员田玉梅与桂英、七叔公机智勇敢地与叛徒马家辉和白军团长斗争,桂英大义灭亲,为了掩护田玉梅壮烈牺牲。田玉梅为了拖住敌人,被白军包围,慷慨就义。
在剧中,我饰演“桂英”,现结合个人的演出实践,从唱腔、念白、表演三个方面,对塑造“桂英”的形象进行具体分析。
一、加强对民族歌剧的认识
《党的女儿》是中国民族歌剧的代表作品,在这部歌剧排演之前,我对中国民族歌剧作了较为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民族歌剧尽管是在借鉴西方歌剧艺术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但纵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江姐》《洪湖赤卫队》等优秀歌剧作品,就会发现,这些优秀的歌剧作品无一不是深深地扎根于民族土壤。民族歌剧就是在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借用传统戏曲的结构原则,以专曲专用的音乐创作为基本手段。从音乐上讲,唱段设计采用戏曲板腔体结构原则是民族歌剧最主要的特征。从文学上讲,民族歌剧的剧词创作也大量借鉴戏曲语言,而戏曲语言创作又是以传统诗歌、民谣等为基础。民族歌剧的发展是建立在汲取民族音乐文化营养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成功塑造民族歌剧中的人物形象就必须加深对中国民歌、歌舞、戏曲的学习和理解。
学习和研究中国民族歌剧与中国戏曲的相关知识,为成功塑造歌剧人物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唱腔与人物形象的塑造
塑造人物形象需要对人物的性格特点有全面的把握。为准确把握人物角色,结合剧本和前人的演出视频,我对桂英的人物形象作了反复的分析和推敲。
《党的女儿》中的桂英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传统女子,但内心又充满了正义感,她和丈夫马家辉都是共产党员,但是丈夫却叛变了革命。面对打击,她痛不欲生,甚至精神恍惚,差点羞愧自尽。在田玉梅的帮助下,桂英逐渐走出迷茫,走向坚定,不但帮助玉梅逃出罗网,并进行大义灭亲的斗争。最后,为掩护玉梅被马家辉打死。桂英的形象矛盾冲突较多,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角色,这为“塑造”桂英的舞台形象增加了难度。
桂英和丈夫马家辉是革命夫妻,二人都是共产党员,马家辉还给桂英和玉梅上过党课,桂英对丈夫的感情应该是既崇拜又依赖。这从桂英出场的唱词得到充分的体现:
“从前有座山啰,
山上有棵树,
花香果又美哟,
枝壮干又粗,噢…”[1](P8)
可见,马家辉在桂英的心中是一颗依靠的大树,但眼见他叛变革命,出卖同志后,这棵大树突然倒塌,精神上的巨大打击,彻底击溃了桂英,使其变得疯疯癫癫、神志模糊,失望和痛苦吞噬着她的心,痛苦与煎熬中桂英唱到:
“忽然长了虫噢,
虫把树来蛀,
花儿纷纷落啊,
叶儿片片枯,噢…”[1](P8)
对桂英一出场疯癫的形象,我也曾反复琢磨。笔者借助之前戏曲演员的舞台经历,便在传统戏曲中寻找相似的人物形象。
首先,我想到的是传统戏曲折子戏《失子惊疯》中的胡氏。该剧讲述的是知府梅俊妻胡氏怀孕14个月未产,妾徐氏嫉恨,诬胡氏将产妖怪,梅欲杀妻。丫环寿春领胡氏出逃,途中产子,寿春去村里寻食。时巴山大盗金眼豹下山,见胡氏美貌,抢上山去,幸被金眼豹的压寨夫人放走。胡氏与寿春相见,悲喜之余忽想到怀中空空,孩儿不见,胡氏大惊,四下寻找,寻子不见,连遭不幸,精神失常以至疯癫。
胡氏的遭遇和疯癫与桂英有相似之处,可以借鉴剧中胡氏疯癫的表演,但其形象和桂英却有着很大的差异,桂英虽然表面上是弱女子,但骨子里却透着共产党员的勇敢与坚毅。
其次,类比的人物还有秦腔《打神告庙》中的敫桂英。敫桂英曾救助落难书生王魁,两人在海神庙山盟海誓,王魁高中状元后,入赘相府,抛弃敫桂英。于是,敫桂英到海神庙申冤告状,一番哭诉后,愤而自尽。此外,传统戏曲中的杜十娘也跟敫桂英有相似的经历,她们都是爱情的向往者、依赖者,面对背叛,内心痛苦、失望,与她们不同的是桂英没有绝望,而是坚强地选择了革命。通过比较,我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视野,桂英的人物形象也变得更加清晰,表演中可以借鉴戏曲人物的若干技巧,但又要跳出传统的程式。这是剧情对人物角色的要求,如桂英唱到:
“大树就要倒哇,
谁来扶一扶?
(忽然扑倒桌上,痛哭。)”[1](P8)
从唱词看出,丈夫的形象在心中倒塌后,桂英仍希望他能悬崖勒马。因此,与传统戏曲中胡氏等人物不同,桂英既疯癫又清醒,她在革命遭遇挫折,内心无比挣扎的时候,以疯疯癫癫的外表来逃避现实。表演中,我抓住桂英内心复杂的情感,了解人物性格,在戏曲演员功底的基础上,融入了歌剧表演的元素,完全地进入角色,比较准确地塑造了人物形象。
准确把握桂英的人物形象后,还需要对人物音乐和整场音乐有深刻的把握,只有对音乐和剧本的内涵了然于胸,才能将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通过声音准确地传达给观众。
“《党的女儿》在音乐语汇风格上,首先采用了戏曲的板腔体(主要是北方的戏曲音乐),同时,由于该剧的故事发生在江西,作曲家在曲调上也广泛采用了江西的地方性民歌音调,将江西的音乐体裁‘歌谣体’与北方戏曲的‘板腔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其独特鲜明的音乐风格并以此作为音乐拓展的支点。”[2]
歌剧通常采用人物主题的写作手法,柔弱、善良的桂英采用了委婉悠扬的江西民歌旋律作为其人物的主题旋律,而性格阳刚的玉梅选择了慷慨激昂的蒲剧板腔体作为其人物的主题旋律。我是戏曲演员出身,故对蒲剧的板式结构非常熟悉,蒲剧和秦腔在音乐结构上基本一致。
在深入理解蒲剧音乐结构的基础上,我对江西民歌作了全面的学习、分析,学唱《日头出来晒山岗》《藤缠树来树缠藤》《桐子开花朵对朵》等江西山歌,体会其中的韵味,这对成功刻画桂英的人物形象至关重要。由于故事发生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歌剧音乐便以江西民歌曲调作为素材,歌剧开场运用“日头落了心莫慌噢,夜来日落有月光噢”这首江西民谣,以暗喻故事发生的地点。歌剧主题曲《杜鹃花》是由江西安远的民间小调《杜鹃花儿开》改编而来,并用杜鹃花象征革命的精神,体现了音乐形式与故事发展的完美结合。歌剧的主题音乐通常是基于戏剧故事而设计、创作的,这必然要求人物形象与其音乐水乳交融。因此,准确理解人物的音乐对成功刻画人物形象至关重要。
桂英出场,其形象是焦急、绝望和神志不清的状态,适应剧情也适应人物形象,唱腔运用游移不定、吟唱相结合的旋律(见谱例1、2)。
谱例1:《从前有座山》前奏

谱例2:《天呀天,地呀地》的前奏

骨干音la、Do、re是客家民歌常用的素材,为了加深对音乐的理解,我分析了江西兴国的客家山歌《打只山歌过横排》、福建山歌《新打梭标》等,了解了客家山歌善用比兴,韵脚齐整,多七字四句等基本特征,掌握了客家山歌“过山溜”的演唱特点,仔细体会民歌蕴含的情绪。事实证明,对江西山歌的学习对于我更恰当更准确地进入角色具有重要意义。音乐一响,我似乎置身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革命老区的血雨腥风中,但还要凸显出反常、惊恐的精神状态。演唱第九曲“从前有座山,山上有棵树”时,既要声音甜美、通畅,还要具有浓郁的江西民歌的味道。气息控制要好,声音感觉从远处传来,表演上要表现出担心、害怕、似疯似癫的状态。演唱第十五曲“天上风在吼雷在叫”时,桂英似乎在讲述东山口的屠杀事件,情绪疯癫而激动,我适当借鉴了戏曲“净”角的演唱感觉,较好地表现了桂英作为一名弱女子的革命激情。充分理解人物性格和深入学习歌剧音乐的创作背景,对顺利完成桂英的唱腔带来极大的帮助。
第四场《一死报党恩》是桂英唯一独唱的一个唱段,这个唱段是桂英在清醒后,觉得愧对党组织,决定以死报答党的恩情(见谱例3)。
谱例 3:

这段唱腔要充分表现出桂英内心复杂的思想转变过程,跟传统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女性一样,桂英从小具有较强的忍耐性,面对黑暗的社会,多少苦水独自吞。因此,第一句唱词要带着一些怯懦的感觉,采用给人倾诉的感觉,娓娓道来,“水”“吞”两个字后的拖腔,我采用秦腔中的哭腔来演绎,进一步强化了桂英悲伤的情绪。当怀中掏出党章后,桂英的情绪由软弱转向坚强,但内心的愧疚让她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决定以死报答党恩。特别是“一死报党恩”的情绪也变得更加激昂,并推向高潮。
这段唱腔运用了板腔体戏曲的结构原则,唱词也是传统戏曲运用最多的七字句,在上下句结构的基础上,不断变奏,唱段将戏曲“板腔体”结构原则与江西的民歌素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桂英当时的情绪和心境。王祖皆评价该剧音乐:“我们便把蒲剧音乐的戏剧性特点与江西民间音乐的抒情性特点有机地给予融合,创作出‘坐北朝南’的音乐新风格,力求音乐创作既要有赣南苏区的生活特征,但又不受具体地区的局限,把北方民间音乐中刚劲粗犷的美质,充实到南方民歌阴柔细腻的情调中去,通过南北音乐融合,获得艺术‘杂交’的优势。”[3](P549)
民族歌剧中的唱段跟中国戏曲中抒情性的唱腔有相似之处,在秦腔等戏曲中,综合性唱腔往往要用许多不同的板式衔接起来,表达不同的情绪。由于对戏曲的板式结构比较熟悉,对戏曲各板式的连接和转换有较为全面地把握,使我比较自如地通过演唱,将桂英的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情绪变化表现出来。
三、念白与人物性格塑造
中国传统戏曲有“七分念白三分唱,白是骨头唱是肉”及“千斤话白四两唱”等说法,这都说明了念白的重要性。与戏曲一样,在歌剧中,念白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而且台词的语言分寸的掌握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和难度。
歌剧台词的表达与歌唱一样,不仅要讲究位置和方法,还要对舞台情景进行深入地理解,细致揣摩每句台词的内涵,将其表现得准确到位。
唱腔与念白是表现人物性格、推动歌剧情节发展最富于表现力的手段,因此,处理好唱腔与念白的关系是成功塑造歌剧人物形象的两个重要因素。从排练开始,我就将念白与唱腔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我从三个层面处理好唱与念的关系。首先是反复研读剧本,熟悉并理解整个剧本的内容,了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然后将桂英的唱腔和念白全部用颜色笔标出,反复朗读。对歌剧的主题、情节、矛盾冲突、人物性格、戏剧结构等有深入的体会与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感知句数的长短、句子的平仄、句意的情感。做到对人物性格的准确把握。与此同时,我还深入学习了其他版本的《党的女儿》,特别学习了孙丽英老师的表演与念白。
歌剧与戏曲相同,唱腔与念白虽然规律可循,但又无“定法”。变和不变永远是一对矛盾,学习前人的表演是提高自身艺术表现力、形成自身表演特点的重要前提。在歌剧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
歌剧跟戏曲一样,角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演员的相互协作更为重要。一出好的戏一定要靠演员的合作,这就要求我对整出戏的人物都有熟练地把握,熟悉其他角色的戏份,特别是玉梅的唱腔和念白、马家辉的唱腔与念白,这样才能确保整出歌剧衔接得自然无缝。
戏曲念白分为“韵白”和“散白”,民族歌剧“根据剧本不同的题材风格,对念白也会有不同的要求,有散文诗似的对话和独白,也有韵白的对话,即使一般口语式的对话。”[4]地方戏曲是用方言来对白,歌剧则是普通话发音,但咬字的力度一定要把握好,恪守“以字为中心”的演唱原则,除了字正腔圆,还要通过念白的四声、语气等表达出念白、润腔和情感的关系。
演出过程中,我将台词的处理置于与歌唱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全剧各个唱词的所有台词的念白形式、声音特点、思想内涵,做到整体的设计与规划。每段台词的情绪、节奏、气口、音量以及轻重音等力争都有准确地把握,如第二场,桂英与马家辉的对白戏。
桂英因为马家辉的叛变,革命同志被捕杀,精神上受到打击而变得疯疯癫癫,因此,她的台词是建立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上,将自己给马家辉做的白小褂剪成布条,这个“剪”的动作,甚至可以加上“戳”的手段,会使人物形象更加逼真。念“血!血!那上面全是血呀!”怀着吃惊,恐惧的语气,音色明暗结合。念到“马家辉”时,可以用厌恶的口气,也可以用高亢甚至刺耳的声音,以表现桂英疯癫中似乎还有些意识。
四、表演与人物形象的塑造
歌剧表演与戏曲表演尽管有很大的差异,但合理地借鉴和吸收戏曲表演的营养对塑造民族歌剧人物形象能够起到巨大的帮助。中国歌剧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其内容、表演形式有待进一步丰富,而中国戏曲则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成熟的表演体系,为民族歌剧表演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从表演程式来看,戏曲与歌剧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戏曲表演注重唱、念、做、打的结合,“四功、五法”是表演艺术的根基。在写意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程式化的表演体系。而民族歌剧则是在西洋歌剧影响下产生的,沿用的西洋歌剧的表演艺术手段——“声、台、形、表”,其表演不受程式的限制,具有较强的写实性。
民族歌剧在表演上讲求“音乐节奏”、“内心节奏”与“行动节奏”的和谐统一,行动节奏就是要通过台步、身形、手势等肢体动作来传达内心的情感。如第四场“一死报党恩”的表演中,我就借鉴了戏曲的表演动作,如在节奏里加上快速的台步,表现出有板有眼、紧拉慢唱的感觉。第二场,桂英刚出场时,采取踉踉跄跄、高低不一的脚步,以表现其精神受到刺激,疯疯癫癫的状态,这一动作,我就借鉴了传统戏曲《失子惊疯》的表演方式。演唱第二场第十五曲,我还借鉴了戏曲甩水袖的感觉,唱“树儿也烧到”时,往左边甩,到“花儿也烧焦”时,右手做出空甩水秀的动作来变现桂英的恍惚。
演唱《从前有座山》时,桂英手拿剪刀乱戳白小褂,剪刀要乱,无章法,表现出桂英精神的不正常。演唱“醒来不如疯癫好”时,采用戏曲“程式化”的台步,有助于表现桂英内心的紧张和意识模糊。
中国戏曲讲究“一身戏在脸上,一脸戏在眼上”“眼是心中苗,七情都看到”,民族歌剧也相同,演员的各种情感都能通过眼睛表达出来。如第二场,桂英从屋里跑出来的,此时的桂英已经处于半疯癫状态。除了肢体和面部表情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用眼神来表现桂英的疯癫。这时的桂英目光一定要涣散、无神,甚至要表现出呆滞的感觉,但又不能让观众以为是闭眼。“从前有座山啰”一段唱,桂英内心的思想变化、神志在清醒与恍惚瞬间的变幻,主要靠眼神和脸上的表情变现出来。唱“花儿纷纷落,叶儿片片枯,咿呀呀子咿哟”时,脸上要洋溢出幸福的笑,但不是傻笑,似乎是一个会唱山歌的小女孩。唱到“咿呀呀子咿哟呀,呀,呀,呀,呀”时,想起来东山口的屠杀,眼睛突然要睁大,眉毛上提,以表现惊吓的感觉。还有神志恍惚的桂英在田玉梅和小程说到东山口时,突然意识清醒了一下,但看到带血的衣服时,又进入了疯癫,这一切惟妙惟肖的细节及其心理活动都要通过眼神的变化表现出来,并让观众理解。
桂英内心的各种活动,都要通过眼睛来传递给观众,戏曲“五法”中的眼法便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一个演员能不能感染观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眼法的把握,戏曲科班对眼法训练为我在这段戏的表演提供了丰厚的积淀。
由于戏曲科班的经历,在表演实践中,我会在戏曲中寻找感觉,然后再将戏曲程式化解,向话剧、歌剧和生活靠拢。努力寻找真实的感受与体会,进入角色,而不是演戏,如果是演戏,永远都打动不了观众。
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排演的《党的女儿》反响强烈,观众对我饰演的桂英非常认可。归纳起来主要得益于自己戏曲表演的功底,传统是一棵大树,有我们取之不尽的营养,只有不断地向传统学习,才能在民族歌剧表演的道路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