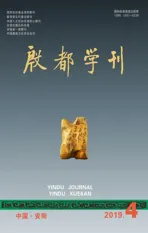从“蜾蠃”的得名看语言的演化
2019-03-13任继昉
任继昉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蜾蠃(guǒ luǒ),是一种飞虫的名字。这种飞虫,属昆虫纲、胡蜂科,身体青黑色,长得像蜜蜂,但是较小,长约半寸,腰细,又名“蒲卢、土蜂、蠮螉、细腰蜂”。
蜾蠃的生活习性,是以泥土筑巢于树枝或墙壁,捕捉螟蛉等害虫存放在窝里,以供其幼虫孵化后食用。古人误认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因此用“螟蛉”比喻义子。《诗·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毛亨传:“螟蛉,桑虫也。蜾蠃,蒲卢也。负,持也。”郑玄笺:“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陆德明释文:“即细腰蜂,俗呼蠮螉是也。”汉·扬雄《法言·学行》:“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文选·刘伶〈酒德颂〉》:“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李善注引李轨曰:“蜾蠃,蜂虫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矣。”周建人《关于熊猫》:“古人看到果蠃把小青虫捕去,封在泥房里,遂说是孵育为己子的。”
直到南北朝时期,医学家陶弘景不相信蜾蠃无子,决心亲自观察以辨真伪。他找到一窝蜾蠃,发现雌雄俱全。蜾蠃成虫平时无巢,仅于雌蜂产卵时,才衔泥建巢,或利用空竹管做巢,每巢产一卵,以丝悬于巢内侧,然后外出捕捉螟蛉衔回窝中,用自己尾上的毒针把螟蛉刺个半死。原来这些螟蛉不是作为“义子”,而是用作蜾蠃后代的食物。古代科学家通过有针对性的观察,才揭开了这个千年之谜。
一
蜾蠃与螟蛉的真相需要探索,“蜾蠃”得名的真相同样需要探索;自然科学需要研究,语言科学同样需要研究。
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下)》:
《释草》:“果臝之实栝楼。”《释虫》:“果蠃,蒲卢。”案:“果臝、果蠃”者,圆而下垂之意,即《易·杂卦传》之“果蓏”。凡在树之果与在地之蓏,其实无不圆而垂者,故物之圆而下垂者皆以果蓏名之。“栝楼”亦“果臝”之转语。蜂之细腰者,其腹亦下垂如果蓏,故谓之“果蠃”矣。[1]
王国维认为,虫名“果蠃”与植物果实名“果臝”同名,这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原因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圆而下垂”,因而其得名之由相同。
王国维是学术大家,创获甚多。但他的这一观点,却非首创,而有所本。所本为何?清代程瑶田有专文《果臝转语记》,其开头说:



古人之于物类也,凡同形同色,则其呼名亦同。《说文》云:“瓢,蠡也。”蠡与螺同,“蠃”为“螺”字之正体。螺之大者可剖之为瓢,与匏瓠剖为瓢者同形,故瓢亦谓之“蠃”。《说文》又云:“蜾蠃,蒲卢,细腰土蜂也。”一曰螔蝓。又“蜗”字下云:“蜗,蠃也。”盖三物同名为“蠃”。其所以同名者,皆以形圆而中细得名。蜾蠃转音又名“蒲卢”,而“蜾蠃”之音又转为“果臝”,《说文》云:“栝蒌名果臝。”盖栝蒌亦为圆形,故字异音同。果臝又作“果蠃”,“栝”、“蜾”,“蒌”、“蠃”皆系双声。若近人称瓠为“胡卢”,或曰“蒲卢”,其音亦由“果蠃”通转。盖瓠亦形圆中细之物。“蒲、瓠”双声,莫不取义于圆转。今江淮之南称物之圆转不已者恒曰“圆滚卢”。故物之圆而易转者,古人皆称以此名。植物之果臝、胡卢,动物之土蜂、螔蝓、螺蛳,所由异物而同名也。即取名不同,其音亦不甚相远,则以在有音无字之前仍为一字也。又《尔雅·释木》云:“边,要枣。”郭注云:“子细腰,今谓之‘鹿卢枣’。”“鹿卢”二字与“蠃”字为双声,即系“蠃”字之转音。形圆中细之物咸谓之“鹿卢”,故凡物之形圆中细者可谓之为“蠃”。观于此例,则植物、动物之得名,非以物类区分,实以物形区别;物形相似,则植物、动物均可锡以同一之名,非若后世之物各一名也。[5]
这种“凡两物相似者,即锡(赐)以同一之名;此物近于彼物者,亦假(借)彼物之名”[6]的方法,是原始人命名造词的重要手段。在为各种不同事物命名的过程中,原始人往往求同存异,抓住这些事物的共同或相似的特征,引申触类,以已知推未知,以此名命彼名,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异类而同名的现象。可见,“语言的古老性和语言的模糊性是成正比的。”[7]

当然,人类认识的这种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反复过程。语言中的词也是由少到多逐渐积累造出的。每当需要为一个事物命名的时候,人们就要将这个事物的特征与已有了名称的事物的特征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即“这个东西像什么”,而不管这两个事物各有什么独特之处,然后以已有的语言形式加以命名。这实际上是忽略甚至有意抹杀、混同事物之间的特点和区别,可以说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使名称模糊化。不这样做,就无法用现成的语音形式来为新认识的事物命名。每当造出一个相似的新名称时,就经历了一次由清晰到模糊的过程。但是,人们在使用这个新名词时,还要利用种种办法,例如语音变换、字形变化等,加以区别,使已经模糊了的概念再清晰化。命名时的有意模糊化与用名时的力求清晰化,就构成了思维的矛盾运动。人类思维的这种模糊──清晰、再模糊──再清晰的过程,接连不断,以至无穷,由最初的浑沌模糊到最后的清晰周密。这就反映了人类思维呈螺旋状上升的发展总趋势。
这些语音和意义都有联系的名称,是同时产生的呢,还是有先有后?如果有先有后,谁先谁后?这单靠语言学本身是难以确定的。但历史学的原始社会发展史分期研究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依据。有关学者为我们列出了较为详细的原始社会发展史分期表。[9]

命名时的这种由此及彼、比况类推的现象,在世界其他语言中也可以发现。在克拉马特一带的印地安语言中,有“l─加在动词和名词前的前缀,形容或指明圆形或橙形、圆柱形、平圆形或球形的物体或轮状物;也指容积大的东西;此外,还指用这种形状的物体完成的行动;或者指身体、臂膀、手或其他部分的圆形或半圆形的波状运动。因而这个前缀常常与云、天体、地表面的圆形斜坡、圆形或球形水果、石头和房屋(房屋通常呈圆形)连用。它还用于畜群、围场、社交聚会(因为集会通常都围成圆圈),等等。”[11]
看来,“圆”这个概念,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圆形或接近圆形的事物中概括出来的:树果、鸟卵的球形圆,瓜蓏的球形或椭圆形、圆柱形的圆,禾穗的圆锥形或圆柱形的圆;球形的立体圆,环形的平面圆;浑然一体的圆,断续相连的圆;实心的圆,空心的圆;静止的圆、旋转的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千差万别,却大同小异,它们都有一个或相同、或近似,或明显、或隐蔽的特征──圆。
同根词的类比孳乳,是在同一意义层次之内沿着水平方向进行的孳乳运动,因而是一种横向的孳乳,其主要表现为意义的扩展。横向孳乳所产生的同根词与同根词之间呈现出平行的联系。
二
“蜾蠃”因“果臝”而得名,那么,“果臝”又因什么而得名呢?现代的语言学家们对这个历史之谜也进行了探索。
张寿林说:“物体圆者,流转有声,音近Gulu,初民模仿,以为称谓。”[12]潘尊行《原始中国语试探》列举“模仿语(一)”是“圆转的声音”说得更形象:
今语模仿一物体滚的声音为gululu或kululu,初民……模仿了做称号。因此圆形物如“果臝”、“蜗蠃”、“栝蒌”、“颗颅”,……都用这笼统的称号。[13]
根据这些材料,基本可以判定,“果臝”产生于语根gulu,“初民模仿,以为称谓”。由语根gulu产生的原始词语“果臝”,成为“蜾蠃”等词产生的根词。
由语根直接生发的原始根词一旦产生,也就为语言词汇的丰富奠定了基础。那些由语根生发而来的根词,有的具有极强的直接或间接的孳生繁衍能力,它的音义形式为后来新词的孳衍提供了现成的条件。既然有了语根和根词,有了现成的语源意义和语音形式,实质内容和物质外壳都已具备,可供借鉴,人类就充分地利用它,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不断地扩展开去,施之于相关、相似甚至相反的事物。于是,由根词孳衍派生出一代新词,再由这一代的词儿孳衍派生出第二代、第三代的新词,以至无穷,一代又一代的新词也就源源不断地孳生繁衍出来。
这些在根词的基础上孳生繁衍出来的一代又一代新词,既然最初出自同一语根,也就可以称之为“同根词”。词的这种孳衍派生、滋生增益的过程,就叫做“孳乳”。
语言的词汇系统,是反映客观现实的概念的存在形式;同根词的孳乳过程,也是人类思维过程的折射。人们的思维过程,是按照“概念、判断、推理”之过程进行的;这个过程,又是沿着横的(空间)和纵的(时间)两个方向层层展开的。因此,同根词的孳乳活动,也就随着人们思维的发展,既沿着水平方向进行横向的扩展,又沿着垂直方向进行纵向的递进。
一个根词一经产生,就成为音义的结合体:语音形式是它的物质外壳,所指事物是它的意义指向。人们就利用这个现成的物质外壳,来它个“旧瓶装新酒”,转而表示别的事物。而新、旧事物(从人们为事物命名的先后次序而言)之间过渡的桥梁,则是它们之间特征或标志的相似性。就是说,将要被命名的事物所具有的特征或标志,与已命名的事物的特征或标志特别相似,人们就以这两个事物之间特别相似的那个特征或标志为线索,进行联想、类比,由此及彼地将已有的语音形式套用到另一事物之上,从而造出新词来。正如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所说:“类比是语言创造的原则。”[14]

三
昆虫名“蜾蠃”产生于瓜果名“果臝”,“果臝”产生于语根gulu,那么,gulu又何来何往?我们可以再接再厉,对这个历史之谜进行深入探讨。
蜾蠃又名“蒲卢”。《礼记·中庸》:“夫政也者,蒲卢也。”郑玄注:“蒲卢,蜾蠃谓土蜂也。《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桑虫也,蒲卢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政之于百姓,若蒲卢之于桑虫然。”“蒲卢”之名,同样可以证实以上之说。
潘尊行说:“有时也用bululu或pulululu来模仿,这就是《尔雅》的‘毗刘暴乐’,木叶滚下来的声音。因此,蜾蠃又叫‘蒲卢’,丘垅又叫‘培塿’。”[13]
语音形式p-l-和k-l-一样,也是起源于摹拟物体折断、劈裂、掉落的响声。《尔雅·释诂下》:“毗刘,暴乐也。”郝懿行义疏:“‘毗刘暴乐’盖古方俗之语,不论其字,唯取其声。今登莱间人凡果实及木叶堕落谓之‘毗刘杷拉’,‘杷拉’亦即‘暴乐’之声转。”这就犹如今语模仿一物体滚的声音为gululu或kululu,有时也用bululu或pululu来模仿一样。正因为如此,k-l-和p-l-两种语音形式常常可以互换。
潘氏以前就曾说过:“吾人于土蜂之变言‘果蠃’为‘蒲卢”,已见k-l-与b-l-两语核之相当矣。同例,蜗牛谓之‘蜗蠃’(《说文》),又谓之‘蚹蠃”(《尔雅·释鱼》),亦曰‘仆累’(《管子·地员》);矛谓之‘屈卢’(《史记·仲尼弟子端木赐列传》),又谓之‘勃卢’(《越绝书》)。吾人得因之以推知蚶谓之‘魁陆’(《尔雅·释鱼》郭注),蚌谓之‘蛤梨’(《淮南·道应》高注),蜃谓之‘蒲卢’,原亦为一语之变。且知《尔雅》中一物二名而互为训,如《释草》‘莞,苻离’,莞之言‘芄兰’,并指其曼生;《释木》‘瘣木,苻娄’, 之言‘块垒’,并状其拥(臃)肿,亦此两语核之变。”[15]
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也说:“苻离、苻娄、蒲卢、蚹蠃,皆有魁瘣拥肿之意。又物之突出者,其形常圆,故又有圆意。莞之名‘苻离’,以其首有台也;瘣木之名‘苻娄’,以其无枝而拥肿也;又蒲卢之腹与蚹蠃之甲,皆有魁垒之意,故四者同名。《释诂》:‘毗刘暴乐也。’‘毗刘暴乐’皆‘苻娄’之转语,其义亦由是引申矣。”[16]
其实,应该颠倒过来说,“苻娄”等名称是从“毗刘暴乐”引申(孳乳)而来的。潘尊行和王国维的话说明:即使是同一种声音,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甚至不同的人,听来也会有所不同,摹拟的结果可能更是五花八门。[17]
从语根g/bulu到“蜾蠃”的分化演变过程,可以图示如下:
小虫大世界,物名大乾坤。从一个小小的虫名,竟然可以看出其背后隐藏的语言演化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