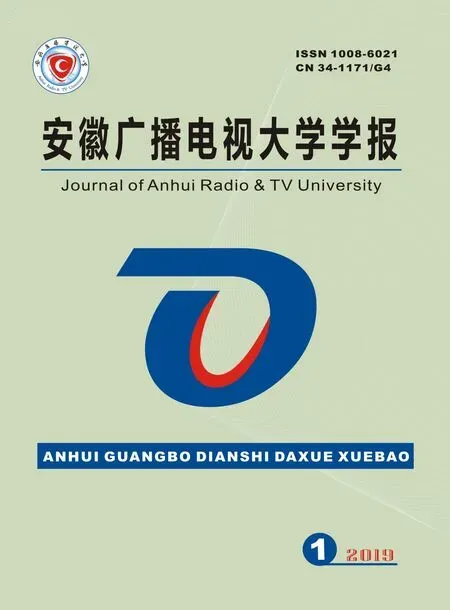为鬼为蜮:华夏民族鬼之元语言审视
2019-03-12黄交军李国英
黄交军,李国英
(1.贵阳学院 文化传媒学院,贵阳 550005;2.贵阳市青岩贵璜中学,贵阳 550027)
一、引言
“人死而为鬼,有诸?”(《郁离子·论鬼》),鬼之存在与否不仅困扰着现代民众,其实古人亦对它进行着孜孜不倦地思绎发问,甚至连明太祖朱元璋都亲自专门撰《鬼神有无论》一文参与讨论,以究其原,足见该主题意义重大,确为千古之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鬼与人类犹如一卵双胎,难舍难分,而初民对鬼之认识感知很早就以文字符号的形式予以记录存留,在我国目前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上溯至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其内容多表达“(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政教合一思想,流露出浓厚信鬼重祀之风尚,然详洽釐析中国古代鬼文化的最佳典范无疑首推东汉时期汉字训诂学集大成之作——《说文解字》,因“文字当以许氏为宗,必先究文字,后通训诂,故《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说文解字正义序》)作为有史以来中华大地上第一部字典,该书释义元语言[注]学界目前对元语言理解尚存争议,笔者界定“释义元语言”包含《说文》该书中许慎训诂所收词语,亦涵盖许氏考形、订音、枚举古字、援引书证等录入的词语。体例模式充分衍射出华夏民族东汉及以前时代有关宇宙、社会与人生等元认知意识,而鬼作为古籍中的核心词汇,被人们频繁指涉使用,几乎贯穿古代宗教、哲学、政治乃至军事等各个方面,成为我们管窥审视华夏初民元认知程度的理想标杆。
二、《说文》鬼类词语的历史表现层次与元语言文化审视

(一)生理感官疼痛不适反映出鬼是造成人类疾病亡殁的原始观念
“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於人,以为淫厉。”(《左传·昭公七年》)在上古人们心目中,瘟疫疾病被视为折磨人类的头号杀手,其神秘存在贯穿于先民的自我审视与世界认知之中,更为突出的是,鬼不但可以导致人横死或夭折,强死之魂魄化为厉鬼且能继续依附人身祸害他人,成为部落民族的群体记忆。
①瘣。《说文·疒部》:“瘣,病也。从疒,鬼声。《诗》曰:‘譬彼瘣木。’”[1]154瘣本义为内伤致病,今《诗·小雅·小弁》作“壞木”,毛传:“壞,瘣也。谓伤病也。”郑玄笺:“犹内伤病之木,内有疾故无枝也。”可知瘣之得名源于古人认为该病因鬼致症,从而给人带来感官疼痛难忍,故中医有“瘣疾”之语。
②疫。《说文·疒部》:“疫,民皆疾也。从疒,役省声。”[1]156疫本指流行急性传染病,引申为疫鬼(古代迷信称施瘟疫的疠鬼)之义,如《玉篇·疒部》:“疫,疠鬼也。”古人迷信兼医学落后,认为瘟疫等高传染性疾病是由鬼神掌控施放,故有“瘟神”“疫鬼”之称,《释名·释天》:“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③癘。《说文·疒部》:“癘,恶疾也。从疒,蠆省声。”[1]155段《注》:“古多借厉为疠。”[3]癘同厉、疠,故称鬼厉。初义是一种恶疮,即麻风病。柳宗元《太白山祠堂碑并序》:“疠疾祟降则祷之。”蒋之翘辑注:“鬼灾曰疠。”引申有瘟疫、杀等意义,《新唐书·忠义传中·张巡》:“臣生不报陛下,死为鬼以疠贼。”
④瘧。《说文·疒部》:“瘧,热寒休作。从疒从虐,虐亦声。”[1]155瘧为疟之古字,会意兼形声。本义是疟疾,病名。《释名·释疾病》:“瘧,酷虐也。”古时迷信谓疟疾为瘧鬼作祟,《搜神记》卷十六:“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瘧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

(二)心理情感恐惧不安折射出鬼给人类造成的心理阴影
“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左传·昭公七年》)正因鬼多以恶鬼、厉鬼等丑恶面目出现,在给人类造成战栗惊悸的同时,该强烈感官刺激转化为一种深层的潜意识,即鬼梦、噩梦等。在中国历代正史佚闻中均记载着不少遇鬼逢鬽类型的特殊梦文化事迹,流露出人们焦虑不安的心理恐惧与过往曾经。(北凉)沮渠京声《治禅病秘要法》卷二云:“埠惕埠惕,是恶夜叉,亦名梦鬼。”鬼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三)祖先崇拜宗教信仰流露出古人祈求鬼魂安宁赐福的良好愿望
《史记·乐书》:“居鬼而从地。”张守节正义:“鬼,谓先贤也。”与西方文化中鬼一直站立于人之对立面不同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鬼与人还存在着一种天然亲和关系,即鬼乃先民逝去之祖先。先民在盟誓监临等重大场合往往邀请先祖鬼神鉴之,以明其心志,如《左传·哀公十四年》“所不杀子者,有如陈宗。”孔颖达疏:“陈宗,谓陈之先人。服虔云:‘陈宗,先祖鬼神也。’”古人对祖先进行顶礼膜拜无疑是视其为本宗族的保护神、代言者,故“敬天法祖”之主旨贯穿于华夏民族的思想并在汉字中有着详细的记录。

⑩禰。《说文新附·示部》:“禰,亲庙也。从示爾声。”[1]9禰同祢,爾作声符兼表近迩义,为形声兼会意字,李祯《逸字辨证》:“《隐元年公羊传》疏:‘禰字示旁,言虽可入庙是神示,犹自最近于己,故曰禰。’明是会意。”指奉祀亡父的宗庙、亲庙,又可称父死后入庙。《广韵·荠韵》:“禰,祖禰也。”


“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扬祢,封禅为首”(《晋书·礼志下》),先民之所以重视天地鬼神,无疑是古人遵从祖训,讲究传承,以便能“克绍箕裘”(《礼记·学记》)、扬名显亲的内心写照与自然反映。例⑨指供祀祖先鬼魂之宗庙;例⑩祭祀亡父鬼灵之亲庙;例指祭天沟通天、鬼;例指柴祭接人鬼于天神。华夏民族推崇天人感应,主张天神、人鬼、地祗三者之间并不存在天然对立的绝缘界限,上古时期就已将民间鬼魂学说与祖灵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以宗庙、祭祖等国家重典形式将其规范化、礼仪化、制度化。殷商武丁以后,祖先之鬼灵更是与上帝合为一体,从而实现了人、鬼与天三者融合统一,使得国民鬼意识更趋强烈醇郁,甚至发展到后世“天下无处非鬼,充塞无间”(元·欧阳玄《暌车志·无处非鬼》)无以复加之地步,以至于陈独秀针对该鬼俗情形特别指出:“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定数观念最为有力。”[4]可见华夏民族鬼文化祭鬼崇祖之民俗历史流泽深广,蔚为大观。
因为汉字作为镌刻我们民族思想与人文意识的符号媒介,忠实载录着华夏民族古往今来风云变幻的点点滴滴,具有原生态与活化石的史料语料价值,可以说一个个汉字的生成变迁历程就是一部部华夏民族砥砺前驱的斑斑信史。而元语言追求释义基元的统一解释,即用最小最简单最经济的字符来找寻解释全人类所有语言思维规律的共性,从而破译人类心智原理奥秘,而鬼字及《说文》中鬼义字符与鬼文化无疑看作是该系列字符之最大公约数与人类文化之最小公倍数的关系。从这个意义而言,汉字是我们华夏民族赖以生存的历史碑铭、血缘基因、文化密码与认知工具,借此可以快速有效地表达世界、认识世界与解读世界[5]。鬼作为华夏民族一种积极的思维活动与精神幻体,体现出前人试图解释与认知自然物象的心理愿望,并通过建立人、鬼与神的沟通交融来达到战胜疾病、趋利避害的主观目的与心理平衡。从认识论而言,无疑是华夏民族面临生存危机智力水准与思维方式的一个重大社会进步,故我们发现鬼之观念超越思想领域,往往被人格化、神格化,成为文学甚至文化的宠儿。与西方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强调怀疑精神的哲学理念不同的是,华夏民族讲究“(付之)阙如”(《论语·子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保持着对古言元典的尊敬信从精神,故《说文》中鬼义词语传达出华夏民族对鬼之阐释历经了从疼痛不适(生理感官)到恐惧不安(心理情感)后祈求灵魂安宁(宗教信仰)的语义脉络,寄寓着“昭祖扬祢,克绍箕裘”之精神内涵与思想情感,确实称得上一部人生与世界的民族叙事诗、语言认知史,是我们继往开来、赖以生存的重要词汇与哲学概念。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为鬼为蜮”一语常用于指称人世间各种妖魔鬼怪。以《说文》所含鬼义词语为考察对象,从释义元语言的角度对其进行文化层面的系统审视,可以看出鬼作为华夏初民面临自然生存危机时经过精心思索塑造而成的一个经典意象,阐释了人们从疼痛不适(生理感官)到恐惧不安(心理情感)后祈求灵魂安宁(宗教信仰)的语义脉络,见证着华夏民族由粗朴质野走向精深玄奥之文明旅程,寄寓着上古人们“昭祖扬祢,克绍箕裘”之精神内涵与思想情感,堪称一部有关人生与世界的民族叙事诗、语言认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