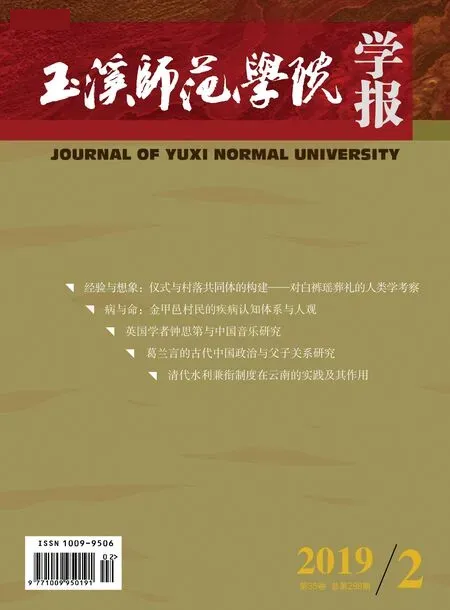英国学者钟思第与中国音乐研究
2019-03-05
(宿州学院 音乐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30年间,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北方地区进行田野工作的西方学者并不多见。即便有一些西方学者在这一时期来到中国,也大多选择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研究,其关注焦点亦非中国大陆民间音乐。20世纪80年代之后,更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学者能够亲临现场进行考察,此时,一大批国外音乐学家来到中国,开始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等,为中国音乐的海外传播与交流创造了良好机会。1980年代末,继上海音乐学院来了第一位学习中国音乐的留学生Raffaella Gallio之后,西方音乐学者们陆陆续续来到中国。其中,为大家所熟悉的有美国学者李海伦(Helen Rees)、荷兰汉学家施聂姐(Schimmelpenninck)、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P.J. Stock)、钟思第(Stephen Jones)、美国学者韦慈鹏(J.Lawrence Witzleben)等。英国学者钟思第,学习中国古代汉语出身,并未受过音乐学专业训练。在进入中国研究民间音乐以前,他是一位汉学家、小提琴演奏家。他长期以来坚持对中国音乐进行研究,对中国音乐的海外传播做出积极贡献,值得学界关注。
一、钟思第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钟思第(Stephen Jones)1953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祖父是村里的鞋匠,拥有一个祖传了200多年的制鞋铺。他的姨妈Edith(1898~1977)起初是位老师,仅仅工作7年后,由于感染猩红热听力逐渐丧失,不得不结束教师生涯,回到家乡靠政府提供的养老金生活。Edith回乡之后开始写小说,一生共出版过11部小说,其中《红雨伞》(The red umbrella,1937)被多次出版发行。受Edith的遭遇以及自身口吃的影响,钟思第在中国的田野考察中遇到盲艺人等患有残疾的艺人会有异于他者的感受。他认为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使得他对文学、老百姓、祖传工匠、性别学、残疾人(结巴、盲艺人)的兴趣在小时候就已经萌生。
1969年,钟思第加入了英国国家青年管弦乐团,在作曲家兼指挥家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1)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1925~2016),法国作曲家,指挥家,以善于清晰而准确的演绎20世纪的音乐而著称,1995年被任命为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家。的指导和启发下进行演奏。1972年开始在剑桥求学,在四年里主要学习和研究古汉、唐代历史和文化、禅宗,并积极参加各种古典音乐活动。他还和劳伦斯·毕铿(Laurence Picken)(2)劳伦斯·毕铿(Laurence Picken,1909~2007),卓越的自然科学家,中国唐乐研究专家,“20世纪剑桥伟大的学者之一”。一起非正式地研究唐代音乐。1976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结束了剑桥的读书生涯之后,钟思第继续在毕铿工作室以非正式成员的身份参与唐代宫廷音乐的研究,协助毕铿编辑唐代宫廷音乐卷的宏伟巨著。毕业后,他常住伦敦,为了谋生,在伦敦各种交响乐团和歌剧乐团演奏小提琴。1980年代初转而演奏早期音乐(Early-music),直到2012年。
本文虽然着重讨论钟思第有关中国音乐的研究,但需要强调的是,他的成长经历为他日后在中国的田野考察埋下了不可或缺的伏笔。由于演出的需要,他经常跟着乐队四处旅行,使得他有机会现场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如塞维利亚的弗拉门戈、布达佩斯的特兰西瓦尼亚乐队、日本的能乐等。长期接触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对其辨识与发掘中国民间音乐提供了很大帮助。
钟思第在国外不依附于任何一个科研机构或高校,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中国音乐研究专家。1995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民间乐社》,是其出版的第一部有关中国民间音乐的论著,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三章有关辽宁、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山西、陕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各地民间乐种及乐社的考察报告,都是他亲自考察过后撰写的(3)初期同他进行田野考察的中国学者,主要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薛艺兵。,并结合中国老一辈学者的考察报告进行对比分析,同时,他还向西方学界介绍了当时中国音乐学界的研究进展和成果。作为钟思第早期研究的老搭档,薛艺兵对此书曾有过详细和中肯的评述(4)薛艺兵.英国学者的新视野——钟思第《中国民间乐社》书评[J].中国音乐,1996(1):119-123.。对中国民间音乐的田野有了较为广泛的了解之后,钟思第于1995年开始对河北省涞水县义安镇的南高洛音乐会进行专项研究。在此之前,在“英中友好协会”的资助下,1993~1995年,他协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完成了冀中、京津地区民间“音乐会”的普查工作。这次普查前后共历时22个月,调查了70多家音乐会,并为其中的50家音乐会进行录音、录像,撰写调查报告。最终,“积累了40万字的文字资料,以及照片600余幅,影印乐谱共18种,录音、录像各数十个小时,取得了有关乐学、乐律、乐谱、乐目、乐社、乐俗研究方面的大量资料。”(5)萧梅.来自平原的报告——记首届中国民间鼓吹乐学术研讨会[J].人民音乐,1996(1):20-21.《中国音乐年鉴》1994、1995、1996卷连载了他们为50家乐社所撰写的调查报告,名为《冀中、京、津地区民间“音乐会”普查实录》,据这50家的调查报告统计,钟思第在普查中采访过的乐社有41家。20世纪90年代初,冀中地区的民间音乐研究风生水起,钟思第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张振涛所说:
一群学者为什么选择这个地区?为什么选择这个乐种?为什么选择非同以往的书写方式?为什么许多地区至今没有形成一种普查态势?难道不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位外国学者的外力推动?我们好像说不出他的作用有多大,但反过来看,如果把其他单位没有启动田野考察、其它地区没有形成同类普查的状况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评价他的作用了。(6)张振涛.咬定管子不放松——钟思第与冀中音乐研究[J].音乐研究,2015(2):15.
二、钟思第有关中国音乐研究的成果
钟思第有关中国音乐的著述,以类别叙,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论文类;二是专著类。据不完全统计,从1987~2013年,他共发表相关论文20篇。其中有数篇能够代表其学术观点的论文,均有中译文版本。如《从“假如钟先生能说汉语”说起》《字里行间读集成:评宏伟卷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切勿进行置身事外的研究》《华北民间法事与道士》《道教仪式中的民族志、表演和历史》等,在这些翻译发表的论文中,有些来自于专著的“结尾”或“附录”。相关论文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与唐乐、西安古乐有关的论述;(2)与河北民间音乐有关论述;(3)有关民间仪式音乐的田野考察报告(山西、福建、江苏);(4)有关中国民间艺人的论述;(5)有关中国音乐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处境论述;(6)在《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的系列文章;(7)有关吹鼓手、吹打班以及民间道士的研究报告;(8)有关中国民间音乐与性别问题的论述。
截至2016年,钟思第共出版过6本专著,按出版年代、田野场地为序,大致包括以下几类:(1)华北、华南地区(1995)(7)Stephen Jones.Folk Music of China: living instrumental traditions[M].Oxford: Clarendon Press (paperback edition with CD), 1995.;(2)冀中地区(2004)(8)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M].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2004.;(3)山西地区(2007)(9)Stephen Jones.Ritual and music of north China: shawm bands in Shanxi[M].Aldershot: Ashgate (with DVD), 2007.;(4)陕北地区(2009)(10)Stephen Jones.Ritual and music of north China, volume 2: Shaanbei [M].Aldershot: Ashgate (with DVD),2009.;(5)华北地区(2010)(11)Stephen Jones..In search of the folk Daoists of north China[M].Aldershot: Ashgate,2010.;(6)山西阳高(2016)(12)Stephen Jones.Daoist Priests of the Li Family: Ritual Life in Village China(with Documentary)[M].Three Pines Press,2016.。从专著内容来看,虽然涉及的田野场地众多,但用功最深、耗时最长的当属河北和山西两地。
在中国的田野考察里,钟思第对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颇为关注,从《采风——新旧中国的民间艺人生活》(13)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M].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2004 .到《李家祖传阴阳》(14)Stephen Jones.Daoist Priests of the Li Family: Ritual Life in Village China(with Documentary)[M].Three Pines Press,2016.一贯如此。
(一)《采风——新旧中国的民间艺人生活》
《采风——新旧中国的民间艺人生活》(以下简称《采风》)出版于2004年,是钟思第出版的第二部著作,是作者花费了十多年(1989~2003)时间在冀中考察的主要成果。为什么在几乎跑遍了冀中地区的情况下选择南高洛?同行的学者薛艺兵说,如果仅仅是为了音乐,他们会选择高桥音乐会或者是屈家营音乐会。之所以最终选择南高洛是因为那里丰富的民俗文化吸引了他们。
《采风》开篇的序言部分,作者交代了第一次去南高洛的经历,整体上对南高洛村的习俗(葬礼和婚礼)、村里的基本情况(村庄的地理位置、行政归属、人口数量、姓氏分布、收入水平)和音乐活动做了一个综述,并得出了持续研究这个村子的动力因素:(1)县干部和村领导的开明支持;(2)南高洛音乐仪式保存完好;(3)音乐会成员个性鲜明,他们的故事有助于形塑观察音乐的角度。
作者通过一个个不同的社会时代来描写与南高洛音乐会有关的人和事,将他们搁置在特定生活中来考察他们的生存对音乐会、对当地音乐的影响。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社会、个人与音乐的关系。该书第一部分从1400年高洛建村开始到1989年截止,主要叙事场景在解放之前和“文革”之后,主要内容在于民间艺人生命史和音乐会社的跌宕起伏。第二部分是作者置身事内的观察与体会,通过长期“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田野考察方法观察南高洛的历史延续,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蔓延到南高洛的现代化对当地音乐生活的影响。
文末作者指出了自己在研究中国民间礼俗音乐时的侧重点,他说:
文化的表达在社会中并不是位于次要位置。相对于关注著作和作品,我更愿意去讨论音乐活动的过程和场景。以前很多学者(包括英国和中国)都倾向于研究“国家的”、专业性的或是著名流派;而Finnegan(1989)的作品已经开始使这种平衡得到纠正。虽然她研究城市,但我的作品与她在本地、业余、非职业音乐方面的结论产生了强烈共鸣:“草根音乐是由业余民间艺人在当地场景下实践”(引自Overmyer1985:183)。当地音乐创作不是整个社会音乐创作的外围:它很少被局外人欣赏,但它维系着社区生活的共同体。它也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基础,尽管这可能不是很明显或者只是基本社会组织的一部分。(15)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M].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2004:363.
(二)《李家祖传阴阳》
曾有学者诟病钟思第写作的内容都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物,无论是国家事件还是农村生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足为奇,因此这种写作不具备学术意义,然而并非如此。在其2016年出版的新书《李家祖传阴阳》的附录中,作者认真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在其新开的微博中,也屡屡提到过这个问题。
《李家祖传阴阳》是钟思第出版的第六部著作,也可能是最后一本。这本书还包括一个完整的纪录片,名为《李满山——一个祖传阴阳的肖像》,影片中详细记录了李满山等人做法事时的场景,片中还不时地穿插一些作者的观点作为旁白。
全书由前言、正文(六部分)、尾声、附录、参考文献、索引、李家谱系表、地图(2幅)及照片(60张)组成。正文前三个部分延续钟思第一贯的写作风格,从历史溯源入手,对各个历史时期李家的仪式活动进行详尽描述。时间起于1926~1927年(李清的早期生活),终止于1990年代。在各个历史阶段,作者通过七个仪式场景叙述了李家阴阳的仪式、代际传承、经文、葬礼活动、复兴等问题。第四部分到第六部分,作者着重叙述了“仪式手册和文本”“仪式音声”(唱诵、打击乐、笙管乐)、“展望未来”。在结尾“返场”的笔墨中,作者借用李满山的感慨作为标题,抒发了自己对民间道教同样的感叹——“今非昔比”(Encore:Thing’s Ain’t What They Used To Be)。
在附录“道教仪式研究中民族志、表演和历史”中,作者从七个方面展开了对道教仪式研究中民族志、表演和历史的论述,这部分是全书的理论升华和观点总结。附录结合地方道教仪式研究中的民族志书写,探讨了社会环境在仪式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社会变迁的仪式环境中,道家的各种生活都是值得运用民族志的方式来进行书写和研究的。并指出全书的主旨在于通过描述另一种不同风格的道教,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和宗教的更便于接受的方法,并试图勾勒出道士们今天的生活是怎样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改变的。
在这里,钟思第掷地有声的表达了他在研究时的问题意识,他说:
当我与中国同事们讨论地方民俗文化报告缺乏当代的历史细节描述时,经常听到有人还击说“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没必要去讨论它。”这种想法具有片面性,它抑制记忆。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经历,即使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老年人也一定有不同的经历,这种记录仍然很缺乏。如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而忽略对二战描写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拉脱维亚、普利亚和新加坡各阶层人们经历都是形似的,而不值得去记录。(16)Stephen Jones.Daoist Priests of the Li Family: Ritual Life in Village China(with Documentary)[M].Three Pines Press,2016:372.
无论是作为音乐学家还是人类学家,亦或是历史学家,都应该在变迁的社会场景中实事求是地记录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钟思第认为“抢救可能确实是田野调查中有价值的方面之一。但是专注于重现昔日的辉煌,往往会淡化当代社会的变迁。这也是音乐(包括中国音乐)里的一个问题”(17)Stephen Jones.Daoist Priests of the Li Family: Ritual Life in Village China(with Documentary)[M].Three Pines Press,2016:369.。因此,“如果只参与抢救,而不记录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有一点奇怪。况且,我们对此知之甚少,而这种方法能为我们提供最详尽的信息”(18)Stephen Jones.Daoist Priests of the Li Family: Ritual Life in Village China(with Documentary)[M].Three Pines Press,2016:370.。在博客文章《民族志的基本要义》中,钟思第再次强调,民族志学者对传统文化所要做的更多的是记录它,包括农村生活的所有问题。而学者在考察中不需要喜欢工人们或是在家道士的曲目,但他们都需要被记录下来(19)Stephen jones. The brief of ethnography[EB/OL].blog. (2017-08-27).https://stephenjones.blog/2017/08/27/brief-of-ethnography/.。
在《华北民间道士与法事》(20)Stephen Jones.In search of the folk Daoists of north China[M].Aldershot: Ashgate,2010.一书中,他同样指出:“研究乡村仪式文化的目的,是了解一直在变迁的老百姓的文化;而不是为了寻找‘绝响’、‘民族文化精粹’等!”(21)钟思第.华北民间道士与法事[J].中国音乐学,2012(1):5.所以他“希望看到的是‘深描’,不光是对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文化生活,而且还应该包括老艺人回忆早期的一些资料”“要注意到艺人对过去的主观回忆”(22)钟思第.华北民间道士与法事[J].中国音乐学,2012(1):5.,我们需要有人这么做,以成为一个民间文化的“hunters and gatherers”(23)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5(1):134.。
2010年以来,钟思第的著作标题中不再出现“音乐”一词,他认为音乐只是研究的一部分,并不能作为主题去呈现,而应该对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仪式格局进行事无巨细的再现。借助执仪者的言行举止,通过描述,尽可能地还原仪式发生时的场景,这很重要,并且需要有人这么做。不难看出,他在民族志的写作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钟思第研究的国内外影响
钟思第在中国的影响,从一些音乐学家的表述中可以体现出来,这种表述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口述,二是文字叙述。下文介绍的大部分学者与钟思第都有过三十年的交往经历,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影响者。这些学者大多都同他做过田野考察,他的名字也不止一次的出现在许多中国音乐学家的纸际笔端与论文论著中,他们或称赞他诚恳、善良、感性、认真,或称赞他敬业、敏锐,做学术有不一样的视野与胸怀等。要想了解这种影响与意义,需要很多工夫,对其作品的研读、对其田野的亲历、对与他接触过的音乐学家的访谈都必不可少。
乔建中认为,钟思第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音乐的一位代表人物。同时,其田野考察、研究方法也影响了与他长期合作的一批中国学者(24)电话访谈,采访者:张黎黎;采访对象:乔建中。时间:2017年1月4日。。与乔建中有着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田青,他说:“钟思第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痴迷’程度,甚至使专门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中国同行们都感到吃惊。他的研究方式及其思想影响了很大一批当代的中国音乐学家,包括我。”(25)采访者:张黎黎;采访对象:田青。时间:2017年2月2日,地点:田青办公室。此外还有萧梅,她认为钟思第在中国的研究比较具有持续性,且持续性的关注“草根”,关注农村真正的现实音乐生活(26)电话访谈,采访者:张黎黎;采访对象:萧梅。时间:2017年1月12日。。作为田野考察的老搭档,薛艺兵说:“他是一位具有严谨学风,执着精神和敏锐洞察力的典型的英国人,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对中国民间的热爱和熟悉并不亚于中国人。”(27)薛艺兵.英国学者的新视野——钟思第《中国民间乐社》书评[J].中国音乐学,1996(2):123.同为老搭档的张振涛说:“他并未独树一帜提出过什么研究范式,也没有多少高深理论,但他认真关注当下的行为和侧重点却启发了我们。”(28)张振涛.咬定管子不放松——钟思第与冀中音乐研究[J].音乐研究,2015(2):15.
有关钟思第对中国民间音乐研究的贡献与影响,中外学者都有撰文进行阐释。由于国内学者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感悟与理解同西方学者有别,因此,对钟思第在中国的音乐研究所做出的评价比起西方学者来说多了一份情感上的肯定。西方学者对钟思第的评价,主要是对他的学术成果进行点评,进而对他的学术特点做了一番认定。以《采风》为例,西方学者从他的研究范围所引发的关注对象认为,他对于国家制度、社会变迁及个人经历的深度思考。尤其是对于国家政策的敏锐观察,是大多中国音乐界学者仅停留在脑海中而未及成文的(29)Rowan Pease.The Music of “Others” in the Western World [J].The World of Music.2005(3):164.。对其在理论框架上的建构,有学者认为其在《采风》中详细运用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及文献学的理论来构架自己的专著体系。有了详尽的资料积累,运用何种理论方法来分析整理是至关重要的,否则费尽心血搜集的原始材料有如一堆废纸,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尽其色。表面看来,他是在叙述一个个活生生的农民、一件件生活琐事。但是那些理论如同水银泻地般融入在他的叙述之中。难以区分作者是在讲述故事,还是阐发理论问题(30)Mercedes M. DuJunco. Review[J].Ethnomusicology, 2009(2):346.。
从将钟思第作为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从他1986年到中国以来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民族音乐学经历了诸多的曲折历程,在此过程中,他的重要性不在于考察本身或他所长期关注的民间乐社,而在于他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思维的影响。诚如薛艺兵和张振涛所说,他扭转了人们对农村艺人的看法,他对“人”的关怀是最有意义的。同其他国外学者相比,钟思第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仪式音乐,对中国民间仍大范围存在的仪式音乐有着与别人不同的大面积普查与重点考察的经历与体验。这在他的著作中体现明显。
与早期中国学者对田野的追求不同,钟思第更倾向于到农村去跟民间艺人学习,去现场观察了解具体的音乐项目,具备较强的音乐能力。虽然钟思第的研究所涉及的田野场地较多,但他对于具有典型中国元素的民间音乐或者是盛极一时的民间乐社则兴趣不大,并保持一定距离。这在其作品与在海外传播中国音乐的过程中均有所体现。
四、结 语
20世纪90年代,就国内学者而言,能够带着西方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领域的知识进入到田野中去,并在这些理论指导下观察民间艺人,解读特定环境中的乐社历史还不多见。因此,钟思第的到来具有一定时代意义。同其他未能有机会进入中国田野进行考察的西方学者相比,他是幸运的。他亲历了民间乐社乐人40年的兴衰沉浮,对由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个人生活的变革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理出一条脉络。“人类学家相信通过研究‘他者’能够比仅仅研究自己能更为深刻地认识自己,……把‘他者’作为认识自我的参照,其存在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31)黄剑波.作为“他者”研究的人类学[J].广西民族研究,2002(4):11-12.因此,我们需要一面镜子或一个参照物来映射出一个相对更加全面和完整的自己。对于中国的民间音乐研究而言,钟思第就是一面镜子,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民间音乐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式。无论是冀中地区的乐社与艺人研究,还是山西阳高地区的道教与在家道士研究,亦或是陕北的礼俗音乐、华北的民间道士与法事,仍会在钟思第及其相关学者所做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开发出更多园地,收获更多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