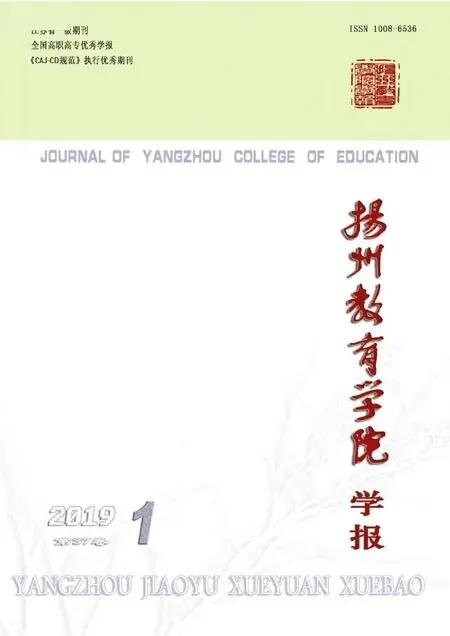《青鸟故事集》:历史的解构与建构
2019-03-05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2)
《青鸟故事集》原名为《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这两个名字都颇有意思,“青鸟”是李商隐的“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中的“青鸟”,它是穿梭于历史隐秘处的信使,“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正是青鸟要报告的内容。在李敬泽笔下,它化身为天主教传教士、波斯商人、异域探索者,为读者打捞历史的浮萍,通过历史中蒙尘的人事物看到中西方交流的暧昧镜像。在中国与西方“看与被看”的交流中历史显得既不真实又特别真实,这就是李敬泽为读者呈现出的历史面目。毕飞宇说“李敬泽的历史是个性审美的历史”,“李敬泽十有八九也是一个历史的审美主义者”[1]。确实,无论是历史讲述的内容,还是历史讲述的方式,都带有李敬泽个人考察、思索的印记,历史成了他眼中的审美对象。审美的过程也是解构重组的过程,李敬泽以什么方式对历史进行解构?解构的背后他要建构的又是什么?
一、文类的解构
如果要给《青鸟故事集》的文学体裁归个类,那将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因为他的文章中包含了各种文体。如果一定要给这种体裁归类的话,或许散文最无可厚非。散文作为四大文体之一,一直都处于边缘性地位,无法被纳入文体的正宗,就连叶圣陶也说:“除去小说、诗歌、戏剧之外,都是散文。”[2]这种极其简单的定义决定了它在大众的心目中并无一个明确的界限,它的漫无边际性决定了任何不被诗歌、戏剧、小说接受的文体一律可以划归到散文的行列中。从另一个角度说,不可归类是散文的文类尺度,将无法具体概括的文类归为散文是符合散文的内在规定性的。
散文没有被各种框架所束缚,它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空间来表达作家的个性,周涛曾将散文形容为文学楼房里的客厅:“在文学这个公寓里,各种文学的形式都有各自的居室,被墙隔开;只有散文没有自己的居室,它是客厅。谁都可以到客厅来坐坐,聊聊天,包括文学以外的人,但是客厅不属于谁,客厅是大家的,它的客人最多,主人最少。”[3]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李敬泽是有意选择了散文这一文类。在《青鸟故事集》第一节《〈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中,作者引经据典,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不相配”的故事,从日本女官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起,历经唐朝的穷波斯与珍珠的故事,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这老外真是,越有钱越抠门啊。”[4]8清少纳言说了一个“不相配”的事,而故事的结束又是一个关于不相配的故事,如此叙事,形成了一个完满的圆形结构,这种描写完全是小说化手法的典型体现。而在其中进行衔接的则是作者在古今之间进行想象的片段式思绪,再结合作者对各种随笔的考证,真实与虚构组装成了一个全新的文类,这种不拘一格的文类正是表达作者个人历史体验的最佳方式。
其实,作者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正史代言人,在小说、诗歌、考古、随笔等杂糅的散文文类中,作者书写的是自我建构的虚实相间的历史,在构建历史的过程中,李敬泽在不同身份、不同时间和空间、不同文体之间腾挪跌宕,没有一种文学形式能够涵盖他历史叙述的方式。因此如果强硬地将他的文字束缚在一个既定的文类中无疑会压抑他的艺术个性,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开始了瓦解文类的冲动,拒绝形式的压迫,冲破主导意识形态的规范,抒发个人性的东西,毕竟“类型的太阳底下是没有新东西的”[5]。当然各种文类相互杂糅并不是李敬泽的独创,在其之前,萧红、废名的实践已向读者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李敬泽在文类上的突破更为大胆、更为彻底、更为深刻。在《青鸟故事集》的每一部作品中都看不到一种纯文类的影子。《沉水、龙涎与玫瑰》中讲述了关于沉水、龙涎、玫瑰的三个故事,在作者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散文式的想象片段和空灵飘逸的语言俯拾即是,除此之外,还有作者在“考物”上的根据,文中随处是“据某某人的……记载”,可以得知,所有关于物的想象都不是作者凭空虚构的,而是有实际的根据,这就使得作者的文章具有了学术思辨性。无论是沉香还是龙涎,抑或是玫瑰,它们都承载着西方对东方的想象,这种彼此之间的想象驱使人类中的一部分去结识另一部分,最后李敬泽的漫漫闲谈具有了哲学的形而上色彩。这就是李敬泽提供给读者的东西,繁而不杂。可以说,李敬泽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洞开了历史的另一种面貌,丰富了散文叙事的空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敬泽体”。
二、意义的解构
历史由无数个必然和偶然组成,必然的成了正史,偶然的被时间蒙尘。抛却李敬泽出生于考古世家的身份背景,他与清少纳言有着同样的审美情趣,于细微之处发现深刻,发现物的实用价值。《利玛窦之钟》中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走了18年才到达明朝帝国的中心,好不容易得以向万历皇帝传达他带来的福音,岂料皇帝只对他的自鸣钟感兴趣,甚至直到清代,传教士的必需手艺就是会修理钟表。在滴滴答答的时间缝隙中两种文明互相误解,利玛窦感到失望:“利玛窦曾经收到过一封欧洲来信,写于1593年,信中说他在1586年写去的一封信刚刚收到,而他看见这封复信时已是1595年了。”[4]133为了自己的信念,他生活在两套时间罅隙中,心灵深处的钟表显示的是欧洲的时间,而历史中的彼时,他孤独地在这个王朝守望着,一直到死。《八声甘州》回溯了利玛窦的中国之旅,而接着利玛窦的探索之旅的是无数异族人:或是传播自己信仰的传教士、或是对异域文化狂热好奇的探索者、或是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波斯商人,他们都看了马可.波罗的对中国的描述,带着对中国的美好想象踏入这片未知的领域,然而当他们一踏入这片土地,误解就已经发生了,他们的想象立即破灭:“马可.波罗的诡计终被破解,原来只需由甘州一直向东就是‘契丹’,而‘契丹’就是中国。科学地理学碾碎了想象地理学美妙的梦境。”[4]163
李敬泽讲述的这两个故事都是关于误解的,利玛窦为中国带来的不仅是自鸣钟和地图,亦带来了西方创造的知识和古代中国人难以目及的广大区域,而宫廷却把它当做装饰物欣赏,他们根本不愿意去了解其他国家正在崛起这个事实,这是中国对西方的误解。而在第二个故事《八声甘州》中,异族想象了一个“契丹”的世界,这个世界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可以说马可·波罗对这个地点的描述激发了他们无穷的想象与期待,他们一个个前赴后继,却原来“契丹”就是中国,而甘州竟如此破败,与他们的想象格格不入。在另一个故事《第一眼——三寸金莲》中,李敬泽讲述的同样是一个关于误解的故事,1792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他们一上岸就紧紧地盯住了中国女人的小脚;安东尼奥尼跑到中国,拍了一部叫做《中国》的纪录片,镜头专照老太太的小脚,这个被李敬泽戏谑为“视觉政治”的事件所要说明的正是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在这种“被看”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与别人的目光作斗争,因为我们心酸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的形象正是被这种目光所确定的”[4]277,正是由于误解,中国在异域的审视中招致批判。
俞耕耘说:“文明之间的理解,总是来自误解。”[6]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误解促成的。李敬泽在文中引用了美国人亨特的《旧中国杂记》中的一则翻译故事,1837年广州知府和知县审讯一名印度水手,由于他们听不懂印度水手的语言,于是找来了当时的大行商蔡懋(老汤姆)担任翻译,由于这位水手说的是“水手语言”,而“老汤姆也有点不走运,他一点都听不懂要他传译的话”[4]183,老汤姆只能找来阿树,阿树会说几句“水手语言”,可是在与印度水手交流的过程中他完全是答非所问,翻译得牛头不对马嘴,还趁机向水手推销自家店铺和货物,最后老汤姆也加入了这个乱译的过程,将知府耍得团团转。在误解中,他们都以为彼此相互理解。无论是误解、误译还是“看与被看”,他们所期待看见的都是想象中的对方,虚构中的“他者”,因为这种偏见,两种文明发生了严重的错位,东方文明被夸大,西方文明被扭曲,接着东方文明被彻底批判,西方文明被过分宣扬,这种由误解、误译合成的偶然性在一次次堆积中固化了两种文明的形象,将历史导向一种必然。
三、历史言说的解构
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只是看解释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罢了。回溯20世纪九十年代先锋文学对于历史言说的解构,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温故一九四二》都是在反叛传统语言和传统形式中凸显出了作家的主体意识。现在李敬泽也延续了这种形式,以戏谑、讽刺、挑逗的语气解释历史,在秉持着“真”的历史原则的前提下,依靠想象来对历史的客观面目进行还原。在《青鸟故事集》中他将叙事变成了一种个人行为,“我”靠想象、靠叙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而历史被“我”的叙述所定型。依靠想象,李敬泽填补了历史缝隙中缺失的部分。《布谢的银树》讲述了1254年法国国王使者鲁布鲁克会见蒙古大汗——成吉思汗之孙蒙哥的故事,西方希望与蒙古合作共同对抗横亘在欧亚之间的伊斯兰帝国,前提是蒙古人要皈依上帝,这简直是一个疯狂的举动,要知道当时的蒙古势不可挡,而不明真相的西方人竟然对蒙古人指手画脚,最后自然只能带着大汗的轻蔑回到欧洲,于是作者想象吃了闭门羹的西方人该是何等的惆怅。这个故事的出处是《鲁布鲁克东行记》,其中作者还参考了《中国基督徒史》,可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如果李敬泽一直延续着这个模式原原本本地将它叙述下去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规矩的符合历史叙述的史学文本,可是作者偏不,他在其中插入自己在1999年与旧金山学者的会话,之后又回到了鲁布鲁克和蒙古大汗的时代,时间、场景的来回变幻是作者在想象中自由遨游的结果,并且可以注意到作者自己经常跳出来说话,“我”“我们”“你们”等叙述语词的使用让人们对历史产生了怀疑:究竟多少是真实的历史,多少是作者的虚构?
再来看一看《雷利亚、雷利亚》,故事的起始点是一次酒吧之行。“我”在哈瓦那酒吧喝酒,喝酒期间“我”由哈瓦那想到了哥伦布,哥伦布曾经将美洲误认作中国,这是一个关于沟通不得的故事,接着,文章用了大量篇幅来描述一个同样的关于沟通不得的故事——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人皮雷斯在中国的悲苦经历。因为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海峡,明朝皇帝迁怒于他而将他和他的随从全部处死,而皮雷斯在中国期间曾经与一位江苏女子生下了一个叫雷利亚的女儿,而雷利亚正是当晚“我”在酒吧遇见的一个外国女人的名字。李敬泽在另一本16世纪葡萄牙人见闻录中发现“雷利亚”是一位女士,据她介绍,她是皮雷斯的女儿,她的父亲当时没有死,而是被流放到今天的江苏邳县,于是李敬泽向他的一位原籍邳县的友人求证,友人的回答是:“可能。”因此才有了这个关乎历史、现实、真实、荒诞的意识流故事。因为“可能”,文学叙事僭越了历史,僭越了蒙昧不清的事实,一切历史都可以被推敲,打上个人的烙印。且看看文中所用的叙述语词:“这位皇帝被我的一个朋友称为‘摇滚青年’,他热衷于游猎,对服装和女人都有非常前卫的品味。”[4]80“但皮雷斯还活着,这对我们这个故事来说至关重要。”[4]84文中像这样的现代性语词使用得非常多,“我”“你们”“我们”的频繁使用更是表明自己有掌控历史的权利。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作者穿梭于现代和历史之间,将历史与现实的片段相粘连,夺走了史学家手中的历史话语权,从而拼成了一幅带有自我印记的画面,因此可以说作者操持的“叙述话语并不是一个还原真相的工具,叙事话语之中的种种修辞无不烙上作家个人历史判断的印记。相形于历史学家,作家在这方面似乎肆无忌惮”[7]。
四、历史解构之后
通过打捞历史的碎片,挖掘被正史遗漏的历史细节,李敬泽想要建构的是一种个性审美化的历史,从对历史意义和历史言说的解构中,这种个性审美化的历史显现出作者两方面的建构努力。其一是在对历史的缺失处进行修补时,李敬泽想要说明历史是充满着偶然性的,很可能就是因为一次笔误、误译而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恩格斯说:“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8]544“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8]393偶然性在正史中一直是被忽略的存在,在《青鸟故事集》中,李敬泽将这种历史因素高高举起,为的就是突出其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飞鸟的谱系》中鸦片战争迫在眉睫,道光皇帝所批阅的英国人的“最后通牒”却被“改译”成一纸陈情诉状,《八声甘州》中东方大国的皇帝竟把来自西方的知识当做装饰的景观,这种种偶然性堆砌在一起虽然会使人觉得有失真实,但它可能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李敬泽所做的就是将正史中有序的、有意义的、充满必然性的历史进行重新解构,公开宣布历史是无序的,大到一位英雄,小到一缕沉香,都曾无意中参与过历史的进程,无数的这种偶然成就了历史的必然,所以没有绝对必然的历史,也没有绝对唯一的历史观。
其二,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个心灵的谈话,克罗齐说:“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能进而促使人们去研究以往的事实。所以,这个以往的事实不是符合已往的兴趣,而是符合当前的兴趣,假如它与现实生活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话。”[9]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对历史的解构过程中,李敬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构起了一种潜在的联系,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搜索与反思,李敬泽得以对话当代面临的问题。《青鸟故事集》中很多戏剧性故事的发生都是“误译”“误解”造成的,而“误译”“误解”现象后面的本质则是语言的不可靠性,两种地域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语言注定不能完全契合,完全平等地交流,即使通过转译的方式。这一事实李敬泽在爬梳历史文化细节的过程中就已经发现了,他表达了自己的悲剧意识:“人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充满误解和错谬的情境,我们和陌生的人、陌生的物相遇时警觉的目光和缭绕的想象,这一切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现实。”[10]
可见,李敬泽在解构传统历史、建构个性审美化的历史过程中,以一种全新视角审视了历史的别样面目,并传达出了他对当代文化交流困境的思考,使其历史叙事丰富了一般散文叙事的空间,突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规范,是当代历史叙事寻求新突破的一次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