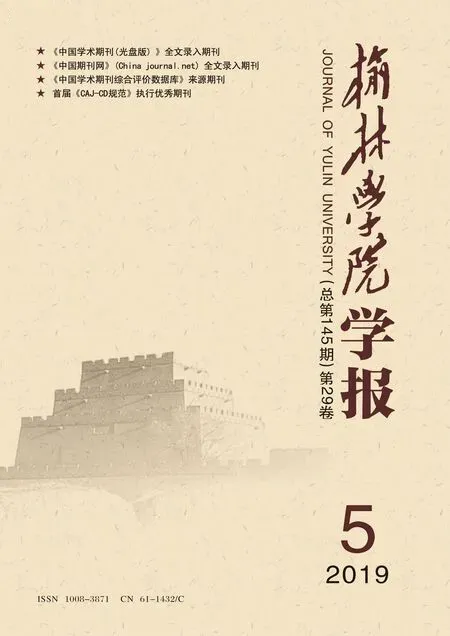“高建群现象”与陕派作家研究现状考察
2019-03-05冯肖华
冯肖华
(延安大学 西安创新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当进入陕西文学研究现状的整体考察后,就会发现一些对研究对象的扎堆、蜂拥以及重复性不平衡现象的存在,这些问题究其因当然是多面的。笔者以为,无论其动因何为,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文学创作及作家作品的研究,研究者的关注点应该更为全面、系统和计划性与整体覆盖性,这样才不至于“热”到极致被推向幻化,“冷”的却被遮蔽使其沉寂,不利于区域文学整体性的推进。陕派作家研究的此种现象当为现实存在。本文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陕派作家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的陕派文学,可谓大起高歌与时代同步,其文学精神的一路引领为学界众家所看好。陕派文学“八大家”之柳青、杜鹏程、王汶实、李若冰、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之创作的高屋建瓴的文学品质,时代领军的世纪史学地位,精神传后的路径导向,也就自然而然的为社会各界所尊定。于是便有了他们文学创作的经典性概述:柳青的“长安十四年”,杜鹏程的“筑路工地”,王汶实的“渭北村舍”,李若冰的“大漠情结”,路遥的“城乡地带”,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陈忠实的“关中叙事”,高建群的“浪漫骑士”等等个性化的文学入场视域的描述。期间,尤为提及的是陕派文学后代的“路遥现象”“贾平凹现象”“陈忠实现象”论域之旨的普遍性论及。要知道,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被提升至“现象”的层面,就意味着一种被解读为经典性、经验性、思潮性的较高文学品质的综合性创作认知,就会被指为文学创作特有的技术性、独创性、引领性的方法论的创新路径的指导性认知。当然,这些作家文学经典化的被概说,拟或文学现象的被界定,都是基于其各自创作实绩、文学成就、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天成,无可厚非。
然而,令人思考的是,在陕派文学后代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四大家”中,“高建群文学现象”的研究相对滞后,较之于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其氛围之热之火,其传播之潮之闹,其成果之丰之博,其文化推介之广之海等的程度要逊色得多。经检索,对高建群文学创作的研究,其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及研究著作的涉及并不是很多。其因何在呢?
我们试图分析一下“路遥现象”“贾平凹现象”“陈忠实现象”三大家的创作研究。从文学现象研究所产生的学缘、地缘来路看,除因茅盾文学奖获奖之天时所形成的全国性研究氛围浓厚追涨的指归外,其作家各自成长经历之学缘、地缘、人缘的因素是很重要的考虑。如路遥研究,路遥是从陕北苦难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且又经延安大学学习培养,成为走向全国的知名作家。路遥的笔下,更是钟情地描写了生他养他的黄土地父老乡亲的悲歌与壮歌,至今仍然激励着陕北一代代青年的前行之路。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路遥或者说路遥研究就有着作家成长经历所给予的学缘、地缘和人缘的得天独厚,也就有了延安大学、榆林学院身先介入,予以深情关照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研究之便。所以,以延安大学、榆林学院为依托,以“路遥纪念馆”(延安大学)、“路遥研究所”(延安大学)、“路遥与知青文学研究中心”(延安大学)、“柳青路遥研究院”(榆林学院)等机构为平台,聚集了陕北众多研究人员,大有成就“路遥学”的学术气派和气概,出版了《路遥评传》(梁向阳)《黄土地的儿子——路遥小说创作论》(贺智利)《路遥研究资料汇编》(马一夫、厚夫)等多项成果。那么贾平凹研究和“贾平凹现象”的缘起,则更多了些综合性因素,即“茅奖”的天机,陕西文化“名片”的影响力,多产作家文学生命持久的感召力,以及学缘、地缘的因素(省城商洛本土文化学系同道们的热情推力),使得“贾平凹现象”的研究逐浪渐起。于是,就构成了以商洛学院为代表的贾平凹本地作家地缘性的研究热情,以西北大学为代表的学缘性的研究,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贾平凹名人效应办学性的研究,以宝鸡文理学院贾平凹文学成就常态性研究等类型。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商洛学院)、陕西文学研究中心(西北大学)、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建筑科大)、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建筑科大)、陕西文学研究所(宝鸡文理学院)等多校多组织研究平台,以及《贾平凹文学艺术料库》(木南)、《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究》(冯肖华)、《<秦腔>大评》《<高兴>大评》(韩鲁华)、《贾平凹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综论》(程华)等成果,都在指向了“贾学”经典化研究的构建。而陈忠实的研究,其地缘、人缘的比重较大,可以说因着作家痴情于文学,钟情于文学的一种深厚的人文情怀的感动和感染。当然《白鹿原》“茅奖”的巨大量级影响是分不开的。陈忠实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就其文化的修养和做人的劲道,是原上的一位先生,乡土村舍群人眼中的一位“圣人”。白鹿原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化,被先生尽揽眼中,诉于笔下,其对传统文化的情怀五味杂陈,将一部书要写成死了后能当枕头用,其对文学的虔诚和较真感染着文化界所有。《白鹿原》的深远影响印证了作家的初衷。人们是怀着对这位乡村先生、较真作家的敬重、敬慕和钦佩进入到陈忠实研究中去。于是,以西安工业大学、思源学院为龙头,以陈忠实与当代文学研究中心(西安工业大学)、陕西作家创作研究基地(西安工业大学)、陈忠实文学馆(思源学院)白鹿书院(思源学院)为基地,投入精力将传统文化与陈氏文学勾联,以兹推动“陈学”的纵深研究,出版了《陈忠实传》(邢小利)、《陈忠实生平与创作》(李清霞)、《生命体验与艺术表达——陈忠实方言写作叙论》(宋颖桃)、《陈忠实散文选译》(马安平)等重要成果。从这些多层次研究组织的先后建构,和多项研究成果的陆续胜出看,都有着高校服务地方文化建设参与的显著特点,高校研究经费倾斜投入的偏顾,以及学院派研究人员情感投入的可贵和可点,所以其研究成果也都具有学院派研究的学理性、公允性、高端性和系列化的特点。对此,“高建群现象”的研究,在此种强大的研究机构和庞大的研究队伍面前可谓微弱了许多。那么,高建群文学创作是否构成了一种“现象”呢?其文学成就和影响是否与学界之关注和研究成为正比呢?也就是说高建群的创作之“质”和“量”的积淀可否上升至“现象”关注的高度与厚度呢?
二、高建群陕派“八大家”地位界定
高建群在陕派作家创作中,作为“八大家”之一当名至实归,作为后“四大家”是名副其实的。二十年前作家路遥就曾对陕西青年作家讲过:“人生的悲与喜,在于你看世界的角度。换一个角度如何?高建群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1]如果我们以平常心态,不依陕西学界的门户师脉所见,那么要谈陕西文学或者陕西文学发展史,高建群文学创作无论如何越不过去的,一道宏大的、且有着鲜明特色的文学大坎、文学大山。虽然他不曾有过“茅奖”桂冠加身,但其文学创作的实绩、成就和影响业已完成了“高建群现象”的文学存在。
那么,“高建群现象”其特征是什么,其在陕西文坛的位置、独特性又在哪里?笔者以为有四大特点,即高建群小说具有独特的英雄主义情结和悲剧大情怀,而非平俗个里的低吟浅唱,如《最后一个匈奴》《遥远的白房子》,那英雄主义悲情令人震撼;具有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的质地厚重,而非对政治策略性的文学解读,如《统万城》,一个剽悍民族的崛起与消亡,一个断代史的挖掘与呈现;具有独特的大西北中国气派风情的浓墨重彩,而非渭河两岸围圈的狭隘游走,如《胡马北风大漠传》《伊犁马》,那西部生命大气象的描摹;具有独特的宗教大文化创新开拓,而非黄土地恋乡一隅视域的徘徊,如《我的菩提树》,对华夏民族历史大文的无限敬慕。这四大独特点的文学抒写,使得高建群文学成为陕派作家中独得、独有、独在靓丽的“高建群现象”风景线。由此,我以为,高建群是陕西文坛一位有着大视域、大境界、大气度、大情怀的作家,以及“高建群现象”的文学存在,即路遥所说的“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的高建群文学现象的不可轻视。
依次思路再做进一步分析,“高建群现象”的这四个特点,从陕西文学总体上看,超越了陕西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也就是常态化创作的黄土地文学的叙事情境。因为众所周知,陕西文学的上代作家因时代的制约,柳青写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互助合作化生活,杜鹏程写战争年代和和平时节建设工地生活,王汶实写陕西渭北新农村面貌,李若冰写大西北地质勘探领域,这些生活的描写都是美丽的共和国时代的主流文学,是时代近距离的反映和观照,当然是陕西文学时代精神主流彰显的骄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到了陕军第二代作家,路遥描写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城乡交叉地带的变革,贾平凹描写新时期传统乡村逝去的忧患,陈忠实描写传统儒学民间权威的乡村伦理等等,这些又从文化与时代,文学与社会的层面予以新的拓展,可以说各有领域各有特点,再次产生了重要的文学影响。
但是综合而论,上述七大家的文学创作中,能将英雄主义、民族文化历史、大西北中国风情、宗教文化柔为一体,并且鲜活的、风情的、集中的彰显出来,仍然缺乏一定的、丰满的多重力度和多彩风貌。所以说,高建群文学现象的四个独特,就尤为鲜明和卓异,具有另一层面的文学高度。一般讲,文学的标高有三种,即阶级文学、民族文学、人类文学。高建群的文学是在民族文学和人类文学的交叉点上建构自己的文学定位和文学品质。这一点应该予以客观地关注和足够的重视。那么这些年由于各种原因,高建群文学现象的研究和关注显然不够,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对其作品文本的广泛研究、追踪研究、推介研究、体系化研究很是弱化。所以,笔者认为高建群文学的研究和推介、“高建群现象”的关注和重视、高建群新作的跟踪解读、应该作为一个文学场域的命题,提高到文学陕军再出发的重要研究日程上来,使这位昔日的“浪漫骑士”,“陕军东征”文坛的黑马回归,成为当下陕派文学中的一面特色旗帜。
三、“高建群现象”:实绩与影响的现实并存
文学实绩是考察一个作家成就的重要标志,它体现了一种在“质”的层面上的“量”的丰厚和多产度。陕派作家高建群自踏入文学之路起,一路留下了层林尽染的文学绿洲,其主要资讯如下:中篇小说约19部,《大顺店》《刺客行》《伊犁马》《狼之独步》《白房子》等;长篇小说约9部,《六六镇》《古道天机》《愁容骑士》《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最后的远行》《大平原》《统万城》《大刈镰》等;散文集约8部,《东方金蔷薇》《匈奴和匈奴之外》《胡马北风大漠传》《西地平线》《穿越绝望》《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等。另有系列报告文学《三千个传奇》《三千具尸体》《大阳从西边升起》和近年的历史文化理论著作《我的菩提树》等。这些煌煌大著之成就,如果从高建群1976年从文起至2018年的当下,期间约42年创作历程,其概率为年均一部。那么这位国家“一级作家”,政府“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跨世纪三五人才”的高建群,其文学创作的本我收获,和给予社会的文学资讯、精神食粮可谓之多,丰盈而别有风情风味,它填补了陕西黄土地文学题材狭窄的空白,开拓了秦地文学创作的疆界,这一不争的事实是“高建群文学现象”的重要特色。
高建群文学的影响,在当今传媒发达的时代可以说随处可见其文化、文学、书法、宗教等活动的信息和身影。这里就不再赘述。那么有几个重要的节点是值得一提的。如20世纪90年代的“陕军东征”现象[2]。以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废都》、陈忠实《白鹿原》三部长篇为代表,学界冠于“陕军东征三驾马车”,后又连缀了京夫《八里情仇》、程海《热爱生命》两部长篇,再称“陕军东征五虎上将”。[3]于是中国文坛哗然,作为其中重要一“虎”的高建群也身名大震。此时他年仅40 出头,一个成熟稳健且又生命经历独厚的最佳文学年轮。陕军东征现象使高建群创作一路高歌,好作不断,文学声誉节节攀升,于是“老舍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庄重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大平原》)、新闻出版广电总署“优秀图书奖”(《统万城》),以及加拿大“大雅风文学奖”(《统万城》),等等各层次各类文学奖项尽收。与此同时,高建群文学的文化推广也日见增多,如陕西电视台组织的作家高建群“一带一路”万里行并出访吉尔吉斯斯坦之文化活动;陕西电台主办的“高建群大话统万城”视频直播,总点击量30余万观众。同时,高建群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应邀为数不多的大陆作家之一。如此等等,这些因作家自身文学创作实绩而胜出的文学声誉的提升,社会文学造世的跟进,以及各类文化活动的彰显,可以说“高建群文学现象”的确作为中国大文学圈,拟或陕西文学圈,值得足够重视和给予有力度的研究,使得高建群文学上升至一个“现象”的经典性、经验性、思潮性的应有高度。更应该以高建群文学本有的“崇高感”“古典精神”“悲剧情怀”“理想主义”正能量元素,来照亮当下文学的理想疲软、精神匮乏、庄严弱化、思想空泛等等文学弊端,以便体现高建群文学的真正本质意义。
当然,高建群的小说文本并非是十分的完美无缺,如果从小说操作规律之技法而论,仍然有不是很精道的地方。如小说构架的松散,其故事的叙事紧凑不足,似有小说散文化的现象。这反映出高建群在小说的结构铺排上的自然平扑的叙事心态,并不去刻意追求故事的起落悬疑。那么作者的这种章法遇到或者以做小说的规律来衡量也就反映出其明显的缺陷来。另外,小说叙述语言上的直扑,也常常夹杂着对历史、对文化、对道德等的政论式的评判,偏离了小说应有的艺术性描写类的精道的语言,等等。那么,高建群的小说既然为之小说,而这些小说文体操作中的缺憾,势必造成了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的混搭。对于读者而言,小说乎,散文乎?其阅读影响势必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