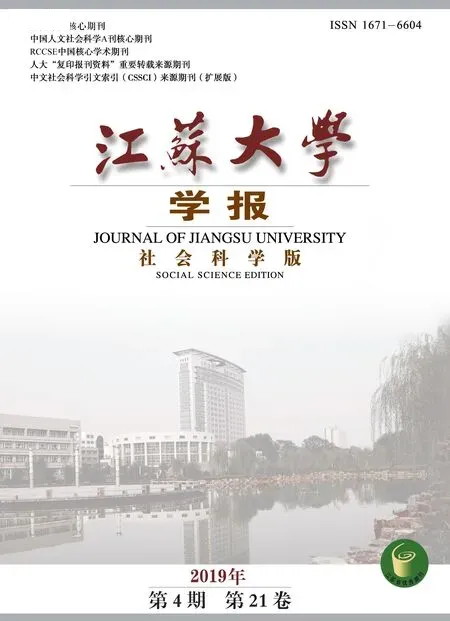赛珍珠的上海叙事研究
2019-03-05朱骅
朱 骅
(上海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1306)
很多学者倾向于将上海作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切入点或“钥匙”[1]1,尽管这个观点有一定的争议性,但美国华裔史家卢汉超先生指出:“中国劳工运动史、中国资产阶级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果不研究上海,那是令人难以想象的”[2]14。上海学或上海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只是从西方的文学叙事切入的上海研究目前不多。实际上,在西方非汉语的上海叙事至少有3类: (1) 西方来华者的上海叙事,其中不乏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例如米勒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G. E. Miller,Shanghai:TheParadiseofAdventurers, 1937)、巴拉德的《太阳帝国》(James Ballard,EmpireoftheSun, 1984)、克里斯托弗·纽的《上海》(Christopher New,Shanghai, 1985)等;(2) 从中国赴欧美的华人的上海叙事,如裘小龙的侦探小说“上海三部曲”(Qiu Xiaolong,DeathofaRedHeroine, 2000;ALoyalCharacterDancer, 2002;WhenRedisBlack, 2004)等;(3) 还有就是美国土生华裔的上海叙事,如邝丽莎的《上海女孩》(Lisa See,ShanghaiGirls, 2009)、谭恩美的《惊奇谷》(Amy Tan,TheValleyofAmazement, 2013)等。考虑到20世纪中叶之前英美两国的在华影响力,英语文本无论从数量还是研究价值来说,都独占鳌头。为了避免结论过于宽泛,本研究将以自认为是中国女儿的美国作家赛珍珠的上海叙事作为个案,了解上海文化根深蒂固的矛盾性。
对于赛珍珠和上海的关系,已有赛珍珠研究界的资深学者做过一些研究,例如周锡山的《上海与赛珍珠,赛珍珠与上海》[3]、裴伟的《寻找赛珍珠的朱厄尔学校》等[4],前辈们侧重于个人史的史实梳理,对赛珍珠和上海的关系做了筚路蓝缕的基础性工作。但从具体文本切入,研究赛珍珠对上海现代性和中国本土性关系的思考,国内外学界比较匮乏。实际上,赛珍珠生活在距离上海不远不近的南京,恰到好处地既有局外人的冷静客观,又能近距离观察上海.
一、 赛珍珠的上海渊源
赛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年)的中国故乡是江苏镇江,父母都是美国南方长老会的传教士。她在华的主要职业生涯是在美国教会开办的金陵大学(Nanking University)讲授英国文学,并辅助丈夫做中国农业经济调查,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熟悉上海。实际上,她同上海有着深刻的渊源。从她为母亲写的传记《异邦客》(TheExile, 1936),为父亲写的传记《战斗的天使》(FightingAngel:PortraitofaSoul, 1936)以及别人为她所写的8部传记来看,上海是她父母来华的入关口岸,是适应中国语言文化的过渡带。上海也是她和家人每一次避难的落脚地或中转站,短则数月,长则经年。她有3个兄姐在上海夭折并葬在上海的外国人公墓中。上海也是她赴美读大学前唯一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地方,朱厄尔女校就在今天虹口区的昆山路上[4]。与她交往密切的知识分子如林语堂、徐志摩等人都生活在上海,她的作品的译者、研究者与出版者也主要在上海。
在赛珍珠的各类中国书写中,几乎找不出哪一本书不提及上海。有的是直接以上海为背景展开叙事,如《中国逃亡》《分家》(AHouseDivided, 1935)、《爱国者》(ThePatriot, 1939)、《梁夫人的三个女儿》(TheThreeDaughtersofMadameLiang, 1969)等;有的只是作为一种威胁传统农业价值体系的他者的存在被隐约提及,如代表作《大地》(TheGoodEarth, 1931)的结尾大儿子偷偷卖地准备搬去上海;续集《儿子们》(Sons, 1932)中王虎的二太太为寻求独立而出走上海;《母亲》(TheMother, 1934)中一开头丈夫离家去上海追寻梦想生活等。虽然在赛珍珠有关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叙事中,上海往往只是厚重的传统社会中闪电般的一条裂隙,但却是改变叙事进程的那一个转折点,让读者无法对整个中国形成田园牧歌般的幻觉。
虽然赛珍珠最为普通读者所熟知的是《大地》,但农村题材只占她的中国书写中较少的部分,以农民为主角的只有《大地》《母亲》和《龙子》(DragonSeed, 1942)这三部。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她明白中国农民被卷入现代性滚滚洪流已在所难免,如果还在那里美谈中国农民的安土重迁,则不符合时代发展。她清楚中国腹地的农民对现代性的突袭毫无准备,几千年来农民以家庭为经济单位形成既无组织又无远见的一盘散沙状态。当农民们被纳入现代性进程时,需要英明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引导,方能避免社会动荡。这一时期她和晏阳初等推动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运动的知识分子密切接触,在创作中不断提及中国知识分子领导普罗大众现代性转化的必要性。
从这一时期她给林语堂的《吾国吾民》(MyCountryandMyPeople, 1935)所作序言可以看出,她已将带领中国变革的重任放在年轻一代肩上:“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民……他们开始为自己国家有这样一个宏伟而坚实的基础感到高兴,并急切地把它变为新的鼓舞人心的力量”[5]。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接受了西式教育,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历,他们有可能带领中国平稳走向现代化。她清楚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关系也同样在撕裂中国知识分子,要了解知识分子是否胜任领导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东西汇流的上海也许是最佳采样点。
近代上海聚集了中国数量最多,类型最广,背景最复杂,思想最尖锐的知识分子。在赛珍珠的上海书写中,反映知识分子问题最典型的要数《分家》《爱国者》和《梁夫人的三个女儿》,分别代表了抗战前、抗战和社会主义这三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故事的主角都有海外教育背景,差不多都经历了这个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历史风潮。尽管各人的生活道路不同,却贯穿着独特的上海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性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赛珍珠这样的“中国通”才能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探究。
二、 《分家》:上海的现代性启蒙
《分家》是《大地》三部曲的第三部,是《大地》男主角王龙的孙辈们的上海生活再现,主角王源是王龙的三儿子王虎的独生子,是奋力走出困顿迷惘为未来寻路的少年中国的代表。故事承接《大地》三部曲的第二部《儿子们》讲述。王虎作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希望儿子王源将来子承父业,于是雇佣德国教官教儿子外语,进行军事训练,并在王源未成年时就打发他南下广州参加新军,然而王源却在北伐时不堪战争的血腥,当逃兵溜回皖北,父子发生剧烈冲突。王源到上海投奔王虎的姨太太。这位姨太太受过良好教育,当年被王虎强娶为妾,因未生儿子而受歧视,遂负气出走。这位姨太太利用其家族医术,在上海过上不错的生活。她安排王源进了大学,王源在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及大伯家的堂兄弟们帮助下,逐渐融入上海生活。他并不喜欢缺乏内容的消费主义,更喜欢读书,特别喜欢在大学的试验田里伺弄庄稼果蔬。在堂兄王猛的影响下,他加入了地下共产主义小组,却没想到国共合作失败,蒋介石政府对共产党员实行清洗。王源被捕,王家通过财力斡旋才将他救出,并秘密送往美国康奈尔大学(赛珍珠夫妇的母校)。在经历文化冲突和跨种族爱情幻灭等一系列问题之后,他认识到农业现代化对人口众多、工业化发展缓慢的中国的重要性,于是发愤图强,拿到农学博士学位。本想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但回国后却不得不经历一系列幻灭的痛苦,最后在上海姑娘梅琳帮助下,完成思想的再本土化。
《分家》是一部典型的上海语境中的成长小说。从安徽来到上海的王源,尽管已经到广州参加过新军,但17岁仍然是一个懵懂的年纪。王源所了解的仅仅是皖北和广州的部队生活,对大千世界一无所知。对他来说,上海是神奇的,是贫富二分的,是霓虹灯下的浮华和霓虹灯外贫困的古怪组合。他和其他富家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愿意看到并努力改变整个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
很多作家和学者为了突出上海的现代性活力,总是将上海与伦敦、巴黎和纽约对比,大书特书上海的西方现代性[6]1。但赛珍珠的兴趣不在此。她的长期中国乡村与城市生活双重经历,使她比项美丽(Emily Hahn, 1905—1997)等住在上海租界中的美国作家多了一个看上海的视角,也就看得更深刻。她在承认上海如梦般浮华的同时,更看到浮华之下的可持续性问题。上海毕竟是中国版图上的上海,不可能如海市蜃楼般逐浪于汹涌而来的西方现代性之上却不受来自任何一方的侵扰。上海的另类现代性与本土性的关系是她关注的焦点。从这层意义上说,赛珍珠是相当有远见的,比起史学家柯文(Paul Cohen, 1934—)倡导“中国中心论”之后[7]3,国际上产生的一系列上海研究来说,早了半个世纪[8]。
她通过王源的视角,不断对比和揭示潜隐在现代繁华之下的中国传统,以及上海现代性对整体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依赖。例如,王虎给王源在皖北包办了一门婚事,命令王源必须在二十日内赴皖完婚。尽管生活在上海,但王源仍无计可施,因为他的经济来源捏在王虎手上。这也是一个隐喻,上海的经济基础并非完全来自于西方的投资或刚刚起步的工业化,而更多地源于从中国各地汇聚到上海的农业收益。由于租界的治外法权特殊性,中国各地富豪为了逃避战乱,不断迁居上海。王家老大一家十几口人因为军阀混战都迁来上海,有房有车有舞会,但没有人出去工作,完全依靠王龙去世留下的大量农田的地租与放债收益。正因为上海的工商资本根基尚浅,所纳之百川主要源自腹地的农业收益,从而不得不对政治高度依赖,对政权变化委曲求全。
上海的启蒙现代性教给王源反抗家长制权威以获得个体的生存意义,并以更广阔的社会激情表达出来。他和当时诸多热血青年一样,投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热潮,加入了上海物质繁华之外的另一个精神热点。赛珍珠理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看作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她特别注意到共产主义思想对民族主义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却走向了农村。诞生于都市的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理论阐述,团结急于变革的热血青年与爱国志士,激发国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普及了民族国家的概念。
王源和堂兄王猛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工人阶级中宣传与发动民族自决自强意识。但在培养民族意识之外,都市中的共产主义宣传并没有充分动员起尚在形成中的缺乏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因此当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清洗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时候,年轻而又缺乏城市市民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不堪重击,不得不放弃消费主义崛起中的城市,转向以静态的土地为核心生产资料的农村。在赛珍珠看来,中国共产党正是转入农村,同最广大的农民相结合,才最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但这个转向却又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中产生的论述不吻合。为了理解这一困惑,赛珍珠倾向于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是知识精英引导的民族主义启蒙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昙花一现,实际上也暗示上海现代性在中国前现代海洋中的孤岛特性。上海照搬西方的现代性必然与更广袤的内地本土性发生冲突,并在支撑西洋现代性的租界体系终止后,被重新本土化。
上海启蒙了王源的心智,启蒙了年轻一代的个体意识,启蒙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意识,也同样启蒙了年轻知识分子对中国本土性一次比一次更深入的再认知。上海是王源赴美前的最后一站,也是他回国后的第一站。他意气风发地回国,才发现现代上海根本无法摆脱传统的围剿。海归的王源已近而立之年,年老的父母,家庭的债务,光宗耀祖的期望,一下子将他紧紧束缚。更大的压力是他无法适应这些年被自己虚妄的爱国激情选择性遗忘的各种传统伦理和价值观。他求职到处碰壁,才发现在美国学习农科,而非政治或商科,让他成为中国现代都市的零余者、中国农村的不速客和家族的不肖子。
最终拯救在现代意识与传统现实中困顿不堪的王源的,是上海女子梅琳,这是一个隐喻明显的安排。她是王源的姨娘收养的一个孤儿。她跟养母学了一手好中医,又在教会医学院学习西医,立志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工作。她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游刃有余,永远把握住二者的结合点。作为曾经的弃婴,她从无到有,中西结合,荣辱不惊,永远知道进退分寸,恰如其分地站好自己的位置,这不正是上海的特质吗?她接纳了王源,帮助一个美国化的知识分子重新在中国找回位置,投入当时已经如火如荼开展的乡建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等以现代性全面改造中国基础的社会实践。
三、 《爱国者》:上海现代性的本土辐射
《爱国者》是赛珍珠六部抗战小说中的第一部[注]赛珍珠最著名的长篇抗战小说主要有《爱国者》《龙子》(Dragon Seed, 1941)、《中国黄金》(China Gold, 1942)、《中国天空》(China Sky, 1942)、《诺言》(The Promise, 1943)、《中国逃亡》(China Flight, 1945)等,其中《中国逃亡》主要关于日据时期的上海美侨生活。此外,她还发表了数量颇多的反映游击抗战的短篇小说。,出版于1939年,此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但赛珍珠已经开始投身于中国的抗战事业,成立“紧急援华委员会”(China Emergency Relief Committee),担任“中国救助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主席[9]243,四处为华募捐。《爱国者》主角吴逸万(Wu Yi-wan)是一个上海银行家的儿子,其祖父来自湖南,晚清时曾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其父也遍历欧美,抱着实业救国的目的开办银行。吴逸万在万般呵护中长大,按理说是最不会成为革命者的人,但一次阴差阳错的入狱,结识了来自陕北农村的大学生刘恩澜(Liu En-lan),并在后者的影响下成为革命者,负责组织和发动闸北缫丝厂的工人罢工,训练工人纠察队,最终被叛徒出卖,成为被清洗的对象。他在家人安排下出逃日本,娶了日本妻子,有了稳定的家庭。然而在日本侵华后,面对山河破碎,他毅然抛妻别子,回国参战。当年侥幸逃过清洗的刘恩澜参加了红军长征,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小说结束,作为国共二次合作国民党方面代表的吴逸万和共产党方面代表的刘恩澜在陕北意外相遇,共同推动抗日统一战线。
吴逸万在法租界出生长大,父母都受过极好的教育,家中流通多国语言,一般革命者渴望通过革命牺牲为民争取的东西,对吴逸万来说是一出生就拥有的。他是彻底现代化的上海人,没有人给他包办婚姻,哪怕他娶日本人,哥哥娶德国人,吴家也欣然接受,体现了海纳百川的上海气度。与之相比,《分家》中来自内地军阀家庭的王源作为第一代移民,在婚姻等各方面都是不自由的,他无法与中原大地断根,身上有无法在现代性浪潮中洗去的前现代农业社会的烙印。但真正令读者困惑之处在于,一个已完成现代性内化,而且现代得如此彻底的年轻人吴逸万,为何如此热烈地拥抱革命?同样,为何灯红酒绿繁华富贵乡的上海会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大的火药桶?这是一个很多学者已关注的问题[注]主要参考文献有韦慕廷(1907—1997)的《1918—1927年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苏联在华顾问的文献》(C. 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1956)、史华慈(1916—1999)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1958)等。。本文尽量避开文献铺陈,而仅以小说文本展开探讨。从表面上看,吴逸万加入革命组织是由于来自陕北的刘恩澜的桥梁作用,但这么一个看起来粗陋的农家子弟为何对吴逸万来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这是了解上海现代性另一面的关键。
贫困的刘恩澜半工半读,但意志顽强,一腔热血,渴望祖国独立富强。这股热血向革命的转化源于他的一次被捕,而被捕的原因在于他参加了上海一家英文报刊的征文。在他用英语所写的这篇激情洋溢的文章中,他从上海声光电的繁华渐渐写到上海之外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展望上海的现代化能成为榜样,辐射到中国各地,带动整个中国的文明与进步[10]46。由于大量状写中国的落后,他被当局认为破坏了中国积极进步的国家形象。数月的狱中生活,尤其是和不断进来继而被处决的各种狱友的交谈,他意识到仅仅靠读书找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不足以改变中国的未来。他在吴逸万帮助下出狱后,开始热烈地拥护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背景下加入共产党,并在高校中组织学生积极分子,深入工人居住区,发动并组织工人革命。刘恩澜是一个对中国的乡村、工厂、学校有深入了解,对普通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有深刻洞察力的新一代知识青年。他是真正的根正苗红,又红又专,对中国农村一往情深的赛珍珠将他定位为中国的未来。
与之相对,吴逸万生活在一个干净、体面而富裕的真空中,他的人生很单纯。突发的短暂入狱让他了解到一个他从不知道的身边世界,另一个上海,另一个中国。这样的一种相遇如同爆炸,动摇了他所有想当然的世界观。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只是极少数人的生活,上海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只有一个,是受洋人操控集聚了太多国际资本的繁华,是盘剥了工人阶级,或者说吸了全中国的血造就的繁华。他与刘恩澜的相遇让他开始了从西方现代性向民族性的转化,他要为上海找到一个根,一个可以托付未来的“本土”。
他转变得如此义无反顾,又如此小心翼翼。他过着双重生活:每天早上出门上学,然后去闸北棚户区启蒙工人,深夜悄悄回到法租界的高宅大院中。他为工人们麻木绝望又怀疑一切的人生态度而焦虑。响应他的号召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年龄相仿的男工。吴逸万也在思考,大家追求平等自由,反剥削,反资本家,反银行家,可等到富人都被打倒了,财富被瓜分了,穷人们一窝蜂搬到吴逸万家这样的豪宅中,那又怎样?很多穷人以为革命就可以分到富人的钱,从此不用工作了,但总要有人制造生活所需吧?没有了工商业的运作,有了银圆又有何用?革命者们都说上海是罪恶之城,可是吴逸万并不清楚究竟要将上海变成什么样的城市才是正确的。
从吴逸万的困惑中,读者看到近现代上海的困惑: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的示范区与领导者,还是罪恶的渊薮?现代化的物质丰盈常常与消费主义伴行,而消费主义必然与农业社会伦理价值基础断裂。上海是否要像热血的民族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斩断外国资本,让上海重返本土?西方式的物质现代化是否就是罪恶?革命不只是让受压迫者夺取政权那么简单,刀光剑影的革命只是冰山一角,启蒙受压迫者将他们培养成未来新政权胜任的建设者,保证现代化在革命后的延续更为重要。有理论认知和现代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的重任在于,将现代性的生产力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在劳动群众中做扎实,从而抵御和化解革命进程中任何一次暂时性的挫折。赛珍珠通过揭示吴逸万的困惑,与读者一起探讨中国的前途,以及上海在未来中国进程中的作用。
然而吴逸万并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群众工作带来的成果。五卅惨案发生了,他成了被通缉的对象,出逃日本十年,直到淞沪抗战后才返沪。他们当初对革命在于发动和启蒙最广大的压迫者的共识,则由恩澜带去了中国的内地乡村,并沿着万里长征一路西行。换个角度看,长征不只是一次政治革命的策略性流亡,更是现代思想向中国腹地的垦荒与播种。
吴逸万回国后成为蒋介石的特使,到陕北推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当恩澜和逸万这两个上海教育出来而背景相异的年轻人站在山顶,面对中原大地展望未来时,上海现代性已获得隐喻性诠释:革命也是上海多元现代性的重要一维。上海的开放、包容、弹性促成了国共两党同仇敌忾以及与世界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这是赛珍珠所展望的上海文化精神的中国性,上海之火可以燎原。
四、 《梁夫人的三个女儿》:上海现代性的再本土化
《梁夫人的三个女儿》讲述的是后革命时代上海传奇女性秀兰和她的三个女儿的故事。梁夫人年轻时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在那里恋爱成家。回国后夫妇二人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因梁夫人没有生儿子,丈夫在外纳妾生子,导致二人分居,梁夫人带着女儿搬到上海,转向实业,开了一家高档餐馆。因为她机敏过人,加之她具有较好的统战作用,因此在公私合营后,依然在上海市中心继续经营她的高档餐饮。她在上海抗战结束后将三个女儿全部送往美国接受教育。大女儿在哈佛大学获得药学博士学位,接受党的号召回国从事中药萃取研究;二女儿研究西洋音乐,嫁给从事核物理研究的二代华裔,二人取道欧洲回国报效祖国;三女儿学习绘画,想回国参与建设,但又担心所学并非国家所需,回国计划没有成行。最终大女儿较为成功地完成本土化,成为中药学专家,业余欣赏毛泽东诗词,践行了梁夫人对她的忠告:“只有取得成功,你才会万无一失”(Succeed, you’re safe)[11]40;二女儿在丈夫因意外事故去世后,取道香港返美,报国梦碎。
梁夫人的故事有很强的上海传奇女性董竹君的影子。董竹君出生于上海,因家贫被卖入妓院,后与同盟会成员夏之时私奔出逃日本,在东京完成高等教育。最终与丈夫理念分歧,离婚后开设了享誉上海滩的高档餐馆“上海锦江川菜馆”。她的女儿们也接受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搬去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12]440-442。对于董竹君在新中国的生活,赛珍珠可能略知一二。赛珍珠需要以这么一位传奇女性的经历为切入点,反思上海现代性在新中国的变化。
《梁夫人的三个女儿》中的上海已经不再纷乱嘈杂,曾经喧嚣的街道平静下来,秩序井然。以外滩为中轴的曾经的租界区域,如今安静、干净、庄严,市井的贫穷、脏乱和烟火气退到了深居简出的上层名流梁夫人看不到的下只角[11]43-44。赛珍珠通过书写梁夫人的一次午后出行,通过梁夫人的眼睛向读者呈现了上海在新中国发生的宏观变化,为小说的场景定调。在此基础上,以代表上海风华的现代女性梁夫人当下的困窘,探讨西方现代性在新中国的境况、出路和生存空间。小说的情节发展一直在京沪两地之间穿梭,从物理空间来看,这部小说以京沪关系隐喻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定位问题。
梁夫人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去北京,这是她和董竹君最大的不一样。她尽可能适应新环境的变化,将自己边缘化到不显眼的静水区。她竭尽全力守住餐馆,实际上就是象征性地守住上海现代工商业的市场属性。残留的餐馆就是残留的老上海,是上海民营资本的缩影与象征。但无论是餐馆还是经营者本人都没有独善其身的能力。她的餐馆能够存在,只为了便于向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友人展示中国精妙的餐饮文化,却又避免官方接待过于正式的情况。梁夫人所做的附属于政府的宏观规划,就像1949年之后中央对上海的定位一样:服务全国。从这一层说,上海现代性中物质的那一面还在,以物资生产的方式引领和服务全国,以计划商品的形式渗入到全国人民的生活中。
梁夫人的餐馆服务性质当然也没有变,因为其私有性质,可以选择性地只服务来沪的有限群体或国外使团。这和餐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精英服务定位没多大差别,但值得注意的是,私人餐馆的自由竞争业态不复存在,梁夫人的餐馆是介乎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形式,保留有限的经营自由,是为新中国依然存在的小众需求提供国营体制难以提供的补偿服务。这是上海在公私合营后残剩的零星私营经济的缩影。梁夫人表面的经营自由其实是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上海现代性中曾经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维度已不复存在,计划经济下物质现代性的过度发展固化了上海市民过度关注物质得失的市民气。曾经引领风气之先的上海精神逐步符号化为卓越灵巧的技工和工程师,而不是电影公司和革命者。
值得注意的是,梁夫人一直认为上海只是一个经济活跃的城市,至少在心理上是这样。上海的国际性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发生严重转向,但当年留下的建筑物和市政设施等仍然可以形构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心理场域,努力抵制文化与精神的平面化。在女儿们陆续回国前,她获得了这份安全,在关起来的花园洋房之中,她仍然延续老上海的生活。然而女儿们回来后,一切都变了,她被亲情的纽带强拉进京沪的“政-商”关系中。
海归的女儿们都被要求去了北京,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知识生产领域主要集中到了北京。1949年之前的上海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辐射功能,现代工业生产和全球化的文化机构繁花似锦,但1949年之后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上海的定位是经济辐射功能,是一个服务全国的巨型工厂,成千上万的工人日夜加班,以完成计划经济的生产任务。作为高端人才的梁家女儿们只能到北京去做民族药学研究和发展民族艺术。赛珍珠没有对此做直接评价,但从梁夫人的视角委婉指出,作为西方舶来思想的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成功,是因为出走内地过程中成功地本土化,中西汇流的上海只适合各种新思想的发端,但任何思想要茁壮成长就必须移植到中国的本土中,北京无疑是更适合的地方。
在《爱国者》中,上海的多维现代性中“革命”的那一维被带到了陕北,推动了时代的进步;在《梁夫人的三个女儿》中,上海现代性的先锋文化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形变为计划商品的卓越品质,尽心尽力地服务全国,但计划生产带来的城市封闭性却不断催生视野不出弄堂口的琐细市民气。梁夫人虽然觉得秩序井然的黄浦滩缺乏活力,但看到肇嘉浜、蕃瓜弄和苏州河沿岸棚户区的改造,也感叹说至少普通百姓获得了半个世纪以来渴望的和平与稳定。上海的绰约风华消失了,但物质现代性留下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素质精良的现代工人阶级,从而可以平实辛勤地服务全国,让全国人以拥有“上海制造”的商品为荣;北京,辉煌的传统中国的象征,在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过程中重归荣耀。
农村包围城市在特定历史时期,因为符合国情与民意而取得胜利,但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实行计划经济,没有充分考虑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从而不能有效激发经济活力,造成之后数十年经济发展缓慢。我们党对现代性发展规律的认识调整花了三十多年,新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梁夫人二女婿在狱中预言的经济松绑、生产方式多元和知识分子价值回归,直到赛珍珠去世近十年才逐渐实现,而在国家策略调整过程中,梁夫人一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五、 结 论
赛珍珠是西方作家中为数不多的书写中国人的世界又如此高产的作家。父母数十年在江苏向中国平民传教的工作,让她了解到长三角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思想;婚后随夫赴皖北做中国农业经济调查,又让她获得对皖北平原农民深刻广泛的第一手知识;之后她长期在南京的金陵大学执教,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小世界,这种覆盖城乡连接中美的差异巨大的中国经历,加上贯通中西的良好教育,使她的作品所反映的中国世界往往有一种史诗般的全景和纵深,对任何历史现象都能比平常人多几个不同的视角解读。
赛珍珠丰富的跨文化跨阶层人生历练,使她既不同于中国知识分子中辜鸿铭这样的国粹派,也不同于江亢虎这样的西洋派;即使相比于她同时代在华的中美跨国作家,也大不一样,例如书写十里洋场的叛逆女子项美丽,在深宅大院中做人类学田野观察的诺拉·沃恩,对逝去的农业中国惆怅怀旧的路易斯·米尔恩,即便和同样是传教士家庭出身的亨利·卢斯、司徒雷登、约翰·何塞等相比,她思考中国的方式也不一样。赛珍珠致力于为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寻找一条理想路径,而她所选的这条路径的地理起点,不是南京而是上海。
她和其他关心中国前途的知识分子一样,有一个百年之问:上海是“另一个中国”吗[13]?或者是“中国本土上的一座外国城市”[14]2?上海是一个在海内外被神化的城市,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不同的上海。李欧梵眼中的上海是摩登的[6]1,卢汉超眼中的上海是小市民气的,古德曼(Bryna Goodman)眼中的上海是乡土的[15]1-8,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眼中的上海是淫靡的[16]6-7,石黑一雄英雄眼中的上海是危机四伏的[17],横光利一眼中的上海是腐朽的[18]30-31,但在赛珍珠的眼中,上海是中国的希望。
赛珍珠对上海现代性的思考跨越了半个世纪。她在20世纪30年代初以海归青年知识分子王源在上海的求学、革命以及学成回国后在上海成功完成本土化过程,暗示上海是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性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赛珍珠在日本侵华之际,在美国领导多个抗日救亡团体,不仅四处演讲筹措抗日经费,还书写《龙种》等小说,向西方公众介绍中国的抗日游击战。在中国遭遇民族危亡之际,赛珍珠开始思考孤岛化的上海在中国、亚洲甚至更宏大的世界格局中的意义。她以《爱国者》中的上海学生刘恩澜为代表,展示上海现代性中的革命维度,如何经过内地的万里长征,远远辐射到陕甘宁边区,并引导中国死而后生,使得全国乃至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受益于上海的革命精神。到了“文革”,已年届八旬的赛珍珠再次以上海为切入点,思考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她看到上海的物质现代性在新中国建设中的意义,并且非常有远见地预测到中美建交,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和公共生活中的地位提升。
当我们今天认同杜维明先生提出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检视上海的价值或者价值取向,必须在方法论上超越排斥性的二分法”之时[19],我们不得不承认赛珍珠通过文学所展示的她对上海现代性与本土性关系的认知相当具有远见。上海是中国的上海,其现代性之根是在中国,上海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最成功的典范。西方的思想和生产技术进入上海,由上海对其进行本土化。上海的摩登、革命、工商业繁荣是中西交融的样板,服务全国,而同时源源不断获得中国腹地人才和物质的支持,形成不断更新的良性循环。